- +1
明智光秀后人:豐臣秀吉是本能寺之變種種“定論”的始作俑者
勝利者散布的偽造事實
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六月二日的早晨,京都本能寺被明智光秀的軍隊包圍了。經過短暫的戰斗后,本能寺陷入了一片火海,在那火焰中,未能實現統一全國之夢的織田信長結束了他四十九歲的人生。緊接著光秀軍攻擊了信長嫡子織田信忠所據守的二條御所,信忠最終也自殺身亡,至此光秀取得了“本能寺之變”的勝利。
可是,僅僅十一日后的六月十三日,光秀在山崎合戰中敗給羽柴秀吉,在朝著居城近江(今滋賀縣)坂本城逃亡的途中丟掉了性命——這就是本能寺之變及其后的山崎合戰的梗概。
以上內容是確定的事實。而作為所謂的歷史常識,每個人都知道不少有關此事的各種傳聞。
比如,信長屢屢苛待光秀,光秀因此產生怨恨而謀反,在吟詠的“如今正是好時機,土岐五月統天下”中宣告了奪取天下的決心;光秀獨自策劃了謀反,臨事發前向重臣們表明心跡,發出“敵在本能寺”的號令后率軍前往本能寺;羽柴秀吉在備中高松城之戰中得知信長被殺,他號啕痛哭,為報君恩,決意復仇;等等。
但是,這一切都是創作的故事。它們只不過是在被稱為軍記物的故事中被創作出來的情節罷了,而這些故事創作于本能寺之變后數十年的江戶時代。
那么,為什么在本能寺之變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創作出來的軍記物里全都寫著相似的內容呢?難道真的是因為它們更接近真相么?
其實它們都是“被當作真相而散布”的故事而已。某個人在本能寺之變發生的四個月后,對外正式宣稱:本能寺之變因明智光秀對信長的怨恨以及他奪取天下的野心而起,且為光秀的單獨犯罪。在不像現今這樣擁有自由媒體的時代,若有人用強權散布“這就是真相”的話,那就會成為“事實”。
而軍記物又在此基礎上各種添油加醋、夸大其詞。
比如“光秀因為被取消了在安土城中招待德川家康的宴席負責人的資格而怨恨信長”;“光秀遭信長留難而被打,所以怨恨信長”;“接到剝奪自己重要領地的命令從而怨恨信長”;“光秀的母親因信長的責任遭到殺害,故而產生怨恨”——該說法就這樣不斷豐滿起來了。
時至今日,還有人從各種方面推測光秀被信長討厭的原因或是光秀怨恨信長的原因,繼續添油加醋。在這之中,居然出現了光秀由于近視眼而眼神兇惡,所以被信長討厭云云等新說法。這樣一來,事情就成了只要饒有趣味,便怎么解釋都行了。

秀吉的政治宣傳書《惟任退治記》
那么,首先將這些說法當作“事實”傳播的人究竟是誰呢?
他就是羽柴秀吉,也就是之后的豐臣秀吉。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這件事情幾乎無人知曉。
如今正是好時機,土岐五月統天下。
這句連歌作為光秀表明謀反心跡的證據廣為人知。它是本能寺之變三天前,在光秀居城丹波龜山附近的愛宕山舉行的名為“愛宕百韻”的連歌會的發句,也就是連歌的首句。那么,為什么這句連歌能如此廣為人知呢?現在,若有重大事件發生,各家新聞媒體會同時對相關的事情進行調查,相關信息一下子就傳播開了。而在當時是沒有這類媒體的,照理說事件的相關消息不可能廣泛傳播。可是唯獨“光秀所作之句”,連同光秀在其中的寓意都一并廣為人知。促成此事的就是《惟任退治記》一書。
《惟任退治記》是在本能寺之變僅四個月后的天正十年(一五八二)十月,羽柴秀吉命其雇用的御伽眾大村由己所寫的二十頁左右的短篇著作,書中簡明扼要地記述了本能寺之變的始末,即所謂的事件報告書。御伽眾乃是陪伴主君談話的近侍,而大村由己則因其文采獲得器重,擔任類似現代宣傳部官員的角色。“惟任”是朝廷賜給光秀的姓氏,如書名所示,這正是一部講述在山崎合戰中秀吉消滅光秀的宣傳書。此書是在事件發生后,最早問世的交代本能寺之變始末的著作,也是秀吉針對本能寺之變發布的官方公告。
通過這本書,秀吉將“本能寺之變是光秀單獨犯案,其謀反動機出自私怨,以及光秀早已懷有奪取天下的野心”變成了本能寺之變的官方定調。
為了證明光秀心懷奪取天下的野心,秀吉所出示的證據便是“光秀所詠的發句”。《惟任退治記》里是如此記載的:
光秀發句云。
ときは今あめかしたしる五月かな
今思惟之,則誠謀反之先兆也。何人兼悟之哉。
(光秀在發句里說道:“如今正是好時機,土岐五月統天下。”現在回想起來,這根本就是謀反的先兆,可當時又有誰明白呢?)
光秀的句子按字面來解釋的話,意為“梅雨淅瀝下不停,便知時逢五月天”,也就是吟詠梅雨情景之句。可是秀吉在《惟任退治記》里,沒有把此句按照字面意思來解釋,而是把“時”作“土岐”,“雨下”作“天下”,“知道”作“統治”,寫道:到如今才明白,此句所含真意為“已經到了由土岐家的我(指光秀)來統治天下的五月”。
可是,被認為是光秀發句的連歌并不只有這一版本。
事實上流傳下來的《愛宕百韻》的抄本有數十種,其中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的抄本里,“下しる”的部分被寫作“下なる”流傳下來。以下便是該句:
時は今あめが下なる五月かな
這句話的意思是“如今在雨下,時逢五月天”。
光秀所詠的句子如果是“あめが下なる”的話,按照字面意思就是“在雨的下面”,就讀不出像《惟任退治記》里所說的“已經到了由土岐家的我來統治天下的五月”的意思了。
那么,光秀原本所詠的到底是哪一句?如果摒除成見,重新考慮四百多年來都被當作定論的“統治天下”一說,又會怎樣呢?
從結論來說,毫無疑問光秀詠的是“雨下”,即詠“梅雨下不停的五月”之意。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惟任退治記》的“統治天下的五月”之說里有決定性的矛盾。
讓我們假想一下,如果確實如《惟任退治記》所說,光秀詠的是“已經到了由土岐家的我來統治天下的五月”,那么本能寺之變是幾月發生的呢?本能寺之變于六月二日發生——不是五月,而是六月。
既然本能寺發生在六月,那么“已經到了由土岐家的我來統治天下的五月”的這種解釋,在月份上就合不來。這乍看只是很微小的問題,可是在歷史搜查里不能放過一點差錯,這和現代的警方搜查是一個道理。
由于《愛宕百韻》是為祈求戰爭勝利而作的連歌,并且將供奉于愛宕神社前,因此絕不會有如此隨便的祈愿。故而這應該被視為硬生生地改寫句子后所產生的矛盾。

被竄改的《愛宕百韻》
很明顯,秀吉為了讓光秀看起來懷有奪取天下的野心,命令大村由己在《惟任退治記》里將連歌改寫成了“統治天下”。如此推理的依據不僅是月份的矛盾,還有一個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光秀詠的確實是“雨下”。
那就是“愛宕百韻”連歌會的日期。秀吉竄改的不僅是“天下”,還有“愛宕百韻”連歌會的“日期”。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抄本等眾多版本都記載著“愛宕百韻”連歌會的舉行日期為五月二十四日,可是《惟任退治記》里寫的是五月二十八日。
正是歷史搜查讓我著眼于這種日期的不同,因為我認為那個改動之中隱藏著某種目的。一直以來,相關研究從未著眼于此并繼續向下挖掘,因為它們是“研究”而不是“搜查”。
歷史搜查的結果是:為了盡量掩飾“奪取天下是在六月(本能寺之變發生在六月二日),而不是五月”這種誰都會發現的矛盾,秀吉故意將“愛宕百韻”連歌會舉辦的日期延至二十八日。若是保留“五月二十四日”的話,誰都看得出月份不合。但改成二十八日的話,感覺就大大不同了。也就是說,天正十年這一年的五月只有二十九天,改成“二十八日”的話,就能以“離六月僅差兩天”而敷衍過去。
這一改動出色地發揮了預想的效果,這正能證明——竄改日期正是出于這樣的目的——推理成立。這樣一來,月份不合這種簡單的矛盾就不會被人指出了,并且這種偽裝歷經四百多年都不曾被識破,甚至至今通用。誰都徹底相信了光秀詠的是“統治天下”。
這一說法之所以會被如此深信,與信長家臣太田牛一在《信長公記》一書中的記述有關。在當時的書籍中,這部書被認為是可信度最高的一級史料。而《信長公記》里也寫著“光秀在五月二十八日,吟詠了五月統天下之句”,這和奉秀吉之命所寫的《惟任退治記》里的內容一樣。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信長公記》是將信長的家臣太田牛一每次寫下的類似日記的原稿搜集整理、編纂而成的著作。乍看與報紙上新聞的寫法相似,但它和軍記物在記錄方法上有明顯的不同。書中既沒有歌頌信長的文章,也完全沒有誹謗光秀的記述。所以,可以認定《信長公記》正是可信度最高的一級史料。
可是,對于不同的記述對象,其可信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并不能因為它是一級史料,就認為其所有記述的可信度都是第一級的,實際使用時也有必要評估每條記述的可信度。
太田牛一是信長身邊的家臣,所以許多有關信長周邊的信息,都是他的親身經歷或是通過可靠渠道取得的,當然具有極高的可信度,包括廣為人知的本能寺之變中信長死前的情況——由于是牛一直接聽到了在場人員的講述,所以可信。可是有關信長周邊以外的信息,則是他不知從何處聽來的傳聞,其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愛宕百韻”連歌會的消息就屬此類。
遭到竄改的鐵證
難道就沒有秀吉竄改日期的鐵證么?作為歷史搜查,有必要確認更切實的證據。在“愛宕百韻”連歌會上,除了光秀,同席的還有著名連歌宗師紹巴,以及他的弟子等十人左右。如果能找到其中某人于二十八日身在別處的記錄的話,那在場證明就站不住腳了。
可是,在光秀及紹巴等人經常參加的堺市商人——天王寺屋屋(津田)宗及的茶會記錄以及與光秀有深交的公家日記等文獻中,并沒有發現光秀等人在二十八日的活動記錄。當我正想放棄時,忽然發現了一件事——有另一個可以讓在場證明不成立的證據。推論順利的話,也許能證明《惟任退治記》中所謂光秀在五月二十八日作歌是不可能的,而二十四日的話就可以。
那就是當日的天氣。
所謂連歌,就是按照被稱為“式目”的一種規則,參與者一人一句銜接作歌的一種詩歌形式。百韻是五、七、五的上句和七、七的下句交替吟詠,把它們連成五十組共一百句。當中有很多必須遵守的規矩,其中一個就是“發句(即首句)必須領會當場的風雅情趣而作”。
光秀的發句詠的是“雨下”,這是光秀領會眼前愛宕山之雨景的情趣所作。也就是說,那天愛宕山上肯定下了雨。如果二十四日有雨,而二十八日沒有下雨的話,就能證明秀吉竄改了日期。這是一種極為科學的證明方式。
于是,我便去調查是否存在記載了當時天氣的史料。幸運的是,有人在日記里記載了天氣。其中一人便是在愛宕山附近的京都居住的公家山科言經——他確實是一絲不茍地記錄了每一天的天氣。
看了他的日記《言經卿記》,便能發現二十四日的天氣寫的是“晴陰、下未”。“晴陰”是“時而晴天、時而陰天”的意思,那“下未”又是什么意思呢?古語辭典里也沒有相關記載。
從《言經卿記》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的記述可知,“下未”既不是晴天也不是大雨或小雨。因為這段時間的日記里有使用“天晴”、“大雨”、“小雨”等詞。為了確認意義不同于這些天氣表述的“下未”的意思,我還試著調查了其他人寫的日記。
那就是位于京都以南約四十公里的奈良興福寺多聞院的院主英俊寫的《多聞院日記》,以及當時所處京都以東約一百二十公里的三河(今愛知縣)岡崎附近的深溝城的松平家忠所寫的《家忠日記》。這兩人都只記錄下雨天。將《言經卿記》中寫著“下未”的四天與這兩人的日記對比,就可得知“下未”便是“下雨”,既非大雨也非小雨,意味著“普通的雨”。
于是,便能從《言經卿記》的記載得知存在疑點的二十四日,京都時而晴,時而陰,后下雨。愛宕山在京都市中心西北方向約十五公里的地方,比比叡山還高,海拔超過九百米。即使現在也要先從京都站起搭五十多分鐘的大巴,再沿陡峭的參拜道路步行三小時才能最終到達山頂的神社。京都市內“下雨”的話,在西邊山地的愛宕山肯定比京都市內還要早下雨。毋庸置疑,五月二十四日愛宕山下了梅雨。
另一方面,《惟任退治記》里所宣稱的二十八日的天氣又如何呢?
參考《言經卿記》,從五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六日都是下雨,而到二十七日雨停,然后二十八日的天氣是“天霽”。“霽”即“晴”,也就是說二十八日的天氣是“晴”。
二十八日的《多聞院日記》和《家忠日記》里都沒寫天氣。因為這兩人都有只記雨天的習慣,所以至少可知“天氣不是下雨”。所以可以認為,二十八日近畿、中部地區是大范圍的晴天。
這樣一來就證明了《愛宕百韻》確確實實遭到了竄改。被所有人毫不懷疑地相信了四百多年的“如今正是好時機,土岐五月統天下”這句連歌,是秀吉為了極力宣傳光秀懷有奪取天下的野心而故意將其中的詞句和日期竄改的結果,以上就是這一偽造行為的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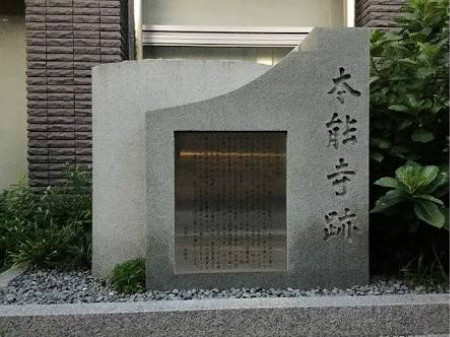
宣傳書里包含的秀吉的意圖
秀吉正當化的不僅是“野心說”,他更通過《惟任退治記》說光秀“企圖密謀叛變。但是,這并非臨時起意,而是出于多年來的反意”,將其說成從很久之前就懷有謀反之心。然后,書中還讓信長留下“所謂以怨報恩,也并非史無前例”的遺言,造成一種信長自己也認為光秀的謀反是出于怨恨的印象。這就是流傳至今的“怨恨說”的源頭。
但是,《惟任退治記》中所謂的“怨恨”是毫無根據的。那不過是秀吉對于光秀的心理活動所給出的一種專斷的解釋。不論光秀是否在很久之前就懷有謀反之心,或是他是否怨恨信長,還是他是否在《愛宕百韻》的發句中蘊含了奪取天下的決心,這些都只不過是秀吉的片面之詞。
所謂的信長遺言原本就很可疑。實際上,可信度很高的太田牛一所作《信長公記》里就寫著完全不同的內容。
秀吉有必須強行這么下結論的動機。整件事情不過是他把對自己有利和自己要鼓吹的內容寫進《惟任退治記》里而已。傳說秀吉曾幾次命令作者大村由己向親王和公家朗讀此書。秀吉利用《惟任退治記》完完全全地創造了世間對本能寺之變的普遍認識。
有一個很清楚的事實是,秀吉本人和他流傳至今的形象是不同的。即便他是信長忠誠的家臣,本來也并不曾仰慕過信長。通過分析《惟任退治記》的記述,就必定能明白事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通讀《惟任退治記》后我注意到,里面完全沒有體現他崇拜、仰慕信長的記述。更甚者,秀吉本人與傳說中被信長偏愛的形象也相差很遠。
在此書開頭描寫信長在安土城的榮華境況的部分,記述了信長每晚耽于享樂的事。該書還寫道,在本能寺之變的當晚,信長如往日一般沉溺于美色,甚至他在遭遇襲擊喪命前,把那些女人“一個一個地刺死了”。原文是這樣的:
將軍傾春光秋月乎,翫給紅紫粉黛,悉皆指殺,御殿手自懸火,被召御腹畢矣。
[此時將軍(信長),把春花秋月時賞玩的粉黛佳人們全部一一刺死,然后親自點燃大殿,便切腹了。]
然而,太田牛一在《信長公記》里寫道,信長當時說“女子勿在此受苦,速速出逃”,下令讓女人們逃跑。因為牛一的記錄肯定是直接取材自從本能寺逃出來的女性處的,所以不會有錯。信長即使面臨自己的死亡,也依然有關懷他人的胸襟。
可是,秀吉很明顯出于某種目的而掩飾了這段事實。他宣揚信長是淫亂殘忍之人,而光秀則因怨恨、野心等私人理由發動了謀反,而其他武將與此事蓋無關系。這就是本能寺之變事后處理的最后舉措。秀吉讓所有的武將都相信他從而集合到他麾下。他做出了如此宣言,并制訂了奪取政權的計劃。而歷史也證明了秀吉依據此計劃成功地篡奪了織田家政權。
依照秀吉的政治意圖而如此寫就的宣傳書,以及本能寺之變所謂定論即源于本書這一重要事實至今仍遭到忽視。由此可見,有關本能寺之變的研究從根本上就是歪曲的。
(本文摘自明智憲三郎著、鄭寅瓏譯《本能寺之變——光秀·信長·秀吉·家康,1582年的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9月。作者系明智光秀之子於寉丸的子孫。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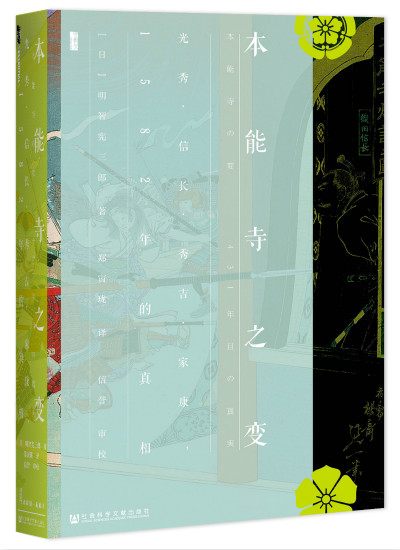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