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社科新人訪談錄|田雷:通過學術研究解答自己的疑惑
為加快培養造就本市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上海東方青年學社從2010年起組織開展“上海社科新人”評選活動,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速成長,逐漸形成了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學人共同體,對于加強社科理論隊伍建設和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發揮了積極作用。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的“上海社科新人訪談錄”專題,邀請2020-2021年度當選“上海社科新人”的14位青年學者進行專訪。本期邀請了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田雷,他的研究領域為憲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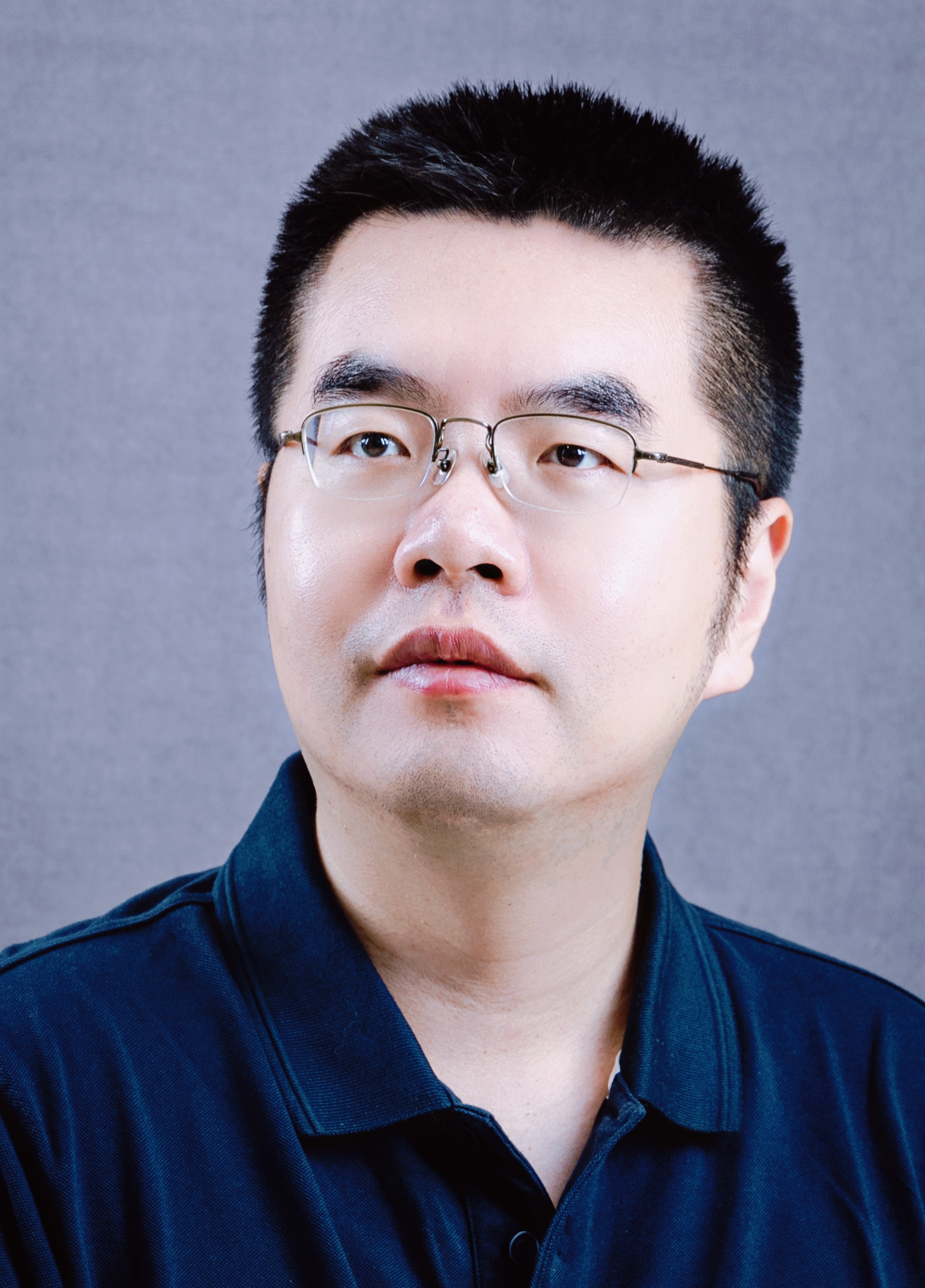
田雷,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憲法學、立法學,側重于法律、歷史和政治交叉的研究和寫作。出版專著《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獲得《法制日報》2021年度“十大法治圖書”等獎項。在憲法、國家制度、教育等領域譯有多部著作,產生廣泛社會影響。參與學術出版,主編“雅理譯叢”,截至目前已出版叢書共計46種,包括法政、人文社科、海外漢學等學科和領域。立足本土,組織出版原創性的法政著作系列“雅理中國”,呈現把研究做在祖國大地上的法政著述。主持“雅理讀書”微信公眾號的日常運營,全方位探索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新形式。
澎湃新聞: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內容?
田雷:我研究憲法。多年前剛進入這個領域時,主要關注美國憲法,不過最近兩三年,轉向了對中國憲法的研究上。在這里說“中國憲法”,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體所指的,就是我國現行的“八二憲法”,在1982年12月4日由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通過的那部憲法。“八二憲法”最特別的地方在于它的穩定性,它誕生于改革開放之初,在它前面是兩部短暫存在的憲法,“七五”和“七八”憲法,所以在“八二憲法”起草過程中,貫穿始終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確保新憲法能穩定下來,就此而言,彭真所領導的憲法修改委員會在起草過程中做了很多自覺的努力,比如有爭議的不寫。今年是“八二憲法”實施的四十周年,這四十年中國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但“八二憲法”經歷了五次修改后仍是國家的根本法,在此意義上,八二憲法是成功的,也是一部好憲法。把我引向“八二憲法”起草過程研究的,其實就是即將到來的四十周年時刻,“四十不惑”,在我看來,如果憲法研究不去關注本國現行憲法的歷史,講不清楚它的創生過程,那就談不上“不惑”,我也希望能通過自己的研究,至少能解答我自己的一些疑惑。
澎湃新聞:您能向我們介紹一下您的學術經歷嗎?您認為自己在學術上取得進步的主要經驗和體會是什么?
田雷:作為一位“新人”,我的學術經歷相對要復雜些。比如我現在在法學院教書,不過我的博士學位是在政治系讀的,從2005年到200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讀博士,研究的題目也和法學院所理解的“憲法”沒什么關系;而在五年前來到華東師大法學院、來到上海之前,我在重慶大學人文社科高研院工作了五年,那里是一個多學科交融、主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學術環境,還有正好是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秋季學期,我到北京大學文研院做了一學期的訪問;非要給自己的研究找到一個學科歸屬,我是研究憲法的,但又是一個非典型的憲法學者,當然在專業研究外,我目前還在從事幾件“跨界”的工作,其中比較值得一提、也略有能見度的是學術出版。我自己偶然也會想,如果借用刺猬和狐貍的比喻,那么我作為學者,到底是刺猬,還是狐貍,我又想要成為什么樣子,當然我只是想,自己也沒有答案。
就我個人來說,說點體會,就是要認識你自己,每一個階段做這個階段該做的事情,這是我現在的想法以及對自己的要求,它并不是我的經驗,更像是反省自己從前不足時所總結的教訓。
澎湃新聞:在您的學術生涯中,遇到過哪些困難?您覺得對于青年學者來說,哪些方面的幫助是很重要的?在您學術成長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經歷對您有重要影響和幫助?
田雷:學術的道路當然會有很多困難,但大部分倒也不是被強加的,既然選擇了學術這條路,它們就屬于自找的苦,是痛并快樂著。而且每個領域都有每個領域特殊的問題和挑戰,解決不了,或者說只能留給時間去解決。
我是從2010年開始工作的,到現在正好有十二個年頭了,大學這些年發生了很多變化,我經常覺得自己有一點是很幸運的,就是我只經歷過極短暫的“青椒”階段,最近三五年入職高校的青年博士大都沒這個運氣了,他們都要經歷一個長期、且考核嚴格的“預聘期”,才能真正安頓下來。在這種競爭不斷加劇并且延長的大環境下,青年學者可能最需要的是小的學術共同體,不是學術social的研討會,不是單位組織的論文workshop,而是在其中可以互相學習且批評的“無形的學院”,當然,我知道這個很難,但從理念上說,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去年年底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也是姍姍來遲,后記里我感謝了很多老師和朋友,那是一個非常長的名單,在這里也無法一一復述。學術成長道路,一個比較好的比喻就是金庸小說里的江湖歷練,我好久沒有讀金庸了,其實原本也不算很熟,所以我一時間還找不到一個人物去比附,不過大致說來,我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師,他們都無私地把自己的深厚功力一招一式地傳授給我,我也在他們那里獲得了各不相同的訓練,更難得的是,我遇到的這些老師雖然名動江湖,但基本上不是搞門派立山頭的,所以我也很早就要自己去闖蕩,自己在摸索之中歷練。他們在學術上教會了我,但并不認為我有必要為他們做什么,我也希望今后像他們一樣——長大后我就成了你。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您覺得當下的學術氛圍是如何促進您個人的研究的?
田雷:氛圍有大氛圍,也有小氛圍。我覺得學者如果說有特權,最大的特權就是你可以選擇自己的小氛圍,甚至可以參與構建自己的小氛圍。雖然考核壓力迫在眉睫,但我們還是可以選擇,選擇研究什么樣的題目,選擇自己的學術同道,選擇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做學問。現在網絡發達,這兩年由于疫情原因,大量學術活動轉到線上,都是足不出戶的免費資源,但好些事情都是雙刃劍,如果社交媒體只是點贊或復制祝賀,年輕學生或學者只是在學術活動中趕場,那么就不是我們在利用資源,搞不好是為資源所驅動了。在目前的氛圍下,我覺得“定力”是很重要,當然遺憾的是,也是很稀缺的。
澎湃新聞:本市面向青年學者有不少相關的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對您的學術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幫助?
田雷:我來上海時間有限,錯過了一些機會,也是非常遺憾。這次社科新人申報,也正好是既滿足了在上海工作的年限要求,同時還沒有超齡的唯一一年,也很幸運在這個一閃而過的機會窗口得以入選。
扶持,有經濟上的幫助,但又不止如此,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種認同和承認。青年學者在起步階段太容易遭受到各種挫折,甚至是打擊。2016年時,我參與了李連江教授《不發表,就出局》一書的出版,現在也就是幾年功夫,“不發表,就出局”就在國內高校迅速落地開花,現在“青椒”階段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有時候,我們需要一次認可來支撐著我們挺過下一個階段。
澎湃新聞:您認為您所開展的哪些課題研究及其取得成果,對您成功當選上海社科新人有所助益?
田雷:如果把課題理解為納入科研管理系統的、有編號有級別分三六九等的研究項目,說真的,我拿到的不多,不算是一個課題型的學者,當然,這本身是一個短板,是我需要改進的地方。
回答這個問題,也許我可以稍微擴展下“課題”的范圍,你現在手頭上到底在做哪些長期的事。我在年初申報答辯時,在個人的研究之外,還重點說了下我這些年來參與學術出版、組織學術翻譯的工作。比如,我主編的雅理譯叢,這些年來出版的品種已經超過了50本,在法學以及不少相關的領域內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最近一兩年,我們不局限于西學的翻譯引進,也開始參與本土原創學術的出版,開始打造“雅理中國”的系列。慢慢地,雅理雖然力量有限,但也成了一個可以發光發熱的平臺,比如我們現在的出版合作包括北京三聯、廣西師大、世紀文景、中信大方,他們在幫助也提升了我們。我想也許這些工作,給我加了一些分。
澎湃新聞:獲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稱號之后,您覺得對于您的課題研究會有哪些助益?“上海社科新人”稱號的獲得,對您的學術生涯的展開會有哪些助益?
田雷:學者需要認可,這種認可支撐著我們去做一些更困難、更有挑戰性的研究工作。我在2020年翻譯了一本書,《慢教授》,出版后有些朋友給我開玩笑,不是不想慢,是實在慢不下來。但問題在于,有些學術,尤其是基礎學科的基礎研究,確實是需要慢工出細活的,既然大環境決定了很難慢,那么似乎只有兩個解決方法,一個是自己再努力一點,比如少刷點朋友圈、微博、知乎,另一個就是可能要通過短期成績的取得給自己先掙出來“慢一些”的資格。
澎湃新聞:您所開展的學術研究,對加快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發揮了哪些作用?
田雷:一個人的研究,無論對自己多么重要,在更大的范圍內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我本科在南京大學讀的,今年正好是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的校慶,也是我本科畢業20周年,想到了在南大讀書時的一句話,今日我以南大為榮,明日南大以我為榮,我想這就是從學術角度處理個人和整體關系的一種思路吧,既要始終保持謙遜,但也不能丟掉自信和勇氣。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看待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整體的學術研究水平與城市軟實力之間的關系的?
田雷:很顯然,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本身就是城市軟實力的一部分,尤其我知道有些朋友的研究就聚焦于上海的歷史和文化。當然,學術終究是小眾的事情,不能以流量為指標,不過學術的展示形態未來也許會更多面,也就是說,很多在專業領域內深挖的作品或許未來要開發出一些“周邊”,僅就軟實力建設的直接效果來說,這些衍生品可能更為大眾所喜聞樂見。
澎湃新聞:您覺得您的學術研究領域的水平提升將會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軟實力的提升?
田雷:作為一位專業學者來說,要腳踏實地,老實本分,把自己專業領域內的問題研究好,一年寫幾篇文章,幾年寫一本書。當然,我還有一個業余出版社的身份,能夠通過這個平臺多做一些好書,也是我接下來要努力的一個工作。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