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舊地上海 | 四川阿姨在上海:65歲的人生繼續(xù)遷徙
鏡相欄目首發(fā)獨(dú)家非虛構(gòu)作品,如需轉(zhuǎn)載,請(qǐng)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tái)聯(lián)系
文:王心怡 汪子祺 肖瑞淳
編輯:林子堯
【編者按】
2022年春天,上海因疫情按下了暫停鍵。在過(guò)去兩個(gè)多月的日子里,我們重新凝視著這座城市,回想著曾經(jīng)置身其中的路,未曾發(fā)覺(jué)曾經(jīng)平常的感受竟如此珍貴。經(jīng)歷了隔離的日子,我們終于重新行走在這片土地上。周遭一切恍惚得不真實(shí),熟悉又陌生。也許,我們未曾真正認(rèn)識(shí)過(guò)這座城市。
“舊地上海”是澎湃鏡相與復(fù)旦大學(xué)、上海大學(xué)兩所高校的中文系同學(xué)聯(lián)合開展的城市寫作計(jì)劃,旨在深入探索上海小眾的角落,理解在這座城市邊緣的普通人生活。這是第一篇,關(guān)于上海的江灣鎮(zhèn)。
2021年11月15日,是文淑珍經(jīng)營(yíng)“文文造型屋”的最后一天。她打算像往常一樣早上9:30開門,晚上21:30休息。現(xiàn)在正是下午生意最好的時(shí)候,三四個(gè)等待理發(fā)的顧客擠在幾平方米的店里。文淑珍穿著理發(fā)時(shí)專用的白色大褂,一邊剪頭,一邊和其他顧客一來(lái)一往地閑聊,手上剪刀利落地穿行于顧客的發(fā)梢,碎發(fā)散落一地。
這間理發(fā)店現(xiàn)在是整條街道上最有人氣的地方。店里傳來(lái)的護(hù)發(fā)產(chǎn)品的甜香和門口旋轉(zhuǎn)的燈箱,都和屋外貼滿了拆遷標(biāo)語(yǔ)的灰白老街格格不入。理發(fā)店內(nèi)的裝潢瞬間將人帶回上世紀(jì)末的香港電影。墻壁上鋪滿白色瓷磚,墻上貼著一張褪色的明星海報(bào),左側(cè)方擺一臺(tái)老式彩色電視機(jī),一米多高的掛式柜臺(tái)橫在前面,三扇半身立鏡,還有一把笨重復(fù)古的理發(fā)椅。時(shí)間好像在這里按下了暫停鍵,只有物件上斑駁的痕跡訴說(shuō)著光陰流轉(zhuǎn)。
但與萬(wàn)壽街上陸續(xù)遷走的住戶一樣,這家理發(fā)店的店主文淑珍同樣需面對(duì)離開與停業(yè)的現(xiàn)實(shí)。早在一個(gè)月前,萬(wàn)壽街上最早的一批拆遷戶就已經(jīng)搬走,此時(shí)沿街的店鋪大半都已關(guān)閉。
一
上海江灣鎮(zhèn)曾是繁華的千年古鎮(zhèn),《宋會(huì)要輯稿·食貨十七》中提到:“江灣浦口邊枕吳淞大江,連接海洋大川,商賈舟船多是稍入?yún)卿两〗瓰称秩胄阒萸帻堟?zhèn),其江灣正系商賈經(jīng)由沖要之地。”但受地理位置影響,江灣鎮(zhèn)成為戰(zhàn)爭(zhēng)中烽火交集的地區(qū),許多建筑古跡都在戰(zhàn)火下蕩然無(wú)存。

文淑珍在理發(fā)店門口留影
沿淞滬鐵路舊址前行,萬(wàn)壽路位于車站西路的盡頭,一眾低矮的私房盤踞在此。這塊區(qū)域如今屬于虹口區(qū),已被劃入拆遷范圍,住戶陸續(xù)遷出。私房的居住條件并不理想,巷弄兩旁還能見(jiàn)到成排的痰盂和馬桶,低矮的房屋散發(fā)著潮濕氣息,即便在陽(yáng)光明媚的白日,也需開燈才能有足夠的光線。
文淑珍的這家理發(fā)店算是這片私房中居住條件較好的,店門右拐十米就是公共衛(wèi)生間,每日有專門的人員負(fù)責(zé)打掃,顧客有需求也非常方便。若是平日在店里理發(fā),她也極少去自家衛(wèi)生間。理發(fā)店是自家私房改造出來(lái)的,廚房用的仍是老式煤氣罐,灶臺(tái)的面積不大,與普通課桌的大小差不多,鍋碗瓢盆堆放在下面,墻上櫥柜簡(jiǎn)單地放了一些調(diào)味料。理發(fā)室與自家廚房相連,玻璃推門從早到晚一直敞開。每到飯點(diǎn),飯菜的味道便會(huì)彌漫整個(gè)理發(fā)室,所有客人都知道今天她家一日三餐吃了什么,文淑珍對(duì)此早已習(xí)慣。
街道辦事處通知文淑珍第二天下午派人幫她搬行李,如果沒(méi)有意外的話,這將是這家理發(fā)店最后一天營(yíng)業(yè)。文淑珍熟練地為一位頭發(fā)花白的老人穿好理發(fā)圍布,并用噴壺將頭發(fā)潤(rùn)濕梳順,老人已經(jīng)年過(guò)八十,是文淑珍理發(fā)店的常客。文淑珍親切地問(wèn)老人這次要剪什么樣的頭發(fā),未等老人開口,旁邊一位年輕女人說(shuō)道:“就后頭推得高一點(diǎn)好了,把伊推得高一點(diǎn)短一點(diǎn)。”
像這樣常規(guī)理發(fā)的客人,恰逢夏日生意繁忙時(shí),文淑珍一天要接待三十幾個(gè),連吃飯的時(shí)間也沒(méi)有。這里剪發(fā)的費(fèi)用一人是10元,燙頭則用老方法上卷后用毛巾包好套上加熱蒸帽,一頭長(zhǎng)發(fā)燙下來(lái)也只要一百多快。低價(jià)實(shí)惠的價(jià)格一方面為文淑珍帶來(lái)了一批固定的回頭客,另一方面也令她無(wú)力負(fù)擔(dān)請(qǐng)其他學(xué)徒幫忙的工資。不論多忙,這家店始終都是她一個(gè)人在操持。
文淑珍家的房子分為兩層,樓下是廚房與衛(wèi)生間,中間用自制爬梯連接,傾斜角度大到上下樓需手腳并用,樓上是餐廳與臥室,上下總面積約80平方米。文淑珍夫婦與兒子兒媳和小孫女一同住在這里。雖然文淑珍不太滿意這間房子需要每天“爬上爬下”,而且燒飯的油煙味難散,不得不“樓下燒飯端到樓上吃”,但是幾十年過(guò)去,也已經(jīng)習(xí)慣了。
兩年前,也曾有人提出花一千萬(wàn)買下這套房,文淑珍猶豫再三,還是決定等拆遷,沒(méi)有賣。如今能拿到的拆遷款只有800多萬(wàn),比文淑珍的預(yù)期“少拿了200多萬(wàn)”,拆遷將使她失去這間沿街的鋪面,理發(fā)生意眼看著也沒(méi)法做了。
給老人理完發(fā),文淑珍一邊用毛巾?yè)壑先松砩系乃榘l(fā),一邊笑著問(wèn),陪你理發(fā)的是你什么人啊?不料老人和年輕女人一同沉默,話音掉在了地上,文淑娟又笑道:“這是你小閨女吧。”年輕女人默不作聲地將老人扶起來(lái),老人點(diǎn)點(diǎn)頭:“是,是,小閨女。”老人走出店面后,文淑珍搖頭道:“其實(shí)一看就是她的保姆,上海的人吶,到老了,都是保姆孝,自己的孩子不會(huì)孝的。”在上海生活了三十余年,大半輩子都與這塊土地相連,文淑珍談起上海時(shí)卻仿佛始終隔著一段距離,將自己排除在上海人之外。

文淑珍在給顧客理頭發(fā)
緊接著來(lái)理發(fā)的是一個(gè)稍年輕的大爺,看起來(lái)與文淑珍年紀(jì)相近,一進(jìn)門就說(shuō)道:“我阿妹又問(wèn)我要鈔票了呀,要400萬(wàn)。”大爺?shù)姆孔邮潜緦儆诟改福?dāng)兵回來(lái)后自己整體翻新一遍,還加蓋了一層。拆遷政策規(guī)定所有子女必須統(tǒng)一簽字合同才可生效。因嫁人早就搬出房子的親妹妹因手里掌握著簽字權(quán),而打起了拆遷費(fèi)的算盤。大爺提出給妹妹100萬(wàn)拆遷款作為和解方案,妹妹拒絕了,動(dòng)遷組嘗試調(diào)解兄妹間的分歧,但雙方互不相讓,年過(guò)半百的親兄妹無(wú)奈對(duì)簿公堂。大爺講話聲音越來(lái)越響,手上比著數(shù)字四,在空氣里使勁晃了晃,說(shuō)道:“兄妹之間打官司,難看吧。”文淑珍不緊不慢地評(píng)價(jià)道:“哎呀,上海多少人為這個(gè)房子鬧得一塌糊涂。都是沒(méi)錢,見(jiàn)了錢都眼紅。”
文淑珍每日在理發(fā)店邂逅形形色色的客人,世情百態(tài)從幾句閑聊中勾勒出來(lái)。但是文淑珍并不是一個(gè)純粹的旁觀者。
二
送走了最后一個(gè)剪頭發(fā)的客人,文淑珍打電話喊來(lái)了住在附近的妹妹,打算讓她替自己在這間理發(fā)店再燙一次頭,當(dāng)作紀(jì)念。
文淑珍對(duì)著鏡子把腦袋后面揪著的小髻拆了,對(duì)著鏡子撥弄著散到肩頭的頭發(fā)。年輕的時(shí)候她喜歡把頭發(fā)這么披著,但是現(xiàn)在披著頭發(fā)做事總覺(jué)得心里煩,到頭來(lái)還是一把把頭發(fā)抓起來(lái)扎上。最近忙拆遷,更是煩累,眼睛都腫著。文淑珍嘆口氣,在理發(fā)椅上坐下,從鏡子里對(duì)站在身后的妹妹說(shuō),先剪短一點(diǎn),能扎起來(lái)就行。
社區(qū)雇來(lái)幫忙拖家具的車很緊張,一家一家輪著往下搬,預(yù)先安排給文淑珍家的搬遷時(shí)間一再往后推,明天下午車終于要來(lái)了。文淑珍的老伴借了個(gè)生銹的平板手推車,一趟趟地從她們身后將打包好的行李往外拖,從他張著喘氣的嘴里,可以聽見(jiàn)他的肺發(fā)出像扯風(fēng)箱一樣的聲響。妹妹問(wèn),你兒子呢?文淑珍嗤笑一聲,他現(xiàn)在多忙的,叫他吃飯還沒(méi)空呢,還叫他來(lái)搬家?又沖著丈夫罵,狗東西什么都要,否則早就搬完了,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統(tǒng)共就四個(gè)箱子。丈夫一面費(fèi)力拉推車,一面哼哼著說(shuō),以為我不敢啊?我當(dāng)初回上海的時(shí)候就一個(gè)包,就一個(gè)包就跑到上海。

文淑珍在文文造型屋燙頭
文淑珍的老伴曾是上海下放到新疆插隊(duì)的知青。1978年,文淑珍高中畢業(yè)后離開了四川老家,拿著姑媽寄來(lái)的路費(fèi),坐了三天四夜的綠皮火車去投奔在新疆庫(kù)爾勒兵團(tuán)當(dāng)兵的姑媽,第二年就經(jīng)人介紹認(rèn)識(shí)了現(xiàn)在的丈夫。兩人當(dāng)時(shí)屬于是自由“談朋友”,感情發(fā)展得很快,不到一年就結(jié)了婚。結(jié)婚之后,丈夫要回上海,兩人趁著冬天農(nóng)閑,偷偷蓋了章,“稀里糊涂就逃回了上海。”
文淑珍第一次到上海,就和丈夫一家一起擠進(jìn)了萬(wàn)壽街的這間房子里,“感覺(jué)像是來(lái)到了外國(guó),每天和人打啞謎”。公婆不識(shí)字,說(shuō)帶江灣鎮(zhèn)口音的上海話。婆婆跟她說(shuō)去“茅房”,她硬是聽成了去“升堂”。丈夫回家沒(méi)看見(jiàn)自己的媽,問(wèn)她。她硬著頭皮說(shuō),你媽去升堂了,鬧了好大的笑話。后來(lái),文淑珍勉強(qiáng)能聽懂一些有關(guān)家務(wù)的簡(jiǎn)單詞語(yǔ),聽到“要燒中為(中飯)”,就把風(fēng)爐拎出去,在河邊扇風(fēng)爐,然后生煤球爐。“看要擇菜我就趕快擇菜,擇完了菜去掃地,吃了飯去擦桌子洗碗,我看到什么就做什么,不講話。”這樣的日子過(guò)了半年,上海接到中央指令,停發(fā)了私自返滬知青10塊錢一個(gè)月的生活補(bǔ)貼,小兩口于是再次回到了新疆。重返新疆,文淑珍心情有點(diǎn)復(fù)雜,雖然干活辛苦,但是在兵團(tuán)基本上“人人都說(shuō)普通話”。
1981年7月5日,文淑珍在新疆生下了自己的獨(dú)子。生完孩子之后并沒(méi)有雙方的老人幫忙照顧,白天兩人又都要出門上班,孩子就送到兵團(tuán)的托兒所。每天早上吹號(hào)之后,連長(zhǎng)會(huì)逐一清點(diǎn)上班人數(shù),如果遲到會(huì)被用廣播點(diǎn)名,整個(gè)連隊(duì)都聽得到。“某某某不像話!”文淑珍生性好強(qiáng),寧愿每天早上不吃早飯,也要給孩子把好屎尿,弄得干干凈凈送到托兒所,然后準(zhǔn)時(shí)去上班。而她也因此弄壞了胃,直到現(xiàn)在還會(huì)發(fā)胃病。
文淑珍在兵團(tuán)沒(méi)有固定的崗位,屬于“社會(huì)主義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養(yǎng)豬、養(yǎng)雞、下地、照看林木、管理青年班的孩子,都干過(guò)。畢竟年輕好學(xué),身體也頂?shù)米。寄芨伞>瓦@么東干干西干干,干了十年。1988年冬天,政策放松了,文淑珍和丈夫帶著兒子,再次回到了萬(wàn)壽街,此后33年,再也沒(méi)有離開過(guò)。上下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開始住了公婆、哥嫂,一家七口擠擠挨挨。如今公婆已經(jīng)去世,哥嫂也搬了出去,但是又添了兒媳婦和一個(gè)小孫女。
三
初來(lái)乍到,文淑珍在上海的第一個(gè)營(yíng)生是做小買賣。她批發(fā)了一些賣給游客的小玩意兒,用包背著,去外灘、上海大世界和百樂(lè)門等景點(diǎn)兜售。游客在外灘漫步,享受著迷人的上海風(fēng)情,她站在一邊,背著包,手里拿著玩具,想著怎么上前搭訕。“我做小生意做不來(lái)的,手都是捧在胸前,拿不出來(lái)。”因此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一天,也賣不出去多少件。同時(shí)還得留著個(gè)心眼,預(yù)防警察來(lái)抓。當(dāng)時(shí)還沒(méi)有城管,賣東西的小販管一身黑制服的警察叫“黑貓警長(zhǎng)”,有人喊“黑貓來(lái)了”,大家一起跑。文淑珍跑不快,被“黑貓”逮過(guò)幾次。路過(guò)的爺叔看著她笑:“哎呦,你這么年輕就做這個(gè)活啊?不找個(gè)工作干干?”
文淑珍也想“找個(gè)工作干干”。她找到一家廣東人開的理發(fā)實(shí)習(xí)班,打算學(xué)習(xí)美容美發(fā)。廣東人白天到工廠、工地去給人剪頭發(fā),晚上上課。文淑珍白天照樣掙錢,晚飯來(lái)不及吃,趕著去上課。放學(xué)之后騎車回家,一身汗,想買個(gè)冰棍兒,但舍不得兩毛錢,回家喝點(diǎn)涼白開,下點(diǎn)面,醬油拌面。
1992年夏天,文淑珍將萬(wàn)壽街的房子沿街的門臉空出來(lái),墻上裝了塊單玻璃,弄了幾個(gè)凳子,開起了一個(gè)簡(jiǎn)易理發(fā)店。空調(diào)沒(méi)有,洗頭的躺椅和池子也沒(méi)有,只能搞一個(gè)桶裝在墻上,弄一個(gè)開關(guān)燒水,客人洗頭的水都從桶里舀。兩塊錢剪一個(gè)頭,客人嫌熱,環(huán)境不好,也不怎么來(lái)。整個(gè)夏天,每天的營(yíng)業(yè)額都不到十塊錢。到了秋天,天氣涼爽下來(lái),客人才漸漸多起來(lái)。
當(dāng)年,萬(wàn)壽街附近居住的基本都是上海本地人。文淑珍說(shuō)完“儂好”“儂飯切估伐”就詞窮,剩下的理發(fā)的過(guò)程中充滿了讓人尷尬的沉默。三十年過(guò)去,文淑珍的上海話已經(jīng)非常熟練,“會(huì)聽也會(huì)講”,常來(lái)店里理發(fā)的客人,也都是老熟人了,有默契在。“轉(zhuǎn)燈他們就曉得店開了。但是老客戶呢,你不轉(zhuǎn)燈他們也會(huì)來(lái)的,我這個(gè)燈轉(zhuǎn)了十多年了。”老客人們進(jìn)門坐下,誰(shuí)都可以跟文淑珍無(wú)縫嘮上一段家常,說(shuō)說(shuō)身體,說(shuō)說(shuō)兒女,親切熟稔。但文淑珍心里總歸覺(jué)得,自己和萬(wàn)壽街的老住戶們不一樣,雖說(shuō)在上海待了幾十年,戶口也來(lái)了,但是一直不覺(jué)得自己是上海人。有客人笑著說(shuō),你是新上海人呀。文淑珍聽了也笑,新上海也不是新上海,我都65歲咧,現(xiàn)在引進(jìn)的人才才是新上海人,我是老的啊,我孫女都6歲上學(xué)了,說(shuō)是新上海人,牙都給人家笑掉。

文淑珍在天井給顧客理發(fā)
不管算不算上海人,萬(wàn)壽街這套房子文淑珍都住了三十多年,是她在這個(gè)大城市的一個(gè)最熟悉的落腳點(diǎn)。門口的理發(fā)店則是支撐著她在此地站住腳的事業(yè)。文淑珍雖然嘲笑丈夫恨不得把房子里的所有東西都原原本本地搬走,不如自己灑脫,但心里多少也有些舍不得。
燙完頭,天色已經(jīng)黑了,文淑珍對(duì)著鏡子端詳端詳,然后把頭發(fā)扎起來(lái),讓妹妹給自己在理發(fā)店門口拍了一張照。“不要拍半身的,要把我這個(gè)(店的)門臉全都拍進(jìn)去。”照片里,文淑珍穿著工作時(shí)的白大褂,站在“文文造型屋”的招牌下,兩手還是像年輕時(shí)一樣喜歡“捧在胸前”,顯得有些拘謹(jǐn)。門口暖黃色的燈箱顏色已經(jīng)有些暗淡了,但是還是堅(jiān)守著這“最后一班崗”,幾十年如一日地轉(zhuǎn)著。
此時(shí)的文淑珍沒(méi)有想象過(guò)在她離開之后這條街會(huì)變成什么樣子。在完成了短暫的紀(jì)念之后,她很快就要回歸到一日三餐的生活中去。今天下午她和丈夫都很忙碌,沒(méi)有時(shí)間做晚飯,幸好冰箱里還有一大塊崇明糕,蒸一蒸就夠幾個(gè)人分吃。為了好熟,妹妹拿著菜刀費(fèi)力地要將凍糕剁開。丈夫見(jiàn)狀急得直罵:“你小心點(diǎn),把臺(tái)子剁壞了呀!”妹妹性格潑辣,立刻反唇相譏:“壞了就壞了,你帶得走嗎?帶到棺材里!”文淑珍聽了在一邊直笑。
糕蒸好,潔白香甜,吃下去飽腹踏實(shí)。可是文淑珍還是覺(jué)得這個(gè)糕沒(méi)有以前街上那家賣糕的店做的糕好吃,那家人是比較早搬的一批拆遷戶,一個(gè)月前就搬走了。這街上小店不少,除了賣糕的店,還有賣手工蛋餃的店、修理羊毛衫的店,這些小店在萬(wàn)壽街拆遷之后,恐怕也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承擔(dān)得起租金的店面。文淑珍的理發(fā)店也是如此。可是她仍然期待搬到新房子之后,能用自己的方式,把這個(gè)老理發(fā)店繼續(xù)開下去。
四
不舍歸不舍,文淑珍對(duì)于搬家換新房并不是沒(méi)有期待。她看了不少中介推薦的房子,最好的打算是能買兩套小間,讓小兩口和老夫妻能夠分開住,那怕“位置買偏一點(diǎn)”。從小到大,不管是在老家四川,新疆,還是上海,文淑珍都沒(méi)有住過(guò)樓房。她想試試一開門進(jìn)去屋里敞亮,客廳房間一眼看盡的房子,而不像萬(wàn)壽街的老屋,房間像疊積木一樣“東一間西一間上一間下一間”。同時(shí)她對(duì)樓房也有自己的擔(dān)心,“現(xiàn)在房子動(dòng)不動(dòng)就造二三十層,往下看我都恐高,萬(wàn)一地震或是海嘯,怎么來(lái)得及跑呢?我要買還是買低一點(diǎn)。”
房子還沒(méi)有看好,為了應(yīng)付馬上到來(lái)的拆遷,文淑珍已經(jīng)在仁德路的小區(qū)里租了一套一樓的房子。新的住所在一個(gè)新式的小區(qū)里,是六層樓的單元房,離萬(wàn)壽街步行距離只有500米。文淑珍家在一樓,從門口進(jìn)去有一條貫穿的過(guò)道,沿著過(guò)道從外到里依次是兒子一家的臥室、廚房、廁所和餐廳。文淑珍和丈夫的臥室沒(méi)有隔斷,只有一張床夾在餐廳和陽(yáng)臺(tái)之間。

文淑珍租住的房子一角
文淑珍一家是11月26號(hào)搬來(lái)的,剛搬來(lái)時(shí)東西很多很亂,清東西就清理了一個(gè)星期。搬來(lái)一個(gè)多月之后,很多東西仍找不到自己在這間房子里的位置,被隨意堆放在房間各處,有些從老屋搬來(lái)的紙箱還貼著膠封。餐桌旁邊的椅子靠背上掛著袋子、坐墊上堆著一大袋紙巾,來(lái)理發(fā)的客人只能坐在床上。過(guò)道靠墻堆了一溜雜物,只留了一個(gè)人通行的空間。客廳里的矮柜上堆滿了各種藥瓶和藥盒,基本上都是些治心血管方面和骨質(zhì)方面的藥。
房間里依然留存著許多老屋的痕跡,用到發(fā)黑的木衣柜被原封不動(dòng)地搬來(lái)擺在文淑珍的床邊,床對(duì)面的壁櫥里堆了很多發(fā)黃的雜志,墻上掛著舊時(shí)鐘,秒針滴答滴答地響,仿佛要把往日的時(shí)光流進(jìn)現(xiàn)在的生活里。老店里燙發(fā)的機(jī)器也被搬來(lái),擺在吃飯的餐桌對(duì)面。
文淑珍理發(fā)的地方就在屋外側(cè)的天井里,幾塊透明的板材和塑料膜將這里密封成了一個(gè)陽(yáng)臺(tái),陽(yáng)光從頂上顫巍巍地照進(jìn)來(lái)——這也是整間房子里唯一可以感覺(jué)到自然光的地方。棚頂上吊著插電的接線板與晾曬的衣服,底下放著一張椅子和一面靠在墻上的全身鏡,鏡旁的小洗手池被用來(lái)給客人洗頭。這就是文淑珍新的造型屋。
雖然環(huán)境已經(jīng)同以前的文文造型屋完全不同,但只要拿起推子和剪刀,文淑珍就還是那個(gè)滔滔不絕的造型師。她正在和客人打趣萬(wàn)壽街附近新開的一家10元快剪理發(fā)店,“一天到晚在門口吆喝,誰(shuí)敢去剪啊?把人的腦袋剪得像個(gè)鴨蛋一樣,小年輕剪得像個(gè)老頭頭。”
搬完家不久,文淑珍立刻給以前的老顧客群發(fā)微信并附上新住所的地址:“需要理發(fā)聯(lián)系我,來(lái)時(shí)提前打我視頻好到門外接你,發(fā)文字沒(méi)有時(shí)間看,以免誤時(shí)喲。謝謝你啦!”信息發(fā)是發(fā)了,客人卻不怎么來(lái)。在萬(wàn)壽街,最忙的時(shí)候一天連剪帶染燙可以掙七八百,平時(shí)也能有三四百。而搬到這里來(lái)幾乎就沒(méi)有什么生意,有時(shí)一天來(lái)三五個(gè)找上門的老客戶,有時(shí)候一天都沒(méi)人來(lái),這是文淑珍以前從未遇到的情況。
在萬(wàn)壽街開店時(shí),文淑珍每周一給自己放一天假。現(xiàn)在因?yàn)樯獠蝗缫酝纱嘁恢軣o(wú)休,只要有人找上門就給人家剪。時(shí)常來(lái)理發(fā)的老熟客會(huì)問(wèn)文淑珍“儂這么大年紀(jì),沒(méi)想著退休啊?”文淑珍的回答只有“生活所迫”四個(gè)字。早幾年兒子和朋友一起創(chuàng)業(yè),賠了不少錢,所以文淑珍夫妻倆生活完全靠自己。而相比于過(guò)去,如今的文淑珍更需要這份理發(fā)店的收入。暫時(shí)落腳的這間房子一個(gè)月租金就將近6000元,而作為知青退休的夫婦倆,依著“369”的政策,工齡17年的文淑珍一個(gè)月的退休金是3000出頭,丈夫的工齡稍微長(zhǎng),20多年,一個(gè)月的退休金能拿到接近4000元。如今兩人的退休金幾乎都要搭到房租里。
現(xiàn)在居住的房子不僅燒錢,也并不讓文淑珍覺(jué)得滿意,她總覺(jué)得住著別人的房子像是“討飯樣的”。房子的面積也沒(méi)有她以前的老屋大,堆滿東西之后沒(méi)有她想象中住樓房的敞亮,反而看著心里堵。來(lái)理發(fā)的熟客也會(huì)開導(dǎo)她,習(xí)慣就好了嘛。文淑珍也不多說(shuō)什么,只盯著椅子上顧客的頭發(fā),一剪子一剪子,一推子一推子地理。只有在理發(fā)的時(shí)候,文淑珍才能暫時(shí)忘卻生活中的一切。
五
此時(shí)老屋的拆遷又遇到了難題。文淑珍的丈夫有兄弟姐妹6個(gè),老屋是她丈夫從家里繼承的。老屋原本屬于幾家人,文淑珍指望拆遷把字一簽,把各自該拿的錢一拿就可以徹底分家,樂(lè)得清爽。但是丈夫的妹妹是困難戶,吃低保,住廉租房。根據(jù)國(guó)家規(guī)定如果低保戶戶頭上的存款超過(guò)10萬(wàn)元就不能繼續(xù)享受這些保障。此次拆遷妹妹按政策可以分到56萬(wàn),雖說(shuō)不是個(gè)小數(shù)目,可無(wú)論如何也難以在上海買一套房,所以妹妹不愿簽字。一天不簽字,拆遷款就一天下不來(lái),文淑珍就得繼續(xù)租住在這個(gè)讓她覺(jué)得像是“討飯”的地方。沒(méi)有生意的時(shí)候,文淑珍就天天往信訪辦跑,可所有的流程都是按照政策來(lái)的,沒(méi)有違規(guī)的地方。文淑珍為了這件事著急上火,她不明白為什么誰(shuí)都沒(méi)有問(wèn)題,事情卻解決不了。

拆遷中的理發(fā)店
文淑珍覺(jué)得自己是一個(gè)很簡(jiǎn)單的人,一生的信條就是“做人只要善良、誠(chéng)實(shí),走到哪都不怕。”搬家前的最后一天,有一位老客囑咐她,搬到新房子要放放炮仗、敬土地神,在新家的生活才能興旺。文淑珍搖搖頭,我不信這些的。那位爺叔勸她,這種東西我也不全信,但是信一信沒(méi)有害處,我出去旅游見(jiàn)到什么寺廟都進(jìn)去拜一拜,總沒(méi)有害處吧!可是無(wú)論爺叔怎么勸,文淑珍只是搖頭,最后沒(méi)有辦法,就說(shuō),我這輩子只信一個(gè)人,就是毛澤東。兩人誰(shuí)也沒(méi)能說(shuō)服誰(shuí),爺叔剪完頭戴上帽子,留下一句略帶火氣的“再會(huì)”。
房間的柜子上有一個(gè)老舊的相框,里面是一張有些年頭的理發(fā)店的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文淑珍把它保存得很好,擺在了最顯眼的地方。這家理發(fā)店不久后應(yīng)該不會(huì)繼續(xù)存在,她明白,如果還想留在江灣鎮(zhèn),就只有蝸居,沒(méi)有多余的地方開理發(fā)店;如果想住大一點(diǎn)的房子,那就只能往嘉定、金山那邊買,老客戶也不會(huì)跟來(lái)。這張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最恰當(dāng)?shù)臍w宿也只能是這存放回憶的舊相框。
天井外面車來(lái)車往,天井里面是電推子的嗡嗡聲。這三十多年的上海生活,已經(jīng)讓文淑珍的生命化成了電推子聲里的煙火氣,濃縮在萬(wàn)壽街的一隅,濃縮在文文造型屋里。從四川閬中到新疆庫(kù)爾勒再到上海江灣鎮(zhèn),文淑珍一生的軌跡幾乎橫跨了整個(gè)中國(guó)。
在同一個(gè)時(shí)間,萬(wàn)壽街的住戶已經(jīng)全部搬完了,只有街尾的一個(gè)商鋪還開著。昏暗的街燈照著夜晚的老街,街上空蕩無(wú)人,除了每一個(gè)弄堂的出口坐著的保安。他們大都裹著厚厚的保安大衣,在寒冷的冬夜打盹。文淑珍的老房子的門口,大門已經(jīng)砌上了厚厚的水泥,紅色的油漆刷上了門牌號(hào),原來(lái)是燈箱的地方堆放著很高一摞塑料凳子。大門上醒目的“文文造型屋”還掛在那里,和隔壁店面的“中國(guó)體育彩票”并立,而不久后這塊招牌也將揭下。這一天是2022年1月7日,離農(nóng)歷新年還有26天,離文淑珍第一次來(lái)上海已過(guò)去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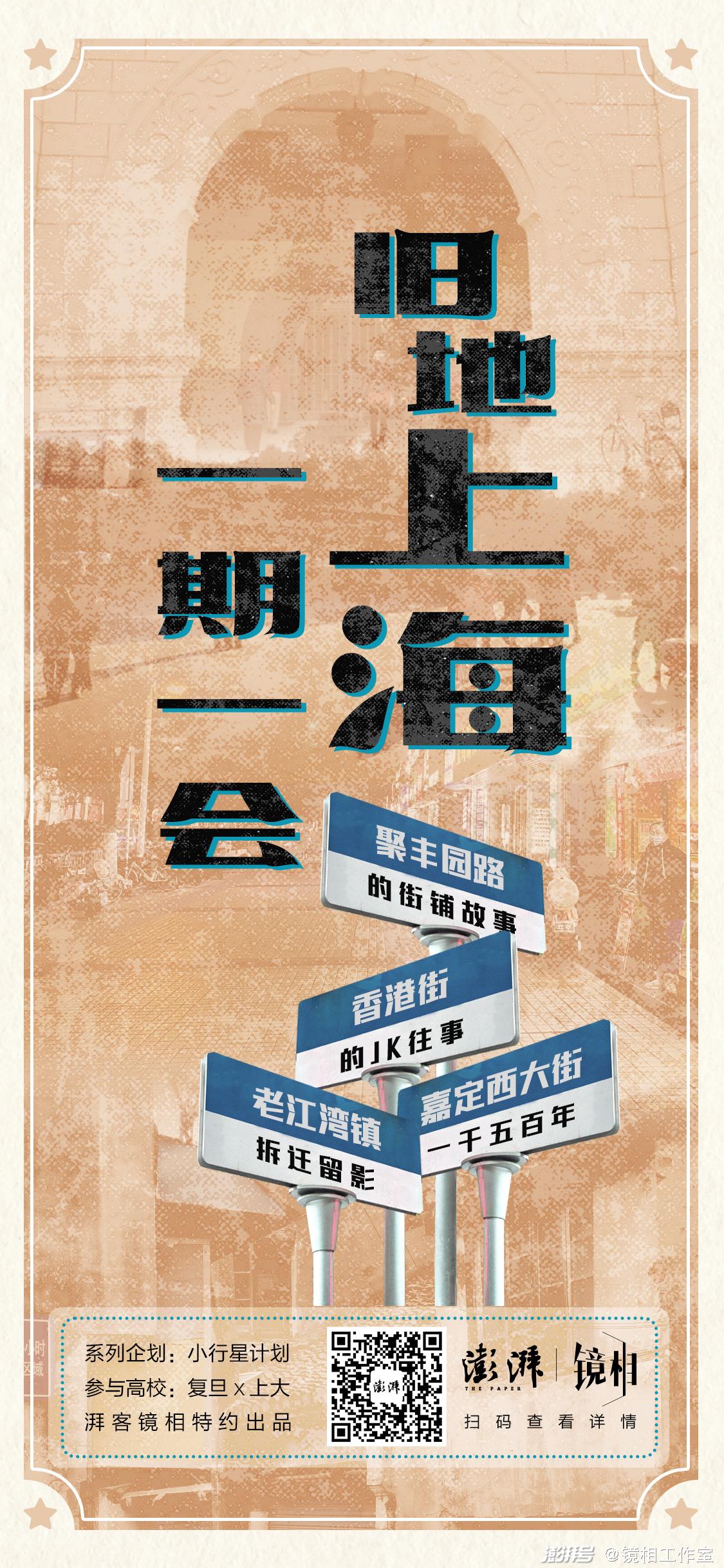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wèn)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