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巴黎聲明是否勾畫出了一個“能夠信靠”的歐洲
2017年10月7日,十位包括政治家和律師在內的歐洲保守派知識分子聯名,以九種文字發表了一份題為《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聲明。這份聲明是這些人5月間在巴黎舉行聚談的成果。(下稱“巴黎聲明”或“聲明”,詳見:http://thetrueeurope.eu/)
這十位作者著作等身。其中,法國政治理論家Philippe Beneton所著《默認的平等》(Equality by Default)、波蘭哲學家和政治家Ryszard Legutko所著《民主中的惡魔:自由社會中的極權主義誘惑》(The Demon in Democracy:Totalitarian Temptations in Free Societies)等已被翻譯成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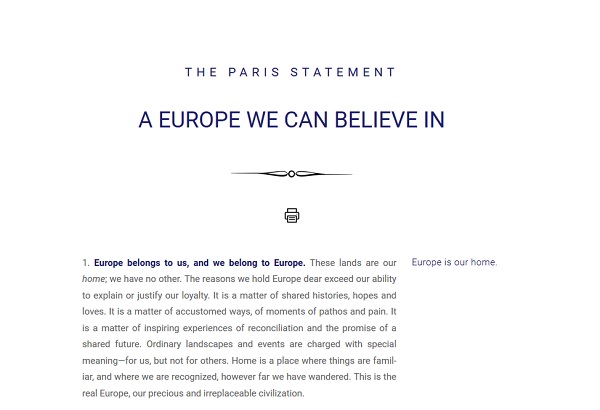
唯一的英國人Roger Scruton是傳統的保守主義哲學家,出版超過五十本書,較近的一本是2014年出版的《如何成為一名保守主義者》(How to Be a Conservative)。他就是親睹1968年5月法國學生暴動后開始擁抱保守主義。
這幾年來,歐盟的一些成員國面臨歐洲身份、國家主權、文化失調等問題,民族國家的意識高漲,本土主義(nativism,或作“排外主義”)在各國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10月中,奧地利保守的人民黨贏得大選,31歲的黨魁、現任外長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即將出任總理,這不過是最近的例子。
巴黎聲明就在這個本土主義高漲的潮流下推出。它并非一份學術性宣言,因此在西方知識界沒有很大的反響。它的目的很明顯,要為本土主義提供宗教與文化上的依據,和政治上的正當性。
這篇聲明在中國倒是引起了不少關注。澎湃新聞10月9日刊出了這份聲明的中文本,在國內引起了相當熱烈的討論。
巴黎聲明的內容
巴黎聲明開宗明義:“歐洲屬于我們,我們也屬于歐洲。”作者聲言,“虛假的歐洲”正在取代“真實的歐洲”。雖然聲明的作者們言之鑿鑿,然而他們所描繪“真實的歐洲”在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這兩個“歐洲”都是稻草人。它不過是“蓬萊仙島”(“真實的歐洲”)控訴“烏托邦”(“虛假的歐洲”)的精心杰作罷了。
首先,他們所謂“虛假的歐洲”到底是什么?
1.忽視與否定基督教的根基:假歐洲是歐洲文明的膺品,迷信進步,歧視歐洲的歷史和傳統,在自由和容忍的口號下一廂情愿地以為穆斯林會被世俗化。
2.多元主義的烏托邦:假歐洲是個超民族國家的帝國,建構在擬似宗教的普世主義情緒上。它滿懷偏見、迷信和無知,盲目地、強橫地追逐一個“仿造的基督王國”。
3.虛假的自由:片面、放縱的自由被倡導,造成家庭解體、個人主義泛濫、道德淪喪。這個自由的膺品用集體性的規則控制歐洲,用“政治正確”管制人們的言論,所要求的同質性和政治劃一是種暴政。
4.普世主義旗幟下的平等:利用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自我克制地接納所有族群。如果穆斯林移民不必融入歐洲文化,歐洲就成了穆斯林的殖民地。
5.不靠譜的全球化信念:歐盟集中權力的運作方式違反成員國的主權原則。市場應當為各社會共同體的利益服務,但經濟掛帥的跨國公司和巨無霸企業損壞了社會的凝聚力,泯滅各民族國家的個性。
所謂“真實的歐洲”到底是什么?
1.基督教的“精神帝國”是凝聚歐洲的基石:真實的歐洲建立在悠久的歷史、宗教、文化傳統上。它重視德性、家庭、個人尊嚴,但并無全面的神圣律法控制世俗社會。
2.真實的歐洲由民族國家共同體所組成:歐洲不是帝國,民族國家間互重,有各自傳統,不求劃一。人民彼此信任,積極參與共同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各政體雖然不一定民主,但歷史悠久,自我約束的法律體系和守法的公民是穩固歐洲的力量。縱有反叛和失敗,改革的愿望仍能讓歐洲不斷尋求更大的正義。
3.不妄自菲薄,去跟隨虛假的普世主義和多元價值: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傳統刺激歐洲追尋卓越,要用尊重歷史和傳統的理念來改革教育,不要被文化精英和巨型企業那種一致性的壓力所蠱惑。回歸家園,尊重民粹,才是真自由。
巴黎聲明中有兩個主旋律,一個是歐洲白人感受到穆斯林移民帶來的“生存危機”,另一個是歐洲傳統價值和其神圣性式微。后者加深了前者的嚴重性,使得歐洲失去抵抗的正當性。這兩個主旋律在36條聲明中不斷重復。
聲明背后的歐洲現實
在筆者的記憶里,1999年起已成為挪威居民的美國作家布魯斯·巴沃爾(Bruce Bawer)2006年出版的《當歐洲入睡時:激進伊斯蘭是如何從內部摧毀西方的》(While Europe Slept: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打響了歐洲恐穆情結的第一槍。
從歐洲大批雇用外來穆斯林工人開始,經過9·11事件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到敘利亞內戰和“伊斯蘭國”引發的浩劫,這一過程更中有大批穆斯林難民涌入歐洲。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6公布的數字,法國穆斯林人口已高達7.5%,德國是5.8%,英國是4.8%。
因著文化、宗教上格格不入和居住環境的隔離,加上極端伊斯蘭分子制造的暴恐事件,歐洲的穆斯林問題日趨嚴重。異質的伊斯蘭文化讓歐洲人深感“歐洲身份”受到威脅。
許多分析家認為,歐洲穆斯林的問題固然真實,但被本土主義者過分放大了。穆斯林問題需要政治上的解決方案,但是,如果用本土主義的思維來解決,將面對違反西方價值和民主傳統的危機。

本土主義的滋長
本土主義就滋長在這個環境中。本土主義者指責穆斯林要用子宮征服歐洲。他們最常用的口號就是:“你們不可以替代我們(歐洲身份)”。這與今年夏天一批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示威時所引用的口號相同,都是為了要維護白人的優勢地位。稱他們為“新右翼”(alt-right)可能更妥當。
本土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不同,一般媒體稱其為“極右”。其實,本土主義的有些主張并不很“右派”,例如管控企業。本土主義綁架了保守主義這塊牌子,本質上與美國的“美國優先”相似,都是戴上“保守主義”面具的白人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反穆斯林、反難民的理念和行動原先從法國開始,逐漸蔓延至歐洲各處。這個本土主義的勢力在歐洲發展很快。大家比較熟悉的領軍人物和黨派包括:英國脫歐派主要人物、曾經擔任英國獨立黨黨魁的奈杰爾·法拉奇(Nigel Farage)和曾經擔任倫敦市長的現任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黨魁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德國極右的“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組織(PEGIDA)和主張相近的“德國新選擇”黨(AfD)黨魁亞歷山大·高蘭(Alexander Gauland)。
在德國9月底舉行的大選中,AfD拿到第三高票(選民多集中在前東德地區)。這是六十年來德國第一次有本土派(排外派)進入國會。據報道,內部斗爭的結果是,AfD的立場越來越接近早年的納粹,而納粹式的相關主張在德國是非法的。
在匈牙利,這種排外氣焰甚至已經波及猶太人,匈牙利主政的黨派到處張貼反猶廣告。
其實,在歐洲政壇上,反對穆斯林最悠久的大約是荷蘭極右翼的自由黨黨魁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對荷蘭日漸增加的穆斯林,威爾德斯感到極度不滿。他說自己并不憎惡穆斯林,但認為問題出在“半本古蘭經”。
在十年前對荷蘭國會發表的一次演講中,他說:“伊斯蘭是放在歐洲的特洛伊木馬。如果我們現在不去制止伊斯蘭化,歐拉伯及荷拉伯只是早晚的事。一個世紀前,荷蘭有大約50個穆斯林,到今天已經將近有100萬穆斯林。……我們正走向歐洲及荷蘭文明的終結。”
2016年7月,威爾德斯被邀請到推舉特朗普為總統候選人的共和黨大會致辭。推動英國脫歐的法拉奇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介紹威爾德斯是“西方文明的希望”!他的黨派雖然在荷蘭今年大選中表現得并不理想,但他的影響力仍然很大。
這股“歐洲身份”的憤怒浪潮雖是針對移民政策,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歐洲經濟失調、工作機會缺乏的刺激。本土派反對歐盟,反對跨國公司,反對科技的突飛猛進。
在經濟失調的現實下,本土的失聯群眾日益增多。他們深感自己被那批不露面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們所壓制。那批遠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所在地)的“建制派”手握“政治正確”和歐盟團結的大棒,令這批失聯人感覺在公共領域和政治上失聲了。他們認為,歐盟秉持帝國思維,是個失敗的政府,因而他們要把權力從精英,從建制派那里奪回到“人民”的手里。
《紐約時報》10月19號刊發的一篇評論《民主可以種下自我毀滅的種子》(Democracy Can Plant the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中提到斯坦福大學政治學系教授Anna Grzymala-Busse的憂慮。對當下流行的本土主義,她認為,“有個標準的專制民粹主義的模板,從匈牙利起家,被波蘭和土耳其忠實地采用:那就是控制打擊法院、媒體、教會、大學”。這個模版也被美國借用了。
本土主義者高調批評法院以及后面的法理,因為法治和民主帶來不便;他們不信任正式媒體,因為媒體批判稱,排外思想不符合民主、平等和人權的歐洲價值;他們反對那些同情難民的教會(天主教為主),認為后者助紂為虐;他們排斥大學,認為那是傳播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毒素”的溫床。
他們認為這類權威代表“虛假的歐洲”。他們要用民主的手段奪權,然后用非民主的方式統治。波蘭、匈牙利、土耳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Anna Grzymala-Busse更警告說,我們不能保證右翼民粹主義“不會轉變為法西斯和納粹的形式”。
《紐約時報雜志》10月12號的專欄文章《白人民族主義在毀滅西方》(White Nationalism Is Destroying the West)中,有一段話十分令人動容:
“白人民族主義在許多方面是極端伊斯蘭主義的鏡像。兩者都迷戀純粹主義形式的懷舊:一個懷念中世紀的伊斯蘭國家; 另一個懷念沒有被移民血緣污染的白人國家。”
這就是巴黎聲明背后本土主義的社會背景。該聲明期望塑立本土主義的正當性。
聲明的理念基礎
巴黎聲明借用“烏托邦”這個名詞表明,問題出在歐洲從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化思想。發布聲明的人士認為,基于普世主義和個人主義理念而形成的主張(人本的自由、平等、正義、容忍)代替了歐洲傳統的價值(公平、同情、憐憫、寬恕、和平、仁愛)。
這兩套價值的具體主張看似相同,實則不然。“烏托邦”帶來了《查理周刊》,帶來了男女平權,帶來了福利社會,但卻失去了傳統神圣性的支柱。這樣的歐洲缺乏處理穆斯林問題的上層道德建筑。筆者認為,聲明的作者把這個看作問題的核心。
回顧問題下面的暗流
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前國會共和黨參議員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天主教徒)2012年曾批評奧巴馬鼓勵人人上大學的言論,認為這是種“勢利眼”(snob)。他聲稱大學是傳播自由主義的溫床。
今年10月初,特朗普總統之子小唐納德·特朗普在阿拉巴馬州一所大學演講時嘲笑大學的文化,認為教授教給學生的是“仇恨宗教”,“仇恨國家”,“圣經是本仇恨的書”。
這類信息說明了本土主義者的共同心態:大學對基督教不友善,大學教育造成年輕人失去信仰。巴黎聲明則要改造教育。
今天大學里講述的是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所開創的“正義論”,傳布的是“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例如“平權”。大學里傳播著杜威、盧梭、休謨、洛克等人有關民主、教育和個人自由的理念。這些思想不但影響知識分子,更影響著歐洲的公眾論壇和歐洲的法理。
巴黎聲明意味著,這些人本的現代主義產物都與基督教背道而馳,雖然這些理念與歐洲知識界的精神面貌,以及歐洲的法律和政治理念息息相關。
一個顯然的問題就是,聲明中的看法是否真正符合基督教所傳遞的價值?是否真是“歐洲家園”的本貌?
歷史證明,單單建立在人本的自由主義和自然主義基礎上的世界觀,對人類文明的前途是個威脅。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雅各賓“恐怖統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然而,否認歐洲的法理和民主政治的主張是否就符合基督教的理念?
可以拿羅爾斯的“正義論”做個簡單范例,因為他的理論所建立的政治哲學深深影響了西方法律上的“正義觀”(雖然還在不斷被修正中)。他的理論也是本土派批評世俗“自由主義”所最常引用的范例。例如,巴黎聲明的作者之一Philippe Beneton那本《默認的平等》就在批評羅爾斯。
簡單說,羅爾斯“正義”理念建立在“公平”(fairness)的原則上,有些人認為,因為它沒有建立在上帝的主權上面,所以不符合基督教的傳統;法律應當建立在猶太法(十誡)的基礎上。
筆者懷疑,在一個多族群的文化現實下,用“上帝的主權”來定義公平、平等、正義這樣一些法律原則,這是否符合程序正義?是否能讓人信服?是否必要?真能滿足人類良知中對公平、平等和正義的訴求嗎?或者,這不過又是 “部落心態”(種族主義)的化妝,一種權力的應用?
筆者認為,用神學立場來批評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是一種范疇上的混淆。同樣地,十誡的原則雖然影響了西方的法理,但是要把十誡作為法理唯一的根基,那也是一種范疇上的混淆。
反思:歐洲因何而偉大?
筆者認為,聲明所要提振的基督教傳統價值是個“虛假的基督教”,是贗品的基督教,并沒有捕捉到基督教的真義。基督教的真義來自耶穌基督“登山寶訓”那種天國觀念。
基督教影響力逐漸式微,這是今天歐洲困境的根源。一個文化中如果失去了神圣性的東西,失去了絕對的真理,那么一切的追尋都變成神圣的了,因為沒有了不能搖動的權威。個人主義掛帥,多元價值觀被神圣化,這是必然的現象。聲明的作者們認識到這點。
然而,這個現象是個文化問題,不是政治所能解決的。更確切地說,這是個信仰的問題。上帝的主權和神圣性不再能凝聚歐洲的精神面貌。沒有了這個中心,一切的理念,包括正義、平等、自由就都成為新的神祗,它們被絕對化了。
解決之道并不是把神權傾注在法理之中,而是幫助歐洲人回歸“心靈的家園” ——基督教的信仰。回歸信仰也不僅是遵守一套教條,或是歸屬一個部落或社群,更不是挑起、深化,或是利用族群間的矛盾。
美國牧師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的主張和作為深具啟示意義。他設在紐約的教會關心底層民眾的就業和社會公義,關懷弱勢族群的權益和他們受教育的機會。
根據基督教“普遍恩典”的原則,多元社會的不同社群之間還是可以找到道德和價值上交集的。難道有族群認為“良善”、“憐憫”、“愛人”、“舍己”、“使人和平”這些是負面的名詞?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凱勒牧師聯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包括律師),期望推動與認可同性婚姻的人士對話,找到良性的交集,減少對抗。可惜,這個舉動在基督教界沒有得到很多共鳴,大家還是寧愿固守疆界(這樣比較安全)。這與特朗普總統所要建的“美麗的”高墻有何不同?
在公共領域,今天的問題往往就是走不出保護自我利益的“部落心態”(例如,白人中心的思維)所致。只有在誠懇尋求交集的過程中,愛心的能力才能顯明。
基督教不是用來撕裂族群的。它與“血緣”、“疆界”和“政治利益”無關。
巴黎聲明的作者們所期望的并非基督教會所信奉的上帝,而是個部落神。基督教會應當關懷的是如何愈合傷口,增進不同族群間的諒解,促成良性互動,在黑暗中給人希望。
那么,巴黎聲明是否勾畫出了一個“能夠信靠”的歐洲?基于本文分析,我們只能反問:能夠讓誰信靠?是讓排外的本土主義者信靠?還是讓一個真正符合基督教精神、有宏遠胸懷的歐洲信靠?歐洲的偉大,不僅僅在于硬件,在于疆界,在于膚色,更是在于軟件,在于人文的精神層面,這個層面恰恰講究同情、饒恕、謙卑、自省的美德。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