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譯者手記|司馬遷的竹簡世界戰勝了秦始皇的青銅世界
司馬遷對陣秦始皇,雖不似秦瓊戰呂布一樣無稽,但多少也會讓讀者詫異。美國學者侯格睿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為我們呈現了一副司馬遷與秦始皇爭奪世界的畫面:“兩個人參加了同一個比賽。他們都試圖通過重新排序歷史、命名和分類以及控制話語的基礎來定義世界。”在這場比賽中,秦始皇憑借強制和暴力,而司馬遷以道德重建作為管理國家和人類社會的基礎,借助《史記》贏得了比賽。他們爭奪的焦點是“定義世界”(在最初動筆翻譯此書時,我曾猶豫是否將書名翻譯為《定義中國》,而不是現在直譯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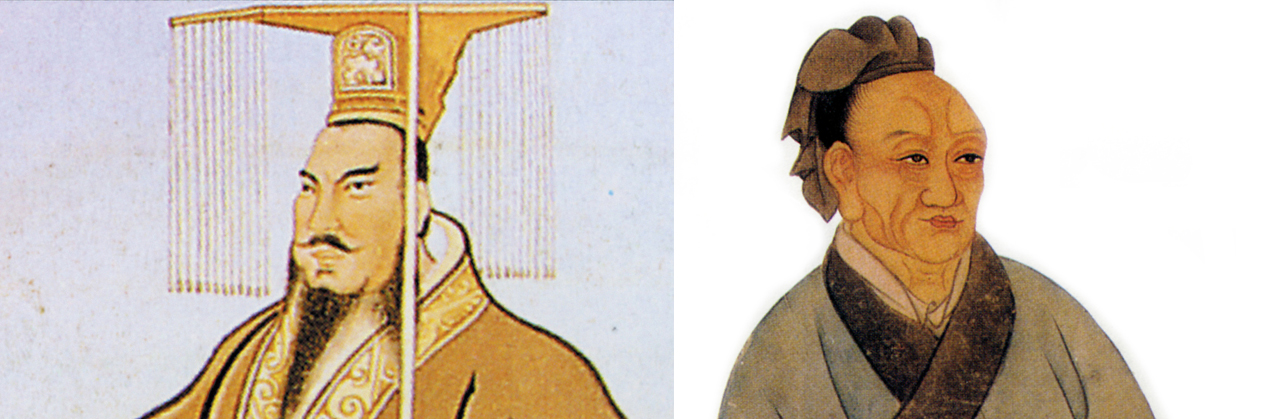
秦始皇與司馬遷
侯格睿是美國當代《史記》研究的重要學者之一,是北卡羅萊納大學艾塞維利分校的教授。1988年,侯格睿獲得耶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史記〉中的客觀性和解釋性問題》(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1999年,侯格睿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其關于《史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該書出版后在美國漢學界有較廣泛影響,被認為是與華茲生《司馬遷:中國偉大的歷史學家》、杜潤德《朦朧的鏡子:司馬遷筆下的矛盾與沖突》齊名的當代美國《史記》研究重要成果之一。該書的結構和各章的具體內容,侯格睿在“前言”中有簡要的概括,讀者可以容易地獲得全書的梗概,此處不贅述,我們將目光聚焦侯格睿組織的司馬遷與秦始皇的比賽上。
司馬遷與秦始皇的比賽,結果顯而易見:司馬遷的竹簡世界最終戰勝了秦始皇的青銅世界。侯格睿客觀地評判了這場比賽。秦始皇以武力建立了統一強大的帝國后,“試圖通過思想的重組使他自己的軍事征服合法化。他試圖改變人們理解世界的范疇,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夠定義世界”,即由他來定義理解和判斷世界的術語。“在重新命名的狂熱中,……一個新世界所有的東西都需要新的名字,它們都來自秦始皇。”不幸的是,司馬遷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消除了秦始皇的努力,“司馬遷寫了一段歷史,其意圖是點對點消除秦始皇的意識形態結構”。《史記》不是一部普通的歷史,因為它不僅講述了過去的故事,還試圖以象征的方式代表過去。就像秦始皇的陵墓一樣,《史記》是一個宇宙模型,一個寫在成千上萬片竹簡上的世界。事實上,《史記》是一個最終被證明勝利了的競爭模型。秦始皇試圖利用他的政治手段來塑造一個沒有歷史的新世界,但最終他被迫只是在司馬遷的《史記》所創造的宇宙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在這場不同尋常的比賽中,“歷史學家——而不是皇帝——是天地之間的真正聯系”,司馬遷的勝出也自然毫不意外。
為什么秦始皇、司馬遷都選擇以歷史作為定義中國的手段呢?侯格睿認為“祖先崇拜、儒學和官僚主義都促成了在中國文明中歷史思想的盛行”,“非常明顯的是,中國人不同尋常地將歷史作為身份認同和發展方向的源泉”。司馬遷不僅把《史記》作為他歷史觀的代表,“而且也以特別的字面方式代表了世界本身,通過它的存在,尋求改變那個世界”。作為客觀世界的模型,“司馬遷的歷史具有一種神奇的魔力,他用寫實的筆法記錄超越普通因果關系的具體話語和行動,旨在以這樣的記錄影響世界。《史記》就是用這樣具有表演感和儀式感的語言呈現這個世界。通過《史記》中的命名、歸類和排序,司馬遷給予宇宙本身一種特定的結構”。《史記》五體結構的靈活性發揮了重要功用,它允許司馬遷在不同主題下,靈活取舍史料,既保證了客觀性,又能發揮歷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司馬遷希望他的讀者在他的模型指引下自己去理解世界。侯格睿相信,讀者即使在模型的指引下找到了理解世界的妙門,也不會離開司馬遷,這也是司馬遷在中國歷史上鶴立雞群的原因所在。
司馬遷的世界模型能夠發揮功能,也離不開他獨特的敘事藝術和對人物傳記次序的巧妙編排,這也是模型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侯格睿通過《孔子世家》的敘事分析指出,司馬遷關于孔子一生的描述,折射的正是司馬遷自己的人生際遇。司馬遷通過描述圣人,也拉近了他與圣人的距離。遭遇坎坷,通過著述獲取后世的認可,這是孔子和司馬遷共同的命運。司馬遷認為這也是歷史的價值,通過歷史學家的努力,讓那些被埋沒的圣賢重新獲得應有的地位,這是天道。天道,不應被局限在一個短的歷史時期。伯夷叔齊雖然沒有善終,但他們被孔子從塵埃中打撈出來,被后世敬仰,這是天道。司馬遷自己正在遭受的坎坷,也必將通過《史記》得到應有的澄清。
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不惜承受腐刑這樣的奇恥大辱。他為何如此急迫地選擇這樣激烈的對抗呢?侯格睿也給出了他的分析:司馬遷發現,他的競爭對手秦始皇從驪山帝陵中復活了,他在漢武帝身上附體了。他們是如此相像,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轍,甚至兩人對長生不老的追求也不謀而合。司馬遷被恐懼包圍著,他一定要完成《史記》,完成世界模型的構建,否則,他與秦始皇的競爭,終將敗在秦始皇的孿生者手上。當他的描述突出了秦始皇和漢武帝之間的相似之處時,讀者認識到這兩個君主其實屬于同一類型的人。相同的批評適用于二者。《史記》的結構允許司馬遷將二者匹配。
侯格睿把《史記》五體結構下呈現的竹簡世界,與秦始皇陵中呈現的微縮的青銅世界作為兩個具象對比。秦始皇在地下復刻了自己統治的世界,他試圖借助祖先精神對后世的控制,通過地下這個微縮的帝國,萬世統治人間。可悲的是,隨著秦帝國的滅亡,秦始皇陵也遭到破壞,他的野心也被司馬遷曝光。而司馬遷的《史記》成為后世膜拜的經典,不斷被研究闡發,司馬遷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愿望被光大。侯格睿之所以將司馬遷的《史記》看作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秦始皇陵近乎模型的結構一定給了他頗多靈感。過去的研究成果對《史記》五體結構之功能也有足夠關注,但鮮有將其上升到客觀世界模型的層面,嚴謹的中國學者更不會將《史記》與秦始皇陵類比,這些給侯格睿留下了足夠的發揮空間。
侯格睿發現了司馬遷的野心,司馬遷害怕漢武帝重建秦始皇的世界,不惜承受腐刑完成了《史記》。司馬遷將秦始皇拉回了他試圖否定的歷史序列中,接受歷史的評價;他通過全面記載漢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貶的敘事手法,將漢武帝置于秦始皇評價體系之下,完成了竹簡世界體系的構建。中國文化中,“野心”不是一個褒義詞,鮮有學者將這個詞用在司馬遷身上,侯格睿很仰慕司馬遷,把他看作孔子一樣的圣人(美國學者杜潤德在《朦朧的鏡子:司馬遷筆下的矛盾與沖突》中甚至將司馬遷稱作“孔子二世”),他認為司馬遷寫作《史記》,有征服歷史的野心,并無貶義。在他看來,司馬遷不僅戰勝了秦始皇,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了孔子關于道德世界的創建,而且塑造了秦始皇和孔子在歷史中的形象。司馬遷以這樣一種體面的方式,結束了與秦始皇的競爭。
《史記》是百科全書式著作,任何一個緯度的解讀都有其合理性,侯格睿從“正名”角度切入,把司馬遷的著史看作他與秦始皇爭奪古代中國的定義權,讓人耳目一新。在侯格睿看來,孔子、司馬遷借助道德教化改變世界,他們實現歷史道德教化的手段,就是“正名”,司馬遷通過《史記》構建了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通過這個模型,將歷史的道德教化功能發揮到極致。較之于《春秋》,《史記》龐大的結構,五體之間的配合,本身就有寓意,什么樣的人入本紀,什么樣的人入世家,在史料取舍、排列及敘事手法上有足夠的空間,使司馬遷能夠盡情發揮。它建構的客觀世界的模型,不僅反映客觀世界,幫助司馬遷戰勝了秦始皇,贏得古代中國的命名權,它也是司馬遷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工具。
侯格睿相信,司馬遷通過《史記》理解世界、改變世界,他希望他的讀者—那些能真正讀懂他著作的人,能和他一起在《史記》所構建的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中,找到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司馬遷選擇了“遁形”,讀者在一個看不見的向導的指引下,與司馬遷共同探尋古代中國,并從中獲得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能力。司馬遷通過《史記》構建了一個開放的微觀模型,并讓模型獲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史記》之所以成為經典,成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鑰匙,這是根本原因之一。《史記》傳世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歷代關于《史記》之注釋、選本及研究汗牛充棟,特別是20世紀以降,海內外關于《史記》的專著及論文更是蔚為大觀,侯格睿作為漢學家,對《史記》這樣一部中國古代經典有如此宏觀之概括,確實值得欽佩,這也是激勵我動筆翻譯的最大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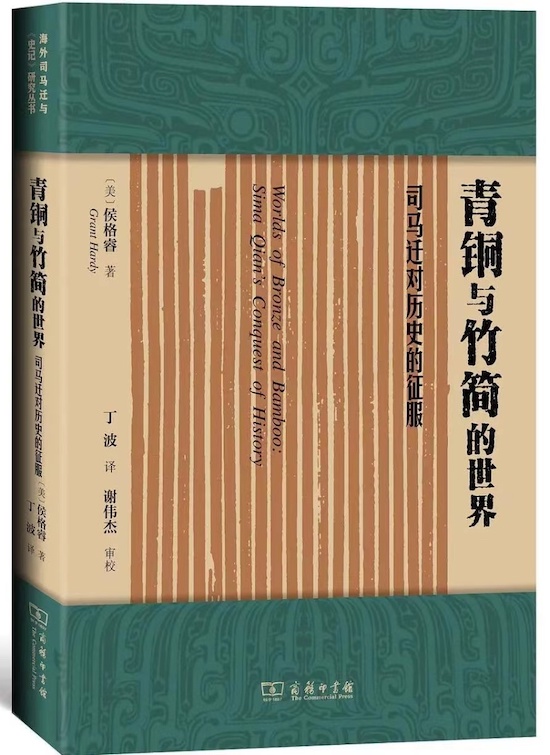
(本文摘自侯格睿(Grant Hardy)著《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丁波譯、謝偉杰審校,商務印書館,2022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本文為該書譯后記,有刪節,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