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5年了,它依舊是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沒有南明史,就沒有完整的明史、清史。沒有顧誠的《南明史》,就沒有完整的南明史。”
1997年,明史大家顧誠耗盡十余年心血,遍尋數百部史籍寫就的《南明史》出版。
25年來,這部榮獲中國國家圖書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的著作,始終代表著“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時至今日,對于想了解明清史的讀者而言,顧誠《南明史》仍然是不可不讀的存在。
2022年,經歷兩次絕版的《南明史》終于再版。重新厘清文字,糾正舊版數十處錯誤,這部堪稱傳奇的《南明史》絕版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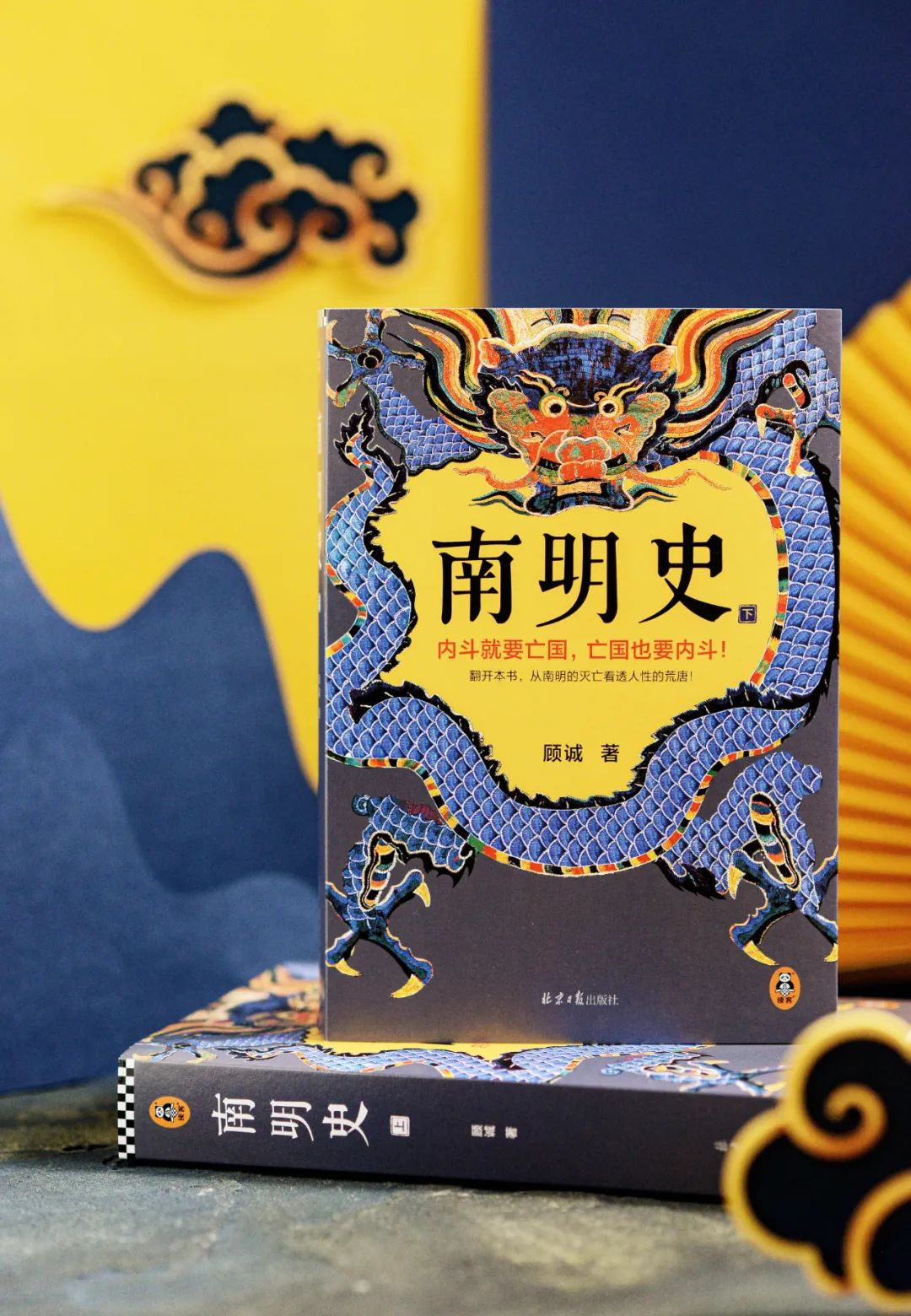
2022版《南明史》
文丨郭曄旻
01
“文章不寫一字空”的史料考據
顧誠(1934-2003)蜚聲學界,一生卻只出過兩本專著,《南明史》就是其中之一。
這本書雖然不屬于“原始史料”,但其對史料的考證之多之精,在同類著作——謝國楨的《南明史略》(1957)、美國史家司徒琳(L.A.Struve)的《南明史》(1984)、南炳文的《南明史》(1992)——里可謂是首屈一指。
在上世紀80、90年代古籍數字化遠未普及的條件下,此書直接引用的地方志達200多部,從東北、西北到東南、西南,縣志、府志、州志、省志應有盡有。未引用但查閱過的地方志數更是數倍過于此數。
如顧誠先生曾在云南昆明停留一月有余,在云南博物館和省圖書館內遍閱館藏的地方志和相關典籍,細讀并摘錄地方志一百多部,而《南明史》書中引用的卻只是其中23部,可證其勞動量投入之大。
甚至為了對讀者進一步負責,顧誠還在書中提醒,所引用的史料大多出自其個人的抄錄,盡管“在摘錄時經過核對,力求準確,也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誤。”
除地方志外,一些珍貴的史料也是顧誠先生在圖書館里首次發現或加以引用。《南明史》書中引用的其他古代典籍和第一檔案館、各博物館收藏的檔案材料達300余部,其中不少為海內外所罕見。以在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發現的《天念錄》為例,從書名看,這本書同南明歷史似乎毫無任何聯系。但實際上,此書作者是清初武將柳同春。此人根據親身經歷,在書中記載了順治五年(1649)南昌守臣金聲桓、王得仁“反清復明”,柳同春化裝出逃,向清軍報信,南昌城破經過的珍貴歷史。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顧誠先生在全面、系統發掘史料的同時,還認真進行審核、辯偽和考訂,訂正了許多史書記載的訛誤。
比如,著名的明清史專家孟森,曾經根據清初遺民查繼佐(金庸在小說《鹿鼎記》里提到過此人)撰寫的《罪惟錄》第22卷的《韓主附記》的記載,斷定南明在人們熟知的弘光(朱由崧)、隆武(朱聿鍵)、永歷(朱由榔)三帝以外,還有一個“韓主”,稱“定武帝”。由于孟森在學術界的影響,這一說法一度流傳很廣,就連權威性的《辭海》里也曾記錄了一個長達十八年(1646-1663)的“定武”年號,并歸之為南明“韓王”所有。
而顧誠在《南明史》里,則利用眾多南明史籍和清初檔案的資料進行排比考訂,指出查繼佐在清初搜羅史料不易,辨別不清,誤信訛傳本不足怪。“根本沒有什么年號定武的韓主”。這就厘清了查繼佐撰寫的《罪惟錄》據不可靠的傳聞,在南明歷史中增添了一個韓王定武政權而對后世研究南明史事所造成的混亂。

2022版《南明史》
也正是因為《南明史》在史料考據上的近乎無懈可擊,另一位當代明清史專家,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的何齡修(1933-2018)斷言,“任何治史者只要涉及南明史,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這本書(《南明史》)的觀點,都不能不讀它,對它所理清的史實,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接受”。
即使是史學理念與顧誠完全相悖的李治亭(《吳三桂大傳》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認“作為明清史研究者,我觀《南明史》,為其精湛的史實考辨,細密之論證所折服”。此外,顧誠之后,多年未有類似篇幅的南明史學著作顯世,恐怕也是諸人亦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嘆吧。
02
新見迭出的獨特史觀
當然,《南明史》絕非在簡單地堆砌史料(“無一字無出處”),實際上這本書也體現了顧誠本人的史觀。
書名里的“南明”指的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上吊煤山(今景山)之后,大明宗室與官員在中國南方相繼成立的幾個政權,主要包括福王弘光帝朱由崧、魯王監國朱以海、唐王隆武帝朱聿鍵與紹武帝朱聿鐭以及桂王永歷帝朱由榔等。
傳統學界一般以弘光帝繼統(1644年6月)和以永歷帝敗亡(1662年6月)的時間作為“南明史”的上下限。但《南明史》的做法顯然與之不同,它將“南明”的歷史定義為從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之變”寫起至康熙三年(1664)著名的“夔東十三家”抗清基地在茅麓山戰役中覆滅為止的二十年左右。

《南明史》的歷史為什么要從李自成起義軍進北京說起呢?在顧誠看來,“這是因為朝廷雖然覆亡,但明朝仍然控制著江南半壁江山”。如果堅持以朱由崧在南京登基作為南明的開始,而將之前幾個月沒有擁立皇帝的時間排除在南明史之外,“就會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難以自圓其說”: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繼統在同年閨六月;隆武帝被擒殺在1646年八月,永歷帝繼統在同年十月,其間都有一兩個月的帝位空缺。既然“國統”三絕不等于南明史三絕,那上限提前到明朝北廷的覆滅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做法。
如果說,《南明史》對南明歷史上限的處理做法顯得合情合理的話,將其下限定在1664年就很難不引發爭論了。
永歷帝被吳三桂從緬甸帶回昆明絞死,向來被看成南明史的終結。當然,在此之后,各地反清勢力仍然打著“永歷”年號。是不是可以以“永歷”這個年號的存續作為南明史的下限呢——比如據有臺灣島的鄭氏三代(鄭成功、鄭經、鄭克塽)就一直將永歷紀年用到1683年清廷統一臺灣。在顧誠看來,由于鄭經參與了“三藩之亂”,而“三藩之亂”的始作俑者吳三桂又明明白白地自行稱帝曰“周”,將臺灣鄭氏置于南明史之內就顯得不合適了。
這個理由當然有其說服力,比如朝鮮王朝民間一直將年號用到“崇禎二百年”乃至更晚,今人自然也沒有理由把明朝的歷史拉長到19世紀。問題在于,《南明史》為什么要將南明歷史的句號劃在知名度不太高的“茅麓山戰役”呢?
這正是顧誠本人明清史觀的集中體現:“基本上是以大順軍余部、大西軍余部、‘海寇’鄭成功等民眾抗清斗爭為主線,而不是以南明幾個朱家朝廷(弘光、隆武、魯監國、紹武和永歷)的興衰為中心”。正因如此,在某種意義上讀者甚至可以將《南明史》視為顧誠的另一部著作《明末農民戰爭史》的“續篇”。絕非巧合的現象是,姚雪垠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同樣以李來亨(李自成侄兒李過的養子)在茅麓山戰役犧牲為結尾。由此可見“夔東十三家”與明末農民戰爭的“一脈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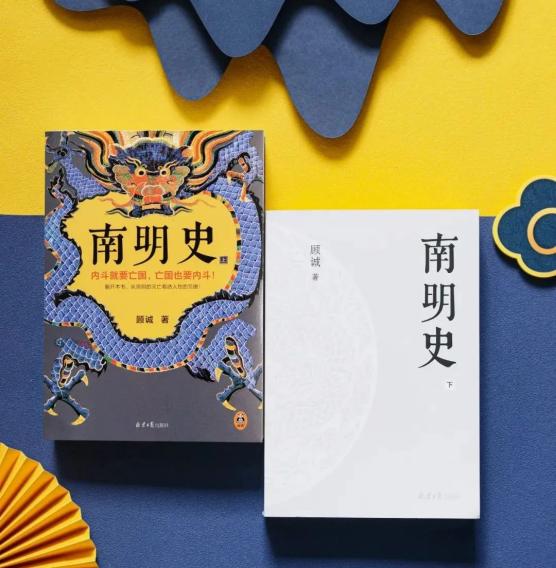
2022版《南明史》
在《南明史》里,顧誠也不認為南明的抗清斗爭屬于單純的殘明腐朽勢力同新興的清王朝進行較量,之所為“稱之為南明,是因為以崇禎帝朱由檢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業已覆亡,這段時期的戰斗要在南方展開,又是在復興明朝的旗幟下進行,而弘光、隆武、魯監國、永歷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僅此而已。
對此,學界并未取得共識。李治亭就認為,這是“給予明清史諸多重大問題以不公正地評價,將80年代以來所取得的某些共識重新給翻了過去”,“按‘武裝抗清運動’終始時間界定南明史,顯然不正確”,“不過是蕭一山式的“民族革命”論的翻版。”學界爭議自然是見仁見智。但也正是由于“夔東十三家”的覆滅在永歷帝敗死之后,《南明史》為此平添了一個章節的內容,對于讀者而言,又何樂而不為呢?
03
打破傳統認知的史論
與史觀引起的爭論類似,《南明史》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與傳統看法有著相當的出入。
對此似乎也不難理解:明清之際的歷史有其特殊性,作為勝利者的清朝統治者為了塑造自身的“正統”形象,一手修書(《明史》、《四庫全書》),一手毀書、禁書(“文字獄”),結果就是諸多抗清人物的形象不免有所歪曲。在這方面,《南明史》所做的工作,就是“正本清源”。
比如南明弘光政權的核心人物史可法,《明史》里一面說他“忠義奮發”,一面又說“蓋明祚傾移,固非區區一二人之所能挽也”。這其實就是欲抑先揚,用來制造清朝“天命所歸”的結論。
但《南明史》則指出,“漢族各派抗清勢力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結果被滿族上層人士“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
而就史可法而言,顧誠在羅列史實后指出,“作為政治家,他(指史可法)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
這就打破了傳統認識里史可法“孤臣無力回天”的形象,而讓他承擔起了弘光政權迅速在清軍南進里滅亡的歷史責任。當然,對于史可法,《南明史》也沒有全盤否定,“一是他居官廉潔勤慎,二是在最后關頭寧死不屈”,尤其是史可法在揚州堅守至最后一刻的氣節是永遠值得后人尊敬和宣揚的。
可以說,考據、史觀與史論,已經幫助《南明史》躋身“經典”之列。2011年,光明日報出版社曾經重版這部顧誠先生的代表作。頗有些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出版參考》在《新聞播報》欄目為之所配的新聞標題赫然寫著:為真史學“衛道”《南明史》新版亮相。盡管時間又過去了十多年,這個結論在今天的“讀客”版《南明史》上依然也是適用的。

◆ 豆瓣9.3分神作,每個“不可不讀”的歷史書單上都有《南明史》。
◆ 內斗就要亡國,亡國也要內斗!從南明的滅亡,看透人性的荒唐。
◆ 明史大家顧誠代表作,耗盡10多年心血,遍尋600余部史籍,同類著作無出其右者。
◆ 榮獲中國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明清史研究程碑式重要作品。
◆ 小說般活潑生動,連印刷廠的校對工人也讀得津津有味兒。
◆ 出版25周年,重新厘清文字,糾正原版數十處錯誤,絕版重來
沒有南明史,就沒有完整的明史、清史。沒有顧誠的《南明史》,就沒有完整的南明史。
——葛劍雄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教授
《南明史》是一部貨真價實的學術著作,但寫得深入淺出,不僅為明史研究的同行所欣賞,而且具有一定歷史知識的普通讀者也能讀懂。據說連印刷廠的校對工人也讀得津津有味兒,這是很值得玩味的現象。
——郭小凌 原首都博物館館長,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它當然不是填補空白之作,但卻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為止所達到的最高水平。
——何齡修 明清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顧誠先生并不滿足于“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而是志在創新和突破,力求解開一個個歷史謎團,探明歷史事實之真相,闡述社會發展之規律。因此,他對搜集到的資料,都下功夫逐一進行認真的審核、辨析和考證,做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此為基礎,運用唯物史觀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論證,進而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
——陳梧桐 明史專家,原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民族史研究所長
所謂“十年磨一劍”,所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已不足以形容本書的研著過程……顧先生受老校長陳垣前輩“竭澤而漁”之教誨,他雖然并未說他的南明史研究做到了這一點,但至少他在這一領域的同仁中最接近這一點則是無疑的。
——秦暉 著名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原標題:《25年了,它依舊是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