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繪理學演進史——讀何俊《從經學到理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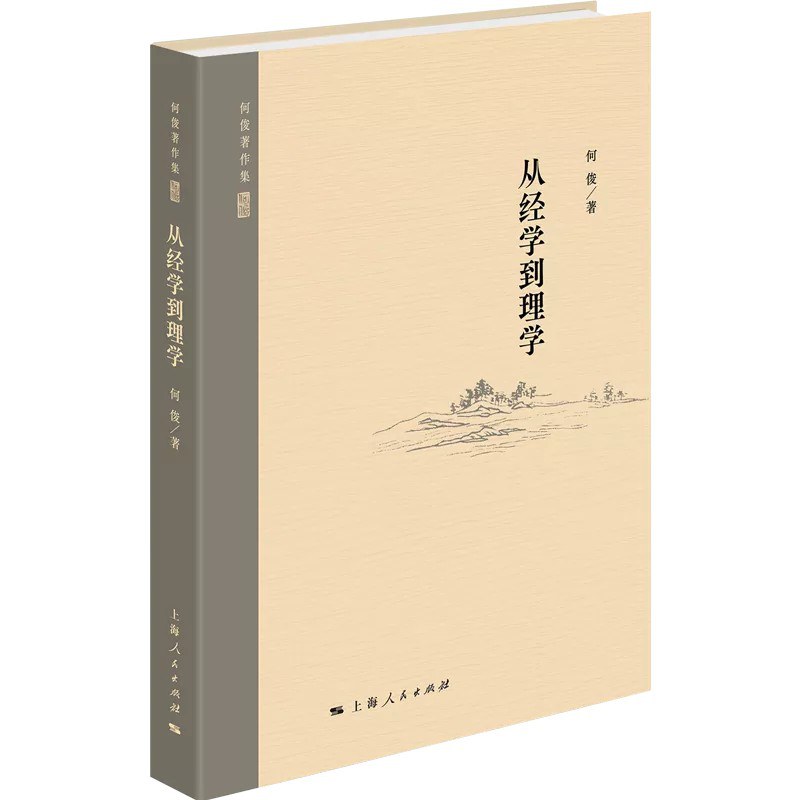
《從經學到理學》,何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凡學皆貴求新,理學亦不例外。盡管近四十年來,理學一直是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研究中最受學者關注、成績也最為突出的領域之一,但就理學史的研究范式來說,卻一直保持著其固有的特征。時至今日,學者們仍深受朱熹《伊洛淵源錄》所開創的理學史研究范式的影響,紛紛以理學代表性人物及其學派作為理學演進的核心線索,繪就理學發展演進的基本圖景。而隨著經學研究的復蘇與理學研究的日益推進,部分學者開始意識到,以往的大部分理學史著作,不僅在人物和學派選擇上過于傾向程朱一派,而且在理學演進脈絡的梳理上亦是重“流”而不重“源”,即對理學中的“學術明星”(如程、朱、陸、王)及其后學的研究已然推進到相當精密的程度,而對漢唐經學是如何蛻變為宋明理學這一關鍵性的問題卻缺乏深入研究,不利于呈現儒學的連續性與整體性。在如此情形下,理學史的寫作該如何跳出程朱“道統論”的束縛,以恢復理學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又該如何兼顧“源”與“流”,以呈現理學從經學中轉出的原因及其具體過程呢?欲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就必然需要對理學的演進脈絡進行反思與重繪。[1]而何俊教授的新著《從經學到理學》,[2]正是這樣一部試圖“重繪理學演進史”的精心之作。
《從經學到理學》采取“序曲—正篇—尾聲”的謀篇布局原則,全書共分為十章,總計26.5萬字。該書開創了“以經著為中心”的研究范式,不僅全方位、立體式地重繪了理學從經學中轉出的發展歷程,打撈出理學演進過程中的諸多歷史細節,還系統地分析了理學與經學之間關聯與區別,對創新理學的研究范式、構建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重構范式:呈現以經著為中心的理學演進史
自南宋以來,理學史的寫作便一直方興未艾,相關著作可謂汗牛充棟。與其他學科的研究范式常隨世運之轉移而改變不同,理學史的研究范式在數百年間卻未曾經過根本性的變革。在《從經學到理學》一書的引言中,作者鮮明地指出了這一點:“縱觀南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元代《宋史·道學傳》、明末清初《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以降,直至當下,不難看到,以人物為對象、以學派為歸趣,構成了宋明理學最基本的研究范式。”[3]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以人物為對象、以學派為歸趣”的研究范式將目光過度地聚焦于理學代表性人物及其學派譜系的建構,而對漢唐經學蛻變為宋明理學的原因與進程缺乏深入研究,讓理學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僅戕害了儒學的連續性與完整性,還淡化了“宋明儒學的系統結構、內在關系及其思想展開”[4];而且,由于后世學者受到程朱“道統論”的深刻影響,故而在人物與學派的選擇上往往唯程朱之見是瞻,亦不能呈現理學的多樣性與復雜性。鑒于既有研究范式所存在的問題,作者特開辟了“以經著為中心”的研究范式,試圖為讀者重新繪制從中唐到清初的理學發展演進史。
為何要開創“以經著為中心”的研究范式?因為作者通過對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的知識觀念進行梳理與分析后發現,“由于經與經學在傳統知識譜系中的首要地位,經的性質與經學的特征始終左右著整個傳統知識系統的方向”[5]。理學承接于漢唐經學之后,只是從先秦一路奔涌而來的儒學之河的一個河段。并且,“就知識形態的宋明理學的實際展開而言,無論是誰,也無論是那一派,所有的思想傳承與創新,無不圍繞著‘六經’這一儒家傳統經典系統的詮釋,以及‘四書’這一新經典系統的建立與闡明而完成”。[6]這意味著,理學發展演進的核心線索不是圍繞理學代表人物而建構的學派譜系,而是儒者們為了解決現實問題不斷用新的方法、從新的角度對“六經”進行的抉發與闡釋。換句話說,理學發展的問題意識、路徑與要義都蘊含在理學家們闡釋“六經”與“四書”的著述之中。所以,只有“返歸以經典系統為核心對象”,才能“通過經典而聚焦于宋明儒學的整體性認識,同時也以經典來涵蓋更多的參與者”,[7]才能真正把握理學發展演進的真實歷史脈絡。需要說明的是,通過聚焦理學家的經著來研究宋明理學,顧炎武的《五經同異》[8]與馬一浮編纂的《群經統類》[9]已開其先。尤其是馬一浮編纂的《群經統類》,跳出了前儒“以人物為對象、以學派為歸趣”的范式,“力圖通過經典而聚焦于宋明儒學的整體性認識”,[10]直接啟迪了作者“以經著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提出。
然而,理學家們流傳下來的經學著作數以千計,“以經著為中心”的研究范式該如何付諸實踐呢?在馬一浮編纂的《群經統類》目錄的啟發下,作者發掘出了一條極為巧妙的切入路徑。這條切入路徑之所以堪稱“巧妙”,在于其具備以下兩個方面的優點。
第一,這條切入路徑在化繁為簡的同時,既確保了經學體系的完整性,又與理學的演進過程基本相符,體現出歷史的真實性。前文已述,理學家們的經學著作數量繁多,即便是經馬一浮先生刪汰后的《群經統類》目錄,亦涵括了八類共五十余種經著,[11]體量亦屬可觀。作者經過慎重考慮,挑選了包括“五經”“四書”以及《孝經》在內的七大類共九部代表性著作作為專題研究對象,涵蓋了理學家們經學詮釋的主要范圍。而且,作者對這七大類經著的研究嚴格按照《春秋》《書》《易》《禮》《詩》《孝經》“四書”的順序在書中依次呈現,不僅囊括了整個理學的演進過程,還與漢唐經學蛻變為宋明理學的實際步驟大體一致,描繪出真實的理學演進脈絡。[12]
第二,作者所選取的經著均處于理學從經學中轉出的關鍵節點,它們具有“坐標軸”的作用,能夠準確地標示出理學演進過程中的問題意識與發展軌跡。如《春秋》類,作者選取了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該書匯聚了啖助新《春秋》學派的主要思想,曾扮演“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13]的重要角色。再如《易》類,作者著重對程頤的《周易程氏傳》和王宗傳的《童溪易傳》進行了深入分析。程頤的《周易程氏傳》自不待言,它不僅是“儒理易”形成的標志,也是易學實現理學化的標志。而王宗傳的《童溪易傳》則揭開了宋人“以心性說《易》”[14]的序幕,恰好構成從《周易程氏傳》到《楊氏易傳》的中間環節。[15]又如《禮》類,作者并沒有選擇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等盛名之作,而是選擇了敖繼公的《儀禮集說》,因為它體現了“理學發展到成熟時期的基于分析的批判的知識考古”[16]精神,與清代盛行的考據學風遙相呼應。除了上述舉例的經著外,作者在《書》類、《詩》類、《孝經》類、“四書”類中所選取的經著亦莫不具備“察勢觀風”的作用。而且,作者在對經著進行專題研析時,不僅會著重探討經著本身所體現出來的理學演變特點,往往還會考鏡其詮釋源流、揭示其后續影響。
這樣,在“以經著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摶結下,《從經學到理學》一書就如同一部由多個精心拍攝的單元所組成的電影。分而觀之,每一章都勾勒了某一經逐步實現理學化的發展軌跡;合而論之,全書所有章節又能夠實現有機融合,共同呈現出從漢唐經學蛻變為宋明理學的整個演進過程。
二、闡微訣疑:打撈理學演進過程中的具體細節
葛兆光曾指出,發掘各種文獻,打撈歷史細節,恢復過去的圖景,是專業歷史學者的作用。[17]作為一部對理學演進的歷史圖景進行反思與重繪的著作,建構“以經著為中心”的研究范式,無疑能夠為整個研究提供堅韌的骨架。但如果想要賦予這一研究以豐滿的血肉,則必然需要作者從歷史的河床中盡可能地打撈出理學演進的具體細節。對前人未曾關注或討論不充分的關鍵性問題進行闡微訣疑,是打撈歷史細節的重要途徑。因此,在《從經學到理學》一書中,作者秉承著“問題驅動”的撰作原則,每一章都圍繞著一個前人未遑深論的問題而展開。伴隨著問題的解決,被該問題遮蔽的歷史細節自然而然地就展現在讀者面前。下面,筆者將略舉幾例予以說明。
例如,理學發展過程中的政、學關系一直為學界所熱議。但是,學者們極少論及的是,當理學家的思想從江湖進入廟堂成為國家的普遍理念之后,其思想本身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從經學到理學》的第四章中,作者特意選取胡瑗的《洪范口義》作為切入點,對湖學進入廟堂的內在機理及其盛衰軌跡進行細致分析,以此管窺“宋明理學與政治權力發生正向關系時所帶來的的問題”。[18]作者發現,胡瑗在《洪范口義》中表達了其政治哲學的根本目標,即“建用皇極”,“完全使人為的政治能夠達到自然的五行相和不相侵,實現天人合一的理想政治”。[19]要實現這一目標,其基本要求在于“行實”,即要經世致用、服務于民生。同時,在《洪范口義》中,胡瑗還對“師”表達了極度推崇,為儒者進入權力世界開辟了新的路徑。值得注意的是,胡瑗一生最大的成就正是在為“師”上。他在蘇、湖地區講學二十余年,立經義、治事二齋,培養了大批重視“行實”的人才。慶歷年間,胡瑗一手開創的“蘇、湖教法”成為“太學法”,“湖學”一舉從鄉野躍入廟堂,成為國家的普遍理念。但是,在權力世界中獲得榮盛的“湖學”,隨即就面臨著來自權力世界內外的其他思想系統如新學、蜀學的強烈挑戰,其自身的批判性與創造性亦在權力的捆綁下全然喪失。所以,到了南宋時期,曾經甲于東南的“湖學”已然無跡可尋。通過對“湖學”盛衰軌跡的梳理,作者表證出“宋代理學在其展開中因與政治的勾連而呈現出的盛衰悖論”,[20]為研究宋代思想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系開辟出全新的向度。
又如,關于宋代易學理學化的發展與延異過程,不少學者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已經有了研究,但鮮有學者對該過程進行統貫性的梳理。而在《從經學到理學》的第五章中,作者重點選取了程頤的《周易程氏傳》、王宗傳的《童溪易傳》進行專題分析,還附論了葉適的《習學記言序目》,為讀者們清晰地勾勒出易學轉出理學及其分別向“心”與“事”延異的發展軌跡。作者指出,程頤將前人分別運用的辭、變、象、占四種易學詮釋路徑統合為一體,構成其傳釋《周易》的特殊的四維模式。在這一四維模式中,“辭”以一統三,占據最大的權重。這樣,“當程頤選擇辭的維度,并論證辭的維度足以涵攝變、象、占時,他的思想指向是努力超越具體的物象與人事而建構普遍性的理”。[21]由此,程頤完成了理學從易學中轉出的理論構筑。然而,程頤易學中的“理”是人對于所見物象的聚合,人只能認識“理”,而不能決定“理”。所以,當后來的學者從其他維度展開對易學之“理”的傳釋時,理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進而呈現出對程頤所完成的理學化易學的延異。[22]如王宗傳雖然深受程頤影響,但以人之性替代了天之理,將“其本在我”作為理論與實踐的歸宿,最終導致“心的功能覆蓋了理的存在”,“為洛學轉為心學已基本打開了道路”;[23]而葉適堅持將理落實到仁義禮智信諸德等生活現象層面,“以呈現事的卦象為根本”,[24]則以《周易》“構成了永嘉事功學的理論依據”。[25]
在其余的諸章中,作者莫不以問題為引領,以打撈歷史細節、恢復理學演進的圖景為指向。如在《從經學到理學》的第六章中,作者細致分析了敖繼公的《儀禮集說》對禮儀復原的追求與敖氏“刪、存、補”鄭注賈疏再“附以己見”的撰著過程,展現了敖繼公基于分析的批判的知識考古精神與整合漢宋學的治學取向,[26]以非凡的學術敏感性清理出理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長期為人忽視的面向。而在該書的第九章中,作者特意選取了朱熹“四書學”著作中不為人所重的《論孟精義》作為研究對象,從文本、語言、身體、仁義、存養、辨學等六個視角逐一考察了朱熹對理學話語的形塑方式及過程,發前人未發之覆,為學界開展下一階段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知其同而存其異:理學與經學之關系的再思考
欲重繪理學從經學中轉出的歷史,必然還需要解決一個問題:理學與經學存在怎樣的關系?在《從經學到理學》一書中,作者對這一問題亦進行了系統的討論。
眾所周知,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降,經學一直扮演著“吾國人之大憲章”[27]的重要角色。因此,在清社頹毀之前,即便歷代學者對理學的地位與性質問題有過諸多討論,但均未對理學歸屬于經學這一前提予以否定。辛亥鼎革之后,在西學“圍城”的局勢下,經學被視為“非科學之統系”,[28]旋即遭廢。而理學則因其細密的理論建構與富于哲學思辨的精神而“被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與理論形態而直接納入現代研究中”。[29]這樣,經學與理學的概念及其形象在民國以降的學人眼中必然出現“視差”,[30]并由此導致當今學界對經學與理學之間的關系問題產生了以下幾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理學是哲學而不是經學,兩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如梁任公在其代表作之一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理學即哲學也,實應離經學而為一獨立學科。”[31]這一觀點在后世頗有影響,如崔大華先生即認為,“就思想理論內容考校,宋代理學與經學并不相同,理學是從經學義理中超越出來的、具有更高的‘理’之哲學本體觀念和獨特理論論題的一個新的儒學理論形態”。[32]
第二種觀點恰與梁任公的觀點相反。不少學者認為理學是經學在獨特歷史條件下發展出來的一種新類型,從整體的角度來說,理學即經學也。如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將兩千多年的儒學發展史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其中經學時代涵蓋從西漢至清末的二千余年時間,理學只是經學發展脈絡中的一個階段。[33]姜廣輝先生進一步指出,理學就是經學的“理學化”,[34]是經學史上的一種特殊形態,兩者的關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35]
與上述兩種觀點不同,在《從經學到理學》一書中,作者始終秉承一種較為折中的觀點,即認為理學產生于尊經的年代,自然要使自身融入經學,兩者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關聯性;但無論從議題還是方法的角度,理學相對于經學來說,都展現出了新的特點,因此不可將經學與理學簡單等同。在作者之前,周予同先生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36]不過,周予同先生將經學視為“僵尸”,[37]表現出明顯的批判立場;而在作者眼中,經學是作為傳統中國的一種重要的學術思想形態而存在的,立場較為客觀。所以,作者雖然可能受到了周予同先生的啟發,但兩人的觀點因為出發點的不同已然是似是而實非。為了闡明自身的觀點,作者從以下兩個維度展開了論述。
首先,理學“不得已”誕生于尊經的時代,[38]所以從思想淵源與經著形式的維度來看,理學無疑體現出了對經學的一脈相承。作者指出,宋明理學是對先秦儒學的“再辟”,[39]其所有成就都源于“回歸經典的創新”。[40]這不僅是說,宋明理學的全部實際展開都是基于“六經”與“四書”的詮釋與闡明來實現的,[41]還意味著宋明理學的經著與語錄體著作“始終沒有溢出六經的整體性”,“這種整體性對于歷史中的儒者而言,幾乎是共同的不言而喻的知識與精神背景”。[42]在經著形式上,宋人經著與漢唐諸儒的經著亦無根本性的區別。如朱子的代表作《四書章句集注》在形式上即與漢唐注疏相近。朱子亦曾自謂:“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43]故而錢基博對朱子曾有如此評騭:“朱子為宋學大宗,而其解經則一依漢儒家法。”[44]
但是,從思想議題與本體建構的維度來看,“理學無疑擺脫了經學”。[45]先談思想議題的層面。理學雖然在形式上寄身于經典的傳釋,但其所熱衷討論的理、氣、心、性問題明顯是漢唐儒者所不曾重點關注的。更重要的是,理學家們在探討“性與天道”的過程中吸收了佛、道的思想資源,為漢唐經學的知識傳統注入了哲學的分析與批判思維,將整個儒學提升到新的思想高度。[46]而在本體建構層面,理學更是表現出了與漢唐經學迥然不同的性格。自程明道體貼出“天理”二字之后,[47]儒者們莫不將對“理”的追求作為自身思想體系的核心——“確認萬物存在的背后具有理據,闡明歷史表象的背后具有邏輯,這正是理學被標識為理學的根本原因”。[48]既然理學家們在思想議題與本體建構上均與漢唐諸儒存在明顯差別,那么當他們面對經典時,必然會體現出與前儒完全不同的心態與詮釋風格。此即四庫館臣所概括的:“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倶排斥以為不足信。”[49]
一言以蔽之,在作者眼中,理學與經學之間是既緊密聯系又存在著內在緊張的關系。乍一看,這一判識似乎略顯左支右絀,但這恰恰蘊含著作者的良苦用心。因為如果忽視了理學與經學之間一脈相承的關系,則理學研究與經學研究就會呈現出各分畛域、相互切割的局面,人為地造成儒學發展脈絡的斷裂;而如果忽視了理學的獨特性,則理學研究與經學研究必然混為一談、難以區分,既不利于理學研究的推進,亦不利于經學研究的復興。因此,只有“知其同而存其異”,既認識到“理學的創新并沒有造成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斷裂,而是在轉進中保持著延續”,[50]又承認理學有其自身的思想特點,方能開拓出足夠的空間,讓理學研究與經學研究都得到充分的展開。
綜上所述,作者在深刻判識經學與理學之關系的基礎上,通過新創“以經著為中心”的研究范式、精心打撈理學從經學中轉出的歷史細節,重新繪就了理學從中晚唐到清前期的演進軌跡。但是,作者的苦心孤詣實不止于此。理學奮進的過程,不僅展現出理學的多樣性與豐富性,還為今人謀求國學新知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即“一切從時代的問題出發,回看既有的經典及其釋傳的歷史,以及在生活世界中的展開,從而致力于用今天乃至指向未來的新的知識形態來闡揚具有根源性的價值”,[51]最終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誠然,創始者難為工,本書無論是在研究范式的構建還是理學與經學關系的判識上,肯定都還存在著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但是這種超越具體人物而從整體系統來重繪理學演進史的嘗試,無疑能為當下的理學研究乃至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帶來全新的氣息。
2021年10月7日初稿
2022年3月改于疫情中
注釋:
[1] 事實上,陳來、張學智、楊國榮、陳衛平、朱漢民、向世陵、何俊等學者于2018年在吳震擔任首席專家的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的開題論證會上就已經對“重寫理學史”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具體內容見陳來:《<宋明理學史新編>將是對宋明理學研究的高水平總結性呈現》,《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張學智:《關于重寫宋明理學史的幾點看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楊國榮:《走進思想的深處——關于重寫宋明理學史的若干思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陳衛平:《理學與后理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朱漢民:《照著儒學學統重寫理學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向世陵:《理學、儒學、經學與陽明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何俊:《宋明理學研究方法與內容的創新期待》,《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2]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3]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2頁。
[4]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1頁。
[5]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7頁。
[6]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2頁。
[7]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1頁。
[8] 在《從理學到經學》的第十章,作者對顧炎武的《五經同異》有深入的分析。詳見《從經學到理學》,第331-347頁。
[9] 關于馬一浮先生秉承“六藝論”編纂《群經統類》的論述,具體見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46-72頁。
[10]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1頁。
[11]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頁。
[12] 作者在書中指出:“理學由經學中轉出,大致起于《春秋》,進而開展于《書》《易》《禮》《詩》,最后歸于《孝經》與‘四書’”。筆者同意作者所作的這一判斷。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5頁。
[13] (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13頁。
[14]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84頁。
[15]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51頁。
[16]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223頁。
[17] 葛兆光:《從細微處看大關節——讀張佳<圖像、觀念與儀俗:元明時代的族群文化變遷>》,《讀書》,2021年第9期。
[18]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33頁。
[19]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16頁。
[20]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31頁。
[21]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49頁。
[22]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46-147頁。
[23]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60頁。
[24]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85頁。
[25]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184頁。
[26]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220-223頁。
[27] 李源澄:《論經學之范圍性質及治經之途徑》,《李源澄著作集(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7頁。
[28]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42頁。
[29]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頁。
[30] 桑兵:《理學與經學的關聯及分別》,《史學月刊》,2020年第5期。
[3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9頁。
[32] 崔大華:《超越經學——對理學形成的一個支點的考察》,《中州學刊》,1996年第2期。
[3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三松堂全集》第3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0-379頁。
[34] 姜廣輝:《“宋學”“理學”與“理學化經學”》,《哲學研究》,2007年第9期。
[35] 姜廣輝:《論宋明理學與經學的關系》,《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
[36] 周予同先生指出,理學在經學權威鼎盛之際,不得已“托庇于經學”,但它作為哲學,實與經學“各自異趣”。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150頁。
[37] 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第604頁。
[38]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48頁。
[39] 此系化用陳淳語。見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8頁。
[40]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頁。
[41] 參見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69頁。
[42]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70頁。
[43]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12頁。
[44] 錢基博:《四書解題及其讀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頁。
[45]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48頁。
[46]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8頁。
[47] 程明道曾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見(宋)程顥,(宋)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24頁。
[48]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8頁。
[49]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頁。
[50]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8頁。
[51] 何俊:《從經學到理學》,第350頁。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