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林奕含逝世五周年 | 我們依然在談女性主義
原創 王梆 花城
林奕含(1991.3.16—2017.4.27)逝世五周年
我們依然在談女性主義
她與她的精神對決
——文學中的厭女現象
王梆
?導讀
女性被女性責難的歷史,是從她降生在父權家庭那天開始的;
女性遭遇的第二重同性責難,來自她那以師之名的“靈魂導師”;
內在性厭女和支撐它的權力機構,以及它們共同砌筑的觀念壁壘,千百年來,深深地影響著女性之間的關系。
本文來自《花城》2022年第2期
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購買《花城》新刊。
一
女性被女性責難的歷史,是從她降生在父權家庭那天開始的。第一個對她指手畫腳的人,往往不是她的父親,而是她那滿口女德的母親。因此“女兒與母親的精神對決”,便成了三次婦女解放運動以來,西方現當代女性文學作品的一大傳統。
奧康納就十分擅長描寫母女沖突,在她的短篇小說《啟示錄》中,她為傳統的母親們訂制了一個“瑪麗式”的女兒,一個體形肥胖,臉色發藍,到處長痘的“討債鬼”,脾氣不好,性格也乖張叛逆。那是青春痘被診斷為“精神錯亂”、女孩十幾歲就得結婚生子、白種窮人被當作“白色垃圾”,黑人依然是“黑鬼”的20世紀60年代——尤其在奧康納自幼成長的美國南方。有過漫長蓄奴史、天主教清教主義和保守勢力深植其中的南方,蠻愚和偏見遲遲不肯退潮,每當刮風下雨,勢必卷土而來。奧康納當然不愿和它們同流合污,所以她要將“罪的現實感”一點一點地,從盤根錯節的舊秩序底下挖出來。瑪麗的反叛和壞脾氣,是她試圖引爆《啟示錄》(《圣經》的最后一個章節)的爆破點。

她要借瑪麗,給那個社會當頭一棒,尤其要給瑪麗的母親,一個活在膚淺和偏見之中的女人,當頭一棒。為了顯得更有殺傷力,奧康納沒有過多描寫母女之間的戰爭,而是借另一個女人——外表優雅討喜,滿腹歧視勢利的杜爾賓夫人,完成了一場象征性的弒母:女孩(瑪麗)啪地合上書,將它朝杜爾賓夫人的腦袋上砸去,然后大跨步穿過等候室,沖到杜爾賓夫人面前,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滾回地獄去,你這頭老疣豬!”女孩吼道。
即使在健康條件極差、無法離開母親獨立生活的情況下,奧康納也不會疏于描寫母女的對決。比如這段:霍普韋爾夫人總會有事沒事,當著客人的面,羞辱她那看起來死氣沉沉的女兒:“你要是不能顯得高興點,那我干脆就不要你了。”(《善良的鄉下人》)每當如此,她那常年患有心臟病,架著一條假肢走路的女兒赫爾加,就會從羸弱的身體里拔出刀子:“你要不要我隨便,我反正就在這里。”奧康納發表的三十一個短篇小說里,至少有六個,描繪的是“霍普韋爾夫人式”的母親,以及“赫爾加式”的女兒。

現實中的奧康納,也承認自己是一個“讓母親難以招架的”女兒,在給友人的信中,她寫道:“如果我母親在我閱讀的時候闖進來說,太晚了,快把燈關了!我就會豎起手指,板起面孔說,才不呢,光是無限永恒的,關不掉。你大可閉上你的眼睛。”
奧康納的母親雷吉娜,44歲便成了寡婦,一個人打理著550英畝的奶制品農場和一大群奶牛,獨自倒騰木材生意,還飼養著一匹波蘭群島矮馬。奧康納25歲那年患了紅斑狼瘡(它亦是置她父親于死地的兇殘殺手),不得不從紐約返回佐治亞州。為了讓女兒行動方便,雷吉娜旋即調整了家居布局。沒有母親的悉心照料,很難說奧康納會平安活過此后的十四年,更別說在和病魔斗爭的日子里,寫下了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短篇小說作品。盡管如此,奧康納還是忍不住,借她筆下的人物,狠狠地抨擊了她那一代人的母親——不管如何強悍,她們大部分是厭女文化浸透過的產物。比如在《火中的圓圈》里,奧康納就不留情面地諷刺了一個叫“扣泊夫人”(Mrs. Cope。Cope在英文里,又有“對付”的意思)的女人:“她除草的樣子,看起來,就像這些草受了魔鬼的派遣,要來毀滅她的花園一樣。”

扣泊夫人不能忍受雜亂,因此她從小就被教導,那是女人的失職;她也不能忍受抱怨,她在唱詩班里學到的價值觀從來就是:“萬物明亮又美麗,無論大小,智慧又絕妙,因為都是神的創造。”[摘自《給孩子的唱詩》(Hymns for Little Children),1848年初版]所以每當有人談起疾病、磨難和死亡,她馬上就會拿起一套“輕巧討喜的陳詞濫調”掩蓋過去,盡管她自己其實正處在磨難的中心——厭女文化自上而下地包裹著她,周圍的男人每時每刻都在鄙視她,他們經過她的農場,就會嘲笑:“哇,扣泊夫人的農場里女人真特么多!”
奧康納的不少作品中,都能看到一個重復的圖案:即“強悍的母親被不知廉恥、巧言令色的陌生來客蠱惑,結果竟讓陌生來客把自己的女兒給拐走了”。可見,奧康納對傳統母親所奉行的女德和禮教,以及由此養成的腦回路,有多嗤之以鼻,以至于不得不通過各種“畸變”進行反抗——它們通常化身為她筆下那些古怪、不合群,亦(像她們的母親一樣)極度缺乏性經驗的女兒。這和伍爾夫早前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伍爾夫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里寫道:“女性在父權環境里生成的焦慮、羞恥和困惑,令她們在表達自身經驗時困難重重,所以在女性的書寫中,才會有如此眾多的畸變。我們應該接受畸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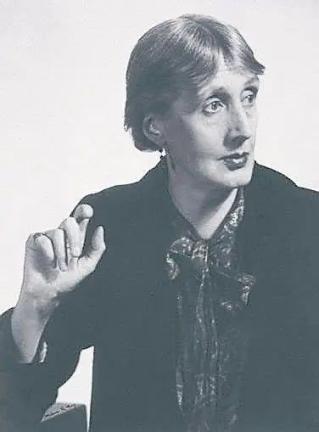
“畸變”也是母女關系打結的結果。英國作家詹妮特·溫特森在回憶自己的養母時譏諷道:“我的母親有兩副假牙。一副亞光,對付日常生活。一副拋光,只在良辰美景中才舍得拿出來佩戴。”[《當你可以正常時為什么要快樂》(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詹妮特的養母是一位嚴厲的清教徒,出于傳教目的,收養了詹妮特。然而自從得知女兒喜歡的人也是女生之后,她就把女兒趕出了家門。因為有這樣一個母親,詹妮特幾度想過自殺。整整兩年,母女之間沒說過一句話。突然,在某個圣誕前夕,詹妮特收到了母親寄來的一張卡片,上面只有兩行字:“這個圣誕你回家嗎?愛你,媽媽。”
不管母親有多頑固、保守,甚至比壓制她的父權社會還要厭女,真要和母親徹底決裂,對每一個女性來說,卻是難以想象的。喬治·艾略特談生命的啟示,她說:“生命是從混沌中醒來,愛上母親的臉那一刻開始的。”人類如此,動物如此,自然萬物無一不被這種天然的母性紐帶捆綁聯結。女兒,因其自身承襲著母親(作為女性)的經驗、女性的集體無意識,以及女性被壓抑的歷史,與母親的關系注定是難舍難分的。奧康納在讀大學時,幾乎每天都給母親寫信,和母親分享自己的生活,不時索要自己愛吃的“蛋黃醬”。詹妮特也在收到母親的圣誕卡片后,馬不停蹄地趕回了家。

當代心理學在探討母女關系的糾結點時,極大程度地引用了性別研究的成果。比如美國臨床心理咨詢師羅斯珂在自己的論著《母女的困惑》(The Mother-Daughter Puzzle)中,就提到了許多性別研究中也同樣顯性的現象:比如當女性的需要被否定,或無法付諸言語,也不能私下交流時,母女之間勢必就會為“哪一方的需要和訴求被對方率先領會”而展開爭奪。母親(像母親的母親)一樣無法教會女兒為自己的需要發聲,因為母親(在代際相傳)中,就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消音體。當代社會母女的最大沖突是:當母親喝令女兒回歸家庭,生兒育女,以顯示其教導有方,極盡母責時,女兒的需要往往是:“不,我要逃離。”
這是一種勢均力敵、兩敗俱傷的對決。因為母親不是紋絲不動的父親和其父權建制,母親是戴著母性光環出場的。母親那溫柔的魚尾紋和憂傷的下頜線,永遠是女兒的鏡像地帶。女兒的每一次出擊,都會強烈地反彈回來,刺傷自己。
波伏娃幾乎把這種刺傷寫絕了,這是她在母親臨終時寫下的句子:“世上沒有任何砝碼,可以稱量我此刻的刺痛。”[《一個非常輕松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

波伏娃的母親弗朗索瓦茲生于19世紀晚期,父親是一位富有的銀行家。她在教會學校里接受教育,長成了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一戰”后,她陷入了家道中落、入不敷出的境地。盡管如此,她依然固守成規,對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亦十分留戀和自覺,每時每刻都在茍延殘喘地維持著舊日的體面和優雅。然而,當她試圖將這套價值觀嫁接到女兒身上時,波伏娃的態度竟是“女人結婚生子是一種將自己賣給奴役制的選擇”(波伏娃語)。朗索瓦茲的失望和孤獨感,是不言而喻的。盡管暗地里,她可能也會嫉妒女兒的自由,尤其是想到自己從未獲得過那樣的自由。孤獨和執念,把她變成了一個強悍、霸道、不容置疑的女人,以至于在《一個非常輕松的死亡》中,波伏娃不得不用“一種既令人珍視又令人憎厭的相依為命”來形容她與母親的關系。
這種緊張的關系在弗朗索瓦茲即將被死神帶走的那一刻,才終于獲得了一絲緩解。彼時的弗朗索瓦茲七十八歲,全身上下被惡性毒瘤侵襲,波伏娃和妹妹輪流守在母親床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弗朗索瓦茲總算在女兒面前流露出(用波伏娃的話來說)“一絲最最輕微的贊同”。波伏娃隨后寫道:“讓我們內心震動不已的,是母親那絲輕微得不能再輕微的贊同。仿佛七十八歲的她,將重新走入生活的奇跡似的。”(《一個非常輕松的死亡》)

作者簡介
王梆,出版有電影文集《映城志》,數本短篇小說繪本集。電影劇作《夢籠》獲2011年紐約NYIFF獨立電影節最佳劇情片獎。作品曾發表于《天南》《中華文學選刊》《芙蓉》《香港文學》《長江文藝》等雜志,入選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大學《中國當代文學選集》,美國“文字無邊界”文學網站,2016年秋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故事新編”中國當代藝術展。非虛構系列《英國觀察》入選《收獲》2018年排行榜專家榜第六位,入圍2019年青年文學獎。
原標題:《林奕含逝世五周年 | 我們依然在談女性主義》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