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石一楓:文學的精神就是反內卷(下)
作為一個生在北京、長在部隊大院兒的“70后”作家,石一楓曾坦言自己深受老舍和王朔兩代“京味”作家的影響。因為與王朔相似的成長背景和語言風格,在很多場合,他都會被問到有關王朔的問題。
但石一楓并不介意,也不焦慮。在他看來,大家都在書寫各自所處的那個時代,都通過北京,去感受整個中國乃至世界變化著的世道人心。后來人繞不過老舍與王朔,那是因為人家確實寫得好,確實捕捉到了時代的“魂”。但是,王朔寫不了老舍那個時代,老舍也寫不了王朔那個時代,他自己也有身處其中的,有許多人和故事可講的時代。
于是,在2018年的《借命而生》、2020年的《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之后,石一楓又在他的文學版圖里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小說首發于《十月》長篇小說專號2021年第五期,剛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單行本。
如果非要用一句話概括,《漂洋過海來送你》講述了三戶人家“抱錯骨灰盒”的故事。一戶來自北京胡同,去世的那姓爺爺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一戶身處上層社會,去世的老太太是個老革命,但她很會賺錢的兒子帶著孫子去了美國;還有一戶是一個海外勞工,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自己的家鄉。那姓爺爺的孫子那豆和爺爺有著很深的感情,他無論如何也想換回爺爺的骨灰盒,于是漂洋過海去了美國,歷經種種,聽聞了另外兩個骨灰盒背后的故事,也終于讓逝去的人回到了他們要去的地方。
石一楓雖然一直在北京生活,但從沒住過胡同,工作后才得以在日常時光走進胡同人的生活空間。這是他第一次寫胡同里的北京人,寫傳統京味文學意義上的胡同生活。小說從2020年開始寫,這一次,他腦海中先冒出來的不是人物,也不是情節,而是一種傳統京味小說的敘述調子,或者說是一種情境與氣氛。
“北京的作家基本上還是有一種情結,愿意寫寫最傳統的老北京人,老舍時代的北京人。”近日,石一楓就新作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因篇幅關系,專訪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中,他談到了新作的由來與構想、京味小說的傳統與延續、中國家庭價值觀的“隔代遺傳”;在下篇中,他從自身寫作的變化談起他對這個時代的感受與發現,以及他的小說方法與文學觀。
此為下篇。

石一楓
在文學的世界里,體貼更多的人心
澎湃新聞:對這篇小說的敘事視角有什么考慮?似乎從《借命而生》開始,包括后來的《玫瑰開滿了麥子店》《漂洋過海來送你》都是用第三人稱展開敘事,《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等前作中常出現的那個帶有石一楓特質的觀察者消失了,這種寫法會要求你對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人物更體貼嗎?
石一楓:對。就我個人來說,我挺羨慕有的作家一上來就能寫第三人稱,而且寫得挺鮮活的,這可能還真是一種天分。然后我有一個特點,就是很長一段時間是通過“我”來敘事。我應該是屬于寫作時敘述者聲音相對強的作家,然后有一個“我”之后,小說會比較順暢,角度處理得也比較好。寫《世間已無陳金芳》和《地球之眼》的時候,我用的是“我”,甚至《漂洋過海來送你》之后我正在寫的新東西,又開始用“我”。我用“我”能夠寫得比較真切,敘事也更從容。
但是這樣有一個問題,這個“我”——有點文化的、游手好閑的小知識分子形象,說實在的能夠接觸到的社會面不是特別廣,如果老被這個人稱限制住,那么有很多人物是寫不了的,比如真正的底層,真正的勞動人民,或者說某些極端生活條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是寫不了的。所以這個時候就得用第三人稱,這對我個人來說還挺費勁的,就是說第三人稱怎么去體貼,不需要一個“我”的視角就能體貼到一個跟你完全不一樣的人物,這個還真是功夫。對于有的作家是天分,但對我可能更是一種功夫,得訓練,然后不斷地去體貼,去揣摩,才能達到。我覺得我可能年輕一點的時候還真不行,歲數大一點,三四十之后,能夠體貼更多的人了,也能更客觀地去看待生活。
當然,作家各有不同,你看王朔基本上沒寫過不是“我”的,都是“我”,但有的作家剛上來寫就是第三人稱,他的第三人稱寫得特別好,可你一看他這輩子沒寫過“我”,也就是說他寫別人特別好,寫自己反而有障礙。現在我覺得比較好的一點是我這兩種都還行,能夠切換,基本上寫一個第一人稱爽一把,然后再寫一個第三人稱的東西,接著又回到第一人稱,跳著來。

《玫瑰開滿了麥子店》
澎湃新聞:雖然這個小說的主線是那豆一家,但我覺得黃耶魯那一條線也寫得很有意思,一方面是咱們前面說的“隔輩親”耐人尋味,另一方面是我覺得黃耶魯比李牧光可愛了。你的小說經常寫到經濟事件,黃耶魯和《地球之眼》里的李牧光一樣被家人強行送去美國,都有一個發著不義之財的父親,但黃耶魯比李牧光多了不少無辜與可愛之處。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這是否也意味著,你對黃耶魯、李牧光這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
石一楓:對,他(指黃耶魯)其實比較無辜。之前寫完《地球之眼》我就反思了,有沒有寫得不夠的地方?就是把李牧光寫得有點簡單,寫成一個純粹的反面人物了。那這個人物一定是純反面的嗎?他身上有沒有更多的復雜性?我當時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所以這一次就希望盡可能地體貼每一個人。不能說身處一個不道德的環境里就一定是一個不道德的人,有時候他只是處境不道德,但這和人道德與否要分開看。還有像黃耶魯的爸爸,這個人物沒實際出場,如果出場的話我現在也會盡量去理解他,因為他的成長環境已經是“叢林法則”,那究竟是他這個人本身就壞,還是生存邏輯使他變成了這樣一個人,我覺得也是值得深究的。
至于黃耶魯,我倒是覺得本質上就挺無辜。這種家里發過不義之財的小孩,往往有一個特點,就是頭腦比較簡單,傻乎乎的,因為他的生活環境太好了。而且大家也要理解黃耶魯這種人,他有他的片面看法,比如他覺得美國不好中國好,是因為他在北京的物質生活超過了美國,但他只看到了北京奢華的那一面,只看到中國大城市奢華的那一面,他看不到別人的生活。所以從本質上說,他就是比較無辜,又目光短淺,是一個井底之蛙,只不過這個井底之蛙被扔到了美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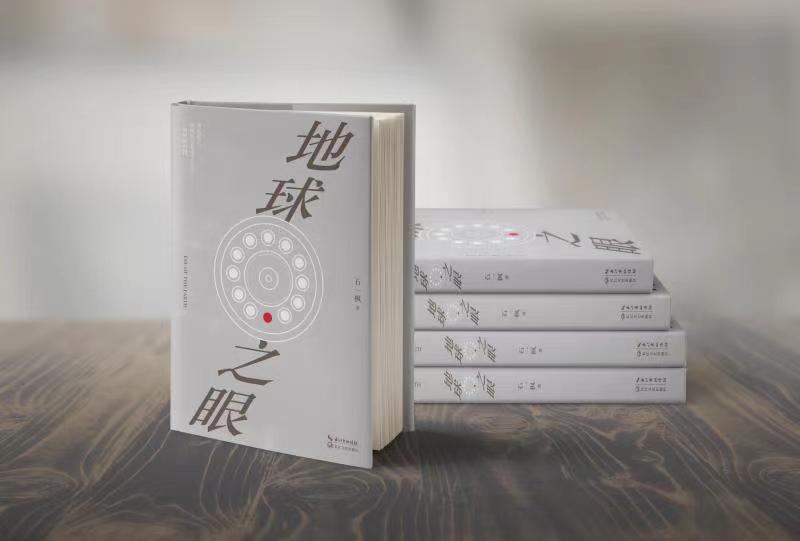
《地球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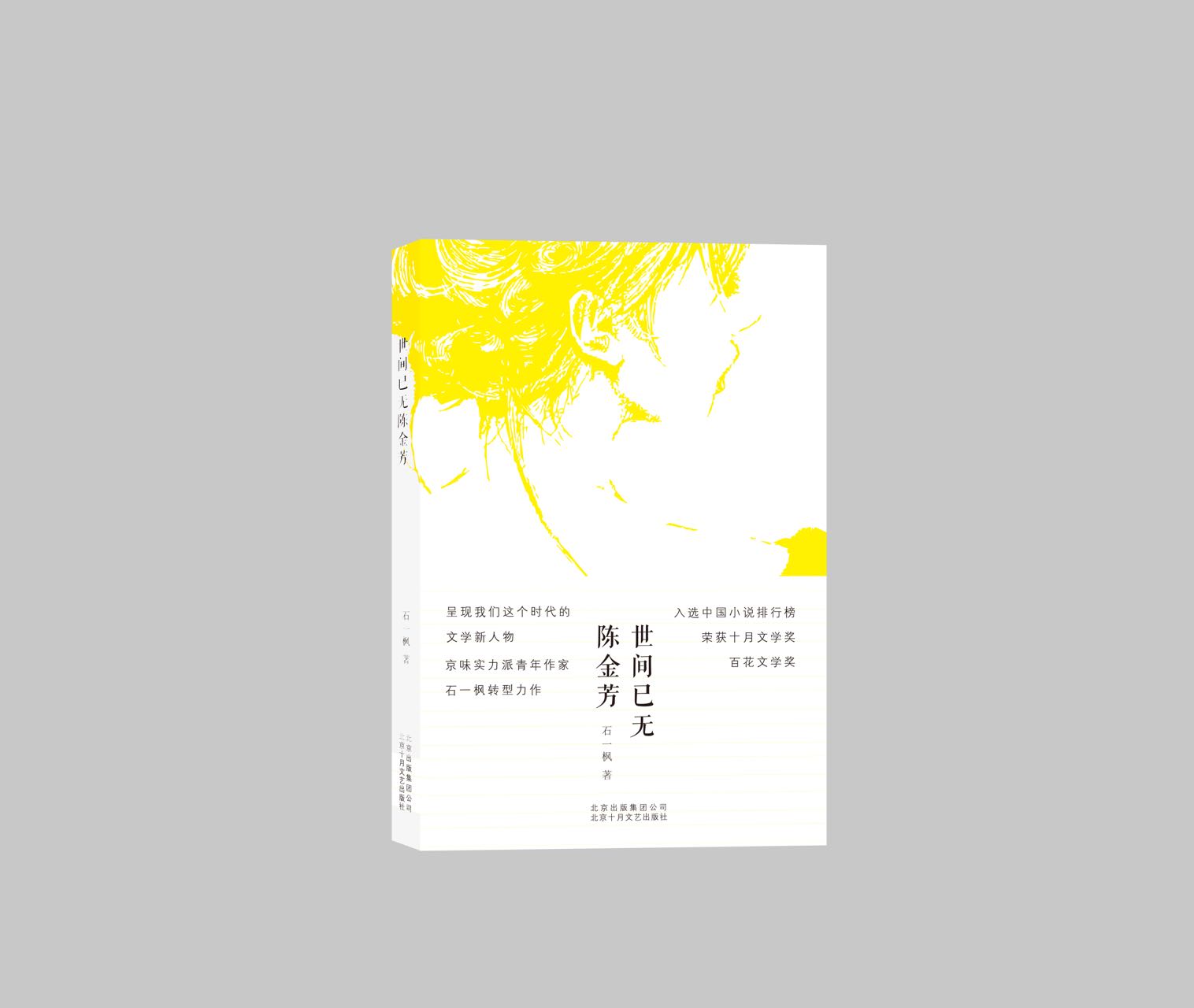
《世間已無陳金芳》
澎湃新聞:從黃耶魯這個名字也能感覺到他爸是一個很奉行“成功學”的人,你對“成功學”一直是有批判的?
石一楓:對,我堅決反對“成功學”,反內卷。文學的精神就得反內卷,都跟著內卷了還寫作干嘛呢?
澎湃新聞:說到反內卷,你這次小說的主人公是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他們習慣的是很閑很慢的生活,那他們如何面對內卷?
石一楓:他們比較悲劇,因為在現在內卷的游戲里,他們基本上是失敗了,被卷出去了。內卷的離心力把他們拋出去了。
澎湃新聞:從小說來看,那豆一家的職業都是酒店門童、司機、賣肉員這樣的。
石一楓:對。如果我們用內卷的標準來看所謂胡同居民,或者說來看每一個中國城市里都有的老居民,會發現他們的悠閑是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參加內卷的權利了。你要有資格,要受過高等教育,要有一技之長等等標準你才能跟別人去卷,但這些人都沒有大文化,沒有受過特別高的教育。這么說吧,他們除了在城市的核心地段有兩間破平房之外,他們在這個社會上一無所有。
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在城市不斷發展和擴張的過程中,一定會有一些人被拋出去,會被這個城市的主流生活給拋棄,那么這些人就是內卷的失敗者,或者說沒有參加內卷的資格。但是文學還會通過他們去看待世界,有時他們比內卷的成功者更能看到生活的意義。
澎湃新聞:這些人其實也令人心酸,好好生活著,也沒干啥壞事,以前還覺得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但突然間不是了。
石一楓:就是突然之間規則變了,標準變了。比如東北的工人是在一夜之間不再是主人,而北京的原住民也是這樣,以前北京就是我們家,但現在我要在我們家門口領低保,就是你突然被生活拋棄了。這是城市發展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可避免歸不可避免,不等于說我們寫作的時候就可以忽視他們。我覺得他們在文學的世界里,在寫作的倫理里,恰恰是舞臺的核心。
澎湃新聞:最近在看《人世間》,這部劇也是講東北的工人故事。
石一楓:是,最早的時候講“看完上海看東北”,就講的是中國沒有工業化的時候,只有兩個地方工業發達,就上海和東北。現在如果你在東北說自己是一個工人,人家一定認為你失業了。
作家如果是明星,寫出來的東西可能也可疑
澎湃新聞:你在生活中有什么愛好嗎?喜歡音樂吧?
石一楓:愛聽點音樂,看個電影,游戲也玩,比如塞爾達。我屬于那種什么都玩一點,但都不是特別精。比如我聽音樂,沒有像格非老師他們必須得用什么音響,然后音響還必須配個什么線,我沒到那個份上,就覺得哪個好聽多聽聽。看電影也是,咱也不懂鏡頭,就是看看熱鬧。反正是一般愛好者,只不過愛好多了點兒。
澎湃新聞:做文學編輯平日要看稿子,那工作之外的話,你會想看什么書呢?
石一楓:我是屬于工作內外看的東西差不多,因為興趣就在這兒,工作內是看小說,工作外也是看小說,就是看小說這事兒本身就是一興趣。
澎湃新聞:那在小說的選擇上呢?
石一楓:我比較喜歡看當下作家寫的當下的小說,經典咱反正也得看吧,但是我覺得差不多得了,沒必要非得一直追蹤外國大師。比如英國作家,看看狄更斯,看看蕭伯納,法國作家看看巴爾扎克,就行了。更有意義的事是中國正在寫作的,跟我差不多一個時代寫作的這些作家,不管年紀大的還是年輕小的,都比較重要,因為你跟人家干的是一個活兒,你們處理的是一個問題,盡管大家的寫作千奇百怪,差異很大,但是歸根結底處理的是一個問題,就是怎么寫中國的當代,怎么寫中國當下的社會和當下的國人。對于這個問題,國外的作家給你的借鑒不是直接的借鑒,直接的借鑒只能是你身邊。所以我更愿意看現在中國的寫作。
澎湃新聞:就你個人而言,你成長于1980—1990年代,經歷了文學最熱和文學開始落潮的年代,你認為文學在社會中理想的位置應該是怎樣的?
石一楓:過去覺得當作家挺棒的,等你當了作家之后,發現作家啥也不是。但我覺得挺好。其實我們得相對冷靜地看這個問題,因為如果作家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或者說是社會的明星,我倒很懷疑在那種狀態下作家能不能寫出比較好的東西。
我們作家,尤其我這樣的基本就是寫普通人的寫作,如果你迅速地成為不普通的人,那么這種寫作真誠不真誠?有效不有效?還能不能完成?我都比較懷疑。所以我倒覺得現在挺好,而且說實話咱們國家對作家真是挺好的,雖說不會有那么多人看你,但是有相對的保證和輔助,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做得都好,有些地方還挺重視的。
在我的理解中,作家就是諸多職業的一種,一個很普通的職業,沒有超越其他職業的意義,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把這個職業做好。同時這個職業也有一些高要求,說得泛泛一點,比如傳承人文精神,或者為人民鼓與呼,這也是這個職業應盡的義務。作家也好,記者也好,其實可能本質上都屬于這一類職業。所以我倒覺得不要希望自己像1980年代的作家一樣是全國人民的老師,我覺得那個狀態其實也不正常,當然可以說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但我真是覺得當時未見得是一個正常的狀態。正常的狀態就是一個普通的職業,你在其中盡好職業的義務。
而且,如果一個職業變成了一個不普通的職業,這個職業很有可能會碰到危機。比如現在的網紅,它不普通,它很可能會出現問題。經常是這樣,朝陽產業充斥著騙子,夕陽產業反而是穩穩當當,踏踏實實。
澎湃新聞:你的作品在專業批評家和普通讀者中都有很好的評價,在寫作的時候,你更多地考慮哪一種讀者的眼光?
石一楓:作家的愿望是大家都喜歡,但我甚至覺得沒有一個作家能夠實現這個理想。可能批評家里是有一些專家比較喜歡我這樣的寫作路數,然后讀者也是,但想做到和能做到的都是有落差的,我盡量彌補這個落差吧。我相信真是好的作品,應該是專家與普通讀者都叫好,我們不要總是拿讀者去反對專家,或者拿專家去反對讀者,真好的東西大家都喜歡。
澎湃新聞:你會有銷量方面的焦慮嗎?
石一楓:還行,焦慮可能也有,你看怎么比吧。比起真正的暢銷書作家,或者說通過寫作實現人生飛躍的作家,我肯定比不了,但是我還比較好的一點是基本靠寫作能夠正常地運轉下去,靠寫作支撐自己繼續寫作,這點就挺幸福了。而且咱們必須得承認,中國整個文學體制有一條比較好,雖然也有人說這不好那不好,但是它對于有寫作能力的人總是能夠給到一定的支持和幫助,從這點來說我倒沒有那么偏激。當然焦慮肯定也有,具體到經濟方面的焦慮,都是這山看著那山高,就是有了游艇我還會想想飛機呢,就讓人沒轍了。

《借命而生》
澎湃新聞:你曾說王安憶像19世紀巴黎的“書記官”巴爾扎克,你是否也想通過自己的寫作,做21世紀北京的“書記官”?
石一楓:那不一定,因為“書記官”這個概念指的是寫到更多的社會層面,寫到更多的社會人群。但是還有一點,你能不能在一個時代里提出一個新的或者獨樹一幟的價值觀,我覺得這一點也特別重要,應該說也是文學應盡的一個義務吧。
澎湃新聞:這是你追求的一個方向嗎?
石一楓:寫作的時候要考慮到。
澎湃新聞:很多人拿你跟王朔比,你對這個事兒是什么態度呢?在我自己的感覺里,你們倆有像的地方,比如貧嘴的時候,但我會覺得王朔是一個觀念性很強的人,你有觀念,但你會讓感受大于觀念,不知道這樣的表述準不準確?
石一楓:從這個角度來說,可能我跟老舍一樣,老舍就溫和一點。王朔的戰斗姿態非常強,老舍就相對溫和一些。我年輕的時候可能更欣賞王朔那樣的戰斗姿態,現在確實覺得要多體諒,然后多思考。跟王朔比的話,我覺得這沒有什么不正常的,因為寫北京生活的,你不可能繞開他,這說明人家了不起啊,是吧,你表現北京就不可能繞過老舍、王朔、劉恒他們這些人,一定會有人拿你跟他們比,我覺得沒有什么問題,而且我一點兒也不焦慮,因為這是文學本身的內在特質決定的,大家都是在寫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王朔寫不了老舍那個時代,老舍也寫不了王朔那個時代,而我觀察、寫作、生活的這個時代,跟他們天生就會有不同,所以不太有那種叫模仿的焦慮。
澎湃新聞:“京味”這兩個字本身就是帶有地域性的。你覺得帶有地域性的“京味”和作為一般漢語的普遍性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關系?
石一楓:這里面可能有一個語言審美,或者說是語言表述方面的地域不同。我們現代漢語的定義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所以北京話就是某種意義的普通話。我們北京的作家用普通話寫作是不需要翻譯的,直接就出來了。但是南方的作家需要翻譯,我就聽余華和蘇童他們說過,南方作家用普通話寫作是需要翻譯的,要先把自己的意思從方言翻譯過來,再寫下來。
哪個好?不好說。你不需要翻譯,那你的表達更自如一點兒,暢快一點兒,但你會發現往往經過翻譯的語言更準確,更凝練。這個翻譯的過程是起到作用的,多過了一遍腦子。還有一個,你把老舍和魯迅做比較,你會發現北京作家的京味語言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是表形,就是表述形態、描摹人物這方面特別好,寫動作、神態會寫得很好,但這樣的語言在思辨的時候是吃虧的,而魯迅用南方人的語言去表現思辨性的東西就會表現得特別好,各有優勢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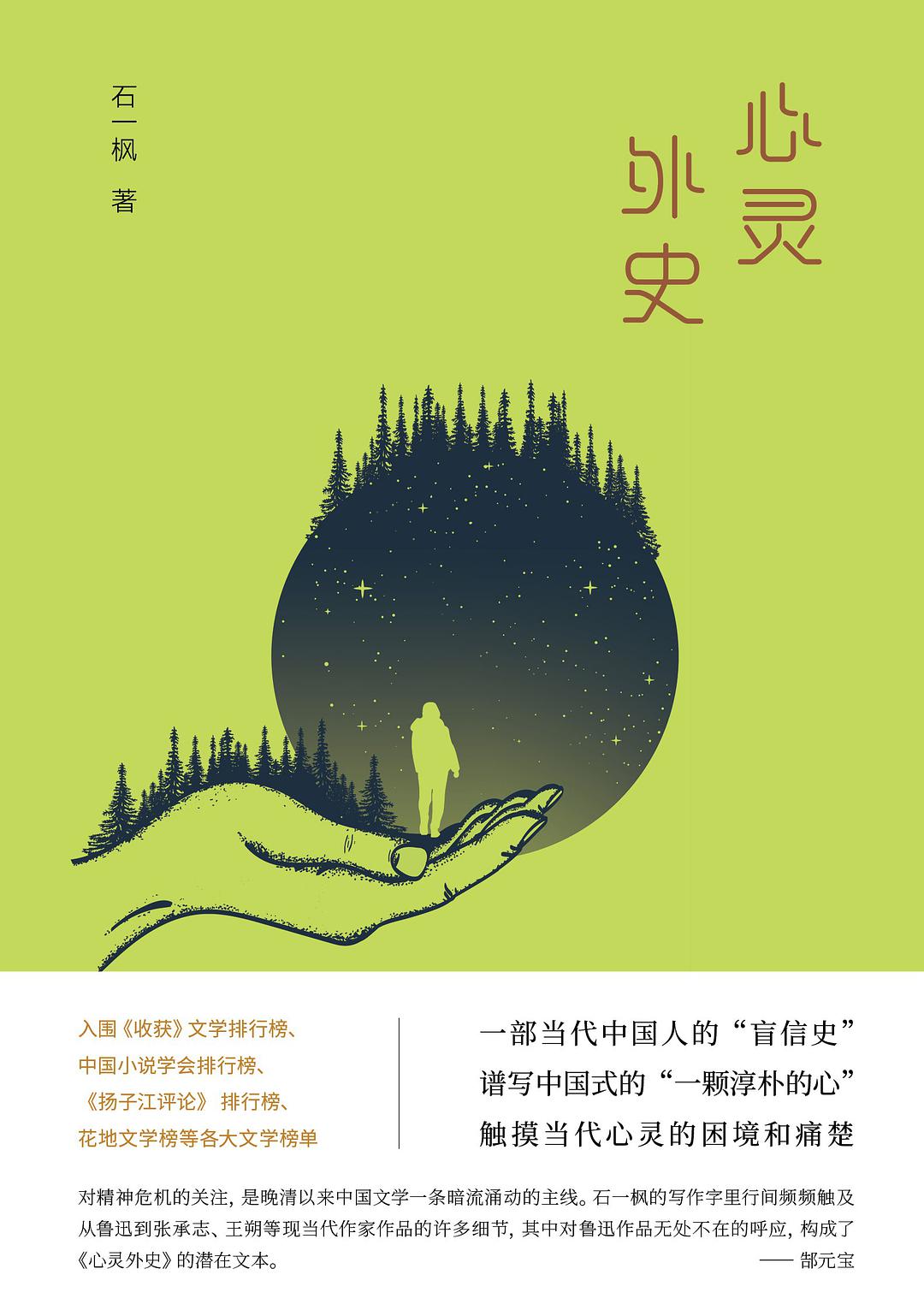
《心靈外史》
【后記】
在這篇當代京味小說里,我們會看到老舍時代的北京人走到今天,命運也在悄然改變。
上一次見到石一楓是在四川的文學期刊論壇,他講到北京過去農村地方的一些鄉民因為拆遷一躍成為中關村附近的有錢人,擁有了無數北清學子或許一生都望塵莫及的學區房。對于這樣的鄉民,有人不屑有人羨,但石一楓還看到了這些鄉民正在經受的“精神虐待”:因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他們在子女教育過程中往往四處碰壁,甚至連老師布置的家庭作業都完成得相當吃力。當時石一楓說:“中國社會有政治等級、經濟等級,也有文化等級。所以,同樣看待拆遷,從不同的時間、地點、立場、視角去看,我們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顯然,北京農村地方的鄉民和這次《漂洋過海來送你》里寫到的祖上“在旗”的胡同居民不一樣,但他們在文化與教育程度上頗具共性,以至于在不知不覺中都成為了今天所謂內卷時代的“失敗者”。對于這樣的“失敗者”,石一楓有同情,有無奈,有反思,他堅定地反對內卷。
在我的感覺里,石一楓一方面是那種有自己觀點的小說家,另一方面,他也打開自己的感受,甚至于讓感受大于觀點。最明顯的一點是《漂洋過海來送你》又一次寫到了通過非法集資謀取暴利的富人,他的形象類似于《世間已無陳金芳》里的b哥、《地球之眼》里的李牧光。盡管《漂洋過海來送你》里的這一人物最后沒有實際出場,但我們能從這個故事里看到石一楓對于這類人行為背后的生存邏輯有了更多的體會,對于個人與時代的角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