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莫沉評《販賣音樂》︱美國早期流行樂的商業(yè)史
音樂從未像今天這般無處不在。任何你能聯(lián)想到的場所——音樂廳、電視、商場、餐廳、公園、出租車、便攜播放設(shè)備、網(wǎng)絡(luò)都充滿了音樂的變體。人們一方面愈發(fā)容易尋獲自己喜愛的音樂類型,另一方面卻難逃熱門金曲、神曲洗耳式的強行轟炸。這些充滿矛盾與驚喜、快樂與感傷、啟迪與愚昧的聆聽經(jīng)歷,經(jīng)過日復(fù)一日、無休無止的漫長實踐,早已深深融入了個體的生活肌理,不斷編織、重構(gòu)或改寫人們的體驗和認(rèn)知。因此,有關(guān)音樂的故事總是如此親切,卻又一言難盡。
一些積極的愛樂人士會努力證明,他們的消費行為并非完全聽命于各種宣傳或價值灌輸,成功的音樂企劃也能以巧思贏得銷量與口碑,彌合商業(yè)與藝術(shù)之間的分野,而那些吸引眼球的“打造金曲的不二法則”“歌手走紅必備的十大要素”等試圖脫離特定歷史背景的總結(jié),顯然經(jīng)不起推敲。音樂的流行,恰巧是精心計算和意義制造雙重作用的結(jié)果。

由于本書聚焦的是1880至1930年的音樂產(chǎn)業(yè)史,對現(xiàn)代理性與科學(xué)產(chǎn)業(yè)布局的討論貫穿全書。經(jīng)過技術(shù)革新、少數(shù)族裔參與、空間改寫、法律支持、跨國合作等努力,美式音樂貿(mào)易已然樹立了新的行業(yè)秩序,音樂傳播也實現(xiàn)了民主化。但無疑,音樂產(chǎn)業(yè)本身是高度制式化的現(xiàn)代組織,音樂生產(chǎn)不是為了滿足聽眾的需求,而是主要源于技術(shù)與資本的考量。進一步說,音樂稱不上是中性的消費品,它的文化與審美價值經(jīng)受著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審視與過濾。
叮砰巷的故事
如今,叮砰巷這個名稱的來源已不可考。1900年,紐約聯(lián)合廣場的盛夏燠熱潮濕,辦公樓的窗戶統(tǒng)統(tǒng)敞開著方便透氣。曲作者能寫出一段朗朗上口的旋律,卻不一定是優(yōu)秀的鋼琴演奏家。這條街上聚集著成百上千的半吊子樂手,也難怪著名的音樂出版商提利爾將這里的樂聲與廚房鍋碗瓢盆的雜亂聲響相提并論。不管是否經(jīng)過了正統(tǒng)歐洲音樂作曲訓(xùn)練,這些來自不同行業(yè)、幾乎都有銷售經(jīng)驗、不到二十歲的小野心家,在曼哈頓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間租下一間辦公室,放置簡單的二手家私和一架立式鋼琴,在門口掛上歡迎“訂制歌曲”的標(biāo)志——叮砰巷之父查爾斯·K. 哈里斯(Charles K. Harris)就是這么做的。1892年,他創(chuàng)作的感傷情歌《舞會之后》(After the Ball)的樂譜狂銷兩百萬份,此后累計銷量超過五百萬份。

歌寫好了。接下來,音樂出版商將面對推廣營銷的問題——我們很難想象,在沒有任何播放設(shè)備和大氣電波的年代,流行曲是如何離開叮砰巷,融入日常生活的。傳統(tǒng)的辦法,是依靠不同層級的代理商出售活頁樂譜(sheet music),也就是把樂譜擺放在商店櫥窗,被動等待顧客來購買——十九世紀(jì)末,幾乎所有美國家庭都擁有屬于自己的樂器——但這個做法顯然是不夠的。出版商希望樂曲出現(xiàn)在任何可能的場所。首先是音樂場合。前文提到,音樂人“入行”前大多從事過銷售工作,如今,這些廣告人(plugger)的身影從晚上七點開始便活躍在戲院、電影院、舞廳、雜耍秀(vaudeville)等娛樂場合,在節(jié)目開始前和幕間休息時間抓緊表演;他們也會雇人在觀眾席充當(dāng)捧場客(claque)或線人(plant)營造氣氛;如果有別家的曲目上演,他們便來回穿行席間,反復(fù)哼唱自家歌曲干擾。不僅如此,為了增強歌曲的感染力,廣告人在演員表演的同時還配上相關(guān)的照片(song slides),這正是MV最早的雛形。施特恩與馬克斯共同創(chuàng)作的《走失的小孩》(The Little Lost Child)便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這種結(jié)合視聽的嘗試雖不是首創(chuàng),但它的火爆讓同行趨之若鶩,越煽情的歌曲越容易找到與之匹配的故事圖片,直到1937年電影流行起來,音樂幻燈片才逐漸式微。
如果說雜耍秀安排了不少合家歡的節(jié)目,場地也相對干凈整潔,那么假扮黑人演出(minstrel show)中常見的性暗示則更像是專為男士設(shè)計的,并不適宜所有人消遣。于是,廣告人把歌曲帶到了更寬敞的城市空間,比如自行車賽場合,他們一遍遍高喊副歌,比拼誰的嗓門大,又或是將樂譜的副歌部分裁成豎條,像現(xiàn)在街頭派發(fā)傳單一般塞到路人手里,隨行的同伴就如播放器一樣演唱,直到“魔音入腦”,人們心甘情愿去購買樂譜。百貨商店是另一個重點推銷場所,因為音樂表演讓購物環(huán)境變得更愜意舒適,簡單來說就是為了討好女性顧客。他們在商場內(nèi)部劃出場地,成立音樂廳,以此培養(yǎng)大眾的音樂素養(yǎng)。至此,廣告人的使命,已不乏教化色彩,且遠(yuǎn)不是實物銷售那么簡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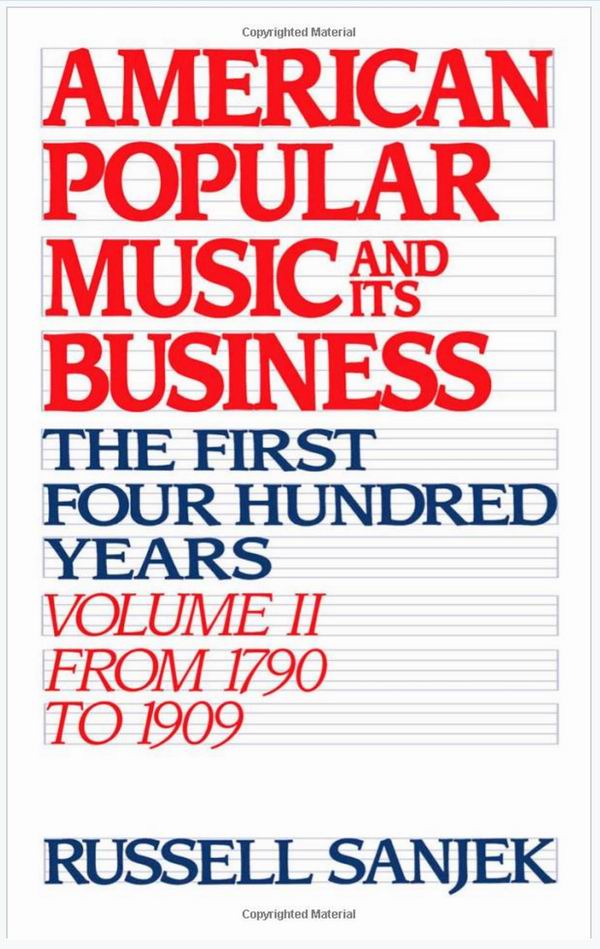
勝利牌留聲機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本書中文版譯為維克多留聲機公司)顯然是本書的主角。作者花了整整三章——接近全書一半的篇幅——從不同角度闡述勝利牌極具啟發(fā)的營銷策略。不僅如此,原版和譯本的封面均印上了留聲機,只不過前者還多了一只名叫尼珀(Nipper)的小狗——勝利牌的商標(biāo)正是這只小狗側(cè)頭聆聽留聲機的樣子。原商標(biāo)的底端另附一句話:“他主人的聲音。”這個著名的商標(biāo)借用小狗溫順體貼的形象,傳遞出顧客至上的企業(yè)理念。勝利牌所做的不光是砸錢那么簡單——除了巨額的廣告支出費用,它還相當(dāng)重看重產(chǎn)品定位。這種策略成功擊敗了強調(diào)技術(shù)參數(shù)的競爭對手,包括愛迪生的國家留聲機公司。經(jīng)過近二十年的發(fā)展,勝利牌的全球唱片銷量在1921年到達(dá)頂峰,共計五千四百萬張。


卡魯索的“爆紅”驚動了歐洲音樂圈,藝術(shù)家們不再嘲笑留聲機只是玩具,紛紛加入錄制唱片的行列。不過,錄唱片的過程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當(dāng)蓋斯伯格把笨重的錄音設(shè)備搬入女高音阿德林娜·帕蒂(Adelina Patti)居住的城堡,卻得苦等到她愿意演唱時才能開始工作。當(dāng)時這位傳奇歌手已經(jīng)六十三歲,兩天后終于同意開始錄音,但她卻異常容易緊張、煩躁。特別是唱到音量偏大的高音部分時,她不懂適度調(diào)整與錄音喇叭的距離——顯然帕蒂的歌聲與新技術(shù)之間需要磨合、調(diào)整。這種現(xiàn)象普遍存在,但卡魯索完全沒有障礙。他聲音洪亮卻細(xì)膩,能掩蓋唱片本身的雜音,似乎天生為唱片而生。一炮而紅的卡魯索此后只為勝利牌錄制唱片,而勝利牌也將卡魯索包裝成神一般的人物。《販賣音樂》詳細(xì)描述了唱片封套、文案如何運用文字的魔力,砸重金主力宣傳,使卡魯索一直身處“頭條”熱度。人們更像是為卡魯索的名氣,而非他的演唱所折服:在一次現(xiàn)場演出間隙,卡魯索代替身體抱恙的狄佩爾唱了一段,但觀眾并沒有意識到是他,僅報以零星的掌聲。我們有時也會讀到類似的新聞:一些成名的音樂人故意在公共場合表演,考驗路人的藝術(shù)鑒賞力,當(dāng)然結(jié)果總讓人啼笑皆非。現(xiàn)代明星形象的建立離不開商業(yè)包裝與宣傳,并且,某種程度上,新技術(shù)的演變的確會左右看似中立的專業(yè)表現(xiàn)。

有趣的是,勝利牌仍把營銷重心堅定不移地放在古典樂唱片上。這種策略無疑是另類大膽的,卻充滿了啟發(fā)性。1912年,勝利牌投入一百五十萬美元的廣告費宣傳紅印唱片,五年后,它已躋身美國五大雜志廣告贊助商,這與其企業(yè)排名(一百七十四名)并不相符,但這不妨礙它繼續(xù)投入,直到1923年成為全美排名第一的廣告客戶。因為勝利牌堅信,紅印系列所代表的文化資本有助于整體銷量提升。除了投放商業(yè)廣告,勝利牌還出版年鑒與雜志。這些出版物非常重視專業(yè)音樂知識,接近三百頁的年度唱片目錄涵蓋了歌劇情節(jié)圖解、名詞釋義,以及世界其他地區(qū)的音樂風(fēng)格介紹,就像一本“百科全書”。

理解現(xiàn)代流行樂及本書的翻譯問題
本雅明在《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中感慨,復(fù)制技術(shù)讓藝術(shù)品失去了獨一無二的靈光。音樂變成了商品,版權(quán)所有者以標(biāo)準(zhǔn)規(guī)格錄制、儲藏和復(fù)制,然后出售。很快,現(xiàn)場表演也納入了版權(quán)保護范圍。在阿塔利(J. Attali)看來,音樂具備多元化的商業(yè)價值,市場環(huán)境等“外部”因素驅(qū)使利潤增長,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分別歸屬買方和消費者,而創(chuàng)作者收獲了愉悅。
本書作者帶領(lǐng)讀者回到現(xiàn)代音樂產(chǎn)業(yè)的起點,一方面肯定技術(shù)進步促進了音樂傳播的民主化,另一方面也看到,在現(xiàn)代音樂工業(yè)體系中,制作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不可避免地面臨各種約束以及寡頭的控制。一些年代久遠(yuǎn)的規(guī)則如今仍在發(fā)揮效用,歌曲的面世過程、暢銷程度完全是技術(shù)手段、唱片公司、宣發(fā)機構(gòu)、社會環(huán)境、文化價值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勤勉、擁有奇思妙想的營銷前輩的故事告訴我們,優(yōu)秀的音樂商業(yè)組織不僅能生產(chǎn)物質(zhì)層面的音樂作品,還可以培育新的消費習(xí)慣和文化價值觀。
最后要提的是本書的翻譯問題。《販賣音樂》的中文版把“再現(xiàn)”(representation)譯成“演出”(126頁),“三拍子”(waltz time)變成“華爾茲舞曲”(13頁),“利潤”(margin)想當(dāng)然地理解為“頁邊空白”(第7頁),重要數(shù)據(jù)“兩美分”(2-cent)換成“2%”,讓人一頭霧水的“勸說校務(wù)委員會”(181頁)其實是指“地方教育董事會”(school boards)……這類本可規(guī)避的訛誤不勝枚舉。另外,一些錯譯完全扭轉(zhuǎn)了行文邏輯,造成不少閱讀障礙。如最有可能“反對”(resist)譯成“堅持”(178頁);出版商為了規(guī)避風(fēng)險,自然是要“減少”,而不是去“制造”(46頁)不確定性;在談到卡魯索的影響力時,漏掉原文中的hardly,變成“第一位引起強烈反響的音樂人”(121頁),語義與后文列舉的著名音樂家的事例矛盾;愛迪生“固執(zhí)己見的態(tài)度”(dig in his heels)變成“找到自己的弱點”(120頁)……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漏譯問題,或漏掉一句話,或整段略過,這種處理手法不僅導(dǎo)致很多張冠李戴的謬誤,更是讓讀者云里霧里:廣告人是否身兼推銷和表演等不同角色?“進行曲之王”桑斯(John Philip Sousa)是否力爭屬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收益?諸如此類由翻譯導(dǎo)致的問題,讓原本中文論述甚少的早期美國音樂史,變得更加難以理解。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