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董牧杭︱日本知名學者為何到中國亞馬遜來謾罵同行?
哈羅德·布魯姆不容置喙地稱莎士比亞“設立了文學的標準和限度”,他就是“一切經典的中心”。然而與中國頗多由話本發展而來的小說相仿,莎翁生前實際上只是創作頗受掣肘的劇團專屬寫手,恰恰是在十九世紀后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的《莎士比亞故事集》(下文簡稱《故事集》)編著者查爾斯·蘭姆姐弟的鼓吹下,莎劇才被人們認為價值主要在于其文學性上,而根本不適宜演出。二十世紀以降,大部分搞明白了莎著劇本性質的學者們可與布魯姆不同,都回過了神來。
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傳播歷程中,相關戲劇演出的重要性也可謂完全不遜色于各式各樣的翻譯出版物。此前漢語學界不但相關著述寥寥,而且成果也有陳舊老套之嫌。去年正值莎翁去世四百周年,陳凌虹老師翻譯、中國近代戲劇史專家瀨戶宏教授《莎士比亞在中國:中國人的莎士比亞接受史》(下文簡稱《在中國》)一書的出版本是填補空白、可喜可賀之事,然而另一日本學界巨擘一樁耍活寶般的舉動卻為之平添了些許喜劇色彩。
如果我們打開《在中國》的中國亞馬遜銷售頁面,就會赫然發現僅有一條用戶評分,并且是個一星差評。一個ID為“樽本照雄”的賬號絲毫沒有掩飾自己對瀨戶宏的憤怒與不屑,從其中稍嫌怪異的漢語表達來看,或許他真的是個日本人:

瀨戶博士要說的是他被林紓欺騙了,所以他誤會了。他就變成受害者了。批評林紓的研究者都冒充受害者。受害者可以隨便謾罵林紓。這真是瀨戶博士所提出的個奇怪論點。瀨戶博士沒有任何證據卻鑒定林紓是詐騙者,而誹謗林紓。
作為研究員采用評測的雙重標準是個致命的缺陷。瀨戶博士敢于莫名地自我毀滅。他的研究員生命已經沒有了。在我閱讀漢譯莎士比亞研究文獻直到現在為止,瀨戶博士的論文內容又最低又最差。
如此一針見血的批評恐怕不像是隨便一個缺乏教養的吃瓜群眾可以寫得出來的,恐怕真有大行家在處心積慮的“抹黑”。巧合的是,樽本照雄恰恰是一位傳奇式日本學者的名字,可謂卓然大家,陳平原先生甚至說過,“(近年關于林紓的翻譯)實證研究中,最值得推薦的是樽本照雄”。(陳平原,《古文傳授的現代命運》)
由此看來這八九不離十就是樽本本人跑到了中國亞馬遜上來罵人。然而在旁人看來無辜地就“敢于莫名地自我毀滅,研究生命已經沒有了,論文質量最低又最差”的瀨戶宏先生恐怕對這來者不善的“稱許”不會缺少心理準備,因為早在1992年2月,日本《東方》雜志第136號就已經刊登過瀨戶宏的《清末小說研究的重要成果——樽本照雄〈清末小說論集〉書評》一文,樽本先生早已領受過來自瀨戶氏犀利程度不遑多讓的“禮贊”:

本書不論是在縱向(文學史),還是在橫向(與其他領域進行比較)上都很難說充分說明了“清末小說”的意義。丸山升先生曾在幾年前評價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現狀時說:“……看待問題過于狹窄,有不良的學術主義……論說雖然屬實,然而通過這種論說能夠證明什么卻不清楚”(《野草》39號)……丸山先生的批評是否適用于整個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尚存疑問,不過倒是很適用于樽本先生的研究……再次重申,在清末小說這樣一個尚未得到充分重視的研究領域,樽本先生的努力恰如灑下第一把桑葉種子一般重要,他的研究應該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樽本先生也承認清末小說的研究剛剛起步。最后,希望樽本先生的研究取得進一步進展,從而消除筆者的不滿。
有著這等新仇舊怨,兩位日本學界大佬在有生之年恐怕都很難會停止他們的耍活寶行為了。不過要想搞清楚這樁恩怨的來龍去脈,就非得從樽本照雄以為的一起由《新青年》制造、林紓主演的莎士比亞翻譯冤案說起了。
不懂外語的翻譯者,分不清小說和戲劇?
稱林紓是中國翻譯史上最為特殊的一位譯者可謂毫不為過。林琴南覺著自己的古文是“六百年來,震川外無一敢當我者”,對翻譯卻極為蔑視。錢鍾書的老師、士林耆宿陳衍得知錢對于外國文學的興趣是因林譯而產生后,竟感嘆道:“這事做顛倒了。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興。你讀了他的翻譯,應該進而學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國了?”而那“不為文雅雄”的譯事在林心目中只怕比自比為“狗吠驢鳴”的詩藝還要不如,石遺老人說在“康長素捧他的翻譯”時,竟“惹得他發脾氣”。
他早年的翻譯甚至飽含著“西人為有父矣,西人不盡不孝矣,西學可以學矣”的啟蒙情懷,但事情的結果往往與人的初衷不同。“斷盡支那蕩子腸”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本是林紓連自己的譯名都不愿意去題署的作品,不料卻風靡全國。自此以后,這位完全不懂任何外語、被新文化青年們視為“桐城謬種”的古文家竟僅僅借由他人口述的幫助,翻譯了多達一百九十種左右外國文學作品, “自19世紀末至1920年代可說是形成了一個林譯小說的時代”。(張治,《中西因緣》)在林譯作品中,莎劇自然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莎士比亞的譯名首次出現在林則徐等人《四洲志》(《海國圖志》的藍本)中對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的片段翻譯里,被譯為“沙士比阿”。然而《海國圖志》長期遭到禁毀,自梁啟超于《飲冰室詩話》中鼓吹“近代詩家,如莎士比亞……其詩動亦數萬言”后,“莎士比亞”才得以成為通行的譯名并真正產生影響。

最早關于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是1903年出版的《澥外奇譚》,譯者已無據可考,此書譯出了《故事集》二十篇故事中的十篇,凡例有“是書原系詩體,經英儒蘭卜行以散文,定名曰Tales From Shakespeare”的說法,瀨戶宏著重強調道這“明確表示翻譯的底本是蘭姆的《莎士比亞故事集》”。
林紓與魏易合譯、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吟邊燕語》出版于次年,全部翻譯了《故事集》的所有篇章,序中林紓有“彼中名輩,耽莎氏之詩者,家弦戶誦,而又不已;則付之梨園,用為院本”的說法。
《吟邊燕語》影響巨大,上世紀二十年代雨后春筍般出現的莎劇文明戲(即中國早期話劇)大多以林譯為藍本進行演出。然而自商人們發現文明戲是個生財之道,紛紛涌入投機后,演出登時變味,業余的演員們莫說劇本,甚至連幕表都一并省去了。
但與《澥外奇譚》相反,這回瀨戶宏根據林紓序中的上述文字,對他進行了嚴厲指控:“可見在林紓的理解里,莎士比亞首先把作品以詩的形式寫下,后來被改寫為戲劇劇本。而實際上眾所周知莎士比亞作品的發表過程和林紓的理解恰恰相反。林紓沒有充分理解小說和戲劇的不同之處,更沒有認識到翻譯莎士比亞作品與翻譯經蘭姆故事化、小說化的《故事集》的不同。”
1916年,林紓在十余年后突然集中翻譯了一批莎翁的歷史劇。 “樽本照雄先生2007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底本是奎勒·庫奇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故事集》”,瀨戶宏在提及“中國亞馬遜評論者”的研究后,依然做出了“歷史劇譯文皆為小說形式,且僅記為英國莎士比亞原著”的批判。

瀨戶宏的說法其來有自。1924年林紓去世后,新文化運動中貢獻最著的社團之一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小說月報》上隨即刊布了鄭振鐸的《林琴南先生》一文。西諦先生彼時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小說月報》更可謂具有 “官媒”性質,此文公認定下了后世評價林琴南的基調。以林紓在新青年們心目中的地位,鄭當然沒有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盡說好話。除了指責林“(翻譯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書)卻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譯的”和“任意刪節原文”外,鄭做出了與瀨戶宏相同的嚴厲指控:
“小說與戲劇,性質本不大相同。但林先生卻把許多極好的劇本,譯成了小說——添進了許多敘事,刪減了許多對話,簡直變成了與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書了……原文的美與風格及重要的對話完全消失不見,這簡直是步卻爾斯·蘭(即蘭姆)在做莎士樂府本事(即故事集),又何必寫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亞”呢?林先生大約是不大明白小說與戲曲的分別的——中國的舊文人本都不會分別小說與戲曲,如小說考證一書,名為小說,卻包羅了無數傳奇在內——但口譯者何以不告訴他呢?”
除了錢鍾書近乎以一種贊揚的口吻“指責”林紓會時不時做出“碰見心目中原認為是原作的弱筆或敗筆,不免手癢難熬,搶過作者的筆去代他寫”的增補原作式翻譯之外,時下學界也往往不以刪減原著作為林氏的罪狀,這些富有“了解之同情”的看法顯然更為明智,“如果沒有那幾年‘譯述’的風行,翻譯小說的發展能直接進入常態嗎”?(陳大康,《當年“譯述”正風行》)
于是分不清小說與戲劇一時間竟成了林紓翻譯上最大的罪名,樽本的亞馬遜留言中所謂“中國學術界上罕見的大冤枉”正是指此林紓冤案而言。他在自己一篇具有學術史意義的重要論文中申說得更詳細,“這種說法與胡適所說‘這真是Shakespeare的大罪人’如出一轍。從此這樣的批評成為一種定論,沒有一個專家反對這個看法,定論益堅,批評者益多,規模極大。”自劉半農、鄭振鐸、寒光、馬泰來至現代學者林薇、鄭振環、郭延禮、瀨戶宏等盡皆認同這種看法。(鄭文惠譯,《林琴南冤獄》)
林紓的腐朽形象,是新青年們塑造出來的?
然而林紓的罪名可不僅僅只有弄不清小說與戲曲這一條。眾所周知,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在《致〈公言報〉函并答林琴南函》中提出了“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的北大校訓原型,林琴南萬分不幸地成為蔡元培平生影響最大的“五四精神”綱領性文件中“答”的對象,真是倒霉透頂。
其實這晦氣也純屬他自找,誰叫這位被解聘的前北大“教授”非得去信蔡元培,盡說些“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之類不合時宜的昏話,終于導致公憤,陳平原先生形象地稱他為“新文化運動自己找上門來的靶子”。
遭遇連番羞辱的林紓終于大失風度,寫出了“很可以把當時的衛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的影射小說《荊生》《妖夢》。《荊生》中,林紓以“偉丈夫”荊生自喻,痛罵田其美(陳獨秀)、金心異(錢玄同)、狄莫(胡適)是“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并把他們痛打了一頓,《妖夢》連帶著把蔡元培也罵了,甚至說他們“化之為糞,宜矣”,影射得如此明目張膽,有人想看不出來恐怕都很難。這兩文一出,他自己“頭號靶子”的位置可算是怎么都推脫不掉了。
林紓甫一去世,就已經“眾望所歸”地被鄭振鐸定性為“反革命”:“在康有為未上書以前,可算是當時的一個先進的維新黨。但后來,他的思想卻停滯了——也許還有些向舊的方向倒流回去的傾勢。到了最近四五年,他更成了一個守舊黨的領袖了。”
自此以后,莫說輿論,就是在學界中,林紓也幾乎同樣一直都是這樣的形象,林紓冤案就此定型。中國清末小說研究在上個世紀可稱顯學,魯迅導其先路,阿英定其筋骨,魏紹昌富其血肉,盡管已經碩果累累,卻幾乎沒有人對此提出過異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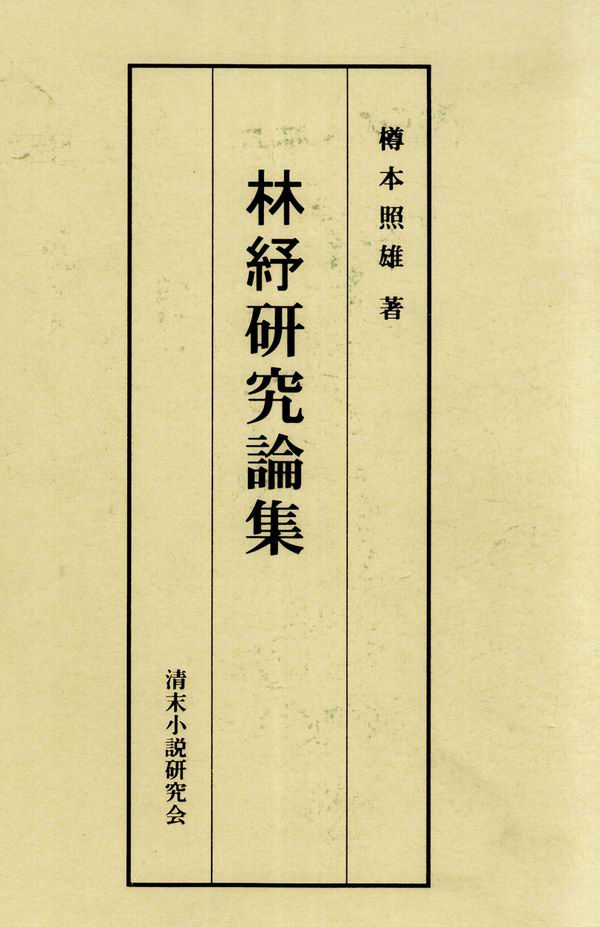
然而樽本卻力圖以一己之力為林紓“平冤”。樽本的學術著作幾乎都由清末小說研究會刊行。成立于1977年的清末小說研究會是一個相當神秘的機構,它沒有組織、會員與宗旨。研究會期刊雖然匯集了世界各國相關學者的論文,但竟是以刊發樽本一人的文章為主,每期花銷幾乎等同于一輛小轎車的價錢。令人震驚的是,這價值數十輛小轎車的費用竟幾乎都由這位傳奇學者獨自承擔。
樽本考訂出林譯莎翁歷史劇所用底本為奎勒·庫奇的故事集、《梅孽》(即林譯易卜生《群鬼》)底本也并非易卜生原著,亞馬遜評論中所說“林紓翻譯時使用的藍本都不是劇本而是小說”的新發現正是就此而言。這些考證如今已成定讞,可謂樽本最大的學術貢獻之一,只是他謙虛地沒有提及自己的名字。
如果以往的學者直接把林紓翻譯的底本都搞錯了,那么對其翻譯準確程度的預估自然會得出完全錯誤的判斷。樽本在一一比對林氏所有底本與譯文后,竟得出驚人結論:“林琴南雖然不是逐字翻譯,但譯文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沒有注明原奎勒·庫奇改寫莎士比亞作品,因此不該責備其將莎士比亞劇本譯為小說,而該責備鄭振鐸等評者未探索林琴南翻譯所采用的版本。”
瀨戶宏當然知曉樽本的考證,并在《在中國》第二章前言中明確寫到“本章是與樽本先生爭論后的產物,所以保留對樽本先生的尊稱”。他不得不承認“林紓將莎士比亞劇作改譯成小說形式這種定論并不正確”,卻賭氣般地堅稱林紓與中國的舊文人不明白小說與戲曲的分別,而他之所以堅信這點,除了林譯莎劇不署改編者之名外,也與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向來就把兩者混為一談有關。
然而樽本為證明自己“北大處于文學改革的重要領導中心,需要樹立一位文學、思想上的敵人加以抨擊來鞏固自身的改革理論……批評林譯莎士比亞及易卜生只是一小部分,而他們立林琴南為敵人,把他與軍人列為壓迫新思想的人物,才是全體新青年們所要的,而這其實與林琴南本身無關”的顛覆與創造性大膽推論,為影射小說《荊生》《妖夢》等進行了看起來相當綿軟無力的辯護,“小說是虛構的,脫離任何束縛、有著高度的自由,所以怎么寫都沒問題”的理由可謂糟糕透頂,顯然難以服人,自然要被瀨戶宏揪住把柄,在《在中國》一書中大加批判。

不管如何,瀨戶宏著述的價值不會因為樽本照雄偏激的攻訐而有所減損,樽本照雄洞見的睿智更是令后學敬服。但遺憾的是,樽本先生實在不太了解現在中國的讀書人——如果他有意把這項事業進行到底,或許最明智的做法是在一個叫做豆瓣的網站再注冊一個ID“樽本照雄”,并且把自己的這條耍寶評論在豆瓣的《莎士比亞在中國》圖書頁面上復制粘貼,還可以順帶再出口惡氣,多刷一個有價值得多的一星差評。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