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陰山八景”:叫“鬼門關(guān)”的景點(diǎn),你敢去嗎?
無(wú)論怎么看,陰間都不是旅游的好地方,雖然不是沒(méi)有人打過(guò)這個(gè)主意。
好像是去年的事,一個(gè)朋友的兒子對(duì)我說(shuō):“既然外國(guó)人搞起了太空旅游,我們?yōu)槭裁床荒芨阋粋€(gè)地府旅游?既然外國(guó)人把火星月球都要圈地拍賣,我們?yōu)槭裁床荒茉陉庨g開(kāi)發(fā)房地產(chǎn)?”這種敢跟洋鬼子叫板的愛(ài)國(guó)精神不能不讓人感動(dòng),但認(rèn)真想一想,把一個(gè)旅游團(tuán)拉到陰間去,則確實(shí)有些技術(shù)上的困難。
當(dāng)然這陰間是模擬仿造的,用幾元錢一畝的價(jià)錢買上一座荒山,然后照著陰間做些景點(diǎn),讓一些有才兒的文人編些廣告詞,春天是“到陰山看花去”,夏天是“陰山背后好乘涼”,這有什么困難?再起些“夜臺(tái)春夢(mèng)”、“奈津殘照”之類的名目,就是把乾隆皇帝從東陵中請(qǐng)出來(lái)題成石碑也不是做不到的事。至于把游客弄成“夜審潘洪”似的昏昏沉沉、迷迷瞪瞪,諸如灌酒精,喝迷幻藥,打麻醉針,用橡皮棒子敲腦殼,然后送進(jìn)水泥攪拌機(jī)里搖上三十圈,再經(jīng)過(guò)一個(gè)報(bào)廢的“過(guò)山車”改裝的傳輸筒送入“景區(qū)”,就完全可以做到了。我說(shuō)的技術(shù)困難不是這些,而是沒(méi)有辦法做成一口極大的“鍋”,把這座陰山罩上,讓它終年暗無(wú)天日,昏昏慘慘。因?yàn)閾?jù)到過(guò)冥界的人說(shuō),那里總是“長(zhǎng)如十一月十二月大陰雪時(shí)”(唐?陳?ài)俊锻ㄓ挠洝罚蚴恰疤焐帲栾L(fēng)颯颯”(北宋劉斧《青瑣高議》),或是“黃沙迷漫,不見(jiàn)日月”(清?袁枚《子不語(yǔ)》)的沙塵暴天氣。

所以這篇小文題成“陰山八景”,并無(wú)招攬游客的居心,只不過(guò)借著歸鋤子《紅樓夢(mèng)補(bǔ)》中“冥間八景”的現(xiàn)成話,把幾個(gè)陰間世的“景點(diǎn)”串在一起,便于敘述;因?yàn)橛械摹熬包c(diǎn)”內(nèi)容實(shí)在簡(jiǎn)略,不好單獨(dú)成文的。當(dāng)然,有的讀者愿意把它當(dāng)做臥游的指南,固無(wú)不可;倘或引起開(kāi)發(fā)商的靈感,真要組織什么“惡狗村踏青”給游客下套兒,那就與本文無(wú)關(guān)了。
鬼門關(guān)
鬼門關(guān),從字面上看,就可以明白是指進(jìn)入幽冥世界的關(guān)口。人的魂靈在關(guān)之外名義上還是生魂,入了關(guān)后就算是正式入了鬼籍。但古代對(duì)地獄或冥界的描述中,幾乎找不到這樣一處所在。實(shí)際上,陰陽(yáng)兩界的分界也不可能這樣具體,所以“鬼門關(guān)”三字見(jiàn)于文字倒主要是在象征意義上。南宋?洪邁《夷堅(jiān)支志?庚集》卷十“劉職醫(yī)藥誤”一條中,被庸醫(yī)治死的鬼魂說(shuō)道:“我一家長(zhǎng)幼十馀口,仰我以生。所坐本不至死,而汝以一服藥見(jiàn)投,使我五臟如刀割,膏液盡為臭穢。腸胃已腐,安得復(fù)生?今只在鬼門關(guān)相候!”此話的意思就是在陰間的官府相候,那時(shí)再和冤家打官司算賬,并不是指在陰間的入口處坐等,——那里想必有衙役和狗把守著,其實(shí)也不是約會(huì)等人的地方。
但“鬼門關(guān)”這個(gè)詞的出現(xiàn)比南宋更早,因?yàn)樵谔瞥瘯r(shí)就已經(jīng)把險(xiǎn)惡蠻荒的地方稱做“鬼門關(guān)”了。《舊唐書(shū)?地理志四》:
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duì),其間闊三十步,俗號(hào)“鬼門關(guān)”。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于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shí)趨交趾,皆由此關(guān)。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guān),十人九不還。”
北流在今廣西,這是最著名的鬼門關(guān),歷代都有人在詩(shī)文中提到它。其成名固然因?yàn)樗男螤铑H似天然關(guān)隘,但最主要的是因?yàn)槿肓舜岁P(guān)“十人九不還”,瘴癘傷人,披甲南征者、朝臣貶謫者都很難北歸。
另外,據(jù)袁子才說(shuō),儋耳(即今海南)也有一處,四面疊嶂崒?shí)型ㄒ坏溃谏乡潯肮黹T關(guān)”三字,旁刻唐人李德裕詩(shī),為他貶崖州司戶時(shí)經(jīng)此所題,云:“一去一萬(wàn)里,十來(lái)九不還。家鄉(xiāng)在何處,生渡鬼門關(guān)。”字徑五尺大,筆力遒勁。過(guò)此則毒霧惡草,異鳥(niǎo)怪蛇,冷日愁云,如入鬼域,真非人境矣。
其他如四川夔州、甘肅平?jīng)鲆捕加薪泄黹T關(guān)的地名,那就只是言其險(xiǎn)要,并無(wú)一去不還的意思了。但北流到了清代,廣西已經(jīng)被了“王化”,“十人九不還”的事已經(jīng)不再,并且因?yàn)榘l(fā)現(xiàn)了銀礦,北流更成了肥缺,所以有人就說(shuō),這“鬼門關(guān)”乃是“桂門關(guān)”之誤。廣西簡(jiǎn)稱為桂,其說(shuō)也可以自圓。
但可以肯定的是,民間先有了冥界鬼門關(guān)的觀念,才會(huì)有陽(yáng)世鬼門關(guān)的比喻。而冥界的鬼門關(guān)也只是一個(gè)象征性的詞。直到了元明之后,在戲曲小說(shuō)中鬼門關(guān)頻頻出現(xiàn),已經(jīng)成了民間對(duì)陰間的代稱了。只是《西游記》第十回中對(duì)鬼門關(guān)落實(shí)了一下,但卻不是如我們想像的大如山海關(guān)、小如娘子關(guān)那樣的關(guān)隘,竟然是一座城池的大門:
太宗遂與崔判官并二童子舉步前進(jìn)。忽見(jiàn)一座城,城門上掛著一面大牌,上寫(xiě)著“幽冥地府鬼門關(guān)”七個(gè)大金字。
因?yàn)槭浅情T,所以進(jìn)去之后能看到街道行人,又走了數(shù)里,便到了冥界的政治中心森羅寶殿。可是到第十一回劉全進(jìn)瓜時(shí),到了鬼門關(guān),
把門的鬼使喝道:“你是甚人,敢來(lái)此處?”劉全道:“我奉大唐太宗皇帝欽差,特進(jìn)瓜果與十代閻王受用的。”那鬼使欣然接引。劉全徑至森羅寶殿,見(jiàn)了閻王。
這樣看來(lái),鬼門關(guān)竟好像是宮府的大門一般了。可見(jiàn)《西游記》的作者對(duì)此等細(xì)節(jié)本不甚認(rèn)真,只用鬼門關(guān)表示進(jìn)入陰間就是了。
順便說(shuō)一下四川(如今是歸屬于重慶市了)酆都鬼城的“鬼門關(guān)”。據(jù)衛(wèi)惠林教授一九三五年的《酆都宗教習(xí)俗調(diào)查》,酆都縣平都山上有閻羅天子殿,天子殿后門稱為鬼門關(guān)。由鬼門關(guān)稍向西南下行為望鄉(xiāng)臺(tái)。此鬼門關(guān)本來(lái)是人造的景觀,其建于何時(shí)已不可考,但在袁枚的《子不語(yǔ)》卷五“洗紫河車”一則中卻已經(jīng)有了記載,并且把它落實(shí)為真的鬼門關(guān),云:
四川酆都縣皂隸丁愷,持文書(shū)往夔州投遞。過(guò)鬼門關(guān),見(jiàn)前有石碑,上書(shū)“陰陽(yáng)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觀良久,不覺(jué)已出界外。
這一步邁出的“界外”竟是真的幽冥世界,于是遇到了已故多年的妻子。
另外民間小戲有《陰陽(yáng)河》,客商張茂深行至酆都縣,想游覽一下當(dāng)?shù)仫L(fēng)光,店小二對(duì)他說(shuō):“出了店門,朝南走一條大路,見(jiàn)一個(gè)石牌坊,那就是陰陽(yáng)界。界這邊都是做買賣的,又熱鬧又好玩,千萬(wàn)不要到陰陽(yáng)界那邊去,那是一個(gè)鬼地。”這里說(shuō)的“陰陽(yáng)界”牌坊,正是袁枚說(shuō)的鬼門關(guān)。

聽(tīng)說(shuō)現(xiàn)在豐都鬼城中的“鬼門關(guān)”還在,但我沒(méi)有到過(guò),估計(jì)既不會(huì)像山海關(guān)或娘子關(guān)那樣的真,也不會(huì)像戲臺(tái)上《空城計(jì)》的城樓那樣的假吧。而進(jìn)了“鬼門關(guān)”,還有“黃泉路”、“望鄉(xiāng)臺(tái)”諸景點(diǎn),只要不另收門票,盡可放心過(guò)去的。
奈河橋
冥界本來(lái)就是人間的復(fù)制品,人間的山河樹(shù)木也會(huì)很合理地在冥界出現(xiàn)。但奈河卻不同于一般的河流,它是一條血污之河。嚴(yán)格說(shuō)起來(lái),“奈河”只是佛經(jīng)中“地獄”(Naraka)一詞音譯的變化,“奈河”就是地獄!但既然這地獄在中國(guó)譯文中變成了“奈河”,于是也就只有把它當(dāng)成河流了。
這里先看看這條奈河自唐代以來(lái)的演變,與人世的河流日久則變小以至湮沒(méi)相反,奈河是由小溪而變?yōu)榫藓拥摹T谔?張讀《宣室志》中,那是一條“廣不數(shù)尺”的小河溝:
(董觀)出泥陽(yáng)城而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如毳毯狀。行十馀里,一水廣不數(shù)尺,流而西南。觀問(wèn)靈習(xí),習(xí)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jiàn)岸上有冠帶褲襦凡數(shù)百,習(xí)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
這樣的河溝不需要橋梁,亡魂至此要脫光衣服,全部留到此岸,然后赤著身子過(guò)河,就算正式進(jìn)入冥府了。這條奈河頗像是幽明二界的分界處,說(shuō)成“陰陽(yáng)界”也是不差的。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也有相似的描寫(xiě):
目連聞?wù)Z,便辭大王即出。行經(jīng)數(shù)步,即至奈河之上,見(jiàn)無(wú)數(shù)罪人,脫衣掛在樹(shù)上,大哭數(shù)聲,欲過(guò)不過(guò),回回惶惶,五五三三,抱頭啼哭。
這奈河自東向西而流,水勢(shì)很急,已經(jīng)不同于《宣室志》的小河溝了。河的南岸有樹(shù),亡魂掛衣其上,卻還是要涉水而渡。渡水之前要點(diǎn)名,“牛頭把棒河南岸,獄卒擎叉水北邊”,想不下水是不行的。
北宋?彭乘《續(xù)墨客揮犀》卷五“獻(xiàn)香雜劇”條記伶人作劇中提到奈河,在人們的理解中,那水也應(yīng)該是深的:
……(劇中)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jiàn)閻羅殿側(cè)有一人衣緋垂魚(yú),細(xì)視之,乃判都水監(jiān)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wèn)左右云:‘為奈河水淺,獻(xiàn)圖欲別開(kāi)河道耳。’”時(shí)叔獻(xiàn)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yǔ)。
小說(shuō)中寫(xiě)奈河者以《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第八十七回和清初人丁耀亢的《續(xù)金瓶梅》第五回最為鋪張。丁書(shū)說(shuō),河上雖有三座橋,有罪的亡魂卻不能過(guò),只能涉水,只見(jiàn)那奈河:
這奈河是北方幽冥大海內(nèi)流出一股惡水,繞著東岳府前大道,凡人俱從此過(guò)。茫茫黑水,滾滾紅波,臭熱濁腥,或如冰冷,或如火燒,就各人業(yè)因,各有深淺,也有淹到脖頂?shù)模街醒模侥_面的,那些毒蛇妖蟒伸頭張口,任他咬肉咂血,那里去回避!
原來(lái)這奈河對(duì)于罪魂已經(jīng)成了一道刑罰,其深淺寒熱俱因各魂罪業(yè)而自動(dòng)變化。現(xiàn)在讓人看來(lái),也不免想到,自唐而至清,原來(lái)整治人的想像力有了這么大的進(jìn)步!
而在《聊齋》中,奈河索性就成了市廛中的臭水溝,九幽十八獄的垃圾糞便全部歸納于此。《王十》一篇中說(shuō)它“河水渾赤,臭不可聞”,淤積的全是“朽骨腐尸”,而在《酒狂》中更添了個(gè)小道具:“水中利刃如麻,刺脅穿脛,堅(jiān)難搖動(dòng),痛徹骨腦。黑水雜溲穢,隨吸入喉,更不可耐”。這都是蒲翁小說(shuō)中的隨意點(diǎn)綴,從而讓我們知道古代的都市中本有此一景,至于距奈河的原始位置太遠(yuǎn)了些,也就不必較真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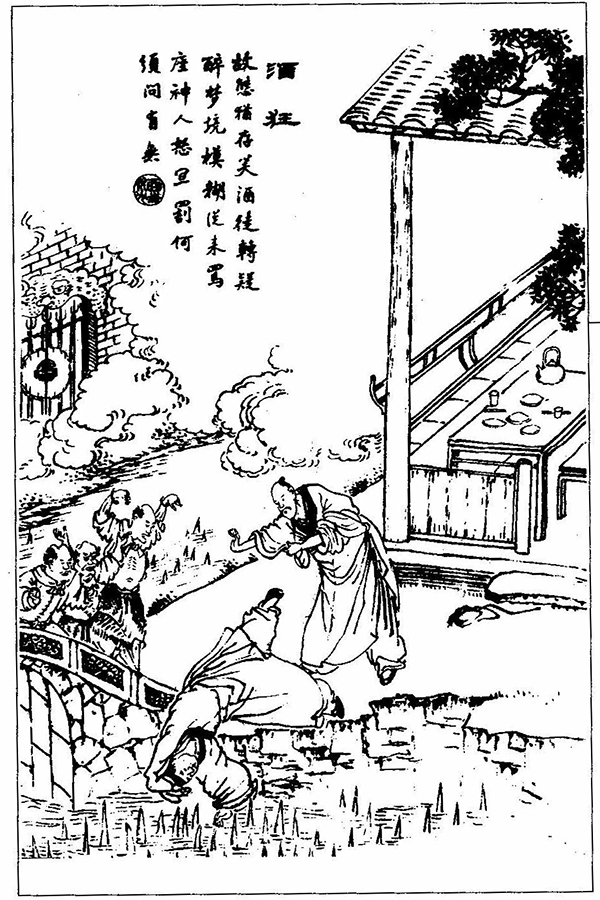
再來(lái)看奈河橋。奈河上的橋梁自應(yīng)比奈河較為后出,如果把條件放寬一些,我們也可以說(shuō)最早見(jiàn)于唐?段成式的《酉陽(yáng)雜俎》,其前集卷二“明經(jīng)趙業(yè)”條云,趙業(yè)病中入冥:
初覺(jué)精神游散如夢(mèng)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眾,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guò)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眾。
此河即奈河,而飾以金碧的那座橋雖沒(méi)有名稱,自然就是奈河橋了。后來(lái)見(jiàn)于宋人筆記中,或稱“冥司橋”(洪邁《夷堅(jiān)支志?戊集》卷四“太陽(yáng)步王氏婦”),只是在《夷堅(jiān)志補(bǔ)》卷三“檀源唐屠”一條中才明言是“奈河橋”。這則故事很重要,言屠夫唐富為冥吏所拘,緣由是他殺了一只蟢子(即蜘蛛)。唐富求道:“自念平生不妄踐踏蟲(chóng)蟻,只記屠牛十三頭、豬二十口,若得放還,誓愿改過(guò)。”于是:
吏云:“此非我可主張,到愛(ài)河橋(明鈔本作“奈河橋頭”),汝自告判官乞檢簿。”遂偕進(jìn)。至一河邊,高橋跨空,有緋衣官人執(zhí)簿立,吏附耳語(yǔ)曰:“此判官也!”兩犬極獰惡,迎吠河津,不容人過(guò)。于是再拜致禱。緋衣為閱簿,曰:“幾乎錯(cuò)了,殺蟢子者乃彭富,與汝不相干。兼汝壽數(shù)未盡,更當(dāng)復(fù)生。”
這條材料不僅是奈河橋的初次見(jiàn)于文獻(xiàn),而且明確了奈河是入冥的正式關(guān)口,專門設(shè)有判官,來(lái)對(duì)入冥鬼魂進(jìn)行審核,不該死的,即時(shí)遣回陽(yáng)世,就是想見(jiàn)閻王也不行(這也許是控制陽(yáng)世的刁民如席方平之類來(lái)告陰狀吧),因?yàn)橛袃蓷l惡狗遮攔著。這是此前此后都不再提及的。但這兩條惡狗也不是沒(méi)有來(lái)由,那就是古印度傳說(shuō)中地獄之主閻摩的那兩條四眼犬娑羅彌耶。(見(jiàn)《梨俱吠陀》Ⅹ)
《夷堅(jiān)丙志》卷十“黃法師醮”一條說(shuō)到陰間有一條“灰河”,與唐人所說(shuō)奈河相似,應(yīng)是奈河之誤,“灰”“奈”字形相近耳。(佛經(jīng)中的地獄有“灰河獄”,或由此而誤,也未可知。)其中提到奈河橋,但是只給無(wú)罪之人渡河用的,也沒(méi)有冥吏和惡犬看守了,至于罪重者,則仍與以往記載一樣,要脫下衣服涉水而渡,而岸上有大柘木數(shù)株,鬼卒就把脫下的衣服掛在上面。 可是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些衣服上都寫(xiě)上每個(gè)人的名字,然后裝到車上,由橋上運(yùn)過(guò),再讓本人穿上。一絲不掛的見(jiàn)閻羅,終是讓人難堪,可見(jiàn)陰司也在逐漸人性化。
明清兩代的小說(shuō)和戲文中提到奈河橋的地方很多,但也人言人殊。最為人所熟知的自然要數(shù)《西游記》中唐太宗入冥時(shí)過(guò)的奈河橋了。冥河上設(shè)有三橋,一是金橋,二是銀橋,三是奈河橋,冥司很是勢(shì)利,金橋是只給帝王將相預(yù)備的,忠孝賢良之輩,公平正大之人,也只配過(guò)銀橋;倘是無(wú)功無(wú)德的鬼魂,那就只能過(guò)奈河橋了。那橋“寒風(fēng)滾滾,血浪滔滔,號(hào)泣之聲不絕”:
橋長(zhǎng)數(shù)里,闊只三皻,高有百尺,深卻千重。上無(wú)扶手欄桿,下有搶人惡怪。枷杻纏身,打上奈河險(xiǎn)路。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兇頑,河內(nèi)孽魂真苦惱,椏杈樹(shù)上,掛的是青紅黃紫色絲衣;壁斗崖前,蹲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銅蛇鐵狗任爭(zhēng)餐,永墮奈河無(wú)出路。
丁耀亢的《續(xù)金瓶梅》也說(shuō)是有三座橋,卻是金、銀、銅,統(tǒng)稱為奈河橋了。但這橋?qū)τ跊](méi)有資格過(guò)橋的罪魂卻是看不見(jiàn)的,他們只能泅水過(guò)河:
這奈河是北方幽冥大海內(nèi)流出一股惡水,繞著東岳府前大道,凡人俱從此過(guò)。只有三座橋:一座金橋,是佛道、圣道、仙道往來(lái)的;一座銀橋,是善人、孝子、忠臣、義士、節(jié)婦、貞夫往來(lái)的;又有一座銅橋,是平等好人,或有官聲,或有鄉(xiāng)評(píng),積德不醇全,輪回不墮大罪,或托生富家、轉(zhuǎn)生官爵,或女化男身、功過(guò)相準(zhǔn)的,才許走這橋。各有分別。這橋神出鬼沒(méi),該上金橋的,一到河邊,金橋出現(xiàn),即有童子引導(dǎo);不該上橋的,并不見(jiàn)橋,只是茫茫黑水,滾滾滾紅波,……
但《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第八十七回中的奈河上卻只有一座橋,只有好人可過(guò):
只見(jiàn)前面一條血水河,橫撇而過(guò),上面架著一根獨(dú)木橋,圍圓不出一尺之外,圓又圓,滑又滑。王明走到橋邊,只見(jiàn)橋上也有走的,幢幡寶蓋,后擁前呼。橋下也有淹著血水里的,淹著的,身邊又有一等金龍銀蝎子,鐵狗銅蛇,攢著那個(gè)人,咬的咬,傷的傷。王明問(wèn)道:“姐夫,這叫做甚么橋,這等兇險(xiǎn)?卻又有走得的,卻又有走不得的。”判官道:“這叫做奈河橋。做鬼的都要走一遭。若是為人在世,心術(shù)光明,舉動(dòng)正大,平生無(wú)不可對(duì)人言,無(wú)不可與天知,這等正人君子,死在陰司之中,閻君都是欽敬的,不敢怠慢,即時(shí)吩咐金童玉女,長(zhǎng)幡寶蓋,導(dǎo)引于前,擁護(hù)于后,來(lái)過(guò)此橋,如履平地。若是為人在世心術(shù)暗昧,舉動(dòng)詭譎,傷壞人倫,背逆天理,這等陰邪小人,死在陰司之中,閻君叱之來(lái)度此橋,即時(shí)跌在橋下血水河里,卻就有那一班金龍銀蝎子,鐵狗銅蛇,都來(lái)攢著咬害于他。”
《青樓夢(mèng)》第三十六回中所說(shuō)奈河橋也是只有一座,高有百丈,闊僅三分,如同在長(zhǎng)江三峽上空架了一條鐵索,亡魂無(wú)論善惡都是不好過(guò)的。而橋下的水卻是“血污池”,里面沉溺著無(wú)數(shù)男女。同是奈河橋,就有這么多不同的說(shuō)法,真是讓人無(wú)可奈何了。……
最后補(bǔ)充一句,奈河橋或稱作“奈何橋”。近人林紓《鐵笛亭瑣記》云:
閩人之為死者資冥福,必延道士設(shè)醮。至第七日,則支板為橋,橋下燃蓮燈,幡幢滿其上,名曰奈何橋。糊紙為尸,納之紙輿中,子孫舁以過(guò)橋,焚諸門外。余問(wèn)道士以奈何出處,則云:“無(wú)可奈何也。”
剝衣亭
初看這剝衣亭,以為是奈河邊上為魂靈們脫衣方便而好心設(shè)置的一個(gè)遮風(fēng)避雨的亭子。但一個(gè)“剝”字卻讓人疑惑,什么剝奪、剝削、剝?nèi) ⒈P(pán)剝之類,都是以一方強(qiáng)加于他方的,所以這剝衣不會(huì)是讓自己從容地寬衣解帶,倒像是屠戶的剝皮了。但顯而易見(jiàn)的是,這剝衣亭肯定是從奈河邊上搬來(lái)的。
亡魂進(jìn)入冥府之前要脫掉衣服,此說(shuō)最早見(jiàn)于唐?張讀《宣室志》,已經(jīng)見(jiàn)于前面“奈河”一節(jié)。其緣由不可考究,或許是人生一世,就要赤條條地來(lái)又赤條條地去吧。可是人死之后進(jìn)入冥世的本來(lái)只是魂靈,人有魂而衣服卻沒(méi)有魂,從他脫殼的那一剎那,這魂靈本來(lái)就應(yīng)該是赤條條了吧。但不管怎樣,民間就有過(guò)這么一種渡奈河之前要脫光的說(shuō)法,而正是此說(shuō),后來(lái)到清代就演變成冥府中的“剝衣亭”。至于人間監(jiān)獄中入獄之始就要脫去衣服換上囚衣,也未嘗不可做為剝衣亭的興建緣由。清?程趾祥《此中人語(yǔ)》卷二“吳某”條:
鬼卒導(dǎo)吳游十殿,威風(fēng)凜凜,固不待言,而奈河橋、剝衣亭、望鄉(xiāng)臺(tái)等多寓目焉。
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續(xù)編》卷四“冥游確記”所記較詳:
見(jiàn)中庭堆衣如山,旁人謂此剝衣亭也,臨終衣服如系僭越,不論有罪無(wú)罪,至此必剝?nèi)ァ?/span>
此處所說(shuō)剝衣,似乎已經(jīng)經(jīng)過(guò)了改造,即不論有罪無(wú)罪,只要所穿的衣服超過(guò)本人身份的,就要?jiǎng)內(nèi)ァ?墒前凑遮じ耐菓]囚的衙門,不是朝廷的接待站,應(yīng)該只問(wèn)鬼魂的罪福,不管他是什么皇親國(guó)戚還是平頭百姓的。當(dāng)然這里的意義在于糾正喪葬風(fēng)俗的僭奢。
清人小說(shuō)《青樓夢(mèng)》第三十四回又有另一種說(shuō)法,剝衣的目的是為了要給有罪的鬼魂披上獸皮:
……至一頂仙橋,卻是十分開(kāi)闊,見(jiàn)居中一亭,有許多人在那邊。挹香近前一看,見(jiàn)眾人擁著一個(gè)女子,在那里洗剝衣服,頃刻身上剝得赤條條一無(wú)所有。挹香見(jiàn)了,忽然大怒道,“陰間如此無(wú)禮的,為何好端端將人家女子剝得如此地位?”鬼卒道:“此名剝衣亭。凡婦人陽(yáng)間不孝父母,都要?jiǎng)兿乱路钏念^換面,去為畜類。”鬼卒一面說(shuō)時(shí),見(jiàn)那女子扒在地上,一鬼將一張羔羊皮替他披上,俄頃人頭畜體,啼哭哀哀。又一鬼將一個(gè)鐵鑄羊面印子往那女子面上一印,只聽(tīng)得幾聲羊叫,面目已非。
不管是人還是亡魂,被剝得赤條條的去過(guò)堂,想起來(lái)也是不雅,所以在一些地方的喪俗中就要加上一條。胡樸安《中華全國(guó)風(fēng)俗志》下編“湖州問(wèn)俗談”中有剝衣亭一節(jié):
凡人死后,俗意須經(jīng)過(guò)此亭。若不預(yù)告說(shuō)明,必受惡鬼所剝。故于臨終穿衣時(shí),家屬婦女,對(duì)死者亦誦杜撰經(jīng)數(shù)句曰:“爾件衣裳那里來(lái),我件衣裳家里來(lái)。文武織補(bǔ)太監(jiān)裁,觀音娘娘開(kāi)領(lǐng)做組襻,彌勒穿去不回來(lái)。”隨穿隨念,以為死者免遭剝衣也。
還有一典不可不說(shuō),就是章回小說(shuō)中寫(xiě)山大王的山寨,也都設(shè)有剝衣亭(如清人錢彩《說(shuō)岳全傳》第三十三回),就是動(dòng)不動(dòng)把“牛子”開(kāi)膛取心的所在,不知是不是從地獄中得到的靈感。
望鄉(xiāng)臺(tái)
望鄉(xiāng)臺(tái)也是比較為人熟知的冥間景點(diǎn),名子有詩(shī)意,是從人間引進(jìn)的。唐人王勃“九月九日望鄉(xiāng)臺(tái)”,杜甫“共迎中使望鄉(xiāng)臺(tái)”,“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xiāng)臺(tái)”,說(shuō)的是成都的望鄉(xiāng)臺(tái),為隋蜀王楊秀所建。唐人吳融“磧連荒戍頻頻火,天絕纖云往往雷,昨夜秋風(fēng)已搖落,那堪更上望鄉(xiāng)臺(tái)”,宋人張舜民的“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xiāng)臺(tái)”,說(shuō)的是塞外望鄉(xiāng)臺(tái),傳說(shuō)為漢將軍李陵所建,也有說(shuō)是蘇武所登的一個(gè)高臺(tái),因登高懷念故國(guó),就命為望鄉(xiāng)臺(tái),但以他那樣的處境,是沒(méi)錢為自己專建一個(gè)了望臺(tái)的。
這望鄉(xiāng)臺(tái)的引入到冥間,大約是宋朝的事,但也不大靠得住。洪邁的《夷堅(jiān)丙志》卷九有“聶賁遠(yuǎn)詩(shī)”一條,記下了聶賁遠(yuǎn)的鬼魂寫(xiě)的一首七律,最末一句是“回首臨川歸不得,冥中虛筑望鄉(xiāng)臺(tái)”。(這個(gè)聶賁遠(yuǎn)在北宋末年出使金國(guó)求和,竟把整個(gè)山西割讓給金虜,所以他回程經(jīng)過(guò)絳州時(shí),絳人大憤,就把他揪到城墻上,“抉其目而臠之”了。)但“冥中虛筑望鄉(xiāng)臺(tái)”,要用讀詩(shī)法理解,也可以說(shuō)成是用了李陵望鄉(xiāng)臺(tái)的故實(shí),未必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有了冥間望鄉(xiāng)臺(tái)的俗信,但不管怎樣,這里是把望鄉(xiāng)臺(tái)與冥間連接在一起了。
到了元代,望鄉(xiāng)臺(tái)已經(jīng)確鑿無(wú)疑地進(jìn)入冥界,除了元人雜劇中常常提到之外,《水滸傳》“牙關(guān)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干,七魄投望鄉(xiāng)臺(tái)上”,早與枉死城同樣出名,成了陰間的代名詞。及至明代,望鄉(xiāng)臺(tái)更是屢屢見(jiàn)于詩(shī)文小說(shuō),最有名的自然是《牡丹亭還魂記》中杜麗娘死后,香魂一縷為花神領(lǐng)到了望鄉(xiāng)臺(tái),從那里可以看到揚(yáng)州的父母。而《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第八十七回中更有詳盡的描寫(xiě):
王明跟定了崔判官,走了一會(huì),只見(jiàn)左壁廂有一座高臺(tái),四周圍都是石頭疊起的,約有十丈之高。左右兩邊兩路腳擦步兒,左邊的是上路,右邊的是下路。臺(tái)下有無(wú)數(shù)的人,上去的上,下來(lái)的下。上去的也都有些憂心悄悄,下來(lái)的著實(shí)是兩淚汪汪。王明低低的問(wèn)說(shuō)道:“姐夫,那座臺(tái)是個(gè)甚么臺(tái)?為甚么有許多的人在那里啼哭?”判官道:“大舅,你有所不知,大凡人死之時(shí),頭一日,都在當(dāng)方土地廟里類齊。第二日,解到東岳廟里,見(jiàn)了天齊仁圣大帝,掛了號(hào)。第三日,才到我這酆都鬼國(guó)。到了這里之時(shí),他心還不死。閻君原有個(gè)號(hào)令,都許他上到這個(gè)臺(tái)上,遙望家鄉(xiāng),各人大哭一場(chǎng),卻才死心塌地。以此這個(gè)臺(tái),叫做望鄉(xiāng)臺(tái)。”
又有說(shuō)望鄉(xiāng)臺(tái)是地藏菩薩造的,菩薩心腸好,這臺(tái)也自然是為了憐憫鬼魂思鄉(xiāng)而造了。《紅樓復(fù)夢(mèng)》第七十七回中有一段:
甄判官指道:“此地名蒿里村。地藏佛慈悲建此高臺(tái),就是世上所說(shuō)的望鄉(xiāng)臺(tái)了。凡人死後七日,取‘七日來(lái)復(fù)’之意,令其上臺(tái)略望一眼,以了一生之事,從此與家長(zhǎng)別。”
此處說(shuō)望鄉(xiāng)臺(tái)在蒿里村,自然是小說(shuō)的隨意點(diǎn)綴。但望鄉(xiāng)臺(tái)究竟在冥界的何處,在不同的書(shū)中有不同的說(shuō)法。山西蒲縣東岳廟中的望鄉(xiāng)臺(tái)是設(shè)在第八殿都市王的奈河橋旁。那只是一個(gè)象征性微縮景觀,已經(jīng)很小了。估計(jì)所以安在第八殿附近,只是為了遷就地方(那里的十殿閻羅是“集體辦公制”,每五位擠到一間不足三十平米的屋子內(nèi),還要留出拷問(wèn)鬼魂的場(chǎng)地),陰間沒(méi)有望鄉(xiāng)臺(tái)說(shuō)不過(guò)去,就找個(gè)空隙安上了,其實(shí)是未必非要第八殿那里不可的。
在蒲松齡《聊齋志異》“耿十八”那則故事中,望鄉(xiāng)臺(tái)是冥府的入口處,但并不是要求所有的鬼魂都要到那里看一看,與人世做訣別的,又叫做“思鄉(xiāng)地”,其說(shuō)比較合理:

見(jiàn)有臺(tái)高可數(shù)仞,游人甚多,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為“望鄉(xiāng)臺(tái)”。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競(jìng)登。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dú)至耿,則促令登。登數(shù)十級(jí),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前。但內(nèi)室隱隱,如籠煙霧。凄惻不自勝。
……
晚出的《玉歷寶鈔》是要給冥府做“定本”的,但對(duì)望鄉(xiāng)臺(tái)安排得很不合情理,而且別有發(fā)揮,把這臺(tái)安在五殿閻羅之處,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鬼魂都要登的:
五殿閻羅王天子曰:“今來(lái)本殿鬼犯,照過(guò)孽鏡,悉系惡類,無(wú)須多言。牛頭馬面,押赴高臺(tái)一望可也。”所設(shè)之臺(tái)名曰望鄉(xiāng)臺(tái),面如弓背,朝東西南三向,彎直八十一里,后如弓弦。坐北劍樹(shù)為城。臺(tái)高四十九丈,刀山為坡,砌就六十三級(jí)。善良之人,此臺(tái)不登,功過(guò)兩平,已以往生,只有惡鬼,望鄉(xiāng)甚近,男婦均各能見(jiàn)能聞,觀聽(tīng)老少語(yǔ)言動(dòng)靜,遺囑不遵,教令不行,凡事變換,逐件改過(guò),苦掙財(cái)物,搬運(yùn)無(wú)存,男思再娶,婦想重婚,田產(chǎn)抽匿,分派難勻,向來(lái)帳目,清揭復(fù)溷,死欠活的難少分文,活欠死的奈失據(jù)證……
后面還有很多,大意是叫這些罪魂看到自己死后家破人亡的景況,讓他們?cè)谌怏w上受盡酷刑之后,內(nèi)心再受一次折磨。《玉歷寶鈔》的作者心理有些變態(tài),專以恐嚇世人為要?jiǎng)?wù),從對(duì)望鄉(xiāng)臺(tái)的改造上可見(jiàn)一斑。但人間也有對(duì)付的辦法,胡樸安《中華全國(guó)風(fēng)俗志》下編“壽春迷信錄”中說(shuō):“人死三日后,有上望鄉(xiāng)臺(tái)之說(shuō),忌家人泣哭。俗以為死者不自知其死,及上望鄉(xiāng)臺(tái)始知其已為鬼物,若泣哭,是使死者之心愈悲痛也。” 實(shí)際上,家人連哭了三天,再不喘口氣也頂不住了。
惡狗村
冥界中的惡狗,最早見(jiàn)于前引《夷堅(jiān)志補(bǔ)》那把守在奈河橋側(cè)的兩條惡犬,其根據(jù)雖然有古印度神話中閻摩王四眼犬,但是陽(yáng)世的關(guān)卡總有關(guān)吏和惡狗把守,則是更主要的。可是到了后來(lái),大約因?yàn)槟魏訕蚺系年P(guān)卡撤了,惡狗失業(yè),無(wú)處安置,便放養(yǎng)到惡狗村中,讓它們自謀生路了。
惡狗村只見(jiàn)于清人小說(shuō)中,但各處說(shuō)得也不盡相同,其中最為人知的是清初人錢彩《說(shuō)岳全傳》第七十一回寫(xiě)何立入冥:
但見(jiàn)陰風(fēng)慘慘,黑霧漫漫。來(lái)至一個(gè)村中,俱是惡狗,形如狼虎一般。又有一班鬼卒,押著罪犯經(jīng)過(guò),那狗上前亂咬,也有咬去手的,也有咬出肚腸的。何立嚇得心驚膽顫,緊緊跟著侍者,過(guò)了惡狗村。
這些惡狗似乎是人間那些勢(shì)利眼小人所化,所以只揀窮困潦倒的路人撕咬。但還有另一種說(shuō)法,就是閻羅王把惡狗村當(dāng)成懲罰罪惡的一種刑罰,清人朱海《妄妄錄》卷九“現(xiàn)在地獄”一條有云:某甲與鄰婦私通,鄰夫死后告到冥府,某甲遂被冥府勾去。抵一公廨,只見(jiàn)自己的一個(gè)親戚不知為何事被牛頭鬼押出,道是要押到惡狗村受無(wú)量苦。故事沒(méi)有詳說(shuō)陰間惡狗村的情況,只說(shuō)某甲還陽(yáng)之后,方知那位親戚已經(jīng)死了一個(gè)多月,“暴棺郊外,棺薄尸臭,為野狗撞破棺板,啣嚼骨肉,狼籍滿地。”
嘉慶間署名歸鋤子的《紅樓夢(mèng)補(bǔ)》第十七回“賈母惡狗村玩新景,鳳姐望鄉(xiāng)臺(tái)潑舊醋”提到的惡狗村就沒(méi)有那么可怕,而很像是游野生動(dòng)物園了:
正在看的高興,忽然那茅屋籬邊走出一只狗來(lái),那狗從沒(méi)見(jiàn)過(guò)這些人夫轎馬的,便遠(yuǎn)遠(yuǎn)望著叫起來(lái)了。這一家的狗叫,便引了那別家的狗聽(tīng)見(jiàn)了,也都出來(lái)叫了,叫著便都跑向轎前來(lái)了。少頃竟聚了百十只大狗,圍住了賈母等的大轎,咆哮亂叫。賈母和鳳姐都怕起來(lái)了,賈珠忙叫人把預(yù)備下的蒸饃,四下里撂了有兩百個(gè)出去。那些狗都去搶饃吃去了,便不叫了。賈母問(wèn)道:“你們預(yù)備下這些蒸饃,原來(lái)是知道有這狗的么?”賈珠道:“這里叫做惡狗村,原是有名兒的地方兒,打從這里過(guò)就要預(yù)備的,若不預(yù)備這些東西,憑你是怎么喝,怎么打,他都不怕的。若打急了他,他便上來(lái)咬人了。這里原有景致,有名兒的叫做‘惡狗村踏青’,是冥中八景里頭的一景呢。”
游戲筆墨,但里面卻寫(xiě)了清代的一個(gè)喪葬民俗,胡樸安《中華全國(guó)風(fēng)俗志》下編記南京民間喪俗有“打狗餅”:“俗傳人死必經(jīng)惡狗村。故易衣后,必以龍眼七枚懸于手腕,以面作球亦可。俗云持之可御惡狗之噬。”這打狗餅在別的地方或作饅頭之類,正是賈珠過(guò)村之前預(yù)備的那些。
有的書(shū)提到,過(guò)了惡狗村,還有個(gè)“亂鬼莊”,一群窮鬼拉扯著你要錢。此處省略不提,以免讀者聯(lián)想,以為是影射那種硬湊景點(diǎn)多收門票的旅游勝地。
破錢山
清?梁章鉅《浪跡三談》卷四言及冥府有“破錢山”,但未做任何說(shuō)明:
……言已,復(fù)帶凌女游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劍樹(shù)鐵床、磋磨臼碓、水浸石壓等獄,又如鬼門關(guān)、望鄉(xiāng)臺(tái)、孟婆莊、破錢山等處,無(wú)不遍歷。……
清?慵訥居士《咫聞錄》卷五“畢發(fā)”條解釋了破錢山的用途,同時(shí)又提起了一座爛銀山:
冥間以紙為錢,猶陽(yáng)間以銅鑄錢也。陽(yáng)世錢有大小,猶冥間錢有好丑也。陽(yáng)世造錢,銅七鉛三,而歹者猶可回爐。冥錢則陽(yáng)間所造,若破爛楮錢,并紙多錫少銀錠,雖多多焚燒,冥中不用,錢棄于破錢山,銀棄于爛銀山矣。且陽(yáng)間金錠銀錠,冥中視之,極為低色,小錠算為三分,中者算五分,大者所算不過(guò)一錢而已。
原來(lái)這景點(diǎn)不過(guò)是個(gè)金光燦燦的垃圾堆,專門堆積民間焚化的不合規(guī)格的銅錢及銀錠的。那些東西在人間化成了灰,到了陰間便現(xiàn)為銀銅,但或因肉好殘破,或因成色不足,不能上市流通,便成了廢品,堆成一景。但既然仍是銅銀,把它回爐重鑄就是,總不至于廢棄吧,所以這個(gè)廢品堆也可以視同原料庫(kù)。陰間冥府里專有一個(gè)機(jī)構(gòu),是給人世間的大官鑄錢的,所取原料的來(lái)源估計(jì)就是破錢山。
唐?李冗《獨(dú)異志》中有一故事,講的就是這事:宰相盧懷慎無(wú)疾暴卒,兒女們大哭。夫人崔氏讓他們別哭,道:“我知道,老爺?shù)拿粫?huì)盡的。他清儉而潔廉,蹇進(jìn)而謙退,四方賂遺,毫發(fā)不留。而和他同為宰相的那個(gè)張說(shuō),收的賄賂堆積如山,仍然健在。張說(shuō)不死卻讓我們老爺先死,老天不是瞎了眼么!”等到夜里,盧懷慎果然又活了過(guò)來(lái),道:“不是那個(gè)理兒。冥司里有三十座洪爐,日日夜夜不停地為張說(shuō)鼓鑄橫財(cái)。我卻連一個(gè)爐也沒(méi)有,豈可相提并論?”交代清楚后一閉眼,再也不醒過(guò)來(lái)了。
這故事一定有人愛(ài)聽(tīng)。既然貪官家里的鈔票都是陰司專門為他造的,那些“不明財(cái)產(chǎn)”的來(lái)歷還追究什么呢。從人間焚紙錢賄賂冥府,陰司再鑄銅錢給人間的官僚做冥福。錢洗得干干凈凈,這種雙向的空手道真是妙極了。
血污池
血污池又名血河池,源于佛經(jīng)中的“血河”。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shuō)華手經(jīng)》卷七:“魔即化作四大血池,其血充滿,於此池邊流四血河。”本與地獄無(wú)關(guān)。至唐?般剌密帝譯《楞嚴(yán)經(jīng)》卷八:“故有血河、灰河、熱沙、毒海、融銅、灌舌諸事。”則血河已經(jīng)成了地獄的一項(xiàng)酷刑。而《正法念處經(jīng)》卷十述大叫喚大地獄之十六處小地獄,其六即名“血河漂”,并云入此地獄者為自殘其身以修行外道者。如“入樹(shù)林中,懸腳著樹(shù)頭面在下,以刀破鼻,或自破額,作瘡血出,以火燒血,望得生天”這類殘身修道者不但成不了道,反而要“墮于惡處,在彼地獄血河漂處,受大苦惱”。
可是不知從什么時(shí)候起,這地獄到了中國(guó)就成了專為婦人所設(shè)的了。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續(xù)編》卷五“佛姆化導(dǎo)”條云:“先見(jiàn)血河浩渺無(wú)涯,有諸女人或倒浸河內(nèi),或蓬發(fā)上指,或側(cè)身橫睡,血流遍體。”這些婦人犯了什么罪而墮入血河,此條未講。但從袁枚《子不語(yǔ)》卷二十二“吳生兩入陰間”一條中可知,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內(nèi),人們認(rèn)為婦人入血污池是因?yàn)樗?jīng)生育,袁枚在故事中借一老嫗之口對(duì)此做了反駁:
吳問(wèn):“我娘子并未生產(chǎn),何入此池?”嫗言:“我前已言明,此池非為生產(chǎn)故也。生產(chǎn)是人間常事,有何罪過(guò)?”
這種為袁枚反駁的謬見(jiàn),《禪真逸史》中卻有個(gè)樣板,在其書(shū)第六回中說(shuō),婦人產(chǎn)育,本身就有了“血沖三光”之罪,倘若是難產(chǎn)而死,那就罪上加罪:“那時(shí)萬(wàn)孽隨身,一靈受罪。閻王老子好生利害,查勘孽簿,叫牛頭馬面叉落血污池里,不得出頭。又有那鷹蛇來(lái)囋,惡犬來(lái)咬。”同樣是人身上的血,婦人下身流出的就是污穢,甚至有了某種邪力,以至紅太陽(yáng)不那么光輝了也是“血沖”的結(jié)果。這種鄉(xiāng)下巫師謬見(jiàn)的根由,大抵與道學(xué)家性神秘的卑瑣之見(jiàn)有關(guān)。道學(xué)流布到下層,往往就生成妖孽。在他們眼里,婦人下體所具有的污穢之力,不僅能污染大氣,讓三光失色,而且在戰(zhàn)場(chǎng)上可以把當(dāng)時(shí)原子彈級(jí)別的武器紅夷大炮變成啞巴。清初董含《三岡識(shí)略》中有一則紀(jì)事云:
先是,流寇圍汴梁,城中固守,力攻三次,俱不能克。賊計(jì)窮,搜婦人數(shù)百,悉露下體,倒植于地,向城嫚罵,號(hào)曰“陰門陣”,城上炮皆不能發(fā)。陳將軍永福急取僧人,數(shù)略相當(dāng),令赤身立垛口對(duì)之,謂之“陽(yáng)門陣”,賊炮亦退后不發(fā)。
張岱的《石匱書(shū)后集》所記更奇:
崇禎九年,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dòng)七賊連營(yíng)數(shù)十萬(wàn)攻滁州。……行太仆寺卿李覺(jué)斯、知州劉太鞏督率士民固守。……城上連炮擊之,賊死益眾。癸丑,賊退,掠村落山谷婦女?dāng)?shù)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斫其頭,孕者則刳其腹,環(huán)向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穢淋漓,以厭諸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向城,城上燃炮,炮皆迸裂,或喑不鳴,城中惶懼。覺(jué)斯立命取民間圊牏亦數(shù)百枚,如其數(shù)懸堞外向,以厭勝之。燃炮皆發(fā),賊復(fù)大創(chuàng)。賊怒,攻益急。
官和匪的陰陽(yáng)斗法完全是出于同一師傳。而董含又道:“后群盜屢用之,往往有驗(yàn)。”可見(jiàn)下民所施巫術(shù)的威力也為士大夫所相信。
但那種忘記自己是從何處而來(lái)的渾人究竟是少數(shù),所以血污池專為生育婦人所設(shè)的昏話也就不大時(shí)興,但演變?yōu)榱硪环N說(shuō)法,仍然是專為婦人所設(shè)。如《濟(jì)公全傳》第一百五十回認(rèn)為是:
這些婦人,有不敬翁姑的,有不惜五谷的,有不信神佛的,有不敬丈夫的,死后應(yīng)該入污池喝血,此即血污池也。
而袁枚認(rèn)為入血池的是毒虐婢妾的婦人:
行至一處,見(jiàn)一大池,水紅色,婦女在內(nèi)哀號(hào)。常指曰:“此即佛家所為血污池也。入此池者,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凡毆婢妾見(jiàn)血不止者,即入此池。”
血污池所以專和婦人作對(duì),紀(jì)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九的解釋最中要害。有一走無(wú)常的人,到了冥間詢問(wèn)冥吏,人間念誦《血盆經(jīng)懺》究竟有沒(méi)有用。冥吏則一口否認(rèn),冥間根本就沒(méi)有血污池,血河之說(shuō)純屬騙局,目的是要誆騙婦女錢財(cái):
為是說(shuō)者,蓋以最易惑者惟婦女,而婦女所必不免者惟產(chǎn)育,以是為有罪,以是罪為非懺不可;而閨閣之財(cái),無(wú)不充功德之費(fèi)矣。
《玉歷寶鈔》所論多悖謬,唯在此事上略有頭腦,并且連男人也一起扔進(jìn)了血池,當(dāng)然中間昏話依然不少:
設(shè)此污池,無(wú)論男女,凡在陽(yáng)世不顧神前佛后,不忌日辰,如五月十四十五、八月初三十三,十月初十,此四日男婦犯禁交媾,除神降惡疾暴亡,受過(guò)諸獄苦后,水浸其池,不得出頭。及男婦而好宰殺,血濺廚灶神佛廟堂經(jīng)典書(shū)章字紙一切祭祀器皿之上者,受過(guò)別惡諸獄苦后,解到浸入此池,亦不得輕易出頭。
俞樾在《右臺(tái)仙館筆記》卷五中又有了新的說(shuō)法。一是走無(wú)常的俞君所述:“血污池專治男子。凡男子惟一娶者,不入此池;再娶者即須入池一次;三娶者,入二次。若有妾者,入池之?dāng)?shù)視妾之?dāng)?shù)。”把血污池變成了多妻妾男人的地獄,這位走無(wú)常的俞君頗有女權(quán)觀念,很像是在影射《癸巳存稿》的作者俞理初。俞樾認(rèn)為這位本家的說(shuō)法是“可為色荒者戒,然于理實(shí)未是也。”他不愧是曾國(guó)藩的弟子,便向冥府提出血污池的改革建議,專門懲治婚外戀以及私奔野合、不由媒妁諸種情事,不管男女,都扔了進(jìn)去:
余謂冥中無(wú)血污池則已,誠(chéng)有之,必為男女之不以禮合者而設(shè)。外婦私夫,悉入其中,則情罪允洽矣。
血污池既然已經(jīng)成了冥間的刑罰,所以自應(yīng)在閻王殿之側(cè)近。但最早的說(shuō)法卻并不盡如此。前面介紹奈河時(shí)說(shuō)過(guò),有的書(shū)就把血污池安排在奈河橋下,只要從橋上失足栽下,就要墜入此池,卻是不分男女良賤的。聽(tīng)說(shuō)酆都鬼城的血污池也是這樣的布置,但只是一汪淺水,污有可能,血是絕對(duì)沒(méi)有的。
孟婆店
孟婆店就是專門供應(yīng)迷魂湯的茶店。店主是孟婆,其茶也如“狗不理”一樣,物以人名,叫做“孟婆湯”,卻是無(wú)人假冒的真正百年老字號(hào)。
幾千年前,古希臘神話的冥界就有“忘泉”,或譯“忘川”,但中國(guó)的孟婆湯卻出現(xiàn)得很晚,保守地說(shuō),只是到明代才見(jiàn)于文字,真讓人不好意思。可是在這迷魂湯出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有了冥間茶水與陽(yáng)世不同的說(shuō)法。其所以不同,就是入冥而尚須還陽(yáng)的人,是不能喝陰間的茶水的,因?yàn)楹攘司筒荒茉倩氐疥?yáng)世,只好留在那里做鬼。《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五引《玄怪錄》(《說(shuō)郛》引作《河?xùn)|記》)云:崔紹至陰司,有王判官降階相見(jiàn)。茶到,判官云:“勿吃,此非人間茶。”洪邁《夷堅(jiān)乙志》卷四“張文規(guī)”說(shuō)的更明確,道:“有持水漿來(lái)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
不僅是茶水,就是冥間的飯食也不能吃。那緣由不難理解,冥界的食物只能來(lái)源于人間,而墳?zāi)估锱阍岬氖称酚忠欢ㄒ冑|(zhì),化為腐臭甚至一攤爛泥。這些腐臭的食品正如其他朽敗的衣物一樣,從冥界一方來(lái)看,卻是很新鮮的。生魂在冥間吃的是看似新鮮的東西,但還陽(yáng)之后,這些肚子里帶回的東西就也隨之“還陽(yáng)”為腐物,于是不死也要大病一場(chǎng)。茶水本無(wú)須有這些顧慮,卻也不能讓生魂飲用,這就是被熱粥燙了嘴,見(jiàn)了臭豆腐也要吹一吹了。但是例外卻也不少,其中就有專供生魂喝的東西。唐人李伯言《續(xù)玄怪錄》“王國(guó)良”條,記冥府中有種飲料,是專供暫到冥界卻還要回歸陽(yáng)世的人喝的,因?yàn)楹攘酥螅筒粫?huì)忘掉在陰間的所見(jiàn)所聞,以便還陽(yáng)之后,巨細(xì)無(wú)遺地宣傳冥間果報(bào),以儆世人。冥間既有可以防止失憶的茶,也就不妨再有抹去記憶的茶,只要有必要,隨時(shí)都可以造出來(lái)的。
關(guān)于迷魂湯的記載,明?朱孟震《河上楮談》卷一“記前生”算是較早的了:
有一仆,年可十二三,自言前世為淮陰民楊氏女,名小閨子,九歲死。死時(shí)人引至一處,男女群聚,各飲以羹。人競(jìng)?cè)∑黠嫞?dú)幼,不能得器,或與一瓦,女墜瓦地上。忽促之去,不得飲。已乃墮一池中,覺(jué),復(fù)生淮陰民家為子。三歲時(shí)父抱就某橋買糕餌,見(jiàn)其前父,手挽之曰:“我閨子也。”父不能識(shí),乃求歸其家,見(jiàn)前母,為道前世事歷歷。二家因共子之。
所飲之羹即是迷魂湯,只是沒(méi)有說(shuō)出名子。喝湯并不需要強(qiáng)制,鬼魂們大約已經(jīng)渴到了十分,所以只有擠搶著才能喝上。而且這迷魂湯是在臨轉(zhuǎn)世時(shí)才喝,也是合乎情理的,不像有些民間傳說(shuō),認(rèn)為人死后到了陰間先喝迷魂湯,如此則喝下之后連自己是誰(shuí)都懵然,還怎么到十王殿去過(guò)堂?那種入冥先喝湯的說(shuō)法亦見(jiàn)于小說(shuō),最典型的就是《聊齋志異》中的《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自言一世為搢紳,行多玷。六十二歲而歿,初見(jiàn)冥王,待如鄉(xiāng)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覷冥王盞中茶色清徹,己盞中濁如膠。暗疑迷魂湯得勿此乎?乘冥王他顧,以盞就案角瀉之,偽為盡者。
還有陳叔文《回陽(yáng)記》:
是夜昏暈,魂從頂出,欲往冥府,明此果報(bào)。忽見(jiàn)本境土地引余而囑曰:“此去有三路,汝須從中路往,馀二路非汝所宜行也,途中湯切勿飲,關(guān)內(nèi)橋切勿過(guò)。犯此三者,必不能回生矣。”余曰:“唯。”未幾,前途果有一婆施湯,湯甚香,飲者甚眾。余至?xí)r果招飲,余即潑地。鬼欲來(lái)?yè)簦藕仍唬骸按耸侨郎豢伞!蹦说妹摗2粩?shù)武,至鬼門關(guān)。
這里的施湯婆婆沒(méi)說(shuō)出姓孟,而且在入鬼門關(guān)之前就要喝湯,也頗為不妥。
到了《續(xù)金瓶梅》第五回中,就有了“迷魂湯”這名目,而且出現(xiàn)了孟婆:“原來(lái)孟婆酒飯就是迷魂湯,吃了骨肉當(dāng)面昏迷(即親骨肉都覿面不識(shí))。”作者丁耀亢是明末清初人,我們不妨認(rèn)為迷魂湯之說(shuō)最晚起于明代。
孟婆神在以往有過(guò)風(fēng)神和船神兩說(shuō),此處的孟婆倒不是風(fēng)神船神的兼職,而是“冥”“孟”二字音近,孟婆即冥婆。在清人編的《玉歷寶鈔》中就為這個(gè)新出現(xiàn)的冥神編出了履歷:
孟婆神,生于前漢,幼讀儒書(shū),壯誦佛經(jīng),凡有過(guò)去之事不思,未來(lái)之事不想,在世唯勸人戒殺吃素。年至八十一歲,鶴發(fā)童顏,終是處女,只知自己姓孟,人故稱之曰孟婆阿奶,入山修真。至后漢,世人有知前世因者,妄認(rèn)前生眷屬,好行智術(shù),露泄陰機(jī)。是以上天敕令孟氏女為幽冥之神,造筑醧忘一臺(tái),準(zhǔn)選鬼吏使喚,將十殿擬定發(fā)往何地為人之鬼魂,用采取俗世藥物,合成似酒非酒之湯,分為甘苦辛酸咸五味,諸魂轉(zhuǎn)世,派飲此湯,使忘前生各事。帶往陽(yáng)間,或思涎,或笑汗,或慮涕,或泣怒,或唾恐,分別常帶一二三分病。為善者,使其眼耳鼻舌四肢較于往昔愈精愈明,愈強(qiáng)愈健。作惡者,使其消耗音智神白色魂血精志,漸成疲憊之軀。而預(yù)報(bào)知,令人懺悔為善。
臺(tái)居第十殿冥王殿前六橋之外,高大如方丈,四圍廊房一百零八間。向東甬道一條,僅闊一尺四寸。凡奉交到男女等魂,廊房各設(shè)盞具,招飲此湯,多飲少吃不論。如有刁狡鬼魂不肯飲吞此湯者,腳下現(xiàn)出鉤刀絆住,上以銅管刺喉,受疼灌吞。
孟婆所管的地方叫“醧忘臺(tái)”,所以迷魂湯也叫做“忘醧”或“孟婆茶”。但這茶的功效不僅是使人忘記前生,還是一種奇異的藥湯,看似本是一種,不同的人喝了卻有不同的結(jié)果,要帶到下世的。可是,來(lái)世的果報(bào)不是已經(jīng)在閻王爺那里定下了么,何必又讓孟婆多此一舉呢?實(shí)在不通。另外,《玉歷寶鈔》把冥界的所有地方都寫(xiě)成死囚牢一般,慈祥的孟婆阿奶身邊也要配上一套鉤刀銅管的現(xiàn)代化刑具,這也可以看出作者不正常的酷吏心理。

在一些小說(shuō)和民間故事中卻不是這樣,孟阿奶管的地方叫孟婆村或孟婆店,從名子上就很有些人情味了。可是還有另一個(gè)極端的說(shuō)法,把這迷魂湯竟當(dāng)作一種后現(xiàn)代的逼供刑具。清代一個(gè)起名叫伏雌教主的人寫(xiě)了本小說(shuō)《醋葫蘆》,在第十六回中說(shuō)道:
原來(lái)地府中,若個(gè)個(gè)要用刑法取供,一日閻羅也是難做,虧殺最妙是這盞孟婆湯。俗話:“孟婆湯,又非酒醴又非漿,好人吃了醺醺醉,惡人吃了亂顛狂。”怪不得都氏正渴之際,只這一碗飲下,也不用夾棍拶子,竟把一生事跡兜底道出。孟婆婆一一錄完,做下一紙供狀,發(fā)放磷仵,帶送十殿案下。
在這里,笑咪咪的孟婆阿奶竟好像是牛頭阿旁了。但這只是見(jiàn)于小說(shuō)的“一家之言”,并未被相信陰曹地府的大眾所采信。
按理說(shuō),不管有沒(méi)有孟婆湯,人們也不會(huì)記住前生的,明代以前的上千年就是這么過(guò)來(lái)的,似也沒(méi)出什么大亂子。那么何必多此一舉,突然想起要喝這碗湯呢?當(dāng)然這對(duì)論證輪回轉(zhuǎn)世之說(shuō)是很動(dòng)聽(tīng)的一個(gè)論據(jù),但卻似乎并不是僅此一個(gè)理由。
在鬼故事中,冥界的鬼魂是猶記生前事的,所以他才能與在世的親屬夢(mèng)中往來(lái),幽會(huì)繾綣,一如平生,儼如陽(yáng)世生活的延續(xù)。但一旦鬼魂的一方要轉(zhuǎn)世為人,于是而成為真正的永別,不但是別而已矣,那投生者竟把一切前緣全都忘記,即使到了人世,竟至覿面而不相識(shí)了,還到哪里去尋找再世的姻緣?《法苑珠林》卷七十五引《志怪傳》的一則故事就講了“一為世人,無(wú)容復(fù)知宿命”這個(gè)令人鬼都黯然神傷的“道理”。這也是佛教的輪回轉(zhuǎn)世說(shuō)對(duì)中國(guó)俗人情感的最大沖擊,但孟婆湯卻給了人們一點(diǎn)兒希望:轉(zhuǎn)生的鬼魂喝了孟婆湯就會(huì)盡忘前緣,可是如果不喝呢?這便為來(lái)世的因緣留下了一絲絲機(jī)會(huì)。當(dāng)然,這機(jī)會(huì)是很渺茫的,所以更多的只是寄托著生人的惓惓之情而已。
但不管怎樣,民間的喪俗中是把逃避喝孟婆湯當(dāng)成一個(gè)節(jié)目了。胡樸安《中華全國(guó)風(fēng)俗志》下編說(shuō)到浙江湖州的風(fēng)俗:
俗傳人死后,須食孟婆湯以迷其心。故臨死時(shí),口啣銀錠之外,并用甘露葉做成一菱附入,手中又放茶葉一包,以為死去有此兩物,似可不食孟婆湯。
而安徽壽春則略有簡(jiǎn)化,是“成殮時(shí),以茶葉一包,加之土灰,置于死者之手中”。新奇一些的是北京。愛(ài)新覺(jué)羅?瀛生先生談到發(fā)喪的“摔盆”風(fēng)俗時(shí)說(shuō):陰間有位“王媽媽”,要強(qiáng)迫死者喝一碗“迷魂湯”,使其神智迷糊,以至不能投生。所以喪家要準(zhǔn)備一有孔的瓦盆,發(fā)喪時(shí)由“孝子”向地上猛摔,如若摔碎,那盆便隨著死者進(jìn)入陰間,王媽媽的“迷魂湯”就要漏掉了。
雖然如此,我卻是主張老老實(shí)實(shí)喝下那碗迷魂湯的。人的魂靈經(jīng)過(guò)閻羅大王、牛頭鬼卒們的“熱堂”,不要說(shuō)遍歷九幽十八獄,即是隨便把鋸解、油烹、蠆盆、蛇鉆、割舌、剜眼之類的小節(jié)目讓你見(jiàn)識(shí)一二種,哪怕只是旁觀吧,也足以讓人精神崩潰的。倘若帶著那種記憶進(jìn)入娘肚子里,恐怕呱呱落地伊始就已經(jīng)是精神分裂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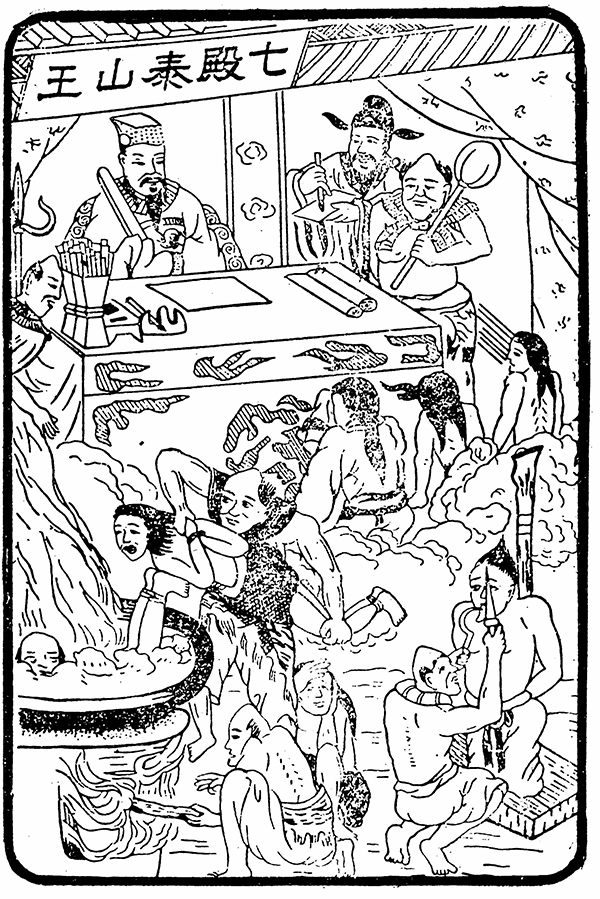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