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歷史學家能從“非虛構寫作”中學習什么?
【編者按】
“非虛構寫作”目前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然而一個學院派的歷史研究者,會怎樣看待和反思這種寫作方式呢?以嚴謹、求真、價值中立為要求的歷史學家們,又能從汪洋恣肆的“非虛構寫作”中,學習些什么呢?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琳的文章,或許能給我們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
2016年11月底,我應“麗澤書院”的邀請,為同學們主持了一次關于“非虛構寫作”的沙龍,這篇文章就是從那次沙龍的講稿整理而來。她其實是一個比較隨性的寫作,是我個人在閱讀過程中的一些不吐不快的想法。坦白地說,我也不愿意把她寫成一篇中規中矩的學術論文,因為她所聚焦的“非虛構寫作”,本身就是為了追求一種更加自由、更具親和力、表現力的敘述方式。毋庸諱言,“非虛構寫作”目前還處于實驗階段,但也正是這種類似于青春期少年的叛逆、浪漫和不拘一格,才讓她具有了直擊人心的魅力。

一、什么是“非虛構寫作”
“非虛構寫作”是時下一個很熱門的話題。許多新的出版物都標榜自己屬于非虛構寫作,一些門戶網站也開辟了非虛構寫作專欄,比如“騰訊.谷雨”。2015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題目是“假如與我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這其實也是典型的非虛構寫作。
可是如果我們犯了學者的職業病,必須要對“非虛構寫作”下一個定義的話,你會發現,其實很少有人對這個詞有特別清晰又特別自信的理解。我曾經專門請教主持過“非虛構寫作沙龍”的著名媒體人張豐先生,究竟什么才是他理解中的非虛構寫作,但是他的第一反應竟然是:“這個問題重要嗎?”這樣的情況,與其說是因為人們少了一點學者的嚴謹和概念抽象的自覺,倒不如說是因為這種寫作形式現在仍然在不斷的探索和試驗之中。各種不同風格、不同題材、不同寫作手法的新作品令人眼花繚亂,也讓習慣于學術思維的頭腦感到深深的無力,甚至是一說即成錯。但是為了給后面的討論確立一個前提,我們還是要交代一下什么是“非虛構寫作”?或者說在一個歷史研究者的眼中,什么是“非虛構寫作”?
如果你在“百度”上輸入“非虛構寫作”這個詞條,出現得最多的一個定義就是:
一切以現實元素為背景的寫作行為,均可稱之為非虛構寫作。又被稱為“第四類寫作”。
這個定義看起來非常簡單,但是對于理解我們所要談論的這種“非虛構寫作”基本上沒有什么幫助。因為如果你接受了這個定義,那么你一定會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區別我們現在所談論的“非虛構寫作”和人們之前非常熟悉的紀實文學、傳記、調查報告、游記、回憶錄,甚至是我們所寫的歷史學或社會學論文?表面上看,后面講的這些也是以現實元素為背景的寫作行為呀。但是我們談到“非虛構寫作”的時候,說的好像并不是這些。也就是說,現在被許多寫作者實踐著的,也被越來越多的讀者所認可的,其實是一種狹義的“非虛構寫作”。根據我自己有限的閱讀經驗,一個高質量的非虛構作品,大概要具備以下幾點特征(或者至少要具備以下一部分特征):
1、敘述歷史或當下真正存在的人或事,簡而言之就是“寫實”。
2、用深度介入的方式挖掘真相,也就是“求真”。
3、用精心構建的敘事結構、寫作技巧和語言來塑造作品的品質,或者可以說是“好好講故事”。
4、用個人的視角進行獨立的寫作。
在我看來,最后一點其實是最重要的。這也是為什么踐行非虛構寫作的人,要給他們自己寫的東西重新起一個聽起來相當拗口的名字。因為這種寫作,她在價值觀上是獨立而且叛逆的,她其實是基于人們對傳統文學和歷史寫作方式的不滿,故而自立門戶出來的一個部分。而且至少在今天的中國,連“非虛構寫作”的載體也并不是那么主流。許多進行非虛構創作的人們,并沒有開宗建派、著書立說,他們許多都是自由作者,依托新媒體、自媒體進行創作。然而或許正是因為這種近乎“野生”的狀態,使得非虛構寫作能夠在束縛和苛責相對較少的情況下自由探索,專注表達,從而迸發出直擊人心的魅力和生命力(筆者按:國外的非虛構寫作情況非常不同,筆者了解不深,所以本文主要是基于中國的非虛構寫作而討論)。
下面,我就從一個學院派歷史研究者的視角,結合一些深深打動過我的非虛構作品,來談一談與“非虛構寫作”相關的幾個問題。我并不想說“如有不當,還請指正”之類的套話,因為這篇小文其實只相當于一個普及帖,肯定會有很多的“不當”,簡直不值一駁。但是毋庸諱言,這篇文章中不免會有一些對前輩師長、年輕學友的苛責,然而這只是出于對現有歷史敘述方式的反思,沒有任何不敬之意。如有無意之中的冒犯,在此先行致歉!
二、非虛構寫作如何“寫實”?
說到“寫實”這一點,歷史學家大概是最有自信的。但是我要非常遺憾地告訴你,其實很多寫歷史的學術或非學術作品,并不是特別尊重或者在意那個所謂的“實”。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那部婦孺皆知、被許多人視為明史啟蒙讀物的《明朝那些事兒》。每年開“明清史專題”課程的時候,都有一些同學來問我:“老師,我的讀書報告能不能寫《明朝那些事兒》?”我的回答永遠都是“Absolutely No !”為什么呢?因為我覺得這部書就好像把明朝的歷史放在哈哈鏡前去照一樣。下面舉幾個例子:
急性子的夏言興沖沖地跑去西苑了,他要表達自己的興奮。而那坐在陰暗角落里的嚴嵩,卻露出了笑容。
徐有貞終于成功了,他帶著疲憊的身軀和長時間的笑容,獨自站在大門前,擋住了上殿的道路。
被嚇出了一身汗的李賢和王翱這才松了一口氣,落到這么個精神不正常的家伙手里,他們也只有認命了。
這樣文字當然非常能夠討好讀者,因為它生動,畫面感很強,不僅有人物的唱念坐打,甚至還有他們的內心獨白。那閱讀體驗,簡直和看電視劇沒啥區別。你想一想,如果換一種平淡的表達方式是什么效果呢?“夏言獨自走向西苑去了,嚴嵩獨自坐在內閣值房”。“徐有貞站在大門前,擋住上殿的道路”;“最后,曹欽并沒有殺李賢和王翱”。不用說,這兩種敘述方式的表現力,簡直就像是五糧液和白開水的差別。但是我要告訴你,根據我讀明代史書的經驗,后面一種表述可能是更接近史料的原文的。因為即便明代人的率真和表達欲遠超中國古代史上的任何時代,但是他們寫下的大部分著作仍然沒有那么豐富的細節。也就是說,在上面這三句話中,大約有一半的文字都屬于作者添加上去的水分。不管是對于學術性的歷史寫作而言,還是對于非虛構性的歷史寫作而言,這都是嚴重違反工作紀律的。
你或許會說,這就是些細節而已,無傷大雅,用不著那么較真吧。但是如果在作者的頭腦中,迎合讀者的想法占了第一位。那么在細節上可以注水,在關鍵性的地方同樣可以注水。所以我認為,《明朝那些事兒》更適合用來娛樂大眾。如果一定要用“虛構”或“真實”來評判的話,那我會說它是一部“半虛構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寫現實的事情,注入一定的水份還好一些,因為你的讀者或許比你了解得更多,或者至少都是有一定的親身經驗和常識的,能夠分辨你寫的東西里面哪些是實,哪些是虛。但是歷史作品的讀者和作者之間,幾乎完全是一種信息不對稱的關系,你注入的水分很難被發覺。所以就會讓人們認為,那些被注過水的東西就是真正的歷史。所以雖然我自己也很喜歡看《明朝那些事兒》,但我從不把他推薦給我課堂上的同學。
如果說非專業的歷史作家出于各種原因臆造細節,那么專業的歷史學家最容易犯的錯誤恰恰是無視細節。《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 一書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這樣的例子。當然,這本書的第一作者李中清先生是曾給予我很多教導的老師,,我個人認為這本書也是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口史領域最振聾發聵的作品,至今仍然未被超越。而且更令人嘆服的是,兩位作者對于中國“一胎政策”的評估和預言,居然被后來中國的經濟、社會變遷一一證實。但就是在這本書中,有一個細節讓我感到非常不適,那就是關于溺嬰的論述。

兩位作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并不是聽任人口惡性膨脹,而是有一些行之有效的人口控制機制,溺嬰就是其中的一個。書中的原文如下:
溺嬰是一種理性決策的結果,根植于一種獨特的生命觀文化。中國的農民不會把殺死親生子女看作是謀殺。中國人在傳統上并不把未滿一周歲的嬰兒看作完全的人。實際上,有一句很有名而且經常被提到的話,說嬰兒只是幼崽,到“兩歲”生命才開始。因此中國的農民和貴族同樣可能把溺嬰看作是一種“產后流產”。
坦白地說,從我十年前第一次看這本書到現在,這句話始終令我充滿質疑而且抵觸。兩位作者認為,溺嬰對于傳統中國人來說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們通常會以一種平常心來看待他。這實在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再仔細去看他們引用的文獻,都是《唐會要》中說怎樣怎樣,《周禮》中說怎樣怎樣,明朝的丘浚說怎樣怎樣。可是我想問的是,寫《周禮》的人和寫《唐會要》的人他們溺過嬰嗎?明朝的丘浚他溺過嬰嗎?為什么相信他們能夠真實地表達父母溺嬰時的內心狀態?雖然我們知道不同時代的親子關系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另一個時代的父母真的會完全按照另一種邏輯和感情模式對待自己的孩子嗎?而且用溺嬰來說明中國人口控制機制的有效性,進而證明清經濟、社會并非那么不可救藥,這實在是一個說不通的邏輯。如果一個時代的發展要一定程度上依賴那些被溺死的小小的亡魂,這樣的經濟和社會還有什么正面評價的意義呢?所以,“傳統的中國人怎樣看待溺嬰”,其實是一個被作者忽略,但實際上需要去證明的細節。
三、非虛構寫作如何對待細節?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優秀的非虛構寫作,是怎樣對待細節的呢?
在談論這一部分之前,請允許我首先介紹一本書,這本書名為《哈佛非虛構寫作課:怎樣講好一個故事》。她源自于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The Nieman Foundation)每年舉辦的尼曼敘事新聞會議(the Nieman Conference on Narrative Journalism)。這個會議的主題就是“非虛構敘事的藝術和技巧”,參與者包括全世界的新聞記者、編劇、編輯和作家。這本書匯集了51位會議發言人的91篇文章,從各個細微的環節告訴你成功的非虛構寫作者究竟如何工作。即便你不想進行非虛構寫作,此書也絕對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讀物。

下面再回到我們正在談論的“細節”問題。我個人的體會是,好的非虛構寫作一定是關注細節的。在這本書中,普利策獎得主伊莎貝爾.威爾克森(Isabel Wilkerson)展示了她的作品《尼古拉斯的男子漢生活,10》(The manful life of Nicholas, 10)中的一個細節:
孩子們排成一列,還有他們的圍巾、外套和腿。男孩們低下頭,這樣母親還能再為他們做一次梳理。雖然她自己上課要遲到了。丟失的手套引起一陣騷亂,接著母親搖了搖一瓶噴罐,在孩子們的外套上、頭上、攤開的小手上來回噴灑,以庇護孩子們上學這一路,因為他們要面對這瘋狂而危險的世界中的黑幫招募和子彈。噴在他們身上的是一種聞起來像藥房香精的宗教圣油。孩子們緊閉眼睛——為了他們能夠在日落時分活著并安好地歸來,安杰拉的噴霧,總是長足有力。
正是從這個頗具儀式感的細節中,伊莎貝爾瞬間理解了暴力對這些生活在芝加哥南部底層家庭的孩子而言,已經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狀態。在看到這個場景之前,她本來已經就“在暴力環境中如何保護自己”的問題,與孩子的母親聊了好幾個小時,都已經準備結束采訪開始寫作了。但是這個場景的出現,讓她改變了寫作思路。后來,這段文字如一個特寫鏡頭一般被放在文章的末尾,收獲了“于無聲處聽驚雷”的表達效果。
但是另一方面,負責任的非虛構寫作者也從不會為了討好讀者而去臆造細節。極其擅長非虛構寫作的美國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曾經說過:
我從不捏造任何東西,包括天氣。一個讀者告訴我,他尤其喜歡《八月炮火》中的一段,那一段寫到英軍在法國登陸的下午,一聲夏日驚雷在半空炸響,接著是血色殘陽。他以為是我藝術加工出了一種末世景象,但事實上那是真的。是我在一個英國軍官的回憶中找到了這個細節。如果存在藝術加工,那也僅僅是我挑出了這個細節,最終用對了地方。

以前我常常認為,只有遵循嚴格的學術規范撰寫的歷史論文,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嚴謹和真實。但事實上,“真實”或許只是一個價值目標,在達致這個目標的過程中,學術性寫作方式和非虛構寫作方式并無高下之分。只是與學院派的研究者相比,非虛構寫作者要持守這樣的信念,需要更多的誠實與自制。
為了如實地展現事情原本的樣子,非虛構寫作者有時甚至會面臨倫理上的困境。美國記者索尼婭.納扎里奧(Sonia Nazario)的作品《被天堂遺忘的孩子》(Enrique’s Journey: The Story of a Boy’s Dangerous Odyssey to Reunite with his Mother)曾經獲獎無數。這本書講的就是作者跟隨一位名叫恩里克的洪都拉斯男孩,非法進入美國國境去尋找他在北卡羅萊納州做保姆的媽媽。在這個過程中恩里克經歷了很多危險,包括嚴寒、酷熱、饑渴、響尾蛇、惡警、黑幫、強盜、湍急的河水、行駛的火車。然而除了危及生命的情況(如溺水),索尼婭一直沒有出手幫助他。最后恩里克身上分文全無,一天只靠洗車掙一頓飯錢,他想要打電話給媽媽。可是雖然索尼婭身上有一部手機,但是她一直沒有借給這個孩子。
依常理來說,這樣的做法已經傷及人道。但是對于非虛構寫作者來說,如果處處出手相助,必然會污染細節,進而導致整部作品的真實性流失,這違反了非虛構寫作的工作紀律。而且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還懷抱著另一層意義上的“善”。下面就是她的一段自白:
任何報道這類故事的人都會見證到傷害。這是敘事性報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們必須考量一名孩子所受到的傷害,也見證現實并有力地傳遞給讀者的好處進行衡量。像《被天堂遺忘的孩子》這樣的故事可以激勵我們的讀者更多地思考這些問題,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作為敘事記者,我們必須努力寫出最能打動人心的故事。這就是我們的使命,也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歷史學家的工作容易多了,至少我們不用面臨這樣進退兩難的糾結。
在“明清史專題”的選修課上,我曾經出過一道“穿越題”:
如果有機會穿越回到1644年,你最希望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國籍、居住地、民族、職業、性別、年齡等)?請試著描述那時TA眼中的中國與世界。
其實這就是非虛構寫作的訓練。有的同學告訴我,他們答題的時候每寫一句話都很難,因為不知道他筆下設定的這個人物究竟是不是做過這樣的事情。一旦具體到細節,就覺得好像處處都需要去認真考證一番。其實有這種感覺就對了,這也正是非虛構寫作(或者優秀的歷史劇、歷史小說)相對于學院派的歷史寫作更考究,也更難的地方。因為論文可以省去或回避一些細枝末節的東西,而出色的敘事則必須是一個嚴絲合縫的整體。不僅要有關懷和情懷,還要在細微之處精雕細琢,任何細節的失真都會讓讀者瞬間出戲。近日,看到一則對演員王功松先生的專訪,他講到在扮演“荀彧”這個角色之前,他會去考證“荀彧作為文人身邊應該帶什么類型的香”,“他們吃飯用的碗碟究竟是什么樣式”,甚至細到“碗底一定要有‘君幸食’三個字”等等。看到這里我只想說:“誰說只有歷史學家才有‘求真’的本事?”
四、“深度介入”何以可能?
所謂的“深度介入”,簡單說來就是與你的對象一起生活。
為了寫一群來自墨西哥的挑蟹肉女工,美國記者安妮.赫爾(Anne Hull)曾經與她們一起工作。這份工作看起來沒什么特別之外,但是當她真正站在工作臺前開始勞作,她才發現這份工作極其辛苦而且艱難。因為每天要站10個小時,而且銳利的蟹殼和刀子隨時可能劃到手。有的時候,手已經因為疲勞而發抖,但卻不可以停下來。這時,她才理解了這些女工的艱辛,以及國外勞工在美國的境遇。
一個更加瘋狂的例子是美國作家特德.康諾弗(Ted Conover),為了展現懲戒制度,他把自己送進監獄工作了10個月。在這10個月中,他成功地申請了懲教官的工作,每天把犯人領進領出他們的囚室,和他們交涉,在工作間隙記下各種細節,然后還要時時擔心自己的“臥底”身份暴露,被那些暴力的同事打暈在停車場。最后,他寫出了影響極大的作品《新杰克》(Newjack: Guarding Sing Sing)。
這種寫作方式我們可能比較熟悉,它與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田野調查非常接近。但不同的是,如果以非虛構寫作的標準來衡量,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更強調的是突破空間上的距離。走到你研究的現場,與你的研究對象相接觸。但事實上,心理的距離是更難突破的。在一些人類學作品中(尤其是早期的人類學研究),讀者始終能感受到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在心理上的疏離。當然,近年來所閱讀到的一些人類學研究,開始變得越來越不一樣,這也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
在關于中國的非虛構寫作中,“深度介入”的一個典范,我認為是何偉(Peter Hessler)的《江城》。何偉在27歲的時候,作為“美中友好志愿者”被派到長江邊的小城涪陵教書。《江城》這本書,記錄了他在這個城市兩年的生活。我個人覺得整本書最具魅力的部分,就是他對他的寫作對象透出很多的理解和善意。比如讓小孩到他的房間里面瘋玩,和學生的親密互動,在飯館老板的家里共度春節。全城人都像看熱鬧一樣看他晨跑,他只是說不習慣。甚至在大街上被人圍觀、謾罵,在他的筆下也是徐徐道來、云淡風清。我能夠感覺得到,這種善意絕不是裝出來的。所以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非常豐滿,作為一個在川東地區生長的人,我覺得我平日里見到的家鄉也就是那個樣子,他甚至還發掘出許多當地人都感受不到的東西。這說明,他的寫作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對他卸下了心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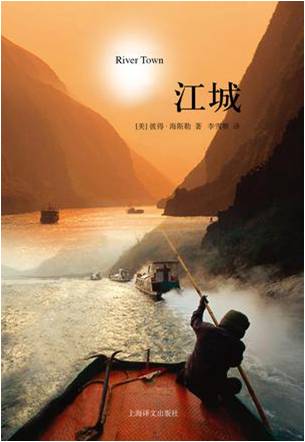
另一個觸動我極深的例子,就是臺灣學者劉紹華的著作《我的涼山兄弟》。這本書雖然是一部學院派的人類學著作,但是我認為已經具備了優秀非虛構寫作的所有要素。也正是因為如此,此書的簡體版在2016年甫一面世,就收獲了許多贊譽。在這本書中,作者講述了自己“涼山遇鬼”的故事:
媽呀,果真,差不多七點左右,我眼睜睜地目睹一顆石頭從那個角落射出,落在我跟前。“它真的想給我看?”我腦中冒出這個念頭,驚愕不已。拉鐵看著我說:“你看見了嗎?”我點點頭,完全說不出話來。他撿起石頭仔細端詳,然后問我:“你覺得這個石頭被燒過嗎?”他把石頭遞給我,棱角確像是燒黑了。“嗯,是被燒過了。”我邊回答,邊在手中把玩、端詳著這顆小石子。拉鐵又滿臉嚴肅地蹦出一句:“火葬場有一堆像這樣的石頭。”我像被電到似到,立刻甩開石子。太恐怖了!
作者非常坦率地承認了“鬼”的存在,沒有做任何的合理性解釋。這樣的“怪力亂神”出現在學術作品中,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正是因為這個故事,讓讀者看到作者與她的寫作對象之間的相互接納。在大的問題上亦是如此,比如對于艾滋病的敘述,作者并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評價,而是從理解的視角展現出離家、吸毒、坐牢,其實類似于當地年輕人的一種成年儀式。因為在家鄉沒有出路,年輕人的心又向往著精彩的世界,所以才會出現許多令人悲傷的事情。“學問無非世道人心”,作者于此已然通透。

最令人動容的還是一部名為《沒眼人》的作品,她的作者亞妮本是浙江衛視的主持人。2002年她到山西拍攝紀錄片,認識了一群被當地人稱為“沒眼人”的盲藝人。從此她中斷了風生水起的主持人工作,在太行山深處與11個沒眼人共同生活了8年,只為記錄他們的人生。她與沒眼人之間的厚重情誼,沒眼人生活中那些細水長流的、嘻笑怒罵的、哀婉纏綿的、憾人心魄的故事,都絕非這篇小文所能繞舌。我只能說:“翻開這本書,你一定不會后悔!”

與非虛構寫作者相比,歷史學家有時倒與自己的研究對象有著驚人的隔閡。研究一個城市歷史的人有可能從未到過這個城市,甚至連這個城市的地圖都沒有仔細看過。講授陽明心學的老師,背熟了“知行合一”、“心即是理”,卻從未真正理解王陽明庭前格竹、龍場悟道時的心路歷程(我其實是在說我自己啦)。然而,歷史學家在今天為何還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為我們的歷史研究一度被“貼標簽”的思維所統治。歷史學要真正貼近她的研究對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同學們交上來的作業中,我也常常看到那些充斥著大話、套話的文章,好像除了這些就不知道該說點什么了。這當然與一個時代的語言習慣有關,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與寫作對象之間存在著極大的隔膜,所以說不出來更加實在的、更加意義清晰的東西。我們太習慣于坐在舒適的沙發上或者書齋里構建自己的研究,反而把一些真正重要的東西弄丟了。
當然,歷史面對的是不可重現的人與事,但是要用心體貼也絕非虛妄。去年讀到李潔非先生研究明代人物的一系列著作(《龍床》、《黑洞》、《野哭》),雖然不是一板一眼的學院風格,也并不屬于本文所討論的“非虛構寫作”,但是作者對于那些人和事的體悟真的是非常用心。他是作為一個人,去理解另一個人,雖然這個人生活在幾百年前,雖然他只能通過文字來走近這個永遠不能再開口說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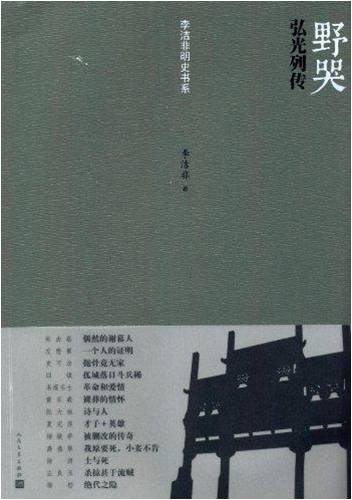
五、怎樣講好一個故事?
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在她的著作《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中談到講故事的重要性:
當你為大眾寫作,你就得寫得清楚,寫得有趣。
沒有必要在準確和優美中二選其一,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不能意識到一個活生生的讀者存在,作家的文字生于書頁,也將死于書頁。
見識、知識和經歷還不足以成就一個偉大的作家,他還要有對語言的非凡掌握作為他發出聲音的工具。
世間無窮事,但化為筆下的歷史則需要表達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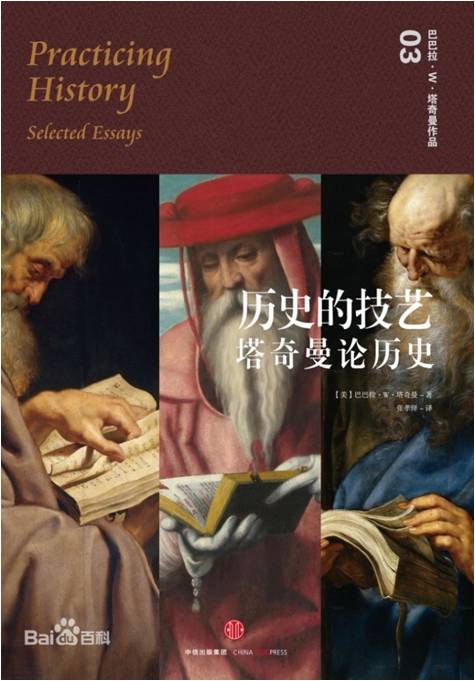
然而,學院派的歷史教育普遍輕視講故事的能力。許多學術水平很高的史學論著,卻不太在意故事的完整性和可讀性。對于歷史學家而言,這其實是一個有點可悲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明朝那些事兒》的作者當年明月,具有驚人的講故事和吸引讀者的天賦,這是絕大多數專業歷史學家無法企及的能力。
在學術作品中,能否加入合理而又出彩的敘事呢?我想是完全可能的。在這方面堪稱大師的史學家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他的敘事巧妙而又多變,頗有非虛構寫作的風格。不信請看:
朕于騎射,哨鹿、行獵之事,皆幼時習自侍衛阿舒默爾根:阿舒默爾根直言稟奏,無所隱諱,朕迄今猶念其誠實忠直,未嘗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共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鋓猻二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余圍場內,隨意射獲諸獸,不計其數矣。
這是《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一書中的一段。你能看出來這些事實都來自于某個史料,但是又表達得非常自然。而且用第一人稱,瞬間就讓讀者和作者都直接面對康熙這個人。對于作者而言,這樣做其實是相當冒險的。因為如果你不能寫出一些實在的、有深度的東西,這種第一人稱的寫作就完全寫不下去。接著再看下面一段:
我們的這位胡先生,具體地說,胡若望先生,此時雙腳站在接待廳門道內,伸長著脖子把頭探進室內,兩眼轉個不停,向里張望了一陣。室內,幾十個穿著教士長袍的神職人員占滿了所有的長椅。室外,給胡若望套上外衣并將他從牢房押送到此的管理人員緊緊地夾住他的兩側,以防他因受到刺激而做出某種意外的激烈舉動。胡若望本人并不知道為什么他會被押到這里來,因為不但沒人告訴他,而且也沒人能有辦法告訴他。胡若望不懂法語,根本不可能開口用法語詢問任何問題,而將也押到此的人對中文也一竅不通。
這是《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的開篇,這段文字就好像是一個精彩的特寫鏡頭,用倒敘的方式,設置了一個非常大的懸念。看了這一段之后,你就會迫不及待地想把這本書看完,看看這位來自中國的胡若望先生究竟在法國經歷了什么,以及于落到那步田地。這就是讓讀者欲罷不能的技巧。本來歷史是已經塵埃落定的事情,所以在歷史作品中設置懸念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史景遷卻成功地做到了。

然而最當得上“神來之筆”的,還數《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命運》一書的結尾。史景遷運用蒲松齡《聊齋志異》里的文學意象,為將死的王氏編織了一個瑰麗而又魔幻的夢境。那種時而飛翔時而墜落,前一秒是明麗后一秒是齷蹉的畫面,正是那個時代婦女心中的憧憬、憂傷與恐懼。作者將現實與浪漫穿插使用,讓人刻骨地感受到郯城那個小地方的小人物的掙扎、麻木、愚昧和死一樣的沉寂。

當然,不是的有的學術寫作都可以寫成扣人心弦的故事。但是打磨文字,盡量使之精煉、優雅;站在讀者的角度,理解他們的好奇心和對個體經驗的敏感,卻是每個歷史寫作者都可以做得到的。因為不管怎么說,我們是希望我們所寫的這些東西為別人所閱讀和理解,所以講好一個故事就顯得特別特別重要,這一點學院派的歷史研究者必須向非虛構寫作學習。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