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真讀拉美|時勢與英雄:西屬美洲革命與美洲解放者玻利瓦爾
【按】美國作家、編輯、記者和文學評論家瑪麗·阿拉納(Marie Arana)的《玻利瓦爾:美洲解放者》一書,2021年8月由周允東翻譯,中信出版集團出版。阿拉納生于秘魯利馬,9歲時移居美國。該書以扎實的史料和小說般的文筆,生動呈現了南美解放者玻利瓦爾的傳奇人生,2014年獲“洛杉磯時報圖書獎”最佳傳記獎。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的“真讀書”讀書會由該所副研究員譚道明發起,主要圍繞拉美經典著作進行精讀活動,已經持續數年。本文來自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和拉美研究中心張琨老師參加讀書會第83期的讀書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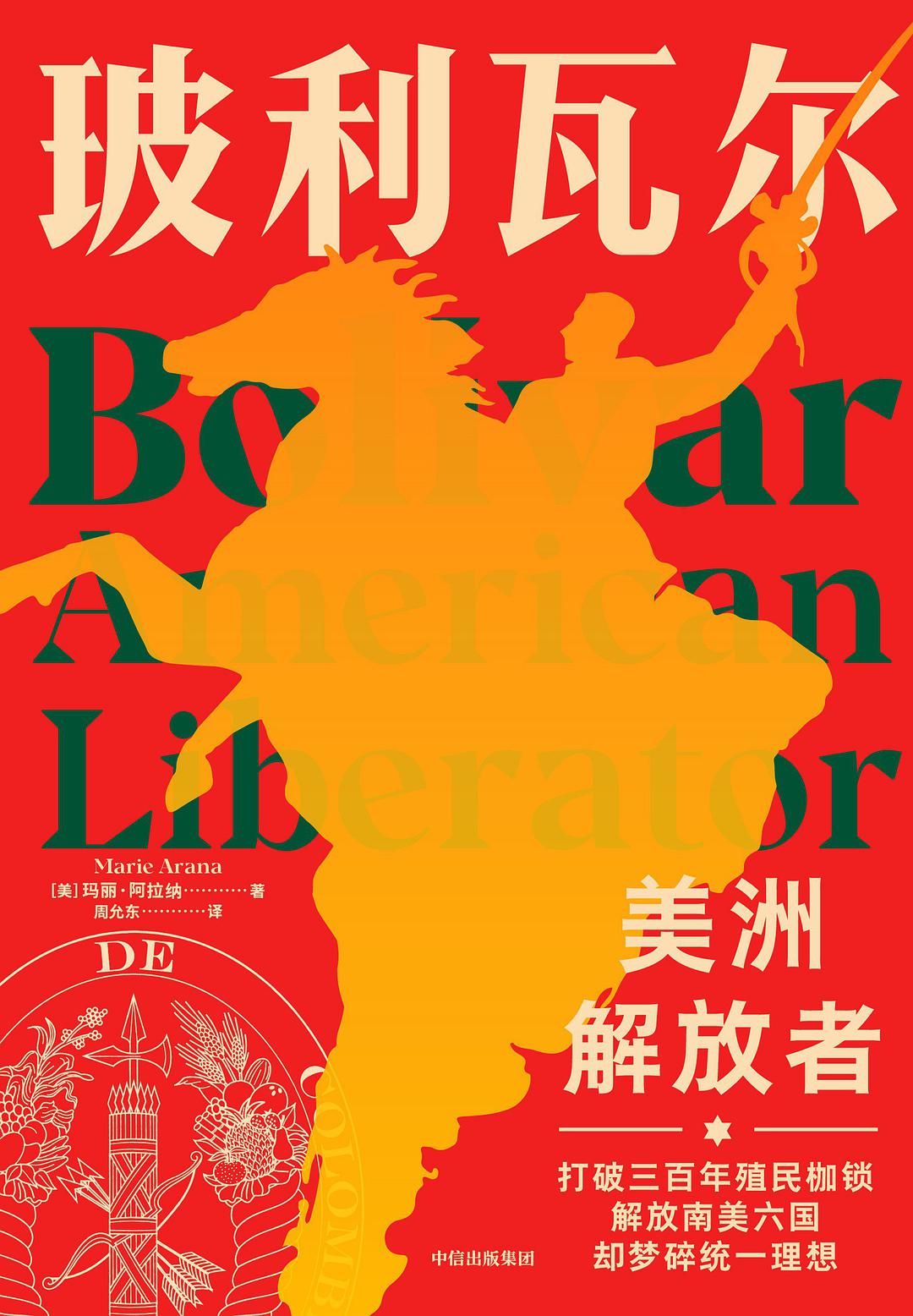
《玻利瓦爾:美洲解放者》,瑪麗·阿拉納著,周允東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
在瑪麗·阿拉納的這本玻利瓦爾傳記中文版出版之前,我就陸陸續續看過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林奇(John Lynch)撰寫的關于西屬美洲革命的著作以及他關于玻利瓦爾和圣馬丁這兩位解放者的評傳。林奇對西班牙帝國、西屬美洲帝國及其中的一些關鍵性人物有著比較深入的研究,對我理解西屬美洲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今天的分享,我會在上述閱讀基礎上對這個中譯本進行評述。這確實是一本不錯的譯著,不管從作者本人的行文風格,還是譯者對詞句的把握,或是翻譯出來的流暢程度,都給了我不錯的閱讀體驗。當然,這也是一本輕學術的著作,與約翰·林奇的學術著作在一些內容上還是有一些區別。
比如說,最困擾我的就是它缺乏大事年表和關鍵詞索引,可能因為并非學術著作。但據文后的注釋量來看,文中大部分情況下的論斷還是都能找到注釋出處的。在后續的解讀中,我會提及我對書中一到兩處地方的疑問以及與其他歷史學家的不同看法。當然,我也是一家之言。因為玻利瓦爾他自己沒有留下什么資料。在臨終前,他吩咐他的秘書把日記和書信等資料全燒掉了。但是,他的秘書奧萊里(O Leary)沒聽他的,再加上玻利瓦爾的最后一個情婦曼努埃拉將玻利瓦爾的一些私人信件也給了這位秘書。所以,后續歷史學家進行研究時所依據的最主要的材料便是這些,還包括他秘書奧萊里據此撰寫的回憶錄。除此之外,委內瑞拉有一個很有名的歷史學家,維森特·里庫拉(Vicente Lecuna)。1940年代,當時委內瑞拉經濟發展情況還可以,民族主義高漲,里庫拉負責編纂玻利瓦爾這一國家英雄人物的檔案集,最終一共編了30多卷。很多歷史學家以這些編纂出來的檔案集作為歷史資料,進一步推進了相關的研究。不過,總體來說,由于距今較遠,也沒有多方面的一手資料相互驗證,很多細節人們到今天還不是十分清晰,或者說,有多種不同的答案。

玻利瓦爾
這一事實其實也給如何解讀玻利瓦爾帶來了很大的闡釋空間。包括對他這個人的品性,對他在具體歷史場景中所作出的決定,不同人都會有不同的解釋。就像這本書的作者阿拉納在開頭所提到的一樣,有一些人出于民族主義將玻利瓦爾神話了,也有些人出于各方面原因貶低玻利瓦爾的人品。我個人主要想從歷史背景、個人經歷和對這本譯注的簡單評價這三個方面來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介紹玻利瓦爾所處的歷史背景:西屬美洲革命。玻利瓦爾之所以重要,因為他在西屬美洲革命中發揮了獨一無二的作用,帶領一幫克里奧爾人上層精英發起革命,并謀求了新興共和國的獨立。拋開西屬美洲革命這個大的歷史背景,是無法談論玻利瓦爾的,反之亦然。從學術史來看,很多歷史學者會著眼于分析西屬美洲革命爆發的結構性原因。比如說,西班牙宗主國長期以來對西屬美洲貿易方面的限制,在中高層職位選擇上更傾向于半島人而非克里奧爾人的做法,又比如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對美洲人身份的認同感。但也有一些歷史學家說,如果不談論玻利瓦爾以及那一批“考迪羅”在這場革命中的作用,那么上述結構性的解釋終究會顯得蒼白。換言之,時勢與英雄是相互成就的。
西屬美洲殖民地時期的行政官僚體系總體上分為西班牙和美洲這兩個大塊,大家耳熟能詳的西印度事務委委員會與商貿用工委員會均位于西班牙,負責總體統籌各項殖民事務。具體的執行機構在美洲被稱為總督區,第一個總督區設立在今天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第二個則位于今天秘魯的利馬。在總督區下,又會大致分為皇家審查院(audiencia),市政廳(cabildo,由當地精英組成)和管理處(corregimiento,但直接對西班牙國王負責)這三個機構,這三個部門的實際功用要根據不同總督區的實際情況來分析。特別是最后一個,直到18世紀波旁改革后才逐步在美洲出現的。西班牙正是通過這種行政機構去統治龐大的美洲的。
其實,在相當長時期內,不同總督區的克里奧爾精英對西班牙人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并不是所有的克里奧爾人精英都強烈地反對西班牙宗主,特別是在波旁王朝改革之后。比如,利馬總督區當時的克里奧爾人精英其實并不是太認同后來由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克里奧爾人或者由新格蘭納達的克里奧爾人所引領的那種獨立運動。這也能比較很好地解釋,為什么利馬總督區,即今天的秘魯是西屬美洲革命時保王黨最堅固的堡壘。這本書介紹了玻利瓦爾由北向南,然后圣馬丁由南向北,最后會師秘魯,想要攻克保皇黨這一最后堡壘。然而,無論圣馬丁還是玻利瓦爾,在處理利馬總督區時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因為在殖民的大部分時期,利馬壟斷了西屬美洲帝國航海的貿易路線,即從利馬港口到西班牙的加迪斯港口。上秘魯與拉普拉塔河流域所有的產品,包括肉類、礦產,都要通過利馬運往歐洲,利馬受益匪淺。而拉普拉塔河總督區則沒有受到這樣的優待。由于位于帝國邊陲,它在17世紀之前發展緩慢。之后,出于良港布宜諾斯艾利斯在前往大西洋方面的便利位置,這里的商人開始有資本與利馬競爭,也更加反感西班牙人在貿易方面的限制。因此,拉普拉塔河總督區的克里奧爾人精英在1810年就揭竿而起了,而利馬總督區則成了保皇黨的堡壘。

1817 年委內瑞拉,西蒙·玻利瓦爾起義
約翰·林奇對西屬美洲革命有一個比較精辟的定義:一場突然爆發、涉及區域廣泛的暴力武裝活動。直接的導火索是1808年拿破侖入侵西班牙。這對于歐洲大陸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對于西屬美洲大陸來說,所帶來的沖擊則更加嚴重。西班牙淪陷后,西屬美洲到底應該走向何方?是效忠于拿破侖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還是繼續選擇塞維利亞的那幫攝政者?還是干脆謀求獨立?玻利瓦爾,圣馬丁,以及稍早的米蘭達開始思考這一系列問題。但是,后來搞獨立戰爭的時候,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上下一心,那么順利。對于印第安人和黑人來說,克里奧爾人精英并沒有顯示出會比西班牙波旁王朝改革對他們更好,在很多方面(如黑奴的自由民身份),克里奧爾人發起的西屬美洲革命甚至在倒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其實跟長期以來不同種族之間的紛爭,特別是印第安人和白人,包括黑人和白人之間,幾個世紀的殖民壓迫和被壓迫的情形是有關的。
我們知道,西屬美洲獨立革命是1810年左右開始的,然而18世紀在安第斯地區就爆發過大大小小1000多場印第安人的起義,其中比較有名的叫圖帕克·阿瑪魯(Tupac Amaru),他自稱是印加王的化身。這些印第安人的起義給克里奧爾人精英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他們在想,假如把這些印第安人和黑人卷入獨立戰爭之中,最后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變成了印第安人對克里奧人的清洗和屠殺。這種事情在1800年的海地是發生過的,也給克里奧爾人帶來了極大的不安。所以,整個西屬美洲革命,除了圣馬丁的軍隊比較早就努力地招募黑人士兵和印第安人士兵,其他地區比較少看到這種現象。林奇有句話說得挺好的,大意是說:克里奧爾人確實想要自由爭取平等,但這種自由平等的具體內容是他們跟西班牙人一樣自由平等,而不希望看到印第安人和黑人與他們一樣自由平等。我覺得這句話比較精辟地反映出當時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屬美洲革命起碼在早期,就是從1810年到1815年這段時期內,我們很難說它是一場進步的革命。這也能夠解釋為什么在圣馬丁之前,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考迪羅們,包括貝爾格拉諾等人,三次通過今天的玻利維亞北上遠征,都失敗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遠征途經的地區居住有大量的印第安人,而這些印第安人對他們宣傳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理念,要么不感興趣,要么覺得他們在畫大餅,在欺騙印第安人。相反,當時利馬的保皇黨人給予這些印第安人的利益,跟他們之間經濟政治方面緊密的紐帶卻是實實在在的。玻利瓦爾后來進軍秘魯的時候,也遇到了類似的困境。
西屬美洲革命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在拉普拉塔河流域興起,然后再是大哥倫比亞地區的革命。第三個階段,當玻利瓦爾和圣馬丁在南北兩地站穩腳跟之后,便南北包夾,進攻西班牙保皇黨最后的大本營利馬。當然,在這三個階段中還發生了很多事件,比如說阿蒂加斯在拉普拉塔河東岸發起的戰爭,還有拉普拉塔河流域以及大哥倫比亞地區內部的紛爭。在西班牙人被沒有被完全驅逐出美洲的時候,這些都是次要矛盾,也許可以放在一邊,但一旦共同的敵人被驅逐出去的時候,這些次要矛盾就演化為主要矛盾了。
就玻利瓦爾本人來說,由于父母很早過世,親戚做了他的監護人。有兩件事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是他的黑人奶媽。這個黑人某種程度上成了他最為信任的人。也是因為這一點,后來有一些貶損玻利瓦爾的人說,他其實是一個黑白混血。在當時西屬美洲的社會,人們十分看重血統的劃分。假如你是混血的話,你可能無法擔任政府軍隊內的高級職務。第二點是他很早就去了西班牙接受教育,又游歷整個歐洲,但這段經歷已經沒有多少遺留下來的歷史材料可以考證了。玻利瓦爾對拿破侖的態度,也是歷史學家們熱衷討論的話題。一些人覺得他是很崇拜拿破侖的,甚至跟拿破侖有過私人接觸,但另一些人說,他一開始很崇拜拿破侖,但當拿破侖稱帝恢復君主制之后,他對拿破侖又比較唾棄。我個人比較傾向于第二種。他后來與圣馬丁在瓜亞基爾的爭論,清楚地表現出他對君主立憲制的厭惡。他在歐洲游學時,閱讀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書,基本的政治理念在那時候已經逐步形成了。之后,當他游歷意大利,對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評價不高。從這兩個證據結合起來判斷,他對稱帝之后拿破侖的態度還是比較明顯的。
歐洲游歷另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是他在西班牙結識的妻子患黃熱病去世了。妻子的去世給他帶來重大打擊,徹底地改變了他。他重返歐洲排遣憂思,將客居英國倫敦另一位美洲的革命先驅弗朗西斯科·德·米蘭達(Francisco de Miranda)說服回來。從后續事件可以看出,玻利瓦爾并不是一個能征善戰的勇將。在第一共和國、第二共和國時期,他輸掉的戰爭挺多的,并不像蘇克雷或者圣馬丁那樣驍勇善戰。圣馬丁是職業軍人,在西班牙參加過抗擊拿破侖的戰爭。而玻利瓦爾,就像本書作者阿拉納提到的,他沒有接受過系統的軍事訓練,帶兵打仗不是他的強項。他的強項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特別是根據不同的情況,將考迪羅們粘合在一起,為同一個目標奮進。要做到這一點,他的心胸應是比較寬廣的,也有一定的謀略,包括收買人心的政治手腕。比如,在倫敦他向米蘭達竭力渲染整個委內瑞拉乃至整個西屬美洲各層級渴望獨立革命的景象。當米蘭達回到美洲,感覺并非如此。兩人因指揮權和戰術問題發生不少沖突,從他出賣米蘭達來看,玻利瓦爾是相當復雜的一個人。關于這件事,這本書有詳細的論述,作者的看法和闡釋比較傾向于玻利瓦爾,認為米蘭達在第一共和國失敗后想徹底背叛革命事業,而玻利瓦爾出于這一點才把他交給西班牙將領的。但如果我們看作者所引用的這兩個注釋,就會發現其實都來自于懷有比較強烈民族主義情感的歷史學家。因此,真實的玻利瓦爾和后續歷史、史學史和出于各種政治原因所塑造出來的玻利瓦爾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委內瑞拉一名著名的歷史學家赫爾南·葛馬拉(Hernan Gamarra)寫過一本書,叫《對西蒙·玻利瓦爾的崇拜》(El Culto a Simon Bolivar)。這本書詳細考察了歷史學家、政治家等不同群體出于各自興趣和利益對玻利瓦爾形象的再塑造。根據阿拉納這本書所選取的歷史學家來看,是帶有美化玻利瓦爾的明顯傾向的。比如,安德烈斯·貝略(Andres Bello),一位同樣杰出的拉丁美洲歷史人物,就將玻利瓦爾對米蘭達的行為定義為背信棄義。約翰·林奇也認為,出賣米蘭達折射出玻利瓦爾人性中的陰暗面,因為玻利瓦爾在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覆滅后也都選擇了戰略性的撤退。那么,為什么米蘭達當時的撤退就被認定是對革命事業的背叛呢?玻利瓦爾與那名西班牙軍官好友之間到底達成了什么樣的協議,就不得而知了。玻利瓦爾與米蘭達的決裂,宣告了委內瑞拉第一共和國的失敗。米蘭達對他當時為什么要走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首先是首都加拉加斯缺乏物資資源,其次是東部黑人叛亂,第三是當時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受影響最大的區域就是革命者所在的區域,而保皇黨的區域沒有受到地震太大的影響。這次地震被各種保皇黨解釋為上帝對叛亂分子的天譴或者責罰。上述三點都對玻利瓦爾和米蘭達的軍隊產生了很大影響。1812年,玻利瓦爾在流亡期間發表了《卡塔赫納宣言》,認為委內瑞拉第一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是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他認為,任何一個新生的國家,都必須依仗一個強大的、集權的中央政府維持自己的運行,而第一共和國政府太過于混亂復雜,這個論斷與他后來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
第一共和國覆滅后,回到祖國的玻利瓦爾開始考慮西進政策。當時的整個委內瑞拉 ,效忠于保皇黨的高喬人的力量過于強大,革命軍隊能夠維持自身統治和影響力的地盤是不多的。所以,他最后決定前往波哥大。哥倫比亞也充斥著考迪羅。玻利瓦爾后來建立委內瑞拉第二共和國的過程中,這些考迪羅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對玻利瓦爾來說,他在委內瑞拉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建設過程中的努力,包括他的自由理念和他對解放整個美洲的理念,某種程度上給他帶來了聲望,使他成為當時一個標志性的人物。同時,哥倫比亞政府內部也意識到,假如委內瑞拉與利馬總督區繼續由保皇黨把持的話,對于新成立的哥倫比亞本身也是一個威脅。假如此時有一個有號召力的人物愿意接過哥倫比亞的軍隊,幫助他們去平定叛亂,何樂而不為呢?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玻利瓦爾會不會成為一個獨裁者,或者說獨掌大權而犧牲掉地方考迪羅的利益?這將是他們后來所考慮的事情。最初的時候,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趕走西班牙人,維持新生共和國的主權和獨立。

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西蒙玻利瓦爾雕像
委內瑞拉第二共和國覆滅可以歸咎為活躍在今天委內瑞拉東南部——就是一個大沼澤——的草原游牧人(las llaneros)。大家可以聯想一下成吉思汗橫掃亞歐大陸的那支軍隊,兩者某種程度上是很相似的,機動性很強,馬術精湛勇猛,將哥倫比亞的軍隊打了個措手不及,第二共和國也就覆滅了。玻利瓦爾戰略性撤退到了牙買加,后來寫下著名的《牙買加來信》。在《牙買加來信》中,他依然強調一個強有力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認為,第二共和國的覆滅,同樣由于地方考迪羅對地方利益看得太重,未能達成聯合性的軍事合作。此外,在這個重要文獻中還提出成立一個西語美洲聯邦的構想。從今天的得克薩斯一直南下,包括巴西外的所有新獨立的西語國家。1826年6月,玻利瓦爾在巴拿馬召開了一次西語美洲聯邦的大會,但響應者寥寥,只有7個共和國參加。阿根廷拒絕參加,墨西哥代表來遲了。玻利瓦爾的這個構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是挺偉大的。假如整個西語美洲聯邦聯合起來,就領土和人口來看,其內部市場完全可以支撐一些拉丁美洲國家20世紀搞的進口替代工業化。
這樣龐大的聯邦共和國要存活并發展壯大的話,對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會是相當高的。事實上,不要說這個西語美洲聯邦,就連玻利瓦爾創建并維持一段時間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都分崩離析了。這就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當時的考迪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讓渡自己的權力,這是存在很大疑問的。考迪羅們聯合起來,在玻利瓦爾的麾下趕走西班牙人是一回事,真正成立一個由玻利瓦爾當總統的聯邦則是另外一回事。沼澤上游牧集團領袖的更迭產生了新的領袖派斯(Paez),此人選擇與玻利瓦爾結盟,一舉擊敗了西班牙人的保皇黨,維持住了第三共和國。
相比玻利瓦爾,圣馬丁更早進入秘魯,但他只圍不打,希望宣傳的先進理念促使利馬總督區發生內部變革。玻利瓦爾揮師南下,兩人在瓜亞基爾相會,討論西屬美洲革命的未來。沒人知道這場會談究竟談了什么。后世史家主要根據玻利瓦爾秘書的回憶錄,還有圣馬丁后來給他朋友的書信來推斷會談的內容。不過,對于圣馬丁的書信,阿根廷歷史學家認為是真的,但委內瑞拉的歷史學家認為是偽造的。根據這些史料,兩位解放者當時主要談論了兩個問題:第一,瓜亞基爾的歸屬問題,屬于大哥倫比亞還是屬于秘魯;第二,獨立后的這些西屬美洲國家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政治體制。圣馬丁和玻利瓦爾是有某些共識的,都覺得當時的拉丁美洲跟北美不一樣,種族太過于混雜,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不適合建立一個美式的聯邦制,都確信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但在采用君主立憲制還是共和制方面,圣馬丁與玻利瓦爾存在分歧。圣馬丁想從歐洲再找一位君主,以便歐洲人承認這些新成立的西語美洲共和國。而玻利瓦爾堅決認為從歐洲找一位君主是歷史的倒退,是對解放美洲事業作出的種種努力的侮辱。他堅持共和制,不允許君主或君主立憲再度出現在西屬美洲。最終,由于圣馬丁更有求于玻利瓦爾,他把兵權交出,自己遠赴歐洲。圣馬丁雖然對玻利瓦爾的品性有過負面評價,比如說他粗魯,為了目標不擇手段,但圣馬丁也清醒地意識到當時混亂的西語美洲需要的就是這么一個人。就像斯賓賽社會進化論中所說的“馬背上的英雄”一樣。假如有人讀過杰克·倫敦寫的《馬丁·伊登》,就可以理解18世紀或者19世紀初期,整個美洲地區對強人的渴望。他們希望有一個克里斯瑪領袖帶領地區走出混亂。
不過,即使是玻利瓦爾也沒能做到這一點。這并不是由于玻利瓦爾無能,而是這在當時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考迪羅們的彼此猜忌,不愿意讓渡自己的權力。他們的私心又進一步影響自己控制地區的民眾,讓民眾意識到與其他地區民眾之間的區別。這種情況直到今天依舊改變不大。玻利瓦爾在秘魯和玻利維亞都推行過改革,但都實行不下去。當他回到大哥倫比亞后,共同的敵人西班牙人已經不存在了,內部的紛爭則開始了。之前的老部下們紛紛說他是個獨裁者。我覺得,當時玻利瓦爾是有獨裁這個想法的,但這個想法并不是出于他個人對權力的渴望,更多的來自于對西語美洲未來前途的憂慮,對一盤散沙的考迪羅們治理國家能力的質疑。如果繼續陷入紛爭,西屬美洲即便解放也沒有未來。這本書中寫到了玻利瓦爾的那段話:“我很慚愧,在付出了所有其他一切代價之后,我們僅獲的只不過是獨立。”這種獨立還要加上雙引號,就像后面拉丁美洲左派知識分子所說的,拉美其實并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經濟和政治上一直依附于其他帝國。
約翰·林奇認為,玻利瓦爾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同時,想要維持一個強大的政府,這是當時的自由派或者同時代所有的考迪羅所不能理解的。這些超前的理念要在后續的時代才能被逐步理解。他認為,玻利瓦爾其實并沒有帶來一場革命,充其量只是一場改革。整個西屬美洲,在玻利瓦爾和圣馬丁領導的獨立運動之后,其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種族關系,都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拉丁美洲的國家構建進程要在西屬美洲革命結束后的1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才逐步成型。
玻利瓦爾自身最大的優勢在于他能夠團結其他考迪羅。這源自他對整個西屬美洲局勢的判斷和對這片大陸未來遠景的構想,還有他有演說的才能和領導的天賦。事實上,對于當時各地的考迪羅來說,打仗并不是一件難事,打贏也并不是一件難事,關鍵的是打贏了之后,你下一步要往哪里去。這個問題在1910年爆發的墨西哥大革命中體現得也比較明顯。一些游擊隊領導人能領導打贏一場戰役,但他們看不到打贏了之后,整個國家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而這正是玻利瓦爾相較于其他考迪羅來說所特有的優勢。他在歐洲的游歷,他對啟蒙思想家大量著作的閱讀,是形成這一優勢的基礎性條件。可以設想,玻利瓦爾在說服這些考迪羅的時候可能會說,你們可以看一下歐洲的法國、英國,包括北美都是如何發展的,我們獨立以后也要效仿他們制定憲法、銳意改革,一步一步把國家發展得更好。這是他能吸引并團結大小考迪羅的最重要的特點。遺憾的是,玻利瓦爾的背后沒有一個牢固的班底始終義無反顧地追隨他。他所做的只是團結這些考迪羅,而缺乏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一缺陷,最終導致了他夢想的破滅。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