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訪談 | 徐則臣:寫作是一個人的戰爭,我寄希望于下一部
原創 訪談者 生活周刊

徐則臣
1978年生于江蘇東海,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青云谷童話》《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馮牧文學獎,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2015年度中國青年領袖”。《如果大雪封門》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同名短篇小說集獲CCTV“2016中國好書”獎。長篇小說《北上》獲CCTV“2018中國好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等二十余種語言。
徐則臣的老家在東海,他對這個地名很糾結,他們家離海的距離大約100里,不過,那叫黃海。其實,東海縣原來叫海陵,意思是海邊的高地,徐則臣特別喜歡這個名字,所以寫進了他的不少小說。這估計就是一種隱喻,他從二十幾歲開始,作品就不停地獲獎,這么一路下來,36歲獲魯迅文學獎,41歲獲茅盾文學獎,幾乎把中國大大小小的獎獲了個遍,成了中國文壇如今最年輕的登頂者之一。但是問及哪一部屬于經典的時候,徐則臣卻說,談一兩百年以后,這個話題太奢侈,如果斗膽認為這種假設成立,他寄希望于下一部。徐則臣還有一個編輯家身份,經過他的手推出來的名篇佳作很多,龍一紅極一時的《潛伏》,莫言獲諾獎后的首部作品,更多是新人的處女作,他卻謙虛地說,“不少人都成了‘千里馬’,但‘伯樂’真不敢當。”
本期焦點人物 徐則臣
青年報記者 陳倉 李清川



1
小時候認為好地方都在別處,
現在覺得故鄉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
青年報:則臣好,你的名字是誰幫你起的?你以寫作為生,就沒有想過起一個筆名嗎?你覺得你的名字對人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徐則臣:我爺爺取的,則字是輩分。剛開始寫作時候想取一個,沒想出合適的,干脆就用原名了。名字應該有心理暗示的效果。像我這名字,一聽就是老同志,想青春點活潑點就感覺不搭調,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反正我很小就被認為比較穩重、少年老成。當然這是好聽的說法,不好聽的就是暮氣沉沉,人也長得太著急。
青年報:你是江蘇東海人,我查了一下地圖,你們并不在海邊,這是為什么呀?你從文學的角度介紹一下你的故鄉吧。
徐則臣:東海屬于連云港,連云港在黃海邊上,我家離黃海大概100里。100里不是個小距離,所以我從小對海沒任何概念。很多年里,我對我們縣跟東海的關系也很糾結,我一直以為我們靠的那個海是東海,后來知道是黃海。我寫過一篇小文章,《東海在黃海之西》,我們在黃海的西岸。那為什么叫東海?有資料說,很久以前沒有黃海這個名字,那時候黃海還叫東海,沒分得這么細。我們縣過去叫海陵,海邊的高地,我很喜歡這個名字,在小說里我常用這名字。
可能每個人跟故鄉的關系都比較纏繞,小時候你會覺得故鄉乏善可陳,好地方都在別處,就好像生活總在別處,所以我們都要到世界去。年輕時候寫文章,談到故鄉我就說,“故鄉的最大特點就是毫無特點”。年既長,發現其實不是這么回事兒,你深入地理解了你的故鄉,你也就能正視它的優點和缺點。會更加客觀,也更加主觀。比如現在說到故鄉,我會說它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因為我們的父母、祖先在那里,那是生我養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童年和人之初的記憶。當然客觀地說,我老家還是挺有特點的,產質量極好的水晶,現在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水晶礦石交易市場。溫泉也很好,天然的,水溫高,礦物質含量豐富,做好了,會是一個康養的勝地。
青年報:你第一次離開東海和最近一次回東海是什么時候?在那塊土地上還有哪些人與事是你念念不忘的?
徐則臣:第一次離開東海是去市里,那時候好像是小學二年級,我爸帶我去連云港的一家軍隊醫院看牙。我長久牙疼,臉腫得像饅頭,剛出鍋的饅頭都咬不動。我爸就是醫生,他也沒招,就帶我去市里的一家軍隊醫院。那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車,也是第一次順便看見大海。特別為海上的那些大輪船擔心,感覺它們飄飄悠悠像剪紙一樣在海面上晃蕩。最近一次回老家是去年,本來年前還想再回去,疫情,動不了。現在我父母還在東海,我媽每年會到北京來幫我們帶一段時間孩子。故鄉所有的人和事我都記得,或者將會被記得。寫作一定意義上就是回憶,當你打開一個時間的缺口,即便那些消失了的人和事,也會源源不斷地奔赴過來。每次陷入回憶,我都會驚嘆十八歲出門遠行之前的生活竟如此豐沛和富足。
青年報: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文學創作的,你第一篇文章和最近一篇文章是什么?這兩次,有什么變化和不變的嗎?
徐則臣:高二的時候寫了第一篇小說,純屬寫著玩。立志要當個作家,開始文學創作,是在大一暑假。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個小散文,名字忘了,內容也含混了,稿費好像十幾塊錢。最近發表的是在《花城》2022年1期上的一個短篇小說——《宋騎鵝和他的女人》,這小說是2020年寫的。如果不是刊物催得急,小說寫完了我喜歡焐著,慢慢改,焐上一年半載是常態。兩次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對文學的理解一直在變。二十多年過去了,想不變也不行。不變的是真誠,從開始寫作到現在,我一直堅持“修辭立其誠”。
青年報:你的文學理想是東海這片土地培養起來的嗎?你覺得故鄉和北京哪個對你影響更大?你文學的故鄉在東海還是在北京?
徐則臣:對每個作家來說,故鄉都是不可替代的,文學最初的種子肯定是埋在故鄉的熱土上。平心而論,故鄉和北京對我影響都很大,還有我曾經生活過的淮安,難分伯仲,它們既平行又交叉地生發著我的文學。不僅僅是作為材料的來源和故事的發生地,更在于它們都是我認識世界、思考現實的背景和參照。即使在小說中沒有出現它們的名字,我也知道它們一直都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共同地構成了我的文學故鄉。
青年報:這是一個大移民時代,有一個人群叫“北漂”。如今你可以說是功成名就,現在還有沒有“漂”的感覺?馬爾克斯說過,我們沒有一個親人埋在這里,這里就不能稱之為故鄉。你認為我們怎么樣才算扎下根來?
徐則臣:我應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北漂,至少剛開始不是。剛到北京我是去北大讀研究生,三年書念完留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才算“漂”著了。“漂”是一個狀態,像浮萍,隨時可能被一陣風吹到另外一個地方。這種隨時可能挪窩的狀態我持續了七年,到2012年才穩定下來。我對空間上的位移和動蕩不是特別敏感,我更在意“漂”之于內心和精神上的無根狀態,大抵就是蘇東坡所謂的“此心安處是吾鄉”。但這個問題,2012年以后我也沒能解決,雖然我已經在這里安家落戶,并且將長久地生活在這里。究其原因,我分析了不下100條,沒有哪條能夠一錘定音徹底說服我,所以我給自己的理由是:這可能就是“現代病”之一。沒那么多為什么,我們就是來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在家靠娘,出門靠墻”的時代結束了。這種心理歸根結底跟你成功還是失敗沒有關系,當然,我也不認為自己就是你所說的功成名就。一個普通人過平凡的日子而已。馬爾克斯的觀點我理解,但從認識論的角度看,這句話對我來說不過是個修辭。我也不知道在今天,怎樣才能扎下根,怎樣才算扎下根;我一直在想的是,在今天,是否有那個意義上的根,以及扎根是否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2
談一兩百年以后太奢侈,
如果這種假設成立,我寄希望于下一部。
青年報:你最新出版的小說集《青城》,里邊三篇小說《西夏》《居延》《青城》,主人公都有著“漂”的身份,隨著我們這一代人的老去,“漂”也許會成為一個遠去的符號。那么,文學價值會不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消失?
徐則臣:文學與它所置身和反映的現實并非直接畫等號,文學的價值亦然。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么幾百上千年前的經典在今天依然能夠常讀常新。毫無疑問,現實或者說現實感的價值的確是文學眾多價值中的重要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同時,現實或現實感的價值也并不會因為時移世易就全部喪失,它可能轉換為歷史價值或其他什么價值。如果一部針對現實的作品換了個時空就失去共鳴的能力,那只能說這是作者和作品的原因。它很可能外在地、表象地、狹窄地理解了現實。文學中的現實從來就不該僅僅局限于當下,它還暗含了歷史和未來兩個維度。
當然,所有的現實和時代必然是人的現實和時代,必須納入到活生生的人的框架下去探討。現實和時代不能自己走到文學的前臺來,必須借助人來發聲、來表達,現實和時代的故事也必須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來呈現、來成全。所以,我們都知道的那個觀點:文學是人學。人學,人與世界之間可靠的關系,以及藝術,才是作品永葆青春的法寶。
青年報:你講得特別好,我都忘記了,你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里的高材生,理論和實踐功底都非常深厚。作家里邊,博士碩士教授,高學歷和學院派特別多,不過也有人說,當一個好作家,與學歷和教育關系不大,他們舉出來的例子是高爾基、莫言等大家。你是怎么看待這一問題的?
徐則臣:車有車道,馬有馬道,條條大路通羅馬;成就一個好作家,沒有包治百病的良方。我是學院里出來的,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這些學習和訓練對我的創作大有裨益,一是給我一個寬闊和全面的文學史背景,另一個就是培養了我的問題意識。但這跟高學歷又沒有必然關系。一個人只要足夠開放、勤奮,閱讀量充分,能找到有效的自我教育的路徑且有所悟,有沒有碩士博士學位,是不是學院派都不重要。
高爾基我不知道,莫言老師我接觸比較多,就舉個莫老師的例子吧。有一次我們聊年輕人的寫作,隨便聊,我提到的幾位90后作家莫老師都讀過,莫老師提到的兩位,很慚愧,他們的作品我完全不熟。別人作何感想我不清楚,當時我很震驚,前輩作家,諾獎得主,竟然這么大的閱讀量,閱讀范圍都囊括到了90后的最新創作。莫老師還把這些90后作家的寫作跟前面幾代作家做了比較。這是個日常的小細節,我覺得還是能說明一些問題的。
青年報:你從二十幾歲開始就不停地獲獎,然后一路下來,《如果大雪封門》獲魯迅文學獎,《北上》獲茅盾文學獎,幾乎把中國的文學獎都獲遍了。你覺得獲獎對于一個作家意味著什么?如今,你寫作的最大動力是什么?
徐則臣:不同的獎是在不同的創作階段給我的肯定和鼓勵,這些肯定和鼓勵對我的創作很重要,也是支持我一直寫下去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很難跳出具體語境來談,談哪個獎更重要、更喜歡哪一個。我一直認為,一個獎對一個創作者,只要是一種有尊嚴的肯定與鼓勵,那就是一個好獎。寫作是一個人的戰爭,不是三下五除二就結束的,曠日持久的跋涉與煎熬需要鼓勵、肯定和呼應,哪怕是批評也好,它會讓你覺得吾道不孤。我們當然都希望自己意志強大,但人是有局限性的,意志也會有鞭長莫及的時候,這時候,來自同行、專家和讀者的呼應就變得非常重要。獲獎就是這樣的呼應。我非常感謝這些年的寫作中得到的諸多呼應。呼應很重要,但你肯定不可能僅僅為了得到呼應而去寫作,持久寫作的動力歸根結底要來自內驅力。像吃喝拉撒一樣必不可少,才是最可靠、最大的動力。對我來說,寫作已成為我思考的一種方式,不下筆,很多問題無法深入。為了把我感興趣的問題一點點弄明白,只能寫。
青年報:你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時候只有41歲,你現在是獲得這一獎項里最年輕的作家,也是唯一的70后作家。從代際來看,你覺得年輕作家在未來,需要靠什么來超越前輩?
徐則臣:過去我還真挺操心的,每一代作家、每一位作家,大家如何自處,如何可持續發展,如何實現對自己和他人包括前輩的超越,沒事我也琢磨。現在考慮得越來越少,有些事琢磨是沒意義的。你絞盡腦汁,那設身處地的真誠勁兒把自己都感動了,但你想過沒有,所有的解決方法都是基于當下的你的個人化的理解,你是在以靜制動,以己度人。能否形成真知灼見?當然有可能,但永遠都是有限的可能。人到中年,我突然意識到,古往今來的所謂智者,他們的篤定并非來自他們總能在關鍵時刻給這個世界支出妙招,而是來自對基本規律的尊重。
天行有常,于整個世界如此,與一代代人、一個個人也如此。每代作家當然會有自身的特點,每代作家也自會有他們的方式,這些特點和方式本身無所謂高下。歐陽鋒倒練九陰真經最后也練成了,在歐陽鋒練成之前,我想金庸先生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九陰真經這么也可以搞成。只要大家還愿意努力,每代作家都可能出現歐陽鋒,至于是一個還是幾個或者一大群,是正練、倒練還是歪著練、斜著練,我們大可不必費心,我們只需要像金庸先生那樣一直耐心地往下寫就可以了,寫不到那個地方你永遠不會知道。所以現在我特別喜歡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俚語俗諺,比如兒孫自有兒孫福,比如船到橋頭自然直。你說它是過日子的心得也罷,是人生智慧的結晶也罷,是哲學也罷,都行,無可無不可,它就是它。
青年報:你的作品可以說是又多又好,如果讓你選擇一部作品,留給未來一兩百年后的讀者,你會選擇哪一部?為什么?
徐則臣:慚愧慚愧。一個文學被視為“快餐”且“速朽”的時代,談一兩百年以后,這個話題太奢侈。不是避重就輕跟老兄打太極,如果斗膽認為這種假設成立,我寄希望于下一部。之前的作品可能有一些值得說道的地方,但我總覺得不夠充分,還有不少我有能力克服的缺陷。希望這些缺陷在下一部能夠避免。
青年報:你還有一個身份,《人民文學》的副主編,你是什么時候進入《人民文學》的?你第一次走進雜志社都干了些什么?
徐則臣:2005年進的《人民文學》,那時候我還沒畢業,但碩士答辯已經結束,老朋友吳玄說,《人民文學》想要人,我就去了。一晃十七年。那會兒地鐵10號線還沒通,從北大坐車去《人民文學》,過了中關村大街,車就一直在三環上跑。從北三環轉到東三環要拐一個彎,那個彎拐得極其平緩,第一次去《人民文學》,特別激動,滿腦子都在想雜志社會是什么樣子,公交車拐彎的時候我沉浸在虛構中不能自拔,就沒意識到,以為車還在從西往東跑。這帶來一個嚴重的后果,直到現在我都沒有調整過來,十七年了,我的感覺里《人民文學》前面的三環路都是東西向的,事實上是南北向的。那時候雜志社應該挺陳舊,說破舊也不夸張。除了主編韓作榮老師一人一間辦公室外,其他每個辦公室里都好幾個人。老韓的辦公室非常小,人多了也坐不下,我到門口跟他打招呼報到,被煙熏黑的屋子里濃烈的煙味對我當頭一棍,我趕緊退到門外。老韓那會兒煙抽得非常厲害,一根續一根,人不離煙,煙不離嘴,一上午只用一次打火機。聊了幾句他就把我交給李敬澤老師了。那時候敬澤老師是副主編,入職談話也是他跟我談的,我才大概明白編輯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兒。敬澤老師是副主編,也沒有獨立辦公室,我們倆對桌,十來平米的房間里還有兩位編輯老師,李平老師和陳永春老師。每天四個人擠一塊兒談文學,熱火朝天。在一個文學青年的眼里,這種辦公條件不叫差,更不是落后,叫有文學氛圍。那時候電子來稿還不多,絕大多數都是打印稿,看著印有“中國郵政”字樣的一個個麻袋一般大的帆布袋里裝滿稿子,做編輯的自豪感和成就感真是油然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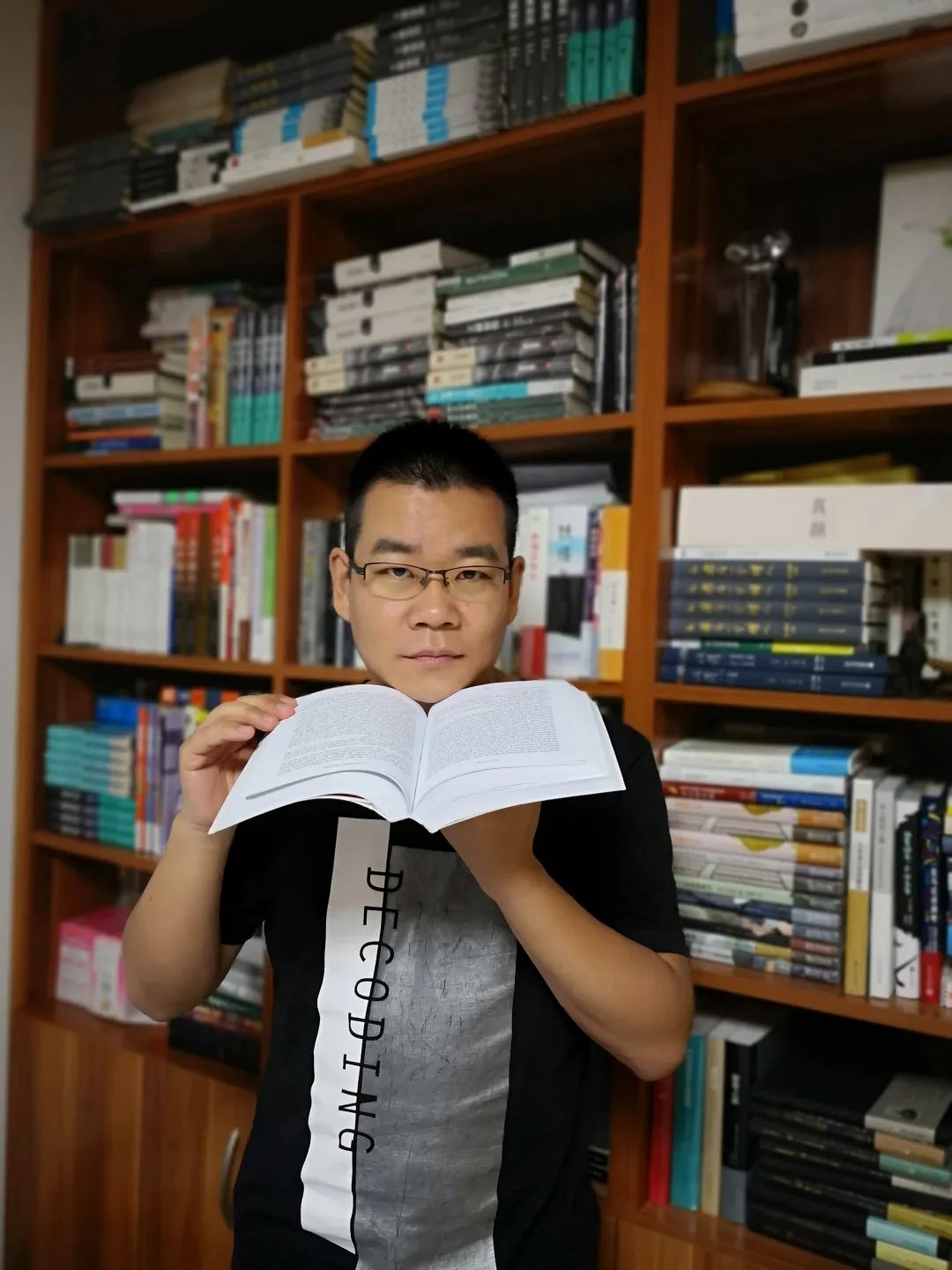
3
不少人在我手里成了“千里馬”,
但“伯樂”真不敢當。
作為編輯,我們的重要是有限度的重要。
青年報:最近一次去上班都干了些什么?這兩次的變和不變是什么?
徐則臣:最近一次上班是除夕之前(采訪是正月進行的——編者注):新一期雜志發稿,處理雜務,和同事互祝虎年吉祥,囑咐大家關好門窗和水電。都是日常工作。你不問還不覺得,你這一問,我立馬覺得這十七年好像只是一天,2005年陽光大好的時候我坐著公交車去上班,辛丑年的大年二十八的傍晚,我鎖上辦公室門下班。辦公室變了,原來我們在五樓,現在到了七樓;十年前裝修過,現在也舊了,但比2005年還是要新一些;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茬茬的人走,又一茬茬的人來,到了今年下半年,我就成了雜志社現有的員工里,待的時間最長的那一個;還有一個變化,就是那時候坐公交車上下班,堵一兩個小時正常,現在坐地鐵,可以掐著點兒出門。這些變化之外的,都是不變的。
青年報:你和《人民文學》歷任主編哪些人有交往?
徐則臣:我在《人民文學》的十七年里,歷經了三任主編:韓作榮、李敬澤、施戰軍。也接觸過三位前任主編:王蒙、劉心武和程樹榛。他們既是優秀的主編、編輯家,也是著名的作家、詩人和批評家。《人民文學》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的,而是從茅盾先生那一代編輯前輩開始,一代代人、一茬茬人專業且敬業地經營出來的。
青年報:由編輯到副主編,你推出來的稿件不計其數,至今回憶起來仍然令你激動的有哪些作品?有沒有經過你這位伯樂而一舉成名的“千里馬”?在與作家打交道和編發作品的過程中,有很多的花絮或者佳話,你能否跟大家分享幾個?
徐則臣:一年十二本雜志,十七年刊發的作品,目錄排起來也浩浩蕩蕩。好作品真是不少,好作家也很多。基于這些,我對當代文學從來都不悲觀。因為沒有回頭做詳細的案頭工作,記憶力也不好,只憑印象說,顧此失彼掛一漏萬不可避免,我就隨口說吧。工作以后編發的第一部現象級小說,可能是《潛伏》。龍一的短篇小說,后來被改編成家喻戶曉的同名電視連續劇《潛伏》。據說,這部劇在中國有史以來重播率最高的電視劇中排第二,第一是《西游記》。小說寫得好,電視劇改編得好,演員演得也好。我去吳橋出差遇到龍一兄,那也是我做編輯后最初的幾次出差之一。龍一答應給我們寫個小說,就是后來的《潛伏》。他覺得我的名字改改適合地下工作者用,徐去掉雙人旁,臣改為成,余則成,留下來潛伏的最后要成功。當時不覺得是個事,我寫小說也會用朋友的名字,省事。改編成電視劇后火成那樣,的確沒想到。要是有前后眼,當初我肯定會和龍一兄商量改掉這名字。電視劇熱播后,很多朋友跟我聊天時,經常一不留心就叫我余則成。還有很多朋友問我跟這名字的關系,我得一遍一遍跟他們解釋。后來我也解釋煩了,再問,我就說,找小說看去。
2017年一個晚上,收到莫言老師發過來的戲曲劇本《錦衣》和一組詩《七星曜我》。當時我在英國,和朋友在回牛津的車上,在手機上一口氣把它們讀完了,特別興奮,劇本和詩我都非常喜歡。跟莫言老師約了很長時間,稿子終于到了。后來2017年的第5期刊發出來。這是莫老師在獲諾獎五年之后,第一次在刊物上發表重頭作品。第二年又發表了他的另一部戲曲劇本《高粱酒》,也非常棒。我還編發過曹文軒老師獲得國際安徒生獎之后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蜻蜓眼》,這部小說在曹老師的作品序列中既獨特又重要。
劇本中,有劉恒老師《窩頭會館》,不是我直接編的,但發這個劇本跟我有關。我在人藝看了這個劇,非常喜歡,正好趕上雜志在籌劃新的一年改版,敬澤主編問我們有什么想法。我說特別喜歡這個劇,可不可以發劇本?因為在此前很多年《人民文學》都沒有發過劇本。敬澤主編就讓華棟兄向劉恒老師約劇本看,那會兒華棟兄是編輯部主任。劇本拿來,我們都很喜歡,就決定發了。《窩頭會館》開了個頭,后來就陸陸續續發了一些優秀的劇本,包括前幾年一個比較重要的話劇《蔣公的面子》。
茅盾文學獎的作品我編過兩部,畢飛宇的《推拿》和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還有一位海外華人作家袁勁梅非常值得推薦,我編過她的中篇小說《羅坎村》,我認為它是新世紀以來最重要的中篇之一。她的長篇小說《瘋狂的榛子》也是我責編的,我一直認為這是一部被嚴重低估乃至忽略的優秀長篇。
責編過眾多作家的處女作或者在《人民文學》上的第一篇作品,不少人都成了“千里馬”,但“伯樂”真不敢當。很多好作品不經我手,換一個編輯也能發出來,也會產生很好的影響;很多作家跟某個編輯沒有建立聯系,照樣可以成為好作家。對一部作品的問世和一個作家的成長,好的編輯的確能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但作為編輯,要時刻保持職業的清醒,我們的重要是有限度的重要。
青年報:現在許多年輕人沉溺于新媒體里,你是怎么看待微信和抖音這些的?這對年輕人的性格和人生會不會產生什么不良影響?
徐則臣:每一種新事物出現,都容易讓求新求異的年輕人沉迷,這很正常,也是規律。別說年輕人,我已一個中年人,自制力還算可以,刷起朋友圈和看短視頻,一不留心也兩三個小時過去了。何況現在很多新媒體,通過云計算還有針對性地給你推送,滿桌都是你愛吃的菜,你忍得住?反正我是經常忍不住。
但話說回來,再好的事,沉溺到不能自拔、忘乎所以,也就是所謂的迷失的程度,那也都成了壞事,不良影響是肯定的。比如浪費時間、視野越來越狹窄、思維越來越單一,乃至逐漸喪失有意義的思考和反省的能力,就像小火煮青蛙,最后只能死路一條。無節制地沉溺于新媒體,對身心的傷害,跟毒品沒啥區別。
青年報:最后一個問題,你除了工作和寫作以外,還有其他的愛好嗎?
徐則臣:業余愛好是寫寫字、打打乒乓球。乒乓球打得不好,但喜歡,也不求技術上有多大長進,主要是享受活動起來和大汗淋漓的感覺。書法是從小就寫,接近四十年唯一沒斷過的愛好。我爺爺老私塾出身,字好,在外地做小學校長,“文革”時被打成右派,被遣回老家給生產隊養豬。平反之前,為補貼家用,每到春節之前就寫對聯賣。后來平反了,賣字延續下來,一直寫到我念大學。我從小就跟著湊熱鬧,逢年過節都義務給街坊鄰居寫對聯,我爺爺我爸他們忙不過來,就我上。雖然是個票友,也算個老手了。的確是喜歡。
原標題:《上海訪談 | 徐則臣:寫作是一個人的戰爭,我寄希望于下一部;不少人成了“千里馬”,我卻不是“伯樂”》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