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遵循埃科的“生活指南”,離百科全書式作家更近一步 | 此刻夜讀
文學報 · 此刻夜讀
睡前夜讀,一篇美文,帶你進入閱讀的記憶世界。

“我堅信寫作仿諷文學不僅合理,而且根本就是我的神圣責任之所在。”
在翁貝托·埃科的小說中,我們早已體驗到什么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公眾場合與人交談時,埃科也經常口出妙語:他說“上帝躲起來了,因為他不想上《VOGUE》雜志”;他說“現實比夢好:假如有東西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而不會怪罪于你”;他說“要建立不朽的聲名,你首先需要宇宙性的無恥”……
如果覺得《玫瑰的名字》等代表作的知識點太過頻密、難以進入,那么從埃科的短篇散文讀起,無疑是接近這位作家的一種快捷方式。近期,收入多篇新篇、直譯自意大利語的埃科散文集《如何帶著三文魚旅行》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在這本“生活指南”中,埃科式的幽默無所不在:他告訴我們如何度過有意義的假期,如何帶著三文魚旅行,如何避免談論足球,如何在美國坐火車,如何談論動物,甚至,如何成為馬耳他騎士……
戲謔、挑釁、幽默,他將深刻與世俗形成了不可思議的結合。埃科以他頑童般的機智和天才般的玩世不恭,對那些我們從未想過的問題予以解答,又對習以為常的答案提出質疑,將一個個看似“無腦”的話題變得既有趣又深刻。他以“仿諷文學”的方式告訴大家,我們熟視無睹的世界里其實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規則,有些需要被遵守,也有不少正在等人們用機敏和睿智去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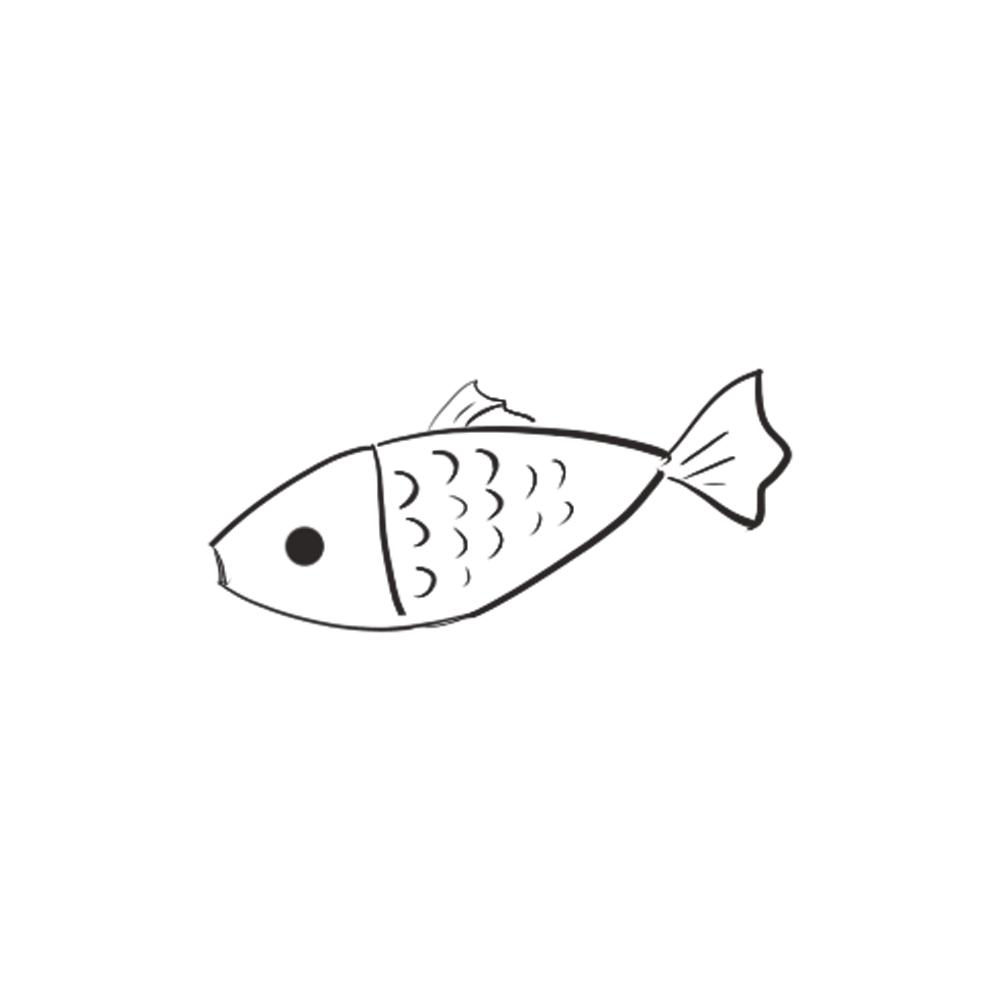
如何避免談論足球

我對足球沒什么偏見。我不去球場,就跟我不去米蘭火車站地下通道過夜,或者晚上六點后不會在紐約中央公園散步的理由一樣。但如果有機會,我也會興致勃勃地在電視上看一場精彩的足球比賽,我承認,這種高貴的運動挺值得欣賞。總之,我不討厭足球,但我討厭球迷!
我不希望造成什么誤解。我對球迷的感情和倫巴第聯盟對第三世界移民的情感一樣:“要是他們都待在自己家里,我也不是種族主義者。”我說的“家”,其實就是球迷通常聚集的地方:酒吧、自己家、俱樂部和體育場,他們在這些地方做什么我都不在乎。假如利物浦球迷來了,我還能在報紙上看看熱鬧,因為從流的血來看,簡直是還原古代斗獸場了。
我不喜歡球迷,因為他們有一個奇怪的特點。他們會這樣說:我不明白為什么你不是球迷。他們堅持認為你應該也是球迷。我可以舉例說明我想表達的意思。我的愛好是吹豎笛,雖然吹得越來越糟糕了,盧恰諾·貝里奧就是這么公開評價的,但被大師悉心指導也是一種非凡的享受。我們假定,我現在坐在一輛火車上,我和坐在對面的先生搭訕,問他:“您聽弗蘭斯·布魯根最新出的唱片了嗎?”
“您說什么?”
“我說的是《淚的帕凡舞曲》,我覺得剛開始節奏太慢了。”
“對不起,我不明白。”
“我是說凡·艾克,您不知道嗎?巴洛克豎笛。”
“您看,我真不懂……是用弓拉的嗎?”
“啊,我明白了,原來您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真有意思。但您知道嗎?定做一根手工Coolsma豎笛,需要等三年的時間。所以Moeck的黑檀木笛子更好些,可以說是市面上最好的。塞韋里諾·加澤羅尼也這么跟我說。聽我說,您有沒有聽到第五變奏。”
“老實說,我到帕爾瑪就下車了。”
“哦!我明白了!您喜歡F大調,我就知道您不喜歡C大調。不過F大調在某種情況下是蠻讓人愉快的。告訴您吧,最近我發現了一首羅埃萊特的奏鳴曲……”
“羅埃什么,這誰啊?”
“我真希望他能演奏一下泰勒曼幻想曲。他應該可以吧?您用的該不會是德國指法吧?”
“您看,德國人有寶馬,我覺得很不錯,最近他們……”
“我明白了,您用的是巴洛克指法,這很對。您看,圣馬丁室內樂團那幫人……”
就是這個聊法,不知道我說明白了沒有:假如這時候,我不幸的旅伴忽然拉響了警鈴,你們一定會贊同他的做法。面對球迷就是這么個情況,要是碰上的是個開出租車的球迷,那就更慘了。
“您看到維亞利了嗎?”
“沒有,可能我當時錯過了。”
“那您今天晚上會看球賽嗎?”
“不看,我要研究《形而上學》第六卷,您知道吧,就是亞里士多德寫的。”
“好吧,您看了之后再跟我說,我覺得范巴斯滕就是年輕的馬拉多納,您覺得呢?但我還是會關注哈吉。”
他就這樣一邊開車一邊說,就好像對牛彈琴。他并不是看不出我不感興趣。問題在于,他無法理解為什么會有人對足球一點都不感興趣。就算我長著三只眼睛,脖子綠色的鱗片上伸出兩根觸角,他也不會明白:我和他不同。在這個大千世界,他沒有差異感,他不知道人跟人是不一樣的。
我舉的是一個出租車司機的例子,但同樣的情況可能也會發生在某個集團總裁身上。就好像潰瘍,窮人會得,富人也會得。但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些球迷一方面堅定地認為全世界的人都一樣,都應該熱愛足球,另一方面又隨時準備打破鄰省球迷的頭,這種極端沙文主義真讓我贊嘆不已。就好像倫巴第聯盟的人說:“讓那些非洲人來吧,看我們怎么暴揍他們。”
如何解釋私人藏書

從小時候開始,因為我姓氏“埃科”的意思是“回聲”,大家都喜歡用這兩句話和我開玩笑:“你是不是別人說啥都會回應啊?”或者“你是不是山谷來的啊?”整個童年我都覺得自己總是莫名其妙遇到一些笨蛋。后來長大了,我不得不相信,所有人都無法避開兩個定律:一下子想到的東西總是最顯而易見的,但他們不會覺得自己一下子想到的東西別人之前也想過。
我收集了一些評論文章的標題,包括印歐語系的各種語言,都是和我相關的,很多在拿我的名字做文章,比如說《埃科的回音》或者《一本產生回音的書》。此外,我懷疑這也不是編輯一下子想到的,可能整個團隊一起開會,討論了二十多個標題,最后主編靈光一閃,說:“伙計們,我想到一個極好的標題!”他的幾個下屬會齊聲說:“頭兒,您真是個天才,您是怎么想到的?”“神來之筆。”他可能會這樣回答。
我舉這個例子,并不想說人們很平庸,沒有創造力,把顯而易見的東西當作靈感迸發、前所未有的發明。這同樣展示出一種精神的敏銳,對無法預見的生活的熱情,對思想——無論多么微不足道——的敬慕。我總是會想到我第一次和偉大的歐文·戈夫曼見面的情形:我喜歡他的才氣,崇拜他的深度和洞察力,他能入木三分地刻畫社會行為的微妙之處,揭示迄今為止還沒人談論過的一些行為特點。當時我們倆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館里,過了一會兒,他看著大街上的人對我說:“你知道嗎?我覺得城市里的汽車太多了。”可能他從來都沒想過這個問題,他腦子里全是其他更重要的東西,忽然靈感一現,說出了這樣一句話。我呢,當時深受尼采的《不合時宜的沉思》的影響,是個勢利鬼,盡管我也這么想,但從沒說出口。
還有一種庸俗的震撼,很多跟我一樣擁有數量可觀的藏書的人都會遇到。進到我家里,一眼就能看到書架,因為家里除了書也沒有別的了。于是客人一進門就會說:“好多書啊!您都讀過嗎?”剛開始,我覺得這是一些不怎么接觸書籍的人說的,他們只習慣于看到擺著五本偵探小說、一套兒童版百科全書的書架。但后來我發現,這樣的話,一些我確信很有文化的人也會說出來。可以說,這些人對書架的看法和我不一樣,他們覺得,書架是放看過的書的地方,而不是用于工作的資料庫。我覺得,面對這么多書,任何人都會充滿求知欲,所以難免會提出這個問題,這表達了他們的焦灼和懊悔。
問題是,當有人拿我的名字開涮時,我頂多一笑了之,客氣的話還可以說句:“好有趣!”但關于書的問題是需要回答的,盡管這時你面部肌肉僵硬,冷汗沿著脊椎骨流下來。我有一次用輕蔑的語氣回答了這個問題:“這些書我都沒看過,要不然把它們擺在這里干什么?”但這個回答很危險,會引發一系列自然的反應:“那你看過的書都放哪兒呢?”羅伯托·雷迪的回答要好一些:“先生,我看過的書比這多多了,簡直放不下。”這會讓提問的人呆若木雞,對你肅然起敬。但我覺得這個回答太殘忍了,也會讓人不安。于是我換了一種說法:“這是我下個月之內要看的,其他書我都放在學校。”這個回答一方面暗示你閱讀量極大,另一方面會讓來客提前告辭。
如何提防遺孀

親愛的作家,無論你是男是女,你可能根本就不在意子孫后代會如何,但我認為此事不可疏忽。任何一個人,即使是在十六歲時寫了一首關于風吹過樹林的詩歌,或者記了一輩子流水賬,就算只寫過“今天我去看牙醫”,都希望后人能視若珍寶。即便真的有作家渴望被人們遺忘,如今的出版社總是會全力挖掘出那些被遺忘的小作家,盡管有時候這些作家一行字都沒有寫過。
要知道,后人是來者不拒的。為了能寫出點兒什么,逮住什么是什么,前人寫的東西更是拿來就用。因此作為作家,你可要當心后代如何使用你留下的文字。自然了,最理想的是在有生之年只留下那些你決定要出版的作品,把其他東西定時銷毀,哪怕是一部作品的三校稿。但即便如此,你還是會留下一些筆記,因為死亡經常來得很突然。
在這種情況下,身后最大的風險就是生前的筆記被爆料,讓人覺得你簡直就是個十足的白癡。如果每個人都回過頭去讀讀自己前一天晚上記在本子上的東西,就會發覺風險太大了,因為任何文字脫離背景都顯得很傻。
假如沒有筆記,第二大風險是在你死后像一陣風一樣掀起關于你作品的研討會。每個作家都希望有人寫學術論文、畢業論文、作品的評注版來紀念自己,但這是很花時間和精力的事兒。死后馬上舉辦研討會,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這會讓一堆朋友、評論家和渴望成名的年輕人匆匆忙忙寫下評論文章,大家都知道,這種情況下只能炒剩飯,把之前人家說的再說一遍。就這樣,過上一陣子讀者可能會對作家本人失去興趣,覺得他不過爾爾。
第三大風險是私人信件公布于眾。作家也是凡人,寫的信和凡夫俗子沒什么兩樣,除非他像大詩人福斯科洛一樣,通過書信來寫小說。作家可能在信中會留下這樣的句子:“給我寄一些治便秘的藥。”或者:“我瘋狂地愛著你,感謝你降臨人間,我的天使!”自然了,后人去查看這些資料也很正常,他們會得出結論,大作家也是人啊!那還能怎么樣,難道他會是一只火烈鳥嗎?
如何避免這些身后的事故?對于那些寫作時記的筆記,我建議你們藏在一個別人想不到的地方,同時在抽屜里放一份類似于尋寶圖的文件,說明存在這些筆記,但要用一種別人無法破解的語言記錄文件的具體位置。這會產生雙重效果,一則隱藏了手稿,二則會催生很多學術論文來討論這張地圖的謎底。
針對研討會,可以在遺囑中寫清楚,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在你死后十年內舉辦的研討會必須捐贈兩百億里拉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搞那么多錢絕非易事,但要違背你的遺囑,那也得臉皮夠厚才行。
情書的問題比較棘手。還沒來得及寫的情書,建議用電腦完成,好讓那幫筆跡學家無從下手,簽名時要用昵稱(“你的小貓咪、小狗子、小兔兔等等”),每換一個情人就換一個稱呼,到時要都算到你頭上也很難。情書可以寫得熱情如火,但建議留下些讓收件人覺得尷尬的細節(比如說“我也愛你的臭屁連天”),這樣對方可能就此放棄公布的念頭。
但那些已經寫好的信,尤其是青少年時期寫的,就無法挽回了。最好的補救辦法是找到收信人,再寫封信給他們,心平氣和地追憶往昔的難忘歲月,再三強調那段記憶不會褪色,即使你死后,也會經常探望故人,重溫舊夢。這一招不見得管用,但再怎么說,鬼魂可是鬼魂啊,那人公布了你的信,也會睡不安生。
你還可以寫一本假日記,在里面要暗示你的朋友們有弄虛作假的愛好:“真是一個愛說謊的女人,我可愛的阿德萊德!”或者:“今天瓜爾提耶羅給我看了一封佩索阿的書信,那是一封偽造的信,但差點兒讓我信以為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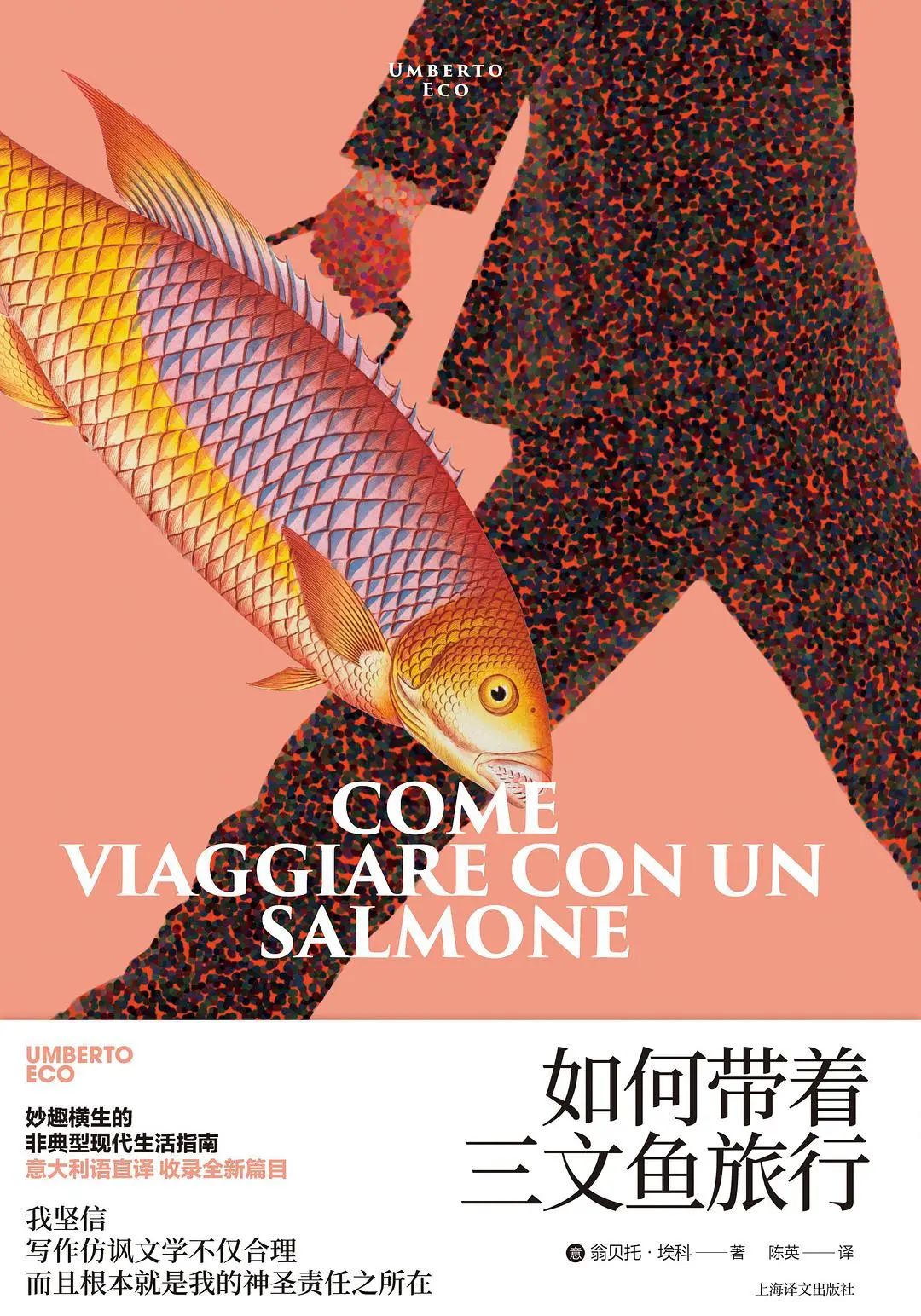
《如何帶著三文魚旅行》
[意] 翁貝托·埃科/著
陳英/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原標題:《遵循埃科的“生活指南”,離百科全書式作家更近一步 | 此刻夜讀》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