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談︱羅新、魯西奇:發現弱者的歷史
6月19日上午,羅新與魯西奇兩位教授的對談在武漢大學珞珈山莊第六會議室舉行。羅新現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魯西奇現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對談活動由武大歷史學院魏斌教授主持。這次活動主題為“發現弱者的歷史”,來自武大、華中師大等校的眾多老師和學生到場聆聽,并參與討論,氣氛熱烈。茲根據錄音整理對談部分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魏斌:羅老師長期研究草原部族強勢者的歷史,為什么開始關注弱者的歷史?
羅新:我過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根據墓志理解北朝社會或南朝社會,根據這點理解再去讀老師們和同代學者的一些重要研究,從這個角度去掌握一點知識;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做所謂草原歷史的研究,草原歷史研究跟草原歷史一樣,很薄弱,將來一定會有學者做得非常好,比我想象要好得多。我現在主要回到從墓志看北朝社會的研究。
我們知道北朝墓志都是以前有錢人、有權的人留下來的,都是當時的上層社會,下層社會的人沒有墓志。但是呢,在讀墓志的過程中,也能看到社會的差異,或者是一些受迫害的受侮辱的,被推到邊緣去的,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人。這個思路我過去很早就有了,我大概在做北方民族社會的時候就盡量避開帝王將相啊、征服者啊,就盡量避開跟這些人過度接觸,擔心跟他們接觸太深,產生對他們的崇拜。
另外,我的性格,別人說我是一個老是跟人家唱對臺戲的人,有點桀驁不馴,不容易當一個順民。這個性格對我的學術研究也是有意義的。第一,在學術思潮上不愿意跟著主流,第二,在研究對象上我不愿選擇大家都崇拜的人,你們喜歡孝文帝,你們喜歡馮太后,你們喜歡研究他們,我就不大樂意,或者我會研究他們的另外一面。我想的是我們不能只看到這一面,還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一些人在歷史上好像總是站在臺面上,在比較熱鬧的地方或是被歌頌的地方,另外一些人處在被擠壓被打壓、作出重大犧牲,同時又被歷史埋沒被遺忘的狀態。所以我更愿意看到被壓迫這一面,因為這一面往往被歷史遮蔽了。當我看到這一面,我就忘不了這一面。
最近在我生活中影響很大的一件事:有一天,我看完電影,散場的時候都十一點、快十二點了,我從電影院走回家,看到路邊有個老太太,也許有八十歲了,也許年輕一點,她擺著一堆東西在街頭賣,但這個點了,街上幾乎沒有什么人了,我走過去了,但我心里覺得很不舒服,又走回來,問她:你是不是在賣東西?這么晚了,又沒有人。她說:白天不能賣啊,只能晚上賣。我們家沒有別人,只有我一人。我覺得她沒有必要撒謊,我顯然只是問問她,不是想買什么東西。不知道為什么,這個事對我影響很大,很久老想著這個老太太。我想生活中這樣的人很多的,人類相當部分是這樣的人,而他們在傳統歷史學里是不被關注的,這些人不會進入歷史學家的寫作當中,或者說不會成為歷史素材,根本不會被記錄。可是他們是我們生活當中的人。
這種情緒這種思路糾纏我很久了。從去年開始,這個思路逐漸清晰,前年在這里參加青年學者聯誼會的時候,我講過“走出民族主義史學”,當然我那時候還是針對民族主義史學,還不知道該怎么辦。但是我們不能只是走出,走到哪兒去呢,這是一個問題。當時能夠設想到的辦法,就是回到個體。用個人來against,不叫對抗,不是抵抗,反正就是在這個背景上,我們還是承認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這一套話語是主體、是主流、是主導,但是不能只有這個,還得有一些在這個背景下的別的話題,比如個人,比如邊緣。去年楊奎松先生出版了一本《“邊緣人”紀事》,那里面講到1949年之后一批很普通的人,甚至一些很糟糕的人的經歷,即使用我們今天的道德標準,寬容的態度來看,這些人都不值得來往。同性戀者、小流氓、小偷,這種人當然你不跟他們來往,但他寫了一群這樣的人。我是非常感動地讀了他那本書。這些人也是歷史學家應該關注的。

大概從這些思路出發吧,來來回回的,這幾年很幸運,尤其常碰到魯老師。我很吃驚啊,萬人之中不知道誰的想法跟你一樣的,我很意外地發現魯老師的想法基本上跟我一樣,當然他比我思考得深一些,關注的具體問題也不一樣,但是我覺得在情感和理論的層面上是有共同的關懷的。而且我相信,吾道不孤,不只有我們幾個人,事實上只要有機會出去談,不管是不是同齡的人,都有同樣的思路,都有同樣的想法。這幾年別的工作做不下去了,因為過去的思路斷掉了,甚至被否定了,做過的都是半成品。我不到五十歲,或剛過五十歲的時候,這種內心的煎熬就很嚴重了,老想做點什么不一樣的。我現在還處在摸索的階段,嘗試去做一個實驗性的工作。
這學期我在民族史的課上,跟同學討論、交流。我當時剛看完這本書,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思路。大家知道,Charles Mann寫了兩本書,都很通俗易懂,一本是《1491》,一本是《1493》。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美洲,這個作者就以1492為斷限,把1492之前看作一部歷史,之后是一部歷史。他不是一個學院派的歷史學家,但是他讀了很多專業的書,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提出“哥倫布大交換”概念的Crosby,大概Crosby跟他私交也很好,還專門為《1493》寫了推薦語。《1491》我讀了之后,感覺不是很強烈,但我讀完《1493》,特別讀到第九章,覺得很棒。第九章題目叫作“逃亡者森林”,寫的是歐洲人對美洲殖民,美洲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殖民的高峰時期,17世紀到18世紀中期,整個美洲的變化非常大。第九章舉了好多事例,搜羅了好多材料,專門講我們剛才說的邊緣人:逃亡的奴隸,反抗者,不服從國家秩序的人。他專門寫了這些人,比如逃亡的奴隸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抵抗了很久,有的抵抗了長達五十年、八十年,有的還部分獲得了成功,使得某個地區的歷史面貌跟過去大不一樣。當然有些反抗失敗了,但他們反抗的時間很長。這是我們過去講歷史、寫歷史都不容易觸及的話題。過去我們的歷史觀就是國家主義史觀。簡單地說,叫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國家主義,不是以哪個民族,而是以國家結構為中心,以它為唯一的衡量標準來談歷史,來結構我們的歷史,來重新敘述過去的歷史。像這樣反國家的,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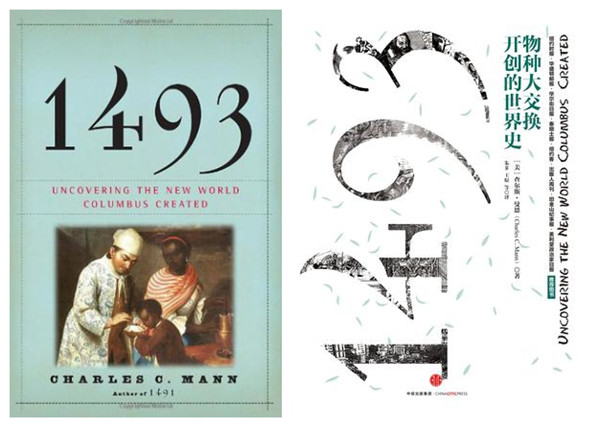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James Scott《不被統治的藝術》,中文譯本叫作《逃避統治的藝術》。我讀Scott的東西,也是很感動。他有一個特點,他把東南亞高地,zomia,這樣一個地區的很多人群,描述成主動逃避國家、逃避大型的社會政治構造,而這種敘述很不符合我們過去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部落到國家那一套。他說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愿意走這條路,當然有的地方顯示走了這條路,但是有的地方的人主動逃避走這條路。我過去寫《王化與山險》討論中古蠻人,魯老師也有一篇文章討論這個時期的蠻人,我們都涉及這個話題,但是在理論上沒有給它總結。我們當時意識到了,這種人不愿意加入到一個更大的政治組織。秦始皇統一六國,其實那是很大的災難。原來是在一個小國家之內服役就很費勁了,但是秦統一之后一下子從安徽從江蘇跑到漁陽服役,那不起義才怪呢,日子沒法過呀。我們過去大概意識不到這種歷史敘述,或者說沒有深刻意識到它所帶來的災難和痛苦,因為都在討論統一啊、國家發展啊這些看似更大的問題,就把那個話題擱下了。像這樣的思路在我內心糾糾纏纏來了好久。如何把這些想法落實到我的具體研究,這就變成我最大的難題。
我想人文學的研究不在于具體課題本身,而在于即使對你說的這個故事興趣不大的人,讀了之后也會有啟發。這就超越了個案,更有價值。我是說,在走出國家主義史學,或者說,在國家史觀的籠罩之下,可以做出一些新的工作。大概很多人已經走出國家史觀了,而我們知道,傳統史學還有一個英雄史觀。很多學者已經走出英雄史觀了,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由于進入現代歷史學之后,問題史學成為主導,作為個體的人在歷史學中似乎變得不重要了,在這種情況下,英雄史觀在悄悄地起作用。所以我覺得今天還存在一個任務,如果回到個人的話,同時要非常警惕英雄史觀。我們所說的個人,其實并不平等,身體狀況、個人能力,等等,都是有差異的。但是這些差異是不是可以放大為歷史,好像變成對歷史發生作用的差異,這是很危險的,不能簡單地就想到這一點,好像有些人就是對歷史影響大,另一些人對歷史影響小,我們內心也不容易懷疑我們的直覺,但是我總覺得我們面臨著真正把英雄史觀從腦子里去掉的任務,必須把這個問題解決。我們總是講帝王將相,總是講成功者,現在真的應該看到那些英雄是被塑造出來的,所有的英雄都是被塑造出來的,都是因為各種各樣的歷史原因被造出來的,上到皇帝,下到普通英雄,都一樣。我相信有一些強勢的力量,但不相信有一些強勢的個人。大概強勢的個人都是各種原因造出來的,在讀歷史、想歷史和寫歷史的時候,怎么把英雄史觀真正拋棄掉、清理掉,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我認為國家史觀、英雄史觀還是目前主導的史觀,所以怎么把這個去掉,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同時,我還在探討一種歷史敘述的方式,就是怎么寫歷史的問題。現在我在寫作上自由度很高了,但是怎么用好這個自由,怎樣寫出一個好玩的,有意思的,也是歷史的東西,是我時刻琢磨的。畢竟我希望我所尊敬的同行看了之后說,你寫的東西也還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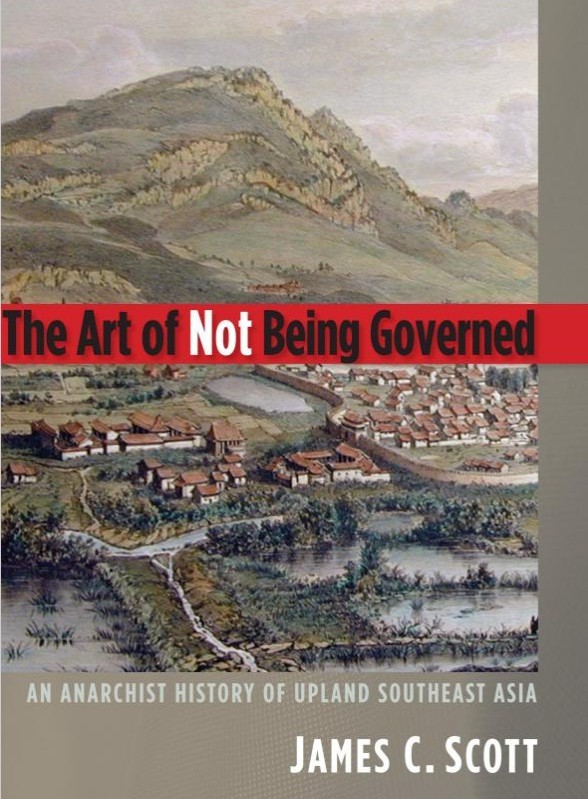
魏斌:您定義的弱者,是像斯科特這樣明確的一個階層的人群呢,還是觀察人群的一個角度啊?其實強弱之分是可以轉換的,每個人既是強者,也都是弱者。像孝文帝,他是一個強者,但早年馮太后在世的時候,他就是個弱者。您怎么定義弱者?
羅新:對。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過去我們說邊緣人的時候,也有這個問題,誰是邊緣人呢?我是這樣想的,人和人之間,人群和人群之間,因為社會現實而造成的強弱高低之別。就他個人而言,作為個人的孝文帝,和作為皇帝的孝文帝,是兩個人。這兩個人有邊緣,有弱者。他失去了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他誰都不能相信,甚至跟皇后說話都拿著一把刀,這樣一個人,你能說他是強者嗎?他已經嚇得要死了,這個人是弱者。代表著國家的時候,他是強者。在他本人面前,他所代表的體制是一個強大得多的強者。馮太后也一樣,她固然有一個時刻強大得不得了,但她有一個國家。跟國家相比,所有的官員、帝王都是弱者。這確實是相對而言的,就像我們搞出一個弱勢群體,當然這是體制化的弱勢群體。
魯西奇:據我理解,這個弱者是相對于民族、國家,甚至大眾而言的。對每個人來說,面對的是遠比自己強大的社會和文化的權力。所有人都可以是弱者,或者說所有人都有弱勢的一面,但這一面經常被掩蓋起來。我想即使是君王,面對國家,就像羅老師剛才舉的孝文帝,作為個人,即使是皇帝,他所面對的制度,那個所謂的文化傳統,他也可能是弱者。如果這樣來理解,把弱者的歷史,理解成個體的人的歷史,會更清楚一些。我們說弱者的時候,容易引發歧義。
魏斌:我們這個話題的意義,在于發現在國家面前,作為個體的人弱的那一面。我們就是要去發現這樣的歷史。
羅新:這就像戴上新的濾鏡,我們專門找其中的這一面。在個人生活中也有跟他(她)個人意志相沖突的地方,我們看,跟個人意志相沖突的時候,他(她)個人是什么反應。這種反應有時候構成了塑造歷史的力量之一,雖然不一定是主導的力量。而這一面往往是被忽略的。過去一般強調歷史是理性的,所以就討論所謂的歷史大勢,歷史的另外一面就不討論了。而歷史的豐富性就表現在個人意志跟周邊環境有沖突的地方(當然也有協調的地方),在發生沖突的地方他怎么反應,這是歷史當中非常有意思的。對于個人能力非常強,權勢非常高,地位非常重要的那些人來說,他(她)的反應是一方面,而對于普通人,小到小蘿卜頭、街上的一個乞丐,他(她)也有個人意志發生沖突的時候,他(她)的反應也應該納入視野。我是想說,應該具備一種敏感,學會一種尋找,老是發現這種例子,討論這種例子,使他們成為歷史觀察的一個對象,成為歷史描述的一個對象。
歸根結底說實話,我是覺得到了一定年齡,學歷史的人,——用唐(長孺)先生的話,“勤著述,終無補”,對不對?但我們還是想有所補的,這個“補”在哪里呢?也許最終還是跟唐先生所說的那樣“無補”,但我們希望有所補,因為不甘心嘛。“補”在哪里呢?那就圍繞我自己的工作做一點事情,如果只是去歌功頌德,去順應國家發展大勢,那實在跟很多歷史學家的初心是不相一致的。如何講出不同的歷史,就是對現實有所回應,滿足自己內心的一點點需要。

魏斌:在我們心目中,羅老師是做統治者的歷史的,他是出于良心發現,來關注弱者的歷史。(眾笑)魯老師,您長期做基層社會的研究,您是從弱者群體出來的(眾笑),您怎么看弱者的歷史?
魯西奇:在國家,在制度,在強大的文化權力面前,甚至在大眾面前,個人非常非常渺小。而且,這種不斷彌漫開來的、逐漸強化的孤立和無助,在這個全球化和所謂網絡的時代,越來越強烈。它反過來讓我去想,在這樣一個世界里作為個體的人的覺醒和對個體的局限性的認知。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很多人喜歡,它很有市場啊。為什么很多人擁護它?其實它提供了一個逃避自己、克服自我覺醒的工具。如果有一個“國家”給我們安排所有的一切,多好啊。
這些年我對華南的研究接觸得比較多,我在思考我們所說的作為個體的人的歷史,或者弱者的歷史,它并不是大眾的歷史。其實作為整體的大眾不是弱者,不管它是否有組織,大眾在本質上跟民族、國家是分不開的。無論怎樣意義上的大眾、民眾或者烏合之眾,都不孤獨,不孤立,都不突顯“個體”,他們甚至“抹殺”個體。各種集體主義的表達和組織,實際上跟“國家”是吻合的。所謂立足于民眾的,從地方社會出發的,自下而上看待國家的,這些研究本質上還是國家的歷史。它是中華帝國史的地方社會版或民眾版,甚至是地方精英版。
我大概從2013年開始涉及濱海地域的歷史,其實我是有意識地想去看,跟山區蠻人一樣,在國家直接控制之后,這群人是怎樣生存的。這兩年我又有一點困惑,當我們把他們當作人群、群體的時候,又賦予了他們力量,甚至賦予了他們反抗的力量。但是在歷史過程中,他們沒有感受到。就像山里的那些蠻人,他們一個個很孤立,只有被裹進某種組織,不管它是政治的還是社會的,他們才感受到他們是那群人的一部分。在我們的研究尺度里頭,羅老師做的宮女的故事,胡鴻討論過的各種群體的問題,我們要把握怎樣的研究對象呢?這是一個我不知道的東西。在墓志里頭,以及其他材料,我們可以看到個體的人;但在更多的歷史文獻里面,我們看到的是一群人,他們由若干個人組成。但是這個群體是不是文獻制造出來的呢?
胡鴻讓我接著羅老師的話來講怎么做。我覺得如果我們來揭示弱者的歷史的話,第一個可能要說清楚他們為什么是弱者。在國家、制度和文化的力量面前,他(她)如何成為弱者。傳統制度史的研究,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結構主義的分析,和作為權力的文化史的考察,這些研究從很多方面告訴我們,作為個體也好,作為群體也好,他們所面對的力量非常強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她)一定弱。他(她)的弱,是指他(她)的個人權力和意志被剝奪了。所以我想有一個東西可以做,就是古代制度如何控制個人的行為,如何侵奪個人意志和群體意志,如果研究這個東西,材料應該是許可的。我這學期上的課是鄉里制度的研究,我的入手點就是想看鄉里制度確定以后,本來不需要繳稅納賦的人,如何被迫給國家勞動。那些散布于農舍田間的農戶,他們被納入王朝國家控制體系,成為編戶齊民。我把這個過程,稱作“從人到民”的過程。我相信,我們同樣可以去關注那些讀書人,又是如何從“人”變成“臣”的過程。在國家制度與機器面前,民、臣都是孤立的個體,他們主動或被動地進入王朝國家體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是孤立無助的。
第二個,羅老師說這些人在歷史的過程中是有自己的能動反應的。面對國家體制,我們的選擇大約有兩種,一種是從,一種是不從。迄今為止華南研究揭示了不同區域不同層次的人群進入國家的方式和過程,他們最終成了這個國家、民族和文化的基礎。在我看來,這是華南研究這些年來做的一個最大的貢獻。那么另外一個選擇,大概有三種方式,抗拒是一種,逃亡是一種,自主選擇、主動死亡是一種,這個概念是從弗洛姆那里來的。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抵抗方式。那些已經進入國家體制的人,被納入王朝國家的人,我們不去看他們進入國家的過程,而關注他們脫離國家的過程,他們有不同的方式脫離國家。他們會成為浮浪人、成為逃戶、成為亡人,這說明他們之前有一個進入國家的過程。我們說到斯科特的研究,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魏斌:也就是說,他們原先都有一個積極融入體制的過程,那么他們脫離國家之后的走向是什么?成為蔭戶,成為附屬民,成為部曲,成為另一種體制下的人。
羅新:但我覺得價值不在于反抗是否成功。也許不成功才是我們史學關懷所在。主要要看他們為什么會有這個選擇。當然也要看到,對他們個人來說,這種選擇是失敗的。或者從外界觀察來看,他們還是被抓走了。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因為這揭示了所謂國家是什么,有助于打破我們對國家一味的崇拜,我們看到國家并沒有那么美好,這對于人的理性認知是很有意義的。
魯西奇:我想意義可能還不止于此。弗洛姆說人類歷史起源于最初的不從,所謂亞當夏娃在伊甸園里沒有聽上帝仁慈的安排,做了上帝不許可的行為,才有了人類的歷史。他從這個角度來講人類的起源。他還講了很多其他例子,總之不從導致革命、導致改良,那么我們可以說“從”服務現實,建設現實,“不從”帶來變革,創造未來。你說的蔭戶的例子,恰恰說明他們要逃離國家直接控制的編戶系統,與此相配合的,這樣一套新的體制出來了。隨著逸出體制的人越來越多,而且是富有力量的那一部分,這就導致了舊有體制的徹底崩解。這是革命啊。
羅新:歷史就是這么塑造的。
魏斌:他們逃離了國家體制,而進入私人控制的一套體制。
羅新:這可能是新的國家體制的雛形,至少是新的國家體制的選項之一。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