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許子東視頻專欄:為什么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至今深受推崇
三八婦女節,許子東老師跟大家聊聊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這部小說有哪些突破意義,為什么它至今仍深受女性主義批評家們的推崇,并給大家推薦一下女性主義的書。
要理解《莎菲女士的日記》在1928年文學史上的意義呢,我們要稍微回顧一下在這之前五四新文學中愛情文學大概是一個什么情況。可以以魯迅的唯一一部愛情小說《傷逝》為例子。
它(《傷逝》)就是男女主角談戀愛,女的到男的書房來,男的就跟她講雪萊、拜倫、惠特曼或者易卜生,女的沒有說話,一直在聽。半年以后,女的就回答說,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估計在講歐洲文學的時候,這個男的就“忽悠”她要離開家庭、要戀愛自由等等。這個故事對我們小時候影響很深,以至于我們小的時候一談戀愛,先要談海明威、畢加索,不好意思先講房子、車子之類的,非常庸俗。但是仔細看魯迅這部小說,有一個很好笑的現象,就是當一個女的等于是給他一個承諾、一個回答的時候,涓生說:可見中國的女性不是完全沒有希望,我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這就有點好笑了,現實當中,比方說一個外地人來上海,他跟上海人拍拖了,他會說可見上海女子也還是有希望的嗎?不會這么說對不對。可見魯迅這部小說,它不單純是愛情小說。以《傷逝》為代表,其他還有像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創造》等等,甚至包括《邊城》、《家》、曹禺的《日出》,這一系列作品他們都有個共同的模式:男的愛上一個女的,這是第一層;第二層,男的可以教女的一些東西,就是男的在文化上高于女的,因此他可以給她講一些道理,給她指出生活的各種各樣的可能性;第三,在象征意義上,男的好像是喚醒大眾的知識分子,而女的呢,就像黑房子里睡著的、等待被喚醒的大眾。第三層意義就是五四文學的基本主題:啟蒙主題。因此,在丁玲之前,愛情文學通常是三層結構:愛情文學、教育文學、啟蒙文學。這沒什么錯,在當時,有它的局限,但是也有它的意義。

電影《傷逝》劇照
問題在于,我們做了一個統計以后發現,這一類的小說,它的男主角有幾個基本條件。其實晚清的青樓小說已經有條件了,王德威總結說男的要三樣:才、情、愁,要有才,要能動感情,要發愁,就是要憂郁、要深刻。那么到了五四的時候,有才呢,還要有一個政治正確,要追求進步,所以為什么《小團圓》挑戰大,大家就很不理解張愛玲喜歡上了那么一個人,當時大部分作品沒有這種情況;還有一個因素是經濟,有錢,但有錢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沒錢一定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沒錢如祥子這樣就很慘,但有錢有時候也是一個隔膜,你看《邊城》里有錢也不一定好,覺慧有錢也救不了鳴鳳等等。有一個特點就是這些男子,當他喜歡上一個女的以后,他一定不花心,沒有一部小說里的男的是渣男,渣男的問題是女作家后來才寫的。
還有一個問題,所有這些男主角都沒有相貌,現在大家說魯迅的每個字上爬了很多學者,我想請學者告訴我,涓生長什么樣。同樣,郁達夫的小說也是(如此),茅盾的小說也是(如此),我們知道翠翠很漂亮,有相貌描寫,二老長什么樣,大老長什么樣,不知道。所以,這里就帶出一個非常嚴肅的、女性主義研究的課題:為什么男作家——男人很自戀的——寫的小說,他不描寫男主人公的相貌,不寫他的身材?第一個原因是,這些小說用的是一個男人的視角去寫的,因此他只寫女的長什么樣;第二,他假定,男的能夠談戀愛,女的會愛上我,不是因為我長得怎么樣,而是因為我有才,有錢,我忠實,我進步,夠了。從男性的觀察角度去描寫愛情,這其實是一個男性中心主義的觀點,不要看他寫女性有多少,寫女性很多,不一定就是他尊重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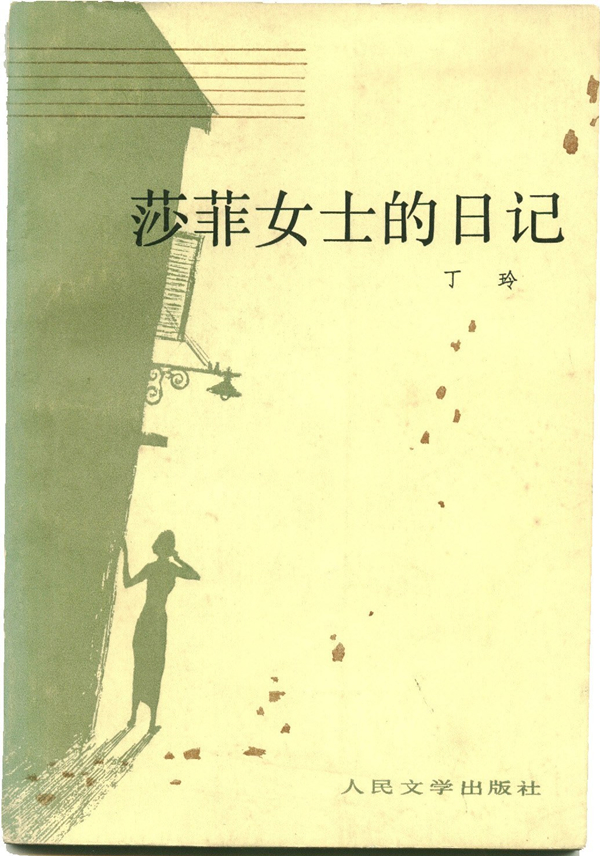
《莎菲女士的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現在我們可以來論述為什么《莎菲女士的日記》有突破意義。它的第一層突破意義是先顛覆了男的俯視、女的仰視這么一個基本的男女關系模式,那就是莎菲的一個追求者,叫葦弟。葦弟非常喜歡她,但是見到就哭,女的不喜歡他,但是也不拒絕他,就放在邊上,香港的說法叫“收兵”,現在的說法叫“備胎”。男的明明比她大,可能個子也比她高,但是她在精神上完全壓倒這個男的。第二層意義更重要,碰到了一個南洋回來的僑生,美男子,一見到就看他的嘴唇,她說像個蘋果,想要去咬他的嘴唇,然后日記里寫:夢想著要吻他的全身,所有的地方……今天網友的微博、微信都未見得敢這么寫。這至少是中國現代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對男性的情色觀察,是一種女性的情欲視角。丁玲后來可是付出了巨大代價,說她玩弄男性,就是因為這個。
除了這本書外,如果讓您推薦值得看的女性主義圖書,您會推薦哪幾本?推薦理由是什么?
我推薦鐵凝的《大浴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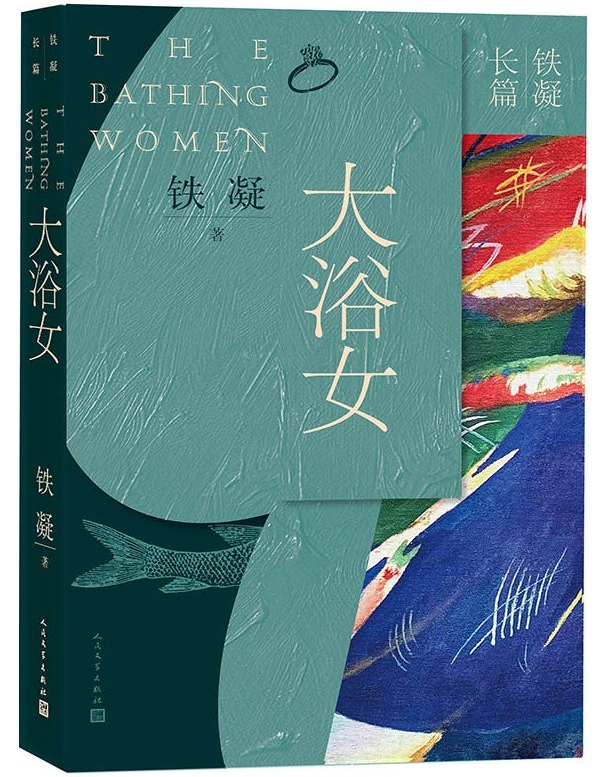
《大浴女》
《大浴女》它也是法國印象派的一幅畫,小說呢,女主角解剖她的媽媽的不倫之戀,然后解剖自己的幾次男女關系的艱難選擇,包括她的一個好朋友,不斷以情色為工具打開她的人生道路。小說背景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寫女性情欲之大膽,不在丁玲之下。我只舉一個小細節,這個小細節我就覺得非常好玩。大約1970年代初,女主角的父母在一個五七干校,干校里把男的干部跟女的干部分開居住,但是他們有一個星期天可以相會。相會在哪里呢?這個地方山上有一個小屋,在星期天,這些男女就會到那個小屋去聚會。去接近那個小屋呢,人比較多,所以要排隊,但是如果一對一對的人在那里排隊,有傷風雅,大家也不好意思,怎么辦呢?就會出現一個場景,那些男女就在山上的路、樹林這些障礙物的地方好像在那里看風景,但是他們都明白誰排在前面,誰排在后面。然后,進去的人呢,知道外面有這么多人在等,廢話就少說了,進去以后該干啥就干啥——這不是我說的,這是小說里面的描寫。但是鐵凝到底是純潔,她就寫到了這些人物趕快做完事,離開了山上的小屋,她就沒有描寫這些人其實也不能做得太快,時間也不能太短。為什么呢?大家自己想吧。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