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臺灣美食家朱振藩:西餐的盤文化與中餐的鍋文化相差太大
被稱為“現代食神”的臺灣美食家、作家朱振藩到目前為止已經品嘗過五萬道菜、千種美酒,自嘲“舍得花銀子,吃掉了一幢以上的房子”。
品評美食之余他自稱也愛“舞文弄墨”,現在大陸和臺灣出版的,以美食、美酒、相學為主題的著作已達將近50部。
除了美食和寫作之外,他還因有36位女弟子而備受關注,其中包括臺灣作家李昂、曾郁雯,主持人于美人、吳淡如,“2014年亞洲佳女廚師”陳嵐舒、演員朱茵、“2005年香港小姐”林莉以及知名臺商何麗玲等。
“我只是帶她們吃喝玩樂,吃飯的時候我很喜歡品酒,又有美女可以欣賞,此生夫復何求。”

朱振藩稱在認識太太之前是個宅男,“沒有女朋友,只好退而讀書,以‘誤人子弟’為業(yè)”:周二和周五晚上批紫微斗數,周三晚上教書法,周六下午教面相,周日教網球,行有余力就出去看風水。
他曾經為相學下過一番功夫,在大學的時候就被稱為“半仙”,就連非本校的學生都要托人找他看相,而他出版的第一本書也和相學有關。但他稱在餐桌上找到人生的真諦后,相學研究就不再重要了。
現在已過耳順之年的朱振藩說自己終其一生就“不學無術”四個字,涉獵很廣但都只是“點一點”,“不過還蠻樂在其中的,不愁沒東西打發(fā)時間”。他希望自己年老的時候還有赤子之心,能夠瀟灑悠游過一生,“平生也無大志,又沒辦法治國平天下,只好修身”。
以下為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朱振藩的專訪:
西方的“盤文化”和中國的“鍋文化”
澎湃新聞:您在書里有講到過“‘吃’也分為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如果你吃了一樣美食僅僅覺得它很好吃,那就是下里巴人了。”那吃文化中的“陽春白雪”是什么?
朱振藩:其實我是覺得真正的美味都藏在巷弄之間,小巷不但藏珍饈,還藏美酒。量產的東西通常都是給一般大眾吃的,所有的飲食品牌都是吃名氣、吃氛圍。但要吃到真正的味道,可能還是要到平民中去尋找。有的小吃店老板終其一生就做那兩三樣,所以越做越精,但就怕傳承的時候青黃不接。
其實所謂“陽春白雪”部分就是通常文人雅士比較懂得吃,一般人可能是饕客的吃法,而不是吃得精和吃得巧。有的菜可能滋味不錯但很平凡,可是經文人品題之后,馬上就身價不同。
我也吃過很多頂級的宴會,像“張大千宴”、“紅樓夢宴”等等不計其數,包括我在大陸的大弟子曾在上海、香港、北京、臺北舉辦的幾次宴會,用中國的美器配上中國的美食,我也都通通吃過。但我還是喜歡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喝幾盞小酒,吃些自己適口的好菜,我覺得這才是飲食的最高境界。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這10多年大陸和臺灣的飲食文化有何值得關注的變化嗎?
朱振藩:其實臺灣西化很嚴重,而大陸現在正好是方興未艾。曾幾何時,中國菜是世界第一,現在知名度卻在法國菜、意大利菜之后,其實據我來看,他們那些都是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但是離真正的“割烹之道”還差得很遠。
我也吃過很多米其林星級的餐廳,吃了以后雖然不至于廢箸而嘆吧,但想想實在很像“辦家家酒”。
然后因為剛好現在的人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動得少,對很多東西了解的也不夠,一看到那些新奇的東西就容易見獵心喜,自然而然外來的飲食文化就水漲船高,再加上現在的大媒體還在西方和日本手上,他們自己推波助瀾,老王賣瓜,所以真的是不堪聞問。

澎湃新聞:那您覺得中國菜比法國菜、意大利菜好在哪里?
朱振藩:西方和日本強調“盤文化”,菜品在盤子里的顯現定要能賞心悅目,讓人吃得下,好處馬上就能看得見。我們中國是“鍋文化”,所有的精華都蘊藏在那一鍋里面,要吃到嘴里才會直沖腦門,驚喜萬分。兩者的差異太大。
現在是麻辣鍋“一統(tǒng)天下”
澎湃新聞:您之前去山東的時候說過有些菜系需要恢復。
朱振藩:其實山東菜主要是膠東幫和膠西幫。尤其是膠東幫中的“福山幫”幾乎完全被北京吸收了。到現在為止,山東本身也不夠富庶和繁華,所以就被京菜取代了大部分。而且因為北京是首善之區(qū),而像江南菜、川菜、湖廣菜通通都有同鄉(xiāng)會館,他們自己已經變成一個體系,所以可以跟原來的四大菜系齊頭并進,這是有地理因素在其中的。現在上海菜也是風行一方。
澎湃新聞:山東菜好像賣相一般,和這個有關系嗎?
朱振藩:當然有關系,其實拉面發(fā)明于福山,最早記載在明朝宋詡的《宋氏養(yǎng)生部》里面。結果到日本,他們在一碗拉面湯頭上的配料下功夫,再加上日本的海鮮,合為自己的文化,把拉面變得有聲有色。其實湯頭也是福山的做法。雖然還稱“中華拉面”,但也和日本的地域相結合,叫“札幌拉面”之類的。
同樣一碗拉面,人家可以做得那么漂亮,我們還在固步自封,這是我們可以就近取法的地方。

澎湃新聞:那除了魯菜,還有哪些菜系值得恢復?
朱振藩:其實在《清稗類鈔》里,那時中國的十大地方菜,江蘇菜就居其五,其中有淮揚菜、
南京和蘇州的京蘇大菜、蘇州菜和無錫菜組成的蘇錫幫。所以那時天下最美味的地方幾乎都在江蘇,也是全國最富庶的地方,再就是杭州菜比較有名。后來江蘇這五個地方集合起來變成蘇系菜,跟魯菜、川菜、粵菜剛好稱為四大菜系。雖然我祖籍是江蘇,但覺得這樣做著實委屈了江蘇。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餐飲連鎖業(yè)對于美食文化的沖擊?
朱振藩:對美食文化的沖擊當然很大。因為他們有品牌,廣設分店,原料的購買成本就被壓低了很多。然后就是同一道菜就想放諸四海而皆準,這樣基本上很難做到。
美國當初國力很強,所以肯德基、麥當勞才能有發(fā)展空間。但現在這些快餐連鎖品牌隨著美國國力不在,就慢慢失去了他們的優(yōu)勢。實際上麥當勞的薯條到底是法國的還是比利時的,兩國還爭戰(zhàn)不休,但總之不是美國的。
澎湃新聞:現在有些連鎖餐飲的營業(yè)額也在下降。
朱振藩:我不知道大陸的麥當勞怎么運作,在臺灣的麥當勞都是先把門店附近可以買的房地買下來。其實他們是要炒地皮,不是賣食物,賣食物只是要維持地價而已。我覺得就飲食來說不足取法。

澎湃新聞:美食文化的傳播有沒有什么規(guī)律可循?
朱振藩:一定是經濟開始帶動的。經濟發(fā)展得好了,商賈云集,各方都來賺錢,也就慢慢帶動美食的傳播。為什么北京飲食業(yè)都是福山幫的天下?福山人開設第一家店賺錢之后,就回去把自己家鄉(xiāng)用的上手的人帶到北京,開始拉幫結派變成“福山幫”。北京所謂的“八大樓”、“八大居”都是福山人的影子。
我看現在一統(tǒng)天下的應該是麻辣火鍋,因為它不論到哪里都可以生存。本來重慶人吃麻辣火鍋是因為濕氣太重,一定要把濕氣去掉,只能麻辣排汗。即使是夏天,男生脫光上衣也照樣吃。這剛好南北皆宜,現在冷氣又發(fā)達,四時皆可。
比如說北方的涮羊肉就不會像四川、重慶的麻辣鍋那么盛行,因為受限于地域和貨源。而麻辣鍋的取材每個地方都有,不一定需要原來的,只是調味料不同而已。所以我覺得真正可以一統(tǒng)中國大江南北的大概就是麻辣鍋了。
澎湃新聞:川菜也全國各地也很受歡迎。
朱振藩:是啊,還有個重要因素,現代人工作壓力大,經常熬夜,身體上就需要一再的刺激,麻辣鍋就應運而生。沒辦法,時勢所趨,也許回歸本然的時候它又不受歡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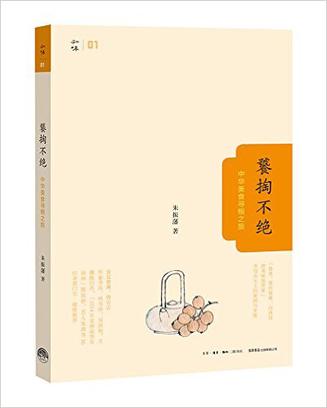
臺灣小吃從南到北只有“雷同”二字
澎湃新聞:您是怎么保持這么好的胃口的?
朱振藩:味蕾很重要。周作人說,五味之中只有辣非必要,我偏偏最愛辣,但我絕不輕碰,要保持我的味蕾的彈性和活化,萬一鈍了,我也就不值錢了。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待臺灣的小吃文化?
朱振藩:從南到北就只有“雷同”兩個字。南味偏甜,北味偏淡,南部好煮,北部是用蒸。講起來是有不同,但實際看過去也沒有什么差別。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從臺灣到大陸的奶茶文化?
朱振藩:其實珍珠奶茶的發(fā)源地在臺中,離我住家隔一條巷子。我念書的時候還沒有奶茶,后來珍珠奶茶將珍珠圓子和奶茶混在一起,是硬湊的。
我覺得每樣東西會起會落,會盛會衰,都是命中注定。興起就莫名其妙興起了,哪一天不再流行了,也就自然消沉了。用這個態(tài)度去看,古今皆然,中外如此。
金庸小說里的菜品與現實有差距
澎湃新聞:“張大千宴”、“紅樓夢宴”的菜單是如何設計的?
朱振藩:做“紅樓夢宴”的人多,“張大千宴”算是我的創(chuàng)舉。張大千宴請張學良和那時的臺灣“總統(tǒng)府資政”張群等人時會手寫菜單。有的菜單流傳出去了,我就收藏了五份,不過不是真跡。
張大千的畫作特別有名,號稱“五百年來一大千”,但他自己認為廚藝更在畫藝之上。他原來的廚師叫做陳健民,后來到東京發(fā)展,開了四川飯店。張大千61歲的時候路過東京,陳健民以六素一葷燒了一道菜,叫“六一絲”,全部都切成細絲,可以湯也可以燴炒。張大千很滿意,以后請別人吃飯開菜單的時候往往都會開“六一絲”。張大千也很喜歡干燒做法,比如干燒明蝦、西瓜盅,這都是他的菜單里面常出現的菜。我就把這些菜集合起來,變成了“張大千宴”。
澎湃新聞:那您有沒有想過根據金庸的武俠小說做一場“金庸宴”。
朱振藩:香港的鏞記做過,我是覺得畢竟是小說,與現實有差距。比如“二十橋明月夜”:一塊大火腿,上面挖二十四個洞,放入豆腐,我覺得這樣做的話應該也不會太好吃。

澎湃新聞:那《紅樓夢》里的菜是不是還比較真實一些?
朱振藩:因為曹雪芹有江寧織造的背景,他小時候也見識過一些,他寫的東西都是有根有據的,而且偏向家常。雖然是大戶人家,可是他們的菜有很多是日常就可以吃到的,比較貼近我們的生活。
澎湃新聞:那您做儒家的菜單是由于什么原因?
朱振藩:我那個時候是臺北市政府的觀光委員,他們正準備把臺北的孔廟和旁邊的保安宮重新賦予生命,活絡觀光,我就出了這個點子。
山東曲阜已經有“孔府宴”了,我想弄一套完全跟它不同的,就把供奉在孔廟里的先圣先賢曾經吃過的菜,比如文天祥跟三杯雞有關,陸秀夫跟貓仔粥有關,朱熹跟莧菜有關,我把這些都搜集起來,組成了一份既可以用于旅游觀光,又有文化背景的菜譜。我是朱子的21世孫,所以有一段時間就會讀讀《明儒學案》、《近思錄》、《宋儒學案》,親近一些儒者,雖然得其皮毛,但也受用不少。
澎湃新聞:那大眾對您的“儒家菜”作何反映?
朱振藩:當時在臺北很轟動,尤其發(fā)布的地方又在孔廟里面,冠蓋云集。
后期弟子以顏值取勝
澎湃新聞:那吃飯的時候會考察弟子嗎?
朱振藩:有時候會考,總不能白吃。而我后期的弟子大部分都是主播和主持人,以顏值取勝,早期的弟子都比較有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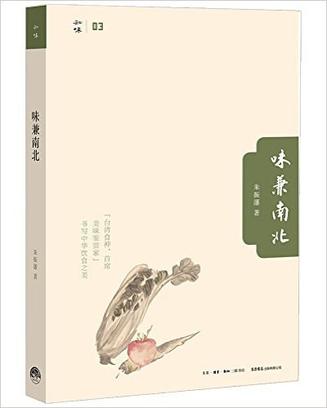
澎湃新聞:跟您學習到怎樣的程度才算出師呢?
朱振藩:我最小的弟子是個很有名的廚師,叫做陳嵐舒,她是“2014年亞洲最佳女廚師”。她本身是燒法國菜的,但也有一些中餐的問題,就私底下就教于我。因為她經常參加很多國際性的廚師交流,人家問到她一些東西她也答不出,就退而就教于我。
澎湃新聞:您的弟子里有悟性很高的嗎?
朱振藩:陳嵐舒就很好,她本身學習能力就很強。她是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yè)的,又到法國從點心開始學起。我的弟子里還有一位可以燒400多道菜,我到現在只嘗過81道。她雖然在臺灣算是真正的名媛,但是她不恥下問,只要吃到滿意的,就會向廚師請教,回去之后還會用自己的慧心巧手加以變化。她叫何麗玲,曾經在杭州和上海開過“兩岸咖啡”。

澎湃新聞:作家李昂拜您為師的時候,您是被她的誠心所打動的。
朱振藩:對。其他的弟子都喊她大師姐。后來她吃了很多日本、意大利和法國的米其林餐廳,是個追星者,但我覺得她還是以價格為取勝,還不是以價值來評斷。
澎湃新聞:您收弟子有什么條件嗎?
朱振藩:至少要見過三次面,觀察之后感覺不錯才行,不然的話就跟丁春秋一樣了。我雖然收弟子,但比較像“邦聯(lián)”,松散沒有組織,如果哪天像“聯(lián)邦”,群體戰(zhàn)力就出來了。我還有個弟子叫曾郁雯,她專門研究日本的飲食和旅游,她們都是各有所本,各有專長。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