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門戶”:傅衣凌學派的治史路徑
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曾在他們的著作中說過:如果說世界上只有一門科學,那就是歷史科學;如果說世界上有兩門科學,那就是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這里表達的意思恰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張宇燕先生所說:歷史科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具體落實到經濟學上看,則恰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吳承明先生所說:經濟史是經濟學之源,經濟學則是經濟史的流。
這其中告訴人們的信息還在于:歷史學正如自然科學中的數學那樣是近代以來其他分支學科的基礎,進入歷史學科的學子盡管似乎已作出了專業的選擇,實際上這是一個包容面極大的選擇,在這個學科里,我們還可以作出更具體、更細微的治史路徑的選擇。套用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傳》中郭靖建議成吉思汗對付金政權的策略就是“既不是攻,也不是不攻;是攻而不攻,不攻而攻”。在這個意義上說:進入歷史專業的學子是幸運的,它將個人稚年期的選擇難題暫時擱置了,因而可以在進入學術之途后,作出更加從容和理性的選擇。中國史、世界史;政治史、法制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環境史、生態史、醫療史等等。
一、治史的基本準入條件
進入一個學科,確實是需要一定的知識儲備的,要進入中外歷史的深邃時空隧道,既往的先師們已經告訴過我們治史的基本準入條件,大體總結為:閱讀文獻的能力,掌握外語的能力,邏輯思維的能力,走進歷史的能力。
閱讀文獻的能力是治史的基本功,也是決定其學術成就高度的標尺。治中國史者,勢必得接觸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史源等學科。古人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就是要在拿到一頁沒有現代標點的文言文后,能夠迅速準確地句讀且闡述出其正確含義的能力。這些方面是要下死功夫的,事實上進入其中也是趣味無窮的。有了閱讀文獻的基本能力后,只要一接觸到原始文獻,我們便能夠發現既往閱讀者的高明和庸俗,便能夠將一段在俗人視為天書的文字中讀到歷史的鮮活和恢弘。
掌握外語的能力決定了治史者的視野寬度。我們要了解別國對該學術問題的研究狀況,需要外語;我們要將自己的學術傳播出去,需要外語;我們要與別國的學者開展合作,同樣需要外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真該特別羨慕那些具有語言天賦的人,他們往往是開展跨文化研究的先天嬌兒。
邏輯思維的能力說到底是清晰地將自己的思想傳達給別人的能力。在寫作上可以用盡量少的文字告訴別人自己的深邃學術思想,在演講時能夠層層推進,暢快淋漓地表達自己的獨到觀點,讓聽眾聽得聚精會神、心領神會、多有共鳴。這一點在當今時代電子閱讀沒有紙張等資源限制狀態下尤其值得推崇的方面。因為我們時常會不自覺地沉溺于長文、長篇大論,最不可容忍的是硬著頭皮看完長篇之后,反復琢磨仍不得要領的狀態。
走進歷史的能力通俗地說就是歷史感,每個人的生活閱歷本身便可以構成自己讀懂歷史、認識社會的現成資源,社會學家費孝通用江蘇吳江開弦弓村的研究、人類學家林耀華用福建古田縣黃田鎮鳳亭村的研究、楊懋春用山東膠州臺頭村的研究揭示了故鄉往往是開展成功學術研究的較佳場域。人類學所倡導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特別注重長期的“參與觀察”(至少6個月),這又何嘗不是尋找到歷史感的最低時間長度啊。我們或許應該鼓勵青年學子在走進歷史現場時能夠更加潛沉一些。社會學更注重當下社會問題的研究,它所倡導的社會調查或許可以短一些。

二、傅衣凌學派治史倡導的知識結構與學術素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前所長林甘泉說:“傅衣凌學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幾個學派之一,學術風格獨特,有成果,有傳人,其弟子是沿著先生的足跡走的。”山東大學王學典在總結傅衣凌學派的學術理路時說:這是一個“系統清晰、特色鮮明的學派,這一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范式’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從經濟史的角度剖析社會,在復雜的歷史網絡中研究二者的互動關系,把個案追索與對宏觀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大勢的把握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善于透過片斷的史料顯示歷史的歸趨,又能從歷史的趨向中看出具體史料的意義。”傅先生“特別注意發掘傳統史學所棄置不顧的史料,以民間文獻包括契約文書、譜牒、志書、賬籍、碑刻等證史,尤重田野調查,以今證古;強調借助史學之外的社會科學理論尤其是社會學的理論與概念,特別注意地域性的細部研究、特定農村經濟社區的研究等等。”傅衣凌先生及其子弟們真可謂踏破了數雙鐵鞋,深入窮鄉僻壤,搜羅的資料往往是別人不屑一顧的破舊物件,卻從其中解讀出了真歷史。
傅衣凌學派認為可以把歷史學做廣義的界定,其彰顯出的知識結構與學術素養可以做如下歸納:
(一)強調多學科知識的融合與運用。
凡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人種學、語言學、精神分析學、生態學、地理學等等學科的知識均可為歷史學所用,凡哲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數理統計、模糊數學等等都可以作為研究研究的方法,既往有學者總結說:“從經濟的角度看社會,又從社會的角度研究經濟”是傅衣凌學派的一個特色,傅衣凌先生入大學時讀的是經濟系,后轉到歷史系,出國留學又學了社會學,平時還特別留心民俗學,對于中國傳統社會中流行的蓄奴習俗深表痛恨,并認為這導致集中了大量社會財富之階層生活的驕奢淫逸、社會下層生活的難以為繼和基本人權的被剝奪,進而衍生出尖銳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導致激烈的反抗斗爭,引起玉石俱焚、社會積累被毀滅的慘劇。
運用多學科知識和方法,傅衣凌先生形成了自己的若干理論性觀點,他說:“長期以來,人們堅信不疑: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也將和西歐一樣,自發地依靠自身的力量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立論是從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引伸而來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馬克思本人的觀點。馬克思晚年在給友人的信中明確表示: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傅先生認識到:中國傳統社會內部產生的官僚專制主義國家政權恰在協調各種不可自我調和的矛盾中顯示出自己產生的價值,傅先生反對將中國和印度、埃及等地區進行類比而得出管理渠道和人工灌溉設施、舉辦公共工程、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的要求是中央集權政府建立的原因的結論,是集權國家出現后由于其地位而具有的功能,而且是其眾多的功能之一,……事實上,在中國傳統社會,很大一部分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是在鄉族社會中進行的,不需要國家權力的干預。“國家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實際上也就是‘公’和‘私’兩大系統互相沖突又互相利用的互動過程。”地方割據和農民戰爭是沖突的基本表現形態,但是這些往往是短暫的、臨時性的,地方割據勢力既可以是興風作浪的始作俑者,或者利用農民起義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可以出面鎮壓農民的起義,保障自我的利益不受損害。大一統的國家政權往往可以利用這些地方勢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進而收編他們,使他們臣服于大一統的權威之下。
漢代以后,財產所有形態和財產法權觀念多元化現象明顯,國有經濟、鄉族共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長期并存,難做剖斷,司法權的多元性也由此衍生,族規、鄉約、鄉例都有推行的空間。思想文化領域的多元性同樣存在。因此,雖然社會上出現許多類似歐洲近代化時期的現象,但往往并不具有導向新的社會形態的征兆。反而是新舊因素和平共處,相安無事,社會結構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化解各種沖擊的能力,商人盡管成邦,成了一個顯著的階層,但他們在政權敲詐下有反抗意識,卻又返回去尋求政府給予保護和特權,斗爭性不強。
(二)強調對“總體歷史”的把握。
法國年鑒學派馬克·布洛赫也倡導“總體歷史”,勒·高夫提倡《新史學》,布羅代爾提出長時段的分析方法,這些在傅衣凌先生那里,早也是躬行的實踐,因此可以說在當時國際交流尚很稀少的時代,傅先生在中國早已走出了類似于法國年鑒學派的路數,只是沒有確定這樣的命名而已。傅先生能從國家機器、社會經濟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在《秦漢的豪族》一文中認為:豪族來源于六國的故家遺族,人數不少,雖然失去了政權,但他們仍“不愿與齊民齒”,秦始皇反復有徙豪之舉,卻并不能徹底,而且隨著世代的繁衍,豪族還可能壯大起來,它們以“保族”、“收族”為圭臬,延續著自己的文化精神。他們將養客作為自己的輔弼,蓄奴作為維持養尊處優的前提,生活奢靡,行為橫肆,往往構成為貧民的剝削者和政權的直接威脅力量,當統治者試圖壓服他們的時候,一些豪強便可能潛伏下來,衍而成為魏晉時期的門閥。
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是隸農制,其根源在于高利貸資本、商人資本與土地資本實現了三位一體,中國專制主義政權以官僚、軍隊實施對地主、商人、農民(隸農)、奴隸的統治,等級界限森嚴,盡管有科舉制度作為激發官僚隊伍的更新,但社會的保守色彩明顯。奴隸來源有俘虜、罪人、賞賜、買賣、貢獻與投靠、犯罪、戰爭、家生等多種形式,他們的法律身份和社會地位都極低,作為他們的主子則往往占田無限,作威作福。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時常表現出的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
因為佃農制的發達和農民的相對離土自由,于是就在農村中出現了三種勞動力形態,即傭工、佃戶和僮奴。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并存,使得中國社會出現了進一步、退二步的情形。本來農民具有相對的離土自由,從農村擠出來的過剩勞動力,可成為傭工,為工業發展注力。但事實是那些可能走向新境界的經營地主和富農選擇了鄉居和離開生產的道路,他們以放高利貸為生,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地主階層的寄生化更趨顯著。他們不斷加大著對佃戶的榨取,將苛刻收取的地租囤積居奇,再度施加對佃戶的剝削,因而導致農民的貧困化,無法實現與城市工商業的有效對接,對地主的依附關系更趨加強。
傅先生分析說:“這廣大的農業人口向全國各地的自由流動,固然在緩和了某一地區的人口壓力和社會矛盾,促進移住地的經濟開發,都發揮了一些作用。不過這大量的農業人口如果過多地向某一地區集中,則必然的會產生降低勞動力的生活水平和技術水平的后果,出現有爭求雇主的現象。城市手工業的雇工制無法獲得健全的發展,主佃關系往往充滿了野蠻的色彩,有時衍生出奴隸式的畸形關系。”在江南地區,地主使用僮奴現象普遍。從政治層面看,那些勢單力薄的普通之家往往也主動尋求具有政治特權的身份性地主的庇護,投靠到其門下成為奴仆、佃戶,胡如雷先生稱這種現象為“第二度農奴化”,在傅先生看來,這是新舊因素糾合而出現的社會關系的畸形兒,地主將高額榨取的地租用于娶妻納妾,繁衍眾多子嗣,結果往往是財產的分散與浪費,依然無法引向生產領域。被榨干的佃農在獨立和自由都被地主控制的背景下,很難求得發展的空間,甚至妻女都可以被主子任意欺凌,有的便舉起反抗的大旗。

(三)強調“自下而上”、“上下互視”的治史路徑。
傅衣凌先生深愛弗雷澤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 這樣的民俗學著作,也喜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這樣的新史學論著,將梁啟超倡導的運用家譜、契約等民間文獻研究歷史方法化為實際的行動,且一發而不可收,這構成了傅衣凌學派的一個顯著特色。傅先生強調民間傳說、路途傳聞、兒提故事都可成為歷史研究的資料,傅先生養成了處處留心,事事關心的治學習慣,他勤于訪書、讀書,亦勤于訪人、切磋。
傅先生認識到:在收集史料的同時,必須擴大眼界,廣泛地利用有關輔助科學知識,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契約文書)證史。他從謝肇淛《五雜俎》中尋覓到新安商人、山右商人的論題,與日本學者藤井宏交談后引起共鳴,其后相互交流,共同推進該論題研究的深化。他從閱讀馮夢龍《醒世恒言》中發現蘇州洞庭東、西山商人是個特別有意思的題目,與南京大學呂作燮交談后更激發了尋找湖南各地活躍著的洞庭商人的情形。傅先生對民俗的關注是個天然的興趣,他在《桃符考》中說:在古人心目中,將桃視作驅逐魔鬼、拔除不祥的神秘之物,就像英國人視山柃為有神秘能力的東西,用它鞭打牛馬,能讓牛馬肥壯,但倘若用金雀杖或柳枝鞭打小孩,則小孩不易長大,因金雀枝不會長成大樹,柳枝亦較早凋零。傅先生曾深受民俗學家弗雷澤《金枝》的影響,所以對民俗的認識也特別地專業、獨到。他指出:以桃驅鬼,曾走過以桃做成人形,即桃人驅鬼的階段,神荼郁壘被定義為驅鬼神人,配合桃人共同執行驅鬼抗魔的職能。近代的春聯與古代的桃符雖然有關聯,卻失掉了原始民俗的本來意義。傅先生在《福建畬姓考》中,考證福建陳氏、黃氏、李氏、吳氏、謝氏、劉氏、邱氏、羅氏、晏氏等都是畬族,其他像許氏、張氏、余氏、袁氏、聶氏、辜氏、章氏、何氏亦有畬族混雜其間。因為“畬與漢人往來頻繁,多沾染華風,改用漢姓,亦喜自托于中原仕族之列。”這里實際上指出了福建人口構成的歷史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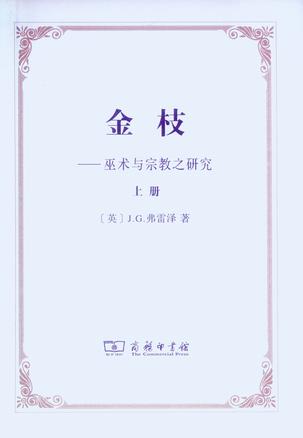
通過相互關照與相互比較,更多地與國際范圍內的同行對話,傅先生走到了國際學術前沿。從中國手工業幫會不是單單存在于城市,而是從農村延長到城市去這一事實,傅先生追索出中國工商階級與封建地主間不但不存在相互的矛盾,反而還存在共通性乃至一身而二任。工商業會館既存在于城市,又存在于農村的事實讓傅先生認識到中國城鄉之間的關系也不對立,農村是城市工商行會的原始基地,與農村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譬如在商人會館中又存在著更小的組織形態,被稱做“綱”,細究“綱”的本義,是專營某類商品的商人組織,更早來源于官營的運輸組織的稱謂,但這一稱謂后來有了被泛化的現象。僅在這一點上,與歐洲的經驗便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傅先生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中國海外貿易經營者的出生地不僅是濱海地區,而且多有一般內地的商人,江蘇華亭、江陰、黃姚是海商聚居的一個根據地,浙江的明州、杭州,亦為海外貿易商人所聚集。傅先生判斷:“當時浙海通蕃之風甚盛,浙人通蕃多從寧波、定海出洋,慈溪有積年通蕃柴德美,杭州歇客之家亦均系通蕃的窩主,紹興則多外商的通事。”福州為中外交通之地,“成化間泉州市舶司移設于福州之后,于是通蕃漸多,省城的河口以及瀕海的瑯岐、嘉登諸島之民,無不輟耒不耕,遠航海外,而福清的通蕃喇噠,當嘉靖間曾橫行于海上。至于泉之安平、漳之月港,尤為中國的海外商人的集中之地。”“漳州梅嶺林、田、傅三巨姓,全部三千家,即全靠經商行劫為活。”廣東海商去三佛齊、滿剌加、暹羅等地的也很多。來自內地的商人如徽商也是海外貿易的重要一支,明嘉靖年間,他們并與福建、廣東商人同任管理外商的一切事宜,后來,徽商在廣州的十三行、寧波的洋行都有活動軌跡。其他像晉商私舶日本,江西商人如亞劉成為滿剌加通事,饒州人朱輔任職于琉球國多年,佛郎機貢使中的火者亞三都是海外貿易的活躍分子。說到福建海外貿易商人,也有不少來自龍巖、汀州。傅先生認為:這么多人在趨利的吸引下,“相率呼群喚侶,麇集而至”,不利于海商資本的集中,而使原始資本的蓄積受到妨礙。當時經營大宗商品絲、糖的有浙直絲客、徽商、閩商、粵商,他們不僅在國際市場競爭,同時也在國內市場相互爭奪。傅先生從徐光啟的《海防迂說》中發現:“若呂宋其大都會也,而我閩浙直商人,乃皆走呂宋諸國,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這樣產生的結果是商人間自我的惡性競爭,不利于大商人的形成。江淮海商對推動中國南北物資交流有著重要意義,但是江淮海商因為遭到封建勢力的嫉妒而遭遇摧殘,海商們成為當時社會結構矛盾、沖突的犧牲品。這些新解釋的形成絕非那些停留在閱讀狹小范圍資料者能夠達到的。傅先生感慨:尋找史料的艱辛固然考驗著治史者的意志,但從史料中探尋出前人所未發的新知識、新認識,那種歡樂卻又是一般人很難體驗到的。
三、傅衣凌學派的傳承與創新
20世紀80年代末,楊國楨先生轉向自己的新領域——海洋史這一學術處女地,先做規范概念體系的工作,繼而主編出版《海洋與中國叢書》(8冊)、《海洋中國與世界叢書》(12冊)、《中國海洋文明專題研究叢書》(10冊)和《中國海洋文明史》,愈加清晰地呈現出中國傳統文明中陸地文明與海洋文明共存的局面,這其中彰顯的“天下大同”觀與西方近代殖民性、掠奪式的不可持續的海洋文明并不一樣,且長期維持著環中國海直至印度洋到非洲東岸的海域的和平貿易局面。楊國楨注重摒棄“陸地思維”,站在海里看中國,呈現出的是與傳統史觀截然不同的“藍色思維”。

李伯重教授的《江南早期工業化:1550-18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02)及其最新力作《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三聯書店2017),在學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李伯重在生產力經濟史研究中所體現的方法論為“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開拓了一條道路”,他長期身處歐美,與國際同行及時對話,且能將西方學界最新社會科學理論方法、概念和成果引進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他提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江南道路”的理論模式,“大約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終于清道光末年”,顯示出重工業畸輕而輕工業畸重的“超輕結構”特征,并提出了與黃宗智停滯論相反的“發展論”,這是對傅衣凌學派的重要拓展。

陳支平教授關于清代賦役制度史的研究、福建家族文化的研究以及東南中國的研究都成果豐碩。他在研究清代賦役制度時,比較側重探討賦役制度與民間社會的關系,注重分析制度表達與制度實踐之間的距離,因為他利用的實錄、檔案和方志、族譜已經有效地實現了二者間的對話(《清初賦役制度演變新探》,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2004年由黃山書社出版的《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制度史研究》對戶籍、易知由單、自封投柜和民間負擔等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深化研究。另撰有《近500年福建家族社會與文化》(上海三聯書店1991)、《福建族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陳支平堅持“自下而上”的學術理路,在臺灣史、臺灣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上有所推進,《民間文書與明清東南族商研究》(中華書局2009)顯示出研究的進一步細致化。

鄭振滿教授聚焦于家族史研究,注重“私”的系統的研究和宗教碑銘的整理與利用,深化了傅衣凌先生的“鄉族論”。《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三聯書店2009)對鄉族組織與共有經濟、家庭結構與宗族組織、民間信仰與儀式傳統、地方行政與社會轉型等都有較為深邃的思索,是傅衣凌先生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結構”的進一步具體化。其《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于1992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2001年出版了英文版,其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近年來,鄭振滿更加專注于田野調查,且力求使民間歷史文獻學科化,其用力方向也呈現出由社會史向文化史的縱深發展,這顯示出對傅衣凌學派的重要拓展。
陳春聲教授博士論文《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十八世紀廣東米價分析》于1992年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體現出對傅衣凌學派和中山大學梁方仲、湯明檖一脈的兼融。陳春聲教授重視“自下而上”的視角,注重田野調查和民間資料包括口頭資料和書信等的利用與收集,對民間信仰、海洋社會的習俗及其由來、海盜活動、田野調查方法的運用及其效果等都作了若干深具理論性和借鑒意義的思考,強調地域脈絡在重構歷史信仰與儀式中表達的世界觀所占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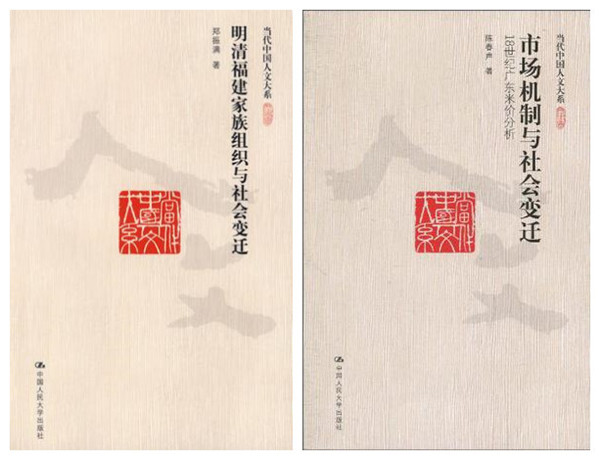
王日根教授較關注民間社會對基層管理和控制的作用,即“民間社會秩序”的建立。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機構固然有許多是官方建立的,卻不乏民間社會的自我管理組織,像家族、鄉族、會社、會館等,這些組織都不僅從形式上,而且從思想深處,不僅對固定居住者,而且也對流動人群實施著有效的社會管理,在歷史演進中,官方努力和民間努力經常能相生相助,共同臻于一個更美好的境界,有些官方的政策或制度就是民間實踐成功經驗的轉化形式,在官方秩序出現紕漏的時候,民間社會有時還能運轉正常。在中國政治文明遺產中有一種“官民相得”的傳統值得我們加以繼承,這可以算是對傅衣凌先生“私”的系統的一點延伸吧。(《明清民間社會的秩序》岳麓書社2003;《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近年來王日根教授追隨博士階段導師楊國楨轉向海洋史,對海疆政策及其影響進行研究和總結,200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明清海疆政策與中國社會發展》,2015年出版《海潤華夏:中國經濟發展的海洋文化動力》,2016年出版《明清河海盜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2017年將出版《耕海耘波:明清官民走向海洋歷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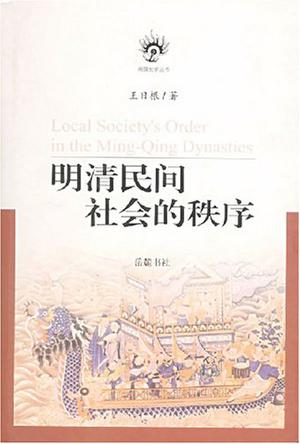
其他像林仁川教授、劉秀生教授、陳學文教授、唐文基教授、蔣兆成教授、郭潤濤教授等均屬于傅衣凌學派的外圍力量。如今,傅衣凌學派已經衍生出更多的傳人,像鈔曉鴻、劉永華、張侃、林楓等教授均顯示出較強的發展勢頭。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傅衣凌學派勢必將代有傳人,薪火綿延。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