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華師大平均每天讀一本書的閱讀達人是如何練成的
對于許多人而言,世界讀書日只不過是一個紀念讀書的節日。然而,讀書日不僅僅應該成為一種具有儀式感的紀念方式,更應該像它宣稱的那樣:“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無論你是年老還是年輕,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裕,無論你是患病還是健康,都能享受閱讀的樂趣”。
2017年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華東師范大學發布了學生閱讀調查報告。除人均借閱圖書、人均閱讀時間、最受歡迎書籍等基本數據外,報告還包括了年度借閱達人、年度館霸(一年中到館天數最多的同學)、最愛讀書的院系等數據。其中,來自哲學系的一位同學以年度借閱458冊圖書的佳績榮登借閱達人的榜首。筆者隨機采訪了四位不同學科背景的借閱達人,他們以四種閱讀風格,四種讀書方式,展示了各自在書海中遨游的精神世界。
閱讀讓我在現實中找到了靈魂的出口
陳子凡是理工學院數學系本科二年級學生,年度借閱圖書291冊,位列本科生年度借閱榜第一位。雖然每天忙于高精度的數學計算和邏輯構建,她卻從沒間斷忙里偷閑地閱讀一些人文社科類書籍。陳子凡說真正喜歡閱讀是因為隨著年齡增長,感覺自己看不透的事情太多,看得透的事情也太多,在20歲這個年紀很難在現實中找到一個靈魂的出口,而讀書讓她可以從別人的故事中去看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去了解他人對待這個世界的態度,從而使自己生活的更通透。

陳子凡坦言最喜歡的作家是維克多·雨果,因為雨果的創作視角很高很廣,幾乎把法國的歷史、革命、戰爭、哲學、法律、宗教信仰等內容全都融匯進了自己的作品中,如同一個濃縮的圖書館一般。最近一段時間,陳子凡迷上了人物傳記,她覺得從一本書中可以縱覽一個人的一生,很多時候人們對他們的偏見和誤解會在傳記中得到修正,因為現實是最好的教科書。
澎湃新聞:你在圖書館借閱的書更多用于學術研究還是個人愛好或其他?
陳子凡:差不多一半一半的樣子。
澎湃新聞:你覺得應該如何從浩瀚如海的書目中選出高質量的書籍?
陳子凡:其實找到一本適合自己的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一般采用的方法是去豆瓣知乎之類的網站搜索相關話題看一下他人的評價與推薦,除此之外,我會比較看重作者,一位作者的文風通常不會有太大改變,有一本適合我的,那么其他作品能夠被我接受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
澎湃新聞:在你的日常閱讀中有幾成書是精讀?幾成是泛讀?精讀和泛讀都有哪些技巧?
陳子凡:專業書籍基本上都需要精讀,而個人愛好類的書籍則視情況而定。有些書開始讀之后,發現雖然能夠帶給我一定的精神愉悅,但是精讀并沒有太大意義,我就會選擇泛讀。技巧而言,精讀時我會用筆做一些標注,然后反復看標注的部分。泛讀時也會將發現的精彩部分重復閱讀。但是由于是泛讀,可能很多書中的價值被我草草略過了。
澎湃新聞:有人說讀書是一個人的事,有人說讀書要和別人交流,如此才能產生思想的碰撞,你怎么看?
陳子凡:讀書這個具體的行為,我認為是一個人的事。但是與他人進行與書有關的交流也是很有意義的。很多時候我們看書由于自身的局限會有一定的理解上的偏差,這時候如果與他人交流,我們也許會有不一樣的視野。
讀書讓我們知道世界的多元性和一元性
劉彥博是信息科學技術學院通信工程系碩士二年級學生,年度借閱圖書370冊,位列碩士生年度借閱榜第二位。在接受筆者的訪談時,他剛剛結束了一天的實驗室生活。雖然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理工科學生,劉彥博卻喜歡“舞文弄墨”,他從六歲開始學習國畫,一直到現在也沒放棄。在這個過程中,除了不斷的練習之外,劉彥博還比較注重欣賞和學習古人的畫本,因為在他看來,閱讀不僅僅是讀文本,畫本同樣讓人受用。
劉彥博覺得閱讀是一個可以跨越時空與作者交流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使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更加多元。而哲學家們構建的哲學體系是每一個理工科人應該學習的,因為所有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上升到哲學層面,哲學有助于整個未來技術領域的構想。
澎湃新聞:你覺得應該如何從浩瀚如海的書目中選出高質量的書籍?
劉彥博:首先是詢問自己的導師,如果導師推薦的圖書一定要好好尋找查閱。然后在英文網站和論壇查找,比如亞馬遜上的圖書榜和豆瓣讀書。然后在Spring的出版社查詢影響指數,對應的圖書在圖書館查詢。
澎湃新聞:在你的日常閱讀中有幾成書是精讀?幾成是泛讀?精讀和泛讀都有哪些技巧?
劉彥博:專業領域的圖書很多都是精讀。比如SCI文獻和EI文獻。自己喜歡的圖書比如《中國哲學史》要精讀。交叉學科的文獻和圖書很多是泛讀。精讀和泛讀的技巧方面,我們可以將每本書的內容提要、前言、章節目錄等很快地從頭到尾看一遍,這樣就能大致了解每本書的梗概、特點及應用范圍等。對于一本讀物來說,可以幾段幾段地粗讀,也可以幾頁幾頁地翻閱。
澎湃新聞:有不少人抱怨,讀過的書很快就忘記了,您覺得在閱讀過程中注意哪些方面可以改善這種情況?
劉彥博:很多經典的圖書或者基礎性的圖書,要讀十幾遍。古人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還有一種捷徑就是很多在相同領域有著同樣愛好的同學,在一起組成讀書小組,每個同學選擇一本書,然后在1周或者2周后,大家用一天詳細的闡述自己所讀圖書的感受,這樣得到的會更多。小組人數不宜過多,3-5人比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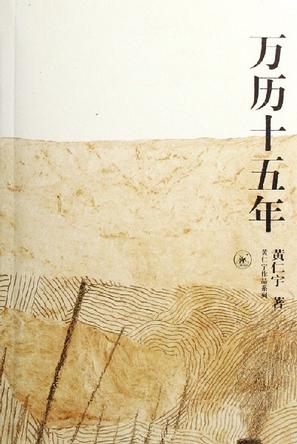
澎湃新聞:您喜歡閱讀哪種類型的書籍?這類書籍給您帶來了哪些改變?
劉彥博:科技類的圖書,我是一定要讀的,因為這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自己選擇的職業和專業一定要為自己負責。要學會喜歡它,欣賞它。并慢慢養成一種職業習慣。歷史的圖書,比如歷史評述類的,比如《漢武大帝》、《萬歷十五年》、《康熙大帝》、《德川家康》,因為讀史可以明志。文學和哲學類的圖書,我喜歡讀《群書治要》、《道德經》、《說文解字》、《南懷瑾全集》,這類書讀了100遍也不覺得多,越讀越有滋味。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樣。
澎湃新聞:您最喜歡哪位作者?他的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劉彥博:我很喜歡馮友蘭先生和南懷瑾先生的圖書。他們構建了一個哲學世界。哲學世界是理工科人應該具備的,這樣有助于我們邏輯思維的建立和對整個未來技術領域的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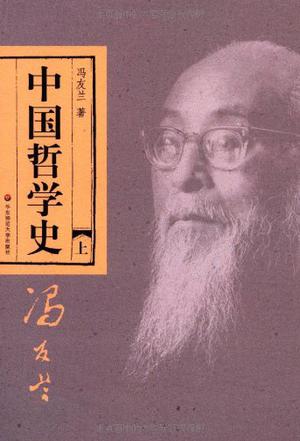
澎湃新聞:您喜歡通過紙質媒介還是電子媒介閱讀書籍?它帶給您哪些不一樣的體驗?
劉彥博:我更喜歡紙質圖書,這種圖書有一種特殊的韻味。我也很喜歡寫一些小紙條夾在圖書里面,把當時讀書的感受寫出來。然后過了一段時間翻出來,一下子當時的感受就會再次浮現,很多時候自己都會被自己感動。哪怕那個時候的我幼稚,都是最真最純潔的自我展現。電子圖書攜帶比較方便,我自己有kindle, 但是我更喜歡紙質翻閱的感覺。
澎湃新聞:閱讀給您帶來的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劉彥博:閱讀可以讓人睿智,看事物的角度更加多元。我們在閱讀的同時其實是和讀者的交流過程。也正是這個過程我們能夠穿越時間的跨度,交流溝通的方式。讀書的過程,讓我們知道世界的多元性和一元性。世界是一元的但是它同時又是多元的,非常的微妙。待人接物的時候,自己更能夠為他人思考。
閱讀可以抵抗虛無主義和物質主義
周亦張是對外漢語學院文藝學系碩士一年級學生,本科期間借閱圖書822冊。如今的周亦張除了完成緊張的課程外,還擔任研究生會文體部部長,擔任過學院大型中外服飾秀活動的導演。他覺得,之所以能勝任現在的工作,和平時的閱讀積累是分不開的。周亦張的閱讀興趣很廣泛,從理論方面的福柯、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到文學方面的特拉克爾、波德萊爾、荷爾德林,他均有涉獵。
從理論方面來說,吸引他的是作家思考問題的方式,理論語言的精確性和新穎性,理論體系的精致性和復雜性。他覺得這不僅有助于自身知識體系的完善,更提升了自己的審美品位,抵抗了虛無主義和物質主義。
周亦張最喜歡的一本書是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因為這本書能夠很好地促進我們理解自身,理解歷史性,啟示我們應該用一個什么樣的態度對待藝術作品、科學等。并且,其理論的解釋力幾乎能涵蓋整個人文科學領域。

澎湃新聞:你覺得應該如何從浩瀚如海的書目中選出高質量的書籍?
周亦張:首先,我覺得對于我的專業領域來說,也即人文社科類,高質量的書籍的書籍一般都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出版社里,比如商務印書館、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華書局、譯林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三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等。我借閱的大部分書籍都是這些出版社出版的。同時,一般這些出版社中的經典都會有很多書系,在書的末尾很容易找到這套書系的其他經典,依靠著高水平編輯的選擇,這樣就能夠了解到很多相關領域的其他經典。第二,每一本經典中,豐富的引用文獻中也有非常多的高質量書籍。第三,平時和老師、同學的交流也能夠獲得很多高質量書籍的信息。第四,平時在亞馬遜上每選一本書的時候都會有相關類型的書籍推薦,里面也會鏈接到很多高質量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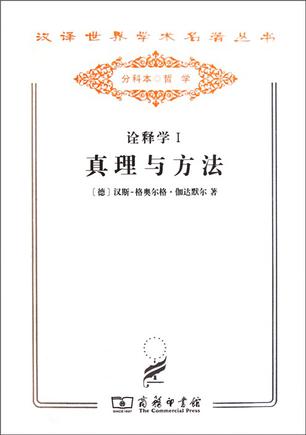
澎湃新聞:在你的日常閱讀中有幾成書是精讀?幾成是泛讀?精讀和泛讀都有哪些技巧?
周亦張:就我個人來說,泛讀和精讀取決于我對這個領域的知識結構的熟悉性和這本書本身的理論難度或經典價值,我很難給出一個比例來。就我現在學習任務緊的時間段來說,我借的書大部分都屬于經典著作了,所以一般都是精讀。假設到了寒暑假,時間比較空的時候,我如果讀一些通俗小說或是其他學科的入門性讀物,一般都會采用泛讀。就我個人來說,精讀的習慣一般是劃線、做摘錄、偶爾會在書上做筆記。讀完以后,我也經常會抽空和同學聊一聊近期讀過的書,談談自己的見解。泛讀就比較懶了,基本就看過算過。有時候如果興趣比較大的話,會根據目錄在心中回顧一下這本書的整個脈絡,或者把這本書的主要觀點在筆記本上整理一下。

澎湃新聞:有不少人抱怨,讀過的書很快就忘記了,你覺得在閱讀過程中注意哪些方面可以改善這種情況?比如做讀書筆記。
周亦張:這也是困擾我的問題,因為我自己記憶力也比較差,很多書看過很快也忘了。我個人覺得可能比較有效的辦法是:第一,定期重讀,邊讀邊在心中整理一下這本書的主要觀點。第二,抓住一切機會,比如閑聊、讀書會、課堂等等,向同學、老師分享自己對這本書的評價。第三,在論文或者平時的寫作中,自覺地聯系、應用、以批判的眼光反思這些書籍中的觀點。簡言之,就是復習、應用、反思。
澎湃新聞:你喜歡通過紙質媒介還是電子媒介閱讀書籍?它帶給你哪些不一樣的體驗?
周亦張:我喜歡紙質,因為電子媒介太傷眼了,無論是電腦和手機。從護眼的角度,Kindle不錯,我身邊有很多同學買了kindle,但我一直沒買,因為我覺得翻頁不太方便,另外,在作為論文引用的時候無法使用kindle上的頁碼。
讀書多了很難找到自己最喜歡的作家
馬俊是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哲學系博士三年級學生,年度借閱圖書243冊,位列博士生年度借閱榜第二位。馬俊從初中開始就是個不折不扣的金庸迷,高考前夕,他還在沒日沒夜的讀金庸。直到父親把他從鄰居家借來的一本《笑傲江湖》撕掉之后,他的熱情才有所收斂。
由于學業的原因,如今的馬俊漸漸把一些愛好轉變成了事業,在圖書館借閱的相關圖書也都轉變成了研究。他覺得在讀書的時候很常見的一個現象就是容易遺忘,能記住的大多與自己所考慮問題相關。因為人的思維總是把自己關心的東西整合入記憶中,而把那些不關心的東西遺忘,這種記憶也可以說是理解。
當被問起如今是否還喜歡金庸的時候,馬俊說:“現在也不確定自己是否還喜歡讀他。讀得越多,越難說自己喜歡哪位作家。喜歡是一種感性的認知,讀書多了理性就多起來,理性一多就吹毛求疵,很難找到自己喜歡的作家。”

如果說極力推薦的書,馬俊選擇柏拉圖的《斐多》,因為這本書所體現出的古希臘人對于人生的認真態度值得每一個人學習。
澎湃新聞:你在圖書館借閱的書更多用于學術研究還是個人愛好或其他?
馬俊:現在借書更多地是用于研究吧,不過曾經也借閱很多與愛好相關的書。一些愛好轉變成了事業,所以借閱相關圖書也轉變成了研究;一些愛好因為研究也無暇顧及,所以相關的書借得也少了。
澎湃新聞:在你的日常閱讀中有幾成書是精讀?幾成是泛讀?精讀和泛讀都有哪些技巧?
馬俊:因為我是做哲學的,一般讀書不可能泛讀,否則就沒法形成連貫的理解。不過寫論文時會泛讀,泛讀是為了查閱一些原始文獻和二手資料。精讀肯定是遠少于泛讀的。
澎湃新聞:你喜歡通過紙質媒介還是電子媒介閱讀書籍?它帶給你哪些不一樣的體驗?
馬俊:我更多地讀紙書,電子書讀得很多的經歷也有。我覺得電子書更適合讀小說,如果讀一些學術著作,不大方便前后翻檢。電子書也有優點,可以檢索,我覺得這點可能已經對我們的研究產生了影響,因為以前的人要找這本書這個概念出現在哪里,要花大功夫,現在這個工作是最簡單的。
澎湃新聞:有人說讀書是一個人的事,有人說讀書要和別人交流,如此才能產生思想的碰撞,你怎么看?
馬俊:嗯,確實蠻重要的,不過交流首先是要有差不多的語境,有相近的背景。因為人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別人可以告訴自己一些沒有涉獵過的東西。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