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照片的傳播(上) | 約翰·塔格

? Berenice Abbott
約翰·塔格代表了美國攝影批評的新聲音,他與普遍的狹隘論調(diào)的區(qū)別在于,他熟悉歐洲馬克思主義和后結(jié)構(gòu)主義論爭中的主要人物的思想。
《表征的重負(fù):論攝影與歷史》是他出版的一部較有影響的攝影理論文集,本書曾被一些專家列為攝影領(lǐng)域的基礎(chǔ)讀物,于2018年由拜德雅引進出版。
本次推送書中《照片的傳播》一文,此文曾被維克多·伯金選入他的攝影理論文集《思考攝影》。由于文章較長,我們分兩次推送(注釋從略),感謝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與拜德雅授權(quá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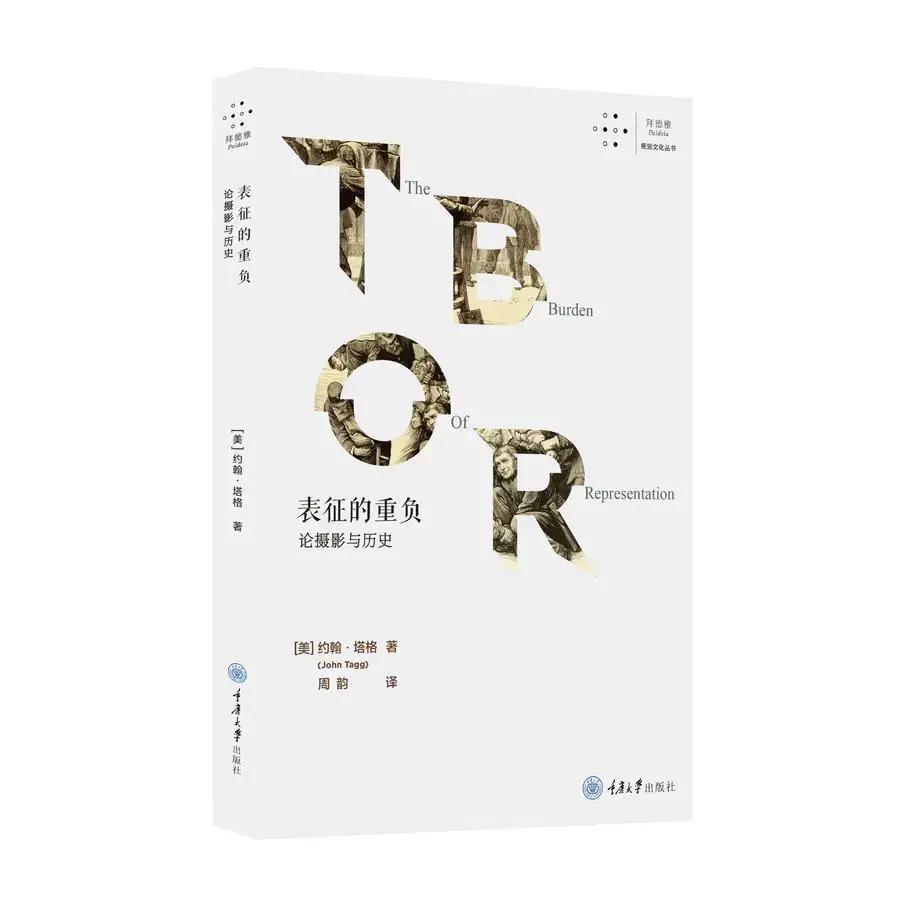
書名 | 《表征的重負(fù):論攝影與歷史》
作者 | 約翰·塔格
譯者 | 周韻
出版 | 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拜德雅
掃碼直接購買
照片的傳播:新政改革和紀(jì)實修辭(上)
文 | 約翰·塔格
譯 | 周韻
1
1951年10月6日,貝倫妮絲·艾博特參加了在科羅拉多州埃斯潘學(xué)院召開的攝影研討會。她在會上提出了如下觀點:攝影和寫作有著強烈的相近性,而這在美國屬于“卓越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光輝傳統(tǒng)。”在論證過程中,她對聽眾們說:“杰克·倫敦在他富有感染力的小說《馬丁·伊頓》中,不只是為現(xiàn)實主義,而且為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慷慨陳詞,里面充滿人類愿望和信念,生活的本來面目,現(xiàn)實世界或者說現(xiàn)實狀況下的真實人物。”艾博特問道:“這不正是攝影所要處理的敏銳的、現(xiàn)實主義的、影像—生成的鏡頭嗎?”隨后,仿佛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她總結(jié)道:“攝影不能無視這一揭示和贊美現(xiàn)實的偉大挑戰(zhàn)。”
作為曼·雷曾經(jīng)的學(xué)生兼助理,艾博特把“無產(chǎn)階級的”和“革命的”小說作者拿來比照的做法令人吃驚。她在這個講座中提到其他作家時情況相同,如共產(chǎn)主義作家西奧多·德萊塞、“煙灰缸派”畫家約翰 ·斯洛恩,盡管后者的作品《理發(fā)師之窗》(1907)預(yù)示了三十年后艾博特拍攝的商店門面照片。顯然,這很重要。艾博特有意在美國傳統(tǒng)內(nèi)定位自己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她還把這個傳統(tǒng)確立為現(xiàn)實主義的。
當(dāng)然,我們必須謹(jǐn)慎確定貝倫妮絲·艾博特所謂的“現(xiàn)實主義”究竟是何意。這不只是題材的問題。無疑,她認(rèn)為現(xiàn)實主義——或者“紀(jì)實價值”——是內(nèi)在于攝影過程的,呈現(xiàn)在每一張“好照片”里,而影像沒有因為夸張的技術(shù)支配而歪曲變形。然而,艾博特在提到杰克 ·倫敦時,也引入了傾向文學(xué)的主題:現(xiàn)實主義聚焦于“真實人物”,“充滿”“愿望和信念”,而這些愿望和信念既屬于人物,也屬于作者本人。再者,這似乎引入了艾博特作品中不那么顯著的一個主題。她認(rèn)為,攝影師的客觀狀態(tài),“不是機器的客觀性能(objectivity),而是明智的人類的客觀性質(zhì)(objectiveness ),其核心帶有個人選擇之謎”。在別處寫到紐約的紀(jì)實攝影時,她敦促道:
必須深思熟慮地從事這項工作,以便藝術(shù)家在敏感和細(xì)膩的攝影感光乳劑中真正記錄下城市的靈魂……用足夠的時間生產(chǎn)表達(dá)效果,其中動人的細(xì)節(jié)必須和設(shè)計的平衡、主題的意義相一致。
這不是杰克·倫敦的粗獷風(fēng)格和廣闊視野,而是表達(dá)了一種現(xiàn)實主義觀念,與艾博特對“個人表達(dá)”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的強調(diào)一致。這也引入了如下觀念:現(xiàn)實主義遠(yuǎn)不是對先前存在的事實的中立呈現(xiàn),它也許包含某些重要的形式策略。誠如艾博特所見,“(對于攝影師來說)第二個挑戰(zhàn)是把秩序強加于所見之物,提供視覺語境和知識框架——對于我來說,這就是攝影藝術(shù)。”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她所謂的攝影的“審美因素”,與她的紀(jì)實或者現(xiàn)實主義目的并不矛盾。這足以讓我們相信艾博特的“現(xiàn)實主義”的“內(nèi)在”特征的復(fù)雜性。我們必須和往常一樣,看到現(xiàn)實主義在意義層面上被界定為復(fù)雜構(gòu)建過程的結(jié)果。僅僅將表征與其實現(xiàn)之前的“現(xiàn)實”作比較,我們無法準(zhǔn)確判定表征的現(xiàn)實主義特征。現(xiàn)實主義表征的現(xiàn)實不是以任何直接或者簡單的方式,與表征“之前”呈現(xiàn)給我們的東西構(gòu)成一致。相反,這是一個復(fù)雜過程的產(chǎn)物,而這個過程涉及對確定的表征手段積極的、有選擇的利用。麥克斯·拉斐爾有力地寫道:
語言甚至違反我們的意愿,逼迫我們在完成的藝術(shù)品和它的自然模型之間進行比較,從而迫使我們偏離以下基本事實:只有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生成精神和開始的既定情境之間的辯證互動,才能產(chǎn)生藝術(shù)品。因此,我們必須嚴(yán)格區(qū)分既定情境(自然)、有條不紊的過程(思想)、總體的布局(藝術(shù)品)。既定情境本身是高度復(fù)雜的。因為除了構(gòu)成自然的一部分,它還包含個體的心理體驗以及社會歷史條件:自然、歷史、個體的不一致、不和諧、相互矛盾,加劇了它們之間的差異。藝術(shù)家要把握這一矛盾,剝離其事實特征,將其變成一個問題——一項任務(wù),即構(gòu)建三個因素之間新的相關(guān)性,把它們?nèi)诤蠟樾碌慕y(tǒng)一性,包含新的內(nèi)在必要形式。由此,純粹的存在變成一種過程,而這個過程的結(jié)果是另一種存在,一種特殊的存在,基于各種矛盾因素所構(gòu)成的新的統(tǒng)一性、為人所感知且表現(xiàn)為物質(zhì)的存在。對于藝術(shù)品的觀看者,這種人造的卻又是“自主的”(自足的)現(xiàn)實是不難理解的。當(dāng)他試圖分析其各個組成部分,以獲得使之存在的過程的洞見,注意到完成的藝術(shù)品與其既定模型之間的差異是不夠的。他還必須知道自然、歷史、藝術(shù)家個性等不同信息是如何創(chuàng)造性地合成的,這個問題是如何解決的——藝術(shù)品是如何產(chǎn)生的——必須知道這個創(chuàng)造過程不僅僅是心理偶發(fā)問題,而且為法則所支配。
麥克斯·拉斐爾傾向于認(rèn)為,創(chuàng)造的構(gòu)建過程及其實現(xiàn)的各個展開階段,是歷史決定的表征,其“深層結(jié)構(gòu)”在特殊層面上是永遠(yuǎn)既定的,在認(rèn)識論或者“知識創(chuàng)造理論”中是確定的。這個創(chuàng)造過程及其各個展開階段都反映在同樣“外在于”歷史的批評程序中。然而,拉斐爾正確地揭示了,雖然歷史學(xué)家在特殊影像的特殊歷史語境中,確定其構(gòu)形手段、布局模式、特殊的使用動機,同時重構(gòu)影像得以實現(xiàn)的方法 ,但是他們必須做更多工作。因為重構(gòu)生產(chǎn)的復(fù)雜條件、手段、過程是不夠的。同樣的分析必須用于作品的接受模式。我們必須把觀眾歷史化,或者回到貝倫妮絲·艾博特,以便說得更準(zhǔn)確些,我們也必須注意具體化:對何人并且是在何種條件下,她認(rèn)為她的攝影影像將呈現(xiàn)為“現(xiàn)實主義的”。
在她的文章《改變紐約》中——她是在1936年編撰的國家報告中,代表她擔(dān)任主任的攝影部寫作這篇文章的,為公共事業(yè)振興署的聯(lián)邦藝術(shù)規(guī)劃部的工作提供了有利的說明——貝倫妮絲·艾博特提出,公眾對她的展覽的反應(yīng)證明,存在“對紀(jì)實攝影的真正的通俗需求”:也就是說,這是“在世界上最偉大都市變化的照片中,為未來保存一種精確的和忠實的記錄”的需求。以此為信念,在沒有取得必要的私人贊助的情況下,艾博特愉快地接受了公共事業(yè)振興署提供的政府資助及其帶來的實際社會支持。作為回報,除了添加紐約市博物館以及此類歷史藏館的永久展品,她提出她的紀(jì)實攝影可以被用于許多直接的、長期的公共用途。她的照片在南方各州的展覽館、“紐約市的五大區(qū)無數(shù)社區(qū)中心” 以及歷史博物館展出,同時被分到各種中學(xué)以及威斯康星大學(xué)展出。它們被刊登在紐約市的旅行指南、報紙、政府報告和出版物上,從《生活》《住宅與花園》《城市與鄉(xiāng)村》到社會工作卷宗和宗教期刊。然而,如果看一看她的展覽目錄,我們會發(fā)現(xiàn),除了紐約的朱利安·列維畫廊等私人畫廊的個展外,還有紐約市博物館和相對較新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的展覽。更進一步,我們也許能注意到,她參加的許多展覽并非致力于社會或者環(huán)境問題,而是專注于“藝術(shù)”。我想到了1936年的“美國藝術(shù)的新視野”,或者1939年的“我們時代的藝術(shù)”等展覽。這兩個展覽都是在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展出的。要理解這類展覽的公共意義,我們也許不得不在私人贊助的博物館的總體政策、目的、話語中定位它們,并且在博物館界定和假設(shè)的狀態(tài)內(nèi),理解這些展覽的作用。
一般說來,雖然美國視覺藝術(shù)領(lǐng)域的成就在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展覽之職尚未下放給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但是這個博物館早已開始嘗試在其展覽中定義美國藝術(shù)的品格和傳統(tǒng)。就當(dāng)代作品而言,1930年代的政策傾向于忽視美國抽象藝術(shù),而推崇“現(xiàn)實主義的”具象藝術(shù)。但是,具象藝術(shù)在1950年代初被博物館館長阿爾弗雷德·H. 巴爾稱為“極權(quán)主義的”。這對貝倫妮絲·艾博特的紀(jì)實作品的選擇和接受產(chǎn)生了影響——事實上,甚至在早期,博物館開始把攝影挪用為藝術(shù),因此有了1938年沃克爾·伊萬斯的個展。這一點持續(xù)至今。
對這些體制潮流的詳細(xì)檢視,對艾博特的“現(xiàn)實主義”的有力分析,都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本文的真正目的是探討現(xiàn)實主義的前提條件。但是,我們將要研究的領(lǐng)域正是艾博特提出的問題領(lǐng)域:攝影和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照片構(gòu)建意義的過程和程序;照片的社會功用;照片的生產(chǎn)和消費的體制框架。我試圖在三個標(biāo)題下或者從三個階段處理這些問題:照片的傳播;真理政體;現(xiàn)實主義條件。我試圖詳盡論述第一個問題,而另外兩個題目會簡略些。
2
首先,讓我們來看兩張照片。表面上,它們在歷史、文化、易于辨識的攝影修辭發(fā)展等方面和我們很接近。兩張照片呈現(xiàn)了兩個室內(nèi)畫面、兩群人、兩套家具和裝飾。似乎很自然就把照片里的兩個人看作夫婦、家人;室內(nèi)畫面是家;家具是兩個社群的標(biāo)志。圖32是1941年喬治亞州尤寧角的一對上了年紀(jì)的中產(chǎn)階級夫婦。圖33是1939年德克薩斯州希達(dá)爾戈縣的一對夫婦,他們是農(nóng)場安全管理局政府資助的受惠者。

圖 32 杰克·德拉諾,《喬治亞州尤寧角》,1941年。(國會圖書館照片部)

圖 33 羅素·李,《德克薩斯州希達(dá)爾戈縣》,1939年。(國會圖書館照片部)
照片的含義豐富。因為每個細(xì)節(jié)——肉體的、衣服的、姿勢的、織物的、家具的、裝飾的——完全暴露在表面,得到全面呈現(xiàn)。因為我們要在這些細(xì)節(jié)所構(gòu)成的總體的照片畫面的意義內(nèi)看每個細(xì)節(jié),所以我們把每個物品看作既是單個的,也是它們所構(gòu)成的整體的一部分:一個被稱之為家的表面完整的意識形態(tài)結(jié)構(gòu)。我們既注意到了它們重要的差異,也看到了它們顯著的相似性:個人物品、各種家具以及它們的相互關(guān)系等的異同;它們共同構(gòu)建了兩張照片里的相同概念——家庭(family)和家(home)的方式的異同。我們所經(jīng)歷的是具有意識形態(tài)話語特征的雙重運動。一方面,物品和事件的意識形態(tài)構(gòu)成,促使總體神話規(guī)劃具體化,其方法是將這個規(guī)劃融入這些特殊歷史時刻的現(xiàn)實中。但同時,物品、事件與神話規(guī)劃的交匯,使得同樣的物品和事件去歷史化(dehistoricise),其做法是用自然和普遍的原型取代意識形態(tài)關(guān)系,以遮蔽這一關(guān)系的顯著意識形態(tài)性質(zhì)。神話結(jié)構(gòu)所獲得的具體性,是以物品和事件失去其歷史特殊性為代價的。
有一種觀點認(rèn)為,由于攝影的優(yōu)先地位,即作為其所表征的事件的實在性(actuality)的必然證明,所以把“自然和普遍”嵌入照片是特別有力的做法。攝影似乎宣布:“這確實發(fā)生了。照相機在此。你自己看吧。”然而,如果照片的這種黏合特征,是根據(jù)界定的程度在“內(nèi)在關(guān)系”層面上部分地實施的,那么這也是由某些特權(quán)的意識形態(tài)機器(如科研院所、政府部門、警察局、法院)所生產(chǎn)和復(fù)制的。給予攝影表征以權(quán)威和優(yōu)先性的權(quán)力,并沒有給其他體制機構(gòu),甚至在同樣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也是如此——如業(yè)余攝影或“藝術(shù)攝影”——攝影新聞只掌握了部分的權(quán)力。你可自問,在何種條件下,尼斯湖水怪或者不明飛行物的照片可被接受為它們存在的證據(jù)呢?
只有攝影的這一運作在某些意識形態(tài)機器內(nèi)受到忽視,其特權(quán)地位問題才被轉(zhuǎn)移到所謂攝影的“內(nèi)在性質(zhì)”。因此,即使對事件、方向、角度、布局、深度的選擇,被接受為代表一系列在意識形態(tài)上重要的、確定的復(fù)雜程序鏈,依然會有人堅持認(rèn)為,照片的“黏合特征”根植于理想中存在的準(zhǔn)控制的、非修辭的層面。羅蘭 ·巴特曾經(jīng)設(shè)想了照片的“自然的”、“天真的”或者“伊甸園式的”狀態(tài)。他說:“由于某些技巧、符號取自同一種文化符碼,仿佛一開始(甚至是烏托邦的)就存在強制擺拍的粗陋照片(正面的和清晰的)。”“自然的”這個詞警示我們注意概念的意識形態(tài)維度。看一看這兩張照片,想一想艾奇特、艾博特、伊萬斯拍攝的照片,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類所謂的“粗陋照片(正面的和清晰的)”是可以在攝影結(jié)構(gòu)的歷史類型學(xué)內(nèi)定位的。這是官方文獻(xiàn)記錄中典型的照片格式,也在更為純粹的照片譜系中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直接攝影”——許多批評家和意識形態(tài)家都說,它包含存在(existence )、“存有”(being-ness )、“連續(xù)停滯”(stasis-in-continuum)的“普遍真理”。
讓我們回到意識形態(tài)話語內(nèi)的“雙重運動”問題吧。這個過程最清晰地出現(xiàn)在展覽“人類家庭”的“家庭結(jié)構(gòu)”中,但這意味著,“家庭”和“家”的意識形態(tài)概念,是在兩個迥異的現(xiàn)實背景中進行“證明”和生動描繪的。另一方面,對這些意識形態(tài)概念的接受,促使我們觀看這些“家庭”和“家”時,卷入某種普遍的本質(zhì)的真理,以致這兩組人物和兩個背景有效地脫離歷史,我們不再能夠或者傾向于觀看、質(zhì)疑或者解釋它們的差異。然而,這也有夸大這一狀況的危險。我們必須記住,意識形態(tài)呈現(xiàn)自身并強加于我們意識的是,結(jié)構(gòu)精致、系統(tǒng)連貫的總體性,其表面的一致性遏制了我們的思想,由此生產(chǎn)一種連貫效果。馬舍雷曾經(jīng)寫道:“意識形態(tài)本質(zhì)上是矛盾的,充斥著各種它試圖掩蓋的沖突。為了掩蓋這些矛盾,它構(gòu)建了各種方法。但是,正因為掩蓋矛盾,反而揭示了矛盾。”如果這兩張照片中,兩個房間的明顯差異表明,兩者之間的差異是階級的差異,那么這也同樣清晰地揭示,一個階級是在另一個階級的支配形式內(nèi)被呈現(xiàn)為現(xiàn)實的,而這一支配形式是被構(gòu)建為生活形式的意識形態(tài)形式 ,是統(tǒng)治階級價值觀、信念、思想模式的實現(xiàn)。由于一個階級的差異——偏差——存在于另一個階級的認(rèn)同內(nèi),因此導(dǎo)致了兩個影像的矛盾并置。這是我們觀看和感覺特殊社會歷史語境中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矛盾現(xiàn)實——1939年和1941年的美國中部地區(qū)——但這一矛盾的揭示,不是通過“揭開面具”實現(xiàn)的,而是通過它對自身內(nèi)在矛盾的各種掩蓋策略實現(xiàn)的。瓦爾特·本雅明寫下這些文字時,比這兩對夫婦照相早了十年。他寫道:
無論攝影師多么熟練,無論他多么精心地安排模特擺拍,觀眾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沖動,去尋找偶發(fā)的小火花,此時此地的小火花,現(xiàn)實和畫面人物構(gòu)成緊張的小火花。要發(fā)現(xiàn)那個不易察覺的燃點,在久遠(yuǎn)時刻的直接性中,未來如此令人信服地嵌入自身,以至于我們在回顧時可以重新發(fā)現(xiàn)它。
現(xiàn)在,讓我們從密布意義的照片中分出兩個細(xì)節(jié)。在每間房的后墻上,可以找到一條掛毯。其中一條掛毯描繪了摩爾人的舞蹈,其異國情調(diào)的背景讓人想起德拉克洛瓦的《阿爾及爾的婦女》。另一條掛毯展示了18世紀(jì)室內(nèi)音樂會的場景,再次讓我們想起法國藝術(shù),想起對話場景,盡管此處的風(fēng)格和人物姿態(tài)并不協(xié)調(diào),人物造型和布局沒有涉及或者提及任何特殊風(fēng)格或者藝術(shù)品。這張照片里,沒有一絲田園風(fēng)光;而在另一張照片里,房間里用的織錦靠墊上裝飾著田園風(fēng)光圖案。
對這些美國夫婦,掛毯上的畫面形象有何意義呢?一個畫面是否讓人想起了可炫耀消費奢侈品的前工業(yè)社會里,那個較穩(wěn)定階級的精致文化?另一個畫面是否像19世紀(jì)法國許多浪漫主義繪畫中的場景那樣暗示一種逃離:某種異國情調(diào)的東西,某種法國人通過發(fā)展旅游業(yè)而唾手可得的原始文化?它是否暗指某種帶有色情和冒險的東西?為何用掛毯——編織的羊毛圖畫?掛毯本身是否暗指某種特殊意義,無論多么隱蔽,是否承載了對家具和家的歷史的指稱?這樣的暗示是否隨著編織形象的實際大小而漸變?在美國私宅的墻上,是否都掛著這些東西,覆蓋著美國歷史上消費這些形象的不同社會階層的文化記憶呢?這些意義重要嗎?有人觀看、研究、欣賞這些掛毯嗎?它們是被謹(jǐn)慎地或者漠然地掛在特殊的有利位置嗎?它們作為形象的意義,與作為彩色裝飾、墻的主題圖案、整體裝飾的構(gòu)成部分的功能,是否可分離呢?它們是買來的還是制作的?發(fā)明的還是抄襲的?它們是價值連城還是一文不值?是受到尊重還是被忽略呢?牢牢盯著這些物質(zhì)的東西,掛在墻上的一塊塊布片,我們能否發(fā)現(xiàn)問題的答案呢?只要耐心分析它們的內(nèi)在特征,我們可否恢復(fù)掛毯上描繪的形象的意義呢?我們是否需要在歷史社會形成的既定層面,以及在確定的特殊社會實踐和儀式內(nèi)發(fā)現(xiàn)這些意義的構(gòu)建過程?在此,在其實際背景中,在其社會運用的真實語境中,我們能看到這些“次要藝術(shù)品”(minor works of art )。如果我們在博物館遇見它們——無論是“美術(shù)”館,還是“裝飾藝術(shù)”館——我們只知道它們失去了功能(無論多么小的功能),脫離了曾經(jīng)決定其費用和價格以及物質(zhì)和“精神”價值的種種社會關(guān)系,進入一種作為藝術(shù)并且只作為藝術(shù)的陌生的“余生”(a-er-life)。藝術(shù)史家需要討論它們的形式、技巧、圖像學(xué)嗎?需要為它們在藝術(shù)史和藝術(shù)的等級制中找到藝術(shù)地位嗎?更加陌生的變形產(chǎn)生了。漢斯·赫斯曾經(jīng)指出:
如果我們看到有哈德里安像或者康斯坦丁像的硬幣,就會把它看作一件藝術(shù)品,一個精細(xì)模型頭像,一份對藝術(shù)史家很有用的文獻(xiàn),一件稀有的美的物品。如果我們看到一塊50便士的硬幣,我們不會把它看作一件藝術(shù)品。因為它是流通幣,仍然有錢幣的作用。但是,它和曾經(jīng)是流通幣的哈德里安像硬幣一樣是藝術(shù)品。如果硬幣脫離流通,進入日本的錢幣收藏,那么我們可以說,它喪失了原有的功能,變成了藝術(shù)品。
我們應(yīng)當(dāng)扭轉(zhuǎn)這種轉(zhuǎn)變,以了解學(xué)院派半身像的金屬印模以及編織成像的彩色布料曾經(jīng)具有的用途、價值、客觀的社會效用,簡言之,傳播性。我們也必須了解,如馬克思所言,只有作為“國家的強制行動”,這種“傳播”才能行得通;反過來,它只有“在符合社群轄地范圍的內(nèi)部流通領(lǐng)域才能生效”。
現(xiàn)在,我要把“傳播性”這個概念提升到另一個層面。讓我們設(shè)想我們不得不再次提醒自己,我們面對的不是掛毯和家具陳設(shè)的在場,而是面對兩張照片的在場,或者在這個案例中,是兩個影像的照相制版的在場。每張照片內(nèi)都精心植入了攝影主題:一張照片利用一對夫婦正看著而我們卻看不到的相冊;另一張則利用收音機上的肖像照,既暗示了“真實”人物的布局安排,又在照片正中引入了歷史的和表征的符號。如果我們有實際的照片,我們就會有——或許這是如此明顯,以致不必進行陳述——兩張?zhí)厥獾募埰⒂浱枴⒂跋瘢蛼焯阂荒R粯樱菏怯赡撤N精巧的生產(chǎn)模式所生產(chǎn)的物品,是在既定的社會關(guān)系內(nèi)傳播、流通、消費的物品;是在某些社會儀式中找到用途、意義、價值的兩張易手的特殊紙片。根據(jù)真實的和確定的有限選擇,即根據(jù)特殊的、個體的或集體的生產(chǎn)者在生產(chǎn)中所具有的選擇范圍,我們會有兩張印有影像的特殊紙片。其中,影像是經(jīng)由物質(zhì)工藝過程構(gòu)建的。即是說,在特殊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內(nèi),在更廣的意識形態(tài)結(jié)構(gòu)內(nèi),在形塑并支持這一結(jié)構(gòu)的社會實踐和社會問題內(nèi),影像才能變得有意義,才能得到理解。誠如蘇珊 ·桑塔格所強調(diào)的,照片是支配對象。她寫道:
它們會老化,會染上其他紙質(zhì)物品的常規(guī)病癥。它們會一文不值,或者會價值連城。它們被買賣,被復(fù)制……被貼在相冊里,被掛在墻上,被印刷在報紙上,被收集在書籍里。警察把它們標(biāo)上阿拉伯?dāng)?shù)字;博物館把它們當(dāng)展品展出。
照片可以用作證據(jù)。它們也可以用于控告。它們可以是自瀆工具或者征服的戰(zhàn)利品。它們也可以是親屬儀式的象征交換的標(biāo)記,或者潛在所屬世界的替代性標(biāo)記。通過帝國主義的民主化形式,即旅游,它們可以對新經(jīng)驗施以殖民權(quán)力,在繪畫從未預(yù)見的領(lǐng)域內(nèi)把握主體。它們出現(xiàn)在我們的早餐桌上,在我們的錢夾里,放在我們的辦公桌或者梳妝臺上。照片和攝影實踐已經(jīng)是許多社會儀式不可或缺的組成——從海關(guān)檢查到婚禮,從司法證據(jù)的公開拘押到性愉悅的私人證據(jù)——很難想象照片被廣泛使用前,這樣的儀式是怎樣的,又是如何實施的。之所以難以想象,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通過信念和實踐的自然化,社會的內(nèi)部穩(wěn)定得到了保護,但問題是,這些信念和實踐是歷史生產(chǎn)的,具有歷史的特殊性。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看待照片和各種攝影實踐。
我并非要極力回避這些問題。例如,在這些照片中,簡潔的構(gòu)圖法雖然符合主體的整潔利落特質(zhì),但它是如何在照片的結(jié)構(gòu)中,一方面表現(xiàn)自豪的和清教的“富足”;另一方面優(yōu)雅地揭示“好趣味”的匱乏;或者,如何用略微不對稱和柔和的光線,把中產(chǎn)階級夫婦的形象變得溫和;如何通過兩張照片之間的視平線差異,改變我們和主體的關(guān)系,改變表面相同的影像的意義。從這個角度分析照片,恰恰要觀察福柯稱之為權(quán)力的“毛細(xì)管式”存在:“在這一點上,權(quán)力回到每個人的毛細(xì)血管,觸摸他們的身體,逐步嵌入他們的姿勢、態(tài)度、話語、學(xué)徒和日常生活。”我們在照片的各個決定因素中看到了它。我們在這些房間里看到了它,即攝影師將曾經(jīng)的圖像系統(tǒng)轉(zhuǎn)變成了畫面中的房間。我在其他文章中描述了這些特點,指出這是與“外在”關(guān)系相對立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意圖在藝術(shù)史方法中找出未破解的方面,確定可以運作精確分析的層面。我并非要在個體形象的復(fù)雜建構(gòu)過程中開啟一條縫隙。我在此要強調(diào)的是,照片的意識形態(tài)存在與它們作為物品的存在具有絕對的持續(xù)性,而物品的“傳播”和“價值”產(chǎn)生于某種清晰的特殊社會歷史實踐,最終成為國家功能。
攝影作為一種生產(chǎn)模式,需要消耗原材料,完善攝影器材,再生產(chǎn)技術(shù)熟練的順從勞動力,向市場投放大量的豐富商品。通過這樣的生產(chǎn)模式,它構(gòu)建出影像或者表征,而視覺世界則是其消耗的原材料。這一切都定位在觀念和表征的相關(guān)系統(tǒng)內(nèi),但在這些系統(tǒng)中,個人或者社群的思想遭到遏制。因為這些系統(tǒng)主要用于順從勞動力及其對相應(yīng)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默認(rèn)的再生產(chǎn)。在這一意義上,攝影雖然在教育、文化、媒體等重要體制機構(gòu)中被用作工具,但是在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和諧化的”核心權(quán)威下,它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控制機器。所謂統(tǒng)治階級,指公開地或者通過結(jié)盟掌握國家政權(quán)、支配國家機器的階級。誠如路易·阿爾都塞所言,“一個階級若不同時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機器內(nèi)并對其行使領(lǐng)導(dǎo)權(quán),就無法長久地掌握國家政權(quán)”。在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國家,統(tǒng)治階級不可能只把國家構(gòu)建為階級壓迫的機器,原因在于任何國家政權(quán)都有必要超越強制的層面。因此,這一必要性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復(fù)制的東西:
一旦資本主義以原材料和生產(chǎn)手段的形式,(在物質(zhì)上)把投資的財富交給民眾,保護這筆財富變得絕對重要。因為根據(jù)工業(yè)社會的要求,直接掌握財富的人不是財富擁有者,而是那些通過勞動從財富中創(chuàng)造出利潤的人。
因此,對國家的闡釋必須在葛蘭西所說的“市民社會”的視域內(nèi)進行。必須構(gòu)建“一定數(shù)量的現(xiàn)實,以區(qū)分性的專業(yè)化的體制形式,將這些現(xiàn)實直接呈現(xiàn)給觀察者”。這些體制的作用,連同顯著強制性的國家機器的作用,是保障政治條件的再生產(chǎn),以及生產(chǎn)手段在此條件下的再生產(chǎn)。這類更明顯的壓迫性國家機器——政府、行政、軍隊、法庭、警察、監(jiān)獄——為意識形態(tài)機器的有效運作提供并創(chuàng)造了條件,讓它們猶如在“盾牌”的保護下運作,且構(gòu)成一種真正的力量。葛蘭西寫道:
在西方,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存在一種恰當(dāng)關(guān)系。當(dāng)國家產(chǎn)生問題時,市民社會的牢固結(jié)構(gòu)立即得到彰顯。國家只是外圍的壕溝,在其背后矗立著有力的防御工事系統(tǒng):一個又一個,幾乎數(shù)不清。
只有通過意識形態(tài)機器,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才會必然實現(xiàn);只有在意識形態(tài)機器內(nèi),被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才可得到權(quán)衡和估量。因此,意識形態(tài)機器同時表達(dá)社會中普遍和有限兩個層面的階級斗爭,劃出這些斗爭的場域,盡管斗爭最終會波及場外。然而,意識形態(tài)不僅僅表征在經(jīng)濟層面正確定位的階級利益或者階級力量。這樣的“利益”和“力量”是在表征層面(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通過確定的表征手段構(gòu)建的,并無先驗的存在。因此,表征不可還原為經(jīng)濟層面既有的階級認(rèn)同。若要恰當(dāng)理解表征這個概念,就應(yīng)拒絕還原主義的解讀,以及階級利益或階級力量在其表征之前就已完全形成但未實現(xiàn)的觀念。
然而,這并非要作如下暗示(如保羅·赫斯特那樣,他雖然對阿爾都塞關(guān)于表征的鏡像理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是他的批評卻暗示了):要么在被表征之物的源頭(source-of- the-represented )的意義上,被表征之物是不存在的,要么被表征之物的源頭和表征之間的關(guān)系是任意的。[26]表征手段和被表征之物的源頭也許是分開存在的——它們可能有各自的“相對自主性”——但是,如果表征的復(fù)雜構(gòu)建過程,不允許把表征內(nèi)容等同于被表征之物的源頭,也不允許把表征和這個源頭對照起來,那么就不會引發(fā)被表征之物“不存在于它的表征過程之外”的觀念。[27]這讓人聯(lián)想到形式主義畫家和批評家的立場。當(dāng)他們認(rèn)識到繪畫的存在模式不同于其所表征之物時,他們就推斷繪畫是完全自主的,“外在”指稱的在場是外來的非本質(zhì)因素的入侵。在經(jīng)濟層面構(gòu)成的階級,與作為社會力量在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層面構(gòu)成的階級之間,不存在任何簡單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但是,這一聯(lián)系也不是偶然的、任意的。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的是表征過程(需恰當(dāng)理解),而在這一過程中,某一層面的表征是在另一區(qū)分性的和“相對自主的”層面上生產(chǎn)的。
也許我離題太遠(yuǎn)了。我想還是回到我要討論和強調(diào)的觀點吧。當(dāng)我們處理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攝影時,我們不是在處理“外在于”現(xiàn)實的東西:那個根據(jù)反映和倒轉(zhuǎn)法則與現(xiàn)實世界相聯(lián)系的鏡像世界。誠如阿爾都塞所言,“意識形態(tài)總是存在于某一國家機器及其實踐或者種種實踐中。這一存在是物質(zhì)的。”皮埃爾·馬舍雷寫道:“因此,研究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不是分析觀念、思想和表征等系統(tǒng)(‘觀念史’方法),而是要研究意識形態(tài)機器的物質(zhì)運作——以及與之相一致的某些具體實踐。”
閱 讀 推 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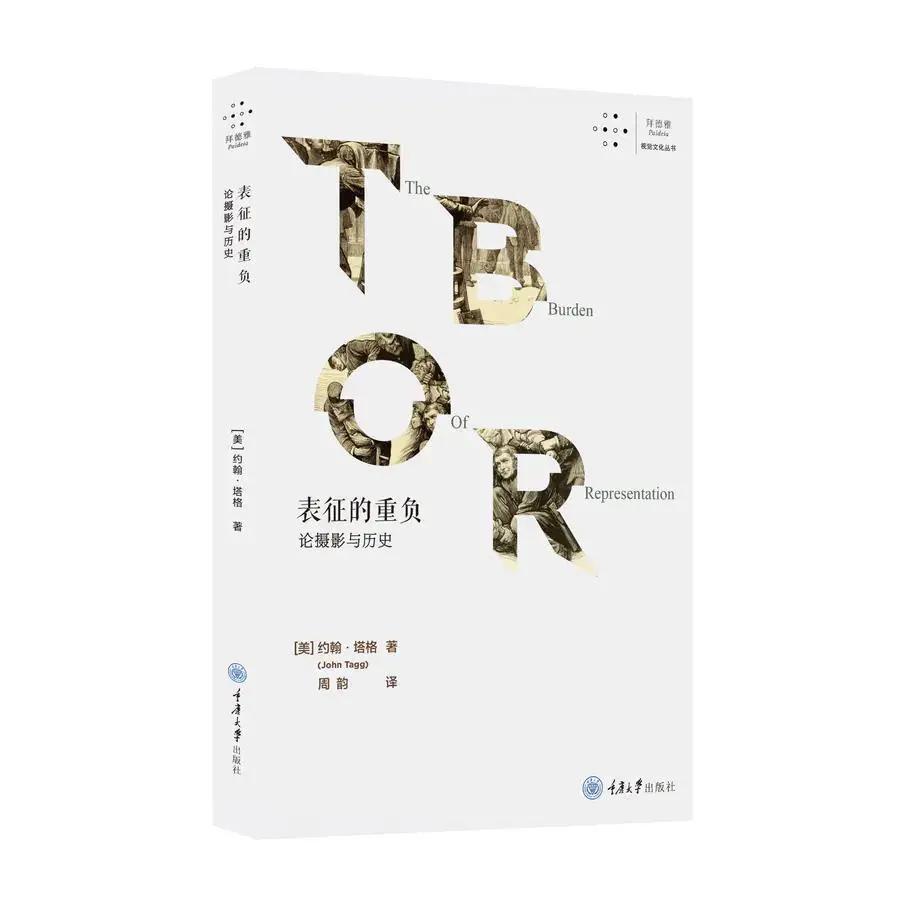
書名 | 《表征的重負(fù):論攝影與歷史》
作者 | 約翰·塔格
譯者 | 周韻
出版 | 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拜德雅
內(nèi)容簡介
在法庭、醫(yī)院和警察局里,在護照、許可證和通行證上,照片被頻繁地用于檔案、證據(jù)和記錄。那些置于鏡頭前的事物與攝影影像之間的對應(yīng)聯(lián)系被理所當(dāng)然地建立了起來,似乎照片就可以斷言一種壓倒一切的真實,證明那些曾經(jīng)存在過的現(xiàn)實。
然而,照片作為此種“證據(jù)工具”,它所擁有的此種“證據(jù)之力”又是如何且在何時被確立并被接受的?哪種類型的照片能夠以這種方式被生產(chǎn)和使用?哪些組織和機構(gòu)有權(quán)賦予它這一地位?這涉及哪些攝影表征的概念,又會產(chǎn)生何種結(jié)果?
通過對攝影進行嚴(yán)格的歷史和體制分析,本書從攝影記錄與現(xiàn)代國家(涵蓋衛(wèi)生、市政、司法、社會控制等)的關(guān)系著手,展示了被織入國家機器與社會網(wǎng)絡(luò)中的攝影所扮演的各種角色,呈現(xiàn)了現(xiàn)代國家和社會的“規(guī)訓(xùn)實踐”與作為“觀看實踐”的攝影的相互關(guān)系。作者將攝影納入現(xiàn)代國家的創(chuàng)生與社會控制的視野中加以考察,書中的觀點植根于他對現(xiàn)代國家的發(fā)展和擴張的歷史性把握。他在書中所展現(xiàn)的問題意識,顯示了福柯思想對攝影史研究的重大影響。
作者簡介
約翰·塔格(John Tagg),藝術(shù)史學(xué)者,策展人,主要學(xué)術(shù)成就在攝影研究領(lǐng)域。他于1980年代中期從英國移民美國,長期擔(dān)任紐約州立大學(xué)賓漢姆頓分校的藝術(shù)史教授。《表征的重負(fù):論攝影與歷史》是他出版的一部較有影響的攝影理論文集,本書曾被一些專家列為攝影領(lǐng)域的基礎(chǔ)讀物。
譯者簡介
周韻,博士,教授,現(xiàn)就職于江蘇第二師范學(xué)院。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美學(xué)和文化,在先鋒派理論方面有一定研究,發(fā)表相關(guān)文章十?dāng)?shù)篇。譯有《大分野之后:現(xiàn)代主義、大眾文化、后現(xiàn)代主義》,編有《先鋒派理論讀本》。
原標(biāo)題:《照片的傳播(上) | 約翰·塔格》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gòu)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