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個(gè)悲摧的循環(huán)
原創(chuàng) 我是艾公子 最愛歷史 收錄于話題 #春秋與戰(zhàn)國 17個(gè)
他的一生充滿了矛盾性和傳奇性。
2500年來,他以復(fù)仇與忠君的雙重標(biāo)簽聞名于世。無論是復(fù)仇還是忠君,他都以極端的方式表達(dá)他的態(tài)度:復(fù)仇以鞭尸泄憤收尾,忠君以忠諫身死告終。
但在他身上,復(fù)仇與忠君又以極其矛盾的方式留待后人評(píng)說,時(shí)而被當(dāng)成不忠不孝的典型,時(shí)而被當(dāng)成至忠至孝的模范。
關(guān)于他的爭議,未曾平息。
他是英雄,也是惡神。是叛逆,也是功臣。
對(duì)他作出評(píng)判的人,或許根本不在乎歷史真實(shí),只在乎自己所處時(shí)代的現(xiàn)實(shí)需要。
后世為他的故事增添了許多傳奇性,層累制造的歷史,使得他的本來面目也日漸模糊。
然而,即便2500年過去,我們依然能從附加在他身上的真真假假的歷史與傳說中,錨定一條清晰而又悲情的主線:
他的父兄因?yàn)橹艺\而被殺,他為了報(bào)仇,隱忍半生,實(shí)施了一個(gè)長達(dá)十五六年的復(fù)仇計(jì)劃,但最終卻難逃父兄一樣的命運(yùn),他仍然因?yàn)橹艺\而被殺。
這個(gè)宿命般的結(jié)局,恰恰是歷史上難以打開的一個(gè)死結(jié),一個(gè)悲摧的循環(huán)。
艾公子今天要講伍子胥(?—公元前484年)的故事,其實(shí)最想講的,就是歷史的悲劇循環(huá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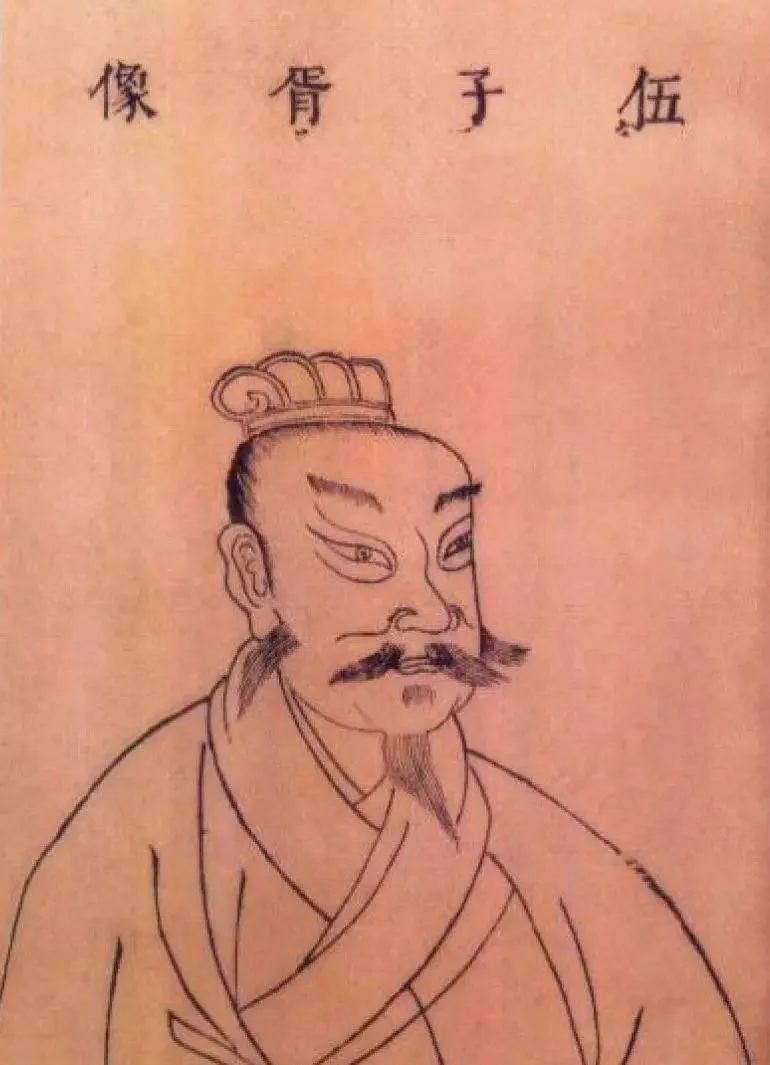
▲伍子胥像。圖源/網(wǎng)絡(luò)

伍子胥復(fù)仇故事的起點(diǎn),是一個(gè)王、一個(gè)美女和一個(gè)奸臣。在后來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忠奸對(duì)立的事情反復(fù)發(fā)生,而這幾乎成為歷史學(xué)家展開亂世敘述的三大標(biāo)配。
王是楚平王,美女是秦國女子,奸臣是太子建的老師費(fèi)無忌。
楚平王讓費(fèi)無忌負(fù)責(zé)太子建的婚禮儀式。費(fèi)無忌看到新娘,來自秦國的女子“絕美”,轉(zhuǎn)頭就給楚平王匯報(bào),慫恿楚平王自己把這個(gè)秦女娶了,再重新給太子娶一個(gè)。
這樣,費(fèi)無忌取悅了楚平王,卻得罪了太子建。為了給自己留后路,費(fèi)無忌開啟了抹黑太子的模式。先是鼓動(dòng)楚平王將太子建調(diào)到城父(今安徽亳州譙城區(qū)東南邊陲),隨后進(jìn)讒言,說太子建在城父厲兵秣馬,結(jié)交諸侯,恐怕要叛變啊。
楚平王信了,召回伍奢進(jìn)行拷問。
伍奢任太子太傅,是太子建的另一名老師。伍氏家族在楚國是地位很高的政治家族,伍奢的祖父伍參在晉楚之戰(zhàn)中曾獻(xiàn)奇謀,助楚軍大勝。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是楚莊王的重臣,見楚莊王不理政務(wù)、沉迷聲色,就給楚莊王出了個(gè)謎語:南方有一只鳥,三年不展翅,三年不鳴叫,這是什么鳥?楚莊王知道伍舉拐著彎兒罵自己不是好鳥,瞬間被激起了斗志說,你的意思,我知道了,雖然三年不展翅,但一飛必將沖天,雖然三年不鳴叫,但一鳴必會(huì)驚人。后來,楚莊王終于成就春秋霸業(yè),人稱“大器晚成”。
根據(jù)《史記》記載,面對(duì)費(fèi)無忌對(duì)太子建的構(gòu)陷,伍奢直言勸諫楚平王:“王獨(dú)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而《左傳》記載伍奢勸諫楚平王的話是:“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意思是,大王您娶太子之妻已經(jīng)是過錯(cuò)了,為何還要一錯(cuò)再錯(cuò),聽信小人讒言,疏遠(yuǎn)至親?
伍奢有伍家流淌在血液里的直言忠諫基因,但楚平王畢竟不是楚莊王,他動(dòng)了殺心。
費(fèi)無忌繼續(xù)進(jìn)讒言說,伍奢有兩個(gè)兒子,不殺掉將來恐成楚國憂患,可以其父伍奢為人質(zhì),把他們召回來,一網(wǎng)打盡。
楚平王對(duì)此“言聽計(jì)從”,一面派人去追捕太子建,一面派人去抓伍奢的兩個(gè)兒子。
問題就出在這里。歷史上,君王為何常常聽不進(jìn)忠臣的直言,而對(duì)奸臣的讒言卻言聽計(jì)從?除了忠臣的直言聽起來刺耳,是否還有可能是因?yàn)椋槌几朴诖陀希f出了君王想說而不便說出來的心聲呢?奸臣是壞,但他們只是君王的代言人,最壞的人其實(shí)是君王本人。
在楚平王派出的抓捕使者趕到之時(shí),伍奢的兩個(gè)兒子——伍尚和伍子胥,進(jìn)行了最后一次對(duì)話。兄弟倆都知道,父親被囚禁,不過是楚平王要挾他們兄弟返楚宮,好斬草除根、永絕后患的籌碼而已。但伍尚為人仁厚,遂將報(bào)仇的重任托付給伍子胥,自己則選擇回到楚宮與父親同死。在《左傳》的記載中,伍尚最后對(duì)伍子胥說:“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
在父兄的印象中,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訽,能成大事。在家族面臨滅頂之災(zāi)時(shí),他最終做出了“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的抉擇。但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在生死關(guān)頭,一留一去,一死一生,這是兄弟倆共同的選擇。
歷史上,生死抉擇的背后,附加著忠孝仁義等各種意義,是一個(gè)古老的二人困境。兩千多年后,晚清的譚嗣同在維新變法失敗后,決定留下來受死,并寫詩說“去留肝膽兩昆侖”,把赴死的人和逃命的人,都置于一個(gè)崇高的地位,因?yàn)槿我贿x擇,都有不同的使命,都不容易。
伍尚束手被捕,等待他的是殉父而死。而伍子胥拉開了弓,搭上箭對(duì)準(zhǔn)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便逃走了。
當(dāng)父親伍奢和哥哥伍尚被殺的時(shí)候,伍子胥已經(jīng)逃亡在了鄰國的土地上。一場(chǎng)偉大的復(fù)仇,拉開了序幕。

▲伍子胥塑像。圖源/攝圖網(wǎng)

在先秦最權(quán)威的史書《左傳》中,關(guān)于伍子胥的逃亡路線,只有簡簡單單的三個(gè)字,“員如吳”——伍員(即伍子胥)去了吳國。
逃亡中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則由其他史書和小說進(jìn)行補(bǔ)述,越往后世,疊加了越多的想象與傳說。
司馬遷《史記》說,伍子胥為了躲避追殺,最早逃到宋國,跟先前已經(jīng)出逃的太子建會(huì)合,然后一同投奔鄭國,最后又去了晉國。不久,太子建在晉頃公的慫恿下重返鄭國,而鄭國人很快發(fā)現(xiàn),太子建可能已被晉頃公收買為內(nèi)應(yīng),于是把他殺掉。伍子胥驚恐不已,連夜帶著太子建的兒子,逃向吳國。
在伍子胥的最后一次逃亡中,他竟然冒著巨大的危險(xiǎn)穿越楚國的昭關(guān)(今安徽含山縣),而不是選擇從其他國家抵達(dá)吳國。這成為一個(gè)難解之謎。
昭關(guān)地處吳頭楚尾,是楚國重兵把守之地。按照正常人的思維,被捕的風(fēng)險(xiǎn)這么大,伍子胥不可能走這條路線入?yún)恰5珡墓糯鷼v史敘述的偏好來看,將主人公置于極大的險(xiǎn)境之中,才能催生出精彩的情節(jié)。伍子胥過昭關(guān)因此更偏向于虛構(gòu)和傳說。事實(shí)上,也正因?yàn)橛辛宋樽玉氵^昭關(guān)的設(shè)定,后世才能不斷往里面增添傳奇情節(jié)。
比如,戰(zhàn)國時(shí)期法家代表作《韓非子》里面,就演繹了伍子胥過昭關(guān)的智謀:
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
意思是說,伍子胥被守關(guān)的負(fù)責(zé)人抓住了,想拿他去楚平王那里領(lǐng)賞。伍子胥反問守關(guān)人,你知道楚王為什么要抓我嗎?因?yàn)槲矣幸活w價(jià)值連城的寶珠,但我已經(jīng)把這顆寶珠弄丟了,到時(shí)我只能在楚王面前說,是你奪了我的寶珠并吞到肚子里去了。那個(gè)時(shí)候沒有B超、X光什么的,守關(guān)人一聽就怕了,趕緊把伍子胥放掉。
司馬遷《史記》則重點(diǎn)講述伍子胥被守關(guān)人追捕,跑到江邊,恰好有一位漁翁劃船而來,渡他過江。伍子胥十分感激,解下佩劍贈(zèng)給漁翁,作為報(bào)答。漁翁拒絕了,說楚王的懸賞令規(guī)定,抓到伍子胥的人封爵,并賜米五萬石,這些都不入我眼,我又怎么會(huì)要你的寶劍呢?
正如法家重在突顯伍子胥的謀略,司馬遷則重在強(qiáng)調(diào)世道人心,在《史記》中,不乏漁翁、屠夫、耕夫這些無名的世外高人,他們地位卑微,與世無爭,但品格高潔,總在關(guān)鍵時(shí)刻代表正義出手,幫助苦主。
到了東漢時(shí)期,當(dāng)時(shí)流行的雜史,進(jìn)一步附會(huì)出新的情節(jié),說伍子胥渡江后特別叮囑漁翁,不要泄露出去。當(dāng)伍子胥因?yàn)椴环判亩仡^再看時(shí),漁翁已鑿船自沉江中。一個(gè)逃亡者的猜忌,和一個(gè)隱世者的高潔,在這個(gè)離奇的細(xì)節(jié)中得到最大的強(qiáng)化。但這已跟真實(shí)的歷史完全無關(guān)。
還有,今天人們熟悉的伍子胥過昭關(guān)一夜白頭,則是到了元代才編出來的。真實(shí)性更加不值一駁。
根據(jù)司馬遷的敘述,過昭關(guān)后,伍子胥生病,中途依靠乞食為生。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史記》中,除了伍子胥,百里奚、重耳、韓信等人都曾淪為乞食者。這可能又是歷史敘述的一個(gè)偏好:將失志的牛人推入山窮水盡的境地,讓他淪為一無所有的乞丐,其實(shí)是為他最終超越困境、成就大業(yè)做好了鋪墊而已。這就跟現(xiàn)在的闖關(guān)游戲設(shè)置一樣,闖關(guān)難度越大,勝利的意義和快感也就越大。
總之,在《左傳》的“員如吳”三個(gè)字背后,歷代史學(xué)家和小說家推演出了伍子胥逃亡和闖關(guān)的許多傳奇故事,只有這樣,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才能促成一個(gè)悲劇人物去完成他的復(fù)仇大業(yè)。因?yàn)椋谡y(tǒng)的觀念中,任何結(jié)局的成功,都不是隨意得來的,中間必經(jīng)過九九八十一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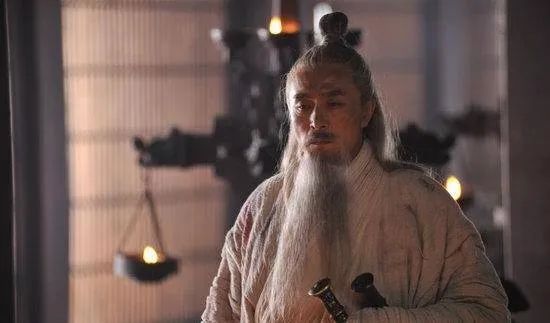
▲伍子胥。圖源/電視劇照

從當(dāng)時(shí)的諸侯形勢(shì)分析,伍子胥歷經(jīng)千辛萬苦也要逃往吳國,是有道理的。
在春秋中前期,主要是晉楚爭霸,能威脅震懾楚國的,除了晉國就沒有了。當(dāng)時(shí)的楚國逃亡者,一般會(huì)先跑到中立國宋國、鄭國,然后到晉國,從晉國尋求復(fù)仇本國的機(jī)會(huì)。流傳到現(xiàn)在的成語“楚材晉用”,反映的就是楚國君臣矛盾,使人才出逃到晉國,并為晉國所用的史實(shí)。
但到了伍子胥生活的春秋后期,晉國大族橫行,內(nèi)亂不止,已經(jīng)無心與楚國爭霸了。來自楚國的逃亡者,如果背負(fù)復(fù)仇使命,依靠晉國攻打楚國來報(bào)仇,就顯得不現(xiàn)實(shí)了。他們只能繼續(xù)尋找有能力、有雄心抗衡楚國的國家,這就是新崛起的吳國。無論是伍子胥,還是與伍子胥有相同遭遇、父親同樣被楚國所殺的逃亡者伯嚭,因此都選擇了奔吳。
但,伍子胥入?yún)菄虮コ挠?jì)劃并不順利。
雖然吳楚兩國為世仇,常年在邊境打仗,但當(dāng)伍子胥向吳王僚獻(xiàn)策一舉攻破楚國時(shí),公子光卻站出來阻止吳王僚,挑明說,伍子胥不過是想替自己復(fù)仇而已,“不可從”。
這是一場(chǎng)讀心術(shù)的較量。公子光看出伍子胥僅為了個(gè)人復(fù)仇考慮,不為吳國社稷考慮。而伍子胥從公子光的阻撓,則看出他有異志,不想讓吳王僚獨(dú)占破楚之功。
伍子胥決定退而求其次,向公子光推薦了一個(gè)名叫專諸的刺客,自己則隱退到鄉(xiāng)下種田去了。
伍奢當(dāng)年說自己這個(gè)兒子性格剛戾,但能隱忍,確實(shí)是知子莫若父。在復(fù)仇計(jì)劃受阻之后,伍子胥選擇了放慢步伐,用時(shí)間去賭公子光能上位成為新一代吳王,再利用其建功立業(yè)、鞏固權(quán)威的需求,游說其攻破楚國。而這注定是漫長的等待。
五年后,伍子胥介紹給公子光的專諸,刺殺了吳王僚。公子光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閭。一上位,他果然把伍子胥從山野之間召回來,任命為“行人”之官,參與國家大政。
又過了九年,吳王闔閭滅楚稱霸的欲望,已經(jīng)比伍子胥滅楚復(fù)仇的欲望強(qiáng)烈得多。伍子胥遂向闔閭獻(xiàn)策,以三支軍隊(duì)分別騷擾的疲楚之策,拉開了大舉進(jìn)攻楚國的序幕。
公元前506年,春秋后期的一場(chǎng)經(jīng)典戰(zhàn)役——柏舉之戰(zhàn),3萬吳國軍隊(duì)深入楚國境內(nèi),在柏舉(今湖北麻城境內(nèi))擊潰了楚國20萬主力。吳國軍隊(duì)隨后攻入了楚國都城——郢都。
這一刻,伍子胥已經(jīng)等了十五六年。但當(dāng)時(shí),他的復(fù)仇對(duì)象楚平王已經(jīng)死去十年,在位的是楚平王與秦國女子的兒子楚昭王。郢都陷落,楚昭王逃入山中。據(jù)司馬遷《史記》記載,十多年間一直胸懷血海深仇的伍子胥,四處搜尋不到楚昭王,怒氣仍無法發(fā)泄,遂掘開楚平王的墓,進(jìn)行鞭尸。但《史記》在另一處則記載,伍子胥僅對(duì)楚平王之墓進(jìn)行鞭撻。
究竟是“鞭尸”還是“撻墓”,已無定論。但伍子胥這一帶有極端侮辱性質(zhì)的舉動(dòng),已經(jīng)嚴(yán)重挑戰(zhàn)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倫理。伍子胥當(dāng)年的好友申包胥,聽到消息后派人傳話,怒斥伍子胥:“你這樣復(fù)仇,未免太過分了!已經(jīng)不講天理到極點(diǎn)了!”
伍子胥則對(duì)來人說:“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yuǎn),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替我向申包胥致歉吧,就說我因?yàn)槟晔乱迅撸鴪?bào)仇心切,就像眼看要日落西山,卻仍路途遙遙,所以才做出這種倒行逆施的事情來。
但這也符合伍子胥剛戾極端的性格,復(fù)仇,他就一定要狠狠地泄憤。
當(dāng)初,伍子胥逃亡楚國之前,跟申包胥說,他(楚平王)殺了我父兄,我一定要滅了他的楚國。據(jù)《左傳》記載,申包胥“勉之”,尊重伍子胥的決定,讓他加油。但申包胥同時(shí)表達(dá)了自己的態(tài)度:“子能復(fù)之,我必能興之。”你能滅楚,我也能興楚。兩人一個(gè)復(fù)仇,一個(gè)忠君,都是合理的訴求,沒有對(duì)錯(cuò),所以互道珍重。
后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申包胥在郢都淪陷后,跑到秦國搬救兵,據(jù)說在秦宮哭了七天七夜,終于感動(dòng)了秦哀公。秦國出兵救援楚國,迫使吳國撤軍回國。
伍子胥的復(fù)仇故事,至此以差點(diǎn)滅了楚國而告終。當(dāng)年的一對(duì)好朋友,各自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的諾言。

▲嘉興南湖伍相祠,匾額題曰“春秋大義”,兩邊楹聯(lián)是“孝當(dāng)竭力,忠則盡命;生為相國,死作濤神”。圖源/攝圖網(wǎng)

有意思的是,申包胥做了楚國的忠臣,而伍子胥最終做了吳國的忠臣。
在伍子胥完成復(fù)仇大業(yè)之后,他并沒有功成退隱,而是繼續(xù)服務(wù)吳王闔閭,成為吳國的重要智囊。闔閭在世時(shí),伍子胥頗受重用,幫助吳國奠定霸業(yè)之基。史載,“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qiáng)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但在闔閭死后,伍子胥在繼位的吳王夫差那里,關(guān)系日漸疏遠(yuǎn)。當(dāng)年與他同病相憐的復(fù)仇者伯嚭,開始取代伍子胥,成為吳王夫差最信任的重臣。
針對(duì)吳國的對(duì)外戰(zhàn)略,是北伐還是南征,伍子胥與伯嚭形成了兩條路線的斗爭。尤其是在公元前494年吳越會(huì)戰(zhàn)之后,吳國軍隊(duì)打得越王勾踐率領(lǐng)殘部退守會(huì)稽山,越國瀕臨亡國。伍子胥與伯嚭的戰(zhàn)略分歧,達(dá)到了空前嚴(yán)重的階段。
伍子胥多次向夫差諫言,一再強(qiáng)調(diào)越王勾踐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力主吳國應(yīng)當(dāng)殺掉勾踐、滅掉越國,摘除心腹之患,然后才能揮師北上,爭霸中原。而伯嚭收受了越王勾踐的賄賂,極力鼓動(dòng)夫差與越國結(jié)盟罷兵,以便將主力投入北伐,盡早稱霸天下,這也可以讓越國獲得喘息之機(jī)。
夫差最終站在伯嚭這邊,僅對(duì)勾踐進(jìn)行奴役式的懲罰,而留給他一條命,也沒有滅掉他的國,這給了勾踐后來臥薪嘗膽翻盤的機(jī)會(huì)。伍子胥對(duì)夫差發(fā)出警告,說天要滅越國,如果吳國不接受,一定會(huì)反遭其殃。而夫差已經(jīng)開始用兵于北方,并被短暫的勝利沖昏了頭腦。
大約十年后,伍子胥在吳國抵達(dá)武力巔峰的時(shí)候,卻已預(yù)見了吳國的敗亡。
盡管先秦的儒家一再勸告,忠君要有度,君王不聽勸諫,可以選擇離開。可是,也許伍子胥血液里流淌著家族忠諫的基因,也許他對(duì)自己的地位和現(xiàn)狀仍有所留戀,他并未像年輕時(shí)離開楚國一樣選擇離開吳國。他采取的最決絕的做法,是在自己出使齊國時(shí)將兒子留在齊國避禍,自己還是返回了吳國。伯嚭則立馬抓住他是一個(gè)“裸官”的把柄,再次向夫差進(jìn)讒言。
夫差徹底被觸怒,當(dāng)場(chǎng)以屬鏤之劍賜死伍子胥。伍子胥自殺前留下遺言,把我的頭顱掛在城頭吧,我會(huì)看到越國滅亡吳國的。夫差聽說了伍子胥的遺言,更加憤怒,命人以鴟夷革裹其尸浮于江,一代忠魂就此長眠于煙波浩渺中。
在伍子胥臨死的時(shí)候,不知道有沒有那么一個(gè)時(shí)刻讓他感覺到吊詭的恍惚?在那一個(gè)時(shí)刻,父親的命運(yùn)在他身上重演了一遍:那一刻,吳王夫差就是當(dāng)年的楚平王,伯嚭就是當(dāng)年的費(fèi)無忌,而他,伍子胥則是當(dāng)年自己的父親伍奢。一模一樣的悲劇,在兩代人身上進(jìn)行了復(fù)制。
數(shù)百年后,司馬遷在給伍子胥作傳的時(shí)候,肯定意識(shí)到了悲劇的循環(huán)。《史記·伍子胥列傳》的整個(gè)敘述,就是被奸臣陷害—隱忍復(fù)仇—再被奸臣所害的故事循環(huán)。在司馬遷的悲情敘述中,隱含著一個(gè)深刻的社會(huì)學(xué)原理,那就是:
在相同的文化生態(tài)中,同樣的人和事總會(huì)不斷地被復(fù)制出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歷史的時(shí)間線是圓形的。整個(gè)春秋時(shí)代,多少亂世豪杰陷于諸侯爭霸的漩渦而無法脫身,真正功成告退、平安著陸的人,或許只有范蠡一人。這使得范蠡成為中國人夢(mèng)寐以求卻極難復(fù)制的理想人格鏡像。而伍子胥,則是更具普遍性的悲劇人格原型,在當(dāng)時(shí)和以后的歷史中,不斷地被復(fù)制。
歷史上的英雄,幾乎都難逃伍子胥式的宿命。

▲蘇州胥門,相傳伍子胥死于此。圖源/圖蟲創(chuàng)意

大約兩百年后,楚國的屈原將伍子胥當(dāng)作自己的鏡像,從中照見了自己的命運(yùn)。
屈原多次在他的楚辭中歌頌伍子胥,對(duì)他的悲慘結(jié)局感到痛心: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忠臣和賢人不一定會(huì)受到重用,可能還會(huì)死得很慘,就像伍子胥受讒言而死,比干被剁成肉醬而死;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憂”——吳王夫差聽信讒言,昏庸啊,等到伍子胥死后,才知道后悔,來不及了;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我屈原真想以伍子胥為榜樣,追隨他而去(后來屈原真的投水自盡,隨伍子胥而去了);
……
屈原為什么要歌頌伍子胥呢?他肯定從伍子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歷史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為伍子胥鳴不平,何嘗不是以伍子胥自況,曲折地傾訴他為國竭忠卻兩次遭楚懷王流放荒野之地的悲憤之情,以及對(duì)楚國前途的悲觀之情。
我在這里專門引述屈原表彰伍子胥的詩句,除了表達(dá)歷史悲劇在英雄人物身上的循環(huán)發(fā)生之外,還想借此闡述一個(gè)歷史常識(shí):先秦時(shí)期,到底存不存在愛國觀念?
現(xiàn)代人容易用后起的觀念去套用早先的歷史情境,甚至去苛求過往的歷史人物。在伍子胥的身上,他在現(xiàn)代就背負(fù)起“賣國賊”的罵名——一個(gè)楚國人,為了報(bào)私仇,投靠外國,不惜引入外國軍隊(duì),還差點(diǎn)滅了自己的祖國,這不是典型的叛徒和賣國賊嗎?
然而,我想說的是,任何脫離時(shí)代背景對(duì)歷史人物的批判,都是耍流氓。
屈原在現(xiàn)代被當(dāng)作偉大的愛國者,但他在詩句里不止一次地對(duì)伍子胥表達(dá)尊敬、同情和愛慕。如果先秦存在愛國觀念的話,屈原還會(huì)如此熾熱地歌頌一個(gè)楚國的叛徒嗎?
申包胥在現(xiàn)代同樣被當(dāng)作偉大的復(fù)國者和愛國者,但他對(duì)伍子胥顛覆楚國的復(fù)仇決心,不僅沒有勸阻,還表達(dá)了加油鼓勁的態(tài)度;即便后來伍子胥的計(jì)劃成真,成為吳國攻陷楚國的帶路黨,申包胥也沒有罵他是賣國賊,而是對(duì)他鞭尸楚平王的殘暴舉動(dòng)表示斥責(zé)。如果先秦存在愛國觀念的話,申包胥還會(huì)鼓勵(lì)一個(gè)楚國的叛徒嗎?
事實(shí)上,愛國觀念是一個(gè)很晚近的概念。用它來評(píng)判先秦的歷史人物,顯然是不適用的。屈原、申包胥他們的所作所為,在今人看來是愛國的,其實(shí)他們不過是忠君罷了。而伍子胥的所作所為,在今人看來是叛國的,其實(shí)也不過是不忠于楚國的君王而已。
春秋戰(zhàn)國時(shí)代,是一個(gè)沒有祖國的時(shí)代。當(dāng)時(shí)的士人階層為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jià)值和理想抱負(fù),在各諸侯國之間游走,采用游說的方式使國君采納其政治主張。范蠡、文種是楚國人,卻為越國所用。李斯、商鞅,一個(gè)是楚國人,一個(gè)是衛(wèi)國人,卻都為秦國所用。類似現(xiàn)象十分常見,當(dāng)時(shí)稱為“楚材晉用”,并不帶有任何道德評(píng)判色彩。
當(dāng)時(shí)人信奉的兩大觀念,一是孝,二是忠。
孝體現(xiàn)在“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也是伍子胥復(fù)仇故事被廣泛稱頌的社會(huì)觀念基礎(chǔ)。
而忠,并不一定要像帝制時(shí)代那么愚忠,先秦儒家推崇的是君臣之間的平等關(guān)系,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所以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主張,君王如果德行有虧,或者屢勸不聽,臣子可以離去,另擇明君。這與帝制時(shí)代臣子必須對(duì)皇帝從一而終的觀念,是截然不同的。
當(dāng)孝與忠發(fā)生沖突的時(shí)候,后來的帝制時(shí)代主張“移孝作忠”,忠大于孝,但先秦時(shí)代恰好相反,是孝大于忠。按當(dāng)時(shí)的說法,叫“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可以為了父親斷絕君臣關(guān)系,但不能為了君王斷絕父子關(guān)系。
在這種觀念背景下,伍子胥向楚平王的復(fù)仇,天經(jīng)地義,無懈可擊。這是他至孝的一面。他后來死諫吳王夫差,則是他死忠的另一面。雖然死忠在當(dāng)時(shí)不像后世那么受統(tǒng)治階層追捧,荀子甚至稱這種死忠為“下忠”,但當(dāng)時(shí)人對(duì)此總體抱持同情、尊敬的態(tài)度。任何時(shí)候,愿意以生命去堅(jiān)守自己信仰的東西,總會(huì)讓人同情和尊敬。伍子胥對(duì)吳王,申包胥、屈原對(duì)楚王,本質(zhì)上是一樣的,都是死忠的體現(xiàn)。
由此可以看出,伍子胥之所以被當(dāng)成至忠至孝的典范,是因?yàn)樗膹?fù)仇和忠諫都具有時(shí)代正義性。而當(dāng)?shù)壑茣r(shí)代開始向臣民灌輸愚忠的觀念以后,伍子胥就逐漸受到了一些歷史盲的苛責(zé):他背叛楚王是為不忠,不能隨父而死是為不孝。
每當(dāng)聽到這些苛責(zé)之聲,我就在想,我們信奉時(shí)代總是在進(jìn)步,但人的觀念,真的也會(huì)一直進(jìn)步嗎?是否會(huì)受到思想的禁錮,反而出現(xiàn)倒退呢?
反正在司馬遷生活的時(shí)代,帝制君臣觀念已開始被重建,但司馬遷顯然更懷念和向往四百年前,伍子胥生活的那個(gè)快意恩仇的時(shí)代。他在給伍子胥寫完傳記后,忍不住贊賞伍子胥是一個(gè)“烈丈夫”,是一個(gè)“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的大英雄。
而千百年來,民間對(duì)伍子胥復(fù)仇故事不厭其煩地反復(fù)傳述,不也正是他們對(duì)昏君暴君不滿卻無法報(bào)復(fù)的一種心理補(bǔ)償嗎?
英雄的歷史悲劇總在循環(huán)發(fā)生,而擊碎這種循環(huán)的時(shí)代觀念,早已老去,只存在于故事之中。這或許才是最讓人悲哀的地方,一嘆!
參考文獻(xiàn):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漢]劉向集錄:《戰(zhàn)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
尚學(xué)鋒等譯注:《國語》,中華書局,2007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
張立新:《逃離與眷顧——伍子胥悲劇命運(yùn)的文化闡釋》,《云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0年第5期
楊華、馮聞文:《伍子胥故事的文本流變和中國古代的價(jià)值觀》,《長江學(xué)術(shù)》,2013年第3期
原標(biāo)題:《一個(gè)悲摧的循環(huán)》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