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深圳湖貝更新:少拆少遷,新舊共生的新模式探索
深圳改革開(kāi)放前20年,羅湖區(qū)以緊鄰香港的優(yōu)勢(shì),沿著廣九鐵路線,率先開(kāi)發(fā)了人民南路以國(guó)貿(mào)大廈為標(biāo)志的商貿(mào)區(qū)、以蔡屋圍各大銀行及后來(lái)地王大廈組成的金融區(qū)、以東門老街為中心的商業(yè)鬧市區(qū)。這三塊構(gòu)成了羅湖區(qū)的金三角,也是早期深圳的時(shí)尚熱鬧中心,加上羅湖有幾棟高層大廈喜用金色,一時(shí)有金色羅湖之稱。
進(jìn)入二十世紀(jì),福田、南山先后崛起,科技、文化、旅游等新產(chǎn)業(yè)的風(fēng)頭逐漸超越羅湖,城市發(fā)展重心西移明顯。2010年深圳總體規(guī)劃一度確定前海是福田中心之后的深圳未來(lái)重心,深感被邊緣化的羅湖強(qiáng)烈要求,把羅湖與福田圈成一個(gè)能和前后海并列的大中心和雙中心。正是這種不甘落后的心態(tài)讓羅湖痛下決心,繼前幾年提出羅湖金三角的振興計(jì)劃后,這次十三五又提出上百個(gè)城市更新項(xiàng)目,要在五年內(nèi)建設(shè)一個(gè)全新羅湖。
一個(gè)重整活力和聲望的羅湖,是靠大量的拆舊建新能達(dá)到的嗎?是的,羅湖老了,街道相對(duì)狹窄,停車位也不夠,對(duì)新產(chǎn)業(yè)新企業(yè)的吸引力不足了。但羅湖大量鏟除老舊建筑,建成福田、南山一樣的新物業(yè),就能將城市重心西移的趨勢(shì)扭轉(zhuǎn)或緩和嗎?這是羅湖區(qū)城市更新必須要面對(duì)的問(wèn)題。比如羅湖在商業(yè)綜合體上從來(lái)都是領(lǐng)先的(從國(guó)貿(mào)免稅商場(chǎng)、天安商業(yè)、東門百貨到近十年都是領(lǐng)先的萬(wàn)象城、KK Mall),擁有最高摩天樓的記錄也是最多的(從國(guó)貿(mào)、地王大廈到京基100和更瘋狂的H700計(jì)劃),如果這些最高摩天樓、最時(shí)尚的商業(yè)綜合體都不能聚攏羅湖的人氣和信心,那么通過(guò)城市更新產(chǎn)生更多同質(zhì)甚至更貴的摩天樓和商業(yè)綜合體,是不是就管用呢?
這就需要追問(wèn)并精確診斷清楚,到底是什么因素導(dǎo)致了羅湖與福田、南山之間此消彼長(zhǎng)、城市重心不斷西移的現(xiàn)象?
第一重要的是地理空間元素,原來(lái)導(dǎo)致羅湖興旺的鐵路+口岸交通,被更多往西(靠近珠江口從而更便捷與香港及內(nèi)陸溝通)的交通連接(依次是廣深高速+皇崗口岸、地鐵+福田口岸、西部通道+深圳灣口岸)所取代;
第二是產(chǎn)業(yè)及人才元素,地域相對(duì)狹小的羅湖憑借口岸、深圳墟和老寶安縣政府所在地的基礎(chǔ)發(fā)展娛樂(lè)、商貿(mào)和金融辦公可以一時(shí)風(fēng)生水起,福田、南山幅員相對(duì)寬廣則更多發(fā)展工業(yè),通過(guò)工業(yè)升級(jí)迅速發(fā)展高科技產(chǎn)業(yè)并吸引了大量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前沿的人才。
這兩方面原因包含的時(shí)空發(fā)展趨勢(shì)都不是人力因素所能左右,也非關(guān)房屋及基礎(chǔ)設(shè)施的老舊,因而目前羅湖遍地開(kāi)花的拆舊建新就不可能對(duì)癥施治,而如此大規(guī)模的外科手術(shù)式的拆建,給羅湖這位老弱病人帶來(lái)的可能是更大的風(fēng)險(xiǎn),并可能干凈地切除了唯一能夠與其它新區(qū)競(jìng)爭(zhēng)的優(yōu)勢(shì)——這個(gè)優(yōu)勢(shì)也是其劣勢(shì),就是老舊與久遠(yuǎn),完全視乎價(jià)值判斷。
拆舊建新的代價(jià)
或者有人會(huì)說(shuō)羅湖的老舊過(guò)時(shí)了,舊的不去,新的就不可能來(lái)。大規(guī)模城市更新正是剔除老朽以便新生。比如說(shuō)橫穿特區(qū)內(nèi)三區(qū)的深南大道,羅湖的深南大道沿線沒(méi)有曠闊的綠化帶及公園,不借助湖貝城市更新項(xiàng)目把深南路邊的大樓和古村拆了,沿線就永遠(yuǎn)無(wú)法有開(kāi)闊漂亮的公園綠地。
消滅臟亂差的城中村與古村環(huán)境,讓這片包括有羅湖區(qū)政府物業(yè)在內(nèi)的老舊建筑升級(jí)換代成高大上形象,并為羅湖深南大道增加開(kāi)闊綠色視野,這大概是羅湖區(qū)政府推動(dòng)湖貝城市更新,并接納現(xiàn)有大拆少留方案(將近40公頃更新范圍內(nèi)拆除70萬(wàn)平米現(xiàn)有建筑、僅僅保留張公懷月祠堂及周邊約56%的古村)的主要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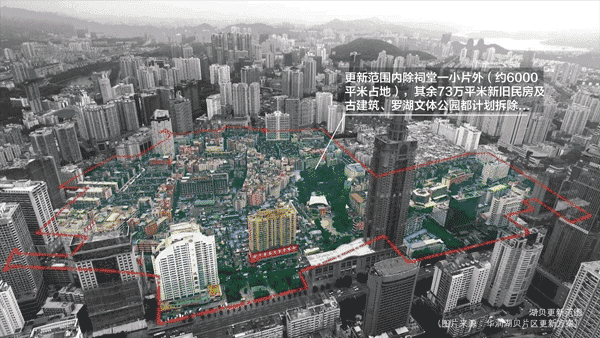
那么羅湖區(qū)要付出的成本有哪些呢?
第一:環(huán)境的。拆除70萬(wàn)平米現(xiàn)有建筑要產(chǎn)生大約100萬(wàn)方建筑垃圾,并在地庫(kù)開(kāi)挖中產(chǎn)生約200萬(wàn)方渣土,兩者相加多過(guò)光明滑坡造成災(zāi)難的渣土;
第二:社會(huì)的。拆除古村和城中村會(huì)讓大約4萬(wàn)住戶居民必須搬離,有些已經(jīng)在這里居住20多年,拆掉的是他們?yōu)樯钲诜?wù)并繁衍撫育第二代的故鄉(xiāng),可能會(huì)造成不小的社會(huì)擾亂,影響到居民居住權(quán)利的保障和“來(lái)了就是深圳人”的認(rèn)同感;
第三:經(jīng)濟(jì)的。低端服務(wù)人口的離開(kāi)會(huì)加大城市服務(wù)成本,加重因?yàn)殚L(zhǎng)距離上班通勤帶來(lái)的交通擁堵,損害城市效率和健康;
第四:文化的。湖貝的空間可以幫深圳上溯到600年前的歷史,而老舊但處于中心或許就是羅湖最獨(dú)特的(與其他區(qū)相比)并可再利用的文化歷史資源。
這四方面的成本如果能夠量化相加,相信會(huì)比羅湖從中得到的地價(jià)及形象收益高得多。
新舊共生的好處有哪些?
那么在羅湖區(qū)政府關(guān)于景觀等方面的預(yù)期和所付出的成本之間,還有什么辦法能趨利避害提供更優(yōu)的綜合效益?
這就是土木再生研究團(tuán)隊(duì)在開(kāi)發(fā)商方案基礎(chǔ)上所做的研究與改進(jìn)。首先滿足區(qū)政府的三點(diǎn)需求:
1)臟亂差環(huán)境改善,在不全部拆除古村和城中村房屋及街巷的前提下能否做到?
答案是當(dāng)然。這里面包括迷你消防系統(tǒng)進(jìn)入湖貝狹窄街巷、老房子結(jié)構(gòu)安全加固及衛(wèi)生、燃?xì)庠O(shè)施的進(jìn)入、下水道改進(jìn)。這些經(jīng)驗(yàn)措施在其它治理好的城中村和古村古鎮(zhèn)都應(yīng)用得非常普遍,比如深圳水圍、皇崗和外地的嶺南新天地、烏鎮(zhèn)、麗江。

2)現(xiàn)有物業(yè)落后面貌能否改進(jìn)?
這個(gè)也是肯定可以做到,開(kāi)發(fā)商的全新項(xiàng)目(比如萬(wàn)象新城)和老舊物業(yè)(湖貝古村)通過(guò)綜合整治品質(zhì)提升后并置在一起,其形象面貌不僅僅有煥然一新感,也有歲月痕跡被精心擦拭后的歷史質(zhì)感沉淀其中,這就像京基100在混搭華僑城loft創(chuàng)意園區(qū)、華潤(rùn)萬(wàn)象城混搭上海新天地或田子坊的感覺(jué),這比所有全新高檔商業(yè)綜合體更加有文化特色,為羅湖增添更多逼格。

3)羅湖區(qū)的深南大道能否因?yàn)檫@個(gè)項(xiàng)目而有景觀上的飛躍?
原開(kāi)發(fā)商方案正是基于這個(gè)考慮把湖潤(rùn)、湖臻兩棟高層住宅樓拆除,并把湖貝古村剩余部分與深南大道之間做成130米寬的開(kāi)敞公園。但在不付出高昂拆遷成本拔除兩棟大廈的前提下,就現(xiàn)有80多米的開(kāi)敞空間能否做出更獨(dú)特和有影響力的景觀?調(diào)整方案給出的建議是,將現(xiàn)有80米敞口做成也許是深圳最長(zhǎng)的臺(tái)階花園,讓大家穿過(guò)綠化樹(shù)木、拾級(jí)或無(wú)障礙地緩坡而上,跨過(guò)湖貝路,以一種環(huán)村城墻的二層系統(tǒng)來(lái)俯瞰、環(huán)游和進(jìn)入格局完整、新舊雜糅的古村,或者通過(guò)這個(gè)二層系統(tǒng)進(jìn)入周邊的商業(yè)及社區(qū)。這樣一種先抑后揚(yáng)的古村體驗(yàn)效果,肯定比將低矮的古村通過(guò)130米開(kāi)寬公園直接敞開(kāi)在深南大道上要獨(dú)特和吸引人得多,因?yàn)榫G化景觀從來(lái)不是以開(kāi)闊寬度來(lái)取勝。

新舊共生還能有哪些驚喜?
在主要滿足區(qū)政府這三項(xiàng)期望的基礎(chǔ)上,調(diào)整方案還有更多超出預(yù)期的貢獻(xiàn):
1)保留和繼續(xù)使用羅湖文體公園原有高大綠化樹(shù)木部分,減少不必要的因?yàn)殚_(kāi)發(fā)對(duì)公共資源的侵?jǐn)_;
2)保留和繼續(xù)使用中興路等綠化市政設(shè)施良好的道路街巷,減少基礎(chǔ)設(shè)施的浪費(fèi)投入和步行友好區(qū)域的不斷減少,并通過(guò)空中各種步行、自行車和創(chuàng)新的個(gè)人捷運(yùn)系統(tǒng)來(lái)立體舒解交通問(wèn)題;

3)在村民與各業(yè)主拆遷賠償預(yù)期、開(kāi)發(fā)容量不變的前提下,保留一半物業(yè)免于拆除,就是為政府增加了15萬(wàn)平米以上的保障房資源,幫助政府更好完成保障房任務(wù),并且盡可能減少拆遷對(duì)原有社區(qū)與居民、原有特色經(jīng)營(yíng)和服務(wù)的侵?jǐn)_和沖擊。
4、在過(guò)去一年關(guān)于湖貝的各種專業(yè)和公眾討論,已經(jīng)將湖貝更新推到了全國(guó)關(guān)注的視野中,新舊共生方案的探索相對(duì)較為周到地響應(yīng)了村民、開(kāi)發(fā)機(jī)構(gòu)、部分居民、歷史文化及社會(huì)關(guān)注者對(duì)方案的期待,也是羅湖眾多更新方案里的創(chuàng)新探索。

新舊共生的困難有哪些?
凡是創(chuàng)新都是利弊相隨,新舊共生方案有哪些困難要克服的呢?
1)通常只有綜合整治(不拆)和拆除重建(拆)這兩個(gè)極端模式的城市更新政策,能否接納這種新舊混合模式?這需要更新主管部門在政策上做出調(diào)整,而這種基于實(shí)踐需求的反饋,恰恰能在邏輯上、價(jià)值觀上和利益關(guān)系上更系統(tǒng)清晰地完善城市更新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也是開(kāi)放創(chuàng)新的深圳必定會(huì)探索的方向。
2)技術(shù)及規(guī)范的突破,比如更新項(xiàng)目掛牌出讓規(guī)定是凈地如何兼容保留物業(yè)、覆蓋率過(guò)大是否有問(wèn)題、不符合日照標(biāo)準(zhǔn)的村民房能否做保障房、保留老舊物業(yè)年限及安全確認(rèn)都復(fù)雜、消防人防相關(guān)限制能否放寬、屋頂花園開(kāi)放管理權(quán)屬等等問(wèn)題。這些技術(shù)及規(guī)范問(wèn)題可能帶來(lái)一些麻煩,但這些麻煩相比大拆除大開(kāi)挖造成的資源浪費(fèi)、渣土場(chǎng)環(huán)境壓力及社會(huì)服務(wù)成本及效率的影響來(lái)說(shuō),是更值得面對(duì)和去解決的小麻煩。
3)不習(xí)慣也沒(méi)見(jiàn)過(guò)這樣的修舊共生的更新方式,不想嘗試未知做法及其風(fēng)險(xiǎn)——這種思維觀念上的慣性和自我設(shè)限,才是這種更新方式推行的最大障礙。但這不恰恰是羅湖區(qū)要解決自身相對(duì)被邊緣的關(guān)鍵嗎?只有建筑的更新,沒(méi)有觀念做法上的創(chuàng)新,羅湖談不上自新,更談不上再現(xiàn)昨日輝煌。
與“城市共生”的雙年展主題相呼應(yīng)

3月20日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發(fā)布新一屆展覽主題是“城市共生”,展場(chǎng)確定在南頭古城城中村。羅湖區(qū)能探索城中村更新的新舊共生模式,將是對(duì)這個(gè)展覽主題的最好回應(yīng)。
(本文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hào)“土木再生”,由公眾號(hào)授權(quán)轉(zhuǎn)載)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