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藏地往事 | 草原上被嫌棄的一生
鏡相欄目首發(fā)獨(dú)家非虛構(gòu)作品,如需轉(zhuǎn)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lián)系
采訪并文 | 楊海濱
編輯 | 林子堯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果洛的牧業(yè)點(diǎn)
倪瓚勁參演《金銀灘》電影的起因說來也巧。1953年夏天,他從紹興到湟源牧校報到,聽同學(xué)說,再往前走三十公里就到青海湖了,便搭輛便車去看地理課上的大湖。沒想到在一片草原上遇到一幫人在拍電影,便好奇地下了車,杵在那看熱鬧,正巧有位手里拿著鐵皮喇叭的男人對他說,快換藏服,和馬步芳的騎兵打仗。
他楞了一下,那人說你不是群眾演員嗎?他馬上反應(yīng)過來說:“是的是的。”轉(zhuǎn)身按要求做了,爬在草地上打槍的姿勢還被那個男人表揚(yáng)。晚上,他和群眾演員坐在帳篷里聊天時才知道,那個拿鐵皮喇叭的人是導(dǎo)演凌子風(fēng)。
他又演了兩個鏡頭,不過連張完整的臉都沒露出來。也就在拍這個鏡頭時,他下決心要當(dāng)電影演員。可這決心還沒捂熱,凌導(dǎo)就對他說:“小倪呀,你還是去學(xué)獸醫(yī)吧。”
他拿著十塊報酬回到湟源牧校。聽說果洛玉樹一帶的工資是西寧的雙倍,就寫決心書,要到艱苦的地方去。在1955年底,他到達(dá)1952年建政的果洛藏族自治州首府吉邁,并分配到達(dá)日縣獸醫(yī)站。這才知道所謂的雙工資就是補(bǔ)助,工資標(biāo)準(zhǔn)全國都一樣。
這時的達(dá)日全縣干部家屬總共不超過二百人,縣城只有幾排橫仄的土坯房,如內(nèi)地一個村子的規(guī)模,荒涼寂寥地處在黃河邊的草灘上,不過它在達(dá)日人心中可是繁華都市,誰都不愿離開這下到連公路都不通的牧業(yè)點(diǎn)。倪瓚勁也想留在縣城,可因年輕又是牧校畢業(yè),牧區(qū)迫切需要獸醫(yī),在報到后的第三天,縣獸醫(yī)站長專門為他配了匹最懂人語能日成百里的“豹花”大走馬去下帳(即下到帳篷,簡稱下帳),這匹馬從那天開始成為他的“專車”,并在后來的20年里隨他走遍了整個達(dá)日草原,直到1975年夏季老死在一次下帳途中……
雖然達(dá)日草原水草茂盛,牛羊成群,數(shù)百公里才有一頂帳篷和幾個牧人,人民政府也已建立數(shù)年并全面展開宣傳工作,可對牛羊群危害的各類病疫情(如口蹄疫)不管不顧,疫情常常如風(fēng)吹過一茬茬地襲擊著牛羊,預(yù)防就成獸醫(yī)們的主要工作,倪瓚勁在牧人不配合的情況下沒了用武之地,只能偷偷摸摸給他們說好話,告訴他們所有藥品全由政府提供無償使用,即使這樣,局面仍然難以打開。
不過也有例外的事發(fā)生。1957年初,倪瓚勁點(diǎn)聽說牧人才旦多杰請了一位從四川阿壩來的游醫(yī),花了二塊銀元把他家一匹馬給騸了,幾天后因感染又死了,就專門找他了解情況。原來這里的牧人為了讓自家的馬性情穩(wěn)定,成為彪悍的坐騎,有騸馬習(xí)慣,那些來路不明的游醫(yī)因技術(shù)原因在騸馬后,馬的成活率只有一半。倪瓚勁就告訴才旦多杰,對于正規(guī)獸醫(yī)來說,騸馬是件小事。

草原放牧一景
才旦多杰相信了他的話,請他為自己另外的馬做騸除手術(shù),然后為鄰居帳篷的兩匹馬也做騸除手術(shù),均平安無事一分錢也沒花。這消息一下在桑日麻草原傳開,牧人自發(fā)牽著自家的馬,在才旦多杰家黑帳篷外扎下小帳篷,排隊(duì)等倪曼巴(藏語里的醫(yī)生)做騸除手術(shù)。
那段時間,他每天起床后,身著長筒黑馬靴和白襯衣,站在帳篷前的草灘上開始做手術(shù),最多一天騸了35匹,最少的一天也騸了10匹,連續(xù)工作了半個月,沒一例死亡。才旦多杰把他騸掉的馬睪丸堆在一個石頭臺上,積攢到了幾百個,臭哄哄吸引蒼蠅亂飛,炫耀倪瓚勁的騸馬術(shù)。
從此他的醫(yī)術(shù)就被很多牧人知曉,和才旦多杰一家人的友情也從這時開始。
冬天,才旦多杰的牛群得了口蹄疫,幾天里死了幾只,他在報告頭人沒得到許可找縣上獸醫(yī)后,擅自騎著馬,在當(dāng)夜凌晨來離他家近百公里外的冬窩子另一家牧人帳篷,把倪瓚勁從睡夢中叫醒,說“牛瘟像黑風(fēng)一樣,會把牛群一掃而光的,請求你快快去救救我的牛羊吧,再晚了我們一家人都沒命了”。倪瓚勁知道牛羊是牧人的生活源泉和所有財富,二話沒說和他連夜到了他家,連續(xù)用了數(shù)天給他家的牛羊打針預(yù)防。在用完帶來的血清后,還有數(shù)百只牛羊沒能打上,就決定騎馬回達(dá)日縣獸醫(yī)站取血清。
由于正值冬天,所有山崗都被白雪覆蓋,才旦多杰怕他一個人迷路或遇到野生動物,陪他一同去縣上取血清。倆人在兩天時間里馱著兩箱藥品騎馬走了近二百公里,回來后連夜挨個將牛羊以及鄰居家的牛羊都打了預(yù)防針,讓健康牛與病牛、牛羊群之間,與鄰居之間的牛羊進(jìn)行隔離,還對牛羊糞消毒、封鎖他們與外界的來往,才讓疫情很快好起來,所以倪瓚勁在才旦多杰和他女兒加三木尕的心里,都是神一樣的人物。
這時期獸醫(yī)工作在都是有跡可尋的。冬季深入到牧人帳篷防凍保畜,春天幫助牧人們接羔育幼,接下來就是大抓七八九,即趁著在牧草茂盛的夏季,為牛羊增膘和過冬前的屠宰作準(zhǔn)備。
起初,倪瓚勁下帳是配有專職翻譯,在他和牧人交流時,翻譯就把他的話譯成藏語,又把牧人的藏話再譯成漢語,很啰嗦,他想,在牧區(qū)當(dāng)獸醫(yī)不會說藏話,連不能自由交流,絕對不是個好獸醫(yī),為讓自己成為好獸醫(yī),從此處處留意自學(xué)藏語,三個月后,發(fā)現(xiàn)翻譯的話有些譯的并不準(zhǔn)確,自己能糾正并和牧人進(jìn)行交流,再過三個月,就驚訝自己無師自通能和牧人無障礙交流了,就不再帶翻譯,一個人單獨(dú)下帳。一年后,他的藏語像母語一樣流暢。
1957年當(dāng)他第一次到桑日麻政府------這時候的縣政府把整個達(dá)日草原劃為七個區(qū)域,這里為二區(qū),象征著區(qū)政府的兩頂棉帳篷就扎在山腳前的平坦草原上,帳篷外有條獅子般純白毛的藏獒守門。

藏族牧人
倪瓚勁每次下帳前,都會買兩斤水果糖隨身攜帶,一則到了牧人帳篷分給孩子和家庭主婦取得信任,二是遇到兇猛的狗,剝幾顆糖喂它增加感情。當(dāng)他看到這條戴著鐵鏈跳躍著碩大身體朝他吠叫撲來的時,趕緊喂它吃糖,七天后那獒見了他就剩下?lián)u動尾巴,只剩下一副歡快的表情了。他就把拴它的鐵璉給取掉,之后就可以看到他走哪,藏獒就尾隨著他走哪跟著晃動。
某天早上,從縣獸醫(yī)站下來的老站長對他說,剛才起來一看我騎來的那匹馬不見了,可能是我昨晚上忘給馬下絆子走遠(yuǎn)了,你趕緊到山背后去找找。
當(dāng)他翻過一座山頭,見前面半山坡上有幾個黑點(diǎn),起初還以為是牦牛,等他看清后竟是幾只狼時已離他很近了,下意識地往后看了看,蒼茫草原在靜寂中不動聲色露出詭異的氣氛,再調(diào)回頭朝前看,那幾只狼已朝他圍攏,他嚇得撒腿就往山下跑,起初還能控制住著身體和速度,但隨著往下沖的速度加快,整個身體如裹挾在泥石流中而身不由己朝山下滾去,直到被一處溝坎絆住雙腳,才重重砸在一處山坡上。立即,他聞到了一股濃重的血腥味,也顧不及哪里負(fù)了傷,想站起身繼續(xù)奔跑,可渾身疼得怎么也站不起來。
就在這時,他看到那只白獒朝荒原狼沖去并撕咬起來,雙方發(fā)出的吠叫像草原天空出現(xiàn)的陣陣春雷,讓人毛骨悚然。他再次努力讓自己站起身來,就看到了荒原狼節(jié)節(jié)敗退四處逃散,白獒身上有幾處傷口像被太陽照耀出的紅云彩,驕傲地挺在山頭上朝他張著。
他又忽見從側(cè)面的半山坡上跑來一位氣喘吁吁的牧女,到了他跟前驚叫著說,阿嘖嘖(藏式感嘆)怎么是你呵?倪曼巴。他這也看清來人竟然是才旦多杰的女兒加三木尕。他問她你怎么在這?她說前面的草原是我家的夏季草場,我和阿媽把羊群趕到這里放牧,我阿媽有事先回去了,我也準(zhǔn)備明后天回呢,剛才看到狼群在追一個漢人就跑來救人,沒想到是你,還被這只白獒救了。
他說:“我現(xiàn)在還需要你幫忙。”她聽后就說: “那咱們現(xiàn)在就去找吧。”他倆翻過一座山頭,在一條山谷里找到那兩匹馬時,已是黃昏,回到帳篷早已滿天星斗。加三木尕對他說: “你一個人晚上回去不安全,留下住一晚明天再走。”倪瓚勁在第二天早上喝了她的奶茶后,騎馬回到二區(qū)的棉帳篷。
隨后的時間里,他常到加三木尕的帳篷,對二區(qū)的人解釋說,他是給她的羊看病,有時連著幾天都不回來,他倆的故事直到一年后的夏季,當(dāng)倪瓚勁再次從達(dá)日縣到桑日麻那兩頂棉帳篷下帳的第三天,就被才旦多杰騎馬來叫他去他的夏季帳篷,等他進(jìn)了帳篷一眼就看到加三木尕和她懷中的孩子。才旦多杰說:“你看看……”
沒等他說完這句話,倪瓚勁突然明白忙打斷說:“不可能!”才旦多杰說:“有啥不可能。”當(dāng)加三木尕睜著難以置信的眼光看他說:“啊嘖嘖……”,表示失望后。倪瓚勁就開始哀求才旦多杰:“求你們千萬不能告訴領(lǐng)導(dǎo),那樣我就會被開除公職……”
才旦多杰說:“我只是告訴你這個孩子已在頭人那報了戶,取名叫智加旦增,可頭人說,按照部落的傳統(tǒng)習(xí)慣叫他倪智加……”
他聽出才旦多杰充滿信賴的口吻,這才喘了口長氣。第二天,他將自己存的三百元錢給了加三木尕,再過半年,加三木尕嫁給了同部落的一個年輕牧人。后來又一次來二區(qū)下賬時,他買了十塊茶磚和一箱白灑看望才旦多杰,才旦多杰還專門為他殺了只羊款待,從此再沒人說起這事。多年后,不知道是倪瓚勁在喝酒時吹牛還是才旦多杰漏出的風(fēng)聲,消息不脛而走。總之,達(dá)日縣有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
而倪瓚勁的婚姻,是在1961年第一次從紹興回達(dá)日縣時,帶回一位穿著江南特有藏青色衣服,非常清爽而又落落大方的女子。他挨個給同事發(fā)了喜糖,說他在老家結(jié)婚,還把老婆帶來了。之后夫妻倆感情一直很好。但直到倪瓚勁在1987年退休都沒有孩子。
有人說那是倪瓚勁年輕時被加三木尕的事嚇成陽萎了,也有人說他老婆生育有問題,還有人開玩笑說,他把馬的睪丸騸得太多遭報應(yīng)。總之,倪瓚勁一輩子沒有兒女,是赤條條來到草原又赤條條回到南方的男子。
翌年冬天,他騎著他的豹花馬到巴顏喀拉山下的納爾根瑪牧業(yè)點(diǎn)下帳,在經(jīng)過一片大草甸上與一只哈熊(學(xué)名棕熊)不期而遇,豹花馬嚇得尥了蹶子,把他從馬背摔下獨(dú)自跑得無影無蹤。哈熊也一楞,站在那看了一會躺在地上的倪瓚勁一動不動,在沒覺出危險后大搖大擺離開而避開一難。
倪瓚勁躺在地上時就覺出左臂疼痛難忍,因納爾根瑪牧業(yè)點(diǎn)沒醫(yī)生,便自我斷定是脫臼了,以為過兩天就會自動復(fù)位,可不料一個星期后疼得更加厲害,這才意識到問題有點(diǎn)嚴(yán)重,趕緊騎馬回桑日麻,可這里缺少醫(yī)生,根本沒有能力讓他脫臼的骨頭復(fù)位,等他又拖幾天回到縣上已是一月后,醫(yī)生說已經(jīng)不可能再復(fù)位。
就這樣,倪瓚勁的左臂落下和一個偉人很相似的殘疾,永遠(yuǎn)僵硬地掛在胸前,就連每天早上穿衣服,都是右手握著左手折騰半天,在騎馬下帳時,先把一根繩子綁在馬鞍上,另一頭綁在殘疾的手臂上做為固定,右手再去抓馬韁繩,以便控制馬在行走中的速度。以至后來入職的年輕人見他這樣,嘲笑他在摹仿領(lǐng)袖人物,當(dāng)知道他是因?yàn)槊摼识鴽]醫(yī)生幫助復(fù)位落下的殘疾,還要騎馬下帳時,都不再吭聲,甚至在說起他時有種肅然起敬的口吻。
倪瓚勁的工資在1956年分配到達(dá)日縣滿一年后,就被轉(zhuǎn)正定為行政25級,又因他為牧人騸馬事件而名噪一時,一年后被縣委書記點(diǎn)名表揚(yáng)漲到行政24級,以后單位再漲工資都是按2%或3%的比例遞長,起初在民主評議工資時因年輕,論資排輩也輪不到他,等有資格了時,又因賬務(wù)問題沒解決而被排除,工資也就一直保持著24級原地多年沒動過。
倪瓚勁從年輕時就抽煙,隨著時間煙癮變得越來越濃,但因工資低舍不得買煙,平時遇到關(guān)系好的同事就直接要煙抽,有時遇到不給他發(fā)煙的人,就支著鼻子嗅對方飄過來的煙味。
那天他到站長辦公室一眼就看到煙灰缸里有四根煙屁股,這時期還沒有過慮嘴煙,被抽過的煙頭都很短,他伸手抓起四個煙頭,搓碎均勻攤在從口袋里掏出早已備好的長條紙上,再卷成喇叭狀,從口袋掏出盒火柴顛出一根火柴棒,用一只手的兩根指頭一劃,“滋啦”一聲在一陣青煙中冒出火花,叼著煙頭對著火苗深深吸了一口,須臾,才重重吐出一個煙柱散開,神情極其陶醉。

倪瓚勁當(dāng)年同事
恰巧撞見這一幕的同事王得利多年后給我講起倪瓚勁時,首先說到了這個細(xì)節(jié),還感嘆地說:“那個時候的達(dá)日縣,我從沒見過有誰撿煙屁股吸的,倪老師是第一個,而且他從口袋里隨時掏出早就備好的長方形紙條這個運(yùn)作來看,撿煙屁股吸肯定有多年的歷史。他有時雖讓人同情,不過有時做得事確立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譬如有次他到醫(yī)院打完針,順手將護(hù)士的瓶酒精帶回家,我后來我才知道他老婆愛干凈,喜歡用酒精消毒,他又不想花錢買,可一瓶酒精才多少錢呵,不值得,而這事被護(hù)士當(dāng)笑料給人說了,再加上縣上某領(lǐng)導(dǎo)嫉妒他不僅演過電影,還能寫一手好公文,有幾年桑日麻公社的年終總結(jié)都出自他手,獸醫(yī)術(shù)也是全縣最好幾個人中的一個,可關(guān)鍵還是他本人不爭氣不重小節(jié),留下把柄就成了人們嫌棄嘲笑他的因素。當(dāng)一個小百姓面對強(qiáng)大的生活的壓力又無能為力時,自然猥瑣成被人嫌棄的模樣。”
1987年前,凡在果洛高原退休的人都有一筆安家費(fèi),但這個政策在這年給取消,而他又正好要在這年退休,眼看著兩手空空回老家,很不甘心找到原籍浙江金華的主管縣長,用紹興土話在他的辦公室哭訴自己在達(dá)日草原三十來年的經(jīng)歷,一個男人的痛哭流涕讓主管縣長起了憐憫之心,動用了特權(quán)將他的工資從24級升到23級后再辦退休,這樣比原先要多拿幾千塊錢,這讓他心滿意足地和老婆離開了達(dá)日草原回到紹興,結(jié)束達(dá)日草原的青春歲月,在回到紹興有沒有想起青春的達(dá)日草原,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生命都會為留下的痕跡而反芻,王得利最后這樣說——他應(yīng)該會常常懷念達(dá)日草原的。
我是在倪瓚勁1987年退休離開達(dá)日草原后的2020年12月,分別拜訪了和他同時代還健在的幾位老同事,并有意識地聊起了他,我注意到大家都像街頭爆米花機(jī)燒得通紅的火膛那樣熱情,尤其談到某些細(xì)節(jié),更如爐膛炸開一地的米花,讓我像看電影那樣看到他在那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中,走過他最好的31年時光的全部經(jīng)歷。
當(dāng)我想到這時,突然就想著打聽一下他在紹興的近況,身處南方的朋友在微信里回復(fù)說,你晚了,12年前他就病故了,我推算了一下時間,那年應(yīng)是2008年,離我們好像很近,轉(zhuǎn)身就能看到那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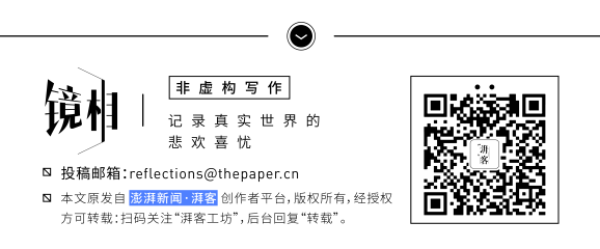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