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喜仁龍:北京舊址上的早期城市
【編者按】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 Sirén)在20世紀20年代初,曾在北京生活居住。他實地考察了北京當時遺存的城墻與城門,并于1924年在倫敦出版了《北京的城墻與城門》(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一書,書中包括細致的勘測觀察手記、53幅城門建筑手繪圖紙、128張實地拍攝的老城墻及城門的照片。不過那時在西方,有關中國城墻城門的話題并不受人關注,因此這本書在首印800冊后便銷聲匿跡了。直到北平解放前夕,當時在英留學、后成為歷史地理學家的侯仁之偶然間發現了這本記錄著北京城墻與城門各類詳細數據及大量精細圖片的奇書,以重價購得并帶回國內,向國人介紹了這部科學研究北京城墻城門的著作。本文節選自《北京的城墻與城門》,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中國歷史學家提到的北京舊址上最早的城市被稱為“薊”。它是冀州最重要的城市,據說在舜帝時期就已經存在了。根據中國地方志記載,這座城市“固若金湯”。公元前723年,這里成為燕國的首都,并在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的軍隊踏平。這座城市位于如今北京城的西北角。到西漢時,這座城市已經沒落。
而到了東漢,約公元70年,在今韃靼城(即明清北京城的內城。清朝時內城只允許滿、蒙、漢八旗官兵及其眷屬居住,其他人則只能居住在外城,即“漢人城”。)的西南角,距薊城以南約10里的地方建成一座新的城市,大部分位于今漢人城的西部。這座城市稱為“燕”,三國時期改稱“幽州”。除了唐朝時曾向這里派駐一支胡人率領的強大軍隊,該城一直寂寂無聞,直到公元936年被契丹占領。當契丹人在這里建立了遼政權并成為中國北方的統治力量時,他們發現這里僅僅是一座小城,不合建都的規制。于是在原址上興建了規模更大的全新的都城,并往幽州的西面和南面擴張得更遠。由于遼王朝已經在更北邊的遼東設立了都城,因此這座新城被稱作“南京”,這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燕京。
布列資須奈德曾沿著現今北京外城南墻外約2.5里以及西墻外約4里處考察,確定了燕京城西南角的位置。東墻位于今琉璃廠(位于前門西面,一條以書店和古玩店著稱的街道)的西側,因為根據《順天府志》引《遼史·地理志》記載,這條街上曾有一塊墓碑,標記此地為燕京城東門外的“海王村”。燕京城的北城墻恰好就在今北京內城南墻一線。

遼的宮城呈長方形,位于燕京城的西南,由兩重宮墻環繞。
當遼被金推翻后(1125年),這座都城又一次經歷了重要的變化。由于資料的來源不同,而收錄時又未加以考訂修正,致使《順天府志》中冗長的敘述出現了含混。不過其中仍有一些部分頗為有趣,引用如下:
金太祖天會三年,宗望取燕山府。因遼人宮闕,于內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門,樓櫓、墉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廒、甲仗庫,各穿復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京師志一·金故城考》)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完顏宗望(后稱太宗)在燕京城內或近畿曾建造筑有圍墻的營壘或碉堡。直到幾年后的海陵王統治時期(1149—1160),才在燕京城的基礎上建成了新的更大的都城,包括新的皇宮。
及海陵立,有志都燕,而一時上書者爭言燕京形勝。梁漢臣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為萬世之基。”何卜年曰:“燕京地廣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天德三年,始圖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養浩等增廣燕城,城門十三:東曰施仁,曰宣曜,曰陽春;南曰景風,曰豐宜,曰端禮;西曰麗澤,曰灝華,曰彰義;北曰會城,曰通元,曰崇智,曰光泰。遂以燕為中都,府曰大興,定京邑焉。都城之門,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其正門旁,又皆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余悉由旁兩門焉。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
顯然這里關于城墻周長的描述并不準確,因為僅燕京舊城的周長就有36里長;如果這個數字僅僅是指新筑城墻的長度,仍然有一個疑惑,那就是新筑的城墻是否是四面全新的,或只是在三面新筑而在北面利用了舊城的一部分?在這部地方志中,另有描述指出,全城周長為75里,這顯然過于夸張,也或許只是印刷錯誤。應當指出,明朝初年對南城(原金中都)的測繪表明,其周長為53280英尺(近30里)。這可能是由于當時的城墻遺存已殘缺不全。要推論金中都的實際周長幾乎已經不可能,但可以確信的是,它比遼代的燕京城要大得多,并向東部有所擴展。中國文獻有著非常明確的記載:
由是觀之,則遼金故都當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其東北隅約當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又考元王惲中堂事記載,中統元年赴開平,三月五日發燕京,宿通玄北郭。(〔清〕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七《京城總紀》)
一些碑刻也反映了白云觀、天寧寺、土地廟等位于今北京內城的西部和南部的寺廟,正在金中都的范圍內。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都包含舊的燕京城,位于今外城以西約4里之外,其東面到達今東便門附近,其南墻極有可能沿用燕京南城墻(外城以南2.5里處),而北墻則位于今北京內城南墻以北約1里處。如果這些推斷是正確的,那么金中都城墻的總長度約54里。
這些城墻都是簡易的土墻,如果中國文獻的記載是準確的,那么筑墻的泥土都是從數里以外靠人工搬運而來的:“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傳遞,空筐出,實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不過令人困惑的是,為什么要從那么遠的地方運送泥土呢!)
至衛紹王時,蒙古軍至,乃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大興尹烏陵用章命京畿諸將毀各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于水。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蒙古兵攻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蒙古兵凡比歲再攻,不能克。(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京師志一·金故城考》)
事實上,由于金人與成吉思汗迅速簽訂了和約,金中都得以保全(1213年),而金朝皇帝已無力再維持其對北方地區的統治,于是遷都汴梁,也稱南京,這是北宋的故都,而當時南宋的都城在杭州。金朝的統治者離開中都后不久,蒙古人便對該城發起了第三次進攻(1215年)。城破后,皇宮被付之一炬,據中國文獻記載,大火整整持續了一個月。大量官員和平民遇難,城市遭到了毀滅性破壞,不過在元朝仍殘存舊宮殿的主要遺跡。明初,金代建筑的廢墟猶存,但隨著嘉靖年間外城的修筑(1554年),這些遺跡逐漸消失。在1260年成為中國北方統治者的忽必烈,曾試圖重建金中都,但這個計劃很快就被另一個更龐大的建都方案所取代。《順天府志》記載:
世祖中統二年,修燕京舊城。至元元年,都中都。四年,始于中都之北建今城而遷都。九年,改大都。城方六十里……(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京師志一·金故城考》)
這一記載也被其他類似的史料,如《元史》所佐證,簡要描述了北京城的起源和早期歷史:偉大的帝國締造者忽必烈意識到,成吉思汗在哈拉和林(今烏蘭巴托西南)的舊營帳不適合作為世界帝國的都城,這樣的都城應當建在中國,而非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因為這里有著最高的文明程度和最富饒的自然資源;至于首都偏處帝國東隅則無關緊要。中國,的確是當時唯一有可能創造世界中心的國家。

時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有官者為先。乃定制,以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據,聽他人營筑。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門外向東五里立葦場,收葦以蓑城。每歲收百萬,以葦排編,自下砌上,恐致摧塌。
可見元大都的城墻是以籬笆或蘆葦模子打圍并夯打筑成的土墻。因此極有可能在明朝以前,磚塊尚未被用于修筑城墻。
新都城的位置,根據上述引文的介紹,是“中都之北”,《順天府志》之后有更詳盡的描述:
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京師志一·元故城考》)
元大都的北城墻位于今安定門和德勝門(現北城墻上的兩座城門)以外,但當時這里應是城墻內的區域。
如果我們接受北京城以北約5里外的那些殘存的土墻就是元代城墻的遺跡,那么關于元大都的北城墻究竟位于何處的問題已經有了答案。它仍然以“元城”之名廣為人知,除此之外很難有其他解釋。這個假設還被明朝文獻所佐證,其中提到,元大都的北城垣在1368年被向南內縮了5里。《順天府志》有這樣的記載:
洪武初,改大都路為北平府,縮其城之北五里,廢東西之北光熙、肅清二門,其九門俱仍舊。(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京師志一·明故城考》)
這段文字可以理解為,新建北城墻上的兩座城門建在了與舊城門對應的位置上,而其他七座城門則原地保留。在《順天府志》的另一段文字中,有一段關于新的北城墻的記載:
元之都城視金之舊城拓而東北,至明初改筑,乃縮其東西迤北之半而小之。今德勝門外有故土城,隆然墳起,隱隱曲抱如環不絕,傳為北城遺址。(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京師志一·元故城考》)
文中所述東、西城墻各縮減了一半乃夸大之說,實際上應修正為縮短了約全長的五分之二,不過這一記述仍相當重要,它清晰地說明了這段曲折的土墻和它原有的兩座城門。
幾乎可以確定,明朝的西城墻和東城墻大抵與元大都一致;平則門和齊化門兩座城門的名稱保留不變,而和義門更名西直門,崇仁門更名東直門。如果這些城墻上的某處發生了改變,它肯定會像北城墻的變化一樣被記錄下來。不過元大都南城墻的位置與建成的明城南墻并不一致,因為它實際上是金中都北界內的一段城墻,而實際上金中都在元朝時依然殘存,被稱為“南城”。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白云觀等建筑位于金中都城內;不過如果金中都北墻不在今北京內城南墻以北至少一里的范圍內,那么這一結論就不能成立。此外,《元一統志》(元代地理文獻)記載——引自《日下舊聞考》:
然考元一統志、析津志皆謂至元城京師,有司定基,正直慶壽寺海云、可庵二塔敕命遠三十步許,環而筑之。慶壽寺今為雙塔寺,二塔屹然尚存,在西長安街之北,距宣武門幾及二里。由是核之,則今都城南面亦與元時舊基不甚相合。蓋明初既縮其北面,故又稍廓其南面耳。(〔清〕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京城總紀》)
又據慣例,觀象臺應建在元大都的東南角,其遺跡在今東南城角以北約1.5里處的東城墻附近被發現。所有這些證據似可確證,元大都南城墻位于今北京內城南墻以北約1—1.5里一線,并且很有可能與金中都北城墻重合(或只有幾步之遙)。南城墻的這一位置直到15世紀初才被永樂帝改變,而北城墻在此之前約50年就由洪武帝下令改動。在后面章節所引用的明朝史料中,這些事實都被清楚地記載。不過在討論后面的年代之前,有必要確認是否有更多有關元大都的資料。元大都雖僅存在約一個世紀,但在此期間卻進行了大量的建設和修復。《順天府志》記載如下:
(至元)二十年修大都城。二十一年五月丙午,以侍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二十九年七月癸亥,完大都城。至治二年十一月,以洪澤芍陂屯田軍萬人修大都城。……至正十九年冬十月庚申朔,詔京師十一門皆筑甕城,造吊橋。(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京師志一·元故城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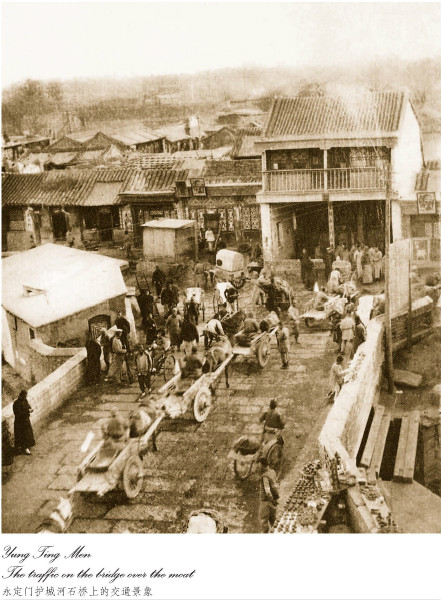
蒙古人的都城元大都,要比今天的北京內城大得多,但也沒有《元史》中描述的周長60里那樣夸張。如果我們所推測的城墻位置是對的,那么其周長不超過50里;中國編年史中的描述很有可能是印刷錯誤或故意夸大。不過,馬可·波羅對元大都的描述更為夸張:
此城之廣袤,說如下方:周圍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哩。
馬可·波羅采用的是1哩等于2.77里的意大利制式的度量單位,那么城墻的周長將超過66里,這顯然與實際不符。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元大都并不是正方形的,而是北端略呈圓角的矩形。馬可·波羅顯然是被元大都的宏偉和輝煌深深震撼了,并對它的各方面極盡描繪。雖然他的描述整體來說是夸大的,但同時也包含一些十分有趣的記載,尤其是關于元大都中一些街道和建筑物的描寫,為我們留下了僅存的史料。比如,他精彩地描述了城墻和城門:
(此城)環以圭墻,墻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墻頭僅厚三步,遍筑女墻,女墻色白,墻高十步。
城墻從頂部至墻基的傾斜角十分明顯,這是極有必要的,因為城墻表面沒有完整的磚面,盡管在頂部有磚石砌筑的女墻。
全城有十二門,各門之上有一大宮,頗壯麗。四面各有三門五宮,蓋每角亦各有一宮,壯麗相等。宮中有殿廣大,其中貯藏守城者之兵杖。
馬可·波羅對城門的印象似乎也有偏差。開有三座城門的城墻只有三面,另一面城墻只有兩座城門。中國的史料無不一致地記載著城門一共只有十一座。城墻上城樓和角樓也很可能不像馬可·波羅所稱的“宮殿”那樣,而是有著柱廊的木結構三檐磚木式建筑。主體為元代所建的鼓樓也屬于這種類型的建筑,它是對早期同類建筑的一種復制。中國的建筑具有很強的連續性,這使我們可以通過現存的建筑,對已經消失的前代建筑的基本樣式有一個較清晰的認識。因此,我們確信,元大都城樓的樣式同明代的基本相似,雖然并不確定其甕城上有沒有另設箭樓。
馬可·波羅對元大都的城市和街道的布局進行了如下描述:
街道甚直,以此端可見彼端,蓋其布置,使此門可由街道遠望彼門也。城中有壯麗宮殿復有美麗邸舍甚多。
各大街兩旁,皆有種種商店屋舍。全城中劃地為方形,劃線整齊,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連同庭院園囿而有余。以方地賜各部落首領,各首領各有其賜地。方地周圍皆是美麗道路,行人由斯往來。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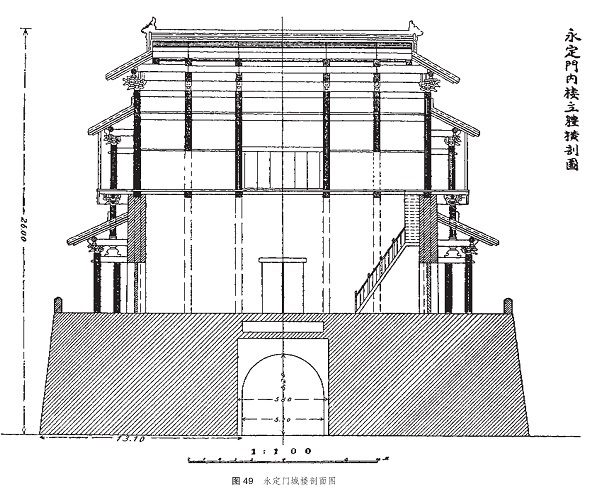
馬可·波羅曾提及帶有“庭院園囿”的“大層”,不過可惜他并沒有對其中的建筑進行更細致的敘述。他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它們早已聞名于世,并且作為見過一兩座這種中式宅院的人,他當然了解它們的全部。除了房屋和庭院的數量以及花園的精致程度的差異,這些建筑并沒有太多的變化。庭院,正是中國家庭的理想中心。
馬可·波羅唯一特別提到的元大都內的建筑是鐘樓,其中他寫道:
城之中央有一極大宮殿,中懸大鐘一口,夜間若鳴鐘三下,則禁止人行。鳴鐘以后,除為育兒之婦女或病人之需要外,無人敢通行道中。縱許行者,亦須攜燈火而出。每城門命千人執兵把守。把守者,非有所畏也,蓋因君主駐蹕于此,禮應如是,且不欲盜賊損害城中一物也。
現在的北京城也有鐘樓和鼓樓,它們位于皇城北邊不遠,位于離東西城墻幾乎等距的位置上。它們的位置在現在看來并不完全在正中,但馬可·波羅對于對鐘樓位置的描述可以從之前提到的事實中理解。元大都的北城墻曾向北移動約5里,且其南城墻位于今天的北京南城墻以北1里多。如果考慮到布局上的這些變化,人們便會發現,今天的鐘鼓樓占據著元大都相當中心的位置,就像其他仍然保留有鐘鼓樓的中國古城一樣。此外,《元一統志》(元代的地理文獻)也證明了這一點:
(至元)九年二月改號大都,遷居民以實之,建鐘鼓樓于城中。
稍有歷史知識便可以發現,今天的鐘鼓樓分別建于兩個完全不同的時期。鐘樓有著更加優美的結構和裝飾,而鼓樓則顯得笨重許多。鐘樓完全是磚結構,建有乾隆時期風格的漢白玉拱券和欄桿以及極具裝飾性的女墻。它是在1745年的一場大火后重建的。其前身建于15世紀初的永樂年間,取代了處于稍微偏東位置的元代鐘樓。鼓樓的寬度是鐘樓的兩倍以上,且建造風格迥異。它的基座是巨大的磚土城臺,兩道拱券打通其底部;上部是由開放柱廊圍合的重檐式雙層樓閣。整個結構顯得老式、傳統,在這里主要表現為體量巨大。雖然經歷了局部重建和整修,鼓樓大體上仍算是元代建筑。如果將它同北京城其他類似的建筑進行比較,比如明朝或清初時期的紫禁城午門,可以發現鼓樓的建筑細節更簡潔(比如斗拱),并且建筑形態笨重,呈現出早期的時代特點。由于鼓樓矗立在直通皇宮的寬闊大街的盡頭,從而產生雄偉的建筑效果。它極有可能是北京城內現存的最古老的宮殿式建筑(類似于中國人所說的“臺”);此外,元大都城內及京畿僅存的元代建筑就只有寺塔了。
然而,令馬可·波羅和教士鄂多立克(忽必烈去世后不久造訪元大都)這樣的歐洲旅行者最贊嘆不已的建筑是皇宮。盡管他們來自孕育不朽而經典建筑的地區,但仍將大汗的宮殿視為世界奇跡之一:面積廣闊,守衛森嚴,門闕重重,宮院深深,亭臺樓閣散見其間;無盡的宮墻似乎隱藏了許多不可言說和探知的秘密。這里的確是世界帝國的中心,其勢力擴張所產生的魅力與其建筑與裝飾的魅力同樣令人震撼。我們并不是要在這里詳細探討元大都的皇宮,但馬可·波羅關于其外觀的描述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元大都中最重要的建筑:
周圍有一大方墻,寬廣各有一哩。質言之,周圍共有四哩。此墻廣大,高有十步,周圍白色,有女墻。此墻四角各有大宮一所,甚富麗,貯藏君主之戰具于其中,如弓箙弦、鞍、轡及一切軍中必需之物是已。四角四宮之間,復各有一宮,其形相類。……
此墻南面辟五門,中間一門除戰時兵馬甲仗由此而出外,從來不開。……
以上文字描述的是皇城,元朝亦稱為宮城。它似乎并不是正方形,而是一個矩形區域,被高墻環繞,四角和城門上建有壯麗的城樓;城的周長也沒有達到4哩(約11里),而是在6—7里。馬可·波羅后文中提到的“大墻”,實際上大致相當于北京“皇城”的城墻。根據元代文獻記載,元皇城周長有20里,而北京皇城周長為18里。對現存遺跡和史料的研究表明,元大都的皇城與明北京城的皇城所在區域近似。馬可·波羅對宮城內的建筑描述不多:
此墻之內,圍墻南部中,廣延一哩,別有一墻,其長度逾于寬度。此墻周圍亦有八宮,與外墻八宮相類,其中亦貯君主戰具。南面亦辟五門,與外墻同,亦于每角各辟一門。此二墻之中央,為君主大宮所在,其布置之法如下:
君等應知此宮之大,向所未見。……

教士鄂多立克的簡短描述證實了馬可·波羅的說法,并用更多的資料說明,內墻與外墻相距半個箭程(bowshot)。
因為在大宮殿的墻內,有第二層圍墻,其間的距離約為一箭之遙,而在兩墻之間則有著他的庫藏和他所有的奴隸;同時大汗及他的家人住在內層,他們極多,有許多子女、女婿、孫兒孫女;以及眾多的妻妾、參謀、書記和仆人,使四英里范圍內的整個宮殿都住滿了人。
讀到這些描述,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戒備森嚴的軍營。元朝皇帝住在這樣的宮苑中,似乎在暗示他統治中國的權力并非上天賦予的,而是兵戈鐵馬威懾的結果。此前的中國都城中,還從未有過如此守衛嚴密、宮墻重重的皇宮。位于長安的唐皇帝的大明宮在城市的北端,呈矩形而凸出北城墻之外,百官衙署設置在其南側與之毗鄰的“皇城”中。開封城內的宋代皇宮也不是嚴防死守的軍事性建筑,雖然宮墻上有角樓和堅固的城門,不過如此強調軍事性卻是蒙古征服者的特性。
在其他方面,元大都的規劃基本以長安城為模型。例如城市平面為方形,根據東、西、南、北確定方位,規則而筆直的路網都被元大都所復制,以及因此也很有可能包括一些官方建筑。野心勃勃的可汗想讓元大都成為有史以來最強大最完美的帝都,從而展現他豐厚的物質財富、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組織能力。1280年,當南宋政權的負隅頑抗最終失敗,元大都由此成為包括整個中國并輻射西亞乃至東歐的龐大帝國的都城。忽必烈的帝國東至朝鮮,西至波蘭,在這廣袤的歐亞大陸間,沒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在規模和顯赫度上與元大都相媲美。1368年,隨著元朝的滅亡,元大都遭受了巨大的破壞,但其主體很快就得以重建,城墻更加堅固,防御更加森嚴,后來它被賦予了一個新的名字——北京,并成為這座“中央王國”的偉大首都。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