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為一朵“木蘭花”:我的木蘭游戲劇場體驗與個人史的社會性
在一家社工機構的志愿者微信群里,我看到了“木蘭的故事”——基層流動女性敘事展演的推薦,這樣的主題在充滿后工業時尚感的798展覽推介中顯得獨樹一格,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通知時間較晚,參與游戲劇場的名額已滿無法再報名。我原本打算只去看看展覽。由于當天的報名者中有人未能到場,我十分幸運地獲得了替補參與演出的資格,有機會通過這個大膽而真誠的項目,短暫地體驗流動女工的生命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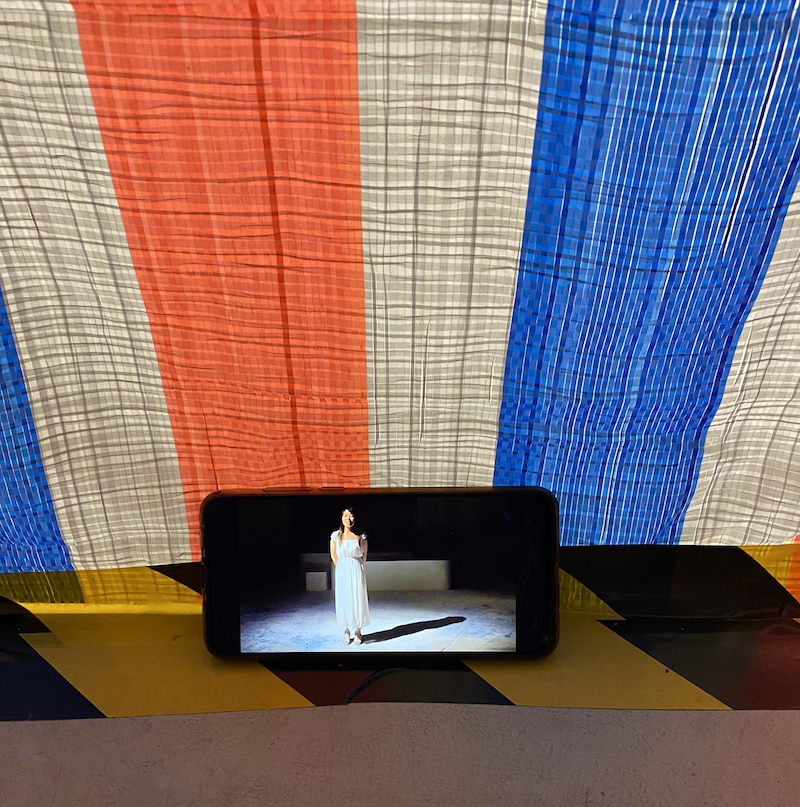
“木蘭的故事”展覽現場
從社區戲劇到游戲劇場
很多人知曉這次“木蘭的故事”的項目策劃趙志勇老師和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是從一部叫做《生育紀事》的戲劇作品。這部作品是由趙老師和“木蘭花開”的姐妹們共同完成的。趙老師將這部作品定位為“社區戲劇”。他認為,社區戲劇與一般參與式戲劇的區別在于,在社區戲劇的創作和演出過程中,職業藝術家和非職業藝術家處于平等地位,演出具有“賦權”的功能,使得在社會結構中被壓抑的人群能夠在表演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從形式上來看,這次“木蘭的故事”游戲劇場回到了一般參與式戲劇的模式:“游戲規則”由編劇事先設定好,參與者并不期待為自己發聲,而是來探索通過角色扮演,共情另一種人生境遇的可能性。不過,相較于一般參與式戲劇對美學體驗方面的強調,“木蘭的故事”依然保留了社區戲劇積極介入社會現實的意圖。如果說《生育紀事》的參與性在于讓身處城市邊緣的流動女工成為表達的主體,與主流聲音形成對話;“木蘭的故事”的參與性則體現在讓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反向地來到城市邊緣,走近這些在為城市提供服務之外就幾乎隱形于公眾視野的女性,嘗試理解她們在生活中面臨的種種困境與抗爭。正如編劇佳靜所說,她希望游戲劇場成為“幫助我們彼此鏈接,縮小理解的鴻溝”的媒介。
發聲者不再是流動女工自己,仍然要讓參與者盡可能身臨其境地感受流動女工的生活處境,這有賴于主創團隊多年來從事打工者聚居社區服務,以及親身參與工人文藝創作所積累的真實素材。對我來說,“這是另一個人的人生”的旁觀者心態只持續到播放第一道人生選擇題的錄音時。在這段錄音中,“我”的一位學校老師要“我”每天下午抽出兩個小時幫她照看孩子,她向“我”保證會幫“我”補上功課,并且告訴“我”,“我”是她最信任的學生,把孩子交給“我”,她最放心。這道選擇題就是“我”是否愿意幫老師照看孩子,在做出不同的選擇后,“我”的人生資源也將被相應增減。游戲模擬人生體驗,我們只知道自己的選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卻無法知道另一個選擇將導向怎樣的未來。這段錄音讓我在一瞬間理解,游戲中的“我”和真實的我自己,盡管成長于不同的家庭環境,卻曾經面臨多么相似的糾結。
成為一朵“木蘭花”
在游戲開始前,我們會抽取一張“初始裝備”卡片,卡片上標示出此時“我”的學歷、健康值、人際關系值和擁有財富的狀態。這些“初始裝備”值并非憑空編寫,每張卡片的背后都是一位真實的流動女工的故事。“我”和她的人生開始于同樣的起點,隨著游戲的進行逐漸走上不同的軌道。
盡管在每次可以做出選擇時都放棄掉一些其他的資源以繼續學習,“我”依然沒能讀完高中,就以初中學歷外出打工了,這將影響“我”未來可從事的工種。這個時候的“我”健康值尚可,而人際關系值已經所剩無幾,我暗自決定,在接下來的選擇中要偏向能夠增加人際關系的選項了。
也許是出于對參與者普遍認知中的女工形象的預期,或者方便將所有人集中在一個場所進行游戲的實際考量,“我”和其他姐妹們的工作場所被選在一家位于南方的電子工廠。在這里,我們通過各種相當有難度的身體扭曲和團隊配合實現“老板”的刁鉆要求,并被鼓勵以夸張有創意的肢體動作表現工作積極性從而獲得額外加分。作為一個并不擅長外放式表達的人,我原本自認與加分無緣地隨便喊著口號,直到在我身旁的姑娘眼中看到了同樣“愛咋咋地”的光。我倆福至心靈,以抱團取暖的姿勢得到了一個創意表達的意外加分。在所有的環節中,友伴關系都是暫時的,只有競爭關系貫穿始終。在經歷了這一番折騰之后,從大家口中說出“異化”這樣在書本上讀來概念頗為復雜晦澀的詞語,簡直成了最自然不過的事。

游戲現場
完成崗前培訓后,“我”成為了一名質檢員。初次上手“找不同”這項工作,身體里那個擁有碩士學歷的我也并沒能給“我”帶來什么幫助,“我”依然找到眼花也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
“我”要面臨另一件人生大事的抉擇了:遠嫁或回家相親。對于“我”來說,保持單身狀態并不在選擇的范圍內。“我”選擇了遠嫁。和丈夫生了一個女娃后,“我”不想再要二胎,被夫家百般為難。“我”生完孩子之后的生活重心就轉向了家庭,一面在照顧孩子和家務勞動中分身乏術,一面消化丈夫“這點事都做不好”的困惑。還好我們都還愿意坦誠溝通,嘗試彼此理解。
“我”出錢幫家里蓋了房子,也實現了人際關系的提升。在游戲結束時,“我”是一個網店的老板,和父母、丈夫、孩子一起生活,沒有多少錢,但所幸沒有負債,命運的盲盒沒有拆出太大的災難,健康和人際關系值都比較高。系統判定,以一名流動女工的身份,“我”獲得了幸福的生活。
“非典型”流動女工
在游戲的結尾,我得以閱讀“借”我身份以度過這一個半小時的女工Y自述的真實經歷。和“我”一樣,她高中沒有讀完就出去打工了,不過并不在南方的大型電子產品工廠,而是在家鄉所在城市的小型服裝工廠。在結婚之后,她隨丈夫一起來到北京,成為一名全職主婦。
比起“我”,Y的經歷在“木蘭花開”的姐妹們中間更加具有代表性。沈琴琴,張燕華(2010)發現,在2006年北京市農業人口普查中,70.9%的流動人口集中在第三產業,從事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流動人口分別僅占12.1%和14.8%。作為對比,2006年上海市流動人口中有54.1%從事第二產業,43.6%從事第三產業。這意味著,比起制造業工廠流水線,在北京的流動女工有更大可能從事家政、餐飲等服務行業。因此她們的生活往往并不圍繞著工廠園區,在市里完成工作后,她們會回到自己的在五環外打工人聚居區租下的房間。趙志勇老師在與“木蘭花開”的成員們交流時也發現,“她們大多是跟著老公來北京打工,生了孩子之后就只能回家做家務、帶孩子。”這樣看來,“木蘭花開”的北京流動女工們,其實多少顛覆了我們對“女工”的刻板印象。她們中的很多人沒有正式工作,為照顧家庭,只能從事更加靈活,同時也更少福利保障的零工經濟。她們的大量勞動付出是在家庭內部,勞動的價值不會體現為工資報酬。
在我對“木蘭的故事”游戲劇場的記憶中,“工作”的內容占了一大半。在我看來,雖然工廠的制度中存在種種不合理之處,這份工作依然是最能體現“我”的價值的所在,它使得“我”能夠獨自在異鄉生活,也是“我”獨立為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的底氣。但在Y的敘述中,工作所占的篇幅是相當短的。她的第一個孩子流產了,于是從第二次懷上孩子開始,她就不再出門工作。自述余下的大半內容,Y都在講述她的婚姻。與“我”不同,Y沒有遠嫁,她和丈夫通過家人的介紹認識,很快便步入婚姻。Y講述了自己與丈夫從起初的隔閡,到丈夫出軌,雙方冷戰,再到和好的整個過程。出于對對方的依賴、為孩子考慮或其他因素,期間Y始終不同意和丈夫離婚。
“我”遠嫁他鄉可以被視為對父母試圖安排自己的人生的一種反抗,“我”自主選擇了自己的配偶,但遠嫁之后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與Y遵父母之命的婚姻并沒有太大不同。那些“我”渴望逃離的桎梏,在接下來的生活中重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在游戲劇場中“我”的敘事框架下,父權制家庭的結構性壓迫是相對外露的,我在游戲中可以感受到較為明顯的不合理之處,“重男輕女”、“忽視再生產的價值”……我可以輕易為這些情節命名。但在Y的敘述中,家庭與社會的結構是相對模糊的,我更多看到的,是Y講述她自己與丈夫的情感關系中的沖突、博弈與和解。或許在了解她們的故事之前,“流動女工”這一位于邊緣之邊緣的身份標簽會讓我們期待她們的故事中出現“壓迫”、“抗爭”這些關鍵詞。Y經歷了很多次艱難的時刻,但在她的敘述中,自己從來不是以一個被動的受害者的身份存在的,她反思自己,積極行動。Y的確以她的方式抗爭了,抗爭的目的是維系這段婚姻,保住自己的生活。這是Y以有限的人生資源能夠為自己和孩子做出的最好的選擇。“我們現在很好。”Y在接近結尾時寫道。從這句看起來和系統給予“我”的評語“生活幸福”十分相像的總結中我讀出的是,Y不是一個童話里等待幸福的公主,她是自己真實生活中的英雄。

展覽現場
個人史的社會性
“木蘭的故事”游戲劇場脫胎于“木蘭花開”社區女工們的真實故事,同時又表現出建立關于“流動女工”的普遍化敘事的企圖。劇場里的每一位“木蘭花”,受到初始設置的原型人物與每位參與者的行為慣習的影響,呈現出多樣化的可能性,但大體上,她是一位來自農村地區,到南方一家流水線大工廠打工,而后結婚、生育的女性。在這個框架之內,編劇最大可能地呈現了一位流動女工在成長、工作、家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種種困境。流動女工面臨選擇的有限性(例如無法選擇是否結婚、生育,只能選擇與誰結婚)是我在游戲中獲得的最深切的體會。從“我”與Y的人生經歷對比中可以看出,這樣淡化區域特征的敘事模式已經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木蘭花開”姐妹們的真實經歷。此外,夫妻共同在外地打工的設定,也無法體現出獨自外出打工的已婚女性的生活境遇。由此便可以看出,“木蘭的故事”項目的兩個組成部分組成部分——游戲劇場和流動女工個人史展覽——之間的互補性。個人史展覽將“木蘭花”的形象還原為一個一個真實的人物,在這里,地理的凹凸綿延、家庭組成形式的多樣、不同人生階段的感悟與愿望都得以顯現。
“木蘭花開”的公益藝術項目以豐富流動女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為主要目標。猶記得在為我們進行導覽時,“木蘭花開”的創辦人齊麗霞表示,希望通過參與文藝創作活動,流動女工們能夠找到對自我的認同,不要在“母親”、“女兒”等身份之中丟掉自己。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它讓我了解到,專注于文娛公益的“木蘭花開”,并不試圖打造分離于現實社會的烏托邦小團體,而是一直意在幫助流動女工認識社會、了解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積極融入社會,訓練在主流話語體系中患上“失語癥”的邊緣人找到自己的語言。這種直指矛盾的鋒利性,似乎是在非以工人為主要參與者的、商業化的文娛活動中難得見到的。由此來講,參與這次“木蘭的故事”活動,于我絕不是單向的了解,更不是居高臨下式的獵奇,它反而成為一個學習的過程。學習提出問題,質疑習以為常的階序結構與觀念的合理性。
(本文首發于公眾號“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授權轉載。)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