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東北老工業人口的日常生活:從工人文化宮談起
隨著紀錄中國新工人詩歌創作的紀錄片《我的詩篇》的公映,“工人文藝”又成為了大眾媒體上一個熱門話題。在我們討論吳曉波和秦曉宇作為新世紀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掌握者,對當代工人文藝的引導與收編有什么問題時,不妨回過頭來尋訪二十世紀工業生產與文化生產的歷史記憶。
從解放前的工人夜校到建國后的工會系統、工人文化宮的建立,東北作為共和國經濟中心其工業生產與配套的文化教育和文藝活動同時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所以我們從張猛的電影《鋼的琴》中,可以看到車間工人們在其作為主體的歷史終結后,借由演奏謀生所呈現出的那個歷史現場中勞動與文藝的關系——文藝的業余與專業之間并沒有一條那么清晰的界限,而工人的勞動也不像今日這般如此不值得追求,所以藝術并非改變個人命運的途經。然而到了改革開放后,生產關系的專業分工使得勞動重新制度化,社會流動的動機也成了從工人到文藝工作者的單向選擇。而到了今天,這一單向流動的可能性似乎也遭遇了危機。
在這一地域遭遇文化與精神徹底的出走之時,回歸這個歷史現場內部就顯得尤其迫切——去探尋其時的文化生產邏輯。對這段歷史的清理及對其后果的認識,不是對東北現代性的自憐與懷舊,而是對當下精神困境的搶救,對未來出路的提醒。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劉巖多年來專注研究東北問題,并于不久前出版了《歷史?記憶?生產——東北老工業基地文化研究》一書。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文化生產被劉巖概括為兩個密切相關并相互交織的脈絡:一個是高度專業化的文化生產系統 ;另一個是單位制下面的工人的文化空間。澎湃新聞邀請了劉巖老師和北京大學的王洪喆老師對談,分別從這兩個脈絡切入,以期從文化生產角度為讀者呈現出一個時代變遷中的東北。此前澎湃新聞已推送這次對談的第一部分:《東北的形象變遷:從陽剛的“共和國長子”到春晚上的鄉土氣》;本篇為對談的第二部分——老工業基地的工人文化空間。孫佳山、周安安和宋念申老師對此文亦有貢獻。
從日據時期的工人運動到解放后的工人文化宮
王洪喆:早期中國工人運動——1920年代一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東北的工人運動在這個版圖里面是很重要的,但我們現在談到那個時期的工人運動歷史是很少會涉及東北。大概是從1923年開始,東北的工人運動在三、四年的時間里,使得工人的工會組織從無到有,這個過程的發生就是通過文體活動和夜校的組織。
以大連為例,當時的大連有大量的日資企業,中共地下黨到了大連之后,就先做了一個摸底,摸底的結果是,這個地方工人的人數已經很多了,但是沒有工人組織,只有一些幫派性質的行會和體育協會,如果想把工人組織起來,就首先要依靠這些幫派,其中大量是體育類的幫派,比如足球等。一方面就是把不同廠的體育行會——每個廠內部都有一個行會,沒有形成全行業的——給橫向的連接起來變成一個行業性質的體育組織。然后跟日本人的一些體育協會打比賽。這個過程當中就有一些愛國主義的動員出來,通過這種方式把一些小型的行會整合到一個比較大型的工人組織里面,大家就有了聯系。
另一方面就是開辦夜校,夜校一開始為了安全起見和工人們的需求,不教跟馬列有關的東西,就是識字、數學、中文、日文。工人說日本人的孩子憑什么有權利接受教育,我們就沒有這個權利。地下黨說好,那就辦夜校。而且這個事情,日本人也喜聞樂見,覺得你們在提高我們的工業人口素質,就放松了警惕。通過這些最基礎的教育,先把工人吸引過來,然后在上課的過程當中,開始夾帶一些馬列的內容,加入革命啟蒙教育。比如上數學課,數學教材里面有《共產主義ABC》等宣傳材料,然后再一點一點開始講。以最重要的大連中華工學會為例,工人白天干活,夜里在夜校讀書,堅持兩年畢業,就能讀書看報,同時擁有了愛國觀念和階級覺悟。日本學者橘樸認為,工學會“強調啟蒙機能”,其初期工作專門致力于會員的知識啟蒙,是“非常高明的”。在會員尚未擺脫知識上的幼稚狀態前,無論怎樣先進的思想指導工人,播下革命的種子也是沒有發芽希望的。因此,“在真正的工人運動開始之前”,必須進行“啟蒙運動”。后來的事實證明了大連中華工學會的革命啟蒙教育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為東北工人運動在五卅后的高潮創造了條件。工學會的活躍分子在沈陽、鞍山、撫順等地建立了組織,逐漸掌握了遼寧工人運動的領導權。
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工學會被查封,會員遭到搜捕和迫害,東北城市里的工人組織是被一鍋端掉。不過已經被組織過的工人一部分被捕入獄,另一部分北上尋找黨組織,成為了30年代東北工人運動和革命斗爭的領導者。抗日戰爭勝利后,東北的城市工作能恢復的這么快,是跟東北工人教育的積累分不開的。除了工學會等組織的遺產,還有些東西可能不好提,所以就沒有辦法寫到官方歷史里。但是我們知道,日本當時是有一些進步的力量,也在東北的工廠里組織工會和工人運動,一直到日本戰敗。
中共在東北獲得政權之后,要恢復生產。恢復生產的一個首要的方法還是去組織工人、教育工人。其實跟二十年代搞工人教育很像,因為那個時候也不可能給工人很多工資,蘇聯又把機器都拆走了。在一段很困難的時期,就是重新要喚起工人的覺悟,要大家一起把恢復生產做好。但是一些從解放區或者軍隊來的干部,直接到地方開始工作,比較急躁,一上來開辦夜校就要講馬列,講毛澤東思想,大干、快上,政治性非常強——說大家要有覺悟,要好好干活什么的。結果各地都有報告說這種政治性的夜校效果非常差。于是1949年東北局總工會在調查的基礎上發了一個文件《東北工人教育中的一些問題》,就說這一階段工人的教育活動不應該直接進行政治鼓動,因為政治性的學習,應該是很系統的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這一階段,還是以工人的需求出發。工人的需求是什么,工人表達的很清楚,就是說我們要有受教育的權利,我們就是要學一些非常基本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術,不要一上來就給我進行政治灌輸。所以工人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在積極提高工人政治覺悟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文化和技術教育”。
工人夜校、文化宮和俱樂部這套系統,是在這個背景下建立的。根據過往的經驗,國家意識到應該有一筆專項的財政用于工人的文化活動建設——工人之前是缺少這個權利。這個跟二十年代的情況很像:就是我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只有日本人有。而解放后政權的合法性首先在于要還給工人這個權利,然后才能去動員他政治覺悟。
1950年8月,全總召開全國第一次工會俱樂部會議,明確規定工人文化宮、俱樂部的主要工作是進行政治宣傳、生產鼓動、文化技術教育,并組織工人、職員群眾及其家屬的業余文化休息和藝術活動。在同一年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工會法中規定:各級政府應撥給中華全國總工會、產業工會與地方工會以必要的房屋與設施,作為工會辦公、會議教育、娛樂及舉辦集體福利事業等之用……工廠、礦場、商店、農場、機關、學校等生產單位的行政方面或資方,應按所雇全部工人實際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按月撥交給工會組織,作為工會經費(其中實際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一點五為職工文化教育費)。由此可見建國后工會的主要職能是組織工人的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
工人文藝:工人與藝術家之間的身份轉換
劉巖:工人運動的斷裂也是全國性的,跟中國共產黨革命重心的轉移有關。最開始革命的重心在城市,后來農村包圍城市,到農村根據地去了。后來又轉回城市,按照一般的歷史敘述,是1949年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黨的工作重心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但實際上準備轉到城市比這要早。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就講“準備轉變”——“由 農 村 轉 變 到 城 市 , 由 游 擊 戰 轉 變 到 正 規 戰”,要打正規戰,就要有工業基礎,就要占領工業城市,于是東北就變得至關重要,因為重工業基本都在東北,毛澤東甚至說:“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爭奪東北,最開始爭的就是大城市,在這個階段,共產黨沒能爭過國民黨,中共東北局和主力部隊一直退到吉林松花江以北。于是又開始反思和調整,動員干部下鄉土改,爭取農民的支持,這樣東北解放戰爭才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但和關內老根據地的土改不同,東北的土改干部是從哈爾濱這樣的大城市派到鄉下去的,指導土改的東北局在哈爾濱。所以,一方面是土改,另一方面,城市工作仍然非常重要。
就在這個時期,誕生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嚴格意義的工業題材作品,就是草明的《原動力》。草明本來也想下鄉去搞土改,但當時東北局的組織部長林楓告訴她,我們今后的工作是城市領導農村,需要有作家熟悉城市,熟悉工廠和工人。于是草明去了牡丹江的鏡泊湖發電廠,寫出了《原動力》。沈陽解放后,草明又到沈陽的皇姑屯鐵路工廠工作,寫出了《火車頭》。《原動力》和《火車頭》,這兩部工業題材文學的開山之作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批評一些老根據地干部的官僚主義和經驗主義,這些干部從農村根據地來到東北的城市和工廠,套用在農村的工作經驗,不會和工人打交道,不知道怎么恢復生產。在《火車頭》中,草明還塑造了一個反對這種經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工會女干部的形象,她在深入工人生產生活的過程中注意到,工人們會自發地用繪畫、歌謠等形式表達情感和訴求,工人的讀寫和文藝創作被小說呈現為和工業生產密切相關的內容。這很大程度上是把草明自己的工作經驗寫進去了,她在牡丹江的工廠擔任文化教員,教工人寫作和唱歌,在沈陽的工廠做工會工作,組織和指導工人進行文藝創作。草明后來就一直留在工廠里,從沈陽去了鞍山,在鞍鋼工作了很長時間,然后又去了北京第一機床廠,在這些工廠里,她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培養工人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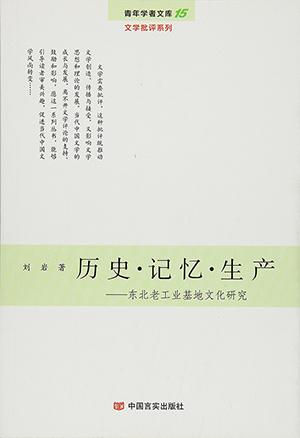
王洪喆:草明1954年到鞍鋼,在鞍鋼工作的十年除了寫出《乘風破浪》,就是成立青年工人業余文藝創作班,直接培養工人作家。草明是一個特別注重工作方法的人,我看過她一些帶工人小組的材料,她特別注重引導工人對文學的興趣,讀古典文學和現實主義,還組織工人觀看分析經典電影,但是她要特別引導你把這些東西跟我們的政治生活結合起來。不僅如此,她還特別有意識地去教育工人從事文學創作不是為了從工人變成一個職業作家——因為有的工人上了她的班或者跟她學了之后,迅速的幾篇作品在媒體上發表,覺得自己是作家了。她要進行集體學習批評這樣的工人,強調工人業余作家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搞文學是為了成為一個無私的人,不能把文學當做敲門磚。她的培訓班十年辦了10期,培養出創作了《沸騰的群山》的李云德為代表的龐大工人作家群,但他們在改革開放后就迅速被邊緣化了。
劉巖:一方面是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很多工人作家變成了專業作家,脫離了工人身份。作家和工人,在新時期成了截然兩分的身份。我曾經分析過大連作家鄧剛寫的《陣痛》,新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改革小說,作者鄧剛就經歷了從工人到專業作家的身份轉變,這是一種相對幸運的轉變,因為當有些人變成了單純的精神勞動者,另一些人就變成了單純的物質勞動者,《陣痛》寫的是后一種轉變中的痛苦,當然,是把它當作進步變革中的暫時痛苦來寫的。具體地說,小說寫的是80年代前期對“以工代干”的整頓。“以工代干”是在毛澤東向全國推廣“鞍鋼憲法”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鞍鋼憲法”的核心原則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參加管理,管理者參加勞動,工人、干部、技術人員相結合,這個原則的實踐在80年代被看作是失敗的經驗。《陣痛》的主人公是一個“文革”時進廠的工人,身份是鉚工,但因為他能寫會畫,所以一直做文宣干部的工作,就是“以工代干”。現在要進行改革了,清理這個“以工代干”,他就回到了鉚工車間,而車間正在優化勞動組合,幾個人承包一個活兒,做的多做的好,獎金就多,他成了最沒人想要的人,所以要經歷一個“陣痛”,重新做回一個工人。與此同時,新分配到廠里的美術學校畢業生替代了他從前的工作,在他從前畫宣傳畫的地方畫廣告。專業分工,更根本地講是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對立,被重新體制化。
王洪喆:當下的復雜性在于,工人作者雖然更想要脫離生產勞動,但現在已經沒有讓工人轉變身份的可能性了。打工詩人和作家通過文學創作,變成一個體制內的寫字為生的人,這種可能性消失了。再往上一代,十年之前,比如鄭小瓊那一代還有這種可能性。她就是一個打工詩人,通過發表打工詩歌,她變成了文聯體制內的一個職業作家。她現在也會去幫助青年打工詩人,但無法再幫助他們復制她的軌跡了。那種三結合的生產關系被改革開放的專業化生產關系取代了。
那么現在的討論就應該回到改革開放是從哪里出發的問題。鄭小瓊這種打工詩人成為職業作家,僅僅是一種單向的流動——大家認為農民工就是一個很差的生活,不值得過,而通過寫作變成一個作家,這個就是好事情,一個良好的社會要復制這個進程,讓更多的人可以實現夢想。
社會流動,實際上完成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雙向代謝——即國家跟工人,或者國家的政治權力跟群眾基礎之間的代謝。不是說個人通過藝術改變了命運,從一個工人變成一個藝術家,不是這樣的敘事。首先,工人之間它有一個內部的循環,以這種業余的方式,不必然走向專業化,因為業余和專業之間并沒有一條那么清晰的界限,而且他的工廠工作也不像是打工的工作那么慘,那么不值得追求,所以工人沒有那么強烈的我要通過這個去實現社會流動的動機。另一方面,如果說有一部分人通過文藝的方式或者通過其他的方式實現社會流動,從工人變成其他的身份,變成文藝工作者,那這個過程一定有一個政治性的前提作為交換,這種從群眾中培養出來的“專業人士”依然要回到群眾中去,比如說草明這樣的作家,她在工廠里工作十幾年,然后回到中國作協做專職作家,但她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工作者,否則無法獲得這樣的流動的機會、渠道。
文化宮系統的解體與滯留在東北的東北人
王洪喆:1945年以后,東北地區為了加速恢復生產,同時配套的文化教育肯定也是加速發展,這兩個邏輯是一樣的。所以那個時候很有趣,你問工人有沒有多少時間去從事業余文體活動,其實是沒有的,工作非常累,時間又長。鋼鐵廠是24小時不能停工的,工人是三班倒,但是這個勞動的狀態跟他的娛樂的狀態是同步的,干活干的熱火朝天,娛樂活動也是熱火朝天的。比如說我訪談的評劇團,就是五十年代進廠的爐前工,原來是鞍山周邊的農民,進到廠里之后就立刻成立評劇團。有專業的工會干事來組織他們,但他們的水平提高的很快,因為經費非常充足。梅蘭芳去朝鮮演出回來第一站到鞍鋼,待一個星期。這一個星期,就第一天在人民劇場公開演出一場,其他的六天都是指導工人八大業余劇團、評劇團是其中之一。各地的專業團體到了這,演出是次要任務,主要任務是指導當地工人文藝團體。
在毛澤東看來,工會是一個組織工人、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場所,是幫助工人成長為國家實際管理者“樂園和學校”。它是一個將政治性融入工人的社會性的組織。所以說,工會和工人俱樂部、文化宮在那幾十年中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其實就是組織工人的文化教育活動,同時工人的社會性以此為中介形成,比如很多工人在業余文藝團體中戀愛結婚。在改革之后,工會要繼續生存,就要利用它之前這些跟文化教育有關的物質性資源,把它們在市場中變成一個可以盈利的項目。一開始國家還有一些規定,比如原來是文化宮或俱樂部,就不能把它轉變為其他的用途,還必須經營文教事業,因此就有很多培訓機構出現。九十年代早期的時候,這些培訓機構還需要辦一些收費比較便宜的班,讓本地有文化宮會員的工人來上。到了后來,只要你辦的是文化娛樂活動或者是教育類就可以,意思就是工會手里的資源也轉變成為市民提供文化服務。既然是為市民提供娛樂,那夜總會、二人轉都是可以的。
劉巖:工人文化宮的角色的變化,有兩個比較顯著的方向。一個方向就是辦各種培訓班,名字還叫“職工培訓學校”,但已經不是為工人服務,而是面向市場社會搞創收。另一個方向就是招商引資,改造成商業化的劇場等文娛場所。比如鐵西區的沈陽工人會堂,原來是沈陽電纜廠的工人文化宮,鐵西的老工廠或者破產了,或者搬遷了,原來廠區的工人文化宮也都不存在了,電纜廠的文化宮是碩果僅存的一個,改名叫“沈陽工人會堂”,成為隸屬于鐵西區總工會的事業單位,但它又是一個自收自支的單位,就是沒有財政撥款,完全市場化運作,所以它租給了劉老根大舞臺,成了劉老根大舞臺在鐵西區的劇場。
在今天,流散的東北人是可以通過大眾媒介看到的,主要是在外地的東北年輕人,他們是流行文化的消費者,也在這種文化中獲得呈現,他們作為文化主體比較容易被看到。反倒是留在東北的老工人群體——過去是工人和下崗工人,現在已經退休了的這批老人,幾乎已經被遺忘了。現在老齡化社會已經是一個熱點話題,對老年廣場舞的討論也越來越多,但似乎還很少把它當作老工人群體的文化生產方式來討論。老工人群體似乎已經瓦解了,但從廣場舞來看,在新的社會環境中他們是不是仍然有自己的組織形式?洪喆好像一直在關注這方面的問題。
王洪喆:當下關于老年人集體文藝的討論缺失了很多東西,我們需要納入一個歷史的參照,這種城市工業人口的集體性文體活動,跟他們的集體工業生產方式之間是有關系的。這個關系曾經是非常直接的,我訪談老工人當年排樣板戲,他們說排《紅燈記》,小廠只能排其中的選段,只排一幕或者兩幕。因為你沒有那么多工人,沒有那么多演職員,也沒有足夠的配合和組織能力,只有大廠才能排全本。你能排樣板戲,說明工廠是有一個復雜工人組織能力的,這不能僅僅用行政命令的強制來解釋。因為當工人離開工廠之后,他這種組織和社會交往的能力,依然是自發地殘留在工業城市中。像電影《鋼的琴》里面演的那樣,在文藝和生產中的協作能力是相通的,這種工業人口的“社會性”,也應該被當做一種發達的現代性加以理解。剛才提到的評劇團,現在平均年齡是接近80歲,都是五十年代進廠的,男工女工都有。現在,在他們的團員一個接一個去世的狀況下,他們還是能堅持每周聚到一起活動、排練,編排新的節目。
如果僅僅把廣場舞,和類似的老年人文藝活動,看做城市空間市場化進程中不同階層對空間和聲音權力的無差別爭奪,是遠遠不夠的。這種老年人的日常組織,里面所包涵的歷史內容,它的社會性,比僅僅爭奪城市空間的定義權和使用權,要豐富的多。當年文化宮里一直在一起唱歌跳舞的那些人,被從工業勞動中排出,進而被從都市人的精神交往和社會性中排出。但他們的身體并不能被抹除,他們依然會頑強地組織起來,聚攏在一起,除了娛樂,當然也會談論政治(邢國欣的文章涉及這一方面)。而且這些組織,它除了娛樂和討論政治,還起到重要的社會支持功能。曾經工會互助共濟的職能,在老年人的自發組織中延伸,比如誰家里出了事情、生病,大家會組織捐款,通過社會網絡找到相關的人幫忙。今天對廣場舞的研究,集中的就是爭奪空間,聲音的政治,但是沒有人深入到歷史和群體內部,去研究廣場舞是怎么組織起來的,他們的生活史,表演的內容形式是怎么商定的,為什么可以保持這么多年一直存在下來。
東北作為中國近現代工業化的原初空間,承載了20世紀國家革命與人民解放的歷史。對這段歷史的清理及對其后果的認識,不是對東北現代性的自憐與懷舊,而是對當下精神困境的搶救,對未來出路的提醒。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