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書評︱金宇澄對談傅月庵:知青、編者、作者

金宇澄,《上海文學》執行主編,近年以長篇小說《繁花》驚艷海峽兩岸,另著有散文集《洗牌年代》、傳記作品《回望》;傅月庵,曾任臺灣遠流出版公司總編輯,副業寫作,目前主事“掃葉工房”,踐行“小農出版”。
網絡昵稱,金為“老貓”,傅為“魚頭”,皆有“編者/作者”雙重身份的金傅二人來了一番“貓魚對談”。在對談的上半場,金宇澄圖繪知青一代,辨析編者和作者的不同角色。
與各地各城青年一起混,好多年的恩怨情仇,罄竹難書
魚頭:我始終覺得你的氣質特別,相對沉穩,也沉重,對人生似乎看得很寬。后來想想,應該也就是改朝換代,解放前后出生的。這一代人(該即是“老三屆”前后?)與其他世代的差異,你是怎么看的呢?
老貓:我屬于這一代,極其混亂的一代,這幫人,1966、1967、1968(畢業)的高中、初中生,碰到1966年“文革”,學校停課,宣傳革命、打砸搶,四處流竄(時稱“大串聯”,坐車吃飯免費),如果父母是“反革命”、“資本家”,一般就做“縮頭烏龜”、“逍遙派”,兩年后“最高指示”發布,集體打包,送到天南地北去務農。
想想看,互相區別,高低不一,志趣不一,出身不一,種種不一,就是搓麻將了,牌與牌根本不一回事,隨便一把抓起來,投放各地農村,然后與各地各城青年一起混,好多年的恩怨情仇,罄竹難書,然后陸續回來,水銀瀉地,蝦有蝦路,蟹有蟹路,大部分做工,然后改革開放,工廠關門等等,多數人處境很差,這群體,這一伙人,是千瘡百孔,內容結構無限的細分,是歷史記錄里少有的,混亂的一代。其他世代怎么可以比?臺灣有這話吧,“竹門對木門”。

魚頭:在臺灣,實在很難想象那種景況,有時或許會想得浪漫了。云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說過一句話:“年輕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大串聯”與“下放”自不同于流浪,卻也都是“移地訓練”,你覺得這一訓練對你的人生,有什么樣的影響?真的毫無養分嗎?
老貓:臺灣有臺灣的特色,比如每次看楊德昌電影,小明的爸爸被關起來寫材料,就會想到我的爸爸。至于流浪,先要有自由。林彪出事摔死,有一句反動話拿來批判——青年上山下鄉,等于“變相勞改”。我勞動的地方,黑龍江黑河,前身就是個大型勞改農場,我就是在勞改,我沒法子流浪。臺灣有這情況沒有?不能隨便亂走,不能隨便去花蓮,沒有花蓮“地方糧票”,你怎么流浪?有錢吃不到花蓮的飯,餓肚子。都是固定在一地方過,除非乞丐。世道跟現在完全相反。
當然也可以講,越貧乏,感受越多,幾頁西方小說,一件膠木唱片,女青年一個背影,一個笑顏,都是格外珍貴難忘,各種影響和養分,靠點點滴滴搜集,不是后世的系統教育。木心在美國給大陸青年講文學課,當然是大陸這種貧困年代產生的遺風嘛,老先生真正的意義所在,他把這個珍貴的老習慣,從七十年代上海,帶到八十年代美國。陳丹青說,噯,這說法有意思。肯定這樣。
那時我回滬探親,小青年都這樣辦,四處找,餓鬼一樣,找有意思的書,有意思的人,無依無靠,等于舊社會一個年輕人找依靠,找黃包車、找蘇北同鄉會,拜青紅幫老頭子那樣,參加秘密私下聚會,比如到閘北一個大姐姐家里,看她打毛線,上海話“結絨線”,一個下午,聽她慢慢跟一幫小弟講《悲慘世界》《簡愛》,因為沒有書,要口述。現有沒有這種人啊,這場面?如果當年我認識木心,肯定比認識一個上海絕世美女還震撼,不夸張的。
十年前碰到了香港科技大學陳建華,他是老上海,現代文學“鴛蝴”專家,八十年代中期到哈佛讀博士,比我大十歲左右,“文革”前和“文革”中,他都躲在上海陰暗角落里寫詩,頹廢主義地下詩歌,當場我心里就難受了——如果當年認識他該有多好啊。這種“當年”,這種心里難受的念頭,進入血液,常常有“當年”,等于杰克·倫敦寫的餓鬼。
因此據說,不少學人對木心《文學回憶錄》不以為然,抽去時代背景,按學堂的教程,來對比一種個性樣式的、歷史的回憶,丟了情感,還做什么文學?人的自以為是,人的遺忘,太可怕。“文革”結束了,陳丹青到中央美院做研究生,一個外地學生見了他就落眼淚,“你上海來的啊!”我完全清楚那種差異,當年除上海北京留了一點殘羹剩飯,還有點貨色,抬頭就是赤地千里!如果忘記了當年情況,是啊是啊,都可以忘記啊,人最容易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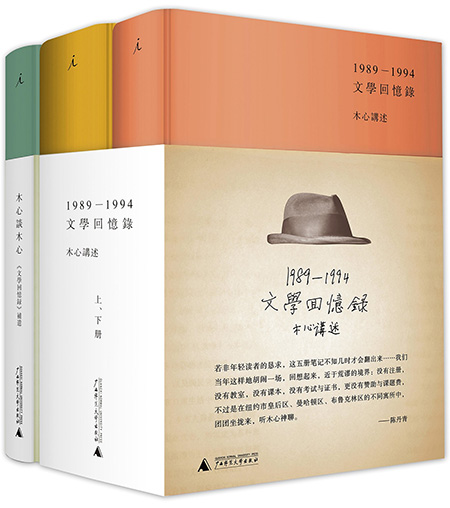
毛澤東的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原因
魚頭:臺灣沒這事。男孩子勉強類似的狀況,大概就是十八歲當兵,抽到外島,被關個兩三年,集體生活,不自由,成天灌輸政治、軍事教育,出操構工什么的,緊張兮兮,敵前唄。但再怎么樣,時間一到,總會“光榮退伍”。
因為缺乏,對知識的饑渴,似乎那老三屆那一代人的特征,且因“準勞改“過,見多識廣,多能“鄙事”。阿城動手就能修這修那,我看你也不遑多讓,什么事都能講出一番真實道理,像散文集里《馬語》那篇,真讓我大開眼界了,那都是實踐體悟來的知識,十足赤金,換在古代,還可按上“格物致知”四字。這書里,類似知識特多,你是怎么煉成的?下放回來,又怎會走上編輯這條路呢?
老貓:人在平靜無望階段,容易被所謂的技能滲透。做馬夫,不知要做到哪一年,就會接受細節了,明告訴你,只做兩年,大概就會心思不定。環境條件很影響人,一匹馬牽過來,地上擺繩,等套住了馬蹄,怎么放倒,怎么用長桿壓緊它,留一個位置,讓師傅過來割開陰囊,當場都不懂嘛,但你在場就有責任,要幫忙,要用力,注意任何的意外情況,記憶就深刻,深入其中,容易懂。
田里吃飯,不會有筷子,鐮刀割兩根樹枝,下筷如雨,菜中有幾塊肉,就是今天焦點,如果盆子里夾出一只醬燒小老鼠,跌下大鍋一起煮熟的?甩在一邊,繼續夾,不會大叫一聲或者嘔吐。生活這樣。農場種植大面積的向日葵,葵花籽“支持國家建設”,據說去造航空汽油。人人的私心是,搞它一些帶回上海,當年是配給制,上海過春節,每家每戶只規定半斤。等葵花籽成熟,乘夜進田,兩三人一伙,老手叮囑,不要怕。暗夜葵花地,花盤低垂,晚風搖擺,如一個個人頭,不許怕,是向日葵。不是人。一人割取,一人收集,一人架起一塊洗衣搓板,下方鋪了麻袋,掰花盤為兩半,不停歇地搓籽。看過了這一夜,細節就不會忘。
有個上海青年是在江西種田,他發覺當地的冬筍,比上海便宜多倍,于是備了小本錢,請一個老農一道進山盜挖,這一路,他一點都不懂,但立刻就懂了,緊張、怕蝕本、擔心被抓進“破壞革命生產”學習班,冬筍通常生長在什么位置上,怎么挖,怎么背到河邊濕沙子里埋起,一路學,埋下就隱蔽,也是保濕、保持運回上海的賣相,還有就是靜等火車。如何運回上海,要細心打聽情報,等哪一趟車次不檢查。火車都要查,禁止搞“資本主義”、“投機倒把”,腦子都要熟記,性命交關,一路心里學下來,任何事情只要跟自身聯系緊密,就知道細節了,死也忘不掉。原因也在于——這本書里有個談話,是“匱乏時代”的原因,毛澤東的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原因。
如何走了編輯這條路,是因為回滬后喜歡寫小說,1986年寫的小說,獲《上海文學》小說獎,不久周介人主編就調我過去。1998年,他在任上過世,我一直做到現在。

你一直挑剔別人,晚上卻滿腔熱情開寫?
魚頭:知識果然還是生命搏來的實在,書本白紙黑字,不免有隔。這種知識,大約是同時代臺灣青年所難有,多半被“升學”、“教科書”給綁住了。要說幸福也很幸福,卻像是被關圍起來的飼料雞,那又是另一種生命經驗了。“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南朝范縝說的真一點兒沒錯。
文集里還有一篇《穿過西窗的南風》,特別浪漫,從上海到大連,一男一女,若有若無,相逢何必曾相識。這里面所顯現的情愫,或可理解下放回來,你為何還是走上寫作這條道路,且成為一名編輯。我好奇的是,編了那么久,也寫了那么久,《繁花》遍地開花之后,“編者”、“作者”這一雙重身份,會否困擾你?還是說“二刀流”相得益彰,讓你寫作時能看得更寬廣些?
老貓:編者和作者不同,編者應該看了最多的普通來稿,作者看了更多的文學經典。編者很清楚目前的寫作基本面貌,而作者一般只關心自己,不會知道如今風行什么寫作套路,是怎樣差不多的老面孔,經典里也沒有。
某種意義上講,除了天才,寫作等于開香皂廠,如果了解了市面上大部分肥皂,方還是圓,一般是什么顏色,什么香氣,自己再做,就可以避免雷同,會更特別一些。不了解的做法,當然也可以——我眼里只有最頂級肥皂牌子,樣樣是外國貨,我就按這個訊息、這個標準做,我直接開工。小說世界和肥皂世界,形式內容要求,大概差不多。產出情況和結果,也會是這樣的情況。

至于雙重身份,兩者混到一起去做,那么,你認真做了編者,就很難寫好自己的文章。編者白天瞪大眼睛,審別人稿件,永遠懷疑,永遠嚴謹挑剔。晚上自己去寫,卻要完全的自信、自我絕對的鼓勵,甚至目空一切才行。你一直挑剔別人,晚上卻滿腔熱情開寫?心理是分裂的,很難受,很難彌合,當然兩件事可以混一起做,“剃頭挑子一頭熱”,要傾斜一頭——比如馬馬虎虎做編者,認認真真寫小說。
我是相反,慢慢沉到了編者的一頭了,慢慢放棄了寫作,吃過分裂的苦頭,白天看稿,晚上自寫,然后第二天一看,這句很不好,那句有問題,到處有問題,自信下降,習性作祟。每天回復作者,挑肥揀瘦,意見多多,日子怎么過?不得不停頓。
魚頭:同感之至!我也深受此分裂之苦,為了“對立的統一”,我的策略是劃定勢力范圍,只在“書”里打轉,寫寫書話、講講跟書有關的事,余者少為。讓編者/作者身份轉換,有座橋梁可走,避免腳下不留神,栽跟斗填溝壑去了。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