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有些事你一旦看見,就無法再忽略|《饑餓、富裕與道德》新書沙龍實錄(上)
原創(chuàng) 三輝圖書 三輝圖書

題圖:《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劇照
作為2021年博古睿哲學與文化獎的獲得者,彼得·辛格收獲的評價是:“在今天這個被社會、技術、政治、文化和經濟變革急遽且深刻改變的世界,他幫助我們找到前行的方向和應具備的智慧,促進我們對自身的認識。”
在彼得·辛格所著的《饑餓、富裕與道德》發(fā)表的1972年,文章中所提出的觀念被認為是激進和超前的。而在人類生活經驗被疫情深刻改變的當下,遠方的苦難、同類的痛苦、關心與救助的義務這些概念或許對每個人都有了新的印跡和意義。
10月,以“如何像幫助鄰人一樣幫助遠方的人”為主題,我們邀請了三位來自發(fā)展與公益領域第一線的嘉賓——Diinsider草根創(chuàng)變者創(chuàng)始人李博倫,共同未來秘書處協(xié)調人黃威,以及公益盒子創(chuàng)始人何流,參與《饑餓、富裕與道德》的新書沙龍,本文是活動的全文整理,包含了三位嘉賓從自身經歷出發(fā)與彼得·辛格的隔空對話,也可以看作是利他主義理念于中國社會的一種真實回響。
實錄分為上下篇,此為上篇。
01
《饑餓、富裕與道德》:時代背景、思想實驗與一種眼光
我覺得人一生總是會讀到一些東西,看到一些事兒,這些事兒你一旦看見,你就沒有辦法再忽略。我覺得辛格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我花了大學三年的時間,再加上大學之前那一年批判辛格,但我最終還是走上了他倡導的這條路……
——何流
李博倫:
關于這本書的話,我覺得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彼得·辛格在前言中提到他寫這篇文章以及去開展一些公益行動的動機其實跟1970年代初的一些社會環(huán)境有關系,像孟加拉的戰(zhàn)亂和饑荒等這些客觀世界的挑戰(zhàn)促使他去參加這些扶貧和慈善的行動。我讀到這里就想到了一個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學者、扶貧的專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我記得很多年前看他的《窮人的銀行家》的時候,他在前言里也是這么寫的。1970年代,他是吉大港大學的教授,面對孟加拉的饑荒,他覺得自己必須要做點什么,所以就放棄了教職,發(fā)起為鄉(xiāng)村女性提供小額信貸的行動。這里面充滿了一種個人的社會責任,也體現(xiàn)了他希望自己的思考能更多地為大眾所接受并被行動化。

作者: (孟)穆罕默德·尤努斯 譯者: 吳士宏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雖然說當我們到2021年回看辛格他的一些解決方案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有些簡單,但當我們從一種國際發(fā)展史,尤其是所謂西方國家的國際發(fā)展史的角度去看的時候,這里面有很多的理念都在實踐過程中遇到了挑戰(zhàn)和批判,包括最早的一些扶貧的理論,基礎設施的建設、綜合的農村發(fā)展、結構調整、私有化,也包括普惠金融等一些具體行業(yè)的變革,以及千年發(fā)展目標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等,后人在從事相關工作的過程中,將這些理念匯聚到學術研究和發(fā)展實踐里,并且不斷的去完善。所以我想沒有一個思想被摒棄了。我們去從事這些工作的過程,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另外一個方面,因為辛格講到了像幫助別人一樣幫助遠方是一種利他主義。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除了利他主義的訴求以外,從事這些發(fā)展工作或者公益工作的過程,也是這些從業(yè)者和學者向這些發(fā)展中國家的機構和個人學習,從而開闊視野、完善認知,并且在從與更多的人交談和交換思想的過程中獲得自身的提升,更好的完成工作的一個過程。所以有效利他也意味著能夠去更好的在這個過程里向對方學習,這是我對這本書以及書中觀點的一些個人的理解。
黃威:
博倫剛才提到了好幾個點都是我比較有共鳴的。首先是辛格作為一個行動者的存在,他的倫理學觀點并沒有停留于紙面。我記得辛格成為素食主義者的轉變非常簡單,有一次在食堂吃飯的時候,跟他在一起的一個朋友點了素食,辛格點了一個有肉的,然后他們就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個理論上的探討——關于有什么能證明吃肉是一個可以被justify的行動,他發(fā)現(xiàn)自己找不到任何理由,所以在結束這個討論后,他回家就問妻子要不要嘗試吃素。后來他又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參與動物保護事業(yè),成為了一個有著多物種關懷的人。從理論到實踐的這個跨越是他能觸動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彼得·辛格 ?Derek Goodwin
另外一個是辛格在這本書里創(chuàng)設了一些很巧妙的思想實驗。辛格也在書里提到,他使用這些思想實驗并不意味著我們在現(xiàn)實面臨的問題就是這么簡單,而是他認為一個思想實驗能在直覺上指出,我們面臨的一些倫理問題它的癥結所在。比如在這本書里,他說如果你去聽一個講座,然后在路上發(fā)現(xiàn)有個小孩兒掉進池塘里,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去救他,只不過代價是你穿的這一身西服可能就要臟掉了,那這個時候你要不要做這個決定?然后他又把這個決定引申到如果掉在池塘里的這個孩子不是近在眼前,而是遠在孟加拉或者其他的地方,那你會不會采取相應的行動。我覺得他用這樣的一個方式非常樸素的指出,至少作為一個人,如果我們承認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動物或者任何生命,都有一個能夠生活下去的權利的話,那你其實是很難找到一個能夠在這個層面上去反駁他的理由。
還有一個是辛格在書里做了很多計算,比如達成聯(lián)合國的千年發(fā)展目標需要花多少錢。結論是全美前1%的富豪每年把自己收入的15%左右捐出來。其實杰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之前也做過類似的運算,在全球范圍內,我們現(xiàn)在積累下來的財富其實是有相當充分的能力可以解決我們在現(xiàn)實中碰到的貧困等問題的。只是說我們是否擁有一個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機制。這個部分可能是辛格在這本書里面沒能去過多展開的。但即使是這樣,我仍然覺得他在這里提供了一個很有效的論證——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采取行動,不管是作為個體或者是一個機構。

杰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美國經濟學家,專長于發(fā)展經濟學,以擔任拉丁美洲、東歐、前南斯拉夫、前蘇聯(lián)、亞洲和非洲的經濟顧問而聞名。
圖源:由Palácio do Planalto,Attribution,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4194148
何流:
我從來沒有跟辛格當面相遇過,不過讀他的東西總讓我有一種特別熟悉的感覺。也是因為這次沙龍的原因,我開始想這么多年彼得·辛格對我的影響。我覺得人一生總是會讀到一些東西,看到一些事兒,這些事兒你一旦看見,你就沒有辦法再忽略。我覺得辛格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
我第一次讀到《饑餓、富裕與道德》這篇論文是我本科面試的時候,牛津的面試流程是在面試前發(fā)放一篇閱讀,然后你在半個小時里讀完它,稍微思考一下,再進去跟面試官討論,模擬以后上課的情形。當時我拿到的閱讀就是辛格這篇論文,當時我并不知道他,然后文章開頭就講1970年Bengal,我也不知道在哪,就說那兒有一場饑荒,又說如果有個小女孩掉到池塘里,那你救不救,肯定要救的,那如果你身上有一身昂貴的西裝,你救不救,那肯定也要,哪怕要毀掉這身西裝。那他問你,那現(xiàn)在Bengal就有這樣的小女孩,你只要給聯(lián)合國組織捐錢就可以救他們,然后花的錢要遠遠少于一套西裝的錢,那你救不救。

作者:[澳大利亞]彼得·辛格譯者:王銀春
出版: 三輝圖書|中國華僑出版社
我覺得他的這些推理往往都會從這些非常顯而易見的事實開始,每一步推導都看起來那么的無辜,看起來那么的正確,但最終會給你帶來一個結論,你應該顯著的貢獻出自己的金錢,顯著的貢獻出自己的生命,來幫助那些遠方的人。我覺得當時我讀到他的結論的時候是非常抵觸的,我記得我進去那個面試,跟老師說了一大堆為什么我們不應該這樣做的原因,為什么這個池塘和這個現(xiàn)實生活不一樣。然后就面試過了。大一倫理課又讀彼得·辛格,大二倫理課又讀,同樣一篇文章,100個角度,每一次寫文章都是批判彼得·辛格,都是說他這兒那兒不對,池塘這兒有問題,那兒和池塘不一樣,這個世界的是什么系統(tǒng)性的問題,所以個體應該去服從組織,讓組織去解決。遠方的人和近處的人他的道德價值就是不同的,所以應該關心周圍,對遠方有其它的責任。
我花了大學三年的時間,再加上大學之前那一年批判辛格,但我最終還是走上了他倡導的這條路。我們現(xiàn)在自己做的事情是去評估分析公益項目的有效性,去尋找最能改善生命的這些公益捐贈,我就在想我和彼得·辛格到底是什么關系。今天的觀眾可能有的沒有完全讀完辛格的這部作品,這個沒關系,他最有名的就是這個論文,他26歲寫的,現(xiàn)在已經是一個70多歲的老爺爺了,但是他還是在講他26歲寫的這篇文章。
我們到底應該犧牲多少自己的金錢、時間、資源來幫助遠方的人?可能很多人就會說慈善應該從周圍做起,遠方跟我也沒有聯(lián)系,我為什么要捐出來90%的財富去幫助不認識的人,就感覺這好像對人要求太高了,這就是彼得·辛格的爭議。有人覺得應該這么做,有人覺得不應該這么做,有人覺得應該有更好的方法。
對我而言,他是一個很影響我的人,讓我重新看待每一件我做的事情,無論是一次昂貴的消費還是其它。比如這臺電腦的話,一臺電腦一萬多,那在非洲避免一個五歲以下兒童死亡是3000到5000美金,大概兩臺電腦的錢,如果這世界每件事都可以做這樣的換算,那我們還能不能消費,我們到底應該怎么活在這個世界上,是應該把每個人都累死,應該大家都把錢都捐出來,我們和全世界最饑餓最痛苦的人一樣痛苦,這才道德嗎?這是我前幾年的感覺,我覺得也是很多人讀完辛格之后想抵抗他的原因,因為他確實要讓個人做出很多的犧牲。
但這兩年,尤其我開始做公益盒子的時候,我在想,其實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次機會,你在商業(yè)領域其實很難去挖掘這些超高額外價值的機會,比如說做股票,有無數(shù)個其他人在出現(xiàn)低買高賣的時候都會比你動作快。而在發(fā)展領域,其實有大量的這些低成本的機會,不需要花多少精力和金錢就可以避免苦難。辛格舉的例子是在非洲做防瘧疾蚊帳,過去每年有上百萬的五歲以下兒童死于瘧疾,所以在非洲發(fā)放防瘧疾蚊帳,或者維生素A補充,大概3000到5000美元,可以避免一個五歲以下兒童死亡。在中國其實也有很多類似的機會,我覺得不一定要把它看作成本,看作成本本身就已經代表了一定的態(tài)度,去幫助別人好像是自己的一種犧牲,是一種消耗,但其實是一個價值,是一個新的實現(xiàn)。

Photo by Lina Trochez on Unsplash
我覺得慢慢的我也開始學會用辛格的眼光去看世界,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可以發(fā)揮價值的地方,我覺得這也是后來我對辛格的思考。但他畢竟是個哲學家、倫理學家,他的時間并不是花在去想這個世界有什么解決方案,技術方案,貧困是哪來的,哪些方法好,哪些實驗結果靠譜,怎么做新的實驗,他講的是原則,是用這些思想實驗把這個世界簡化出來,然后從簡化的模型中推導出一些基本的做事原則,我總結他倡導的就四個字,能幫就幫。其實非常簡單的四個字,但是一說到遠方的人我們也要能幫就幫,甚至說到不同的物種,非人類的動物,我們也能幫就幫,那最后要推導出來的后果會非常復雜多樣,我覺得這也是辛格為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當然我對他也有很多批判,比如后面他講比爾·蓋茨,我覺得他可能對這些有錢人太過于寬容,他讓美國的中產一年捐助80%的個人收入,然后比爾·蓋茨捐了30%他就在這兒說比爾·蓋茨的好話,但可能對于這些超級有錢人來說,他們的義務也應該是成比例的。
02
全職公益:主動性的旅程
我覺得如果換做我在國內,在街上碰到一個外國人被警察圍著,我可能第一反應不會是說我要去站出來。所以這個事情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觸動,也包括讓我想要去嘗試一下做這方面的工作。
——黃威
李博倫:
我覺得我可能不會把自己定義成公益從業(yè)者,可能更多覺得我是從事跟發(fā)展實踐相關的。我最早關注發(fā)展領域應該是05、06年的時候,當時學校里面組織了一個讀書會讓我們讀《百年孤獨》。在此之前我對亞非拉沒有什么概念,當時讀那本書的同時也看一些相關的評論,看得多了之后才大概能明白。因為這跟我了解的歐洲、美國、東亞其實挺不相同的,所以就有很多的好奇心,拉美是什么樣的?非洲是什么樣的?東南亞是什么樣的?基于這個好奇心的驅使,就讀很多非洲、拉美的人物傳記,小說,就這么進入了這個領域。
讀大學的時候會有一些困惑:到底應該做什么工作,從事什么樣的行業(yè)?當時也讀了很多書,其實很多都是我覺得可能像三輝會出版的書。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家們會思考是應該留在自己的部落去做好部落的事情,還是要走出我自己的社區(qū)或國家,去更好的去服務這個大洲或者國際的事務。這些閱讀挺觸動我的,我當時想即使我之后從事中國本土的工作,也想去更廣闊的世界走一走,所以后來就通過各種機會去了很多的國家和地區(qū)。從2012年到2016年,這段時間就在各個國家瘋狂的走,去了亞非拉的五六十個國家。
我最早的時候其實想去一個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但是后來也做了很多反思,覺得自己還蠻適合做一些新的東西,一個方面是因為個性,我經常會和別人有不同的觀點,另外一個就是看到行業(yè)里面的一些問題,更希望去做一些自己的試驗,嘗試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帶著這些想法開始了一些創(chuàng)業(yè)的實踐。最早是在讀書期間就開始做一些,但是當時的工作并沒有做得很好,一些項目后來就無疾而終了,但累積了一些經驗。
五六年前開始做現(xiàn)在的這個組織,其實也還是在這個領域里面慢慢深入。個人的關注點也更多的是從微觀角度關注在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領域的這些創(chuàng)新者、基層的從業(yè)者、社區(qū)的工作者……他們怎么樣能夠更好的獲得一些支持,怎么樣更好的去發(fā)揮他們的創(chuàng)意,以及怎么樣能更好的和現(xiàn)有的一些政府部門、企業(yè)投資和國際合作接軌。這些年基本是在這樣一個螺旋式的軌跡中曲折的上升,不斷的去完善自己的工作。
黃威:
我接觸公益的時間可能會比博倫稍微晚一點,2013到2017年這段時間我在學校,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公益類的項目。最開始讓我有這個想法的時機,也有點契合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我去塔吉克斯坦的時候。當時是學校里有這樣的一個類似于國際義工的機會,去塔吉克斯坦教語言。最初的感覺是這是一個我一輩子都不會想到要去的一個國家。所以最初就是帶著這樣可能是好奇的一個想法就去了。大家知道中亞有五個斯坦,我去機場的時候在路上跟司機聊天,他問我要去哪兒,我說塔吉克斯坦,然后司機的第一反應是,哦,你說的那個哈薩克斯坦。你會發(fā)現(xiàn)大家其實連這些國家的名字都叫不清楚。
塔吉克斯坦有一些前蘇聯(lián)遺留下來的問題,也存在政治上的不穩(wěn)定和腐敗等問題。比如塔吉克斯坦是可以強制征兵的,如果說你沒有在學校讀書,又不是家里的獨子,部隊每天開著兵車在街上找這樣的人,找到了他是可以直接把你帶到部隊去的,然后再通知你的家人說你的孩子在我們這兒,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而且因為基層的警察薪水不是很高,就導致大量的腐敗情況出現(xiàn)。
我在塔吉克斯坦呆了一個多月,差不多每周都要體驗兩三次被警察攔住查簽證護照同時索賄的情況。有一天晚上十點多我上完課回家,被六七個警察攔住查我的證件。我平時一貫的反應是假裝聽不懂,但那次他們當時就打算把我?guī)ё撸鋵嵲诨鶎泳焓菦]有權力去查這個東西的。他們正要把我?guī)ё叩臅r候,旁邊路過了一個塔吉克斯坦大叔,他看到我一個人被六七個警察圍著就進來問發(fā)生了什么,然后他正好有一個中國朋友,他就給那個朋友打電話,讓朋友問我到底是什么情況。在我解釋完后,他選擇了幫助我這個遠方的人,他當時站在我面前跟六七個警察爭執(zhí),最后把我的證件要回來了。我覺得如果換做我在國內,在街上碰到一個外國人被警察圍著,我可能第一反應不會是說我要去站出來。所以這個事情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觸動,也包括讓我想要去嘗試一下做這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個契機就是我之前一直想要做戰(zhàn)地記者,當我在媒體實習了之后,還是覺得希望做更實際的工作。所以我的研究生選擇讀了跟社會工作相關的專業(yè),學習了暴力預防這樣的一個方向。開始是在社區(qū)里做暴力預防的工作,后來也去了政府間的國際組織。最后我覺得也不是說我選擇了公益,可能也是機會使然。最早加入共同未來是做志愿者,有一次去參加一個活動,碰巧共同未來在那里擺攤,我就發(fā)現(xiàn)原來國內還有一個組織是在做難民援助相關的工作,到去年的時候回來開始全職,因為我覺得比起做政府間組織的這種協(xié)調性的工作,我可能還是更喜歡做一些直接服務的工作,共同未來是一個不錯的可以讓我嘗試的平臺。
何流:
做公益很多時候是基于對遠方的理解,然后再去做事兒,我覺得好像這個框架可以套到我身上,但我覺得我更多的是基于一種不滿,所以才想做現(xiàn)在的事情。我最早做公益的時候,應該跟多數(shù)人都一樣,就是上學的時候。那會兒上中學,要感謝我的前女友,因為當時我們那個學校里就有一個每周都要去當?shù)鼐蠢显旱幕顒樱敃r我喜歡這個女孩兒,她每周都去,為了表現(xiàn)自己的善心,創(chuàng)造跟她接觸的機會,我也跟著去。然后就去了兩年,我從一個志愿者,慢慢就變成這個學校社團的負責人,到后面帶著那個當?shù)氐睦先撕凸聝旱綄W校里參加音樂會,幫他們籌款,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到我畢業(yè)把這社團交給下一屆的時候,我就開始想這兩年花了這么多精力,為這些人做了這些事情,我到底有沒有讓人家的生活變得更好?就感覺自己像是走了一場旅行,這場旅行里面,我看見了不同的風景,不同的人,做了一大堆事兒,鍛煉了我的能力,但是他們的生活好像是一樣的,他們依然需要關懷,持續(xù)的關懷。有些六七十歲的老人是有智力障礙的,有時候這周看見你,下周就不記得了,這周跟你玩兒,下周可能就跟你發(fā)脾氣。所以我就在想,我花這么多精力到底有沒有幫到人家。慢慢的,公益對我來說,就從一個滿足善心變成了一個有點像對自己的思維挑戰(zhàn),我到底怎么能把這事做得更好。
在本科的時候,我也去云南、非洲等地的村里,做各種各樣非常實際的項目,但每個項目做下來我都覺得好像做的還不夠,有做的更好的方法。因為我的社會關系,因為我看到了這個機會,因為學校有這個廣告,所以我就能參與,但這個是我能對世界發(fā)揮最好作用的事兒嗎?好像非常的不確定。就在那會兒我在網(wǎng)上看到Givewell,辛格這書里也提到了美國的這個組織,在全世界去分析往哪兒捐錢社會回報最高,最能夠改善生命。當時就讓我覺得眼前一亮,原來做公益還可以系統(tǒng)化的做,而不是說我關心什么議題,或者我恰好看到什么信息,我恰好對什么東西感興趣我就去做這個領域,而是說可以比較客觀的去看全世界有哪些問題,有哪些可解決的方法,我們能做什么,成本效益怎么樣,所以我覺得這套理論其實對我影響特別大。我就從一個最早時候的有志青年變成了一個混沌青年,然后再看到了一點希望,感覺這世界還是有點能做的事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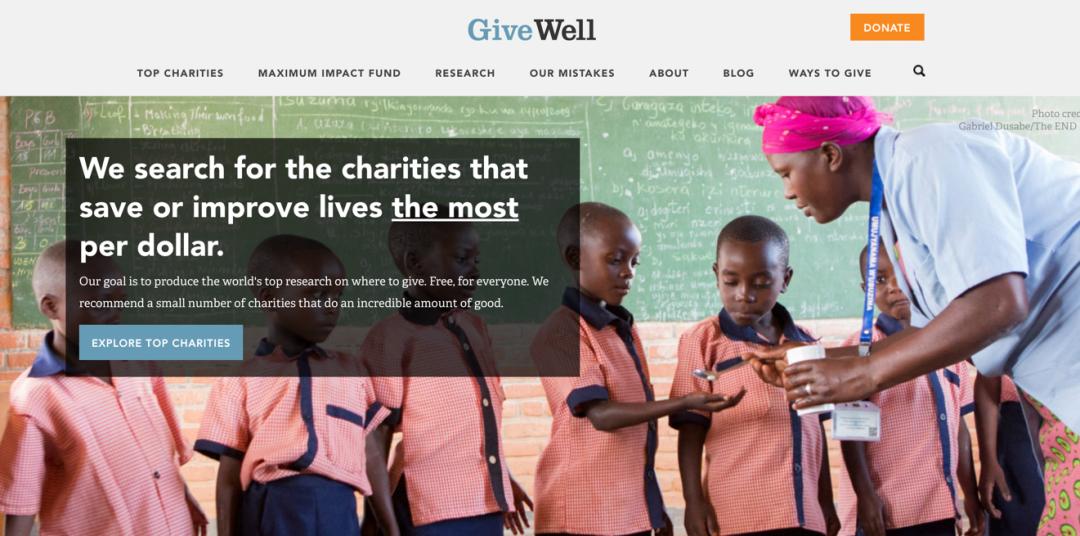
Givewell(https://www.givewell.org/)網(wǎng)站截圖
其實這也是我和共同未來的緣分,那個時候我正好在牛津遇見了劉毅強,我在牛津辦論壇,他過來做嘉賓,我覺得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正經做公益的人,之前我沒有認為這是個選項,就是公益行業(yè)在那兒,有一群人,他們吃土,他們很苦,他們?yōu)榱诉@個世界,特別有愛。2018年接觸的劉毅強,然后2019年共同未來獲得聯(lián)合國咨商身份,我還“尾隨”他一塊兒去瑞士開會。這讓我意識到,原來公益是個可以做的東西,不是報紙里寫的。我本來就很熱愛創(chuàng)業(yè),又想做對世界有價值的事情,知道了原來這還可以當一個職業(yè)來做之后,慢慢就有了公益盒子。我相信在未來我一定還會遇到一個瓶頸,可能又需要某種新的突破,但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公益盒子是我的最新的突破。
03
未定型的公益組織:工作方法與成長之路
主持人:
在《饑餓、富裕與道德》這本書當中,安德魯·庫珀(Andrew Kuper,LeapFrog Investments創(chuàng)始人)在針對辛格《饑餓、富裕與道德》一文所寫的一篇相對持批判態(tài)度的文章中提到:“采取何種方式解決貧困問題是一個關乎判斷的問題:理解社會系統(tǒng)或情境的相關特征;考慮哪些原則與其相關,它們是否在實踐中提出了相互競爭的需求,其他主體可能會如何行動;以及最后,依據(jù)行動的情境進程做出判定。想請問三位所在的組織所致力于解決的具體問題是什么?你們是怎么理解這些問題背后的社會情境的,以及你們和團隊經歷了什么樣的過程來做出判定?

安德魯·庫珀是新興市場投資公司LeapFrog Investments的創(chuàng)始人兼首席執(zhí)行官,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教員,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他還擔任卡內基倫理學與國際事務委員會高級顧問,也是庫珀研究所(一家媒體與社會政治學領域的咨詢公司)的聯(lián)合主管。
這個培訓現(xiàn)在做了五年的時間,共九期,這些人有的來自于聯(lián)合國機構,也有很多來自于各個社區(qū)層面。我們在開會的時候,可能就能聽到所羅門群島的叢林和海風的聲音。通過這些工作,我們是嘗試通過更多的合作來實現(xiàn)這個目標。我想從一些很感性的角度去想,也是有意義的。
——李博倫
李博倫:
首先我不覺得我們組織是解決貧困問題的,解決貧困問題非常復雜,可能歷史上很多學者和實踐者都力圖解決貧困問題,包括黃威剛剛提到的杰佛瑞·薩克斯,他在非洲有一個很有名的千禧村項目,但后來評估的話,沒有特別成功。我覺得相對來講,我們在成立之初所定義的解決的問題是新興國家當?shù)氐囊恍┗鶎觿?chuàng)新組織的賦能。
最早是潘基文做聯(lián)合國秘書長的時候,他創(chuàng)設了一個叫聯(lián)合國青年問題特使辦公室,邀請很多的青年人參與關于國際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的咨詢,這個事情我參與了蠻多的,后來就借助了相關的網(wǎng)絡發(fā)起了一些亞太地區(qū)的青年組織,也因此有機會和當?shù)氐囊恍┣嗄耆巳ソ涣鳌N野l(fā)現(xiàn)大家有很多有創(chuàng)意的想法,他們比那些國際援助機構更了解自己的社區(qū),也能夠更真切的去定義他們所在社區(qū)面臨的問題,并更多的和社區(qū)的一些關鍵領袖進行交流,我覺得他們的這些項目其實是更有可能在被賦予同等程度的資源的情況下獲得成功的。當時我很感興趣的問題是,是否有一些方法可以更多的去和他們產生直接的交流合作?我們組織在最早的發(fā)起階段所定義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成立后,我們最早的一些試驗和合作是在東南亞國家完成的,因為我們最早的創(chuàng)始團隊國籍會非常多元,現(xiàn)在也還有四個國籍。當初的想法其實蠻多的,第一,我們是不是可以幫助他們去做更多的媒體倡導和宣傳;第二,我們是否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更多的捐贈。后來我們也做了很多嘗試,比如說一個工作就是,我們會為一些當?shù)氐倪@種創(chuàng)新組織制作視頻,用講故事的方式去呈現(xiàn)這樣一種推廣的素材,幫助他們去認識到一些目標受眾。有一個例子是緬甸有一個做教育科技的組織,他們希望能夠把虛擬現(xiàn)實和3D打印的技術融入到教學材料中,幫助緬甸最偏遠的一些山村的孩子了解最先進的教學。當初他們也是一個初創(chuàng)機構,我們和他們一起合作做了很多這種相關的創(chuàng)意設計。因為他們的產品具有一些可視化的屬性,所以后來通過一些倡導工作,獲得了緬甸當時教育部的采購,也成為了緬甸的一個明星社會企業(yè)。
與此類似,我們覺得其實也可以去培訓一些在各個國家的年輕人,他們第一對在自己的社區(qū)創(chuàng)業(yè)感興趣,第二又能夠去開展一些傳播倡導。其實國際發(fā)展里面有一個模式叫TOT(training of trainers),也就是說為培訓者去做培訓,所以基于這樣的一個理念,我們當時就做了一個叫做全球通訊員的項目,去各個國家尋找一些既有對于發(fā)展領域的熱情,又通過一些創(chuàng)意或寫作的方式去做傳播的人,去對他們開展一些媒體培訓。這個培訓現(xiàn)在做了五年的時間,共九期,這些人有的來自于聯(lián)合國機構,也有很多來自于各個社區(qū)層面。我們在開會的時候,可能就能聽到所羅門群島的叢林和海風的聲音。通過這些工作,我們是嘗試通過更多的合作來實現(xiàn)這個目標。我想從一些很感性的角度去想,也是有意義的。
當然我們也會去思考怎樣幫助這些組織獲得更多的支持。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我們也做過一些技術類的平臺,但是后來不是很成功,沒有繼續(xù)下去。我們也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投資者,幫助傳統(tǒng)的捐贈者去更好的進行工作,所以后期從2018年開始,也是因為中國慢慢的成為了一個新興的援助國,在一帶一路國家開展很多的工作,我們也和一些官方機構合作,去開展更多在地的執(zhí)行和研究工作。
這些是在這個歷程中我們做過的一些事情,以及我們怎么去理解我們的工作,當然其實每過一年,我們的目標都在重新被定義,我們做的工作也在不斷的調整和豐富,有的時候也會有一些改變,但是我們依然懷有著初心,在面對很多挑戰(zhàn)和困難的時候,也希望能夠力圖去實現(xiàn)最初設立的目標。
黃威:
我覺得共同未來在在地性這一點上跟Diinsider的一些想法是很相似的,當然我們的角色可能不太一樣。摘錄的庫珀的這段話也挺好的,這個也是他對辛格的一個反對的點,就是說當號召大家捐贈的時候,辛格可能沒有意識到公眾在捐贈的時候,需要理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區(qū)之間,是怎樣復雜互動的。比如說我今天買了一個蘋果的手機,它其中的芯片可能是用來自于剛果金的礦石制作的,而剛果金的采礦行業(yè)蘊含了大量對童工的剝削,不管是勞動的剝削還是性剝削,也可能涉及到這個國家內部的沖突等一系列的問題。或者比如說在美國或者是國內買寵物罐頭,這個罐頭里的魚可能是泰國的魚奴被奴役的產物,他們被囚禁在船上或者是無人島上,被迫的為他們的主人進行免費的捕撈工作。在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下,當我們去消費的時候,其實很多元素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
《血與大地》便是對這一勞動生產網(wǎng)絡的調查報告,點擊圖片查看相關推動
那說回到這個問題,當你真正的開展援助工作,會碰到很多的阻礙,比如說辛格提到的發(fā)蚊帳,但是蚊帳可能會被受助者拿去捕魚用或者這個受助者根本就不會使用這個東西去防蚊蟲。再比如說在孟加拉的一個村子里要去教會這個媽媽怎么給他的孩子提供營養(yǎng)的膳食,但這個媽媽可能會因為你在這里對她的育兒方式指手劃腳而非常生氣,從而不愿意聽從你的任何的指導。包括蓋茨基金會之前做的一個項目,在一些非洲國家設置公共廁所,但是公共廁所的這個使用的習慣本身是從西方傳來的,在部分的非洲國家和地區(qū),人們如廁的方式可能跟西方傳播而來的這種完全不一樣,那要怎樣讓人們產生行為上的改變?很多這樣的細節(jié)問題都是需要去不斷的發(fā)現(xiàn)和解決的。
那么對于共同未來來說也是這樣。我們最早想要去做的,其實是關注難民——受到暴力沖突影響被迫遷徙的這樣的一個人群,尤其是其中的兒童和女性。我們最早關注的是這些人受教育的權利,也包括工作這種發(fā)展性的權利。在最初之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關注點,是源于2015年歐洲的難民危機。可能還有朋友會有印象,當時有一個照片是一個兩三歲的敘利亞的小男孩艾蘭·庫爾迪,他的尸體在土耳其的海灘上被發(fā)現(xiàn)。最早也是因為這個照片,當時共同未來的創(chuàng)始人Michael帶著自己的律師包括記者朋友首先到歐洲做了一系列的調研,然后發(fā)現(xiàn)難民危機最嚴重的地方其實不在歐洲,而在敘利亞的鄰國,有幾百萬的難民在那里尋求庇護。比如說在土耳其可能有三四百萬,然后在約旦、黎巴嫩。在黎巴嫩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因為暴力沖突而遷徙,可能是敘利亞人可能是巴勒斯坦人。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我們就決定在敘利亞的鄰國開展一系列的更具體的調研工作。最開始的時候,在寒暑假,我們會派國際志愿者到前線去提供服務,包括為兒童提供藝術療愈和教育和陪伴,這個過程其實跟何流剛才提到的一樣,就是你做這個工作到底是為了自己開展事業(yè)還是真正有效的去幫助到你的服務對象。在很多的國際發(fā)展或者說國際義工領域,大家會去討論你是不是在做一個志愿者旅游,就是可能只是志愿者在享受這個過程而沒有真正幫到服務對象。
當時也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希望第一能夠把短期的項目變成長期的項目,第二是在我們服務這些難民兒童的過程當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一方面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對他們的影響很大,另一方面對照料者的影響也特別大,比如說很多母親她們自己也遭受了創(chuàng)傷的影響,她們的丈夫可能在戰(zhàn)爭中失去生命,或者她們的親人被迫流離失所。同時她們也面臨著經濟上的壓力,比如說她到了土耳其或者黎巴嫩,在這樣的一個國家,他們的身份并不是難民署認定的難民,更多的時候是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是沒有辦法獲得工作許可的。再加上很多工作行業(yè)非常排斥女性,也就是說這些媽媽可能無法有收入來源。在這樣的情況下,巨大的生存和經濟上的壓力會進一步影響到她們對孩子的照料。
考慮到這些方面,在2019年的時候,我們在黎巴嫩開了我們的前線項目,這個項目一方面圍繞對于兒童的語言教育,另一方面是圍繞女性的,比如我們會提供縫紉的職業(yè)培訓,幫助她們宣傳手工藝品,也會嘗試幫助她們對接一些渠道,包括在中國進行部分銷售。同時我們會把銷售所得返還到項目的使用中去。在這個過程中還是會碰到很多其他的問題,比如說產品的跨國運輸、成本的控制、如何能構建一個可持續(xù)的援助工作的模型,這些問題很多是我們現(xiàn)在仍然在面臨的。所以每個階段我們都在不斷地發(fā)現(xiàn)新的問題,然后思考如何調整我們的方法去更好的幫助到服務對象。
何流:
先說安德魯·庫珀,其實我覺得他的文章里有很多正確的廢話,所有人都會同意這個貧困問題關乎判斷,然后要理解特征,考慮什么東西相關,什么東西有什么具體的需求,怎么行動。我讀完他這篇文章,很多地方其實都有這種感覺,這里面有好多大詞兒,但是他好像并不是在針對辛格,這里也沒幾句話辛格真的會反對。
我們不應該把辛格想象成他要代替全世界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這么多人在琢磨怎么消滅貧困,然后突然辛格站起來說,只要每個人捐錢就行了,這不是辛格的價值,他也不是想干這個事兒。當時他26歲哲學系剛畢業(yè),想著怎么跟夫人分配一生的收入,所以安德魯·庫珀去批評他這個方法就好像說邊上有個池塘,我說我應該跳下水救,然后有人說你為什么不開快艇呢?如果開快艇有效,我們也開快艇,根本的這個爭議在于原則,但是安德魯·庫珀好像并沒有直接跟原則發(fā)生碰撞。那另一種理解安德魯·庫珀的方式就是其實他和辛格距離沒那么遠,辛格講我們有責任幫助窮人,那安德魯·庫珀講我們應該尋找最好的技術方案,尋找有效的方法,不能全靠熱情,全靠對于道德的理解,還是要冷靜一點把資源分配好。我覺得這個是所有人都會同意的。
從我們的工作來講,其實我們也是想把這件事兒做好,就是想把慈善資源分配好,尋找真的可以幫助到別人的機會。Givewell在全世界發(fā)現(xiàn)救命的最好的辦法。那公益盒子的問題就是,在中國怎么樣實現(xiàn)社會價值的方法最好,或者哪些公益組織的成本效益最好。我們之前也做了一個議題分析,發(fā)現(xiàn)了17個衛(wèi)生健康方面的干預措施都有非常好的成本效益,也有相應的公益組織在做,包括白內障手術、兒童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減鹽、母乳等。所以我們把這些公益項目的背景調查做好,看哪些最值得捐贈。

Photo by Shane Rounce on Unsplash
那我們和辛格有什么關系?我覺得一方面可以把我們看作一種傳承,以這樣有效利他、講求證據(jù)和有效性分析的這種流派去做公益;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對他的一種挑戰(zhàn),對于辛格來說,或者對于很多在國際上去看怎么能把錢捐好的人來說,中國可能不是最優(yōu)先的地方,非洲是,東南亞是,因為這些地方看起來還有非常簡單就可以去避免的苦難,像Givewell常年都推薦非洲。之前我們也聊過,他們覺得中國的問題其實是不是都解決的差不多了,也不需要我們來幫你看,你的政府很強,民間力量很強,收入水平很高,那中國真的這樣嗎?我相信就是在中國的鄉(xiāng)村里或者低收入地區(qū),你走一走,中國不是那樣的。很多老外覺得中國已經發(fā)展的很好了,北京上海就能代表中國,差一點兒的成都、武漢至少是中國平均水平。大家都看到中國這個樣子,肯定覺得非洲更重要,我們是覺得其實在中國還存在很多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解決的民生問題。如果是一個全球視角的話,也應該多關注中國本土的,它是具有世界性的意義的。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