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劉少雄:宋詞代表了中國文化陰柔中的韌性
劉少雄,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從事詞學及“東坡文學”研究、教學三十余年,其在臺大開設的唐宋詞、東坡詞課程廣受學生歡迎,其后錄制的《東坡詞》《宋詞之美》《唐宋詞的情感世界》等公開課及音頻節目也受到網友好評。今年,他的《蘇軾詞八講》《傷離別與共春風:至情至性唐宋詞》先后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發行。近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就詞學相關話題采訪了劉少雄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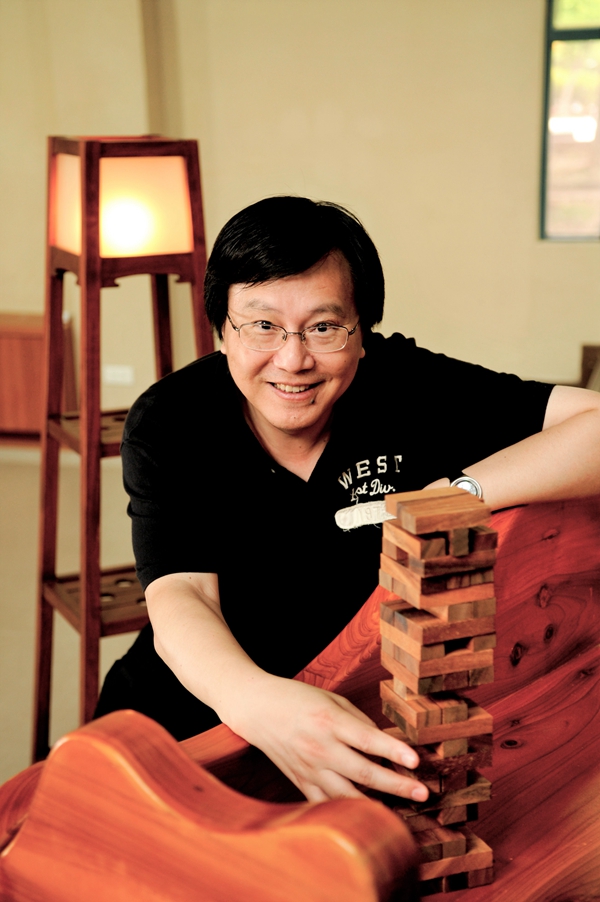
劉少雄教授
澎湃新聞:您的書中有一個核心觀點是:“宋詞代表中國文化陰柔的一面”,但卻是一種“陰柔中的韌性”,呼應著宋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入世情懷,請問這應該如何來理解?
劉少雄:詞原是都市文明發展起來后的一種配合音樂而歌唱的詩,由樂工、歌女在坊肆表演傳唱,它的內容,寫景多不出閨閣庭園,言情則不外傷春怨別,遂表現為一種精微細致、含蓄委婉、富于陰柔之美的特質。一般的文人詞通常是以吟詠“好景不常、人生易逝”之哀感和“此情不渝”的精神為主旋律;前者乃意識到變化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后者是不忍放棄的執著情懷,兩相激蕩而產生一種抑揚頓挫的節奏,詞之美就美在有著這樣的情辭跌宕的意態。而這跌宕之姿,我以為是與整個宋代文化氛圍所形成的精神特質相呼應的。
我們都知道詞這一種文體最長于言情,如果說宋朝是以詞為代表文學,那么宋人多情便不言而喻了。宋代的偉大心靈、杰出文人幾乎都曾填詞,在他們的詞里歌詠著種種親友之愛、男女之情,及家國之思、故鄉之念,充滿著人情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悲歡離合、盛衰哀樂的情懷。宋人多情,是不爭的事實,充分體現在詞的寫作中。歐陽修說:“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柳永說:“多情自古傷離別。”東坡說:“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多情,難免帶來煩惱,但也只有情能讓生命展現光彩,不至于枯萎,并能見證生命的意義。宋人多情,也長于思辨,在詞的世界里,他們所抒寫的情,所呈現的意境,有多樣的姿態,或表現為執著的熱誠,或表現為豪宕的意興,或表現曠達的懷抱,展現出各種跌宕的情思,充滿著興發感動的力量。我們細讀兩宋名家詞,既感受他們真摯的情,也能從中體會宋文化的特性。
宋代以文立國,看似卑弱,其實內里卻有著一種堅韌的精神支撐著。宋朝自建立統一政權以來,即處于相當艱難的境地,內部積貧難療,對外積弱不振,不若漢唐之富強。然而國勢貧弱的宋,卻是秦漢統一王朝之后,年祚最長的朝代。兩宋周邊環伺的敵人,都非等閑之輩,先后是遼、金兩大強敵,最后面對的則是橫掃歐亞的蒙古。北宋為金所滅,宋室南渡,雖失去半壁江山,但也支撐了頗長的時間。錢穆《國史大綱》說:“在蒙古騎兵所向無敵的展擴中,只有中國是他們所遇到的中間惟一最強韌的大敵。”可見宋絕非不堪一擊的弱國,仍有它頑強的一面。這種國族精神,也反映在宋代整個文化當中。鄭騫《詞曲的特質》說:“宋朝的一切,都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陰柔方面,不只詞之一端。……柔并不一味的軟綿綿,而要有一種韌性。”宋詞代表中國文化陰柔的一面,但所謂陰柔不是一味的纏綿軟弱,而是要有一種堅定的生命力,可稱之為“韌性”。詞有韌性,才能成為文學之一體。這種韌性,來自認真熱誠的生命意態,不屈不撓的精神,抒發為文自有一種格調,一種骨氣。詞雖寫感傷之情,但名家之作普遍都不卑下,反而筆力沉健,抑揚有致,正因有這韌性在。宋詞里所表現那種執著的信念——即使歲月多變,人事難料,但此情不渝——正呼應了宋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入世情懷。如同像野草一般,柔中帶剛,總有著無窮的生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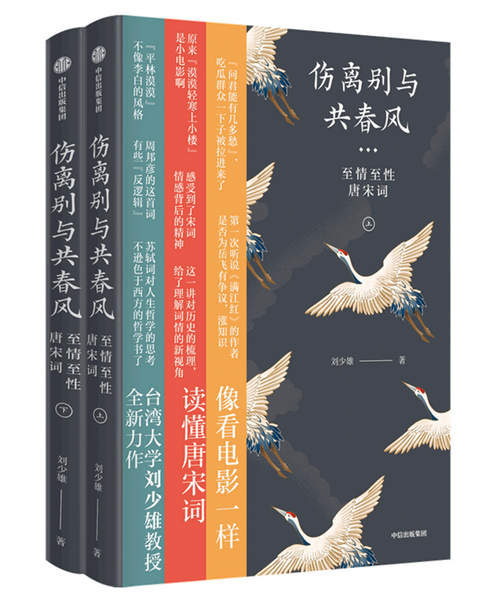
澎湃新聞:《至情至性唐宋詞》中辟有專章討論宋詞里的時間意識,包括東坡詞中的時間感您也多有著墨,但是時間意識在中外諸體文學中普遍存在,在您看來,宋詞中的時間意識有何特別之處嗎?
劉少雄:感時傷逝本是中國古典抒情文學的重要主題,詞也不例外。詞基本上是配合當時的流行音樂而填寫的,音樂乃時間的藝術,而流行音樂所依附的商業都市而產生的時間觀,和《詩經》、樂府的樂調所依附的農業社會而形成的時間觀不盡相同。物質文明世界帶給文人心理的時間焦慮感特別強烈。中唐以后,考科舉入仕普遍成為讀書人的主要出路,他們的生命成長便無形中納入一個相對固定的模式里,大家都有著相類似的進階歷程,如能在合理的年歲如愿考試及第并進入官僚體制,那人生便有了保障,可是競爭激烈,仕途難料,失敗和失意的人畢竟居多,這些人流落異鄉,或者終日流連坊肆,到最后自感懷才不遇的讀書人更能體認自己的命運原來與擔憂年老色衰的歌女沒什么兩樣。白居易《琵琶行》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就說出了男女的共同悲哀。由此可見,文人詞從中唐開始逐漸成形,不是沒有原因的。詞人在時空流轉中產生的悲感,多偏向陰性自我的顯露,接近于女子的心性,因此在詞的創作中常有“男子而作閨音”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詞人所代表的是一種細膩、敏感的生命型態。
時間之傷,可以說是詞的主調,它與其他文類最大的不同處是它獨特的表現方式。詞的抒情性,主要是以時空與人事對照為主軸,在情景今昔、變與不變的對比安排下,緣于人間情愛之專注執著和對時光流逝的無窮感嘆,美人遲暮、年華虛度、往事不堪、理想成空等情思遂變成詞的主題。而詞的體制,如樂律章節之重復節奏、文辭句法的平衡對稱,更強化了這種婉轉低回、留連反復的情感韻味,極富催化感染的作用。因此,詞的情韻,就是一種冉冉韶光意識與悠悠音韻節奏結合而成的情感韻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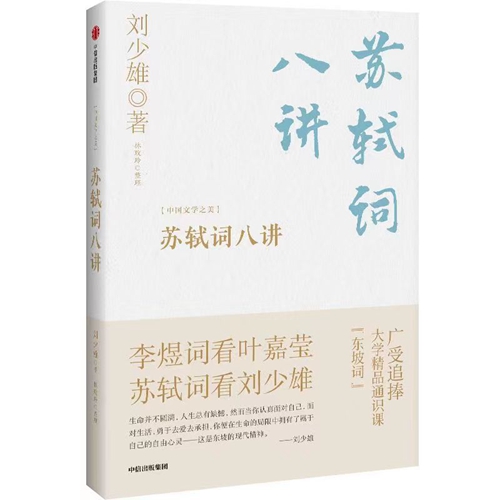
澎湃新聞:關于東坡之“以詩為詞”的爭議和討論是蘇軾研究中的老問題了,您在書中是以完全正面的角度評價這個問題的,是不是可以說,“以詩為詞”恰恰是蘇軾開拓宋詞格局的關鍵?
劉少雄:東坡以詩為詞,在詞須合樂的辨體意識中,確實被認為非當行本色,乃詞的一種變體。但若從詞的文學性而言,東坡以詩為詞,卻提升了詞的意境、開拓了詞的格局。
首先要知道詞至東坡,能在本質上產生一大變化,關鍵是東坡其人及其為文態度。東坡之所以能移風易俗,變“謔浪游戲”之體,為抒情言志的長短句,“指出向上一路”,“使人登高望遠”,這與他的出身、才學及創作心態有莫大的關系。人格決定詞格之高下,而詞格的高低,則影響詞體的尊卑。東坡從未以詞人自居,他始終保持大學士、大詩人的高雅品味,不故意避俗。他以真誠的態度寫作詞篇,對詞體的看法自然不同于流俗。所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東坡這種不主故常,于法外求變的創新精神,當然也貫徹于詞的寫作中。正因為他這種“吾道一以貫之”的精神,遂能將詞提升至更高的境界,寫入了一己的高尚情操與真實情感,詞體便能因人而貴,得以晉身詩歌之林。
東坡以詩為詞,不可諱言,剛開始時受到本色派的質疑,曾引起一番討論,但南渡以后的詞壇,受到時世的影響,大家對東坡詞便有了不一樣的認識及評價。當時,以詩的觀點作詞、論詞已是普遍的現象。東坡作為一般士子景仰的人物,他的詞作別具指標性的作用。以詩入詞,或以詩之余力為詞,這些說法后來演變成“詩余”的概念,一時大為流行。稱詞為詩余,在南宋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因為將詞與詩拉上關系,無疑也提高了詞的地位,使它不再局限于歌兒舞女的藝壇,更納入了文人的創作范圍,而更重要的一點是這種說法寬解了文人原先視詞為小道的心理,正式承認了其文體的價值,從此詞的發展便更為蓬勃,于是乃有辛棄疾、吳文英等致力追求新意境的專業詞人出現。
東坡“以詩為詞”真正的意義,不僅僅是“寓以詩人句法”,使詞“精壯頓挫”而已,更重要的是內容題材的擴大、精神意境的提升。用詩的句法句式入詞,或以脫胎換骨的手法融化前人詩句,或如詩一般地使事用典,都能增加詞的藝術效果,使詞質更為凝練、詞句更加妍美、詞意更形豐富。另有一點,詞本管弦冶蕩之音,容易牽引情緒,使人陷溺于旖旎、幽怨、傷感的情懷里,而詞既與樂合,則可近雅卻又不能遠俗,人在如此氛圍中,日久浸淫,自嘆自憐,恐怕也會消磨了壯懷逸志。東坡“自是一家”的醒覺,就是要從這一陰柔細致的世界中走出,不耽于音聲,不陷入悲情,這是“以詩為詞”值得注意的一個層面。
總之,東坡“以詩為詞”,藉詩理、詩趣來提升詞的意境,如是,詞的情韻便能多一份思致。這詩化的意念,正可看到東坡協調情理以求得內在生命之安頓的一番努力。
澎湃新聞:您在《蘇軾詞八講》中援引夏敬觀《手批東坡詞》的話,認為:“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而一些以往作為其豪放詞風代表的“激昂排宕”之作卻被認為“乃其第二乘也”,比如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您能就此給我們做一點簡單的析解嗎?
劉少雄:詞以言情見長,而所言者多為男女情事,個人身世之感、時空流轉之嘆。詞以妍雅精致之筆觸,配以拗怒柔婉的樂律,開闔轉折間,時空之感悠遠深長,纏綿幽怨,含蓄委婉,最能發揮中國文辭的抒情特性。就是說,婉曲之美,是詞體的基本特質,在神不在貌,無論寫兒女之情或士人之思,代擬或自述,應社或抒懷,傷春怨別或詠物紀游,凡屬詞體,這種情辭本質不可或缺。詞人或可藉詞言志,說理議論,發為豪放之調,但如過于直切而不能道出深細要眇的情思,則往往會被認為終究略遜于本色之作。的確,詞體作為一獨立的文體,雖然可與詩文交接,存有新變的空間,但亦必有不容改易的本質。所謂婉轉曲折,就是詞這一抒情文體最基本的言情模式。如我在書中所說,東坡這首《江城子?密州出獵》由射虎打獵寫到抗敵保邊,抒發老而能用的壯懷,語意激昂。東坡已有年華漸衰之感嘆,又有不甘牢落而意欲奮起的斗志,一上一下之間,身與心的沖突對抗,展現出一種氣韻,跌宕出一份豪情,因此成就了這首詞。但這種抗老的執拗態度,容易造成精神緊張,而過度流蕩激情必然暗指生命的摧折,東坡實在無法長期負荷。畢竟,這只是東坡一時氣盛之作,豪放終非東坡的個性特質。夏敬觀說:“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東坡這類作品其實數量也不多。
澎湃新聞:蘇辛對比也是詞學中大家一直津津樂道的話題,您在兩本書中有兩處蘇辛的對舉頗有意思,一是說所謂的“春女思,秋士悲”,辛棄疾更類女子春情,而蘇軾更近秋士悲懷;二是引鄭騫先生的話,認為蘇軾是“從窄往寬里寫”,而辛棄疾恰恰相反,這兩點乍看來都有點挑戰我們對稼軒詞的認知,您能大致說明一下嗎?
劉少雄:古語有云:“春女思,秋士悲。”女子春日情懷,其實最能象征詞的情韻。春天是一個奇特的季節,處處鶯飛草長,充滿著生機,氣候卻不穩定,陰晴難測,變化多端。因此,大地雖長出許多花草,冒出無數新芽,可是這些植物能否順利生長,卻充滿著變量,難以逆料,所以春天雖生機盎然,卻也有幾分渾沌。身處其中,既感受到生命的喜悅,享受著青春的甜美,又有些隱憂,怕春光易逝,好景不常。這如同女子的心情,一方面自盼自顧如春花一般的美麗年華,但又擔心春花不見采,美人遲暮。這種既感受美好又猶疑不安的情緒,就是春情,也是詞里最重要的一種情緒。
所謂春秋代序,春與秋分別牽引出不一樣的情懷。從心理層次去看人生意境的一種分別,秋天乃是屬于士大夫的情懷,是懷抱理想的士人,走到中年,回顧一生的情懷。時序入秋,一年也就過了大半;人到中年,一生也已過半。而秋天是農家收獲的季節,相對于此,中年檢視一生,卻發現自己理想落空、功名無望甚至有家歸不得的士人,面對寒冬將至,暮年不遠,那悲感是非常深切的。例如,宋玉的《九辯》和杜甫的《秋興》八首,都抒寫了這種悲秋的心情。通常來說,詞比較多寫傷春之情,而詩則多述悲秋之感。我們讀宋詞會發現一個現象,就是東坡以詩為詞,他的詞很少傷春之作,反而秋夜抒感卻寫出了新的意境,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永遇樂》(明月如霜)、《念奴嬌》(大江東去)等篇皆是;可是,稼軒表面上是一個英雄豪杰,其實他的情思比東坡纏綿,他寫了好多傷春、惜春之作,名篇如《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祝英臺近》(寶釵分)就是代表。換言之,稼軒能寫春情,他的心性比東坡更近于詞,因此他更能掌握詞的體制形式,其規律之精嚴,針線之細密,簡直可與清真、夢窗一較長短,我們細讀他的長調就可知曉。蘇辛并稱,而同中有異,異點之一就在規律。
至于蘇辛豪曠之辨,我頗贊同鄭騫先生的看法。他在《成府談詞》說:“王國維《人間詞話》云:‘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拈出豪曠二字,與白雨齋持論暗合。予謂:曠者能擺脫,故蘇詞寫情感每從窄處轉向寬處。豪者能擔負,故辛詞每從寬處轉向窄處。蘇《滿庭芳》‘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一首,是曠之例證。辛《沁園春》‘老子平生,笑盡人間,兒女恩怨’一首,是豪之例證。”鄭先生以為蘇詞空靈超妙,辛詞沉著切實,蘇辛風格不同,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他們異中有同,東坡之表現為“曠”與稼軒之表現為“豪”,都是性情襟抱上同一種性情的兩面——二人在生命的底層都有著剛健的力量,只是在人生問題的處理態度上不同。東坡詞不黏滯于物情,每遇著傷感之事,多能提筆振起,以景代情,化愁懷于清遠的意境中。東坡詞如清風明月,給人清泠、遼闊、沉靜之感。詞境即心境,東坡詞里的明月清風,正是他靈明超曠之心境的投影。至于稼軒的豪,就是用力量去擔當人世間的拂逆與苦悶,遇事情總是從寬往窄里想,于是“越想越窄,甚至窄到無地自容,無路可走,還能夠挺然特立,還能夠昂首闊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這就是豪,也就是‘擔當’”。有稼軒那樣的性情胸襟,才有那樣的“豪”,也才有那樣傲岸不平、慷慨縱橫的筆力;因為他是從寬往窄里想,所以他的詞自然就是從寬往窄處寫。那是因內而符外的文體表現。葉嘉瑩先生分析歐陽修詞說:“歐陽修的詞里一方面有傷感悲哀的感情,但他又要將它排遣掉,要向它反撲,從而表現出一種豪興。傷感是一種下沉的悲哀,反撲卻是一種上揚的振奮,這兩種力量的起伏是造成歐陽修詞特有姿態的原因所在。”這從情辭意態論析豪興的特色,可以用作“稼軒詞豪”說很好的腳注。稼軒詞沉郁頓挫,別具抑揚跌宕之姿,正是由于生命中高低兩種力量的拉扯。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將晏幾道與秦觀一起標舉為“最具詞心”的作家,認為晏幾道在技巧上超越了晏殊、歐陽修,“已達令詞之極致”,在您看來何謂“詞心”?晏幾道“小山詞”之“極致”又體現在哪里?
劉少雄:清代馮煦《蒿庵論詞》說:“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又說:“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于內,不可以傳。”詞表達的是一種幽微、含蓄的情致。在兩宋人中最能體現詞的陰柔之美,應屬晏幾道(號小山)與秦觀(號淮海居士)二家;他們是天生的詞人,心思銳敏,易感而多情,最具“詞心”。
晏幾道是晏殊之子,時代與蘇東坡相當,可是他認識黃庭堅,卻與東坡似無交往。他的父親晏殊,七歲號為神童,十五歲進京考試一舉成名,是當時的名臣。史書記載:晏殊自俸甚儉,而豪俊好賓客,且喜獎拔人才,一時名士,如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王安石皆出其門下。小晏為名相之子,中年以后,家道漸式微,終身仕宦不顯。他大概是位矜貴疏俊、忠厚耿介、恃才傲物、不求仕進,以歌酒自放之世家子弟。
小山約晚于柳永數十年,其時慢詞已漸興盛,而其作品卻仍以小令為主。內容大體未脫閨閣園林之景、傷春怨別之情,詞風亦承《花間》、南唐遺緒,詞中多屬緬懷往昔、自傷淪落之感。由馮、李而晏、歐,令詞一以清雋為尚,但也逐步展現個人之情懷思致,小山于此,可謂一脈相承。王灼《碧雞漫志》說:“叔原詞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盛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氣韻高華朗潤,是二晏詞風相似之處。但由于性情、遭遇的不同,小晏詞流露的并非理性的反省與操持,而是一種情緒的耽溺與感傷。小山詞多寫高堂華燭、酒闌人散之空虛,華貴之中難掩悲涼凄婉,濃艷的文字色彩營造出的卻是黯淡氣氛,無復乃父之思致深廣、平淡溫潤,最能具現詞之“文小、質輕、徑狹、境隱”的特質,充滿著幽微、細致、輕柔之美。馮煦《蒿庵論詞》將之與善寫登山臨水棲遲零落之苦悶的秦觀比并,鄭騫則以“露紅煙綠”說其婉麗凄清。
晏幾道“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在遣詞造句方面也特別講究。他的作品大多構思精巧、音韻和美、造語秀逸,綿密地摹寫了高堂華燭曲闌人散的悲戚,詞境延續晏歐,遠在《花間》之上,而技巧更超越晏歐,已達令詞之極致,所以黃庭堅說他“嬉弄于樂府之余,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
澎湃新聞:所謂“詩無達詁”,要向青年學子和普通愛好者講解詩詞實有其艱難處,在基本的文句疏通、背景介紹之外,您似乎相當反對勾連本事,但對于發散式地體情講解卻頗費篇幅,以您的經驗來權衡,講詩詞要如何避免泥于本事,又要如何避免過度解讀,其中的標準和界限在哪里?
劉少雄:詮釋的活動既然是一種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感活動,在自由的聯想之中勢必有其限制的一面,不然,便無所謂“溝通”。過分強調作品的客觀性,以為作品的解釋如同解謎一樣,有且只有一個答案,這種態度禁錮了文學活潑的生命,固然值得批判;而任意行事,無視于作品的客觀存在,以一己之意強加于作品之中,這種濫用了自由聯想的詮釋行為,同樣不值得欣賞。葉嘉瑩《談詩歌的欣賞與〈人間詞話〉的三種境界》一文說:“我以為對詩歌之欣賞實在當具備兩方面的條件,其一是要由客觀之理性對作品有所了解,其二是要由主觀之聯想對作品有所感受。”這里約略提到文本的客觀性與欣賞者的主觀性,及兩者間互相協調的問題。文學詮釋活動基本上就是一個主客觀互動、辯證的過程,《孟子》一書所揭示的“以意逆志”的詮釋方法,其本意便是如此。《孟子?萬章篇》云:“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朱熹注云:“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孟子說“以意逆志”,如朱子所謂“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作者的情志形之于文,讀者因文起興,以己意追索并且體悟作者的意旨,在這順逆往返的詮釋過程中,務必在“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的條件下進行;換言之,詮釋必以文本為依據,乃不容置疑的事實。孟子所言已關涉整體與部分的互動關系,雖未確切深入到“詮釋的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的復雜性問題,但已有若干關聯。詮釋的循環,是詮釋活動里必然有的現象。文學作品的詮釋,乃由字以識句,由句以識篇,反過來看,不知篇意難以掌握句意,不懂句意則對字義的體會可能就不夠深刻,因此,需要隨時調整角度,交互引證,方可有得。至于審察字句的解釋是否有所偏失,除可將其放在篇章結構的大脈絡來加以檢視外,還須斟酌其釋意有否超出字義的引申范圍及一般的語言結構成規;依此,文學詮釋到底還是有它的“客觀標準”的,讀者的語文感受能力有異,可有深淺不一的看法,但必須受制于文本在文辭字句上的客觀要求,而罔顧此一尺度,斷章取義,強植今意于前人的作品之中,這些解釋,雖或喧騰一時,終究是經不起考驗的。
《孟子》書中,還有一個概念常被后來的文學研究者引用,那就是“知人論世”之說。頌讀詩書的目的,由論世以知人,所關心的是人格精神的交感,指出一種道德修養的途徑。孟子所言雖非直接指向文本的解釋,但其說則亦未嘗不可轉化為一種對文學詮釋的客觀的限定,作為“以意逆志”過程中的參考。對于作者生平、創作理念及其生存的文化政經環境的考察,屬于作品的外緣研究,是可提供創作發生背景的說明的。文學詮釋活動是一種互為主體的活動,讀者詮釋作品,除了認知自己的時空條件外,也須顧及作者及其作品產生的歷史性,因為這樣,會使得作品中的文辭意向有一種規范性的指引作用,比較容易能破除時代混淆的迷障,不至于因太過主觀而以今代古;再者,對作品的背景知識所知愈深透,便愈能設身處地地走進作者的情意世界,通過“境界的交融”,主客觀作辯證的融合,這在詮釋者的立場言,就是一種同情的了解。
因此,綜合來看,“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之法,雖不能完全涵括詮釋的各個面向,但兩者的互用,起碼揭示了一個詮釋的基本準則,就是在面對作品進行主體解悟的過程中,詮釋者隨時要對其主觀性有所自覺,并且須服膺某些客觀的要求,方能達到比較有效的解釋。
澎湃新聞:您之前的一檔音頻課程取名為《唐宋詞的情感世界》,這次結集的書稿又叫《至情至性唐宋詞》,您覺得,“詞”是否較之于其他文體,更能反映中國人的情感世界和情感方式呢?
劉少雄:是的。詞是中國文學中最優雅精致的文類。它是一種融合著美麗與哀愁的文體,作家填詞往往在妍雅精致的筆調下,蘊含著真摯動人的情懷。因此而知,文人詞的世界,是一個有情的世界。唐宋詞以長歌短調、清辭麗句,抒發人間情誼,表現為沉重的或輕淡的、溫柔的或熱情的姿貌,既具古典美,又富浪漫情,值得細細吟詠。如何面對人倫世界中的情,始終都是人間難以回避的課題。宋人以優美動人的筆觸言愁說恨,著實令人沉醉;但我們讀詞,不應只是尋愁覓恨,陷溺其中。宋代許多偉大的心靈,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辛棄疾,都表現出勇于承擔、面對失落情緒的態度,歷盡艱辛,仍不失對人世的信任,依舊相信人間情愛之美好。誠如上文所說,詞具備一種陰柔中的韌性,表現為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極具興發感動的力量。古人,因時感事而作詞;今天我們,緣情興感而讀詞——古往今來,牽系著彼此的就是變化人生之中那不變的情誼。以今情讀古詞,讀的不只是唐宋名家的情意,其實更能讀到一己的內在情思。如是,時空交感,彼此同心,我們的情感天地顯得更深美、更渾厚、更寬廣。
我們為何要讀詞,讀古人的詞?這些古代作品有何現代意義?負面的情緒,化為傷感的文學,能否提供正向的能量?本書的撰作,無非是想適切回答這些問題,并希望帶領大家進入唐宋詞的情感世界,分析其中最關緊要的內容,分享唐宋文人出入其間的體驗,及其所創造的情感境界,體認詞情之美、詞體的美學與倫理意涵。
澎湃新聞:與此相關,我注意到,您在這兩本書的書末都專門討論了閱讀詞作的現代意義,尤其是捻出了詞與情感教育的問題,那么,您希望借由讀詞、講詞達到怎樣的“情感教育”目的呢?
劉少雄:文學教育是人文教學重要的一環,而詩詞教育則以愛與美為核心內容,為學生奠定更根本的內在知識,而體驗可豐富其生命內涵,并在有形無形間貫通、激發、支持其外在的知識學問。詩詞詮釋是以情感喚起情感,一種感動的歷程,也是觀察、發現而創造意義的活動。因此,我選擇了詞,作為一種情感教育的實踐。選擇情詞作為主題,是因為男女情感最能貼近生活,最能讓人產生共鳴。
講解“詞”和“東坡”,我想強調兩點:一、宋詞的精神富有現代的意義——宋詞,尤其是文人詞,呈現了一種陰柔中的堅韌個性,一方面不排斥物質文明,講究格律形式,另一方面則堅守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和內在性靈的潔癖感,要求作品情真意切、內容婉雅有致。教人不要輕視情感的作用、溫柔的力量。二、東坡的表現為自由精神做了很好的詮釋——東坡“以詩為詞”,既拓寬了詞情,同時也解放了文體,這樣勇于創造的精神,帶給我們許多啟發。任何一種體制,不至于僵化,就必須在破立之間、依違之際翻轉出活力,才能顯現意義。而所謂自由,唯有在限制中去體驗,才會有更充實的內涵。通過詞的研讀,預期成效有以下幾點:學習自我溝通、學會同情了解、梳理負面情緒、激發感官意識、學習創新的精神。總的來說,編撰這兩本書不只是純粹帶領大家去欣賞詞體之美,我更希望大家能體會人情之美好,知道如何表達情緒,并學會將這些感動融入生活中,豐富一己的生命內涵,加深與人的聯系,成就更美好的生活意境。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