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讀︱仇鹿鳴:職業讀書人的專業與業余
我素來沒有盤點一年閱讀的習慣,一來多少中了點后現代的毒,對于年終總結這種秩序感強烈的儀式懷有本能的抗拒,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盡管在大學中以教書、做研究為稻粱謀,使我表面上具有了職業讀書人的身份,但至少對我個人而言,這種“職業讀書人”的身份反而降低了閱讀上的自由度與愉悅感,因授課、研究所需自然是要不斷地披覽各種相關的史料及論著,但這種閱讀無疑具有相當強的目的性,而且受制于學術規范的要求及當下發達乃至過剩的學術生產力,大量圍繞論文寫作(或可美之名曰知識生產)所展開的閱讀,不但內容頗受局限,毋庸諱言,所讀論著的質量也參差不齊,加之專業閱讀往往并無多少公眾性可言,因此要來進行盤點總結,或者推薦一二,確實讓人有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茫然感。蒙澎湃編輯厚意,應允給我很大的自由度,便勉力就2016年記憶中讀過或瀏覽過,印象深刻的著作和論文做一簡要的回顧,亦盡量避熱趨冷,以示與通行的排行榜有所區別。
從專業閱讀的角度而言,2016年印象最深的一組論文是鐘焓撰寫的,包括《安祿山等雜胡的內亞文化背景——兼論粟特人的“內亞化”問題》(《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失敗的僭偽者與成功的開國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傳奇性事跡為中心》(《歷史研究》2012年第4期)、《森部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評介》(《中國中古史研究》第4卷),無論是對前人研究得失的評騭、對史料的分析與運用,還是借助理論工具對于研究結論的提升皆讓人佩服不已。

在媒體上,鐘焓更多的是以新清史批評者的身份而為公眾所知,這多少掩蓋了他本人的研究業績。最近一兩年來,新清史這一話題漸漸從學界蔓延到媒體,任何學術話題一旦被賦予公眾性,其討論往往無可避免地走向失控。目前而言,中文世界對于新清史一般的了解,仍以劉鳳云、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較為便利,其中如羅友枝《再觀清代》一文雖有刪節,但在網上并不難找到完整的譯本。除此之外,程秀金《“新清史”清朝統治模式之述評——以清朝平定和管轄新疆為中心》(《學術月刊》2015年第6期)一文的介紹與評述也堪稱扎實周詳。但就筆者對相關論著閱讀的直觀感受而言,或許有一背景值得注意,如果說上一代漢學家多成長于六十、七十年代左翼運動的潮流之中,因此對于中國近代的命運及其奮斗抱有相當的同情,那么1980年代以后完成學術訓練的新清史研究者一方面受到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的對象多集中于中國的邊裔與少數族群,其共情的對象已悄然發生了轉移。因此,其對于建立在征服基礎上的傳統帝國(如列寧所謂沙皇俄國是各民族的監獄),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依舊大體保持了原有疆域與民族構成,這一歷史現象的必然性與合法性抱有懷疑,甚至傾向于加以否定(如羅友枝《再觀清代》被刪一節),至少認為是需要討論的話題(周錫瑞《大清如何變成中國》,《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第121期)。這無疑與中國學者思考與論述的起點有不小的距離,這種先天的差異使得雙方的對話與評論很容易導向情緒化,互相質疑對方的研究預設(中國學者或許被天然地視為民族主義者),如柯嬌燕在網上貼出的回應文字中多處質疑何炳棣寫作《捍衛漢化》一文時的身體狀況(Ho, a revered scholar then retired and known to be in uncertain health, would have been the last individual against whom other scholars would evince indignation. We know that even geniuses can have a bad day and produce a ponderous irrelevance such as Ho 1998,http://www.dartmouth.edu/~crossley/comment.shtml)。毫無疑問,攻擊研究者具有政治目的已超越了正常學術批評的范疇,但柯嬌燕對何炳棣身體狀況輕率的評論,恐怕也距離政治正確稍遠。事實上,何先生的壞脾氣與好身體同樣為眾周知,何炳棣的反駁文發表于1998年,在此之后,還出版了相當轟動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之后又發表關于先秦諸子的論著,直至2012年辭世。
如果細讀過鐘焓的論文,其實不難體會他個人對于新清史的批評最初并不是基于民族主義的情緒,作為一個民族史學者,鐘焓本人的研究其實非常重視內亞視角,對于各種流行的理論工具也并不陌生,但他的研究路向或仍傾向于傳統的東方學,即強調考據,以廓清史實為研究的第一要義,對于歷史性質的解釋與判斷則屬于錦上添花。因此,他發表的長篇述評《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是多語種史料考辨互證的實證學術還是意識形態化的應時之學?》(上篇刊《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7輯,但下篇似未見刊出),我最早在往復上讀到,不但是國內學者在學理上對于新清史最為系統的批評,恐怕更反映出作者與新清史研究者在治學理路上的分歧,盡管他們都強調內亞傳統對中國的影響。從目前不多的譯介中不難注意到,新清史特別是新清史2.0所涉及的很多議題,確實是傳統的清史領域關注不多的,至于在新清史的脈絡下被凸現的種種面向,是否足以改變我們對清帝國性質的認識,待到熱度冷卻后,自可以交付學術史來加以檢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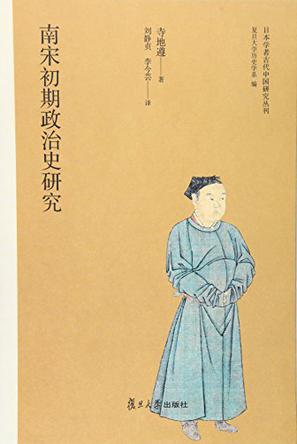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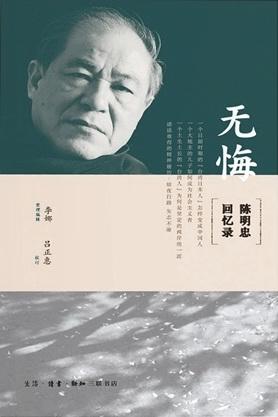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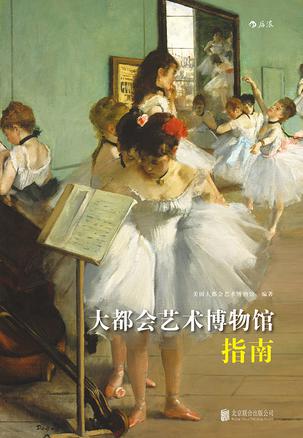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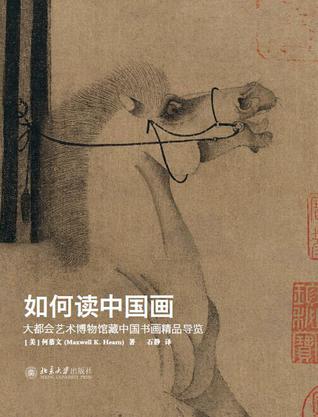
若問去年買到圖錄中最滿意的一本,可以舉出的是《心放俗外——定州靜志、凈眾佛塔地宮文物》(中國書店,2014年),一來定州靜志、凈眾兩寺唐宋地宮出土文物精美,特別是靜志寺出土了從北魏、隋、唐、宋歷代的舍利石函、石棺、石志,所存銘文詳細記載了靜志寺歷代供奉的情況,頗具史料價值。兩寺地宮本身都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囿于條件,一直未見有完整的展出,浙江省博物館舉辦的特展是個難得的機遇。二來這一圖錄與國內很多特展圖錄一樣,不但定價昂貴,而且似未見公開發行,后來僥幸在孔夫子舊書網上以半價覓得一本,也算是意外的驚喜。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