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宣揚(yáng)哲學(xué)流浪六十年:親近那么多大師,是時(shí)代給我的禮物
從1957年進(jìn)入北大哲學(xué)系聆聽(tīng)熊偉、馮友蘭、張岱年等諸多哲學(xué)大師的課程,到1979年遠(yuǎn)渡重洋來(lái)到法國(guó)第一大學(xué)攻讀博士學(xué)位,與德里達(dá)、福柯、布迪厄、斯特勞斯等20世紀(jì)著名法國(guó)思想家深入交往,再到2010年成為上海交通大學(xué)講席教授,年近八旬的哲學(xué)家高宣揚(yáng)已經(jīng)在哲學(xué)的世界里流浪了六十年。
這六十年里,高宣揚(yáng)著作等身。今年,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了高宣揚(yáng)文集,最先問(wèn)世的是《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導(dǎo)引》,之后還將有更多著作陸陸續(xù)續(xù)出版。
12月17日,一個(gè)冬日的下午,高宣揚(yáng)教授和同濟(jì)大學(xué)中文系的張生教授在上海交大出版社展開(kāi)了一場(chǎng)對(duì)話,主題是“高宣揚(yáng)哲學(xué)流浪六十年”。對(duì)于高宣揚(yáng)來(lái)說(shuō),哲學(xué)不意味著一個(gè)學(xué)術(shù)課題,哲學(xué)就是他的人生。

學(xué)哲學(xué)不但要看懂原文,還要學(xué)會(huì)原文語(yǔ)言的思考方式
高宣揚(yáng)受聘于同濟(jì)時(shí),張生聽(tīng)了兩年高老師的法國(guó)哲學(xué)課。他回憶到高宣揚(yáng)講課基本上是直接讀法語(yǔ)的,讀一段,學(xué)生跟著讀一段,然后進(jìn)行解釋。
除了法語(yǔ)外,高宣揚(yáng)還通曉英語(yǔ)、德語(yǔ)等語(yǔ)言。對(duì)于高宣揚(yáng)來(lái)說(shuō),掌握外語(yǔ)對(duì)于學(xué)習(xí)哲學(xué)非常重要,而這樣的重要性是他當(dāng)年在北大哲學(xué)系讀書時(shí)老師們教育他的。
“當(dāng)時(shí)我去鄭昕(注:已故著名哲學(xué)家、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老師家敲門,他第一句話,你會(huì)德語(yǔ)嗎。我說(shuō)不會(huì),他說(shuō)那不行,馬上去學(xué)德語(yǔ),到德語(yǔ)專業(yè)去上課,不要擔(dān)心,我馬上打電話給馮至,讓他教你德語(yǔ),馬上去上。就這樣我上了兩年馮至先生的德語(yǔ)課。”
高宣揚(yáng)也提到在北大時(shí),老教授們非常注重看原著。對(duì)于一個(gè)德語(yǔ)剛?cè)腴T的人來(lái)說(shuō),看德文原版《純粹理性批判》無(wú)疑相當(dāng)困難。“教授跟我說(shuō),你要學(xué)這個(gè)東西必須一句一句來(lái)學(xué),很困難怎么辦?他叫我每個(gè)禮拜用三天的時(shí)間,三個(gè)下午到他的家去,在他書房里,一句一句地先讀先翻譯,然后糾正。那段時(shí)間,另外有個(gè)先生過(guò)來(lái)了。他們直接講德語(yǔ)溝通,強(qiáng)迫我聽(tīng)德語(yǔ)。所以踏踏實(shí)實(shí)地讀原著,這是打下基本功必需的,不能逃避的,所以我后來(lái)也是這樣的。”
為什么學(xué)會(huì)原文語(yǔ)言對(duì)于學(xué)習(xí)哲學(xué)如此重要?高宣揚(yáng)說(shuō),“學(xué)哲學(xué)不但要看懂它的原文,理解它的意義,你要學(xué)會(huì)用它原汁原味的思考方式,它的語(yǔ)言方式來(lái)進(jìn)行思考和把握它的精神。翻譯成中文以后再回過(guò)頭去研究它的意思的話,因?yàn)橹形牡恼Z(yǔ)言結(jié)構(gòu)和模式不一樣,這個(gè)模式本身反映了思想精神本身的特點(diǎn)和差異性,所以要盡可能地——我說(shuō)的是盡可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盡可能地去學(xué)會(huì)就它原文、原著反復(fù)地讀,一次不行,就兩次,反復(fù)地對(duì)它的基本語(yǔ)句研究,這樣才能真正理解。”
列維-斯特勞斯每個(gè)禮拜花5個(gè)小時(shí)請(qǐng)教數(shù)學(xué)家數(shù)學(xué)問(wèn)題
張生問(wèn)高宣揚(yáng)在法國(guó)學(xué)習(xí)的時(shí)候,那些老師是怎么培養(yǎng)研究生,怎么和學(xué)生交流的。
高宣揚(yáng)回憶,他感受到有兩個(gè)差異。“第一個(gè),法國(guó)的教授對(duì)研究生是高度開(kāi)放和自由的,也就是說(shuō)他把你帶進(jìn)來(lái)就讓你自由地思考,自己準(zhǔn)備論文,自己看書,鼓勵(lì)你在他們舉辦的研討會(huì)上去發(fā)言,去討論問(wèn)題。他們通過(guò)你的讀書筆記看你對(duì)著作的理解達(dá)到什么程度。”
第二點(diǎn)是法國(guó)老師鼓勵(lì)學(xué)生走出自己的專業(yè)框架,進(jìn)行文學(xué)、人類學(xué)、語(yǔ)言學(xué)、政治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等各領(lǐng)域的來(lái)往。他特別提到著名人類學(xué)家列維-斯特勞斯的例子。“他在1930年代,沒(méi)有正式進(jìn)入到人類學(xué)領(lǐng)域之前,一個(gè)禮拜用5個(gè)小時(shí)的時(shí)間去請(qǐng)教當(dāng)時(shí)最著名的數(shù)學(xué)家,學(xué)數(shù)學(xué)家怎么思考數(shù)學(xué),思考高等數(shù)學(xué)各個(gè)方面的成果,來(lái)理解人類思考模式的差異性。”
高宣揚(yáng)也提到“長(zhǎng)程迂回”式的學(xué)哲學(xué)的方法。“后來(lái)我接觸的另外一個(gè)老師,他批評(píng)海德格爾在短程迂回。他說(shuō)我要打破這個(gè)短程迂回,從哲學(xué)到社會(huì)學(xué)到人文學(xué)到各個(gè)領(lǐng)域,再回來(lái)到哲學(xué),再?gòu)恼軐W(xué)出去,這是一個(gè)長(zhǎng)程的迂回。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學(xué)哲學(xué)的某個(gè)專業(yè)固然需要專業(yè)的研究,但是專業(yè)研究不能夠離開(kāi)這些長(zhǎng)程的迂回。這給我一個(gè)很大的教育,使我后來(lái)也學(xué)會(huì)除了哲學(xué)以外還研究別的東西,這個(gè)對(duì)我受益很大。”
20世紀(jì)法國(guó)哲學(xué)的發(fā)達(dá)并非突然,19世紀(jì)下半葉就已播種
20世紀(jì)是法國(guó)哲學(xué)的世紀(jì),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法國(guó)突然間涌現(xiàn)了德里達(dá)、福柯、列維納斯、斯特勞斯、利奧塔、鮑德里亞等一大批世界級(jí)的思想家、哲學(xué)家。
張生援引當(dāng)代法國(guó)哲學(xué)家巴丟的說(shuō)法,提到西方哲學(xué)的三個(gè)重要時(shí)刻。第一個(gè)高峰是古希臘,到了19世紀(jì),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是第二個(gè)高峰,第三個(gè)高峰就是法國(guó)哲學(xué)。為什么20世紀(jì)的法國(guó)哲學(xué)如此發(fā)達(dá)?
高宣揚(yáng)澄清了一個(gè)誤解,許多人以為20世紀(jì)的法國(guó)哲學(xué)是突然爆發(fā)的,但其實(shí)早在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法國(guó)哲學(xué)已經(jīng)開(kāi)始開(kāi)出它的奇葩,早就已經(jīng)打破了19世紀(jì)末以前,德國(guó)哲學(xué)有著重要影響的局面。
“法國(guó)人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在20世紀(jì)以后不斷創(chuàng)新,主要是因?yàn)檫@些思想家的創(chuàng)造精神比較活躍。他們不甘心于停留在原來(lái)的西方傳統(tǒng)的框架之內(nèi),甚至要打破自己的法國(guó)傳統(tǒng)。19世紀(jì)下半葉開(kāi)始,法國(guó)哲學(xué)就開(kāi)始打破笛卡兒的意識(shí)哲學(xué)。笛卡兒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理性,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歷史的作用。從19世紀(jì)開(kāi)始,法國(guó)哲學(xué)開(kāi)始向非理性部分——感性部分、感情部分有了新的發(fā)展,在這方面法國(guó)人應(yīng)該說(shuō)比德國(guó)人更早一步,因?yàn)榈聡?guó)有過(guò)這個(gè)嘗試,在19世紀(jì)中葉,先是叔本華,然后是尼采,這兩個(gè)人都想打破理性主義,但是他們很快被德國(guó)的理性主義壓下來(lái)了。但是在法國(guó),這個(gè)東西就一直發(fā)展下來(lái)。”
因此,高宣揚(yáng)提醒我們,理解法國(guó)哲學(xué)在20世紀(jì)重要的影響,不要忘記或者說(shuō)不要脫離整個(gè)歷史發(fā)展的背景。
存在主義還沒(méi)有過(guò)去,精神依然延續(xù)
上世紀(jì)80年代,國(guó)門再度打開(kāi),西方世界各種思潮涌入中國(guó)大陸。在這些思潮中,最有影響力的無(wú)疑是存在主義,手捧一本薩特的《存在與虛無(wú)》是那個(gè)年代文藝青年的“腔調(diào)”。
1978年在香港,高宣揚(yáng)用三個(gè)月時(shí)間寫出《存在主義概說(shuō)》,這是漢語(yǔ)學(xué)界第一本全面研究存在主義的權(quán)威著作,這也是高宣揚(yáng)第一本引起重大關(guān)注的著作。
為什么當(dāng)時(shí)存在主義對(duì)1980年代的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產(chǎn)生如此大的影響力?
在回答記者這個(gè)問(wèn)題時(shí),高宣揚(yáng)首先簡(jiǎn)單勾勒了西方存在主義產(chǎn)生的背景:它直接與資本主義本身的命運(yùn)連在一起。19世紀(jì)末開(kāi)始到20世紀(jì)上半葉,資本主義有兩次危機(jī),特別是二次大戰(zhàn),對(duì)資本主義打擊特別嚴(yán)重,那種情況下,西方人開(kāi)始憂慮,悲觀,找不到出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xiàn)了存在主義。
同時(shí),存在主義對(duì)于自我行動(dòng)、自我承擔(dān)的強(qiáng)調(diào)也深深影響了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人。“存在主義特別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走出危機(jī)的陰影,靠自己去創(chuàng)造,這是存在主義的基本原則,我先活出來(lái)我才有本質(zhì),也就是說(shuō)是我決定我的存在才能造出這個(gè)世界。所以薩特在1948年寫的一本書里它說(shuō)什么是存在。存在就是以它自身的顯現(xiàn)造就這個(gè)世界的存在。什么意思,就是我一出來(lái),我到這個(gè)世界上,我要靠我的努力,我的存在造就我喜歡的世界。就是這樣一句話。這句話就是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的命運(yùn)靠自己去決定,自己來(lái)創(chuàng)造。薩特講這句話還特別強(qiáng)調(diào),我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存在,決定自己存在的同時(shí),我特別強(qiáng)調(diào)責(zé)任的重要性,他說(shuō)這就意味著當(dāng)你意識(shí)到自己用行動(dòng)來(lái)造就自己的世界的時(shí)候。你必須意識(shí)到正是因?yàn)檫@樣,你的責(zé)任是重大的。所以他把責(zé)任的關(guān)聯(lián)和這個(gè)存在,創(chuàng)造世界,連在一起。”
這些年,存在主義作為一種社會(huì)思潮,在國(guó)內(nèi)的影響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過(guò)去那么大了。今天其實(shí)已經(jīng)很少有人再去談薩特了。對(duì)于存在主義已經(jīng)式微的說(shuō)法,高宣揚(yáng)并不完全認(rèn)同。
高宣揚(yáng)教授解釋道:1980年代到今天,世界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中國(guó)封閉到中國(guó)開(kāi)放到現(xiàn)在發(fā)生的時(shí)代的改變,同時(shí)還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世界性的事件,全球化、恐怖主義、網(wǎng)絡(luò)化的出現(xiàn),這些東西使得原來(lái)在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在二次大戰(zhàn)后流行的存在主義,就顯示出它的時(shí)代性有點(diǎn)距離了。
但高宣揚(yáng)認(rèn)為這個(gè)距離是表面的,“存在主義本身的口號(hào)是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存在的創(chuàng)造性、自我創(chuàng)造性,創(chuàng)造的同時(shí)有責(zé)任來(lái)改變這個(gè)世界,在這個(gè)意義上,這個(gè)精神還是繼續(xù)延續(xù)下來(lái)的,而且在現(xiàn)在這樣一個(gè)后現(xiàn)代的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化的時(shí)代,越是要顯示出個(gè)人責(zé)任的重要性。”
同時(shí),高宣揚(yáng)也提到,存在主義從20世紀(jì)中葉以后慢慢滲透到哲學(xué)、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各個(gè)領(lǐng)域,包括法國(guó)的新浪潮、新小說(shuō)都受到存在主義影響,“這說(shuō)明它的成果不是已經(jīng)過(guò)去了,相反,已經(jīng)滲透到各個(gè)領(lǐng)域去了。”
有機(jī)會(huì)親近這么多中外大師,是時(shí)代給我的禮物
對(duì)于今天的中國(guó)學(xué)人和普通讀者來(lái)說(shuō),那個(gè)大師輩出、星光璀璨的時(shí)代已經(jīng)遠(yuǎn)去。而高宣揚(yáng)或許是少數(shù)和中外大師有過(guò)深入交往的學(xué)人。對(duì)此,在場(chǎng)的同濟(jì)大學(xué)歐洲文化研究院副院長(zhǎng)徐衛(wèi)翔教授由衷地表達(dá)了他的羨慕。高宣揚(yáng)笑笑說(shuō)這是時(shí)代給他的禮物。
1957年,高宣揚(yáng)進(jìn)入北大哲學(xué)系時(shí),是北大哲學(xué)系大師云集的時(shí)代,由于特殊原因,來(lái)自全國(guó)的哲學(xué)教授都調(diào)入北大哲學(xué)系,當(dāng)時(shí)的北大哲學(xué)系集中了35名教授。
這么多年過(guò)去,高宣揚(yáng)依然清晰記得當(dāng)年在北大課堂聽(tīng)課的場(chǎng)景。“從上世紀(jì)50年代開(kāi)始,直接聆聽(tīng)很多先生在北大課堂上課的情景。他們講話的口氣、他們對(duì)我們的教導(dǎo),每一段話、每一個(gè)概念的解釋都是牢牢記在心里。我能夠順利地在1979年以后出國(guó),都是他們給我在心里面種下的種子。”
而說(shuō)到在法國(guó)的三十多年里,他除了感恩還是感恩,“30多年里能和那么多大師交流,我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法國(guó)老師對(duì)他的意義,除了學(xué)養(yǎng)之外,更獨(dú)特的地方在于,將激情注入到寫作和思考中,這是法國(guó)思想家如福柯等人的治學(xué)行文的重要特點(diǎn),“他們教我怎么來(lái)思考,教我怎么表達(dá)語(yǔ)言,教我怎么把情感滲透到文字上面去。情感沒(méi)有情是死的,生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生命是有感情的。思考也好,寫也好,有一種激情在里面,這樣的創(chuàng)作和寫作是活的。”
張生也說(shuō),“以前我們交往的時(shí)候,高老師評(píng)價(jià)一個(gè)事物或者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東西特別喜歡說(shuō)這是一個(gè)活生生的東西。”
盡管已年近八旬,高宣揚(yáng)依然沒(méi)有停止在哲學(xué)王國(guó)里的流浪,“我還沒(méi)有感覺(jué)累,腦子里東西特別多,多到感覺(jué)很緊張,每一分鐘都很緊張,因?yàn)橐獙懙臇|西太多了,要想的東西太多了,要講的話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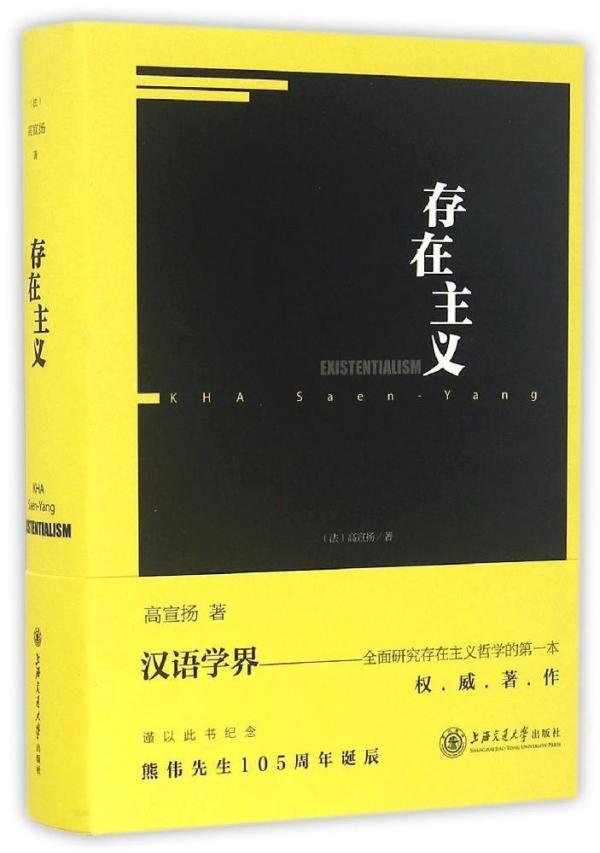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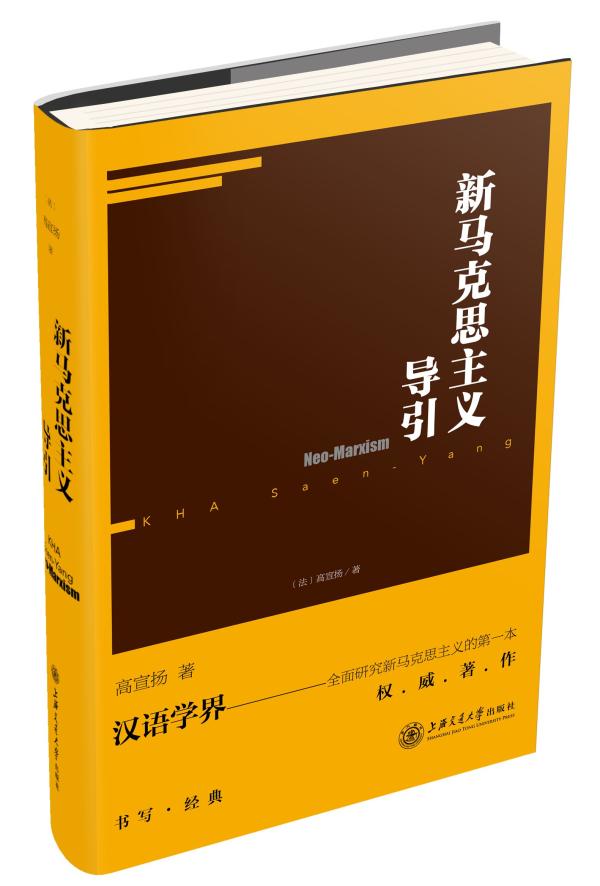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