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書評︱柳存仁抗戰(zhàn)后的選擇

欲多知道一些上海淪陷時期文壇內(nèi)幕,非得柳存仁(1917-2009)現(xiàn)身說法不可,偏偏柳存仁金口難開,自擺脫樊籠以后,便對那段歷史諱莫如深,自己不講,別人問起他也是不講。其實你越是堅不吐實,別人越是好奇,我便是好奇者之一。那年月,文載道(金性堯)墮坑落塹之程度比之柳存仁強不了多少,可是金性堯勇于自省,“(朱樸)后來和黎庵合辦了《古今》,朱樸是沒有金錢和權(quán)勢的,但因投靠了周佛海,經(jīng)濟上也有了保證,成為周門一個高級清客。我也是相差無幾,后來是自甘附逆。作為《世紀風(fēng)》的作者原是很清白的,作了《古今》的不署名編輯,政治上便有了涇渭之分”(《悼黎庵》)。
前些天與宋希於君聊起柳存仁具體哪年離開大陸的,他的研究結(jié)論“上限是1951年”。非常之巧,宋君和我都正在讀的柳存仁兩文《我從上海回來了》和《四年回想錄》(署“柳雨生”)。我的一位上海朋友也是好奇者,他建議我買柳存仁所著《外國的月亮》,里面一篇題為《巴金》的文章證明至少“1947年冬”柳存仁尚在上海,而且已是“自由之身”。
《我從上海回來了》乃日記體,連載于1941年1月和2月的《大風(fēng)》雜志第七十六和七十七期。《大風(fēng)》社長是簡又文,主編陸丹林,主辦地在香港,桂林設(shè)有分社。這兩期為土紙所印,我懷疑是在物資匱乏的桂林印刷的,香港還沒窮到這份上。日記“凡七天,(1940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又九月四日,五日各一段”。柳存仁稱“來港的印象當(dāng)然大體上是極好的,特別是從孤島回來的人,至少感覺到這里的空氣非常的自由,情緒非常的興奮”。柳存仁來港的目的很明確:“我因為上海的環(huán)境日益惡劣,把一切安頓之后,決意到香港來。”“我住在上海真是太苦悶了,苦悶了三年多,總想吐出這一面積壓久了的悶氣來。在學(xué)校里面上課,學(xué)生們常常喜歡發(fā)問‘柳先生!我們這一課古書讀法舉例究竟和抗戰(zhàn)建國有沒有關(guān)系呢?’這樣令人躊躇的問題,是常常可以聽到的。”“今天是孔子誕日,在‘孤島’上是僅有八天懸旗慶祝的一天。好了!以后不一定要是今天,天天人們都可以看見燦爛無疵的光榮的國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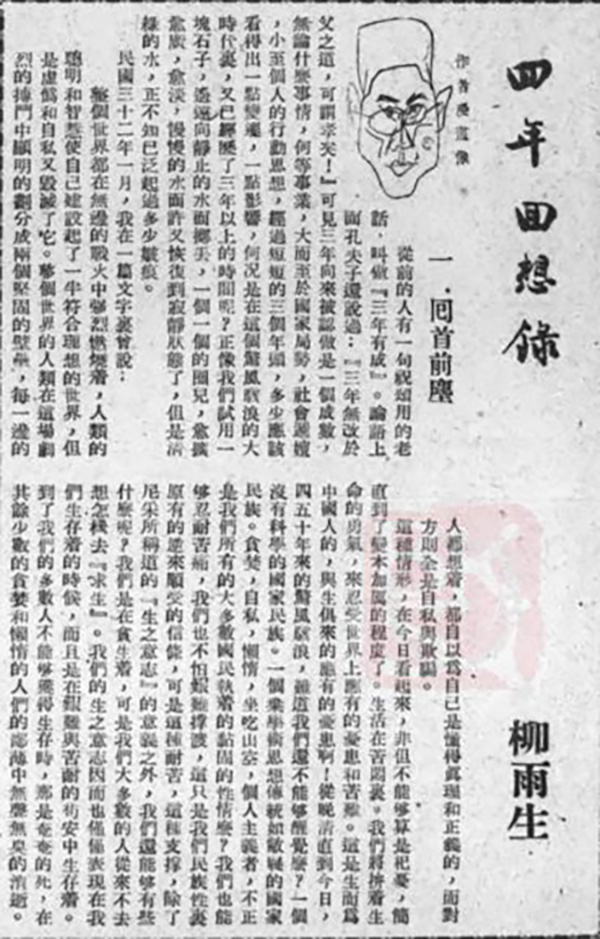
顯而易見,柳存仁忍受不了日本人的鳥氣,一腔熱血,無以報國,所以逃離上海奔往香港。本來香港只是個中轉(zhuǎn)站,柳存仁在《四年回想錄》里稱“我到香港去最初不過是過路,目的地是赴湖南某地國立師范學(xué)院任職”。看來柳存仁很像《圍城》里的李梅亭、顧爾謙、趙辛楣,接到了內(nèi)地高等學(xué)府的聘書,不同的是柳沒有赴教,從而改變了人生之路。
柳存仁在日記中稱:“是不是從香港經(jīng)過那一條唯一的通內(nèi)地的孔道——沙魚涌——經(jīng)過惠州,韶關(guān),到湖南籃田國立師范學(xué)院去呢?是的,是的,我們應(yīng)該不辭艱困的一塊兒到內(nèi)地去工作。”
提到“內(nèi)地”,柳存仁的語調(diào)忽然高了八度,如歌如詩,激越飛揚,仿佛身處抗戰(zhàn)前線一名宣傳員:
內(nèi)地!這在我們久困孤島的同胞們看來,是一個多么有興奮力量的名辭啊。想起連綿千萬里戰(zhàn)線的南北疆場,英勇抗日不屈不撓的國軍,可歌可泣毀家紓難的老百姓們,流離顛沛的難胞難童,幾千磅重的大炸彈摧毀不了的統(tǒng)一團結(jié)御侮的熱忱,堅苦卓絕令人敬佩的賢明領(lǐng)袖,啊!我們又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來!讓我們鼓舞,讓我們謳歌,偉大的新中國從西南抗戰(zhàn)根據(jù)地重新的生長起來了。遙想怒吼聲中的新中國的波濤,它的力量的雄壯,內(nèi)質(zhì)的純潔,外觀的美麗,無一不像我們船艙外面所能夠眺望到的洶涌澎湃的大海一樣偉大。
十八個月后,柳存仁哪怕一句上面的話也寫不出來了。
我對宋君講,這個柳存仁很有意思啊,忍不了“孤島”的上海,卻忍得了淪陷的上海,宋君稱柳的父母都在上海呢。是呀,柳存仁在日記中寫道:“在小船上和岸上的人惜別時,父親微白的頭發(fā)在我的眼鏡中看來,愈覺得花白了;母親的眼睛微腫,卻和正在揩著熱淚的賜蓉相映。”(“賜蓉”是柳存仁的妻子。柳存仁于《古今》第十期的《談自傳》里曾寫:“民國二十九年夏,在滬,與上海姜小姐結(jié)婚,愛情彌篤,遂赴香港。”)
柳存仁于《四年回想錄》更強調(diào)了這個理由:“我于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八日回到上海,恰為香港戰(zhàn)事后的五月。……上海雖不是故鄉(xiāng),卻是家人父子團聚的所在,幾個月不通家書了,重因親老弟幼,終于經(jīng)過相當(dāng)?shù)膮捑牒推D殆的旅途,返到自己的家里。”
柳存仁剛到香港,就謀到一個“香港政府文化檢查官”的差事,迅速地融入了香港文化圈,舊雨新知,席不暇暖。當(dāng)時有很多知名文化人士避難到香港,文化人聚在一堆,知識分子的臭毛病便泛濫開來,柳存仁也加入了筆仗,筆仗對手竟是鄒韜奮、沈雁冰、范長江這樣的大名頭。柳存仁回到上海后將筆仗之前因后果寫入《四年回想錄》,多少顯得有那么一點兒自我標(biāo)榜。
1940年8月29日抵達香港,1942年5月8日回到上海中間是二十個月,柳存仁所說“香島十八月”對不上數(shù)呀,原來柳存仁1942年3月到廣州小住了兩個月。

《四年回想錄》刊在1944年11月《光化》雜志第二期,“編者按”云:“《四年回想錄》并非私人的瑣事憶念,乃是四年來港,滬,京,平文壇一角的實錄,也就是將來‘文壇史料’之一。”此文附有的照片,現(xiàn)在看來都是珍貴的合影,其一,“民國三十年夏攝于香港。后排右首第二人起,徐遲,徐誠斌,葉靈鳳,戴望舒。前排左首起第一人林憾廬,右為柳雨生”(見圖一)。徐遲的自傳《江南小鎮(zhèn)》第四部(1938-1946)與柳雨生的經(jīng)歷有交集,卻沒有提過柳雨生的名字。其二,“知堂先生在蘇州。前排右起,柳雨生,陶亢德,周啟明,汪馥泉,楊鴻烈。后排沈啟無,龍沐勛”(見圖二)。可惜由于雜志制作的原因,均極其不清晰。

此文關(guān)于淪陷上海文壇,柳存仁就他所參與的那一部分,除去“核心機密”,畢竟談了不少,我們所抱怨的是他河清海晏之后的三緘其口。事實上三緘其口的當(dāng)事人并非柳存仁一個,上海有,北京也有。
柳存仁于風(fēng)雨如晦的“香島十八月”,也有極其輕松的閑暇,我就在《大風(fēng)》(九十,九十一期)上讀到他的譯作《明代的彩色印刷》,使人想起巴金說的話:“事實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價買來的《金瓶梅詞話》對于現(xiàn)今在生死關(guān)頭掙扎著的中國人民會有什么影響呢?”
(本文刊于2016年12月18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題為《柳存仁<四年回想錄>》)
閱讀更多謝其章的文章: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