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清宮戰圖中的“十全武功”:被形塑的尚武文化
作為極少數的滿族何以能夠統治中國近三百年,可以說是清史研究的核心課題。“漢化說”認為滿洲人接受并與漢人文化同化是清朝成功的基礎,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新清史”研究則認為滿族主體性才是維系清帝國的關鍵;前者多強調清朝對明代官制與儒家思想的承襲,后者雖不否認漢文化的影響,但更關注于非中國傳統官僚體制、清帝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的治理方式等面向。盡管學界相關的回響與討論很多,也不乏替代模式的提出,但由于雙方對于“漢化”的定義未必一致,所關注的層面也不甚相同,因而被稱為是“沒有交集的對話”。的確“漢化說”與“新清史”的最大分歧之一,容或在于前者所重視的中國傳統官僚制度與文化于清代之傳承,卻不是后者研究的重點;后者側重的滿洲獨特之八旗制度、尚武文化或是多民族帝國的統治策略,也非前者關懷的核心。如果“漢化說”主要以中國本土社會為范圍,聚焦于滿人對漢人政治傳統的受容,“新清史”則更看重滿洲統治集團如何維持對蒙古、西藏、漢人等多民族的支配,而著重研究清帝國和邊疆族群的關系,可以說兩方討論偏重的統治對象與區域有所不同。理論上二者的研究應該在中國本土的漢人社會有所交集,但一般來說,“新清史”在主張滿人作為外來征服集團,需以八旗制度等來強化滿漢定位之余,或也認可清朝并行中國傳統的王權思想以獲取漢人的支持,或將之整合在清帝國超越所有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共時皇權(simutaneous emperorship)之一部分,而未就滿洲皇帝于中國本土的統治與“漢化說”有更深入的對話與討論。換言之,雖然“新清史”強調滿人主體性而引入了族群認同、多民族關系等面向而豐富了清史研究,但除了少數觸及清帝透過南巡與江南士大夫和商人的互動外,“新清史”基本上是透過包融“漢化說”,一方面認可中國傳統王權對清廷的影響,另一方面將之詮釋為或與滿洲人集團的統治正統性并行,或視中國本土為清多民族帝國的一環,而并沒有完全撼動“漢化說”對于滿族何以能夠統治中國本土社會此一問題的答案,也就是清廷采取的漢化政策(不論是“漢化說”隱含的被動還是“新清史”強調的主動)。

如此的回答難免令人感到老調重彈,尤其是清史研究在這些年“新清史”高舉滿洲主體性的洗禮之后,漢化政策仍是滿族能夠統治中國本土社會的關鍵因素;然而,如果我們換個方式從被統治者的角度來提問,何以中國本土社會被極少數的滿族統治近三百年,就會發現既有的答案和“新清史”批評“漢化說”忽略滿洲主體性一樣,漢人作為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容或也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倘若“新清史”提醒我們,清廷對于滿洲以少數族群統治占大多數的漢人十分自覺,維持滿人統治與滿人集團的凝聚性是清朝統治成功的重要條件,以八旗為例,其制度的發展也隨著時間有所變化;那么漢人在同樣滿漢比例懸殊的歷史情境下,又何嘗沒有意識到自身被支配的地位?換句話說,清廷采納了漢人傳統的王權思想,就足以讓漢人長期接受滿人的統治了嗎?滿洲皇帝以儒家思想作為漢化政策的核心,即能贏得儒家精英的長久支持嗎?滿人對漢人近三百年的支配關系,除了中國傳統王權與漢化政策,是否還需要其他的機制與過程才得以確立并維系?
皇清文化霸權
本書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來思考滿人對漢人的支配關系。文化霸權原本是用來指涉資本主義制度下文化與權力的關系,討論支配群體如何透過文化象征等作用,促使被支配者默認接受其從屬地位,但對歷史學的討論而言也可以有所啟發。尤其統治者如何贏得被支配者對既有社會秩序的共識、如何持續地創造其合法性以維持其支配地位,被支配者又如何參與使其被支配合法化的共謀之中,以及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文化并非界線分明而是可穿透的等概念,更能幫助我們分析極少數的滿族如何長期成功支配絕大多數的漢人。
相對于其他征服王朝,清朝宮廷除了采納漢人的王權傳統之外,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其對士大夫文化的積極收編以建構其皇權。以康熙朝為例,宮廷開始大量地實行當時盛行于文士間的藝文模式,并將之轉換為皇權和清宮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將盛行的晚明董其昌(1555~1636)繪畫風格收編成為清宮院體之一的正統畫派;模仿當時流行的董其昌等帖學書風,成立御書局大量頒賜御書;受到明清官員以戰事為中心的奏議合集的影響,首創將上諭與奏折等加以編纂的官修史書方略;承襲明清文人出版詩文集而刊刻大量御制詩集;轉換明清文士的園林詩作與圖繪而為康熙《御制避暑山莊詩》,其中的御制詩一改文人唱和的社交取向,而加入大臣的批注來見證皇帝博學圣德,圖畫則無文士園景圖聚焦于近景的小品模式、季節變化、人物等引領觀者游覽的元素,而借由數量龐大的景點與廣闊園景顯示皇家苑囿的宏闊氣度等。這些康熙轉換與收編明清文士文化的舉措為其他征服王朝所未見,不僅為乾隆帝發揚光大,后續的清帝也多少有所承襲。即便是漢人皇權,也沒有對時下盛行的各式文士文化有如此高度興趣者。歷代皇權對士大夫文化的態度,雖然不無少數如宋徽宗(1082~1135)或明宣宗(1399~1435)等以文藝事業著名的皇帝,但也不乏對文士有所忌憚的皇帝如朱元璋(1328~1398),而像盛清皇帝如此積極又全面地收編當時流行的士大夫視覺文化以形塑皇權者,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是故不能僅以“漢化”泛論之,而必須重視其形塑皇清文化霸權的作用。
從統治的角度來看,清朝的宮廷文化除了繼承原來漢人皇帝透過皇室收藏、祥瑞圖像等宣示王朝天命的傳統王權做法外,清帝作為統治漢人社會的少數族群大規模收編原屬中國本土社會精英的文士文化,建立滿洲皇權凌駕于士大夫的位階,不能說不是建構清朝皇權相當有效的方式。這也是為什么本書以“皇清文化霸權”,來指稱滿洲統治者在中國傳統王朝統治的正統性之外,另行發展出的支配中國本土社會的不同模式。此模式為“文化霸權”,是因為滿洲支配群體借由收編中國既有社會價值體系中層級居高的文士文化,贏得被支配的漢人對原來社會秩序的共識;經其轉換建構成各式“御制”、“欽定”宮廷文化,加強以文士為首的被支配漢人之從屬地位,更強化了皇權在中國本土社會秩序中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清宮文化需要滿洲皇帝一再地接續展演以維持其支配地位;而正是被支配的漢人精英之參與,才讓其被支配合法化的共謀得以維系。如此的文化霸權之效應,即是“皇清”——清朝子民認可滿洲皇權——的展現。建構“皇清文化霸權”的媒介不是“新清史”所言滿洲外來征服集團的政治模式,或是“漢化說”強調中國傳統王朝統治的儒家正統,而是穿透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文士文化。因此,本書跳脫“漢化說”與“新清史”的框架,從皇清文化霸權的角度,重新反思滿族得以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不同機制。
反思滿洲尚武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借由“皇清文化霸權”的媒介——文士文化——所建構之清宮文化,并不限于各類“御制”詩文、書畫等宮廷藝文,還包括被視為清廷軍事文化展現的方略,如前述也很可能與明清官員的戰事奏議合集有關。方略與戰事奏議合集的關系,一方面提醒我們士大夫“武”文化面向的存在,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所謂滿洲特色的論述,未必為滿洲所獨有而與漢文化無涉。尤其“滿洲以騎射為本”的尚武精神,向來是清史學界對滿洲皇帝強調武勇、武備、武勛等軍事文化的一貫認識;也的確從立國之初,清帝王就一再下旨必須維系滿洲尚武根本,而清代特有的大量戰碑、方略、戰爭儀式和戰勛圖像,更被視為其提倡軍事文化的具體展現。然而,一概以滿洲特色來概括清帝國的尚武文化,不免有本質論的危險。雖然清史學者大致將清代的軍事文化分為清初、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乾隆中后期三階段,但主要還是以發展完成的乾隆朝來總括清帝國的崇武文化。事實上,相較于其他康熙朝就開始建立的戰碑、方略、戰爭儀式等,戰勛圖并未出現于康熙時期,而是到了乾隆朝才大舉制作,顯然與其他的武勛模式十分不同,不可一概而論。尤其如果康熙皇帝率先實行了其他紀念武勛的模式來提倡滿洲尚武精神,那么為什么未沿用當時宮廷已經開啟的大型圖繪計劃如《南巡圖》的方式來制作戰勛圖像?戰勛圖像在康熙與乾隆朝制作與否的差別,提示了清帝國的尚武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滿洲本質,戰勛圖像或可作為考察其武勛文化建構、發展與機制的指標。

在清帝國采取的種種武勛文化模式中,由滿洲皇帝直接下旨、內務府監管制作的戰勛圖像,對皇權所欲強化的武功文化尤其關鍵。前述如正統畫派、康熙《御制避暑山莊詩》等清宮圖繪,不只是反映皇帝品味的藝術作品,或是象征皇權概念和帝國統治的視覺符號,更可以是滿洲帝王推行文化霸權的重要手段。透過追尋戰勛圖像的歷史,本書將論證此類原本在傳統中國政史與畫史中非常邊緣的題材,在明代卻是官員間盛行的視覺文化之一環,清帝王透過轉化漢人精英的視覺表述遂行其文化霸權,到了乾隆朝逐步形成以戰爭圖像為核心的武勛展示,最終確立了展現滿洲武功霸權的體系。也就是說,清帝國的尚武文化不是透過帝王的諭旨就足以維系的滿洲價值,而是必須一再尋求支配漢人精英文化的動態過程,亦是建構“皇清文化霸權”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也是本書標題“刻畫戰勛與清朝帝國武功”所要討論的課題。此處的“帝國武功”主要不在考證清代征戰的歷史,而是析論清宮如何將相關的事件表述為展現帝國武力征服的功績,尤其是作為視覺表述關鍵之戰勛圖像在其中的作用與意義。
跨越傳統畫史的戰爭圖像
相對于歐洲視覺藝術中,戰爭題材作為最高階繪畫類型的歷史畫之分支,有著豐富多元的表現,關于戰爭的圖像在歷代中國畫的題材中則顯得稀少、特殊而邊緣。與一般中國繪畫記錄的通則相反,關于戰爭的繪畫條目少見于傳統畫史著錄,卻多見于正史文獻。傳統書畫著錄中有關戰爭的少數繪畫條目,多非刻畫交戰場面,而是以相關的儀式為題材。且其描繪的主題有限,基本上以唐代的故實為主,例如描寫唐太宗(599~649)于長安近郊的便橋與突厥頡利可汗(579~634)結盟的《便橋會盟圖》與《便橋見虜圖》,以及唐代宗(726~779)時郭子儀(697~781)退回紇的《免胄圖》。兩者經常托名繪畫大家如李公麟(1049~1106)和劉松年,主要出現在元代之后的著錄,但都非畫史常見的題材,也難以在傳統畫史中歸類。例如《宣和畫譜》就毫無記載,也很難歸入其十門“道釋、人物、宮室、番族、龍魚、山水、畜獸、花鳥、墨竹、蔬果”之內。即便現代學者重新發掘出如“子女畫”、 “別號圖”等盛行于特定時空的繪畫類別,或是當今因受到西方藝術史學影響而加以關注的“敘事畫”、“城市圖”等新界定的類型,戰爭圖像也不易歸屬其中。
然而相對于戰爭主題在畫史分類的困難,鮮少記載繪畫藝術的正史文獻中,卻不乏皇權紀念當代或當朝事跡的相關戰爭圖像。其中最為聞名的應屬皇帝詔命繪于宮殿的功臣圖,包括西漢麒麟閣、東漢云臺、唐代凌煙閣、北宋崇謨閣、南宋景靈宮與昭勛崇德閣等,都見于正史記錄。畫史著錄的漢代和唐代功臣圖條目則多傳抄自正史,北宋之后的功臣圖甚至失之未載。除了功臣圖之外,正史尚有個別戰爭圖像的記載。例如《遼史》中更有遼圣宗開泰七年(1018)“詔翰林待詔陳升寫南征得勝圖于上京五鸞殿”、遼興宗重熙十六年(1047)“謁太祖廟觀太宗收晉圖”、遼道宗九年(1063)詔畫 “灤河戰圖”以褒耶律仁先(1013~1072)擊退叛軍皇太弟重元(1021~1063),均是少有畫史著錄和當今學者關注的戰圖材料,但因未傳世而難以確認其樣貌。不過,從這些條目可見相對于其他題材的圖繪,歷代戰爭圖像逆轉了畫史與正史記錄數量的對比,顯示其位處傳統畫史的邊界,卻也因此得以跨入政史的范疇,其特殊性可見一斑。
清宮戰勛圖像的研究
歷代畫史罕見的戰爭題材,卻大量出現在乾隆朝制作的一系列銅版畫中,這顯得十分特殊。其中最先完成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最為聞名,其以看似極為寫實的風格描繪乾隆“十全武功”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準噶爾和新疆的戰役,長久以來都是清史通論和清代藝術展覽不可或缺的宮廷圖作。對歷史學者而言,《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為清帝國大肆推動的武勛文化之一環,與戰碑、方略、戰爭儀式等同屬滿洲尚武精神的表征。對藝術史學者來說,《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既是清代畫院一大特色的紀實畫代表,更是清宮藝術受到西方影響的中西融合風格之見證。雖然兩者都認可《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是理解清帝國政治與藝術的重要媒介,但是學界借由其所展現的清代歷史與美術史樣貌,卻又不脫既有的刻板印象。若將清宮戰勛圖像放在歷史發展中,不論是前述第二節所言這些銅版畫是乾隆朝新出現的武勛文化類型,或第三節所論其亦屬歷代畫史少見的題材,都會發現這些銅版畫戰圖是乾隆朝中期的嶄新表現,那么首要之務或許在于厘清如此特別的圖像制作為何在此時出現,才能進一步探索其意義。

過去藝術史研究對清宮戰圖的討論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將其放在清宮大量出現紀實圖像的脈絡中;二是將其視為西方影響的產物。前者指出清宮圖繪中存在大量歷代少見的描繪當時人物與事件且看似真實之紀實圖繪,《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就是其中一例。學界雖然不乏將個別案例與特定政治脈絡聯結的研究,特別是對于記錄帝國特定人、事、物的討論,如對皇帝肖像、南巡圖、職貢圖等的研究逐漸增多,但對清宮紀實畫作的整體考慮和其意義的探索仍有限。少數有所討論的學者如聶崇正一方面將清宮紀實繪畫的數量與質量歸結為“歐洲傳教士畫家供職宮廷”,另一方面則是清代皇帝的個人因素如“注重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弘歷本人雅好文翰,在位時間長等”,以及滿洲“注重反映自己民族”的特色。然而,這些原因與學界在個案中所見的政治脈絡不甚相干;以《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來說,也未能解決為什么乾隆朝才出現的問題。
后者“西方影響”說強調清宮圖繪中看似視覺真實的效果,挪用了來自歐洲的透視與形塑體積等繪畫技法,明顯地受到西方影響而產生了中西融合的風格。近年來學界對“西方影響”的預設頗多反省,除了挑戰“影響”說的被動性,而改以能動性(agency)來思考中西文化相遇過程中的復雜現象外,也具體探究所謂的“西方”為何,以厘清清宮在全球化脈絡下的定位,都讓清宮畫史有了新的視角。具體就西洋傳教士于北京起稿、送至法國制版印刷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而言,最近畢梅雪(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指出流通廣泛的佛蘭德斯畫家Adam Frans van der Meulen(1632~1690)所制關于法國路易十四(Louis XIV,r. 1643~1715)之銅版戰圖,比過去學界猜測的Georg Philipp Rugendas I(1666~1742)的作品,更可能是啟發乾隆制作《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的歐洲來源。的確,耶穌會士于1697年準備帶到中國的雕版集成(Cabinet du Roi),很可能就囊括Van der Meulen的戰圖銅版畫,本書第五章也討論兩者的確有相近的圖式,而讓我們再次確認清宮與全球視覺網絡的關系。然而,辨認出“西方”的來源,尚不足以回答為什么康熙年間就流入清宮的路易十四時期銅版畫,要到乾隆朝中期才產生影響;或是從能動性的角度來看,何以乾隆宮廷此時開始選擇歐洲銅版戰圖的媒材等問題。
銅版戰圖和其他“中西融合”的清宮圖繪,的確制造出傳統中國畫法難以達成的視覺真實效果,但這不表示清宮紀實圖像為對當時事物的真實寫照,紀實畫并非寫生意義下的寫實作品,卻經常是依據稿本并針對不同需要加以調整,而制造出來的虛擬真實。學界對于明清看待歐洲寫實表現的態度,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從晚明畫壇的曲折回應,明末清初民間的高度興趣,到盛清院畫的直接援引,已然勾勒出在全球化的風潮下,當“中國風”逐漸席卷歐洲的同時,中國也如火如荼地率行“西洋風”。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對寫實表現的追求,會自動隨著時間的移轉而加強;更不表示歐洲繪法的視覺真實效果,可以自動地加諸所有的繪畫題材,衍發出一致的擬真程度。前者如詞臣畫家鄒一桂(1686~1772)的《小山畫譜》,批評西法“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便是著名的例子;后者如《康熙皇帝讀書像》明顯的陰影處理,就與《康熙南巡圖》的正統派做法迥異,顯示西方繪法并非全面地應用在不同主題的圖像,不同題材對于視覺擬真的追求有所差別。也就是說,制造西法的視覺真實效果并非清宮圖繪的共同目標,應該進一步追問的是,歐洲繪法的視覺真實效果,在清宮不同圖繪中有何作用?
就清宮圖繪的祥瑞圖像、職貢圖等沿襲自漢人皇權的視覺傳統,特別是歐洲繪法于其中的作用而言,或可參照同樣以寫實風格著稱的北宋宮廷繪畫。畢嘉珍(Maggie Bickford)對宋徽宗朝祥瑞圖的討論,尤其對思考清宮的類似題材圖繪很有幫助。她一方面比較過去祥瑞題材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對照當時眾多的祥瑞論述,認為宋徽宗朝祥瑞圖“并不只是報導,亦非插圖,更不是徽宗文字記錄的圖像對照,而是……[祥瑞]本身。……徽宗的圖繪以最近、最新的方式精致地演繹古代展示祥瑞征候的傳統。……如果畫家的作用在于制作能夠發揮功能的祥瑞圖像,那么正確地描繪……對于達到預期的結果是很關鍵的”。也就是說,徽宗朝祥瑞圖像的寫實風格并非為了以圖繪證明祥瑞的真實存在,而是以當時所能掌握的最新圖繪技術來正確地制作祥瑞本身。對畢嘉珍而言,清宮制作祥瑞圖像時援引的是此歷史悠久的祥瑞傳統,因此清宮挪用歐洲繪法的目的,容或也未必是以看似寫實的風格來證明祥瑞的真實存在,而是以其所能掌控的最新繪法來正確地制作祥瑞本身。又或者,如果宋代以后的祥瑞文化有了新的變化,那么我們也必須分析清宮祥瑞圖像的寫實風格,在不同祥瑞文化下有什么意義。
同樣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等清宮戰圖中,歐洲繪法所造成的視覺真實效果之作用與意義,亦必須與過去的戰爭圖像相參照,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認識。如此或許也才能跳脫清宮紀實圖像或“西方影響”的框架,這也是為什么本書追溯明清戰爭圖像的發展,以期為清宮戰圖之所以在乾隆朝中期才出現提出解釋,并進而理解戰勛圖像與滿洲尚武文化的關系。
(本文系馬雅貞著《刻畫戰勛: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一書導論,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9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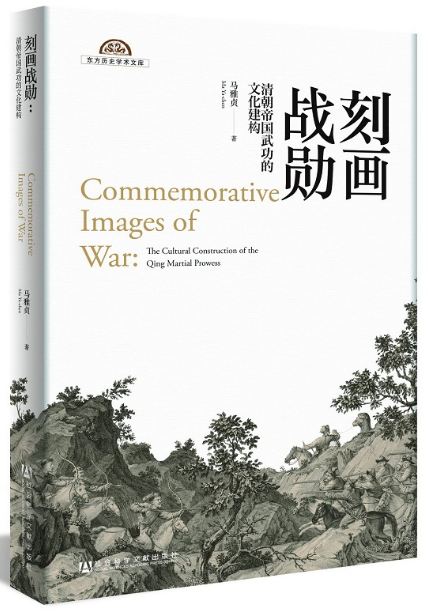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