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個19世紀的英國礦工閱讀希臘哲學到凌晨3點
在人類歷史上,對于很多勞動人民來說,都很難獲得書籍,擁有的閑暇時間也非常少,所以他們的閱讀在物質與方式上都受到了限制。康沃爾郡的木匠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出生于1800年)覺得數學書籍非常耐讀。正如他在自傳中回憶的那樣:一本代數或幾何的專著只花了我幾個先令,我卻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仔細研究。還有一些人的時間不夠用,而不是缺書,比如后來成為書商的詹姆斯·拉金頓(James Lackington,1746-1815),他是倫敦的一名修鞋匠。他設計并和工友們一起遵守著一套令人震驚萬分的睡眠制度,每晚只睡3小時:
我們中的一個人一直熬夜工作,直到其他人在約定的時間起床,等所有人都起床后,我的朋友約翰和你卑微的仆人就在他們工作時輪流為他們大聲朗讀書籍。
蘇格蘭高地的馬具制造工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也展現出了同樣謙卑的奉獻精神,他經常在工作時找別人讀書給他聽,而且每晚舉辦讀書會,“通常有兩三個聰明的鄰居”來參加。這樣他的兒子休(Hugh,1802-1856)成了一位影響重大的作家也就不奇怪了,他改變了地質學研究,也預言了達爾文(Darwin)的未來。另一位早期的蘇格蘭讀者很聰明,他是一個四處游走的石匠,就把自己習慣走的路線教給他的馬,自己就在騎馬時閱讀書籍。
最佳讀者獨創獎必須頒給19世紀的蘇格蘭人詹姆斯·薩默維爾(James Somerville)。他是個流動勞工,有11個孩子,孩子們穿的衣服破破爛爛,都是他們的母親瑪麗(Mary)用收集來的破布縫制的。他們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8歲開始工作,打掃馬廄和挖溝渠。他堅持不懈地閱讀書籍,后來成為恩格斯(Engels)欽佩的政治家,并在自傳中記敘了自己的童年。這家人四處游走尋找工作,住的破舊房屋大多沒有光線,所以詹姆斯隨身帶了一扇完全用玻璃造的窗戶裝在每間住所里。
現在很難想象,對于受過教育的窮人來說,照明是一個多么艱巨的問題。許多工人不得不在月光下閱讀,因為由動物油脂制成的蠟燭——通常是牛油或羊油——太過昂貴,他們買不起,而石蠟制成的蠟燭專屬于富裕家庭。在一些地區,有燈芯草可以使用,拿它浸泡在油脂中制成燈芯草燈,但像動物油脂一樣,燈芯草燈會產生煙霧和臭味,而且需要不斷修剪。難怪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統治時期,圣詹姆斯宮(St James’s Palace)的兩名男仆下班后在市場擺攤賣宮內蠟燭頭,生意興隆。不久之后,他們有了自己的事業:福特南·梅森百貨公司(Fortnumand Mason)。
在缺乏書籍的環境中,最不可能成為安慰書的大部頭著作也能變成一本安慰書。磨坊工人托馬斯·伍德(Thomas Wood,出生于1822年)上學的學校里只有《圣經》,于是他以每周一便士的學費進入了機械學院,他在那里找到了查爾斯·羅林斯(Charles Rollins)的六卷《古代歷史》(Ancient History)。伍德年老后在《基斯利新聞報》(Keighley Nes)上記述了羅林斯“給我留下的印象40年也消抹不去”。薩默塞特郡的一個農家男孩約翰·加農(John Cannon)經常利用去集市的機會溜進一位好心紳士的房子,在那里讀了約瑟夫斯(Josephus)的巨著《猶太古史》(History of the Jews),接著讀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
牧羊人與世隔絕的生活很適合閱讀書籍。威爾特郡的牧童埃德溫·惠特洛克(Edwin Whitlock,出生于1874年)一邊照料羊群,一邊“從頭到尾”閱讀《1867年郵局大全》(1867 Post Office Directory)。這驅使他不斷纏著鄰居向他們討要更多的書。他不到15歲時,就已經讀完了狄更斯和斯科特的“大部分”作品,以及一部12卷的《英格蘭歷史》(History of England)。在蘇格蘭的克拉克曼南,牧羊人約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ie)不僅擁有一個藏書370本的圖書館,還有全套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和《漫步者》(The Rambler)。
與惠特洛克相比,煤礦工人的工作環境像地獄一樣,也許正是因為那樣慘淡的生活,他們從一開始就為了自學煞費苦心。他們打造了“世界各地勞動人民創建的最偉大的文化機構網絡之一”(引自2010年的一份分析報告)。一項關于很多礦工圖書館的研究發現,1741年,最早的礦工圖書館建立于蘇格蘭的格蘭拉納克郡。圖書館里的書包括流行的寓言和“廉價的恐怖小說”,會使礦工變得激進。一位威爾士的礦工回憶道,羅賓漢(Robin Hood)的故事被大量借閱,因為人們喜愛傳達劫富濟貧的思想的故事。
在整個維多利亞與愛德華時代,有一本書比其他任何書籍更能吸引工人階級的讀者。純粹就知名度和影響力而言,哈麗葉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是哈珀·李(Harper Lee)的祖先。在這個給圖書頒獎盛行的時代,我們很難想象斯托的反奴隸制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曾產生過的影響。北威爾士的一名礦工解釋道,這本書“把我們的情緒搞得一團糟。我們感受到鞭子的每一次抽打。我們的內心與靈魂都能感受到切膚之痛”。迪安森林的一位煤礦倉庫管理員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他是怎樣“深受這本書的觸動”的。伊麗莎白·布賴森(Elizabeth Bryson,出生于1880年)是鄧迪一個貧苦人家的女兒,她驚嘆道“啊,這現實呀!”廣泛思考后,她道出了書籍帶來慰藉的本質:
突然之間,振聾發聵的文字在書頁上熠熠生輝,那是我們過去無法見到的。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是誰,這個“我”又是什么?我從三歲起就一直在探索這個問題。——《驚奇回顧》(Look Backin Wonder,1966)
“一位普通人”寫于1935年的匿名自傳講述了他怎樣在工廠里偷偷摸摸地閱讀斯托的書,閱讀時許多“咸澀的眼淚”落在他的“號碼印字機”上。
大男子主義的工友會對讀者帶來危險,水手倫諾克斯·克爾(Lennox Kerr,出生于1899年)發現自己因為閱讀書籍而“受到懷疑”:
我必須一見到機會就接受每一個挑戰,比如哪怕我不愿意也要狠揍別人的臉,或是吹噓自己捻接繩子的技術——來證明我即使閱讀書籍也沒有影響自己當個好水手。
然而克爾也敏銳地察覺到:
人們感覺自己……不受公共場合中他人的冷嘲熱諷審視時,內心的隱秘渴望就會浮現出來。他們那內心深處創造的渴望出現了,而不僅僅是當個聽話的工人……在諱莫如深的黑暗中,他們更加浪漫、更加勇敢、更加有詩意……我聽說有個人,他是我們船上嘴巴最下流的,卻在黑暗中對著海浪拍打船首的沙沙聲朗誦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獨處時,人成為他想成為的樣子,而不是被迫假裝自己的性格。——《渴望的歲月——自傳》(The Eager Years: An Autobiography,1949)
老板們似乎對待工人在工作場所讀書寫字持寬容態度。一位斯溫頓火車工廠的工人閱讀了奧維德(Swindon)、柏拉圖(Plato)和薩福(Sappho)的原版書籍,然后用粉筆在車床上寫下了希臘和拉丁字母。工頭一開始讓他把這些字清理干凈,但得知了這是什么后,他的態度發生了好轉。羅蘭·肯尼(Rowland Kenney,出生于1883年)偷偷地閱讀書籍,直到有一天他的工頭“用帶著蘭開夏郡口音的聲音鏗鏘有力地”朗誦了丁尼生(Tennyson)的《食蓮人》(The Lotos-Eaters)。他才放下心來。因為“如果像他這樣一個愛打架、喝酒、該下地獄的人”也喜愛詩歌,那么肯尼也可以光明正大地閱讀書籍。
諾丁漢郡的礦工喬治·湯姆林森(George Tomlinson)也有過同樣令人感動的驚喜。他習慣了在“離地面半英里的地方”閱讀書籍,卻被工頭打了一頓,因為他在讀一首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詩時,讓幾輛運煤卡車撞車了。第二天,工頭把自己的一大堆詩集借給了他,并附上了警告:“如果你把他們帶進煤礦坑,我就敲掉這塊木板。”后來,一個礦工工友撿起了他掉落的幾頁自己寫的詩,湯姆林森羞愧得無地自容,但他的同事只是說,“不太好,小伙子。你想讀雪萊的詩”。

1871年,倫敦南達勒姆煤礦工人
這段經歷簡直難以置信:蘭開夏郡的礦工喬·基廷(Joe Keating,出生于1871年)把礦渣從煤礦中鏟出,筋疲力盡后還要在家閱讀希臘哲學直到凌晨3點。他私下與一位不知名的工友交流,我把這位工友叫作C:
C嘆了一口氣,說:“天堂隱藏著萬物命運之書。”
喬·基廷說:“你引用了蒲柏(Pope)的詩嗎?”
C說:“啊,我和蒲柏英雄所見略同。”
這次交流之后,基廷不再感到那么受疏遠了,還組建了一個室內弦樂四重奏樂隊,演奏莫扎特和舒伯特(Schubert)的作品。
工人階級閱讀書籍的歷史難以考證,在傳記和書籍的歷史中記述都有不足。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在紐約生活時,在偶然的一天見到了一幅比現有敘述都要意蘊豐富的景象:一位非裔美國卡車司機向他介紹了《羅熱同義詞詞典》(Roget’s Thesaurus),一位酒店服務員在他講課時引用了布萊克和馬克思的話,一位雜技演員讓他閱讀了伯頓(Burton)的《憂郁的剖析》(Anatomy of Melancholy,1621)。旁邊那個不倒翁順便操著濃重的布魯克林口音解釋說,伯頓對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影響是深遠的。
令人驚訝的是,當分析無產階級閱讀時,有時仍然是以居高臨下的態度進行的。2001年,一位學者在評論卓別林自己的閱讀時,從叔本華(Schopenhauer)和柏拉圖到惠特曼(Whitman)和愛倫坡(Allan Poe),稱其為“哲學與情景劇、高雅文化與低俗喜劇的雜種,體現了自學成才者的典型口味”。“雜種”這個詞散發著文化優劣論的臭味,暗示著血統純正的高等生物避開了“低俗喜劇”。當然,無數偉大的小說家,許多博士的催生者,正是通過這種折中主義而變得偉大。
有觀點認為,普通人能直接接觸到書籍既是一種威脅又是一種驚喜。托馬斯·伯克(Thomas Burke)是一位研究倫敦東區生活的歷史學家,他因“時尚高雅的倫敦西區小說家”傲慢自大,看不起與他同住在白教堂區的人而感到憤怒。1932年,他寫道:
我們的一位“有文化的小說家”以驚奇的口吻記錄道,拜訪白教堂區的一戶人家時,這家的女兒們正在閱讀普魯斯特(Proust)的書籍和契訶夫(Chekhov)的一卷喜劇。這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真實的倫敦東區》(The Real East End,1932)
伯克指出,貝思納爾格林圖書館里總是擠滿了當地人。我的父親(出生于1913年)成長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他的警察繼父住在貝思納爾格林,他們一貧如洗,雖然他14歲就輟學了,但是他所閱讀的書籍非常廣泛。
另一位不看好自學成才的學者是Q.D.利維斯(Q.D. Leavis)。她憧憬著一個黃金時代,那時“大眾獲得的娛樂都來自高級趣味,而不是記者、電影制作人與流行小說家的迎合之作”。
弗吉尼亞·伍爾芙努力理解大眾的閱讀習慣:
我經常問我那些沒文化的朋友……為什么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一本通俗的書都不買。對此,沒文化的朋友回答道——我沒法模仿他們的語言風格——他們認為自己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人。——《伍爾芙隨筆集》(The Collected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2013)
現在,英國文學史上有一種略顯瘋狂的理論,認為現代主義者開始晦澀地協作是為了抵御無產階級讀者,因為這些讀者正在變得傲慢自負,入侵了文學殿堂。這一理論還認為,當普通民眾開始閱讀而且該死地理解了艾略特(Eliot)和伍爾芙的作品,后現代主義就應運而生,以擊退登上了文學界這艘大船的新無產階級寄宿者。后現代主義的斯文加利(Svengali),雅克·德里達看似是一個民主人士。他斷言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間沒有區別,暗示麥當娜(Madonna)的演唱會和《哈姆雷特》(Hamlet)一樣好,因為藝術發生在觀眾或讀者的腦海里。但他自己寫的散文卻是一團亂麻,令識字的大眾望而卻步。正如一位看過他演講的評論家所說,他與其說是一位邏輯學家,不如說是一位行為藝術家,他玩弄文字,享受著一種非常法式的自由聯想模式。他自己也沒有通過民主試金石的測試,因為在學術界之外沒人閱讀過他的作品。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坦率得驚人,他預言了“一個以藝術區分的新貴族”會像以血統區分的舊貴族一樣冷嘲熱諷地愚弄大眾。畢竟,他要對付的是“與兔子一樣的頭腦賽跑……我們是巫醫和巫毒的繼承人。我們這些長期被人鄙視的藝術家就快能拿到控制權了”。為了確保成功取得控制權,龐德的意象派試圖為“意象派”這個詞申請專利,防止拙劣的模仿者入侵這一新風格。那是在1914年,大約是在巴特西郵差的兒子理查德·丘奇的童年時代,他在自傳《橋上》(Over the Bridge)中哀嘆,“普通人能接觸到書籍的問題在于知識分子無法從中獲益”。令人高興的是,龐德的繼承人桂冠詩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和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都來自“兔子”階級,而作家的背景對作者和讀者來說都不是關注的焦點。
為了結束這一節,我忍不住要講一個麥考利講過的故事,講的是工人階級對“經典名著”的真實反應,它闡明了一條道理:你不可能永遠愚弄所有的人。18世紀時,一位意大利罪犯被賦予這樣的選擇,要么被判成為一名苦役犯,要么選擇閱讀朱卡迪尼(Giuccardini)20卷的《意大利歷史》(History of Italy)。他剛開始選了那本書,但讀了幾章就改變了主意,成了“劃槳的奴隸”。
無產階級、普通民眾,或者隨便什么你用來形容草根讀者的詞,都經歷了艱難的歲月,他們為了獲得書籍以及閱讀書籍的自由和光明而斗爭。他們面對的敵人遍布可怕的當權派。每個階層的女性讀者都面臨過非同一般的障礙,卻通過振奮人心的獨特方式,用智慧來規避這些障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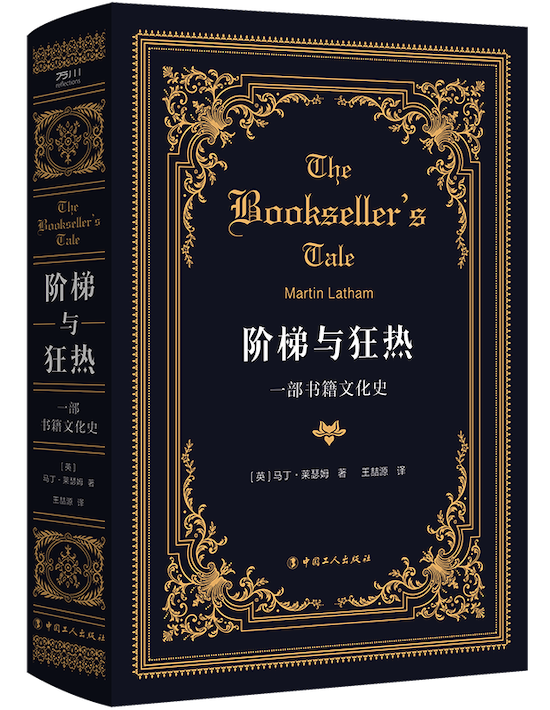
(本文摘自馬丁·萊瑟姆著《階梯與狂熱:一部書籍文化史》,王喆源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1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