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是置身歷史之外,還是更深刻地代表了時(shí)代? | 人物·茨維塔耶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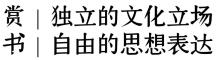
俄羅斯白銀時(shí)代女詩(shī)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被布羅茨基等人視為“20世紀(jì)最偉大的詩(shī)人”。茨維塔耶娃的詩(shī)以生命和死亡、愛情和藝術(shù)、時(shí)代和祖國(guó)為主題,被譽(yù)為不朽的、紀(jì)念碑式的詩(shī)篇。她的詩(shī)在詩(shī)歌界有廣泛影響,擁有龐大讀者群。她的詩(shī)歌選集《致一百年后的你》遴選了詩(shī)人一生各個(gè)時(shí)期代表作品,既有少女時(shí)代熱烈的詩(shī)篇,也有困苦的流亡生涯中對(duì)故國(guó)的思念,一直到臨終前的絕筆。
作為一個(gè)二十世紀(jì)的流亡者,茨維塔耶娃的命運(yùn)充滿了悲劇色彩,但她的詩(shī)學(xué)世界卻是完整而多面的,她時(shí)而是“象征主義的信徒”,時(shí)而又展現(xiàn)出阿克梅主義的特點(diǎn)。茨維塔耶娃的詩(shī)句飽含熱情、大膽奔放,應(yīng)和了她跌宕的人生。她的文體精確、清晰、輪廓分明,她的詩(shī)才激烈、活潑、有力,詩(shī)歌的節(jié)奏是快速劇烈的斷奏,她的詩(shī)是感嘆,而不是雄辯。她精心修飾的句子如同閃爍的火花,像電流一樣穿過人的全身。互不聯(lián)系的詞語(yǔ)被用來作為跟上詩(shī)人步伐的路標(biāo)。
詩(shī)人的命運(yùn):瑪麗娜?茨維塔耶娃

文 | 馬克?斯洛寧
譯 | 浦立民 劉峰
天才少女茨維塔耶娃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1892-1941)的詩(shī)歌與曼德爾施塔姆和阿赫馬托娃的詩(shī)歌迥然不同,它在俄羅斯二十世紀(jì)文壇上占有獨(dú)一無二的地位。瑪麗娜作為一個(gè)藝術(shù)史教授和莫斯科博物館館長(zhǎng)的女兒,是在學(xué)者和藝術(shù)家們極有教養(yǎng)的環(huán)境中長(zhǎng)大的;她陪同她患病的母親(一位優(yōu)秀的音樂家)到了國(guó)外,在瑞士的學(xué)校上過學(xué),精通法語(yǔ)和德語(yǔ)。據(jù)她在回憶錄中說,她六歲就開始“作詩(shī)”,十六歲就發(fā)表了第一首詩(shī)。幾年以后,她發(fā)表了兩本詩(shī)集,但一直瞞著家人。這兩本詩(shī)集是《黃昏的紀(jì)念冊(cè)》(1911)和《神燈》(1912),當(dāng)時(shí)只引起幾個(gè)詩(shī)人和鑒賞家的注意。1912年以后,茨維塔耶娃寫了許多轟動(dòng)一時(shí)的詩(shī)歌,反映了她激情的氣質(zhì)和驚人的嫻熟的技巧。1922年,莫斯科國(guó)家出版社出版了茨維塔耶娃的兩本書:詩(shī)體民間故事《少女王》和《里程碑》(帕斯捷爾納克說,他為這本薄薄的小冊(cè)子的抒情力量完全吸引住了)。1912年,她和大學(xué)生謝爾蓋?埃夫龍結(jié)了婚,并為他生了個(gè)女兒阿里阿德娜,人們都叫她阿利婭。后來她又生了個(gè)女兒。但在瑪麗娜過著悲慘而貧困生活的革命時(shí)期,這個(gè)女兒由于營(yíng)養(yǎng)不良而夭折了;他的丈夫當(dāng)時(shí)正在南方和反共產(chǎn)黨的軍隊(duì)作戰(zhàn)。戰(zhàn)爭(zhēng)勝利后,瑪麗娜被批準(zhǔn)出國(guó);1922年他們一家在柏林再次團(tuán)聚。這時(shí),俄文書籍在德國(guó)很受歡迎,茨維塔耶娃出版了三本小冊(cè)子,即《離別集》《獻(xiàn)給勃洛克的詩(shī)》和《普緒赫》,還有一部題為《手藝集》的詩(shī)集,這部詩(shī)集確立了她作為流亡者中第一流詩(shī)人的聲譽(yù)。她的一家后來遷居到布拉格。1925年,茨維塔耶娃又生了個(gè)男孩(取名格奧爾吉,母親叫他穆爾)。隨后,全家定居法國(guó),從1926年至1939年他們住在巴黎的近郊。
從不幸的流亡者到最偉大的詩(shī)人
茨維塔耶娃是在她創(chuàng)作的全盛時(shí)期到歐洲的。在十七年的流亡生活中,她創(chuàng)作了她的最佳詩(shī)歌和散文。旅居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幾年,是她創(chuàng)作最旺盛的時(shí)期,也證實(shí)了她是有創(chuàng)新天才的詩(shī)人。她的兩首長(zhǎng)詩(shī)《山之詩(shī)》和《終結(jié)之詩(shī)》都是描寫愛情,愛情的錯(cuò)綜復(fù)雜,不同情感的對(duì)比,以及遭受分離折磨的痛苦。它們措辭劇烈,感情深刻,辭藻華麗;還有長(zhǎng)達(dá)七十五頁(yè)的詩(shī)體故事《花衣吹笛手》(即《捕鼠者》)無可置疑,這些都是二十世紀(jì)俄國(guó)詩(shī)歌中最優(yōu)秀的作品。《花衣吹笛手》是根據(jù)中世紀(jì)一個(gè)神話故事寫成的,其中一部分無情地揭露了德國(guó)小城鎮(zhèn)哈麥恩的自由民那種心胸狹隘、平淡無奇、卑鄙自私的心理狀態(tài);這個(gè)城鎮(zhèn)因耗子侵襲為患。另一部分則是一個(gè)浪漫故事,描寫一個(gè)神秘的青年吹笛手,并把他作為詩(shī)歌和魔法的象征。老鼠隨著笛聲而離開了這個(gè)小鎮(zhèn);吹笛人要求同市長(zhǎng)美麗的女兒格麗塔結(jié)婚作為酬報(bào)。他遭到了斥責(zé)和辱罵;為了報(bào)仇,他用迷人的笛聲拐走了城鎮(zhèn)上的兒童。吹笛人把兒童引到一個(gè)幻想的天堂,他們愉快地溺死在一個(gè)神秘的湖泊中。
這種被茨維塔耶娃稱之為“抒情性諷刺作品”的形式是別具一格的。它連續(xù)運(yùn)用剛勁急促的韻律,詩(shī)中多警句,經(jīng)常壓縮到一個(gè)詞,顯示出她使用語(yǔ)言的精湛技巧,這種技巧把簡(jiǎn)練的釋義和銳利的箴言結(jié)合在一起。《花衣吹笛手》于1926年在布拉格俄文月刊《俄羅斯意志》上全文刊登。可是,當(dāng)時(shí)流亡國(guó)外的評(píng)論家們沒有領(lǐng)悟到它那種無與倫比的獨(dú)創(chuàng)性。四十年后,《花衣吹笛手》經(jīng)過審查官的稍稍刪改后,就在1965年莫斯科出版的茨維塔耶娃詩(shī)集中重新刊出。
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茨維塔耶娃于1928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整卷詩(shī)集《離開俄羅斯以后》,這是她生前發(fā)表的最后一部作品,而這一次流亡者的報(bào)刊對(duì)這一文學(xué)事件又未予以重視(當(dāng)然,在蘇聯(lián)就根本沒有提及這件事)。這是她悲慘命運(yùn)中的典型事件之一。在蘇聯(lián),她的作品被禁止發(fā)表長(zhǎng)達(dá)三十年之久。當(dāng)她在歐洲流亡時(shí),她的作品只為一小部分內(nèi)行的讀者所欣賞。更糟糕的是,她不得不在極端困苦的物質(zhì)條件下寫作。在這十七年中,她時(shí)刻遭受貧困的威脅,不得不為生存而斗爭(zhēng)。她要解決兩個(gè)孩子和體弱多病的丈夫的衣食,還得照顧他們。瑪麗娜除了在家中燒飯、洗衣和護(hù)理外,還得養(yǎng)家糊口。整整幾個(gè)月,全家的收入主要靠她微薄的稿酬和少數(shù)幾個(gè)朋友偶爾的資助。她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寫道:“你簡(jiǎn)直不能想象,我過著怎樣貧困的生活。除了寫作,我沒有其他掙錢的門路。我們正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
但是經(jīng)濟(jì)困難還不是茨維塔耶娃最大的不幸,還有寂寞和孤獨(dú);她痛苦地意識(shí)到,賞識(shí)她的作品的人寥寥無幾。她從不懷疑自己作品的價(jià)值,但她感到氣憤的是,流亡者和俄國(guó)人都不重視她。與此同時(shí),她的女兒阿利婭決定返回俄國(guó);此外她的丈夫謝爾蓋由于政治上的變化,不僅倒向共產(chǎn)主義,而且還使他卷入1937年由一名前共產(chǎn)黨官員,蘇聯(lián)秘密特務(wù)伊格納西?雷斯進(jìn)行的暗殺事件之中。瑪麗娜對(duì)此事一無所知,而埃夫龍從法國(guó)逃往莫斯科的事,對(duì)她來說真不啻是晴天霹靂。她和她年方十三歲的兒子留在巴黎。兒子也熱切要求母親回到祖國(guó)去。她在流亡者中的處境簡(jiǎn)直難以維持下去;最后只得跟隨丈夫和女兒一起回到蘇聯(lián)。盡管她認(rèn)為這樣做是她的責(zé)任,但她是懷著沉重的心情和不抱任何幻想離開法國(guó)的。她曾對(duì)一個(gè)朋友說:“我在這兒是多余的人。到那邊去也是不堪設(shè)想的;在這兒我沒有讀者;在那邊,盡管可能有成千上萬(wàn)個(gè)讀者,但我也不能自由呼吸;也就是說,我不能創(chuàng)作和出版詩(shī)集。”但是,她在莫斯科的遭遇卻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她原先的可怕預(yù)測(cè)。
從1939年她回到蘇聯(lián)直到她逝世為止,她能發(fā)表的僅僅是一首早期的詩(shī)歌,并且只能翻譯一些外國(guó)詩(shī)人的作品。幾個(gè)月后,她的丈夫、女兒和姐姐都被捕了。阿利婭在監(jiān)獄、集中營(yíng)和西伯利亞的流放中一共度過了十六個(gè)年頭。1956年她才被“恢復(fù)名譽(yù)”,以后住在卡盧加附近的塔魯薩,直到1975年逝世為止。我們至今仍然不知道埃夫龍被處死的確切日期:可能是在1940年,也可能是在戰(zhàn)爭(zhēng)剛爆發(fā)時(shí)。
1941年,當(dāng)?shù)萝娤蚰箍仆M(jìn)的時(shí)候,茨維塔耶娃和她的兒子穆爾撤退到葉加布拉,這是韃靼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自治共和國(guó)卡馬河畔的一個(gè)村莊。有一些作家住在她附近,但她向他們求助,都遭到了冷遇。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在一個(gè)餐館里當(dāng)女廚子。她的兒子身材魁梧,要求參加志愿軍;這時(shí)候,她覺得自己完全孤獨(dú)了,周圍的一切都對(duì)她冷漠或敵視。她感到一切都在一種世界性的災(zāi)難中崩潰了。1941年8月31日,她懸梁自盡,被埋葬在一個(gè)公墓里。沒有人參加她的葬禮。
茨維塔耶娃死去二十年以后,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她才在蘇聯(lián)國(guó)內(nèi)外以及流亡者中間獲得了贊譽(yù)。筆者自1923年以來一直在做促使她作品出版的工作。1952年筆者曾公開表示這樣的看法:“重新發(fā)現(xiàn)茨維塔耶娃的作品,對(duì)它們重新作出評(píng)價(jià)。并給予應(yīng)有地位的日子即將到來。”1957年,帕斯捷爾納克在他的《人與事》中寫道:“她的作品的出版對(duì)俄羅斯詩(shī)歌來說將是一個(gè)偉大的勝利和偉大的發(fā)現(xiàn),這一姍姍來遲的禮物必將立即充實(shí)并一舉震動(dòng)俄國(guó)詩(shī)壇。”到那個(gè)時(shí)候,她的手抄本詩(shī)篇必將激起俄國(guó)青年們背誦她詩(shī)歌的熱情。新的詩(shī)人競(jìng)相效仿茨維塔耶娃,并稱頌她為他們的大師。她的聲譽(yù)和影響正在令人難以置信地日益增長(zhǎng)著,她的許多詩(shī)歌已在文學(xué)年鑒上重行刊登,1961年出版了她的詩(shī)選,四年之后又出版一本有各種注釋的、厚達(dá)八百頁(yè)的詩(shī)集,并附錄一些論文、回憶錄和評(píng)論。無論在東方或西方,人們都普遍地認(rèn)為茨維塔耶娃是本世紀(jì)最偉大的俄羅斯詩(shī)人之一。
她要表現(xiàn)運(yùn)動(dòng)著的、永不寧?kù)o的自然力
凡是認(rèn)識(shí)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人,同筆者一樣,都還記得她是一個(gè)身材苗條、為人正直的年輕婦女,一頭金發(fā),襯托著一張端莊、自重的臉龐,常常由于她那奇妙的微笑和一對(duì)大大的近視眼而顯得神采奕奕。她的個(gè)性和她的藝術(shù)(帕斯捷爾納克稱頌她的藝術(shù)“技巧之卓無與倫比”)同樣地吸引著人們。從根本上來說,她是個(gè)浪漫主義者,她似乎要體現(xiàn)和表達(dá)出運(yùn)動(dòng)著的和永不寧?kù)o的自然力,一股沖破人間的牢籠永遠(yuǎn)向上的浪潮。實(shí)質(zhì)上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傾向,近似“狂飆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的荷爾德林和其他德國(guó)詩(shī)人的精神,但它卻沒有軟弱、悲傷和憂郁。一些評(píng)論家談?wù)撍哂小敖韼接⑿邸钡臍飧拧1M管她寫下了大量有關(guān)愛情的抒情詩(shī),但她確實(shí)具有一種活力,一種和她的女性容貌、羞怯而文雅的舉止似乎不相稱的激動(dòng)和力量。
她像所有真正的詩(shī)人一樣,致力于使現(xiàn)實(shí)理想化,并把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事變?yōu)榧?dòng)人心的事件,變?yōu)橐环N令人振奮,經(jīng)常是神話式的東西。她把客觀的事實(shí)、感情和思想加以擴(kuò)大:不論當(dāng)時(shí)什么樣的東西占據(jù)她的思想和心靈,她都以非常強(qiáng)烈的手法,用詩(shī)歌或者更簡(jiǎn)單的對(duì)話來表達(dá)它們,使她的讀者和聽眾都能全神貫注。她妙語(yǔ)連珠,并倍加欣賞精通快速對(duì)話游戲的對(duì)話者。這種對(duì)話酷似網(wǎng)球比賽,詞句像來回飛舞著的網(wǎng)球。她是個(gè)智力超群、思維敏捷的女子,能把幽默感和駕馭抽象概念的能力結(jié)合起來而不失對(duì)具體現(xiàn)實(shí)的理解。她廣泛地閱讀世界各國(guó)文學(xué)作品,具有敏銳的評(píng)判能力和驚人的記憶力——這明顯地表現(xiàn)在她的論文和散文體的回憶錄中。盡管她與形而上學(xué)相距甚遠(yuǎn),并且把上帝的問題留給神學(xué)家們(她不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解決。但是,她試圖在塵世間,在人的身上和大自然中尋找神圣的火花。這種尋求是過分的,就像她對(duì)詩(shī)歌、對(duì)創(chuàng)作的想象力或?qū)^去的偉大人物的激情也是過分的一樣。在她一生的各個(gè)時(shí)期,她曾崇拜過拿破侖或歌德;而且她會(huì)突然把一些孤立的同時(shí)代人置在受人尊敬的地位,隨后又突然會(huì)把他們推倒在地;她常常由夸張的贊美變成極端的失望。她從來沒有保持中立或冷漠的態(tài)度,而總是似癡似狂地?zé)釔刍蛘咴骱匏囆g(shù)作品或個(gè)人。她特別喜歡的格言之一是:“文學(xué)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愛來推動(dòng)的。”她意識(shí)到,自己過分的熱情和憎恨使她無法適應(yīng)日常生活的常規(guī)。“在這個(gè)錙銖必較的世界中。我對(duì)我過分的感情激動(dòng)該怎么辦呢?”她在一首暴露性很強(qiáng)的詩(shī)歌中感嘆道。
她在流亡者的文學(xué)世界里給人們留下了一個(gè)奇特而獨(dú)一無二的形象,在那里,先前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不是保守主義便是象征派和阿克梅派的傳統(tǒng)思想。茨維塔耶娃偶然也使用象征派的隱喻,她還喜歡勃洛克和別雷,但她既不是他們一派的人,也不屬于其他任何流派。她的作品的整個(gè)要旨以及大膽進(jìn)行語(yǔ)言實(shí)驗(yàn)使她接近于赫列勃尼可夫和帕斯捷爾納克,并有時(shí)接近于馬雅可夫斯基;一般說來,她屬于二十年代的先鋒派。她的文體是精確、清晰、輪廓分明,她喜歡銅管樂器勝過長(zhǎng)笛,她的詩(shī)才的特征是激烈、活潑、有力,詩(shī)歌的節(jié)奏是快速劇烈的斷奏,有強(qiáng)烈的重讀,分散的詞和音節(jié)頓挫合拍,就這樣從一行或一個(gè)對(duì)句轉(zhuǎn)到另一行或另一個(gè)對(duì)句(連行)。詩(shī)人強(qiáng)調(diào)的是表達(dá)和詞的重讀,而不是悅耳的曲調(diào)。她不像馬雅可夫斯基那樣大聲叫嚷,她的詩(shī)是感嘆,而不是雄辯,她喜歡演奏打擊樂器而不是小號(hào)。但是她的呼聲經(jīng)常是刺耳的,幾乎成了尖叫。
這位被她文學(xué)上的敵手稱為亞馬孫的詩(shī)人,對(duì)自己的要求同對(duì)別人一樣嚴(yán)格:她憎恨一知半解的非專業(yè)者和空洞的贅言,并不惜時(shí)間去找尋正確的詞匯和一種適當(dāng)?shù)恼Z(yǔ)調(diào)。她這樣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作品中,倒有點(diǎn)兒像個(gè)苦行者。當(dāng)人們指責(zé)她的自我主義太過分時(shí),她回答道:“人在世間的唯一任務(wù)是忠于自己,真正的詩(shī)人總是自己的囚犯;這種堡壘比彼得—保羅要塞還要堅(jiān)固。”
茨維塔耶娃的詩(shī)作初看起來似乎是晦澀難解的,但這種表面的印象主要是由于她那簡(jiǎn)潔的、幾乎是電報(bào)式的文體所造成的。這種文體截然不同于平庸的蹩腳詩(shī)人的那種冗長(zhǎng)累贅、捉摸不定和結(jié)結(jié)巴巴的胡言亂語(yǔ)。她精心修飾的句子如同閃爍的火花,像電流一樣穿過人的全身。往往省略了短語(yǔ)之間的語(yǔ)法連接,不斷破壞詞語(yǔ)的連貫;同時(shí),互不聯(lián)系的詞語(yǔ)被用來作為跟上詩(shī)人越來越快的步伐上的路標(biāo)。除了她二十年代初的民間故事《少女王》和《小伙子》外,方言只是她極為豐富的詞匯量的一部分,并且同她優(yōu)美的韻律和語(yǔ)言創(chuàng)新融為一體。
她喜歡采用追溯詞根的方法。她通過去掉前綴,改變?cè)~尾及一、二個(gè)元音或輔音(有點(diǎn)像法國(guó)的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者)而成功地揭示各種詞語(yǔ)的原始意義。她巧妙地運(yùn)用了語(yǔ)音學(xué),從聲音的接近中得到詞語(yǔ)的新意義。例如,她的長(zhǎng)詩(shī)《山之詩(shī)》就是建立在俄語(yǔ)“山岳”(ropá)和“悲哀”(rópe)這兩個(gè)詞的相近發(fā)音上,她從這個(gè)主詞中驚人地引伸出大量的派生詞來。這種“音素的游戲”并沒有蛻化為矯揉造作和玩弄語(yǔ)言的拙劣伎倆。這種對(duì)詞語(yǔ)“核心”和“真情”的探索,不僅使詞語(yǔ)重放光彩,而且還賦予它們更深的含義,襯托出它們感情上的實(shí)質(zhì)和概念的價(jià)值,從而達(dá)到了一種形式和精神罕有的統(tǒng)一。她的簡(jiǎn)短有力的詩(shī)行、韻律、頭韻,暴風(fēng)雨般的節(jié)奏,高度激勵(lì)人心的感嘆,表現(xiàn)了詩(shī)人不屈不撓的、叛逆的天性。
是置身歷史之外,還是更深刻地代表了時(shí)代?
茨維塔耶娃在身后獲得的榮譽(yù),終于使當(dāng)局經(jīng)過一再拖延之后承認(rèn)了她的地位。她的姐姐阿娜斯塔霞從監(jiān)獄釋放后,于1960年來到葉加布拉,并在那塊人們認(rèn)為埋葬著女詩(shī)人遺體的墓地上,豎起了一個(gè)簡(jiǎn)單的木十字架,上面寫明茨維塔耶娃出生和死亡的日期。這就是在蘇聯(lián)對(duì)這位偉大詩(shī)人唯一的公開紀(jì)念。但是,她的詩(shī)歌卻活在千百萬(wàn)人的心里。茨維塔耶娃的詩(shī)歌和大量的蘇聯(lián)普通詩(shī)歌截然不同,無數(shù)讀者都重視這一事實(shí)。她一反那種空洞而虛偽的宣傳或口號(hào),以及政治性的和愛國(guó)主義的夸夸其談,而提供了完全真實(shí)的、純抒情的和獨(dú)特的題材;它們充滿著真摯的情感,浪漫主義的幻想,對(duì)獨(dú)立的歌頌,對(duì)愛情和大自然的憧憬。單從她的一整套詩(shī)的題目來看,也頗新穎別致:《空氣之詩(shī)》《樹木》《云彩》《阿芙洛狄忒贊》《紅馬》和《步行頌》。她的劇本是獻(xiàn)給卡薩諾瓦和十八世紀(jì)的其他探險(xiǎn)家的;在她強(qiáng)有力的和富有想象力的論文中,包括豐富多彩的回憶錄和內(nèi)心獨(dú)白中,描寫了她所熟悉的作家和藝術(shù)家。她的書信由于具有高度文學(xué)價(jià)值而成為她著作中另一重要的篇章。例如,她和帕斯捷爾納克進(jìn)行柏拉圖式戀愛的通信。
茨維塔耶娃作品的整個(gè)內(nèi)容對(duì)于在束縛下的蘇聯(lián)讀者看來是完全與眾不同的,因?yàn)樗彤?dāng)時(shí)發(fā)生的事件以及俄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政治環(huán)境的現(xiàn)實(shí)毫無聯(lián)系。在二十年代初,她在詩(shī)作《天鵝營(yíng)》和《彼列科普》中,贊揚(yáng)過的“白軍”(這兩首詩(shī)在她死后在國(guó)外出版),1939年,她為納粹占領(lǐng)她親愛的捷克斯洛伐克而寫了一系列歌頌自由的詩(shī)篇。但是,在她其余的作品中,竟沒有一篇是與革命有關(guān)的。她置身于歷史之外的生活、幻想和創(chuàng)作;她也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有一次說道:“我和我的世紀(jì)失之交臂。”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詩(shī)人雖然和她周圍的生活相隔如此遙遠(yuǎn),卻使用了最革命的詩(shī)體和富有挑釁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試圖徒勞地用教條和口號(hào)來駕馭詩(shī)歌的御用詩(shī)人來,她就更真實(shí)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個(gè)時(shí)代的精神。
(選自《致一百年后的你:茨維塔耶娃詩(shī)選》,有刪節(jié),經(jīng)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小標(biāo)題為編者所加)
【相關(guān)圖書】

致一百年后的你:茨維塔耶娃詩(shī)選
[俄]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 / 蘇杭 / 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 2021-9
本書是茨維塔耶娃的詩(shī)歌選集,由俄語(yǔ)譯者蘇杭先生選譯,譯文忠實(shí)可靠。本書包含了茨維塔耶娃100來首抒情短詩(shī)以及一首敘事詩(shī)《山之歌》,收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詩(shī)歌世界》《兩個(gè)詩(shī)人——兩位女性——兩種悲劇》《詩(shī)人的命運(yùn):瑪麗娜·茨維塔耶娃》三篇長(zhǎng)文,文章均出自俄國(guó)頗有聲譽(yù)茨維塔耶娃研究者之手,深入解讀詩(shī)人的精神世界和詩(shī)歌藝術(shù)。書名來自傳唱廣泛的同名詩(shī)歌,茨維塔耶娃對(duì)詩(shī)歌形式的革新亦在這本詩(shī)選中體現(xiàn)出來。詩(shī)人見證了二十世紀(jì)二三十年代的戰(zhàn)爭(zhēng)和變革,她的詩(shī)同時(shí)也展現(xiàn)出悲劇性的社會(huì)變革中,個(gè)體意識(shí)和精神生活的轉(zhuǎn)向,成為一種時(shí)代的現(xiàn)象。
原標(biāo)題:《是置身歷史之外,還是更深刻地代表了時(shí)代? | 人物·茨維塔耶娃》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