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千年王安石︱變革下的日常:北宋熙寧時期的理政之道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爭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致“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后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后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面貌,以饗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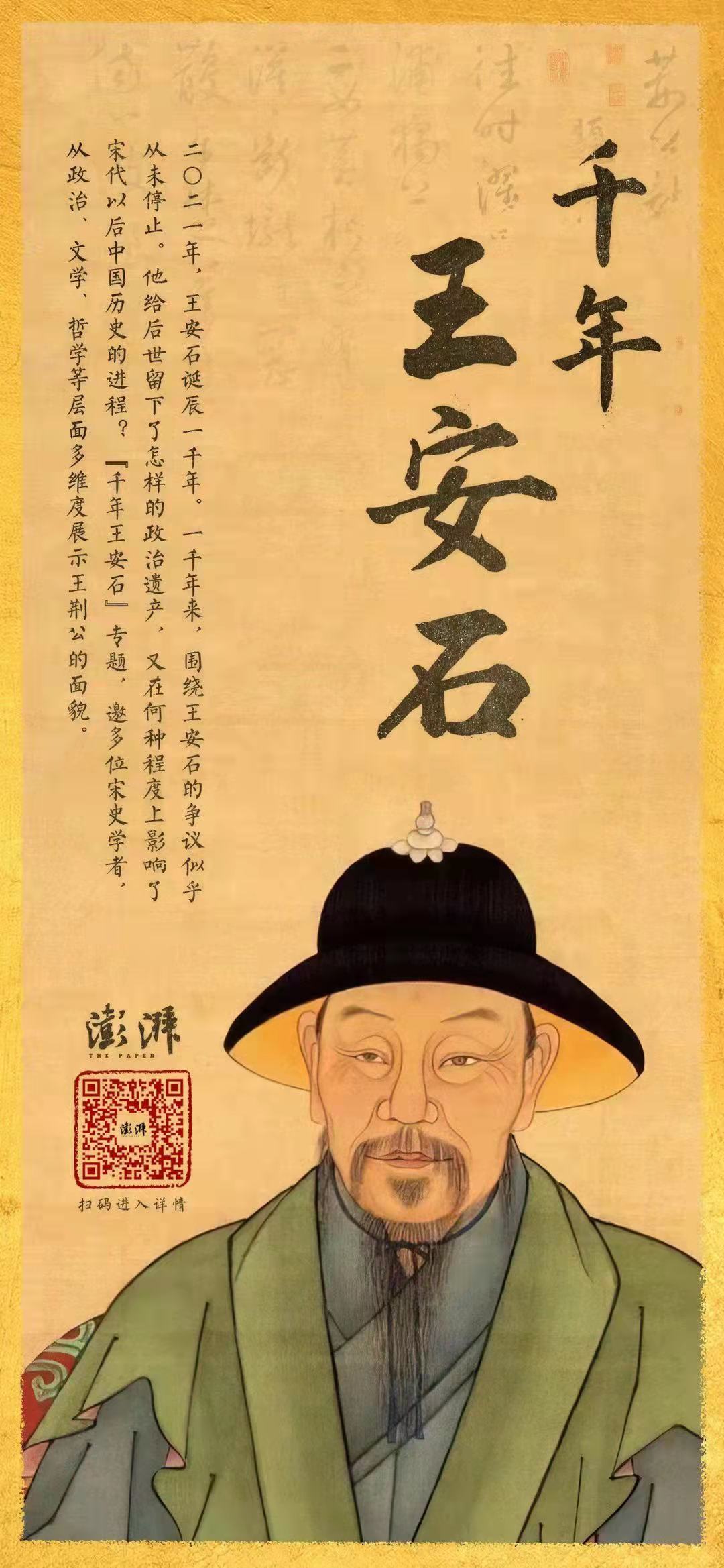
北宋熙寧變法歷來為學者所重,史籍記載及現有研究成果對熙寧新法本身關注頗多,耕耘已精 。然而令人困惑之處依然存在:在這個被變革籠罩的時代,史籍記載中那些并不突出的既有政務狀況如何?推行新法與這些已有政務關系怎樣?如果把研究目光也投射到這一時期日常政務處理的狀況,我們可以發現在“變革”的大主題下日常政務處理的方式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熙寧時期雖更側重推行新法,但日常政務處理與新法在理政方式上頗具共性。透過日常政務處理方式的變化,尋求熙寧時期處理政務的原則、政策調整的整體方向正是本文措意所在。
宋神宗在治平四年(1067)正月即位后 ,開始一展抱負,試圖通過改革解決北宋中期以來的弊端。王安石“變風俗、立法度” 的設想與神宗一拍即合,遂得到神宗倚重進行變法革新,熙寧初,宰相曾公亮甚至有“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之語 。雖然兩人在施政過程中也存在分歧,但熙寧前、中期,君相二人意見結合相對緊密,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大多得到神宗的最終支持。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變革雖是出于王安石的主導,很大程度上也是神宗意旨的體現。此期政治局面是君相二人共同努力塑造的結果,二人的共識大于分歧。
“清中書之務”:中書之政的變革途徑
王安石在熙寧二年(1069)二月出任參知政事后 ,便陸續推出了一系列新法,于此同時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既有機構的舉措,改革首先從作為“政事之本”的中書開始。對于中書之政,時人已有“清中書之務”、“中書失其政”等說法 。不少學者的研究表明,自王安石創置制置三司條例司開始,熙寧時期的中書逐漸集中了大量事權 ;新進的研究對此又有所推進,認為熙寧時期的中書“清中書之務”與“增中書之權”兩條線索并存 ;王安石對國家機構職能的改革也十分引人關注,認為熙寧變法包括“均天下之利”與“立朝廷政事”,兩者不可偏廢 。就王安石本人而言,在一次與神宗討論新法時言及新法最重要措施之一的青苗法“于治道極為毫末” ,似乎也不以新法措置作為自己施行“治道”之重,“均天下之利”也許不如我們現有研究中認為的那么重要。這些研究對熙寧政事的說法紛紜不一,這當然是從多層面、多角度觀察熙寧之政給朝政帶來變化的結果。不過,我們需要進一步提問的是,這些“說法”與認識揭示了怎樣的政治邏輯?這仍需從當時的政治舉措入手,對熙寧之政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清中書之務”,據《神宗正史·職官志》記載:
神宗初即位,慨然欲更張之。謂中書政事之本,首開制置中書條例司,設五房檢正官,以清中書之務。又置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理天下之財。
制置三司條例司設于熙寧二年二月 ,即王安石任參知政事的當月,制置中書條例司(編修中書調理所)設于熙寧二年九月 ,中書檢正官設于熙寧三年九月 。這段史料對司屬設置順序的梳理并不準確,但從中可以看出神宗君臣對“政事之本”的關注。繼制置三司條例司理財之后,又設制置中書條例司等,目的是“清中書之務”。雖然王安石盡量避免給人以中書專權的印象,如設置三司條例司時,王安石拒絕獨領,特意先后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樞密副使韓絳共同典領,這一人員組合方式將三司使副排斥在外,而以樞密院、參知政事統之,這在此前北宋歷史上確實異乎尋常 。實際上王安石堅持“特置一司”固然是因為其身份為參知政事,制度規定上尚未進入宰相議事的核心 ,但創置專司也為的是“事易商議,早見事功”,“凡所欲為,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 ,此二人與王安石關系較為近密 ,這一組合方式也確有繞開其他宰執、避開既有制度層級,減少推行阻力的意圖 ;在朝臣反對新法時,王安石也常常以條例司的名義捍衛新法。 自設置專司起步,神宗君臣正可利用這三個機構,從整頓國家財政、行政兩個方面著手,清理故務,制定條規,為新法布局鋪路,推出新政。
王安石以宰執身份設司置屬引發了朝臣的批評,尤其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被認為是“政出多門”、“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中書之外又有一中書” ,宰相“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 ,熙寧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 。但制置中書條例所仍存,相對于三司條例司,中書條例所因名義上置屬于中書,受到的批評較少。隨后不久中書又設置了五房檢正官,從其職能上看,檢正官直接承繼了制置三司條例司的主要工作 。而作為專門用以“清中書之務”的重要部門,中書條例所直到熙寧三年八月,才上報“合歸有司二十二事” ,發揮作用。這樣的結果與神宗和王安石在熙寧二年六月所表示出的“中書置屬修例,最是急事”、“此乃政事之本” 這樣高的預期不盡吻合。這意味著什么?特別是在罷三司條例司與設置中書檢正官前這段時間,中書條例所是王安石在中書唯一留下的屬司,它到底發揮了怎樣的功用?
事實上,編修中書條例早有故事。仁宗天圣(1023-1032)中,宰相始編例為五百策,這是宋代中書編修條例的最早記載,其后陸續編修過三次條例,總計達二千策。 景祐二年(1035),參知政事宋綬上所編修中書總例四百一十九冊,受到皇帝褒諭,宰相呂夷簡為此十分自得,稱“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 通過編修條例,把各項雜務梳理概括成為例則,就有章可循,若把政務歸之有司或任人責成,則有可能使宰執從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中脫離出來,節省宰執時間,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不過,仁宗朝幾次修例均屬臨時性質,沒有為此專設機構,而由參知政事提領編修或中書五房自行編修 。王安石始置官司,令專人提舉編修條例,可以看作是在仁宗朝編修條例基礎上的發展和深化 ,但其用意顯然不止于此。
王安石在熙寧二年二月出任參知政事,籌措新法事宜,四月王安石提出:
中書事猥并,若不早置屬,以眾事歸之有司,則無可為之理。
言下之意是指中書若欲“有所為”,首先應該清除猥并瑣務,為推行新政騰出手來,使中書的職責更能適應推行新法的需要,以達成神宗君臣欲以中書為新政“根據地”的愿望。神宗十分同意此點,認為:“今欲治,當自中書省。”王安石遂進言:
當選在下豪杰之士,(今)[令]編修條例,點檢文字。
編修中書條例被提上日程。五月,把中書要處理的諸司日常政務編成條例,分門別類進行整理,開始了編修中書條例的準備工作 。九月,條例所正式成立,成為繼制置三司條例司設置后又一個新法機構。多用“先具合減省名件逐旋進呈”的辦法,減少中書事務,酌量歸類到相應部門 。實踐了王安石的預設:置屬司,以眾事歸之有司。對既有政務而言,清理瑣務歸之有司是“清中書之務”最本質的含義,這一層面的作用的確可稱之為“清中書之務”。
隨事而另設機構,本是有宋以來慣用的做法,為清理中書之務而置所,表面上看也無特別之處。不過,《神宗正史·職官志》的編纂者把編修中書條例所與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并舉,共同作為“改造”中書職能的機構,但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實際上沒能達成“清中書之務”的初衷,“清中書之務” 顯然不能成為二者之間的關聯,而置屬修例也不僅僅是為了清理中書瑣務歸之有司,除“清中書之務”外,編修中書條例所應另有作用,與檢正五房公事的職能構成并立。
此次修例不是由參政提領,而是著意于另設機構,與以往慣例有別,另設編修中書條例所的意義,王安石曾有所透露,即“當選在下豪杰之士”來編修條例。其實這種置專司擇人專任其事的想法在熙寧二年二月置三司條例司時已經有所言及:
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則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條理司以講求理財之術焉。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這段對話有兩個要點:“人才難得”,必得擇人行法;設置專司為成事之依托。這兩點獲得神宗認可。簡而言之,神宗認為若以人系事,或因人敗事,若以專司為依托,擇人而行其事,則事可稍成。其后,他又數次向神宗進言:
今中書乃政事之原,欲治法度,宜莫如中書最急。必先擇人,令編修條例。
王安石欲以中書為基地推動變革,其邏輯順序是:擇人——編修條例——清中書之務——以中書為推展政事之重心,以此來“治法度”。其中“擇人”為最急之務。以編修條例的方式擇人,物色和培養能夠適應新形勢、新規范要求的人材。可見,以中書條例所擇人,顯示了該機構的特殊功用,用以擇人的標準,更是王安石匠心所在。面對神宗的敦促,王安石表明了這一用意,熙寧二年:
六月十四日,上謂王安石曰:“中書置屬修例,最是急事。”安石曰:“此乃事之本也。凡修例者,要知王體、識國論、不為流俗所蔽者乃可為之。若流俗之士,所見不能出流俗,即所議何能勝舊!今陛下欲修條例,宜先博見士大夫。……且今日條例,皆仁宗末年以來大臣所建置,人情豈肯一旦盡改其所建置以從人?恐須陛下獨斷,乃能有為。”上曰:“待朕自選得人,但恐遲。”安石曰:“此事誠不可遲,然亦不可疾。若不知王體、識國論、可與變流俗之人,則與不修條例無異,此所以不可疾也。然今非無人材,要須陛下留意考擇,恐亦不可遲也。”九月十六日,(三司)條例司檢詳官李常、呂惠卿看詳中書編修條例。
在這段史料中,王安石首先為神宗提出具體的施政建議,引導神宗深入認識設置編修條例所的作用,要求皇帝先“博見士大夫”,挑選適合變法的人材,避免“流俗之人”進入條例所阻礙修例變法,進而暗示條例所應擔負起遴選“不為流俗所蔽者”進入中書修例的重任。這正是設置條例所另一層更為重要的政治用意。此時神宗對王安石甚為倚重,擔心“自選得人,但恐遲”,遂委任責成,把拔擢那些沒有沾染“流俗”的“在下豪杰之士”之權托付王安石。在王安石“中書屬官,須精擇可以備諫官、侍從者”的標準下,中書檢正官均“高選士人”,以朝官充任 。
編修中書條例所清除不少中書“猥并”事務,同時也起到了變更舊制、確立新法的作用,是王安石在中書控制局勢的重要機構。自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推行新法后,朝中士大夫反對意見越來越多,那些曾經對王安石寄予厚望,支持他當政的士大夫也逐漸走到王安石的對立面,還有一些士大夫保持中立,支持者不多。這是王安石要求朝廷另外啟用敢于變更既有制度施設官員參與新政的原因。由于“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 ,王安石用人眼光不再限于已占據高位之士大夫,轉而著重提拔新進之人,為王安石日后全面統領新法事務做了準備。設置條例所,破舊的同時得以立新,使清理了庶務之后的中書更能專注于變法革新。條例所積極為新法儲備人材,這些士人官僚是所謂的“在下豪杰之士”,他們受到王安石的稱譽,認為有共同政治理念,卻尚未進入國家核心政務。因此,王安石及神宗對設置該機構均顯示了急迫而謹慎的態度。且編修中書條例以清中書之務,是前代已有的“故事”,置司藉以儲備人材,不易引人非議,減少了施行的阻力。這些從編修中書條例所選拔出來的官員,主要有李常、呂惠卿、胡宗愈、俞充、李承之、張琥(璪)、黃好謙、曾布、鄧綰、鄧潤甫、馬珫,在熙寧三年九月設置檢正中書五房后,不少人先后成為中書檢正官 。
中書檢正官的職權,主要有編修、詳定詔敕條例,檢舉、督促諸司職事,提舉在京百司事務,察訪、處置地方事務,尤其是新法執行的情況。其職能所轄涵括了編修中書條例所的編修條例立法職能,且更有擴展,正式成為宰相屬官 。中書檢正官既能檢正立法,同時也檢正新法實施。制置三司條例司罷后,中書檢正官更成為在中書專門輔助王安石處理諸項政務的機構。呂惠卿曾對王安石出任宰相后中書理政的狀況有過評論:
人主以天下事付中書,中書以付五房,人主豈能盡看文字?罪無輕重,但憑中書而已。
在君主的信賴與支持下,中書得以過問“天下事”。中書通過五房檢正官,直接參與到多項政務的實際運行和管理當中,而檢正官也直接向中書負責。在時人心目中,此時“中書”所指,似乎僅是宰相王安石。而王安石主要依靠的支持力量,則主要來自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即中書檢正官。
從以上分析可知,熙寧初年的“清中書之務”之所以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一方面,利用編修中書條例所編修政務處理例則,清除中書瑣務歸之有司,可以保證中書作為決策機構更加專注于統領新法,這是編修中書條例所最基本的工作,這一職能直到中書對新增事務修例進行規范的要求降低,才于熙寧八年十月罷廢 ;另一方面,在編修例則同時,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延續制置三司條例司的部分職能,通過編修中書條例所援引“新進”之人進入政府,轉而成為中書檢正官的主體,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務,在政務運行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編修中書條例所的雙重職責,使清理中書政務呈現特別狀態。通過這種方式,王安石得以以中書為變法重地,推展變法。不過,熙寧對政務的整頓不僅限于中書門下,對包括樞密院在內的整個中樞部門,均有類似的舉措。
“澄省細務”:對中樞政務的整理
熙寧初整理中書政務,先后設置編修中書條例所與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清除中書瑣務同時,編修例則修治法度,藉此引入一批能力行王安石新政的官員,促使中書成為推行熙寧新法政務的核心,編修中書條例所與中書檢正官的設置可以構成一個過程的兩個步驟 。然而編修中書條例所的職能大部分被中書檢正官所取代之后,并沒有如制置三司條例司一樣被取消,而是繼續設置至熙寧八年。究其原因,其一是因為二司雖同為新設機構,但中書條例所“法度之所自出” ,名義上是中書下屬機構,而非如三司條例司是在“中書之外”置司;其二,“清中書之務”實有其指,是神宗君臣不滿于北宋以來朝政因循茍簡的狀況而進行的變革,屬于當時整個中樞機構“澄省細務” 的一部分。
趙宋君臣對中樞機構處理政務狀況的不滿早有所載。仁宗景祐二年(1035),杜衍新任御史中丞,就曾上言:
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只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月不過數四足矣。若末節細務,進谷帛樣,閱甲胄弓矢,點馬,補試吏員,特有司之職耳,陛下何必親決。
三事大臣,即所謂“三事大夫”,鄭玄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為三公也” ,此概言國之重臣。杜衍認為二府長官作為政府首腦不應陷入瑣碎細務,應增加一起“坐而論道”的機會,關注國家的大政方針;而此時仁宗親政不久,積極聽斷政務本無可厚非,不過皇帝親臨“細務”還是引起御史的關注,認為具體庶務應該交付有司。杜衍還建議道:
欲望圣慈當清閑之燕,迭召兩府臣僚,賜坐便殿。一月之中,只乞三兩次召對。俾其極獻替之說,酌古今之宜,究治亂之源,達幽隱之意。
要求皇帝與二府長官一起,定期參與二府坐而論道,討論較為宏觀的政事。而皇帝不必躬親庶務、二府長官能“坐而論道”,均是以“末節細務”分流至有司為前提的。反映了杜衍對皇帝與二府長官在國家政務中職能作用的定位。
雖然杜衍的這一建議在當時沒有得到仁宗及其他朝臣的積極響應,但仁宗朝始終不乏要求宰相“坐而論道”、“論道經邦”的呼聲 。慶歷四年(1044)八月,范仲淹主持改革時也曾提出類似建議,認為“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 。對二府不能“坐而論道”,未起到輔佐帝王的作用,只是因循舊常,維持朝政運轉這種處理政務的狀況深表不滿。
二府之任因何會產生這樣的問題?此與宋初立國制度設計的原則有關。北宋前期中樞權力機構的突出特點是以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分理民政、軍政、財政,把國家政事依事系任進行分類,各自行使獨立職權,每類事任下實行決策與施行一體化,軍國大政上則由宰執經御前會議共同討論,共同決策 。使本來擔負著決策重任的中書、樞密院有了接觸大量行政“細務”的可能。這套務實的制度體系,確實使趙宋在建國之初穩定政治局面起了很大作用,然而趙宋立國形勢逐漸穩定后,隨著政治形勢逐漸轉變,宋初設置的這套制度體系越來越顯示出弊端。
英宗即位后,有志于“改作” ,十分留意當時行政中的弊端,努力尋找根源。在設官分職方面,他認為“惟制治之本,必始于官,設官之方,其亦有擇” ,把“官冗之患” 作為當前政務亟待解決的問題。這是沿襲仁宗朝以來一直存在的觀點。另外,對現行的政務處理方式,英宗也把目光放在加強國家機構的職能上,與杜衍、范仲淹的意見頗為相近。治平三年(1066)五月,英宗對宰相表達了這一看法:
十七日,詔中書、樞密院自今朔望會于南廳。是月,帝謂宰相曰:“朕日與公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繁,所以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本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
英宗希望能與宰相共同商討國家大政方針,自身卻困于需要省閱的文書過多,難于備覽。遂讓中書把一些已有制度規定,有章可循的事務交付有司。中書遵照這一旨意,那些日常政務中的“細務”,用熟狀預先擬好處理意見進入畫可后,付中書行下;對于“事有定制”者,中書也趁機清減政務,并歸之有司,由有司提出具體處理意見,或可交付中書。這些下行之政令中書則以敕牒等文書行下執行 。而每月朔、望日,本是百官朝會的日子,英宗特意在此日讓二府長官聚集議政,希望敦促他們“從容講論治道”。英宗對當時政務處理方式的意見,客觀上是采用了杜、范等人要求把二府之責與有司職責區別對待的建議。英宗在位時間短暫,這一辦法施行的時間及效果不得而知,但已為現行制度弊端另辟解決之道,使這不同以往的制度變革取徑具有了可操作性。
清除政府瑣務、進而區分政府之職與有司之職的變革取徑,在神宗朝得到了繼承,受到士大夫的肯定,要求皇帝和中樞減省細務,專注于國家要政 。治平四年(1067)六月,神宗為此下詔,付諸行動:
詔:“令中書、樞密院應細務合歸有司者,逐旋條陳取旨。”初,侍御史張紀言:“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不當溷政府之嚴。若溝洫當決諸水監,漕運當決之三司,其禮樂征伐、號令損益,自系朝廷議論,有司得以奉行。”故有是詔。
這條詔令是基于臣下建議區隔“政府之嚴”與“有司之職”的建議而下達的,目的也是要把政府職能從“細務”中解脫出來,明確二府與有司的分工。值得深思的是,張紀的建議似乎更進一步,分別舉例指明政府和有司各自應處理事務的范疇,認為有司對本司事務即可決事行下,不必特以政府之名行下;那些國之重事,乃取裁于朝廷,由政府下達有司奉行。無論如何,此建議促成神宗著手把“中書、樞密院應細務合歸有司”,把政府把職責更多地放到需要決策的大政方針上去。熙寧二年四月,神宗“令中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 ,促使二府加強決策職能。
在實施整理中書、樞密院“細務”的具體步驟中,作為推行新法的“政事之本”,中書顯然更為重要,“清中書之務”走在了前面。對樞密院庶務的清理,稍晚于中書。熙寧三年(1070)五月,設置審官西院,詔書中說明了設置原因:
國家以西樞內輔,贊翊本兵,任為重矣,而狃于舊制,自右職升朝以上,必兼擇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親有司之為,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員至眾,非張官置吏以總其事,則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礪中外之才。宜以審官院為東院,別置審官西院,置知院二,領合門祗候以上至諸司使磨勘及常程差遣事。俾銓敘有常經,黜陟有常守,官修而紀律振,任專而考察精,庶熙治綱,以副朕志。
熙寧三年以前,合門祗候以上中、高級武官的磨勘選任由樞密院負責,三班院負責小使臣等低級武官的銓選和常程差遣,樞密院對三班院工作負有督導之責。神宗不滿樞密院“以三公府而親有司之為”的狀況,采取與“清中書之務”類似的方式,決定突出樞密院的決策職能。把中、高級武官中大使臣的選任之責從樞密院劃分出去,由審官西院負責,樞密院負責督導審官西院和三班院,并負責橫行以上武官的遷轉及一些重要差遣的選授 。審官西院設置后不久,“仍省樞密院六十有二事歸之”,王安石認為此舉是“省細務,乃可論大體” ,使得樞密院的職責更加清晰。
審官西院設置一個月后,朝廷對樞密院與審官西院各自的職責、相互關系又做了詳細規定:
舉路分都監、知州軍已上使臣,送樞密院,本院依前項指揮,先付吏房上腳色訖,卻批付審官西院;舉常程差遣等使臣,并直送審官西院施行。
腳色,指在官員磨勘時,初入仕者要記錄籍貫、戶主、三代名銜、家庭人口、年齡、出身履歷,如已注授差遣、升轉官階,則還需注明舉主、有無過犯等,把這些主要情況綜合成文狀,存于官府;仁宗朝以后,大使臣磨勘,腳色須在禁中、樞密院各留一份 。設審官西院后,大使臣出任的一些重要差遣,仍需樞密院吏房勘驗、備錄,再批付審官西院具體施行;常程差遣事則直接歸審官西院,無須經樞密院具體處理。熙寧四年正月,朝廷再次重申了樞密院、審官西院、三班院各自人事權力的范疇及三個機構的隸屬關系:
詔應奏舉大小使臣邊要任使,仍舊樞密院銓量才器。其余舉官及陳乞差遣,送審官西院、三班院定差;軍員老病當降軍分,送殿前、馬步軍司指定職名,并申院降宣。以樞密院細務繁多故,又省常事歸之有司。
這條詔令,強調了樞密院仍保有對重要職位的人事任命權,如委任邊地要員等。不過,具體常程事務則交由審官西院、三班院負責,有司確定人選后僅需申樞密院降宣指揮行下,樞密院不再直接插手具體的常程人事選任。頒下此詔的原因,是“以樞密院細務繁多”之故。經過這幾次調整,突出了樞密院的督導政務之責,具體選任之權則大為縮減。
不過,朝中對神宗君相設置審官西院以清理樞密院“庶務”的動機,有不同說法。據《長編》載:
先是,上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為不如置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院議也。及文彥博等對,乃言其不便。……議者謂絳及安石協謀,欲沮彥博且奪其權,因建此議。然先時大使臣差遣皆屬樞密院,無先后名次,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頗患其不平,此據司馬光《日記》 。
當時對此舉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此舉乃王安石、韓絳欲奪樞密院之權,以削減樞密使文彥博的權力;作為樞密院長官的文彥博事先沒有參與商議,神宗在決定設置之后,文彥博上殿入對才提出反對 。另一種是李燾傾向取司馬光的記載,認為樞密院所掌武臣升朝官的磨勘、差遣,本已十分混亂,為時人所詬病,本就亟需整理,此舉是有的放矢,不一定是專為奪樞密之權。那么,如何理解審官西院的作用呢?
首先,我們看到,無論是中書還是樞密院均采取了調整官員人事選任權的舉措,調整的方向均是要把常程選任權歸之有司。恰如王安石所言“省細務乃可論大體”,說明神宗與王安石在致力于清除政府所管轄庶務,加強政府“舉大政”職能方面,對中書與樞密院采取的行動一致。審官西院設置后,人事選任仍接受樞密院降宣指揮,沒有脫離樞密院事權范圍,僅是在樞密院掌管的行政事務中區分了決策與常程事務的處理方式,審官西院依然受樞密院統領。此舉體現的是神宗精簡中樞機構事權、俾其得“務大體”的決心 ,設置審官西院是神宗君臣對政府等重要職能部門整體進行改革的一個步驟。
其次,神宗及王安石對樞密院庶務的清理,不僅限于清除常程人事選任權,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庶務。熙寧四年十一月,開封府推官上奏,請求批準僧志滿為福圣院主持,朝廷下詔:
詔:“開封給牒差。自今寺院有(關)[闕]當宣補者,罷宣補及差官定奪,止令開封府指揮僧錄司定奪。準此給牒。”開封府尹舊領功德使,而左右街有僧錄司,至于寺僧差補,合歸府縣僧司,而相承奏稟降宣。上欲澄省細務,諸如此類,悉歸有司。
開封府尹舊領功德使,負責管理寺院僧尼事務 ,后開封府尹漸不置,以權知開封府事兼功德使 。左右街僧錄司負責開封府轄內僧尼的具體管理,地方上則由府縣僧司負責 。一般僧職遷補委開封府,開封府指揮僧錄司(都僧錄、僧錄)定奪 ,地方上由僧司負責,但仍奏稟樞密院,相沿成習。樞密院得旨后降宣,并委派專人處理。如今指令開封府長官充分調動自身職能,與兩街僧錄司、州縣僧司主理僧尼事,樞密院此后不再降宣及差官定奪。其他類似有司可以負責處理的事務,均需從樞密院事務中清除出來。此亦可證神宗調整樞密院職能的方向同中書一致,意欲樞密院盡可能地減少常程細務,使其職責更加突出、集中。
清理樞密院庶務的同時,朝廷也著意加強樞密院管理職能。熙寧二年五月,樞密使文彥博等人稱樞密院“欲檢尋本院諸文書,凡關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于遠者,并刪取大旨編次成冊,仍于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得到皇帝肯定并賜書名《經武要略》 。熙寧三年十月,樞密院開始命人刪定諸房例冊,編修《經武要略》,初由他官兼領 ,后于樞密院專置檢詳官四人:
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秘書丞、館閣校勘王存,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陳侗,大理寺丞劉奉世,前秀州崇德縣令蘇液,并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存,兵房;侗,禮房,戶房;奉世,吏房;液,權同兵房。侗、奉世仍改太子中允,液改著作佐郎。禮遇、添給、日直、人從、出謁之禁,視中書檢正官。帶館職及本院編修文字依舊,余差遣并罷。既而存以母老辭,改差秘書丞朱明之。新、舊《紀》并書置樞密院檢詳官。
從檢詳官待遇“視中書檢正官,帶館職及本院編修文字依舊,余差遣并罷”上可以看出,檢詳官之設,是比照中書檢正官而來的,而在人員設置上,也不乏王安石有意為之的影跡。王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 ;蘇液,“介甫素善待蘇液” ;王存辭任后繼任的朱明之則是王安石之妹婿。不過,陳侗、劉奉世與王安石的關系則相對疏遠。陳侗,曾得到文彥博的舉薦,富弼辟為僚屬 ;劉奉世為劉敞之子,為樞密院檢詳官經年,吳充自樞密使拜相,奏請以奉世為中書檢正官,“雅信重之” 。檢詳官人員設置所體現的狀況是王安石對樞密院事務確有“干預”,但并非掌控。其后,加強對樞密院人事管理 ,增設對軍隊定期考核 等事務也納入檢詳官的職責范圍。應至元豐改制時,罷樞密院檢詳官 。從編修《經武要略》的目的上,以及樞密院檢詳官的設置、職能上看,檢詳官的確在實質上加強了樞密院職能,這一時期對樞密院政務整頓的方式與目標與對中書清理瑣務是相輔相成的。
那么,如何理解王安石與此時樞密院的權力關系?不同利益群體權力博弈是認識時局的重要視角,樞密院政務的清理整頓確實無法脫離王安石的“干預”,此舉有利于避免樞密院成為其改革的牽制力量,然而如果把這些舉措僅僅理解為奪樞密院之權,卻也限制了思考路徑,未免失之狹隘,放開視界,即可體察到這一時期神宗君臣試圖通盤整頓既有體制統轄政務所付出的努力。
熙寧時期“澄省細務”的思路,均是對二府日常政務進行制度性調整,調整的方向均指向把有司“細務”從政府中剔除出去,進而集中于決策事務。清除部分庶務,減少了二府舊有事權,卻加強了二府專注國家大政方針的職能,在這點上,中書與樞密院沒有區別。只是“清中書之務”的情況更為復雜。同為“澄省細務”,“清中書之務”更多地是在改革的主導者王安石推動下進行的,此舉“立”重于“破”,為中書成為統領新法重地掃清道路的同時,促使一批改革者集中在中書,通過他們,宰相王安石手中掌握了越來越多的政務處理權。
相比較下,樞密院在熙寧年間的機構整頓,在“破”的方面上雖然去除了部分人事權及具體事權,但樞密院正副長官人選多以文彥博、呂公弼、馮京等反新法者充任,更多起到的是“異論相攪”的制衡作用。在“立”的方面上,體現為設置了與中書檢正官相對應的樞密院檢詳官,王安石對此保留了一定影響力;樞密院余下的選任“邊要任使”之權,在實際運行中也受到中書的“侵奪”,選將用人之權多歸于宰相。如熙寧對西夏、荊湖、四川、廣南等地用兵的將帥人選上,主要任用了王安石所支持的韓絳、王韶、沈起、章惇、熊本等人 。不過很顯然,王安石對樞密院的“干預”并未達到全面掌控樞密院政務的程度,而是側重加強機構職能且避免樞密院掣肘其推動改革。兩相對照,更凸顯出了熙寧時期“政本”之地“中書之務”的重要性。也許這就是《神宗正史·職官志》在追述熙寧年間制度變革時,僅突出強調了“清中書之務”的原因所在。
“澄省細務”歸之有司,既響應了北宋前期朝臣整頓政事的呼吁,也代表了神宗君臣調整日常政務的方向:把行政細務從決策機構中清除出去,調整理順局部制度,是熙寧時期從體制上更革時弊的努力之一。這一過程與熙寧時期推動各項變法革新事務交織在一起,當時國家政務的重點在于新法,中樞制度的清理、調配是以應對新法需求、保證新法運行為導向的。“澄省細務”,尤其是“清中書之務”,為變法革新做了制度上的清理,這一過程在中書成為新法運作的重心后,事實上就中止了。不過,區分政府之職與有司之職成為日后制度變革的方向,直至元豐改制,制度體系有了更徹底的整理。
整頓與監臨:對三司財政的管理
“熙寧初,上立政以理財” ,熙寧之政以推行新法為重心,財政是這一時期政務的重點,改革沖擊最大的無疑是原本由三司負責的財政體系。“王安石為相,始持冢宰掌邦計之說” ,制置三司條例司罷后,繼以司農寺、諸路提舉常平司為推行新法機構,由中書統轄,檢正官直接參與管理;同時,新政沒有忽略對于既有三司系統財政事務的管理,如何處理三司“故務”,更能全面地體現王安石推展熙寧之政的特點,而相對新法,這恰恰也是學界研究王安石變法較少關注的內容,是以下文就與本文主旨相關內容擇要討論熙寧年間三司的狀況。
北宋前期的三司理財體制是在唐中后期稅收制度、軍事體制發生巨大變化下逐漸形成和發展而來。其執掌范圍頗廣,本來“于天下財計無所不統” ,在宋人心目中,其職能幾乎可以與唐代尚書省相提并論 。除掌有唐三省體制下戶部的主要職事外,三司還兼工部、太府寺、將作監、都水監、軍器監等職事;幾乎集財政管理、收支、監察為一體 。三司官吏雖非由本司長官任命,但三司使對于其下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員具有舉薦權。國家財政大計等重要決策性事務雖仍需二府決策,但三司本身負責的戶口、田產、錢谷、食貨之政令十分繁復龐雜 。宋太宗時曾憂慮三司“綱目既眾,簿書愈多,奸幸彌作”,“欲并三司為一,命官總判”,有整頓三司職能之意,其實調整仍側重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加強糾督之責,沒有更通盤的整頓。 神宗與王安石以三司事務繁雜,“多侵奪有司職事,事非其事”,三司副使、判官“多不才者” ,也措意整頓三司政務。在“富國強兵”大目標下,改變理財方式,觸及三司既有體制也在所難免。
熙寧二年十二月,尚在運行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便上言請編修《三司簿歷》,裁奪三司事務,并把三司歲計及如南郊禮之類的重要花費編為條則(式),后權三司使吳充請以三司勾當公事官計會,逐案編定。 除編修簿歷、例則外,對三司機構和職能也進行了部分調整。《文獻通考》中對整頓三司政務的方式曾加以概述和評價:
熙寧中,以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建官設屬,取三司條例看詳,具(所)[可]行事付之。三年,罷歸中書。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新法歸司農,以胄案歸軍器監,修造歸將作監,推勘公事歸大理寺,帳司、理欠司歸比部,衙司歸都官,坑冶歸虞部,而三司之權始分矣。
“三司之權始分”,也是不少現有研究論著所秉持的觀點 。《通考》中的這段敘述的確可以說明熙寧為推行新法之便,重新調配資源,重振、重組機構職能,對既有三司體系造成影響。然而該記述頗有脫落錯位之處:上述制度變化并非均發生在熙寧三年(1070);對三司下屬諸機構變化的記述則混淆了元豐改制前后的狀況。欲明了這些制度變動是否導致“三司之權始分”,有必要查看《通考》中這段史料的來源。
今存于《宋會要輯稿》中的《神宗正史·職官志》中關于三司的一段記載與《通考》極為類似,二者應有淵源關系 ,現截取其中最相關者如下:
熙寧初,上立政以理財。二年,以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制置條例,建官設屬,取三司條例看詳,具可行事付之。三年,罷歸中書,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新法歸司農。
……
勾院,前世或合為一,或分為三。熙寧七年,詔以鹽鐵、度支、戶部三勾院為都勾院,省主判官二,而胥吏皆如舊。明年,復減勾覆官二,存其一,余皆酌損之。
憑由理欠司,熙寧八年,詔與入內都知押班通領。
開拆司,熙寧八年廢,及沈括為使,言自廢開拆司,三都文案坐失關防,無以檢察,遂復置。
從[疑衍]衙司,掌大將、軍將。熙寧七年,詔大將、軍將以千五百人為額。
提舉帳勾磨勘司,熙寧五年,曾布言:“給納斂散,登耗多寡,非有簿書文籍以鉤考之,漫不可知。”遂選吏二百置司,以驅考天下帳籍。以至三部勾院,亦皆選置官吏,責以審復[覆],優其吏祿,課以功限[限,一作“罪”],制為賞罰,仍選官提舉。……(熙寧)八年,詔提舉三司帳勾磨勘司官止差一員。十年,詔擇資任稍深者為提舉,位主判官上。元豐元年,詔止依三司判官法。后數日,復置催驅官一。是歲冬,三部帳司各置官專管勾三員,使、副通舉升朝官。
……
帳司、理欠司,歸比部;衙司,歸都官;坑冶,歸虞部。尚書戶部,其屬有三,曰度支……曰金部……曰倉部……舊三司使,即今尚書;舊三司副使,即今侍郎;其權發遣副使,即今權侍郎;舊三司判官、推官及判子司官,即今郎中、員外郎。元豐元年以前,使、副、判官及判子司官并勾當推勘等官,并附此。
歸比部、都官、虞部的應該是原來帳司、理欠司等司所掌職事,而非這些機構歸隸其下。元豐新制下的尚書戶部下轄子司除度支、金部、倉部外,還有戶曹,分為左、右兩曹,史料所述之時應是還處于制度轉換過程之中。這段史料在敘述增置機構的同時,也言及增設、調整了一些屬員的職能:
時吳充為使,始請復置推勘官。
……
主簿,熙寧七年,省三部都孔目、勾覆官各一,而置主簿三員。詔于京官選人內奏舉。章惇以既置主簿,則承受催驅及鉤銷簿歷皆可辦,由是奏廢開拆司。復廢主簿。
勾當公事官四人,舊用京朝官,熙寧八年省一員,內一員,仍改用三班使臣。
上述記載頗為瑣碎,卻有利于我們從中觀察從熙寧到元豐改制過程中三司機構、人員調整的具體狀況。宋初以來,三司財政體系的基本結構是下轄鹽鐵、度支、戶部三部,三部下設二十余案,分類負責三司職事;同時,三司下又設若干子司,主要負責財政上的監督、審核、防漏、補闕等事務,其職掌與二十余案的職事互有交叉 。前引《文獻通考》截取這段記述的開頭結尾組合起來,其省略的中間部分,卻是三司從熙寧初到元豐改制期間變化的重要內容,變化集中于三司諸子司,增設、省并了一些機構和職位。這些陸續發生的調整,基本上沒有改變三司機構整體制度面貌,調整的方向似乎也并非以“分權”為指歸。《文獻通考》及現有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權”上,忽略了這一過程所造成制度面貌,以及調整三司機構的目的。以下試從三個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在職掌財政事務方面,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后,以新法歸之司農寺,這部分新增財政事務沒有歸入原本負責財政的三司之下,而是在三司之外另由司農寺管理。這種安排本身,使三司在管理國家財政方面失去了“獨尊”的地位,“侵三司利柄” ,在這一層面是成立的。不過,三司本身的事權雖沒有被司農寺“侵奪”。但因熙寧年間推行新法為政事之重,比較而言司農寺地位更為重要,三司地位有所降低,這卻不是司農寺是否分了三司事權帶來的結果。
第二,熙寧年間新增了屬司和屬員來整頓三司,其中以三司帳勾磨勘司(帳司)最為重要。熙寧三年十二月,王安石任相后不久,便以宰相身份提舉編修《三司令式》并《敕》及《諸司庫務歲計條例》 ,以詳定帳籍所清理三司文帳 ,正式開始整頓三司。有鑒于長期以來三司“簿書不治”、“無覆察之實” ,“三司帳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 等問題,神宗聽從了編修中書條例所官曾布的建言,覆查三司“給納斂散,登耗多寡”等財務狀況,清理積壓賬目,在熙寧五年(1072)十一月,為“驅磨天下帳籍”,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兼提舉三司帳司勾院磨勘官 ,遂詔以“提舉帳勾磨勘司”為名 。提舉官設置以后,原本負責審查賬籍的三部勾院也開始清理舊有帳籍 ,整頓內部政務。直到元豐五年官制改革,才罷三司帳司,職事歸于比部 。
新增屬司進行整頓的同時,三司也加強了某些屬官的職能,即三司推勘公事官、三司勾當公事官。三司推勘公事為三司推勘院長官,三司推勘院曾設于太祖開寶八年(975),不久即罷 ,只保留了推勘官;英宗治平三年(1067)罷推勘官 ;神宗熙寧二年(1069)九月,復置推勘公事官,掌推劾鹽鐵等三部公事 ,說明此時重新加強了對三部的監察力度。三司勾當公事官,熙寧之前也曾有興廢,熙寧二年九月,復置勾當公事官,掌點檢諸路上供財物等事,路級財政狀況也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督管理。三司推勘官罷于元豐元年(1078)十二月,職事歸于大理寺 ,勾當公事官廢罷時間不詳,應是隨著元豐改制罷三司歸戶部而取消。增置屬司與設置屬官,均著眼于清理三司諸項政務,有助于加強三司自身職能。
第三,大力整頓既有機構。新法推行中,以將作監取代修造案、軍器監收胄案軍器制造之職,將這部分職事從三司劃分出去。不過三司諸案及子司中,以鹽鐵設案,度支錢帛、發運案,戶部修造案及開拆司最為繁劇 ;章惇曾建議廢除開拆司,代之以主簿,然終不可行,廢而復置。這樣,除修造案外,其余四個三司最為繁劇的案、子司依然隸屬三司,行使其職能。三司勾院,掌檢舉三司失陷財賦,糾察鹽鐵等三部錢糧出入之數,太宗時期就屢有分合 ,熙寧七年(1074)合三部勾院為三司都勾院,精簡了機構及吏員。憑由理欠司,取消主判官,而由入內都知押班通領,也得到精簡。衙司,掌管三司大將、軍將等低級武職人員,從事押綱、宮內役使等短期差役事,人數眾多,此時在制度規定上限定了員額 。
由上可見,熙寧年間對三司的整理主要集中在諸子司所掌職能方面,對三司既有案、司的調整,使三司的部分職能得到歸并、整合。在此過程中,三司雖有減省一些具體事務,但對三司諸案所掌職事改動并不甚多,三司仍保留了大部分事權,歸并、精簡部分機構及人員后,反而使事權更為集中;三司新增的機構和職位,清理了既有政務,加強了內部的管理和監督。這些舉措均有助于加強三司自身理政職能,有利于整齊政務、集中事權。
熙寧年間推行新法的同時,對三司既有政務進行清理整頓、加強監督,客觀上使三司喪失了在財政事務中“獨尊”的地位,因此容易給人一種三司之權被侵奪的印象,然而若把三司所進行的諸項舉措均歸于“分三司之權”這樣的認識,則易使人忽略一個重要的現實:熙寧時期三司內部職能得到整合、加強,三司在國家財政體系中的整體實力并未受到嚴重削弱。同時也應看到,無論是以司農寺主理常平新法,還是整頓三司政務,宰相對財政的控制力度的確前所未有,對國家財政的管理方式,與熙寧時期處理日常政務的方式是一致的。
熙寧時期政務的管理方式
“清中書之務”、“澄省細務”、整頓與監管三司事務,三者的著眼點均在于清理瑣務,加強政府機構職能,其中“清中書之務”還有另外一層重要意義:在“清中書之務”的名義下,通過編修中書條例所和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的設立,援引了大批為王安石所用的變法人材,他們不僅是推行新法的重要力量,也是整頓日常政務的重要力量。前文雖有提及,因涉及熙寧推行政務的特點,是以此點仍需有所闡明。
在政府內部,宰相王安石與其屬下的中書檢正官構成一組政治決策和指揮執行的團隊。在政令傳達中,檢正官也直接參與其中,自成體系,有很強的獨立性。御史楊繪曾就此狀況提出意見:
言:“近者進奏院班下四方及流內銓牓示條貫,其首但云:據某房檢正官申具,其末又云:進呈奉圣旨依檢正官所定,首末并以檢正官為文。若不曾經中書、門下,殊失朝廷號令之體。”
又言:“臣常論朝廷號令之體不當首末止作檢正官名目,尋聞先已改更,只作諸房者,臣竊疑猶未當理。夫奉圣旨指揮頒下者,即朝廷之政令,諸房乃胥吏之曹名,今作檢正官名目尚謂失體,況止作某房名目,則天下之人豈不訝其所出乎!況已經中書、門下參定,則可只作中書、門下,何必須曰某房哉!臣又聞諸房檢正官每有定奪文字,未申上聞,并只獨就宰臣王安石一處商量稟復,即便徑作文字申上,其馮京等只是據已做成申上者文字簽押施行。臣竊謂國家并建輔弼,不惟凡事欲集長以詳處其當,亦欲防權柄專歸于一門也。今檢正官等皆朝廷選用之人,不識體如此,是致外議嘩然,咸謂雖涂注亦有只是宰臣王安石與都檢正官曾布商議,而參知政事馮京、王珪或有不先預聞者。”
楊繪批評的核心,首先是不滿于檢正官在朝廷事務中的影響力。從進奏院、流內銓接受的文書內容中,可以看到檢正官在政務的決策和執行中起到的作用:檢正官既可“申具”中書,又可把擬定意見作“奉圣旨指揮頒下”,通過進奏院頒下諸路,成為中書處理政務決策與施行的樞紐。其次,楊繪對“權柄歸于一門”的批評,也是不滿于王安石獨專政柄。在政務處理中,宰相王安石與都檢正官曾布結合得十分緊密,具有相當大的排他性,甚至參知政事也儼然被排除在外,檢正官名義上是中書屬官,卻基本上只聽命于王安石一人,事實上成為王安石一人的屬官。
此時王安石身為宰相,具備了統領百司及各種政務的權力,而檢正官除了新法事務,還兼領許多其他部門差遣,通過檢正官,對政務或是直接管理,或是監督、整頓,使國家整體政務運行中出現前所未有的特殊理政通道,甚至直達地方。由于中書增加了對人事權的控制,中書對出類拔萃者可直接擢用,“不以次選差” ,增加中書用人的靈活性,選拔了一批地方官員為推行新法助力,與這條通道相輔相成。
這批人中,王安石最為信用、能力最強、始終堅定推行新法者,當屬曾布與呂惠卿 。熙寧四年(1071)七月,御史中丞楊繪曾以曾布為例,指出推行新法中用人方式問題,從中可以看出曾布所歷之職:
勘會曾布熙寧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自海州懷仁縣令轉著作佐郎,閏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詳衙司條例,熙寧三年四月五日差編敕刪定官,八月二十四日差編修中書條例,九月六日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九月八日差權同判司農寺,九月十四日授集賢校理,九月二十三日差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十月四日差看詳編修中書條例,熙寧四年二月五日差直舍人院,二月八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五月三日差詳定編敕,七月十三日試知制誥。從選人至知制誥止一年十個月,舊官太子中允班在尚藥奉御之下,新官知制誥班在觀察使、待制之上,可謂不次矣。
對照曾布墓志銘、傳記等其他相關史料記載,楊繪所述基本不誤。楊繪雖批評的是曾布不次升遷之速,但從中透露的信息卻可有別樣的解讀。在這短短的“一年十個月”中,曾布擔任了十數種差遣,此后,曾布又任判司農寺兼詳定編修三司令式敕、諸司庫務條例 ,以及權三司使、河北西路察訪使等職 ,直到熙寧七年八月,曾布因市易務事與王安石、呂惠卿不協,落職出知饒州 ,離開朝廷。歸納起來,曾布在熙寧年間歷任各類編修敕令官、編修中書條例、檢正官、判司農寺、權三司使及兩制官,參與了熙寧新政實施的主要過程。作為王安石另一個倚重的人物呂惠卿,任職情況與曾布類似,歷任的職務有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編修中書條例、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知制誥、權知諫院、判軍器監、提舉制敕庫等,熙寧七年四月,出任參知政事 。這些差遣除授并非全為次第遷轉,而是存在同時以一身兼數職的狀況,職任涉及國家立法、行政、財政、朝廷監督專使等多方面的政務。
在諸多差遣中,曾布、呂惠卿由編修中書條例所官至為中書檢正官后,長期充任此職務,二人均是作為宰屬身份而同時相繼兼任了諸多其他差遣。雖然官員同時兼任不同差遣是北宋建國以來一種常見現象,但熙寧年間曾布、呂惠卿兼任事權牽涉之廣,這在此前是不多見的。類似的,熙寧時期政府不少部門長官的知、判官大多由中書檢正官兼任 ,這種以中書屬官兼領多種職務的人事任用方式在熙寧年間是一個重要現象,甚至對二府、諸司行監察職責的臺諫官,也多由中書檢正官或王安石信用之人兼領,如此操作之下,使得王安石推行新法的阻力大為減小 。
中書檢正官管理的事務范圍不僅限于新法,日常政務的管理也包括其中。對于國家既有機構的日常行政,中書采用清理整頓、加強審核監督的方式來提高機構職能,這與“澄省細務”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熙寧三年七月,神宗詔令“中書考察內外官司,置簿記功過,俟歲終及因非次除擢,檢錄比較進呈,擇其尤甚者進黜之” ,具體辦法是“內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核,而中書皆置之籍” ,中書對下面具體事務部門施行普遍而切實的考核之權,其中尤以刑訟、人事為要。
獄訟方面,王安石十分留心“論正刑名”,任參知政事時即認為中書應親理刑名:
有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即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所謂國體。
反駁了宰相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的觀點。熙寧三年,中書向皇帝進呈五項刑名不當事,神宗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王安石認為對刑訟的監管、刑名的議定關于“國體”,人主及宰相均應予以充分重視。熙寧四年(1071)正月,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要求加強大辟案件的刑事審核,稱:
天下所斷大辟,委提點刑獄司勾考,刑部詳覆,恐多疏略,容有冤濫。又奏至不以時讞,故久系獄囚。乞自今令刑部月具已覆過大辟案,逐道申中書委檢正官覆詳,大限十日,小限七日,如有不當或無故稽留者,取旨責罰。
大辟案件的覆查本由大理寺負責,再由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后,交付中書;雖然宰相名義上對審刑院的裁決有再次覆查之權,但通常流于程序,而確實存在疑議的重大案件則多通過詔獄審理 。李承之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要求把大辟案件的覆詳之權歸于檢正官,不當者可直接通過中書“取旨責罰”。不久,李承之即“駁正法寺大辟四人及刑部失覆大辟一人”得以遷官 。檢正中書刑房的覆詳之權凌駕于刑部、大理寺、審刑院之上,擁有了最終審覆權。王安石明確支持此舉,規定:“若刑房能駁審刑、大理、刑部斷獄違法者得當者,一事遷一官。”加強審核及對官員的監督,有助于防止案件留滯、“冤濫”,也使中書得以更直接地參與到國家司法事務管理當中,擁有了更切實的監督權。
人事方面,熙寧四年十一月,中書對審官東院選任的州郡長官也加強了審察:
詔應知州、知軍、通判,令審官東院自今具名赴中書門下審察人材。
對出任川、廣、福建等邊遠地區的官員更是如此,神宗命令“審官院定差知州、軍、監人,并當日具姓名申中書,次日付中書審察,堪任差委,即引見取旨” 。意在加強審核監督,周知遣去地方官員的履歷及才能,有助于保證地方(尤其是邊遠地區)的政務處于朝廷有效控制之下。中書“審察人材”,并非是中書將審官東院銓選之權全部收歸己有 ,直接取代審官東院選拔官吏。通過對審官院東銓選人員進行審察,促使審官東院更有效地行使自身職能,亦是這一舉措的用意所在。流內銓的狀況類似,都檢正曾布曾權同判流內銓 。其用心也不僅在于直接選材,更是意在加強流內銓自身職能。中書對諸司的行政監管,有助于促進諸司更大地發揮效能。
當時王安石對于新法與既有日常政務的管理方式不盡相同。熙寧期間推行的諸項新法,乃既往政務所無,這些新政的制定、管理、實施,甚至監督均直接由中書負責,檢正官兼領其任。其中司農寺作為負責新法議定、推行的機構,在新政中最為重要,長官基本由中書檢正官兼任 。其他新設機構,如市易司、軍器監、將作監,亦多由檢正官兼任其職,講究制度,推行政務。對于國家既有機構的日常行政,王安石則采用清理整頓、加強審核監督的方式來提高機構職能。尤其是重視對國家機要部門政務,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采取力度很大的清理整頓工作。對具體事務部門則施行普遍而切實的考核之權,主要事務仍直接由中書檢正官負責,歸于王安石領導。以此達成對新法與日常政務行之有效的管理。熙寧時期這種人事結構所形成的推行政務的方式,使得新法與既有日常政務都逐漸統合到同一人事結構管理之下,改變著以往日常政務運行的面貌。
新法在地方推行的過程中,也采取了特置專司、專人的方式。一方面,為了督導新法在地方的實施,察訪新法推行的狀況,從中央多次派遣中書檢正官為察訪使下訪,保證新法及時有效地施行 。在地方上,熙寧期間推行的諸項新法,既無法獲得所有地方官員的認同,官府也無法更換大量地方官,因此王安石設置提舉常平司和常平官系統來另立推行新法的新管道,即在原有機構外另設新機構,任用一批官員專職從事新法推行事務。在實際操作中,提舉官逐漸獲得政府資金和地方事務的處分權,又因新法事務繁多,主要依靠提舉官執行,使得事權日重,最終獲得了與其他監司并重的重要地位。同時也使得反對新法的藩鎮重臣歐陽修、富弼、韓琦等人或致仕或削弱其影響力,減少變法阻力。 以中書檢正官兼察訪使、專置提舉常平司,做法與熙寧時期整體變革的思路是一致的。
結語
熙寧時期“變革”是時政的主旋律,彌散性地充斥在朝政當中,既有的日常政務也籠罩其中。熙寧之初,設置專司、專人整頓日常政務,首先自中書門下展開,然后延及樞密院、三司,其中對中書門下的整頓因其具有雙重意義,成為整個中樞“澄省細務”的重點。神宗君臣一方面有鑒于此時的中書政務充斥大量“細務”,認為中書若欲“有所為”,首先應該清除猥并瑣務,為推行新政騰出手來,使中書的職責更能適應推行新法的需要,以達成神宗君臣欲以中書為新政“根據地”的愿望;另一方面,王安石為推行新法,設置專司展開新政,在神宗的支持下,援引一批中低級官員進入改革的核心,先后充任編修條例所官及中書檢正官,逐漸以檢正官兼領其他部門事務,掌握朝廷各種要職,建立了一條以宰相王安石為首的特殊的行政通道。前者是“清中書之務”、編修條例的直接原因,而后者則構成實質上的潛在推動力量。
從政務展開的實際效果上看,神宗君臣先后利用制置三司條例司、編修中書條例所、中書檢正官、樞密院檢詳官等機構安排人員,清理故務,制定條規,為新法布局鋪路,推出新政,憑借這條特殊的行政通道,新法被快速而密集地推行開來。相輔相成地,憑借這些機構和這一用人方式,對既有日常政務,特別是中書、樞密院及三司的政務,進行清理整頓、加強審覆監督,強化國家機構處理政務職能,極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能。整頓故務與推行新法相配合,共同塑造了熙寧之政的局面。
熙寧時期用人及政務處理方式,使熙寧之政的影響力在兩方面突出了出來:其一,熙寧時期理政方式的變化導致“中書權重”成為必然之事。“中書權重”不僅體現在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通過中書檢正官取得了諸多事權上,更體現在宰相王安石與檢正官構成的這種自成體系的政務運作方式。利用這種理政之法,中書逐漸發展成為集決策、行政、核查職能于一身的政府機構,隱然居于樞密院、三司之上,熙寧之政的快速展開也得益于此。“權力”的變化,深層的內在原因即在于此。其二,熙寧時期對中書、樞密院日常政務調整的整體方向頗為一致,均是努力區分決策事務與常程事務,這是熙寧“澄省細務”的核心。這一政府改革的方向,在施政理念、政務運行等方面為元豐改制在制度設計上區別決策與行政做了必要的準備,客觀上構成從熙寧之政到元豐之政的內在聯系。在這一變革敦促下改革日常的諸多舉措施行過程中,熙寧“舊日常”漸次轉向元豐時期的“新日常”。
從更為宏觀的層面上看,神宗與王安石推行新法無法根本脫離北宋立國以來形成的政治環境,這一系列舉措采用的手段,突破了既有制度結構及政務運行方式的擠壓,新法推行方式對現有政治有很強的針對性,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對推行新法而言無疑是行之有效的。然而此種政務運行方式的弊端也顯而易見,熙寧年間的政治紛爭與此有莫大關系。這一方式對人事團體更是有著極大的依賴性,特別是神宗與宰相王安石之間君臣相得,一直是王安石推展政務的基石,王安石與中書檢正官上下相承則構成政務運行的“通道”,這意味著人事關系的改變必然會深刻影響熙寧之政以降的政治局面。
(本文首刊于《文史》2016年第3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