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馬大為院士:內(nèi)卷導(dǎo)致科研短平快,勿簡(jiǎn)單替人“抬轎子”
“我可以很誠(chéng)實(shí)地告訴你,當(dāng)時(shí)我對(duì)化學(xué)沒興趣。”中國(guó)科學(xué)院院士、中國(guó)科學(xué)院上海有機(jī)化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馬大為毫不掩飾求學(xué)時(shí)對(duì)數(shù)學(xué)的熱愛。
曾經(jīng)“對(duì)化學(xué)沒興趣”,一直想“混到數(shù)學(xué)系”。35歲因偶然發(fā)現(xiàn)一類可以提高烏爾曼反應(yīng)效率的氨基酸分子而“一戰(zhàn)成名”,最終因有機(jī)化學(xué)研究當(dāng)選中國(guó)科學(xué)院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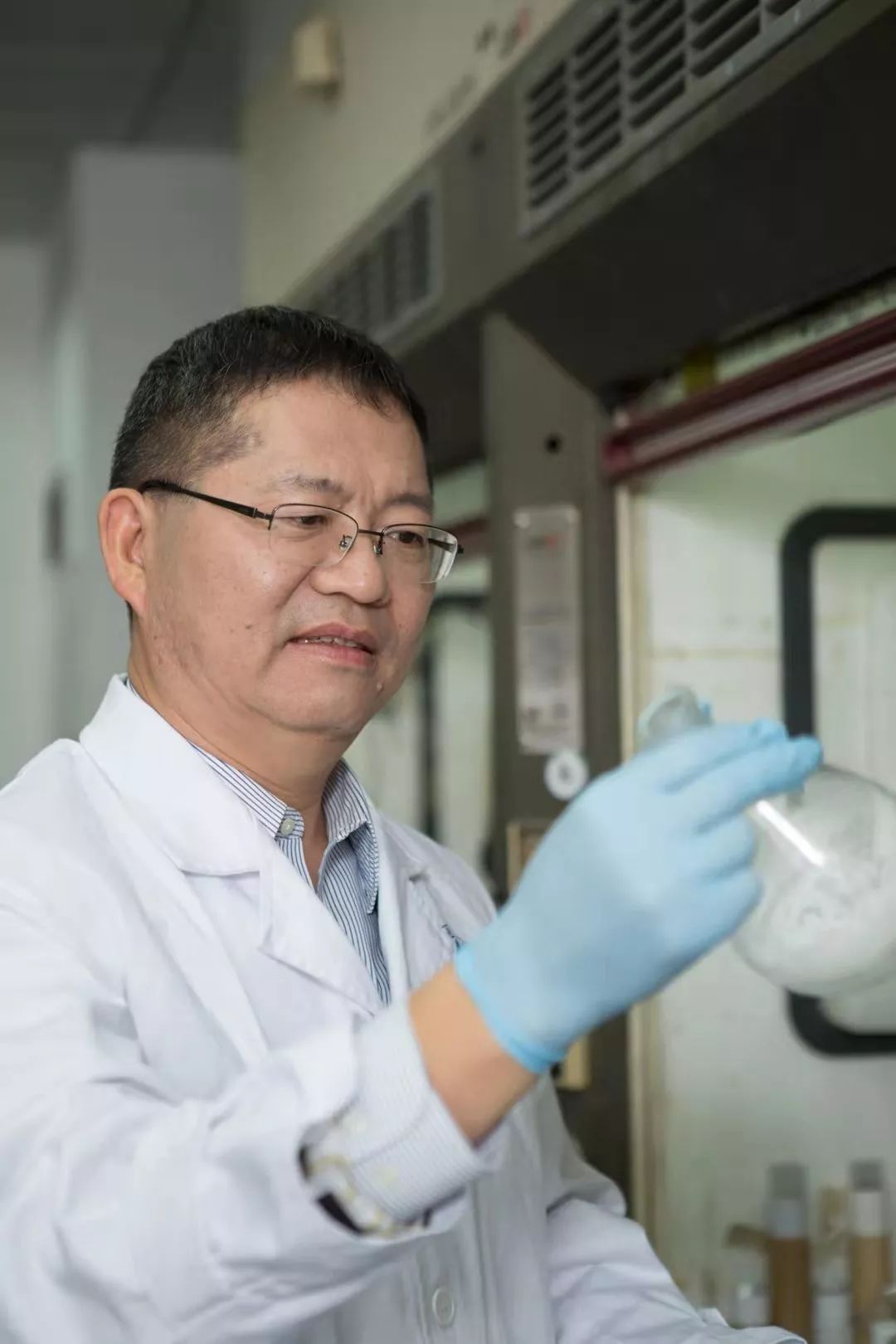
如今58歲的馬大為只要不出差,幾乎仍舊每天花10-12小時(shí)撲在辦公室看資料,夢(mèng)想找到催化效率更高的第三代配體,讓第三代催化劑實(shí)現(xiàn)三位數(shù)的工業(yè)化應(yīng)用,為藥物合成提供更簡(jiǎn)便的方法。
“也不能保證一定能發(fā)現(xiàn),但它的意義非常重大。”馬大為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shí)表示,做科研可以說有95%以上的時(shí)間是失敗的,但失敗是一個(gè)好機(jī)會(huì),“我們要鼓勵(lì)大家去探索無人區(qū)。現(xiàn)在很多科研人員就做一些相對(duì)比較簡(jiǎn)單、容易做出來的東西,但現(xiàn)在國(guó)家已經(jīng)到了一定要做原創(chuàng)、探索無人區(qū)的時(shí)候了。”
他也感慨科技界的“內(nèi)卷”,“很多大學(xué)和研究單位沒有按照科研的規(guī)律招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學(xué)術(shù)帶頭人、首席研究員),實(shí)際上相對(duì)于世界一流大學(xué),我們每個(gè)大學(xué)的PI都是超員的。”
這就導(dǎo)致了嚴(yán)重的內(nèi)卷,很多年輕科研工作者在面臨這些壓力時(shí)首先想到的是生存,做些短平快的研究。而短平快的研究很難產(chǎn)生重大影響,也難以將成果轉(zhuǎn)化成現(xiàn)實(shí)生產(chǎn)力。
對(duì)于年輕科研工作者,馬大為告誡,科研不應(yīng)扎堆湊熱鬧。即使扎堆湊熱鬧,也不要“做了幾篇文章幫人家抬轎子,自己也沒得到什么就走了”,而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到一定的深度,在這個(gè)過程中發(fā)現(xiàn)和解決重大問題。
馬大為以氨基酸銅的絡(luò)合物為催化劑實(shí)現(xiàn)了碳–氮鍵的高效構(gòu)筑,為含苯胺片段的藥物及材料的合成提供了一種簡(jiǎn)便、實(shí)用的方法。他與四川大學(xué)教授馮小明、南開大學(xué)教授周其林因在發(fā)明新催化劑和新反應(yīng)方面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xiàn),為合成有機(jī)分子,特別是藥物分子提供了新途徑,斬獲2018年未來科學(xué)大獎(jiǎng)物質(zhì)科學(xué)獎(jiǎng),并分享價(jià)值100萬美元的民間資本捐贈(zèng)。

馬大為與家人在未來科學(xué)大獎(jiǎng)?lì)C獎(jiǎng)典禮上
2019年4月,馬大為拿出未來科學(xué)大獎(jiǎng)的300萬元獎(jiǎng)金,在母校社旗一高設(shè)立了“未來獎(jiǎng)學(xué)金”,用于獎(jiǎng)勵(lì)品學(xué)兼優(yōu)的學(xué)生。從獲獎(jiǎng)人轉(zhuǎn)變成捐贈(zèng)人,今年10月,北京奇點(diǎn)未來自然科學(xué)發(fā)展基金會(huì)舉辦的“成為‘未來’科學(xué)家——贈(zèng)書暨讀書分享會(huì)”系列活動(dòng)在河南省南陽(yáng)市舉辦。活動(dòng)中,主辦方跟隨馬大為回到家鄉(xiāng)的南陽(yáng)一中與母校社旗一高,與學(xué)生共同聆聽大科學(xué)家的求學(xué)經(jīng)歷與科研故事。馬大為鼓勵(lì)學(xué)生,只要努力,將來也有機(jī)會(huì)通過科學(xué)改變世界。
“當(dāng)時(shí)我對(duì)化學(xué)沒興趣”
馬大為1963年9月出生于河南社旗縣,這是一個(gè)距離南陽(yáng)市50公里左右的小縣城。南水北調(diào)中線工程引漢水北上,直接經(jīng)過這里。
父母都是教師,中學(xué)時(shí)代趕上“科學(xué)的春天”萌發(fā),看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報(bào)道后對(duì)數(shù)學(xué)充滿興趣,也把數(shù)學(xué)家陳景潤(rùn)和張廣厚視作偶像。
他在數(shù)學(xué)上花時(shí)間最多,那時(shí)候河南沒有什么課外教材,他就托人從上海帶來看。反倒在化學(xué)上花下去的時(shí)間連數(shù)學(xué)的1/10都不到,高考前零零碎碎兩周時(shí)間看了一遍化學(xué)。
但他熱愛的數(shù)學(xué)并未在高考時(shí)眷顧他,“我一出考場(chǎng)就想起來了,移項(xiàng)時(shí)符號(hào)沒有變。”由于失誤丟了20分,高考數(shù)學(xué)只有77分,化學(xué)卻拿到了90多分,報(bào)考山東大學(xué)數(shù)學(xué)系“直接給分到化學(xué)去了”。
“當(dāng)時(shí)我對(duì)化學(xué)沒興趣。”1980年,馬大為進(jìn)入山東大學(xué)化學(xué)系就讀,前半年一直想“混到數(shù)學(xué)系”,還去數(shù)學(xué)系轉(zhuǎn)了幾圈。但那時(shí)候沒有轉(zhuǎn)專業(yè)機(jī)會(huì),只能硬著頭皮學(xué),“說實(shí)在的,還是很郁悶。”
直到半年后,馬大為漸漸發(fā)現(xiàn)化學(xué)也是門有意思的學(xué)科。改變他想法的,是那時(shí)候讀過的科學(xué)史。居里夫人從瀝青提取鐳的故事,讓他覺得化學(xué)也不錯(cuò)。
大二的有機(jī)化學(xué)里,不可預(yù)測(cè)的繁多變化讓他覺得有趣又有挑戰(zhàn)。“一定要培養(yǎng)自己的興趣。我跟很多研究生也一直在講,假如你喜歡這個(gè)專業(yè),你看別人的相關(guān)文章時(shí),能夠像音樂家聽音樂時(shí)那樣,從中得到一種興奮感。”
近幾年,“生化環(huán)材”四個(gè)專業(yè)由于就業(yè)難而被戲稱為“四大天坑”。馬大為認(rèn)為這是誤解,真正的“生化環(huán)材”專業(yè)就業(yè)非常熱門,比如他所從事的有機(jī)合成專業(yè)已經(jīng)面臨“招人都招不到”的情況,“做新藥研發(fā)的企業(yè)需要這樣的人,做化學(xué)合成工藝的研究企業(yè)也需要這樣的人,所以現(xiàn)在這類人才在市場(chǎng)實(shí)際上很短缺。”
“生化環(huán)材”對(duì)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影響深遠(yuǎn)。今年諾貝爾獎(jiǎng)委員會(huì)在解讀2021年諾貝爾化學(xué)獎(jiǎng)的研究發(fā)現(xiàn)時(shí)提到,全球35%的GDP涉及化學(xué)催化。石化工業(yè)產(chǎn)品、化肥、藥品、塑料、香料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物質(zhì)都依靠催化制備。
馬大為曾多次呼吁,要重視化學(xué),不應(yīng)對(duì)化學(xué)有偏見。通過基礎(chǔ)研究和新技術(shù)開發(fā),改變?cè)泄に囘^程,減少化學(xué)品生產(chǎn)過程產(chǎn)生的污染,這些都是重要的化學(xué)研究課題,“這個(gè)行業(yè)將來實(shí)際上對(duì)人才的需求還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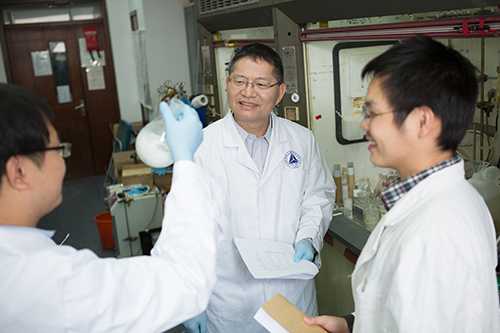
馬大為在實(shí)驗(yàn)室
“仔細(xì)看這些能夠改變世界的東西,化肥也好,農(nóng)藥也好,醫(yī)藥也好,材料也好,大部分這些相關(guān)物質(zhì)最早都不是我們發(fā)明的,甚至我們?cè)谥圃爝@些東西的工藝好多也都不是我們?cè)瓌?chuàng)的。”
馬大為說,中國(guó)現(xiàn)在是生產(chǎn)和制造這些品類的大國(guó),接下來需要讓中國(guó)研發(fā)在發(fā)現(xiàn)新功能物質(zhì)和創(chuàng)造新生產(chǎn)工藝方面做出一些引領(lǐng)世界的成績(jī),如果把學(xué)習(xí)“生化環(huán)材”專業(yè)的重要性提升到這樣的高度,就有很多事要做。
夢(mèng)想找到第三代配體
馬大為是山東大學(xué)第一個(gè)考上中科院上海有機(jī)化學(xué)研究所的學(xué)生,他在這里完成5年碩博連讀,“金屬有機(jī)化學(xué)知識(shí)已經(jīng)基本到了頂峰。”他決定出國(guó)換一個(gè)研究方向——天然產(chǎn)物合成和藥物化學(xué)。
1994年,馬大為結(jié)束在美國(guó)匹茲堡大學(xué)和梅育診所的博士后研究。即便當(dāng)時(shí)在美國(guó)年薪已經(jīng)有3萬美元,他還是選擇回到國(guó)內(nèi)。當(dāng)時(shí)的上海有機(jī)化學(xué)研究所面臨科研人員青黃不接的問題,在有機(jī)所的不斷動(dòng)員下,馬大為加入團(tuán)隊(duì)。
“上海有機(jī)所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算是比較接近國(guó)際先進(jìn)水平的一個(gè)研究所了,特別是在有機(jī)化學(xué)方面。但實(shí)際上我們當(dāng)時(shí)跟國(guó)外的差距還是非常大的,就像我們當(dāng)時(shí)的經(jīng)濟(jì)一樣,反差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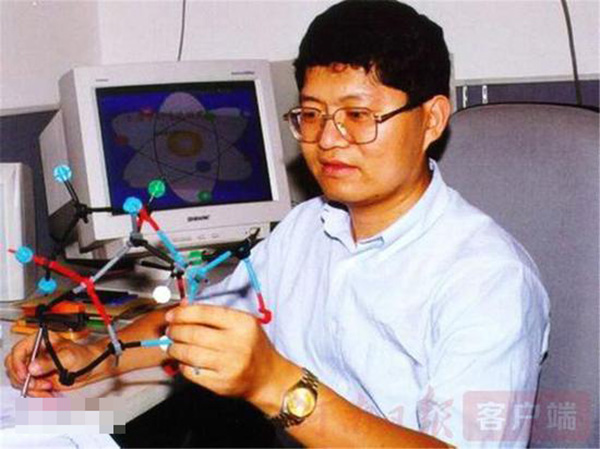
年輕時(shí)的馬大為
拿論文發(fā)表來說,那時(shí)候國(guó)內(nèi)一個(gè)研究所一年發(fā)表幾篇二區(qū)文章都覺得很不錯(cuò)了,而這對(duì)國(guó)外科研單位而言是很容易的事。國(guó)外的研究思路更高端,30多年前交叉科學(xué)研究已經(jīng)開展得紅火了。實(shí)驗(yàn)條件更不用說,“那時(shí)候我們確確實(shí)實(shí)是很艱苦的。”
但回到有機(jī)所后,1998年,馬大為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類氨基酸分子,可以提高烏爾曼反應(yīng)的效率。烏爾曼反應(yīng)由德國(guó)化學(xué)家在1901年發(fā)現(xiàn),它能將簡(jiǎn)單的鹵代芳烴和其它親核試劑偶聯(lián)在一起,構(gòu)成一個(gè)更加復(fù)雜的分子。這是化學(xué)和制藥工業(yè)研發(fā)過程中常常使用的形成碳碳和碳雜鍵的重要方法。
但經(jīng)典的烏爾曼反應(yīng)需要大量銅的催化,溫度要達(dá)到150~250攝氏度,這可能會(huì)破壞一些脆弱的分子骨架,大大限制了反應(yīng)的應(yīng)用范圍。
結(jié)果“無心插柳”,他發(fā)現(xiàn)的氨基酸分子能作為銅源催化劑的配體,提高烏爾曼反應(yīng)的效率,大大降低反應(yīng)所需要的溫度和銅催化劑的用量,成為化學(xué)合成實(shí)驗(yàn)室“每天都要用的反應(yīng)”。這種配體也為荷蘭皇家帝斯曼集團(tuán)的抗高血壓藥物培朵普利和英國(guó)一家醫(yī)藥公司的干眼病治療藥物的工業(yè)化生產(chǎn)提供關(guān)鍵助力。
之后,他又用了整整10年,一屆又一屆學(xué)生接力,經(jīng)歷了四五批學(xué)生,終于找到了催化效率更高的第二代配體——草酰二胺,這一配體出現(xiàn)后的短短幾年里,已經(jīng)在工業(yè)上產(chǎn)生了上噸級(jí)的應(yīng)用。馬大為說,第一代催化劑已經(jīng)有兩三個(gè)工業(yè)化應(yīng)用,第二代催化劑的工業(yè)化應(yīng)用有希望上兩位數(shù)。
如今,58歲的他還在繼續(xù)探尋第三代配體。他希望催化劑的“效率再提高一點(diǎn)點(diǎn)”,“成本再降低一點(diǎn)點(diǎn)。”這樣才有機(jī)會(huì)變成更加通用的工業(yè)催化劑。
“也不能保證一定能發(fā)現(xiàn),但它的意義非常重大。”馬大為說,他現(xiàn)在的夢(mèng)想就是找到這種配體,讓第三代催化劑實(shí)現(xiàn)三位數(shù)的工業(yè)化應(yīng)用。
科研“內(nèi)卷”

馬大為在南陽(yáng)為學(xué)生簽字贈(zèng)書
2000年以后,中國(guó)科研的很多方面都慢慢和國(guó)際水平接近。但是哪怕在10年前,馬大為也沒有想到,中國(guó)科研可以取得如此進(jìn)步。
以化學(xué)領(lǐng)域論文發(fā)表為例,馬大為說,10年前,我國(guó)一區(qū)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不到美國(guó)一半,二區(qū)文章的發(fā)表數(shù)量達(dá)到了美國(guó)的一半。“就這10年,從2010年到2020年,我們已經(jīng)達(dá)到了一區(qū)文章跟美國(guó)一樣多,二區(qū)文章是人家兩倍的程度。”
“你可以想象我們的科研隊(duì)伍發(fā)展多么快。”但馬大為在很多場(chǎng)合都向化學(xué)工作者提出,即使有比美國(guó)多的論文,“有哪幾個(gè)人敢說我們?cè)谶@個(gè)領(lǐng)域是最頂尖的。”
“在科技界現(xiàn)在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了,跟社會(huì)上一樣,都在內(nèi)卷。內(nèi)卷的主要因素就是很多大學(xué)和研究單位沒有按照科研的規(guī)律招PI,實(shí)際上我們每個(gè)大學(xué)人都是超員的。”
馬大為表示,與國(guó)外高校相比,國(guó)內(nèi)高校的科研人員數(shù)量是國(guó)外的幾倍,“一些大學(xué)的初衷可能就是想多點(diǎn)人可以多發(fā)點(diǎn)文章,數(shù)字上好看一點(diǎn),大學(xué)排名高一點(diǎn)。它并不是要為在哪一個(gè)領(lǐng)域做出更重要的發(fā)現(xiàn)而設(shè)計(jì)這個(gè)位置去招人的。”
這就導(dǎo)致了嚴(yán)重的內(nèi)卷,很多年輕科研工作者在面臨這些壓力時(shí),首先想到的是生存。“他就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有些問題可能10年8年也不一定能解決出來,盡管這些問題是非常重大的,但他覺得如果這樣做很有可能研究沒做出來,人已經(jīng)被非升即走的制度給趕走了。”
而短平快的研究很難產(chǎn)生重大影響,也難以將成果轉(zhuǎn)化成現(xiàn)實(shí)生產(chǎn)力。真正有影響力的科研,要么在創(chuàng)新上是源頭,要么將研究工作做到極致最后實(shí)現(xiàn)轉(zhuǎn)化。無論是做領(lǐng)域里的“第一人”,還是“最后一人”,都需要大量積累和投入。而現(xiàn)實(shí)的情況是,“基本上大家都不去著邊,都在中間擠來擠去。”
“像這次諾貝爾化學(xué)獎(jiǎng)就是這么一回事。”今年化學(xué)諾獎(jiǎng)花落“不對(duì)稱有機(jī)催化”。在2000年前發(fā)現(xiàn)的所有通用催化劑要么是金屬,要么是酶。德國(guó)科學(xué)家本杰明·李斯特和美國(guó)科學(xué)家戴維·麥克米倫在2000年各自發(fā)表了關(guān)于第三類催化劑的發(fā)現(xiàn)。依靠有機(jī)小分子,不對(duì)稱有機(jī)催化的新型催化模式誕生了。
但馬大為表示,在有機(jī)小分子催化領(lǐng)域里,大約一半的論文發(fā)表都是中國(guó)貢獻(xiàn)的,實(shí)際上最終是烘托了這兩位科學(xué)家工作的重要性。“講穿了就是幫人家抬轎子,當(dāng)然在抬轎子的過程中你修煉得很好,最后在這個(gè)領(lǐng)域做得甚至超越他了,那也是一種說法。但你最后做了幾篇文章幫人家抬轎子,自己也沒得到什么就換個(gè)熱點(diǎn)領(lǐng)域去研究,這可以說是現(xiàn)在國(guó)內(nèi)科學(xué)界普遍存在的一個(gè)問題。”
勿簡(jiǎn)單“抬轎子”
在馬大為看來,科研“內(nèi)卷”的破局方法是分類改革,把基礎(chǔ)研究交給精英,把應(yīng)用研究交給市場(chǎng)。
“國(guó)家應(yīng)該滿足一部分精干人員從事基礎(chǔ)研究所需要的經(jīng)費(fèi),假如他們基本上不為生活和科研經(jīng)費(fèi)發(fā)愁,他們的研究品位自然會(huì)高一點(diǎn),就可以靜下心來做一些更有價(jià)值,更有探索性的基礎(chǔ)研究。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有很多科研人員號(hào)稱在做應(yīng)用研究,但實(shí)際上他的應(yīng)用研究很難跟市場(chǎng)接軌。”因此需要把應(yīng)用研究交給市場(chǎng)去引導(dǎo),讓市場(chǎng)檢驗(yàn)創(chuàng)新和實(shí)用的程度。
同樣,高等教育應(yīng)該把培養(yǎng)不同種類的人才放在中心位置,并非每個(gè)高校都適合進(jìn)行基礎(chǔ)研究。“有的大學(xué)可能連研究條件都沒有,但想著我們招了一批博士做教師,就要?jiǎng)?chuàng)造條件去做基礎(chǔ)研究,又開始買設(shè)備,然后再去招研究生,去申請(qǐng)新的碩士點(diǎn)和博士點(diǎn),相當(dāng)于又?jǐn)偭艘粋€(gè)新大餅。”
對(duì)于年輕科研工作者,馬大為告誡,科研不應(yīng)扎堆湊熱鬧。即使扎堆湊熱鬧,也不要“簡(jiǎn)單地抬轎子”,而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到一定的深度,在這個(gè)過程中發(fā)現(xiàn)和解決重大問題。
另一個(gè)很多人缺乏勇氣去挑戰(zhàn)的科研方向是“完全獨(dú)辟蹊徑”,“要想哪些領(lǐng)域是重要的,哪些問題還沒解決,通過自己的努力,有可能在5年10年后開辟一個(gè)新領(lǐng)域。”
“做科研,可以說95%以上的時(shí)間是失敗的。”但馬大為認(rèn)為,失敗是一個(gè)好機(jī)會(huì),能讓人了解失敗的原因,分析并解決問題。“我們要鼓勵(lì)大家去探索無人區(qū)。現(xiàn)在很多科研人員就做一些相對(duì)比較簡(jiǎn)單、容易做出來的東西,但現(xiàn)在國(guó)家已經(jīng)到了一定要做原創(chuàng)、探索無人區(qū)的時(shí)候了。”
馬大為在博士后階段所學(xué)的復(fù)雜天然產(chǎn)物合成和藥物化學(xué)本質(zhì)上是要通過一步步反應(yīng), 將一個(gè)簡(jiǎn)單分子一點(diǎn)點(diǎn)拼成復(fù)雜、有功能的分子。
回國(guó)后,他也帶領(lǐng)團(tuán)隊(duì)進(jìn)行了很多具有重要生理活性的復(fù)雜分子的合成研究。例如,為抗癌藥曲貝替定找到了一種迄今為止最簡(jiǎn)便的合成路線。這一抗癌藥由于結(jié)構(gòu)復(fù)雜,被稱為世界上最難合成的兩個(gè)抗癌藥物分子之一。采用新路線后,原先40多個(gè)合成步驟現(xiàn)在僅需26個(gè),這意味著藥物制備成本可大大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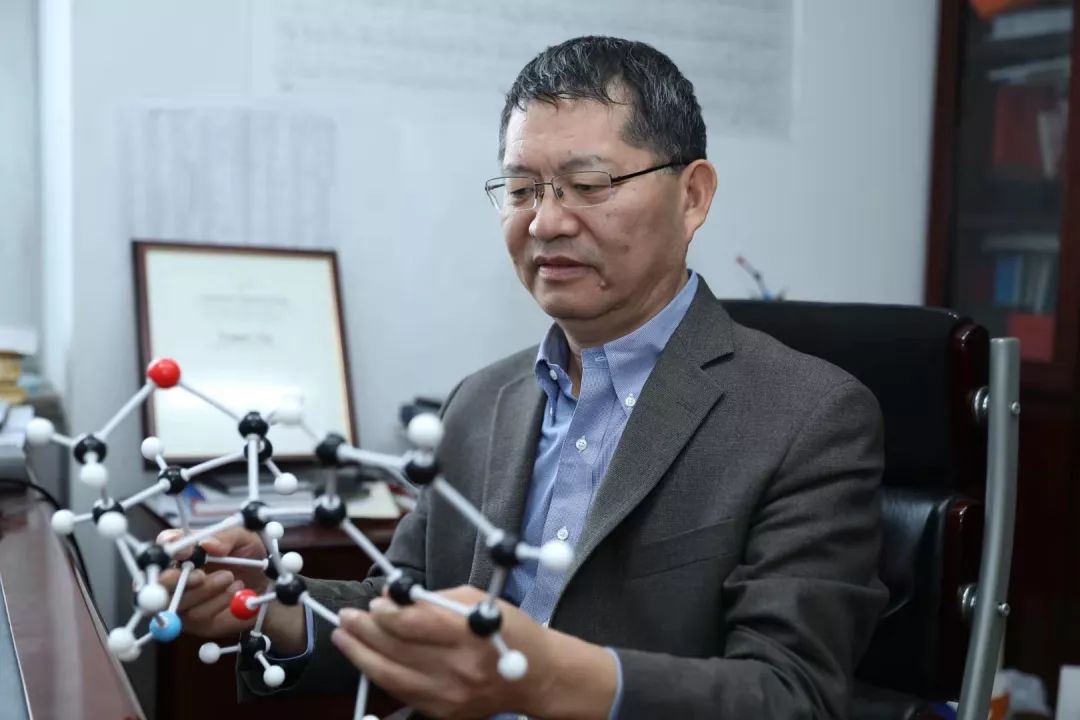
目前除了探尋第三代配體,馬大為團(tuán)隊(duì)還在研究天然產(chǎn)物。“天然產(chǎn)物過去被變成新藥的機(jī)會(huì)還蠻多的,就像青蒿素也是一個(gè)天然產(chǎn)物。”他認(rèn)為,如果能掌握天然產(chǎn)物產(chǎn)生生物活性的機(jī)理,就能為藥物研發(fā)提供很多重要線索。“現(xiàn)在難度還是蠻大的,研究起來確實(shí)比較困難,但也是我們想做的一件事。”
“匹茲堡所在的美東地區(qū),做有機(jī)合成這個(gè)行當(dāng)?shù)挠袀€(gè)傳統(tǒng)要求,就是工作強(qiáng)度非常大,每天干12小時(shí),每周干6天甚至7天是很多實(shí)驗(yàn)室的硬規(guī)定。”他把這樣的傳統(tǒng)也帶了回來,“人家已經(jīng)那么先進(jìn)了,還這么努力地干活,你要想趕超人家的話,連這個(gè)都趕不上肯定不行。”
如今的馬大為,只要不出差,幾乎仍舊每天花10-12小時(shí)撲在辦公室看資料。“這也是一種愛好,不去看看好像心里著急了。”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