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千年王安石︱巔峰對決:王安石與司馬光關系千古爭議再考察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爭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致“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后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后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面貌,以饗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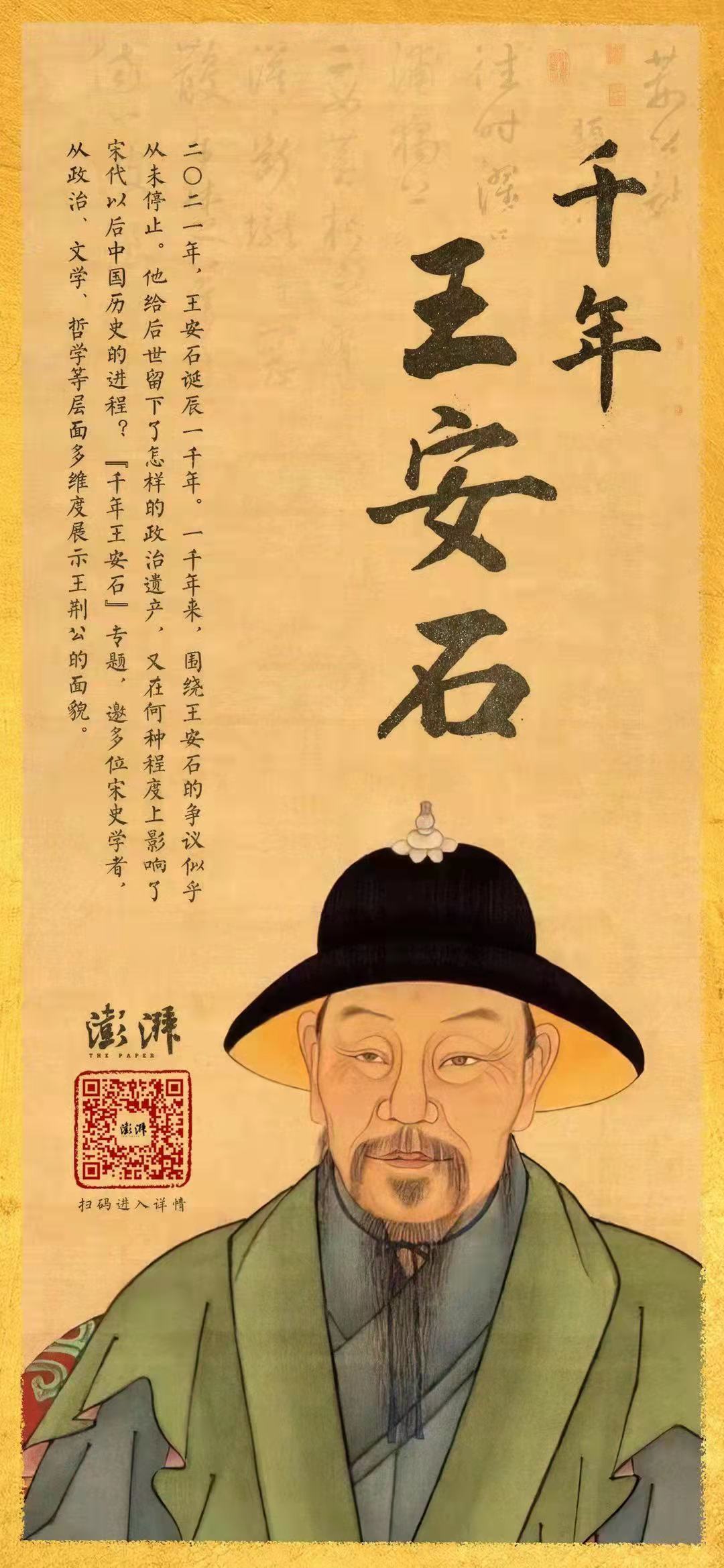
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位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無疑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一個是變法的積極推動者,一個是極力反對者,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在北宋中期那個大變革時代,變法與反變法這兩派對立的情勢,到神宗時日益尖銳化。兩方劍拔弩張,各不相讓,終至由暗斗而演為明爭。當時王安石曾云:“切以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所異故也。……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后人之同情王安石新法者輒說司馬光之反對乃鬧意氣,而其實不盡然,他對很多社會問題的理解不同于介甫,而最重要的是他所服膺的政術的基本觀念——“道”和介甫根本不同的緣故。(參見程仰之《王安石與司馬光》,顧頡剛主編《文史雜志》,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1942年1月),收入《文史雜志》第2卷合訂本)
關于司馬光為“反對王安石變法”“借題發揮”而形成理論建構的評價的說法影響頗大。而這一評價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胡三省對司馬光史論之評價有關。胡氏曾言:
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傳以書局為事。其忠憤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儒爭維州事之類也。(《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
胡三省該段帶有強烈主觀色彩之論一出,后人信為“確論”,大肆發揮,致使對司馬光的評價日漸被政治化,由此成為批判司馬光的充分根據,胡氏所提之“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儒爭維州事”要么從時間上可判定無關,要么根據司馬光自己言論可推斷當與王安石變法無關。(參見楊渭生《試論司馬光的學術思想》,收入《宋史研究論集》第一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47-48頁)胡三省將司馬光的學術與王安石變法牽強地聯系在一起的做法,對后世有關王安石、司馬光學術思想的評價產生了極為重要的消極影響。反觀熙豐變法和元佑更化的歷史實際,不難發現,王安石與司馬光之所以在政治上形成“冰炭不可同器”之對立,固然有時代和個人性格等偶然因素的牽絆,但從根本上看,當與兩人在哲學思想上的諸多分歧恐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加之作為理學集大成者、也是作為后世官方哲學的奠定者朱熹,對王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的否定而對其政治操守與道德文章肯定的雙重評價,被元代史臣斷章取義而化約為對王安石的全盤否定之影響,形成了在梁啟超《王安石傳》誕生以前,數百年間對王安石進行總體否定的主流看法。到底如何形成對王安石的客觀評價,乃成為時至今日,在宋史學界、宋代哲學史研究界依然爭論不休的重要問題。以下從兩大方面,對該問題進行簡要回應。
“天變不足畏”與“守道不守法”
首要的一點則是集中體現在王安石“天變不足畏”與司馬光“守道不守法”的分歧的理解上。
天變不足畏,是熙寧變法時期的反對派加給王安石的罪責。事實上,王安石提出過“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卻沒有明確提出過“天變不足畏”,然而在思想上,王安石還是有“天變不足畏”之痕跡的。
在傳統社會,天命論是社會的統治思想。它不僅是士大夫們的一般宇宙觀,同時也是政治斗爭的工具。北宋熙寧11年間的反變法派,無不以天命論為依據,反對變法。如御史呂誨日:“方今天災屢見,若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靈臺郎尤英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富弼道:“王安石進用多小人,以致諸處地動。”范鎮云:“乃者天鳴地震,皆新法勞民之象。”鄭俠說:“熙寧七年大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文彥博謂:“市易司賣果實,與天下爭利,致使華州山崩。”如此等等。反對派的這些說法,是其反對變法的口實,也深深地影響了篤信天命的宋神宗。
但是,天命論并不是反變法派的專利,變法派當然也可利用。當鄭俠說天旱是由安石變法所致,當文彥博說華州山崩是市易司賣果實所致,王安石即對神宗講道:
華州山崩,臣不知天意為何,若有意,必為小人發,不為君子。漢元時日食,史高、恭、顯之徒,即歸咎蕭望之等,望之等即歸咎恭、顯之徒。臣謂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為,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當怒望之等,怒恭、顯之徒。(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九)
他是完全可以用天命論反司馬光等人的。但是,哲學不能只是反對異己的工具,而首先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天命論固然可以用來反擊反對派,但變法派卻不能以此安身立命。因為天命論尚存有導向人無所事事,被動順應的現實可能。如果人事都由天命決定,則會消弭人的斗志。故因循守舊者多與天命論有著親緣關系,而變法者卻不能以此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必須強調人事,而不是天命或天變。沒有人事,又何來破弊俗、立法度呢?因此,整個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一直強調修人事,而不是不畏天變。因為在王安石看來,自然災害只是由時數造成的,對人事究詰不休當是極其可笑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賑災。
早在知鄞縣時,王安石即已確立了這種思想。他在《再上龔舍人書》中說:“且五帝三王之時,可謂極盛最隆,亦不能使五谷登常,而水旱不至,然而無凍餒之民者何哉?上有旱政,而下有儲蓄之備也。”王安石認為堯湯時代雖亦曾發生過水旱,然因賑災得力,并未成災。熙寧七年(1074)四月,神宗以久旱不雨,憂見于容色。每次輔臣進見,未嘗不嘆息憂心,欲盡罷保甲、方田等法。王安石對神宗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噗雖逢,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圣慮耳。”(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二)結果遭神宗批評:“此豈細故耶?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耳。”(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二)張希清先生曾認為王安石這一言論完全否定了董仲舒的災異觀,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王安石在這里并沒有否定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
熙寧八年(1075)冬十月,彗出東方,神宗詔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王安石又上言日:
臣等伏觀晉武帝五年,彗實出軫,十年,軫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上下傳會,或遠或近,豈無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國日久,則日“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所以多歷年所,亦日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驗,及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誕,況今星工豈足道哉?(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九)
在王安石看來,“天道遠”,“人道邇”,水旱有其常數,上下附會,只是偶合罷了。可以修人事以應天,修政以救災。循此而論,天變亦不需恐懼,更不應以天變而動搖推行新法的決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安石是有“天變不足畏”思想傾向的。
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不畏天變并不是完全否認了天道、人事之間的緊密關系,而只是說,天變并非是由政治行為所造成的,對天變本身要認真對待,修人事以消除天災。在這個意義上說,對天變亦要畏懼,不畏懼是不對的。所以他在《洪范傳》中講道:
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由后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己懼,不曰天之有變,某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蔽是蒙蔽,葸是不敢進取,固是固陋因循,怠是怠慢。(《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
在這里,王安石充分意識到,在天人關系上有兩個誤區:一是天人的盲目感應,“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有了這種思想,則會受其蒙蔽而無所進取。故而,反對派以天變反對新法,這當然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另一種是天人相分說,“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由此不知取法天地,統理萬物,把自己從天地萬物中抽離出來,則其結果一定是雖亦日修人事,其實是不知如何修人事,這也是他所反對的。在王安石看來,修人事應當是質諸天地自然的,即“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此即“不蔽”、“不葸”、“不固”、“不怠”的態度。如上所提,他勸神宗修人事,即是在這一意義上的修人事。有學者據此提出王安石于此徹底否定了董仲舒天人感應論和洪范災異學說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參見鄧廣銘:《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修訂版)
當然,也不能說王安石完全不相信天命,或者說,明確地主張“天變不足畏”。他有時也相信天命,他常以“畏天變”來稱譽神宗,固然是應時之辭,但他有時也徑直勸神宗祈天永命。如熙寧六年(1073)三月,“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幾分。神宗詔:‘自十四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仍內出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王安石言曰:‘民每欲雨,陛下輒一祈未嘗不輒應,此陛下致誠感天之效。然今歲日食正陽之月,恐宜以此降德音。’上從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三)如此等等。這說明了王安石雖身為宰輔大臣,基于對人有限性的體察,所以不可能完全擺脫天命論的影響。
如前所論,司馬光一方面也持守天命,但他認為天和人各自都有一定的局限,故而又主張天人相分,天人共濟。落實在常與變的問題上,他表現為對“道”與“法”的區分,并主張采取不同的態度去面對。如他曾講:“夫道有因有偱,有革有化,因而偱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下乃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效也。”(司馬光:《法言集注》,第293頁)但是,他是反對變革“道”的。另一方面,司馬光還提出社會的各種制度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如其所言:“物久居其所則窮,故必變而通之”。社會的各種制度長期不變,最終,物極必反,必得加以變革才行。司馬光認為,在人類社會中,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人類是不能改變的,只能加以認識利用,但是對于禮儀制度卻是可以而且必須適時地加以變革,由于“時異事變”、“世變風移,故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所謂“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司馬光:《法言集注》,第293頁)人們必須遵循客觀規律,但不必也不應死守各項具體的法規制度,故他講“圣人守道不守法”。(司馬光:《溫公易說》,第645頁)
司馬光在熙寧三年三月,奉命擬策試題時,正擔任諫官,享有風聞言事之權力。然而當其引導參試者批駁“三不足”的策試題被否決后,司馬光即此罷休。與此同時,司馬光以故舊好友的身份曾接連致書介甫,批評王安石主持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和拒諫”,建議停止變法。其信中所談,涉及王安石變法的人事、組織措施、指導思想等方面,皆是從具體的處事方式上進行的規勸。然從另一方面來看,司馬光試李清臣等策試題以及隨后神宗帝與王安石的對話來看,形成其以三不足批判王安石變法,亦不是沒有可能。臺灣地區學者林天蔚曾在《宋代史事質疑》中指出,司馬光以“三不足”之說的內容作策試題,“目的在于試探民意,亦可能是擬制造反對的輿論”。被王安石稱作“赤幟”的司馬光,作為是反對變法派之領袖,“三不足”之說出自其手,似也在情理之中。而以司馬光長期從政的政治才干與主持編撰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所展現的文學才能來看,要概括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這樣的話語,亦當非難事。但不能不說,這樣的做法當與司馬光“天人相分”的思想有一定的沖突。

司馬光
司馬光是保守主義者嗎?
第二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就是作為反對王安石變法領袖人物的司馬光之“保守主義”定性問題。
司馬光生活的北宋中期,由冗官冗費冗兵的“三冗”導致了嚴重的積貧積弱危勢,各種矛盾空前激烈,“天下之勢危于累卵”。面對此情此景,許多有識之士紛紛要求變革舊制,以求救世。即所謂“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陳亮:《陳亮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25頁)由范仲淹等發起的“慶歷新政”和緊接著的王安石變法皆是當時歷史變革必然要求的體現。審時度勢、順應時變,司馬光此時也力主變革,反對一味固守舊弊。
首先,司馬光曾屢屢上札,敦促皇帝決心變革。司馬光認為當時“國家承百王之弊”,而“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要求勇于“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他堅決反對那些凡事守舊、不思變革、“當更而不更”的做法。認為“凡國家之弊、在于樂因循而多忌諱”、“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循舊例而已”。指出“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何必事事循其陳跡,而失當今之宜也”。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應拘守先王祖宗令典。對祖宗的太祖太宗的令典成法,司馬光更是屢屢提出變革要求。他要求當朝皇帝革除太祖太宗的獨攬政權,凡事“一一躬親閱視”的做法,反對當朝皇帝沿用太祖太宗重視培植“腹心羽翼”的陳規,反對太祖太宗開始的大肆“推恩”、隨意授官于各級官僚親屬的貫例,他也反對用人唯講年資出身,不問德行才能的“祖宗”舊法,認為“夫資途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
其次,司馬光直接提出了許多變革的主張、措施。他從“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的前提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教育等領域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如其所言:
收拔賢俊、隨材授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慎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勇、罷去贏老、以練士卒;完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司馬光:《傳家集》卷四十一)
從當時最迫切的經濟變革來看,司馬光提出了不少“豐財”措施,這集中體現在其仁宗末年所上之《論財利疏》中。司馬光在該文中認為要恢復經濟、增加財利、必須采取三條根本措施,即謂“方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所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是要求變革當時管理經濟的官員不都由根據“出身資序”的原則而來的“不曉錢谷”的“文辭之士”擔任,且因每每頻繁的調動,致使這些官員養成不熟悉、熱心本職工作的陋習,故他主張“精選朝士之曉練錢谷者”來擔任經濟官員,而“不問其始所以進”,不必講“出身資序”加以提拔,并確保其任職相對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馬光提出的一系列致治經濟軍事教育的變革措施中,包括了眾多的改革先王舊制和祖宗成法的內容,它充分表現了司馬光是一個具有強烈變革精神的改革者。如他反對當時實行“三代之時”“兵出民間”的“古制”,主張革除以民代兵的“刺義勇”和保甲法,實行唐起的募兵法;要求改革“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的先王祖宗的郊祭禮制,主張只在“大慶殿恭謝天地”即可;在其所著的《書儀》中,屢屢變革《儀禮》中冠婚喪禮的古代儀制”;他甚至無視孔圣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的圣條,以“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而不改”的氣概,要求哲宗立改剛死的父皇神宗之新政。
這些主張革除先王制度祖宗令典的措施,清楚地說明了司馬光決不是倡導“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保守分子,而是一個決意從現實出發、拋棄一切不適宜于實際需要的舊的政令制度變革者。
司馬光何以一直被當作保守主義者呢?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他是王安石變法的頭號反對者。通過對司馬光著作的考察來看,在“變”與“不變”的問題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一致的,都主張要變革弊政,而在“如何變”上,司馬光就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
概括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其基本點有二:一是在內容性質上指斥王安石的新法是“困民之法”,它以“聚斂相尚”、“其害乃甚于加賦”。二是在方式方法上批評王安石變法是“輕改舊章”、“盡變舊法”、“獨任己意”,急功近利。盡管后人認為司馬光在元佑更化中有“意氣用事”“負氣求勝”“以恩怨自是非”諸缺陷,但其中亦有不少合理之處。他主張針對實際、實事求是,穩重而行變法的態度,大要可以歸諸其中和之道。在他看來,改革方案須經過充分周密地協商討論,不能僅憑幾個人臆斷而定,“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眾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善”。顯然,在這方面,司馬光的指責和主張在相當程度上是積極的。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其深刻的內在根源正在于此。任何變法既是革弊除陋,因此一既要追求發展速度與效度,還要考慮到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三者的有機結合才是社會改革穩步推進的重要保證,決不能盲目冒進。
由此可知,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并非從根本上反對變法,只不過是不同意王安石式的變法而已。這一點還可從司馬光對王安石新法進行具體分析,而不是一概否定的態度看出。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并非采取任意的全盤排斥,而是持有因有革論:“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于舊法者則存之,其余臣民以為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厘革”;“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因此,在哲宗元佑初年,司馬光實際執政后,他雖對王安石變法持強烈否定態度,但在具體過程中并未全部推翻“新法”,比如對王安石關于改革科舉與學校的變法內容,司馬光就肯定其是“革歷代之積弊”,基本予以繼承下來;再如“方田均稅法”,從現有文字資料看,司馬光亦不曾提出異議。即使對其反對最力的免役法,司馬光亦并未要求完全恢復舊法的差役法,而是主張各州各縣從各自實際出發。“曲盡其宜”,對原差役條款“于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乞改更”,視情況吸收了免役法的一些內容。
總之,司馬光雖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但決不能據此即認定他是一個頑固守舊者。我們決無理由將異于王安石的變法者皆斷為保守主義者。通過以上的分析應該不難看到,司馬光乃是一個典型的反王安石變法的變革者,是一個異于王安石激進型變革者的穩健型變革者。司馬光喜說“自然”,他以為“自然”便是“無為”,便是守常。《迂書》說:“古之有以異于今乎?天地之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為而獨變哉?”天道是守常的,不變的,治“道何如而獨變哉”?他認為“法不可變”,應以因循為務。他曾致書介甫暢論老氏的“無為”政術,他說: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硙硙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司馬光:《傳家集》卷六十)
他認為介甫的變法是老子的政術。他最喜漢初的黃老無為、“以因循為用”的政治。史載神宗讀《資治通鑒》至曹參代蕭何事,問曰:“漢守蕭何之法不可變乎?”司馬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脫脫等:《宋史·司馬光傳》)這里的“祖宗之法不可變”之語并不是在強調墨守陳規。在司馬光看來,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不可變的,而是要強調一種因任時勢,法乎自然,反對刻意人為的精神。故他批評王安石“用心太過”。
“從司馬光上述豐富深刻的變革思想及其主張,從司馬光強烈沉穩的變革精神與氣質看,司馬光也應算是北宋杰出的變革者。”(董根洪:《司馬光哲學思想述評》,第358頁)盡管為了增強反對那打著“法先王”旗號的王安石“新法”的力度,他也曾說過“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陳詞濫調,但從其總體的思想傾向和長期的現實表現來看,司馬光決不是泥古不變的頑固派,而是一位堅持儒學基本原則,穩健通變的改革家,將司馬光定位為保守主義者是一個“證據不足,有欠公允”的判斷。
在司馬光的視野中,王安石在政治上是一個“力戰天下”“不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之人。盡管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進行了徹底地否定,但卻對其文章和人格予以肯定。在神宗不堪各方彈劾壓力,準備罷安石相位前征求司馬光意見時,司馬光并未落井下石,而是力陳王安石嫉惡如仇、襟懷坦蕩、忠直耿介,有古君子之風。王安石去世以后,剛上臺任宰相的司馬光在給呂公著的信中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司馬溫公集》卷六十三)后根據司馬光“朝廷宜優加厚禮”之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王安石與司馬光這一對中國十一世紀政壇上最耀眼的明星,共同的君子人格操守,截然對立的政治立場,引發起了后世更為激烈的黨爭和關于北宋亡國之因的追思爭議。對兩人政治立場的厚此薄彼亦成為后世長期爭論的重要問題。這一千年前的巔峰對決盡管以形式上王安石新法的盡廢而落下帷幕,但當年那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卻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后王安石時代”。
王安石與司馬生前的磊落襟懷和凜然風范,卻大節略同:彼此的友誼既年深情篤,各項重大的分歧,也毫不涉及個人的利害沖突。維系趙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構成他們全部關系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在政策的爭辯中,他們各執己見,寸步不讓,略無情面;然而,在個人之間,卻依舊洽守友義,不負夙契——既沒有權勢的傾軋、陰險的殘戕,也不曾互相誣謗、暗害中傷。他們身后的榮辱遭際,以及與新學、理學在兩宋之際的升降沉浮,對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演變與發展,都有著重要關聯。正如宋人馮澥所說:“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今天身處改革的年代,當我們反觀千年前的這一爭議時,對于兩人的關系及各自的歷史定位時,恐定會有新的認識,形成新的解讀。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