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楊瀟 步履不停
楊瀟 步履不停 原創(chuàng) 肖恩 鳳凰網(wǎng)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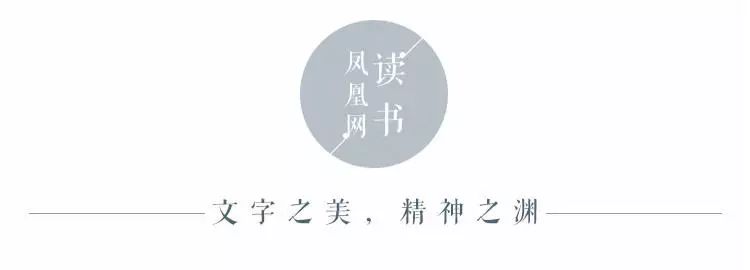
“人生苦短,像個(gè)少年一樣投入吧,體驗(yàn)吧,燃燒吧,縱身一躍吧,哪怕你改變不了什么,哪怕你一點(diǎn)兒都不重要。”

楊瀟,作家,代表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lián)大》
一、子弟
“李煥英!”“喊什么呢,小王八蛋。” 電影《你好,李煥英》里,賈小玲穿越回自己出生的前一年,即1981年,重遇了媽媽李煥英,彼時(shí)她是勝利化工廠打鐵車間的一名女工。
八零后作家楊瀟,與電影內(nèi)外的賈小玲同歲,生于與取景地不算遠(yuǎn)的湖南衡陽。倘若劃破時(shí)空,這兩個(gè)看似不搭邊兒的人,興許也能建立起交情,因他們有一個(gè)共同身份:廠礦子弟。

《你好,李煥英》劇照
在國家“三線建設(shè)”工程里,湖南地處二、三線之間,1958年拔地而起的國營廠,為軍事戰(zhàn)略輸送原子彈生產(chǎn)材料。外公、姑姑、媽媽都是廠礦工人,身為第三代子弟,楊瀟解釋起“醇化”、鋼瓶質(zhì)檢和輻射監(jiān)測(cè)工作也不含糊。重工業(yè)制造把數(shù)道程序切割成段,上承下至,一步步一環(huán)環(huán),牽連著大時(shí)代的安全感與榮耀,也扣緊父輩的腰包、糧票、孩子,和全部的生活。
豆瓣“廠礦子弟”小組里有一個(gè)帖子,號(hào)稱匯集“最全軍工企業(yè)代號(hào)”,從101廠列到999廠。楊瀟家所在的廠礦是二開頭,對(duì)外稱“新華材料廠”。有那么段日子,在廠里上班兒,腰桿興許比百年前的族長白嘉軒還直挺,還有人家里添置了單車、縫紉機(jī)、電話,倒映在中國東北角的另一個(gè)鏡像里,是六名前鋼廠工人哼著《心戀》,去偷一架鋼琴。

《鋼的琴》劇照
脫口秀演員李誕也是廠礦子弟,不同于他的“集體生活一天三遍號(hào)”,楊瀟印象里的廠礦特色,不在人群密度,而是某種雜糅感。譬如外公外婆家的單元樓,住著上海人、東北人、湖北人、河南人,口音各異,本地人也不說方言。還有小孩子眼里的“全世界”——相比普通單位,廠礦更接近一個(gè)自給自足的小社會(huì),從家屬院到子弟學(xué)校,從商店、書店到燈光球場(chǎng)、工人俱樂部,生活設(shè)施完備,文娛活動(dòng)也豐富,“是周邊農(nóng)村和市區(qū)小孩都沒辦法想像的,有一種自豪感”。
很多年后,楊瀟認(rèn)識(shí)了一個(gè)詞——“飛地”(Enclave),它帶著陌生化的地緣意味,成為成年子弟對(duì)家鄉(xiāng)廠礦的新注解。或許只有時(shí)間能回答時(shí)間。那些糾纏在一起、清淺的人際因緣,填不滿這座臨時(shí)存在的孤島。孤島深處是野墳,楊瀟說,老人們聊起地下挖出的尸骨,分不清是哪一場(chǎng)戰(zhàn)亂的遺骸。從這里長出來的生命也撲朔得緊,楊瀟的初中同班同學(xué)有好幾位已經(jīng)離世,原因不一,腦癌、白血病,幾乎驗(yàn)證著坊間的傳聞:“我們廠人個(gè)子很高,有人開玩笑說是因?yàn)楸惠椛溟L大的,因?yàn)楹先似毡楸容^矮。”
“孤島”傍水而居,“島民”隨水流動(dòng)。廠礦一側(cè)是北流的湘江水,另一側(cè)通京廣鐵路,幼年時(shí),楊瀟沿著一條鐵路支線捉蝗蟲,抬眼有火車載著重金屬轟隆隆駛來,后來變成一批大人在火車站扎猛子“下海”。

《少年巴比倫》劇照
楊瀟的父親出走于1997年,奔赴深圳之春。高中時(shí),楊瀟南下探望父親,緊盯著深南大道的花花綠綠,暗示自己“一定要考出去”——90年代國企效益下滑,廠礦里堆滿衰敗的跡象,沒有什么比一雙工人推開子女的手更迫切,因此除了奠定獨(dú)子最早的閱讀序列,還要不斷給他“考出去”式的敲打。
如今,廠礦敘事附著在不同形態(tài)的創(chuàng)作里,若隱若現(xiàn)。在一張名為“廠礦子弟”的音樂專輯里,有首歌直接被命名為《與父輩不一樣的活法》。反觀楊瀟,看不出反叛的少年心性,但他也在一篇文章里寫過:“從小到大,眼看著父母這一代在必然性與偶然性間、在不如意與更不如意間掙扎,覺得‘控制’常常是人世間大多數(shù)痛苦的來源。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
自由的“代價(jià)”是他白白浪費(fèi)掉50分,考到離家1500公里的天津。接下來是北京,然后是德國漢堡、美國劍橋,工作之余穿過大半個(gè)地球。父親離世時(shí),他人在威尼斯,往家趕的路上,一種道不明的情感也跟著遠(yuǎn)去了。

《我11》劇照
“我們這一代,尤其是70末80初這一代,都生活在不自知的假定里面,因?yàn)槌錾褪恰睹魈鞎?huì)更好》,我們是聽著這首歌長大的。” 80年代生的廠礦子弟如今正處青壯年,今日即“明天”。這些年,楊瀟感到世界加速前進(jìn),“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往車窗外扔?xùn)|西,扔掉被這個(gè)時(shí)代認(rèn)為過時(shí)的東西”。也許廠礦也是一種“過時(shí)”,是處于倒計(jì)時(shí),終將在某一天、某一刻被徹底遺忘。
成為寫作者后,楊瀟第一個(gè)想寫的就是廠礦。他和出版社編輯羅丹妮聊過,這些故事貫穿個(gè)人史、家族史、時(shí)代史,沒有什么比親自講一講更有意義。但回溯歷史不如想象中容易,很多東西已經(jīng)很難挖掘出來了。重新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的人,像某種熱帶植物,長出了柔軟的芯、厚的葉和殼。
廠礦也在修枝減葉,再生長。前幾年,楊瀟家所在的老廠引入了一條生產(chǎn)線,儼然煥發(fā)又一春。每年冬天,他還會(huì)回到小時(shí)候的燈光球場(chǎng),和新廠的工人大哥們一起打球。楊瀟是小球高手,但排球不太行,就跟著學(xué),反復(fù)練習(xí)。
說到這些,我以為他徹底放棄了書寫計(jì)劃。“不算放棄,”楊瀟說,“也許以后還是要寫。”
二、書生
新世紀(jì)的聲音,一種是“輕松一下Windows 98”,還有一種是“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那時(shí)候憑借一份還算體面的薪水,和無價(jià)的感召力,“媒體能拿走最好的學(xué)生”。

《南方周末》1999年元旦特刊
楊瀟畢業(yè)于南開大學(xué)中文系,身上不少特質(zhì)得益于母校的學(xué)術(shù)氛圍。他記得當(dāng)時(shí)的室友,大一上學(xué)期就在課本扉頁上寫:目標(biāo),博士生導(dǎo)師。“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是碩導(dǎo)了,”楊瀟翻出手機(jī)里的老照片,“我們寢室六個(gè)人,出了兩個(gè)大學(xué)教授。"
千禧年的大學(xué)校園,是關(guān)心世界、辣評(píng)時(shí)政的思想高地。所以說起那年,楊瀟念了一串自己常逛的論壇(BBS)名:清華大學(xué)水木清華、復(fù)旦大學(xué)日月光華、南京大學(xué)小百合、北大一塌糊涂……同樣攪動(dòng)人心的,還有各大論壇的當(dāng)日話題榜,“類似于現(xiàn)在的熱搜”。還有段時(shí)間,同城高校間為網(wǎng)大(netbig)論壇上各自的排名掐架,直接惹惱了一位南開老教授,他站在講臺(tái)上說:不管你上什么大學(xué),如果不自我學(xué)習(xí),都是一樣。
很早嘗到了媒介自由的味道,楊瀟開始追趕小時(shí)候的夢(mèng)——當(dāng)記者,同時(shí)放棄了去復(fù)旦讀研究生的機(jī)會(huì)。彼時(shí)他已進(jìn)入復(fù)試名單,學(xué)校還打來過電話,后來他才知道,話筒對(duì)面的那個(gè)人,恰是當(dāng)時(shí)在復(fù)旦任職、現(xiàn)在的中山大學(xué)傳媒名師張志安。
媒體在他身上制造了不少巧合。楊瀟深深記得,他去新華社面試那天是2003年11月11日,《新京報(bào)》創(chuàng)刊日。“現(xiàn)在好難想像這種畫面,去體制面試的畢業(yè)生,人手一份《新京報(bào)》。我還記得頭版是克林頓擁抱艾滋男孩的照片,二條是袁凌寫的調(diào)查報(bào)告,SARS后骨壞死患者調(diào)查。”

《新京報(bào)》創(chuàng)刊號(hào)
曾經(jīng)的新華社是一流新聞工作者的天地,也是人文學(xué)者、作家的居所,用楊瀟的話說,“很多縫隙里面藏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譬如科幻作家韓松、《城記》的作者王軍。
后來到了《南方人物周刊》,周圍的人更“奇怪”,楊瀟一本正經(jīng)地總結(jié)為“具有生物多樣性”。這里有人“敏感”,有人“悶騷”,好在大家都按照原本的樣子生長,以至于后來團(tuán)隊(duì)解離,不同的人也走入了完全不同的軌道:吳虹飛是歌手,易立競(jìng)登上綜藝舞臺(tái),劉子超成為旅行作家,林珊珊和杜強(qiáng)創(chuàng)業(yè)內(nèi)容公司……
媒體人的性情也與媒體氣質(zhì)有關(guān)。如果說《南方人物周刊》充滿書生意氣,《南方周末》里就是腥風(fēng)血雨,記者們會(huì)為一篇稿子拍桌大吵,在站內(nèi)論壇把對(duì)方罵得狗血淋頭。作家李海鵬曾任《南方周末》主筆,他筆下的老東家有另一個(gè)溫柔的面向:“報(bào)社里有一點(diǎn)兒草莽氣,一點(diǎn)家庭氛圍,一點(diǎn)兒舊報(bào)館的書生氣”,“每個(gè)人都受惠于它的聲望”,“當(dāng)你得了月度好稿獎(jiǎng),評(píng)語就像你是最了不起的人類”。
“我們至今仍然覺得,那是個(gè)特別好的工作。”楊瀟說起與前同事們的追憶。同樣的感嘆出自前《南方周末》記者、真實(shí)故事計(jì)劃的創(chuàng)始人雷磊:我曾以為自己能干到退休。
時(shí)間太長,變故太多,很難描繪一群“最優(yōu)秀的記者”離開的路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記掛著同一件事:08年的汶川大地震。楊瀟的另一位朋友、四川籍作家李靜睿當(dāng)過八年記者,在那一年遇到了巨大的精神危機(jī),“人生似乎從此劃出一條清晰界限”。直到現(xiàn)在,提起那份“最好的職業(yè)”,她仍自我判決為“逃兵”,“躲在虛構(gòu)后面,躲在了時(shí)代后面”。

汶川地震紀(jì)念碑
從廢墟走出來的楊瀟,說起當(dāng)年采訪過、現(xiàn)在已經(jīng)30歲了的北川孩子,心會(huì)“軟一下”。用以抵抗時(shí)間的辦法,是寫下去。從楊永信13號(hào)室事件、芮成鋼案,到昂山素季獲釋,再到北京唐家?guī)X“蟻?zhàn)濉保宦房碧健⒂涗洠萌馍礤N煉記憶,引發(fā)共鳴,也收到了一些回響。2013年,楊瀟帶著“新聞學(xué)界的最高榮譽(yù)”——哈佛尼曼學(xué)者的身份,前往美國進(jìn)修。哈佛的精英式教育,磨去他身上一層對(duì)管理學(xué)的成見,回到北京后,當(dāng)上了《時(shí)尚先生》雜志副主編。
時(shí)尚雜志,一線明星、國際大牌和市場(chǎng)紅利的代名詞,但在一個(gè)自認(rèn)不擅長管理的寫作者看來,是事無巨細(xì)的忙碌、文字服膺于“大片”和永遠(yuǎn)摸不準(zhǔn)的讀者與公眾號(hào)閱讀數(shù)據(jù)。如果幾年前聊起這些,楊瀟會(huì)批駁信息過載和用戶下沉,如今他已經(jīng)神色自如地復(fù)盤起離職心路了:“我知道我不會(huì)在時(shí)尚集團(tuán)干太久,由奢入儉難嘛,就消費(fèi)降級(jí)。以前我還買西太后、巴寶莉,后來降到Massimo Dutti,很快發(fā)現(xiàn)也不行了,太貴了,就優(yōu)衣庫、淘寶。”
從新聞機(jī)構(gòu)、文化刊物到商業(yè)雜志,我以為最終“勸退”他的是娛樂至死的反噬,是,也不是。楊瀟的穩(wěn)定性在于,能撬動(dòng)他的只有內(nèi)心對(duì)自由的排序。他最在意“自己掌控自己的時(shí)間”這件事,為此放棄過不少找上門的工作機(jī)會(huì)。“太累了,”楊瀟回想那些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的日子,“和人吃飯都只能約在公司樓下。”
盡管幾次投入浪潮,但他從來都不是什么社交達(dá)人。他直言自己采訪時(shí)能切換成“假嗨”狀態(tài),如果參加飯局消耗了能量,就出門暴走,“把散落的自己一片片找回來”。后來離開媒體,大有退隱江湖的意思,斷絕社交,不看朋友圈,友情轉(zhuǎn)發(fā)也一并省了……
“我不是文藝青年,也從來沒有過作家夢(mèng)。”楊瀟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這一點(diǎn)。他身上有一股飄搖滌不掉的少年氣,隱約還是子弟時(shí)期的輪廓:十幾歲關(guān)心釣魚島,一度被書架上的《中國可以說不》吸引;別人白衣飄飄地寫詩、看《海盜電臺(tái)》,他迷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每周必讀《21世紀(jì)環(huán)球報(bào)道》……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捷克劇作家,曾于1993-2002年間擔(dān)任捷克共和國總統(tǒng)。圖為捷克街頭舉著哈維爾照片的年輕人。
當(dāng)一個(gè)這樣的人開始獨(dú)自遠(yuǎn)行,“孤獨(dú)”也許是注定的。30歲以后,楊瀟與過去的好朋友們逐漸形成分野,他未婚,全職寫作,寫一種很難定義的體例——?dú)v史非虛構(gòu)和旅行寫作的結(jié)合。被問及同儕壓力,他思索良久,給出的結(jié)論是“和他們寫得不一樣”。他斷定自己在用“特權(quán)”換“自由”,為此必須承擔(dān)失去參照系的危險(xiǎn)。
具體到寫作,也有很多東西觸不可及,比如小說。在楊瀟看來,小說的高度倚仗于天分,非虛構(gòu)更依賴市場(chǎng)和整體行業(yè)的發(fā)展,“寫得再差還有一個(gè)資料價(jià)值”。而之所以沒成為新媒體寫作者,也是看到了周圍人腳下的泥濘。“這年頭你的稿子不能只是好或者很好,而得是超級(jí)好,才有機(jī)會(huì)在熱鬧喧嘩的自媒體汪洋大海里殺出一條血路”。
行業(yè)變了。好在楊瀟沒有過多停留,他有了其他可追尋的東西,或者說,他一直都有。十年前,楊瀟在緬甸見到結(jié)束了21年軟禁生活的昂山素季,聽她講“道德”、“對(duì)與錯(cuò)”、“愛與慈悲”。如今這朵“玫瑰”再陷鋃鐺。而她當(dāng)時(shí)說過的話,像拋出的一枚硬幣,重新懸置在了空中——“這個(gè)世界是圓的,也許什么時(shí)候好多事情要重新來過,也許到那時(shí),我就又走在時(shí)代前面了。”

昂山素季,緬甸政治家,曾獲諾貝爾和平獎(jiǎng)。1989年被緬甸軍政府軟禁,2010年獲釋,2021年2月1日再次被軍方扣押。
三、行者
楊瀟提到過兩次落淚。一次是在昆明閑游,偶遇西南聯(lián)大舊址,“非常刻奇地?zé)釡I盈眶”。還有一次是看許知遠(yuǎn)采訪許倬云,老先生回憶抗戰(zhàn)歲時(shí),痛哭流涕,他也跟著哭得稀里嘩啦。
“遺民”、“放逐者”、“喪家之狗”,不再扮演種種不合身的社會(huì)角色后,這些原本屬于特殊歷史時(shí)期的字眼,開始頻繁出現(xiàn)在楊瀟的人生詞典里。半新半舊的廠礦系統(tǒng),奄奄一息的傳統(tǒng)媒體,他參與過它們的好時(shí)光,也接受了光陰不再,但若從中剝離出完整的自我,需要找到新的意義和與自己相處的辦法。
我問他如何定位自己,楊瀟反問,如果自稱“城市新中產(chǎn)階級(jí)”是不是很蠢?采訪中,他說過很多個(gè)“如果”,類似的反思也常常出現(xiàn)在他的寫作里:如果一個(g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duì)國家的認(rèn)識(shí)都來自報(bào)紙和書本;如果一個(gè)旅行愛好者,會(huì)把沿途的風(fēng)景作為“成果”展示給別人;如果一個(gè)公民,擅于思考而行動(dòng)力萎縮……最好的方式可能還是出發(fā),重新出發(fā),解決自己與身處時(shí)代的關(guān)系的憂慮。
時(shí)代不乏憂慮者,尤其是知識(shí)分子。抗戰(zhàn)初年,南遷途中的林徽因眼看著士兵們往相反方向走,罵自己“‘慚愧’兩字我都嫌它過于單純”,她寫信給沈從文,“后方的熱情是罪過,不熱情的話不更罪過?二哥,你想,我們?cè)撛鯓拥幕钪庞蟹ㄗ影差D這一副還未死透的良心?”后方的熱情與良心,還凝聚成一條蜿蜒曲折、充滿新奇與冒險(xiǎn)的迢迢長路,300余名大學(xué)師生曾經(jīng)此出發(fā),穿草鞋,睡石板,一路昂揚(yáng)高歌,只為“去我所知最好的學(xué)校”……楊瀟不明白,是什么造就了我們與那代人的巨大差距?

湘黔滇旅行團(tuán)舊照
18年春天,楊瀟用一篇公眾號(hào)文章,正式宣布重走“湘黔滇旅行團(tuán)”之路。這次計(jì)劃符合他一貫的行事風(fēng)格:獨(dú)行,步行,歷時(shí)余月。文章發(fā)出后,故友紛紛轉(zhuǎn)發(fā)、打賞,為行程添了些孤單和悲壯的味道。他看了看大家的轉(zhuǎn)發(fā)語,“有人說我在放逐自我,還有朋友說選了一條困難的路,要堅(jiān)持,感覺這個(gè)年頭做這件事是很傻、很笨重的,可是對(duì)我來說很愉快,甚至很酷。”
臨行前,他盡可能向每個(gè)人輕描淡寫,對(duì)媽媽也編了一套說辭。然后一路回避“景點(diǎn)”,回避“舒適的旅行”,克服偶發(fā)的關(guān)節(jié)疼痛、腸胃病和炎癥,為了減負(fù)還切下過半塊肥皂。偶有苦楚時(shí),他想起湘黔滇旅行團(tuán)成員、植物學(xué)家李繼侗說的:“試試一個(gè)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簡化到什么限度,因?yàn)槟菚?huì)讓你知道自己究竟為何所累。”

湘黔滇旅行團(tuán)中10位教師的合影
原本的生活漸行漸遠(yuǎn),沿途的故事不斷涌來。有時(shí)候是快手直播的青年、言語高深的江湖郎中,有時(shí)是不太好吃的米粉,和一些拆遷標(biāo)語、“反標(biāo)語”。西南大后方的煙火中,也頗有些文學(xué)性的瞬間。比如湘江邊的那場(chǎng)黃昏,楊瀟聽見身邊的捕魚人對(duì)著自己的娃娃說:這是我的太陽,不是你的太陽,你的太陽是八九點(diǎn)鐘的。
還有一次,一位老人對(duì)他朗誦自己的詩:“世間萬物都增價(jià),老來文章難值錢。”楊瀟濕著眼睛,心中升起一股共情的自憐,現(xiàn)實(shí)難題再度撞進(jìn)腦海。出發(fā)前,他做足了苦行的準(zhǔn)備,卻不太敢預(yù)設(shè)文本的未知——他要邊走,邊寫,一路撿拾和拼裝時(shí)代遺風(fēng),而不僅僅是為自己出發(fā)。
面對(duì)龐雜的資料,“職業(yè)病”還發(fā)揮了作用。多年記者生涯,楊瀟堅(jiān)持不拖稿、不留別字、不坑編輯,如今置換成寫書,是依靠超強(qiáng)自律和慣性,當(dāng)日收集的信息,當(dāng)天整理完畢。經(jīng)歷了漫長的篩選、分類、爬梳,這本后來被命名為《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lián)大》的書,僅電子版參考資料就超過了60GB,內(nèi)含900個(gè)文件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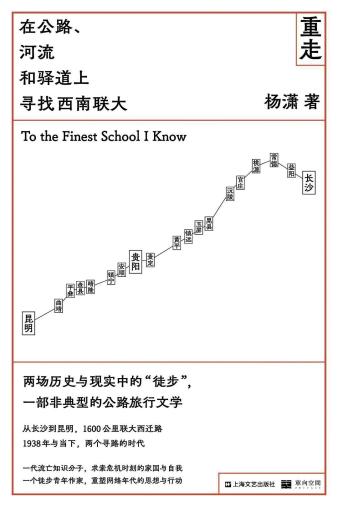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lián)大》,楊瀟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文件里的大部頭,是走訪聯(lián)大二代、三代人留下的。楊瀟先拜訪了語言學(xué)家趙元任的女兒趙新那——楊瀟和這一家人算是有些緣分,2013年在哈佛訪學(xué),他宿舍幾十米外就是趙元任的故居。1941年,湘黔滇旅行團(tuán)進(jìn)入昆明后,合唱的那首“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迢迢長路到聯(lián)合大學(xué)》),由趙元任改編,詞曲間充滿浪漫與希望。
趙新那是趙家后來留在國內(nèi)的唯一一個(gè)孩子,與父母27年未得相見。她給楊瀟講了一個(gè)故事,說逃難經(jīng)過九江,母親看上船上小販賣的一尊白觀音,講價(jià)到一半,空襲警報(bào)響起來,對(duì)方下船跑了,讓趙家落得了一個(gè)沒給錢的觀音菩薩。這座觀音后來跟著他們漂洋過海,在父母兄弟間輾轉(zhuǎn),見證了這些年的幾多風(fēng)雨。去年,趙新那去世了,享年97歲,楊瀟甚至沒來得及親自送她一本贈(zèng)書。

趙元任一家合影,右二為趙新那
還有103歲的吳大昌。這位在湘黔滇旅行團(tuán)拿過“步行矯健獎(jiǎng)”的老人,如今常戴一頂尖頭小帽,到大學(xué)操場(chǎng)上和年輕人一起運(yùn)動(dòng)、拉伸筋骨。楊瀟說,他每次都會(huì)拉著自己講好幾個(gè)小時(shí)的話,即使剛做過手術(shù),聽力也不好。——一場(chǎng)演講中,楊瀟還說起重走路上那些沿途遇到的老人對(duì)他的幫助之大,“可惜大家現(xiàn)在都不愿意聽老人說話”。
再老的人,也當(dāng)過稚氣的孩子。當(dāng)年,吳大昌與楊瀟偏愛的旅行團(tuán)成員查良錚(詩人穆旦)在同一個(gè)分隊(duì),后者的著名事跡是邊走邊背英文字典,背一頁撕一頁,人抵達(dá)聯(lián)大,整本字典剛好背完、撕完。吳大昌的故事少了些振奮,在聯(lián)大讀書時(shí),他長時(shí)間陷入苦悶,為排解郁結(jié),還偷偷跑到學(xué)校教室后面爬電塔,寫信問馮友蘭“悲觀”和“人生的意義”。
這位長壽老人,比自己多擁有近兩倍的人生,楊瀟好奇,他如今又怎樣看待人生?“人生就是,活著就是活著,”吳大昌告訴他,“……你就好好過生活,你在生活里頭過好生活,就沒有問題。”

吳大昌與楊瀟
吳大昌的這份“樂觀”,后來被楊瀟寫成了書的結(jié)尾。但他也聲明,那不是答案,他還沒有自己的回答,也不想用前人的經(jīng)驗(yàn),為當(dāng)下提供一種解法。“很多問題(光靠)想是沒用的,只有做起來才有答案。有時(shí)候我看見身邊的朋友耽于思考,耽于左右權(quán)衡、思前想后,我就特別著急。預(yù)設(shè)也沒有用,反正都得要經(jīng)歷過,才有辦法。”
楊瀟自己的辦法,也是近幾年才找到的。一次新書活動(dòng),他提到以塞亞·伯林的《狐貍與刺猬》,狐貍知道很多東西,刺猬卻有一個(gè)絕招。所以如果非要形容自己,那么以前他總以為自己是只狐貍,現(xiàn)在莫名其妙變成了刺猬。或許有些時(shí)候,人需要的就是一場(chǎng)天翻地覆的改變。
談及最近的狀態(tài),“刺猬”跳脫地說,正在認(rèn)真賣書,賣到體重都掉了好幾斤。“一天到晚都在回微信,但我已經(jīng)很久沒處在這種‘連接’的狀態(tài)里了,有時(shí)候覺得挺好,和世界有了許多交流界面,有時(shí)候又覺得茫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接下來,他將繼續(xù)行走,同時(shí)給手頭的項(xiàng)目“記憶的策展”收個(gè)尾。——疫情前,楊瀟用40天時(shí)間走訪了一批與20世紀(jì)德國歷史勾連的博物館,從中探討人如何處理當(dāng)下與過去、未來的關(guān)系。“我很好奇德國人是如何面對(duì)自己20世紀(jì)沒有好的歷史這件事的,又如何向年輕人和觀眾展示那些不好的記憶。”
說起這些的時(shí)候,楊瀟看起來輕快又利落,好像剛從遠(yuǎn)方歸來,又能立刻出發(fā),奔赴什么別的好地方。大概步履不停,總有未知的快樂,像他建的聯(lián)大歌單里,那一首《旅途愉快》,是這樣唱的:“世界簡直不算可愛,寶貝,但還是那樣開心,你也要來。”
*文中部分參考信息,來自《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lián)大》、《子弟》、公眾號(hào)“寫字兒”,及播客忽左忽右(《李靜睿:只有日常生活是不夠的,人需要公共生活》)、螺絲在擰緊(《楊瀟 ×吳琦:當(dāng)海量信息淹沒我們,如何生還,甚至創(chuàng)造?》)、真故FM(《前調(diào)查記者自述:我曾以為自己能干到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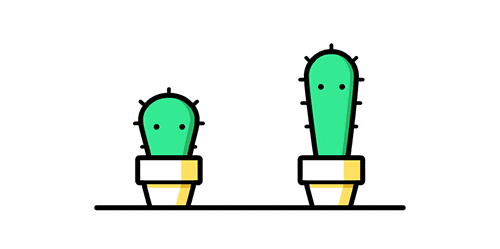
采訪&撰文 | 肖恩
編輯 | 巴巴羅薩
主編 | 魏冰心
原標(biāo)題:《楊瀟 步履不停》
本文為澎湃號(hào)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chǎng),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tái)。申請(qǐng)澎湃號(hào)請(qǐng)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