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喬姆斯基|心智研究的前景
【編者按】作為具有世界級聲譽的公共知識分子,諾姆·喬姆斯基在其50多年有關政治、哲學和語言的寫作中,為現代語言學帶來了變革,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原創力、最廣博的政治和社會評論家之一。《喬姆斯基精粹》集合了他1959年以來最重要的作品——從他對B.F.斯金納的開創性評論到其暢銷著作《霸權還是生存》和《失敗的國家》,是對喬姆斯基思想的一次全面概覽。本文摘編自書中《展望未來:心智研究的前景》一文,澎湃新聞經世紀文景授權發布。
語言學習并非真正是兒童才做的事情 ;它是發生在處于某種恰當環境中的孩子身上的事情,就像在提供適當的營養和環境刺激下,孩子的身體會以預先規定的方式生長和成熟一樣。這并非說與環境的本質毫不相干。環境決定了普遍語法參數的設置方式,從而產生出不同語言。早期的視覺環境以某種相似的方式決定了對水平線和垂直線的受體密度,實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此外,和身體成長一樣,在語言習得中,富有刺激的環境與缺乏刺 激的環境之間可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或者更準確地說,和身體成長的其他方面一樣,語言習得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屬于人類共同稟賦的能力有可能繁榮地發展,也有可能受到限制和抑制, 這取決于它們成長的條件。
這種觀點也許更加普遍。不應把教學比作往瓶子里灌水,而是幫助花朵以自己的方式成長,這是一種理應受到重視卻沒有得到足夠關注的傳統見解。任何優秀的教師都明白,教學方法和教材內容,遠不及成功地引起學生天生的好奇心、激發他們自我探索的興趣這般重要。學生被動學到的東西很快會被忘記。學生天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被激發以后,他們自己發現的東西不僅會被記住,而且會為今后的探索、調查或是重要的智慧貢獻打下基礎。
我們如何運用語言知識,包括兩個方面:感知和產出。那么,我們想知道,已習得一門語言的人在理解他聽到的內容和表達思想時如何運用自己的知識。在這些講座中我已經談到了這個問題的感知方面。但到目前為止,我并未提到產出這個方面,即我所稱的笛卡爾問題,這是從語言使用的創造性方面所提出的問題,后者是一種尋常卻引人注目的現象。對于一個想理解語言表達式的人而言,必須由心智/大腦決定其語音形式和詞語,然后運用普遍語法的原則和參數值投射出該表達式的結構表征,確定其各個部分如何關聯。我已經舉過幾個例子來說明該過程是如何發生的。然而,笛卡爾問題帶來了一些我們未曾討論的其他問題。
至于涉及這種知識的表征、獲得和使用的物理機制有哪些,我還沒有講。探討該問題主要是將來的任務。進行這種探討的部分問題在于,出于倫理原因,我們不會考慮把人當作實驗對象。我們無法容忍以動物實驗的合理方式(無論是對還是錯)對人進行實驗研究。因此,我們不會將兒童置于受控環境中,觀察他們在不同實驗設計的條件下學習了哪種語言。我們也不允許研究人員在人腦中置入電極來調查大腦內部運行情況,或通過手術切除部分大腦來確定會產生何種影響,但對除了人之外的實驗對象通常會這么做。研究人員僅限于進行“自然實驗”,如損傷、疾病等。試圖在這樣的條件下發現人腦機制是異常困難的。
就心智/大腦的其他系統而言,例如人的視覺系統,對其他生物體(貓、猴子等)的實驗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諸多信息,因為這些物種的視覺系統顯然十分相似。但就我們所知,語言機能是人類獨有的。想通過對其他動物大腦機制的研究得知人的心智/大腦機能,幾乎沒有可能。
就提出的這些問題而言,我們也許會給出下列答案:語言是一種習慣系統,是一種通過訓練和條件限制獲得的行為習慣系統。該行為的任何創新方面都是“類推”的結果。其中的物理機制本質上與接球和其他技巧行為涉及的一樣。柏拉圖問題未曾受到認可,被當作細枝末節而不予考慮。人們一般認為,語言“被過度地學習”;問題在于要解釋這樣一個事實:為何需要大量經驗和訓練才能獲得這些簡單技能。至于笛卡爾問題,也未曾在學術圈、應用學科和整個知識界中受到認可。
讓我們回到笛卡爾問題,即我此前所說的如何以慣常的創造性方式使用語言的問題。請注意,我在此關注的并非具有真正美學價值的語言使用,也不是優秀的詩人或小說家、出色的文體學家作品中所謂的真正創造性。相反,我考慮的是更世俗的東西,即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語言使用。它具有鮮活的特性,不受外部刺激和內部狀態的控制,與情景切合并能激起聽者進行恰當的思考。該問題的由來值得關注。
該問題產生的背景是心智—身體(mind-body)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就是后來所謂的“其他心智的問題”。笛卡爾提出宇宙機械論,這對當時的物理學是個重要的貢獻。他深信,在我們經驗世界里發生的一切事情,實際上都能用他的機械概念——用通過直接接觸而相互作用的物體(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接觸機械論”)——來解釋。他試圖用這些術語解釋一切,從天體運動到動物行為,乃至大部分人類行為和感知。他顯然認為,自己在這項任務上幾乎大功告成,剩下的只是在自己的總體概念上添加細節而已。但并非我們所有的經驗都能適用于該框架。他指出,最顯著的例外就是我此前所說的語言使用的創造性方面。笛卡爾認為,這完全超越了機械論概念的范圍。
每個人通過內省都能覺察到自己擁有心智,心智的屬性與構成物質世界的物體明顯不同。現在假設我想確定另一種生物是否也有心智。笛卡爾主義者提出,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進行某種實驗項目,用以確定該生物體是否顯示出人類行為的明顯特征,而語言使用的創造性方面是最突出的例子,也最易于研究。笛卡爾主義者認為,假如把鸚鵡的器官以某種形態置于給定的刺激環境中,鸚鵡“說”的話是被嚴格確定好的(否則就可能信口胡言)。但與我們一樣具有心智的生物體就不是這樣,實驗應該能揭示這一事實。當時人們提出要做許多具體測試。假如這些測試讓我們相信該生物體具有語言使用的創造性,那么懷疑它不具有像我們一樣的心智就毫無道理了。
我此前曾提到,更籠統地講,該問題在于“機器”是在固定的環境條件下被迫以某種方式運轉,其零部件也以某種方式組裝,而人在這些情況下只是“受誘導或傾向于”以這種方式行事。人也許經常或總是受誘導或傾向于做某事,但我們內心都明白自己在這件事上的選擇余地很廣。而且我們可以通過實驗確定其他人也是這樣。笛卡爾主義者(十分準確地)得出結論,被迫與只是受誘導和傾向之間的差別很大。即使沒有在實際行為中表現出來,這種區別也是關鍵性的。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可以用機械術語準確地描述人類行為,但這不是對人類基本特征和人類行為根源的真實描述。
為了說明機械論無法解釋的關于世界的事實,有必要找到某種超機械論的原則,我們姑且稱之為“創造性原則”。笛卡爾主義者認為,該原則屬于心智,心智是與得到機械論解釋的身體完全分離的“第二物質”。笛卡爾本人寫過長篇著作論述機械世界的原理。本來最后一卷是關于心智的,但據說在得知伽利略面對宗教裁判所時被迫宣布放棄自己對物質世界的信念之后,笛卡爾就毀掉了這篇完整著作中的這一部分。在他保存下來的著作中,笛卡爾暗示,我們也許不“具備足夠的智力”去發現心智的本質,“盡管我們如此在乎我們自身的自由和中立(而缺乏嚴格的界定),以至于我們沒有比這理解得更通透的事情了”,而且“我們從內心體驗和感知到自身存在的這個問題,只是因為我們沒有從事物本質出發理解其不可理解性就懷疑該問題,這就很荒謬了”。
對笛卡爾主義者而言,心智是單一的物質,與身體不同。這個時期的大部分猜測和辯論都是關于這兩種物質如何相互作用的——例如,心智的決定如何可能導致身體的行動。沒有“動物心智”這回事,因為動物只是機器而已,聽從機械的解釋。人類心智這一概念構思不可能和其他種類的心智或具有不同構成的各種人類心智區分開來。生物要么是人類,要么是非人類;不存在“人類性質的不同程度”,除了外在的身體方面,人類沒有基本的變異。正如哲學家哈里·布萊肯所指出的,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在這種二元論觀念中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
笛卡爾主義者認為,心智是一種“能用于所有突發情況的普遍工具”。請注意,該主張與笛卡爾認為的我們也許不具備足夠的智力去發現心智本質的觀點不一致。認為心智具有內在局限的結論肯定是正確的;心智是一種“普遍工具”這一觀點可能來自某些先輩的觀點。他們普遍認為,人類語言機能和其他認知系統都在適用于各項智力任務的“一般學習機制”范圍之內。
近些年間,笛卡爾用來檢驗是否存在其他心智的測試又以新的面目出現了,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設計的測試,現在被稱為“圖靈測試”,用以確定機器(例如一臺程序化計算機)是否具有智力行為。我們把圖靈測試用在一個裝置上,向它提出一系列問題并看看它的回應是否能騙過觀察者,讓他以為是另一個人在回答。用笛卡爾的話來說,這種測試可以檢測該裝置是否和我們一樣具有心智。
今天,我們應當如何回應這些觀點?笛卡爾的觀點絕非荒謬,也不可被輕易忽視。假如機械原理的確不足以解釋某些現象,那么我們必須尋求這些原理之外的東西去解釋。至此,那就是我們熟悉的科學。我們不必接受笛卡爾的形而上學思想,該思想假定有一種“第二物質”,這是一種不加區分的、缺乏組成部分或相互作用的子部分的“思想物質”(res cogitans,即精神實體),即解釋“意識整體性”和不朽靈魂的意識寶座。這一切都無法令人滿意,也沒有對提出的任何問題給出真正的答案。然而,這些問題本身十分嚴肅。正如笛卡爾所認為的那樣,僅僅因為我們想不出解決事實的方法就否認在我們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未免太荒唐。
觀察笛卡爾心智-身體問題和其他心智存在問題說法的走向,這是很有趣的。只要我們對身體具有確定的概念,就能合理地提出心智-身體問題。假如我們沒有這種確定而不變的概念,就無法追問某些現象是否在該概念范圍之外。笛卡爾主義者根據其接觸機械論提出了相當確定的“身體”概念,在許多方面反映出常識性的理解。因此,他們能合理地闡釋心智-身體問題和其他心智存在的問題。也有人試圖為進一步發展“心智”概念做了重要的工作,包括 17世紀英國新柏拉圖主義者所做的研究,他們探究了感覺和認知的范疇和原理,其研究路數后來被康德繼續拓展,并在20世紀格式塔心理學中又被重新發現。
另一條發展路線是17、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普通和哲學語法”(用我們的術語講就是“科學語法”),尤其在其早期深受笛卡爾概念的影響。這些對普遍語法的探究旨在揭示語言的一般原則。這些原則被認為與思維的一般原則沒有實質性差異,因此按照傳統的表達來說,語言是“心智的鏡子”。出于種種原因——有些合理,有些并不合理——這些探究被輕視和放棄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在20或30年前才再次獨立地煥發生機,但所使用的術語截然 不同,也并未借助任何二元論的假設。
看著笛卡爾的身體和心智概念如何進入社會思維,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最突出的是讓——雅克·盧梭基于嚴格的笛卡爾“身體”和“心智”概念的自由意志觀點。因為擁有心智的人與機器(包括動物)截然不同——盧梭這樣認為,也因為心智的屬性遠勝于機械的確定性,所以對人類自由的一切侵害都是非法的,必須要直面并加以克服。盡管這種想法后來的發展摒棄了笛卡爾的框架,但它的起源與這些古典思想有著很深的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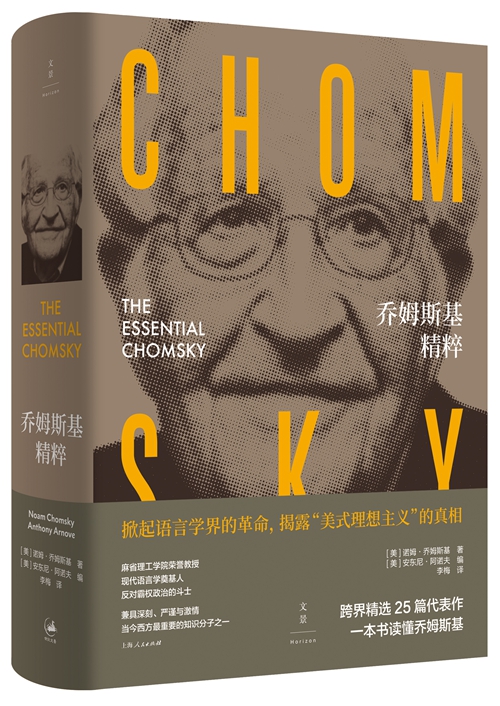
《喬姆斯基精粹》,[美]諾姆·喬姆斯基著,[美]安東尼·阿諾夫編著,李梅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