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陸蓓容評《追尋江村秘藏》|鑒藏史何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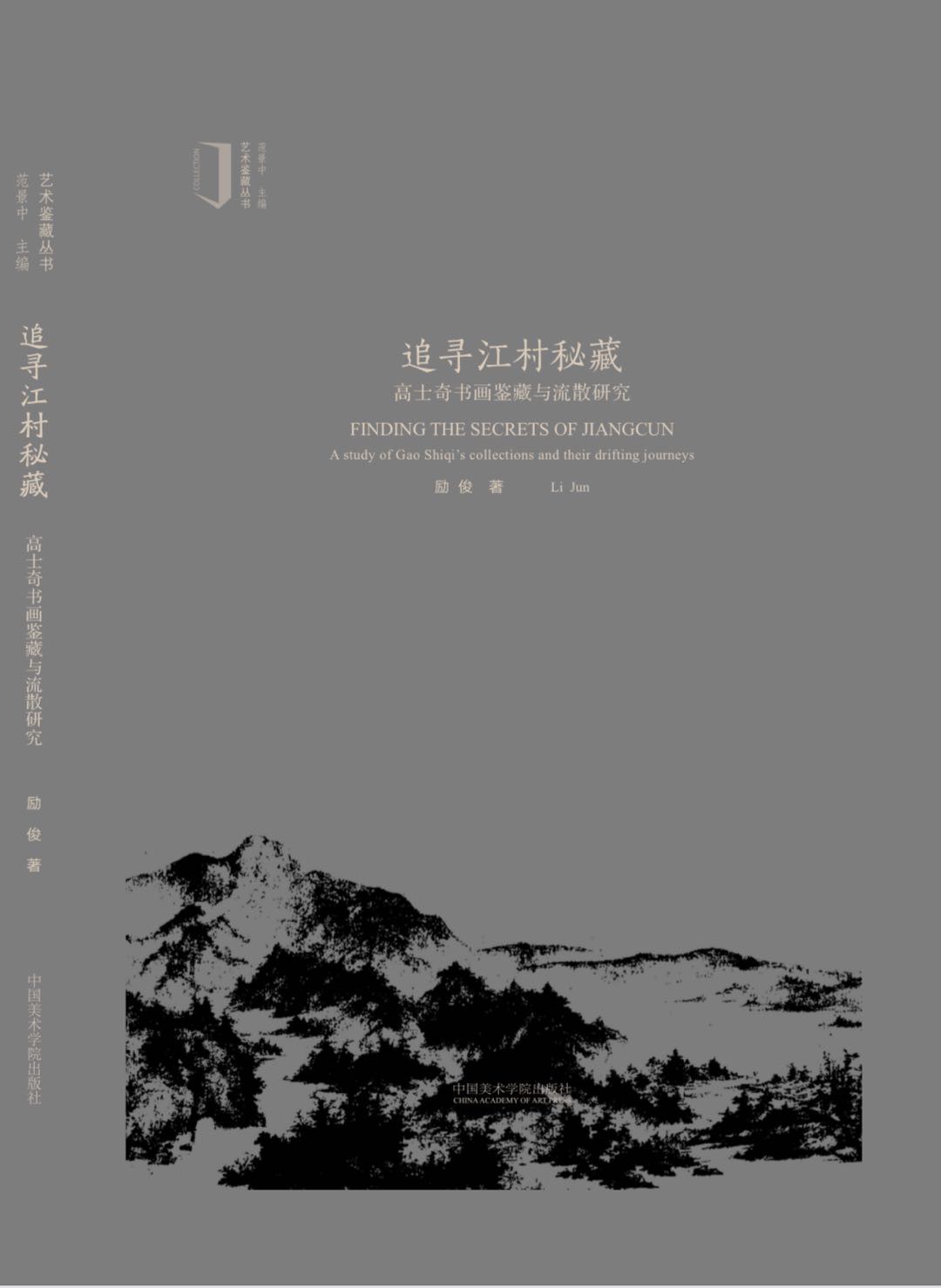
《追尋江村秘藏: 高士奇書畫鑒藏與流散研究》,勵俊著,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390頁,128.00元
我曾經的研究對象宋犖與《追尋江村秘藏》作者大著研究的對象高士奇是一對老友;在書畫收藏事業上,宋、高二位也是同志,因此我對本書處理的時段與史料都相對熟悉。這部書研究康熙年間一位重臣高士奇(1645-1703)的書畫收藏之路。那是收藏家群星璀璨的時代,不過,像高士奇這樣身前身后文獻齊備的情況實屬難得,它們讓這部書有一副堅實的骨架。
其正文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作者考證了傳為高士奇所作的《江村書畫目》。因為其中有向康熙進呈贗品的記錄,民國間“發現”此目的羅振玉等學者便一再坐實此說,致使今日的學術研究很難繞開這個問題。過往的文獻學者未必留心這類清中期非主流書畫賬簿,美術史學者又未必關心“文獻生成”這類議題,竟至于無人想過,賬簿的形成,常常有一個歷時甚久的過程。在稿本狀態下,它可以一直生長,至某一抄本,才可視為某條一支流的終點。作者詳細討論了《江村書畫目》里的各個類目,從稱謂、作品、書寫習慣等角度,指出其中每一個具體門類的成書時間并不一致,各部分的編輯者也不會是同一個人。由此,高士奇本人向康熙進呈偽作的論斷就不攻自破了。
一部書的故事尚且如此蜿蜒曲折,人的一生當然更加波瀾壯闊。第二部分深描了高士奇人生中每一個重要的腳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白衣讀書人,在家鄉結了婚,從杭州來到京城;以門館寒士之身,入宮傭書;投了康熙帝的脾氣,終于苦熬得科甲正途,名正言順地坐上好位置;遭遇政治盟友的背叛,在滿漢官員斗爭中落于下風,只好頂著招權納賄的惡名奪職回鄉;期間喪妻失子,又重新回到權力中樞,直至病亡。
盡管處理過大量機要政務,高士奇并沒有養成矜嚴愍默的性格,反倒相當樂于作詩、寫題跋,展現一部分私人生活面貌。康熙時期的滿漢奏折已經整理出版,而瞻慕風流的后代文人又曾大力收藏當日的名賢尺牘。作者大量利用這些第一手文獻,讓它們彼此勾連互證,重現出古人復調的生活。他竭力細讀了詩文中的每一個典故,也關心聯句詩中各人出場的順序,析論往往精微入妙。
高士奇入朝攬權之際,既是南方士人獲得政治機遇的時期,也是新王朝漸漸穩定、書畫市場存量充足、價值體系日漸形成的時期。他久居過的都城與江南,又正是書畫傳統悠久、傳世作品豐富的地方。天時地利都是契機,名利場中揖讓晤對、政治漩渦中載浮載沉的日子,也是聞見日廣、藏品日豐的好時候。
每個人的一生都受制于各種方向的合力,并被它牽扯著走向終點。有時,我們管這種力量叫做命運。書畫收藏這件事情,本來就在高士奇的命運線上。所以描述就是解釋,講他也就是講它:他的人生經歷,足以說明他是如何漸漸聚攏起一份書畫收藏——甚至部分包括他為何選擇主動公開一部分收藏。在得罪鄉居的三年之間,高士奇曾經主動刊刻《江村銷夏錄》,這是當時第一部在作者生前公開出版的書畫著錄類文獻。作者對此最大膽且巧妙的推測,是將它視為一份官員財產公示清單。刊刻它,部分是為了回應那份貪贓枉法的彈章。
這是一個無法證實的推論,未必人人都能同意。不過,倘若遺貌取神,倒可以說其間反映出作者選定的書畫鑒藏史研究路徑:把作品與言論放在作者一生的境遇之中來理解,就是在嘗試還原收藏這件事對一位古人究竟可能意味著什么。倘若這摻雜著自污、自證與自白的一端過于現實,難以接受,那么也許值得提醒:我們所熟悉的銷憂樂志、與古為徒那一端,也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甚至同地又同時。因為人是復雜的。
高士奇非常熱愛寫題跋。他的文辭不算優美,但少考證而多隨記,談天氣、朋友、家人與花木,記下詳細的日月歲時,故而親切可讀。這些材料極其常見,可形神俱散,并不能據以論述他的“鑒藏觀”,是以過往的研究者并未就此用力。作者把這類史料按照時間順序串聯起來,真實展現了作品與鑒賞者之間的關系,也非常深切地說明了一個淺顯的道理:收藏家會在藏品上投射種種現世的感情。
很遺憾,收藏的故事一定是以聚攏始,以散失終。第三部分如同年譜的“譜后”,讓這個故事染上了一點哀傷的色彩。幾代后人層累的記載、藏品卷端的印章、《石渠寶笈》等后代著錄和乾嘉年間的詩文筆記一起,幫助復現了江村遺藏逐步散失的過程。它們一部分進入乾隆宮廷,一部分在民間不斷易主。于此,我們接近了另一個常識:書畫實物承載著動蕩不息的人事變遷過程。變是常態,而常,倒是變態。藏品由民間走向宮廷的流散之變,關涉著趣味改易、知識轉型、交流減少等一系列情況。數十年后,不難觀察到收藏者的整體水準有所下降。不論皇帝本人,還是像吳榮光這樣的高官藏家,其一般知識與趣味,都很難再達到康熙時期的水平。固然曾有一些論文從各種角度論述過這個過程,但放在一個人的生命之歌里聽,這段尾聲便格外令人嗟嘆徘徊。
全書正文像宮娥話舊,又像天孫織錦。只牽引話頭,鉤沉故事,而不引證駁斥,更不肯長篇大論,攀扯時賢。作者以高士奇本人的命運,來展現“收藏”這件事的方方面面,讓讀者不知不覺地走近眾生喧嘩的康熙時代,看帝王心術、人臣權柄、都市繁華,也看一幅畫、幾首詩、兩三朋友,和終將抹平恩怨的溶漾江湖。
在作者業余投身研究的十余年里,我也從學生變成了學徒工。文科學問既講方法,又訴諸人類生活的種種經驗,但好像真不考校“科班出身”。掩卷增愧,并非虛語。不過也想借此機會,放言談一點工作心得。此書關于高士奇如何收藏的描述,已經真實地還原了這種活動究竟會有多少維度。有一批頂級的經理人,同時為幾家高級客戶服務,幫他們收羅藏品、加以裝裱。有一些最為優秀的畫家,為高級藏家臨摹副本。在我讀過的早早晚晚幾十部清代賬簿和著錄里,還有門客為東主整理藏品,區別等第;下僚向上官贈禮,送一堂寫滿吉祥話兒的十二扇屏風;父親為兒子分家,在每一件作品下蓋上木戳。書畫是一種實物載體,大家愛它的動機有別,方式也不同。人們未必總愿意,也未必總需要深究它的品質。即便精鑒詳考,斷代定名,固然可能是為了某種理解和重建藝術史的理想,但也同樣可能是為了展示權力,滿足虛榮,或者轉手賣更多錢。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可能”,還可能經不同人之手,疊加在同一件作品身上。
同一件作品,對進博物館看展覽的我們,和在書齋里展卷的鑒藏家們,在作坊里修補接割的裝裱匠們,在真跡難覓的時代,對著粉本苦苦臨摹的藝術家們,并不是同一種東西。若把名家書畫——尤其是畫——當成作品,討論它事實層面的真偽、技法層面的優劣,從而建構起一部歷史,那它當然只能是百家姓與報菜名的組合。既往的各種中國美術史課本之所以枯燥無趣,正因這一維度太過單薄。從前基于專家鑒定結論而完成中國大陸公藏書畫編目工作,也正因這種思路,而刊落了太多“不值一提”的作品,令人朝夕懸想不置。
鑒藏史研究的意義在于,它能夠告訴我們:在普遍意義上,作品的絕對真偽,相當不重要。相對優劣,偶爾也不那么重要。有時候,并且常常是重要鑒藏家的選擇、認定和敘述,才為一段繪畫史架起了價值體系,或者為一件早期的無名作品點定身份,并把它安排進那體系里去。那些進入書畫史的名字,都曾經過無數輪這樣的淘洗,是因為權重代代增加,才能夠留得下來。所以,是明清收藏家為我們今天的故事寫定了雛形;而他們熟悉的情節,又有著更久遠的來源。可是操縱話語,決定這權重的一代代人,動機千變萬化,水平天差地別,常常近于亂點鴛鴦譜,偽與真,壞與好,人人各一是非。寫到這里,倒可以隔空回應一下高士奇的進贗之說。即便他確實曾經用假畫兒做過貢品,也不見得全是奸臣的心術。回到那個時代的語境里,這沒什么。
藏家選擇什么,以及他“不選擇什么”,意味著某些價值觀。鑒藏史研究就是在討論每一時期價值觀的邊界,并提醒從業者,我們或多或少都在這歷史的邊境線內展開工作,統統是如來掌心里的孫悟空。為藝術史增加一重鑒藏的維度,當然不是為了讓枯燥繁冗的故事變成喧嘩與騷動,也不僅僅是為了挖掘出幾位影響過風勢的大藏家,而是為了建立這樣的認識:書上的顧陸張吳、文沈唐仇,本來就只是一個個朦朧的倒影。即便在托形以傳的明清時代,董其昌、王石谷也莫不皆然。辨析不同層次的“實物”,為這倒影勾清輪廓,常似西西弗斯推石頭;既然如此,倒不如看一看影子究竟曾經傳播到多遠的地方,人們對它的信仰有多深。
從創作的一面出發,有時是做減法。剔除偽品,正本清源,便如十五以后的月亮,清輝日減。從收藏的一面出發,常常是做加法。凡有月光處,都在同一段傳統之下。這月色伴人云間水上到層城。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