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像量子的語言和被語言說出的世界
著名的量子物理學家費曼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想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說,沒有人理解量子力學”,當然這也包含了他自己。

我想費曼這句話包含了兩層意思,其一就是量子物理學本身并不像牛頓經典物理學那樣統一和規整,而是由很多科學家在諸多層面分別發現的理論結合起來形成的一套針對極小的量子層面的數學表述,所以要想全面的了解量子物理學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其二,也是更為關鍵的一點是,就連費曼也經常告誡周圍的人,不要去試圖問量子物理學為什么會這樣,而是在已經得到的量子理論之上去探索會發生什么。
可能這么說起來有些空洞,如果單拿出來一個量子理論中的現象,比如說量子糾纏,兩個相距甚遠的例子,竟然可以實現一種超光速的協同,如果這種現象放在現實生活里,就是心靈感應或者隔空取物了。

不斷追問量子物理學為什么會是這樣,最終可能會導向形而上學或者神學的境地。所以大多數物理學家會采取一種工具主義或實用主義的態度,把量子理論看成數學公式,去使用就好了,至于為什么,交給無聊的哲學家吧。
費曼的這個斷言也仿佛可以成為討論量子物理學的免責聲明,下面就針對量子理論的一些關鍵問題,進行一點點的思維探索,雖然并不會給量子理論帶來什么進展,但也許會改變一些認知方式和模式,對理解日常的一些現象會有所幫助。
量子理論最關鍵的基石就是所謂的“波粒二象性”。在牛頓的經典物理學中,一切都是以粒子形態存在的,這世界仿佛是一個布滿縮小版的臺球空間,一個個原子都像臺球一樣,如果沒有外力作用它們是不會動的,而只有碰撞之后,原子就會遵循牛頓定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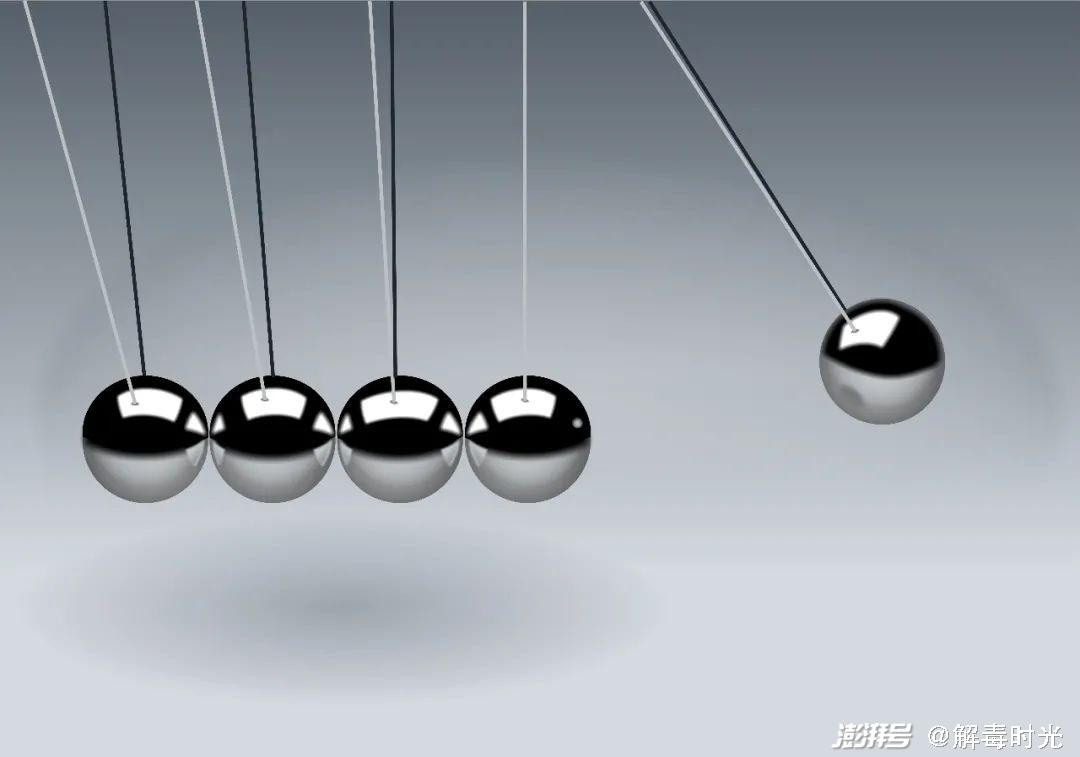
在雙縫干涉實驗以及后續的一系列證據的確認下,現代的物理學家已經達成了共識,所有的物質除了具有粒子性之外,也具有波動性。粒子性很好理解,它就像我們現實世界的不斷細分的模式。但波動性又代表了什么呢?說一個物質是波動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用一種通俗的比擬方法來說,粒子性代表的就是一種實體狀態的存在,而波動性則代表了一種關系性。粒子就仿佛是一顆顆的珍珠,而波動性就是將這些珍珠串成串之后的項鏈。
設想一下,當我們把物質不斷細分,到最后不可再分的時候,會出現什么狀況?按照常識去想,可能會得到一個非常小的物質,這就是粒子性的想象。但我們再換個角度去思考,如果把一個人無限細分,得到了非常多的小的物質之后,那么人的思維、感覺都去哪兒了,這些性質在細分中被忽略掉了。所以必然有一些特性是無法切分下去的,也就作為整體所獨有的,局部所不具備的特性是無法細分下去,我們可以把它們稱作關系,而由這些關系所構成的一個類似于物體的東西,就是波動性。

可以說粒子就是一種孤獨的存在,而波動表現的就是粒子之間的關系。但量子理論中還有一個更加詭異的測不準原理,也就是說在粒子性和波動性之間,我們只能更精準的測量一種,當我們選擇觀察粒子性,那么波動性就變得模糊,反之亦然(如果用物理學的語言來說,就是無法同時獲得位置和動量的準確測量)。
這就好像是給了我們一副近視鏡和一副遠視鏡,可以通過它們看到不同的東西,但我們無法把它們同時戴上。其實這并不意味著實在的情況,只不過是針對人的測量能力,或者說認識能力,但卻也詭異的表現出,當我們想測量粒子時物質就是粒子的,當我們想測量波動時,物質就是波動的。
由此還可以引申出一些的就是,我們認識到的世界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認識的方式,或者說分類的方式。所以世界也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這些認識方式的疊加,只有當我們從某個角度認識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向我們呈現出我們要看的那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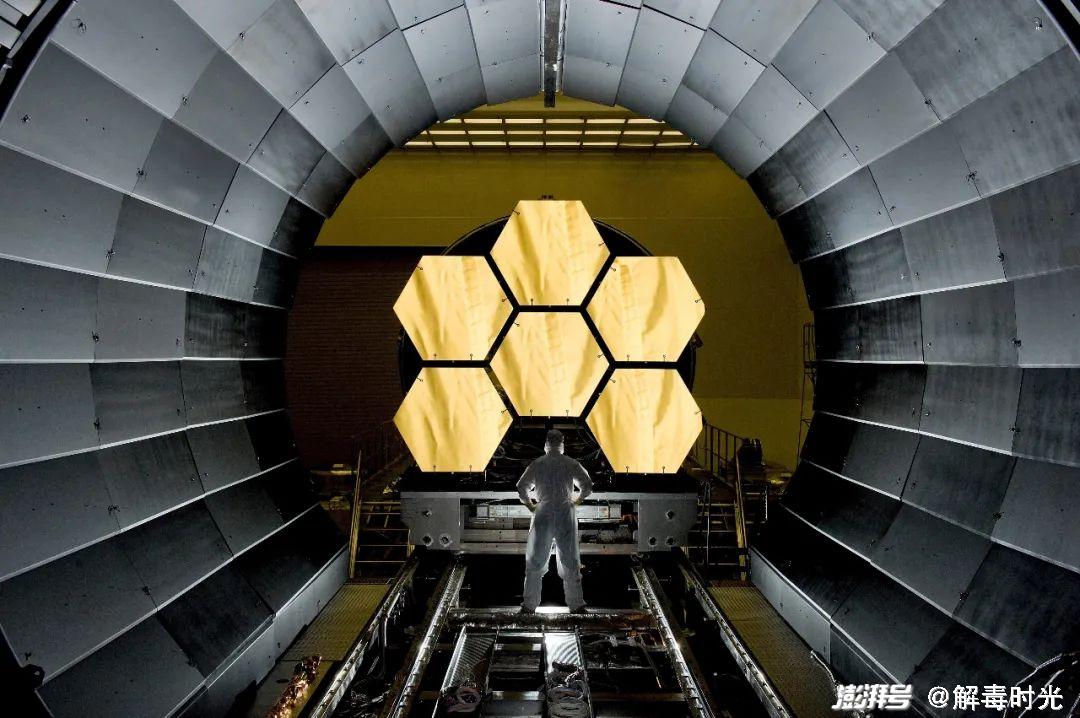
而這種世界存在的方式,就可以被看作量子理論中的“疊加態”,著名的薛定諤的那只貓,就是處在生與死的兩種可能的疊加態當中。在量子理論中,世界仿佛是可能性的疊加態,只有當我們去觀察并且參與其中的時候,疊加態的方程才會坍縮成某一種可能并向我們呈現。
以上這些就是在不涉及任何數學和物理實驗的情況下,能談論的量子理論了,在深入了解這些理論的時候,還有一個意外的發現,就是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和量子理論之間的“糾纏”。
語言的量子隱喻
語言也具有粒子性和波動性,如果我們把粒子和波動抽象為個體和關系這兩種模式的話。
語言是由最小單位詞匯構成的,這些詞匯可以被看成一個個獨立的粒子存在,當然這些詞匯是有其代表的意義的,只不過含義可能不唯一。當我們把詞匯匯聚在一起,形成一句話的時候,更重要的往往是語境,而不是具體某個詞的意思,也就是說這些詞之間的關系成為了表達一句話的關鍵,這也就是語言的波動性。

有一個著名的例子:
一個女孩種的樹上有一些黃色的葉子,她把它們染成了綠色。她的鄰居正在找一個綠色的主題,這個女孩就對攝影師說,拍我的樹葉吧,它們都是綠色的。
第二天,一位植物學家來找女孩,想要研究一下她樹的綠色葉子,可女孩又說,這些葉子不是綠色的。
同樣的一棵樹,對不同的人,女孩說出了不同的判斷,表達了不同的意思。在這兩個判斷中,說給攝影師的綠色指的就是顏色,而說給植物學家的綠色就是指生命的、自然的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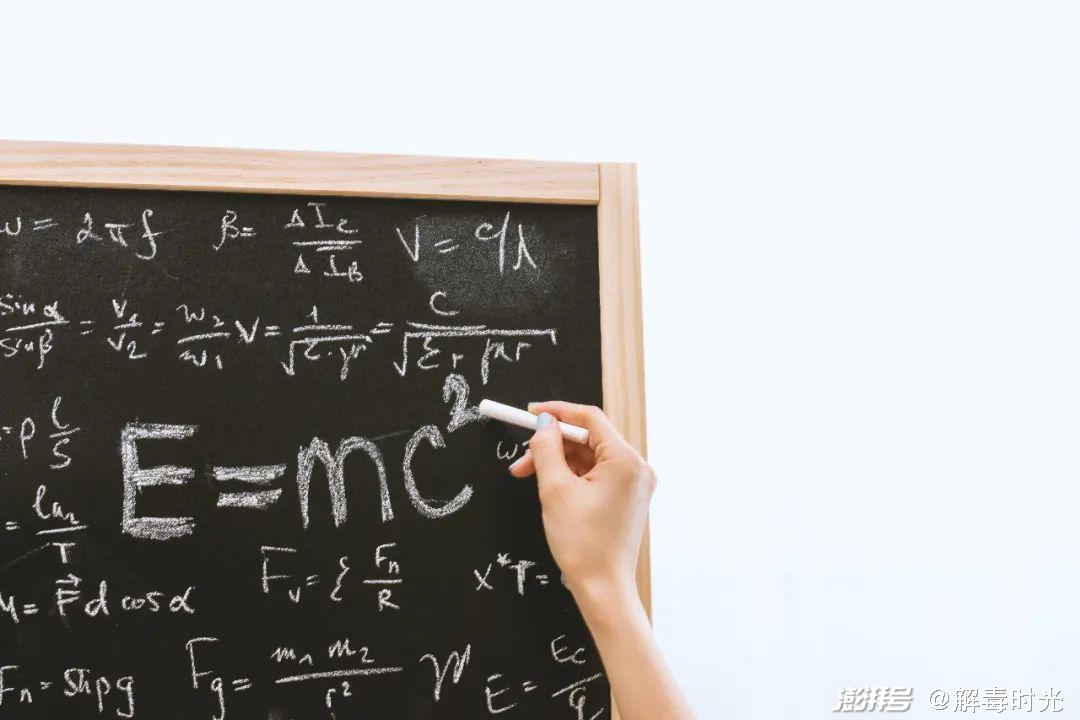
如果語言僅僅是粒子的,就無法把這兩句話區分開,這是必須要用到波動的關系特性,也就是通過語境來去判斷這個綠的到底指的是什么。但這樣一來,也會帶來語言的測不準問題,當我們關注某一個詞的真實含義,往往就會忽略掉語境的關系,但當我們把焦距拉開,關注語境的時候,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也會被模糊掉。
實際情況就更不是如此的簡單,設想一下當我們想要表達的時候,是如何挑選出一個個的詞組成的句子?是什么力量,讓我選擇了用“選擇”而不是“選出”或者“選中”?如果說背后是我們的意識或思維在其作用的話,那么在詞語被選出前,意識或思維是以什么樣的形態存在的(因為在日常的體驗中,思維和意識大多是以語言的形式存在的)?
如果不是意識在主動的挑選詞匯,那么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意識恰好碰到了那個他想用的詞,就說出了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么?而且我們還要面臨著在不同情況下用不同的程度的詞匯這種復雜的情況,在一個沒有語言的大腦深淵中的意識,究竟如何點亮自己,在神經元中劃過一道閃電,將詞語找出并連成句子的呢?

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的一句話也許能夠帶來啟示,他說,圖像激發幻想,言語刺激占有欲。意思就是圖像往往能夠描繪出諸多的可能性,而文字最終把這些可能性固定下來。
如果用量子理論來構造一個語言的隱喻的話,就是圍繞著要表達的意思,在意識中會有一種疊加態的存在,很多種表達的可能性疊加在一起,當我們的思維說話的時候,這些可能性坍縮為我們真正說出的那句話。

當然,有的物理學家并不認為這是一種隱喻,目前有一些理論傾向認為人類大腦就是一個量子系統,語言也就是這個量子系統的一種表達產物,所以語言就具有量子特性。對此在人類還沒有充分了解大腦產生意識的原理之前,也只能被當作是一種合理的假設,對此不能太當真,也不能輕易否認。
但當從量子過渡到語言的時候,這種同構帶來的發現,可以將我們帶入一個新的領域,也就是對世界整體的認識上。
從量子、語言再到整個世界
量子理論帶來的一個重大啟示就是當我們將某些物體無限細分下去的時候,總有一些屬性是無法再分的。反過來看,量子理論會帶來一種被稱作“涌現”的特性,也就是整體具有局部不具備的特性。這一點在人類身上最為明顯,單獨組成人體的那些原子、分子甚至器官都不具備思考的能力,但當它們組成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能思考的生物。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總體并不等于局部的加總,或者說局部在構成總體的時候,它們的排列關系,互相之間的組成方式會帶來總體的一些全新特性。如果用粒子性和波動性的抽象來說,就是實體和關系構成了我們所看到的世界的整體。

大多數時候,我們的感官能認識到的首先是實體,每一個存在的物品,春花秋月,潮起潮落,這些都是一種實體化的認識。但在這背后,諸如牛頓定律、相對論、量子力學這些都是代表著種種關系。除去這些高深的內容,哪怕是走在路上,我們依然能通過鞋子感受到摩擦的存在,在磁鐵吸引中感受到磁場的存在,關系也同樣是可以被間接感知的。
世界仿佛是一塊蛋糕,能被認識到的最終形狀取決于我們怎么切它,但我們也不要忘記,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塊快的蛋糕,還有蛋糕之間的縫隙,那種關系,代表著我們當時切它的痕跡。而且當我們真的切割開的時候,可能就割斷了一些關系,世界就不再是那個原本的世界,而只是被我們人為分離的世界。
世界是粒子的,也是波動的,是靜止的,也是運動的,是實體的,也是關系的,是局部的,也是整體的,世界還可以是很多,也許我們根本就認識不到,也許我們可以不斷發展自己的認識方法,從而可以還原那個坍縮的波函數,接近那個真實的世界,但我們仍舊永遠也無法觸達它,那個整體的、現實的、存在并變化著的世界,而只能根據我們自己的認識來獲得一個屬于我或我們的世界。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