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話牛津歷史學(xué)家(下):永遠(yuǎn)無法打一場針對抽象的戰(zhàn)爭
“伊斯蘭恐懼癥”如何成為一種全球現(xiàn)象
澎湃新聞:您還寫過另外一篇文章,闡釋“伊斯蘭恐懼癥”是如何成為一種全球現(xiàn)象的。您提到,在談?wù)摗耙了固m恐懼癥”時(shí),即使是美國人也不例外,他們會(huì)將9·11事件與從十字軍東征到奧斯曼土耳其圍攻維也納城的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但諷刺的是,20年后,美國就這么草草地從阿富汗撤出了。
費(fèi)薩爾·德夫吉:“伊斯蘭恐懼癥”的問題,確實(shí)會(huì)發(fā)生。無論如何,我們目前在西方看到的是對與聯(lián)軍合作阿富汗人無盡的痛惜,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在喀布爾機(jī)場已經(jīng)被撤離,另外一些人涌向了巴基斯坦、伊朗邊境,在美國、在英國,外界似乎有太多的同情。目前還沒有太多的反移民和反難民的聲音,但是這很快也有可能發(fā)生轉(zhuǎn)變,就和敘利亞最初的情況一樣,一開始敘利亞人是受歡迎的,但隨后迎來了反移民和反難民的高潮,也導(dǎo)致歐洲國家的極右翼更為強(qiáng)大。所以這是有可能發(fā)生的,也很有可能以一種“伊斯蘭恐懼癥”的方式發(fā)生,就像敘利亞人的情況一樣。極右翼擔(dān)心恐怖分子正在通過難民的流動(dòng)滲透到西方國家,但現(xiàn)在這一刻還沒有發(fā)生,我們要觀察一段時(shí)間,看看那里(歐洲)會(huì)發(fā)生什么,但我認(rèn)為風(fēng)險(xiǎn)肯定是很高的,“伊斯蘭恐懼癥”的問題也將會(huì)是更加重要的。

維也納之戰(zhàn),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被歐洲“神圣同盟”擊退
澎湃新聞:很有趣的是,三年前我在敘利亞遇到了一些歐洲的極右翼,他們往往都與阿薩德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guān)系,當(dāng)敘利亞政府軍奪回大片土地時(shí),他們?yōu)榘⑺_德歡呼。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歐美一些極右翼支持者也在為塔利班慶祝。
費(fèi)薩爾·德夫吉:這非常有趣,因?yàn)樵跀⒗麃啠憧梢韵胂螅@些極右組織可能會(huì)把阿薩德政府視為是一個(gè)非伊斯蘭的政府,但是我們不能這么看塔利班,因?yàn)樗麄兊恼畬?huì)是遵循伊斯蘭教法的。一方面,阿薩德政府得到了來自俄羅斯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得到了像伊朗這種伊斯蘭國家的支持,這是曖昧而矛盾的。塔利班可能也是如此,也許歐洲的極右翼運(yùn)動(dòng)更加關(guān)心的是難民是否會(huì)涌入,其次他們才會(huì)關(guān)心政權(quán)本身。
同時(shí)我也認(rèn)為,極右翼反自由主義和反全球化、新西方自由主義的性質(zhì)實(shí)在太過強(qiáng)烈,以至于他們看到任何反對這種政治形式的人都會(huì)自動(dòng)成為他們的盟友,所以他們建立起了這種荒謬的“友誼”。極右翼同時(shí)也模仿著一些對象,即使是他們不喜歡的人。在這種基督教“圣戰(zhàn)”的思想中,人們的心被團(tuán)結(jié)在一起,塔利班其實(shí)也是類似的,因?yàn)槲鞣降臉O右翼其實(shí)與政治伊斯蘭分子在某些方面有著共同點(diǎn),他們對于社會(huì)的幻想——人類在道德上可以是完全純潔的、在這個(gè)社會(huì)中男女完全隔離、保持等級(jí)制度、法律是嚴(yán)厲的……他們共享著所有這一類的想法,即使二者的合法性來源全然不同。所以你會(huì)經(jīng)常看到,伊斯蘭恐懼的極右翼們和伊斯蘭國家、領(lǐng)導(dǎo)人及政府之間的關(guān)系似乎相當(dāng)矛盾。
澎湃新聞:為何人們只會(huì)說“伊斯蘭恐懼癥”,而從來沒有過“基督恐懼癥”或是其他宗教的恐懼癥?歷史上也發(fā)生過很多基督徒實(shí)施極端襲擊的事件,2018年發(fā)生在新西蘭清真寺的襲擊就是一個(gè)例子,但是人們并不會(huì)責(zé)備整個(gè)基督徒群體。
費(fèi)薩爾·德夫吉:現(xiàn)在,“伊斯蘭恐懼癥”這個(gè)詞好像十分自然,每個(gè)人都會(huì)用這個(gè)詞,但其實(shí)這個(gè)詞是新造的,從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才開始使用,這個(gè)詞有太多需要批評(píng)的點(diǎn)。首先,這是一種“伊斯蘭例外論”(Islam Exceptionalism),沒有其他的“恐懼癥”,只有“伊斯蘭恐懼癥”。當(dāng)然,現(xiàn)在一些印度民族主義者也會(huì)說,世界上存在一種“印度教恐懼癥”(Hindophobia),但這種邏輯其實(shí)還是“伊斯蘭恐懼癥”的邏輯。
我不喜這種例外論的行動(dòng),就像我也不喜歡“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這個(gè)詞,對于其他宗教來說,不會(huì)有這種詞,只有伊斯蘭教。這種例外論把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從這個(gè)社會(huì)的語境當(dāng)中剔除了。關(guān)于“伊斯蘭恐懼癥”的有趣之處在于,人們選擇了“伊斯蘭”這個(gè)詞,但這并不適用所有穆斯林,而“恐懼癥”(phobia)這個(gè)詞是一種分析心理學(xué)的術(shù)語,通常指的是精神疾病。一方面,這個(gè)詞把問題政治化了,另一方面,它注重的是抽象化的概念——伊斯蘭,而非作為個(gè)人的穆斯林。這種現(xiàn)象其實(shí)有很長的歷史,人們反對的是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而不是信仰它的人。
在兩個(gè)案例中,都會(huì)有虛偽的事情發(fā)生,因?yàn)閷?shí)際上“伊斯蘭恐懼癥”的受害者不是伊斯蘭教,它只是一個(gè)抽象概念,它不存在,它的受害者是穆斯林人民。同時(shí),伊斯蘭教被呈現(xiàn)為受害者,也授予了一些人“政治代理權(quán)”,因?yàn)椤耙了固m恐懼癥”這個(gè)詞的存在,穆斯林再次陷入激進(jìn)分子宣傳的刻板印象的圈套中,即穆斯林在任何地方都是受害者。我認(rèn)為,穆斯林也很有必要否認(rèn)自己是受害者,因?yàn)槿后w一旦被視為受害者,會(huì)導(dǎo)致非常可怕的心理障礙,也會(huì)妨礙穆斯林作為一個(gè)公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共鳴。這是我對“伊斯蘭恐懼癥”的反對意見。同時(shí),我也同意,確實(shí)存在特別針對穆斯林群體的偏見和歧視,就像人們對黑人、對亞洲人,或是女性的歧視一樣。
穆斯林與西方:多元化還是同質(zhì)化?
澎湃新聞:您也提到了“伊斯蘭例外論”,其實(shí)很多西方的學(xué)者也尖銳地提出,他們看到穆斯林嘗試了這么多年,都沒能完全讓自己的國家成功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或者說是達(dá)到西方標(biāo)準(zhǔn)的現(xiàn)代化,他們認(rèn)為問題出在伊斯蘭教本身。您怎么看待這個(gè)問題?在您看來,政治伊斯蘭運(yùn)動(dòng)是由根植于伊斯蘭這種宗教信仰的意識(shí)形態(tài)所驅(qū)動(dòng),還是說,這是一種對政治、經(jīng)濟(jì)等其他機(jī)制的結(jié)構(gòu)性變化所作出的回應(yīng)?
費(fèi)薩爾·德夫吉:當(dāng)然,我認(rèn)為任何“合法的”歷史學(xué)家都會(huì)選擇第二種,否則,就會(huì)創(chuàng)造出例外。確實(shí),政治伊斯蘭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導(dǎo)人可能會(huì)回到宗教文本,甚至是很久以前的文本本身,但是隨著時(shí)間流逝,這些文本的意義會(huì)發(fā)生改變,語境不會(huì)是相同的。政治伊斯蘭主義者和反政治伊斯蘭主義者另一重諷刺的關(guān)系在于,二者都認(rèn)為存在一種單一的、持續(xù)的歷史。我反對這一點(diǎn),我認(rèn)為歷史是改變中的歷史,一切都取決于政治、經(jīng)濟(jì)等結(jié)構(gòu),它們當(dāng)然會(huì)改變。文本和教義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它們在不同的語境下起著不同的作用,也擁有了不同的內(nèi)涵。
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發(fā)生的變化,有時(shí)重要,有時(shí)不重要。這些過去的元素、正在發(fā)生的事情和從那個(gè)時(shí)代開始起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和辯證關(guān)系,對于每個(gè)人來說都是如此。所以我想強(qiáng)調(diào)的是,我們不能將這些穆斯林團(tuán)體當(dāng)中的任何一個(gè)排除在外。當(dāng)然,人們可以像我一樣對他們持批評(píng)態(tài)度,但同時(shí)又不將他們排除在外。例如,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出現(xiàn)在歷史上的一個(gè)特定階段,此前從未出現(xiàn)過。但是法西斯主義利用了很多歷史上的元素,反猶太主義早于法西斯主義,在西方基督教當(dāng)中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這段悠久的歷史在納粹主義那里被拿去做了非常不同的事情。相似的是,種族主義也出現(xiàn)在法西斯主義之前,但是它同樣被改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形式。如果我們可以這么討論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我們也可以如此討論政治伊斯蘭主義和圣戰(zhàn)主義,或是任何相關(guān)的事情。
澎湃新聞:您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張口閉口‘穆斯林統(tǒng)一’只會(huì)使穆斯林遠(yuǎn)離統(tǒng)治其社會(huì)的民族國家構(gòu)成的政治社會(huì)。”在談?wù)摎W洲穆斯林移民的語境下,可能很多人會(huì)同意這種說法。在穆斯林移民融入西方社會(huì)的問題上,您更贊同哪種方式?是像英美一樣更多地允許文化多元,還是像法國一樣,在所謂的“世俗主義”(la?cité)框架下進(jìn)行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ulation)?
費(fèi)薩爾·德夫吉:我認(rèn)為這取決于不同的國家和它的傳統(tǒng)。我愿意相信,以多元化的方式來理解政治生活是可行的,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必須看起來一樣,做一樣的事情。但我想比起允許多樣性、堅(jiān)持公民身份的統(tǒng)一性,這個(gè)問題更多是一個(gè)是否獲取平等機(jī)會(huì)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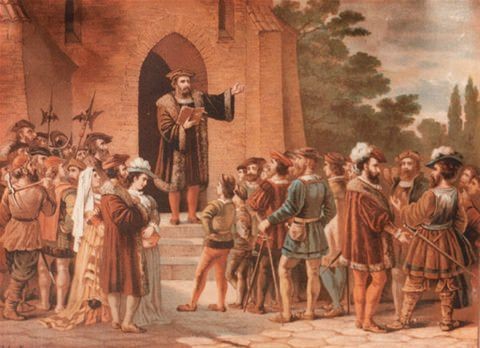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我想知道,如果法國能夠確保所有的公民都得到平等對待,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這些問題是否還會(huì)出現(xiàn)?大多數(shù)法國穆斯林都是世俗的,法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的通婚率是歐洲最高的,這意味著許多人都很好地融入了“法式生活”。但是如果他們?nèi)匀粫?huì)因?yàn)樽约旱拿只蛘吣w色被歧視,那么就有問題了。需要統(tǒng)一的公民身份還是多元化的公民身份,這與各國的傳統(tǒng)、憲法和歷史有關(guān),不能以同樣的方式普遍化,但是可以普遍化的是所有公民的平等,一旦這一點(diǎn)得到保證,我認(rèn)為其他問題就不會(huì)那么成問題了。
我們必須記得,歐洲,特別是西歐,有著很長一段時(shí)間的轉(zhuǎn)型期,直到很近的一段時(shí)期社會(huì)才變得多元起來。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前,歐洲也是一個(gè)完全基督化的社會(huì),可能會(huì)有一些猶太人,但猶太人在一些國家也會(huì)遭到驅(qū)逐。在被征服之后,穆斯林、猶太人在西班牙被驅(qū)逐,在英格蘭被驅(qū)逐……盡管有一小部分猶太人,但他們的存在也不被寬容。隨著宗教改革,西歐出現(xiàn)了新教教會(huì),這些國家必須進(jìn)行重塑(refashion),無論是新教國家還是天主教國家,它們必須在內(nèi)部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所以統(tǒng)一基本上是歐洲傳統(tǒng)的一部分。
到了20世紀(jì)中期以后,歐洲才不得不開始應(yīng)對多元化的問題。但其實(shí)我們看看亞洲和非洲,這里聚集著大量的宗教、民族和語言多元的群體,無論是在中國、印度、中東,還是非洲,似乎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每個(gè)人都要在語言、宗教或族群上統(tǒng)一的情況,其實(shí)世界其他地區(qū)并沒有西歐所具有的同質(zhì)化(homogeneity)歷史。我認(rèn)為,在一種“制造同質(zhì)”的政治議程下,西歐其實(shí)比其他地區(qū)面臨的問題更大。
現(xiàn)在是西歐歷史上第一次真正面臨種族、民族和語言多樣性的挑戰(zhàn)。在過去,西歐只有特定的幾個(gè)國家擁有一種以上的語言,而這些語言之間的區(qū)別可能又不大。總之,這都是關(guān)于同質(zhì)化的問題,公民身份的問題也與之相關(guān),問題在于,我們能否在不同質(zhì)化的情況下實(shí)現(xiàn)平等?我想在亞洲、中東或是非洲,我們可以更容易找到這個(gè)答案。北美甚至南美是另外一種情形,因?yàn)檫@些國家是殖民者建立的國家,它們吸引了歐洲不同地區(qū)的人來定居,當(dāng)然,他們也有土著人口,還奴役了非洲來的黑奴,所以他們已經(jīng)不是同質(zhì)的了,不可能再像西歐國家那樣變得同質(zhì)化。
比起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法國模式可能正在進(jìn)入一種危機(jī),盡管兩種國家都遭遇了恐怖襲擊。法國的“世俗主義”模式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我不清楚,一旦法國社會(huì)開始在人口結(jié)構(gòu)上發(fā)生變化,它還是否可行。即使法國在帝國時(shí)期,社會(huì)也非常同質(zhì)化,基本上是羅馬天主教教會(huì),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律開始標(biāo)準(zhǔn)化,一種民族性被創(chuàng)造出來了。帝國末期,隨著移民的到來,突然間一切似乎都處于危險(xiǎn)之中。

畫家菲力波托(Philippoteaux)描繪了1848年革命的景象,1848年革命后七月王朝覆滅,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 。
歐盟的出現(xiàn),讓更多的人開始質(zhì)疑民族性格的重要性。金融主權(quán)不再存在,某種程度上政治主權(quán)也不再存在,因?yàn)橛辛藲W洲議會(huì)。因此,文化問題變得更加重要。國民手里的金融、軍事和政治主導(dǎo)權(quán)被奪走,他們能夠依靠的只有這些歷史和文化身份。我認(rèn)為與其說這是一個(gè)政治原則問題,這更多像是一種心理上的問題。
“你永遠(yuǎn)無法打一場針對抽象的戰(zhàn)爭”
澎湃新聞:人們在談?wù)摬煌恼我了固m運(yùn)動(dòng)的時(shí)候,總是傾向于把它們分成“溫和的”、“極端的”,但事實(shí)上它們在理論上可以算作擁有同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根基。在這20年來我們談?wù)摗胺纯帧钡臅r(shí)候,“極端主義”又幾乎和“恐怖主義”劃上了等號(hào)。在您看來,“溫和”與“極端”之間有分界線嗎?“溫和”是如何走向“極端的”?
費(fèi)薩爾·德夫吉:我認(rèn)為沒有一種真正能夠區(qū)分的方法,當(dāng)然,這兩種說法經(jīng)常會(huì)被提及,特別是一些政府可能會(huì)用到。我們會(huì)認(rèn)為“極端”意味著人們會(huì)使用殘酷的暴力形式,但是其實(shí)并不總是這樣。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現(xiàn)在人們竟然嘗試區(qū)分“好基地組織”和“壞基地組織”,所以,即使是20年來我們看到的最惡劣的敵人,他們當(dāng)中也可以分出溫和和極端。
這取決于哪些團(tuán)體可以被西方國家利用,或與之進(jìn)行談判,與他們實(shí)際做了什么幾乎沒有關(guān)系。大多數(shù)的政治伊斯蘭組織可能沒有像“伊斯蘭國”一樣蓄意、殘暴,像“努斯拉陣線”還有一些其他的組織可能會(huì)很暴力,但這(溫和與極端)通常與暴力程度無關(guān),而與國際地緣政治有關(guān)。
還有一點(diǎn)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實(shí)際上所有這些組織都沒有對任何一個(gè)國家形成既定的挑戰(zhàn),即使是在伊拉克或是敘利亞,除了摩蘇爾被占領(lǐng)這樣的事件。之所以這些組織得以變得如此強(qiáng)大,與國家被制裁有關(guān),也與國家之間的代理人戰(zhàn)爭有關(guān),許多外部力量被卷入,他們各自支持自己的代理人,這是我們熟知的故事。這也更能說明,這些組織的“極端”與“溫和”與他們本身的關(guān)系不大。所以,這是一個(gè)很難回答的問題,因?yàn)榍闆r會(huì)隨著地緣關(guān)系的改變而改變。
澎湃新聞:前一段時(shí)間我在采訪前美國資深外交官傅立民的時(shí)候,他的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恐怖主義是一種戰(zhàn)爭的工具,并不是你可以反對的東西,它不是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不是一個(gè)國家,它是一種手段,一種暴力的手段。你確實(shí)無法有效地反對一種手段。”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我們今天應(yīng)該如何應(yīng)對恐怖主義的威脅?
費(fèi)薩爾·德夫吉:我確實(shí)認(rèn)識(shí)傅立民,我曾經(jīng)在貝魯特和他見過好幾面。我完全贊成他說的這段話。恐怖主義是一種工具形式,對于恐怖分子來說,它可能具有存在意義,但是它并不特定于任何意識(shí)形態(tài)。當(dāng)然可以有伊拉克恐怖分子,也可以有巴斯克恐怖分子,也可以有伊斯蘭恐怖分子……許多不同種類的恐怖分子,有國家恐怖主義,還有非國家恐怖主義。確實(shí),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戰(zhàn)爭是荒謬的,但美國人打了一場這樣的戰(zhàn)爭。
美國人有很多場戰(zhàn)爭,并不是真正的軍事戰(zhàn)爭,比如反犯罪、毒品或貧困的戰(zhàn)爭,這是一種政治語言被軍事化的現(xiàn)象。不僅僅是語言被軍事化了,在哥倫比亞等南美國家,在這場“反毒品戰(zhàn)爭”當(dāng)中,實(shí)實(shí)在在的戰(zhàn)爭也發(fā)生了。“反貧困戰(zhàn)爭”也是真實(shí)存在的,因?yàn)橛袝r(shí)貧困的人會(huì)成為目標(biāo)。“打擊犯罪戰(zhàn)爭”也是一樣,這導(dǎo)致非裔美國人的監(jiān)禁率非常高。這些戰(zhàn)爭雖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軍事戰(zhàn)爭,但具有非常真實(shí)的影響和后果。
所有這些戰(zhàn)爭,都是針對抽象(abstraction)的戰(zhàn)爭。反貧困戰(zhàn)爭,反毒品戰(zhàn)爭,是什么意思?毒品只是一種商品,商品是怎么流入的?為什么人們會(huì)去購買?誰在推銷這些商品?導(dǎo)致吸毒上癮的社會(huì)問題是什么?這才是人們必須考慮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反恐戰(zhàn)爭也是一樣的,雖然他們沒有用“恐怖主義”(terrorism)這個(gè)詞,-Ism這個(gè)詞綴指的是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他們用的是“反恐怖戰(zhàn)爭”(war on terror),“恐怖”這個(gè)詞,只是一種工具。
你永遠(yuǎn)也沒有辦法打一場針對一種工具的戰(zhàn)爭,你也沒有辦法打一場針對抽象的戰(zhàn)爭,像是恐怖、犯罪、貧困……你必須要理解誰才是你要與之戰(zhàn)斗的人,而這正是這么多年來人們疏忽的。阿富汗之所以到今天的局面,是因?yàn)樗兄匾氖虑槎急蝗藗兒雎粤恕H藗冴P(guān)注的一切都是有關(guān)工具的,人們把某些群體工具化,人們找來了外部承包商重建,找來了非政府組織為婦女賦權(quán),但實(shí)際上這些都沒有觸及任何真正的問題。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