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廖梅:《姜義華口述歷史》糾謬六項
《姜義華口述歷史》由姜義華口述、熊月之撰稿,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出版。
姜義華教授和熊月之教授都是資深歷史學者,被年輕一輩尊稱為歷史學家。熊月之教授2000年發表《口述史的價值》一文,被個別學者視為新世紀口述歷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兩位歷史學家的強強聯合,將為口述史領域增添一部力作:口述者將以歷史學家的視野和睿智,反思七十年家國歷程;執筆人在口述文本的整理、注釋和編輯方面推陳出新,于理論和操作規范上同時為學界留下榜樣,將大陸口述史的發展推向新高度。
可是,閱罷全書,一切期待皆成泡影,讓人遺憾萬分。
除了口述者的風發意氣,書中鮮見歷史學家對于個體、群體和國家命運的省思。全書無前言、無注釋、無附錄,只有短短一頁又五行的撰稿人后記。記錄者完稿倉促,既沒有創新,亦未能體現大陸目前口述歷史作品的發展水平,只能說這是一部未經整理的粗糙的口述史料,屬于低水平的口述史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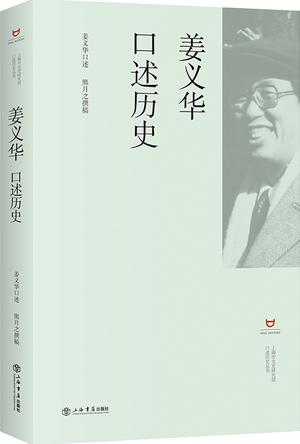
第一,主客職責不分,既侵犯了口述者的獨立性,又損害了撰稿人的客觀性。
《后記》中提到,撰稿人進行了“部分史實核對與文獻補充”。由于缺乏注釋說明,現在讀者不知道哪些史實經過核對,哪些是口述者的原始口述,哪些文獻又是撰稿人補充添加的。將口述者和撰稿人的工作混為一談,甚至越俎代庖,不利于口述史的健康發展,更損害了口述史參與雙方的獨立性和客觀性。今天,略有經驗的口述史從業者都會用注釋等手段清晰地劃定各自的文責。
第二,與他人現有記載不符之處,未能并列異說,以供讀者參考研究。
第61頁,“因為我從1959年起一直在做章太炎研究,當時受命注釋章太炎的兩篇文章。”第168頁《姜義華教授學術活動年表》又言:“遵照毛澤東關于注釋章太炎《秦獻記》與《秦政記》的指示,注出初稿,由譚其驤修改審定。”
這一說法,與現存記載有異。
1972年至1975年參與為毛澤東注釋大字本古籍的劉修明等先生,于1993年整理出版《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花山文藝出版社)一書,詳細介紹了注釋往事、注釋篇目及時間。劉修明在前言中清楚回憶,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王守稼、許道勛、董進泉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吳乾兌、劉修明五人被借調參與點校注釋工作。“此外,參預部分注釋工作的,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譚其驤、楊寬、鄒逸麟、王文楚先生,中文系的王運熙、顧易生、章培恒先生等人。”同書版權頁“參加本書部分注釋工作的”人員名單,除上面七位,又增添“李霞芬、潘咸芳”兩位。也就是說,參加長期注釋工作的正式借調人員有五人,短期或部分參加的有九人或更多。在十四位有名有姓的參與者中,沒有姜義華的名字。
劉修明又介紹:“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布置注釋章太炎著的《秦獻記》、《秦政記》二文。太炎二記已有北京注釋的簡注本,我們見到過這個本子,看來是叫我們重注的。八月中旬注釋印制完畢,上送五份。”
這段話有時間有細節,顯然劉修明等人確實有著注釋太炎二記的經歷。
朱永嘉先生《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2012年,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1、286頁兩度談及參與注釋人員:“在復旦是譚其驤作最后校訂的,王守稼與歷史組的劉修明、許道勛、董進泉、李霞芬、吳乾兌等來往于寫作組與復旦及中華印刷廠之間具體完成這項任務。在復旦參加過這些工作的有譚其驤、陳守實、楊寬、王運熙、章培恒、胡裕樹、顧易生、鄒逸麟、王文楚、徐連達等老師。”
和劉文相比,朱文增加了陳守實、胡裕樹、徐連達三位老師。但在一長串注釋者名單中,依然沒有姜義華的姓名。那么,姜義華為什么說自己注釋了太炎二記呢?是劉修明等人遮蔽了姜義華的功勞,還是姜義華將他人的經歷挪到了自己身上?
《悠悠長水:譚其驤后傳》第54頁出現了姜義華的名字。朱永嘉希望譚其驤為青年教師和其他人的注釋初稿把關。1973年“8月11日下午,章太炎《秦政記》的注釋稿送到,譚其驤改至次日凌晨2時”,“13日早上姜義華(歷史系教師)來家取走稿子”。“下午3時又開始校改章太炎《秦獻記》,也是到次日凌晨2時”,“5點多周維衍(歷史地理研究室教師)、鄒逸麟來拿走一部分稿子。6點完稿,晚飯后又修改,7點20分由周維衍取走。”
在譚其驤日記中,姜義華的功能為取稿。而且太炎二記取稿人不止一人,除姜義華外,還有周維衍、鄒逸麟。當時,為勝利完成大字本注釋任務,動員了大量教師力量,有人負責行政組織,有人查找資料,有人跑腿,有人做初稿,有人最后把關,有人跑印刷廠。姜義華時為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員,在職責范圍內,也參與注釋的輔助工作,比如提供資料文本、跑腿取件。善意推測,在取送《秦政記》之時,姜義華可能提出了自己的注釋意見。
但取稿、提出個人注釋意見,只能說參與了注釋工作。四十年后,將輔助工作籠統、模糊地描繪為“受命注釋章太炎的兩篇文章”,“遵照毛澤東關于注釋章太炎《秦獻記》與《秦政記》的指示,注出初稿,由譚其驤修改審定”,絕口不提王守稼、劉修明等五位正式借調從事初釋工作的年青教師姓名,不提當時已成建制的工作班子,顯然不符合事實全貌。

為防遺漏,筆者繼續爬梳,在朱永嘉先生回憶中又找到數條姜義華和章太炎相關活動,不過都發生在太炎二記之后。《姜義華口述歷史》未提這些經歷,本文尊重口述者意愿亦保持緘默。也許口述者猶記當年汗水,但現下不便多談,于是就把這份汗水往前挪到校注太炎二記上,以為壯歲的紀念。當口述人的回憶和現有史料發生沖突,甚至口述人過于拔高自己時,口述史的通行作法是在注釋中陳列其他史料和說法,糾正口述人的偏差,向讀者呈現歷史全貌。可惜,《姜義華口述歷史》未能以注糾偏,導致書中史實頻出差錯,降低了整部口述史的史料價值。
再如,119頁,“譚先生(指譚其驤)是在院系調整后從浙江大學來到復旦的”。這句對譚先生履歷的描述,亦與現存傳記不符。該節文字曾以《復旦歷史系的那些名師們》為題刊登在2015年第5期《世紀》,甫一發表,金沖及先生等人立即提出糾正意見:譚其驤先生在上海解放后、1952年院系調整之前已調入復旦;《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對此有過準確記載。口述者遂于第6期《世紀》發布《關于〈復旦歷史系的那些名師們〉的補正》,承認記憶有誤。
第三,對于口述中的明顯錯誤,未能做到質疑糾誤。
第62頁口述者自述1970年代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許壽裳日記》:“在北圖,我還找到《許壽裳日記》和嚴復的一些手稿,《許壽裳日記》中有他和魯迅等人在東京聽章太炎講學的記錄。”
事實是,北京圖書館無《許壽裳日記》,口述者不可能在北圖發現這部日記。
參見姜鵬《姜義華先生發現〈許壽裳日記〉了嗎》考證,第一,許氏長子回憶,許氏自民國元年以后才開始撰寫日記。第二,許氏大部分日記在1937年燒毀。第三,現存許氏日記兩種,(1)1928年至1933年日記(缺1929年)保存在魯迅博物館。(2)1940年至1948年日記已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分別在日本(1993年)和大陸(2008年)出版,日記原稿現藏福建閩臺緣博物館。

這個推測是正確的。姜義華在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中引用了朱希祖1908年3月20日聆聽太炎演講的日記。該書240頁注1寫道:“《朱希祖日記》,北京圖書館藏,共二冊,記錄了他在日本的留學生活。第二冊系一九〇八年日記。一九七四年在一偶然的機會中發現,蒙北京圖書館慨然允許作了摘錄。這里應對北京圖書館特別表示感謝。”
查《章太炎思想研究》全書,再無感謝北京圖書館之處,亦無提及許壽裳日記之處,倒是引用過許壽裳的《章炳麟》(頁223)。可以肯定,在2015年的口述回憶中,口述者將朱希祖記成了許壽裳,而撰稿人亦沒有核對口述者的其他著述,造成明顯失誤。撰稿人不是章太炎研究專家,不了解章太炎及其弟子情況,可以理解,沒有一位歷史學家能夠掌握所有歷史細節。但是,俗話說“勤能補拙”,撰稿人既然為口述者做口述史,就應該查閱口述者的相關材料,包括口述者的主要著述,這是口述史前期的必須準備。顯然,撰稿人的案頭工作不夠充分、認真。
又如,《姜義華口述歷史》第67頁“搞一套中國文化史叢書,請周谷老擔任主編,下面有四個常務編委,北京兩個,龐樸、包遵信,上海兩個,朱維錚和我。”
這里有兩處明顯失實的錯誤。第一,中國文化史叢書只設編委會常務聯系人,不稱常務編委;第二,中國文化史叢書的編委會常務聯系人印在每本著作的扉頁,從1985年至1992年只有兩人,為龐樸和朱維錚。1994年增加出版社代表巢峰,共三人。1996年陳昕取代巢峰任出版社代表,依然三人。關于中國文化史叢書的編輯出版和編委詳情,還可參見姜鵬《〈中國文化史叢書〉出版的臺前幕后》(2016年3月1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從1985年至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出版26種中國文化史叢書,這套叢書影響很大,各大圖書館都有收藏,很多學人個人也收齊全套,只要在書架上抽出一本叢書,就可以看到正確的編委會名單,舉手之勞,不費吹灰之力。
不知為何,于編委、書、出版社都在的情況下,口述者居然大膽虛構出一個想象的編委會,虛構出一段想象的歷史。而撰稿人居然未加求證,照錄不誤,把這段虛構的歷史放到陽光下與讀者見面。可惜,朝露雖美,遇日則遁。
我們無法理解口述者的心理,可能愈回憶愈興奮,想象與真實混雜,在高亢的情緒中步入幻覺世界。采訪人事先未做好案頭準備,事中未果斷打斷幻覺式回憶,事后未做好文本整理,導致書中類似虛構不勝枚舉。
第四,與口述者本人其他作品說法不一之處,未加校對核查,結果出現記憶混亂,一事兩說。
比如前引口述者1970年代前往北京圖書館發現資料一事,口述者2015年回憶在1975年(第169頁);但口述者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則言1974年。到底哪個正確呢?口述者對自己親身經歷尚有兩說,涉及他人的回憶又有多少準確性呢?
可能有讀者提出疑議,也許口述者1974年、1975年兩赴北京圖書館,因而兩種說法都對。筆者查閱同為章太炎著作編注組成員朱維錚教授的遺稿,找到否定的佐證。口述者以章太炎著作編注組成員身份赴京查找資料,“原來說要去兩個月,后來我大概去了兩個多星期就回來了”(頁62)。為何提早回滬?原來,1974年下半年,張春橋在《文匯情況》上批示,“不要影響上海和外地的關系”,不準出滬收集資料。口述者應該在張春橋批示之后,被半途召回。此后編注組出滬申請全部被駁,口述者未能再赴北京。因而,口述者在章太炎編注組期間,只去過一次北京,至于到底是1974年還是1975年,已是一筆糊涂賬。
又如,口述者口述在《歷史研究》上以“宋斌”筆名發表《評齊赫文斯基之〈中國近代史〉》(頁59),查1975年第5期《歷史研究》,準確篇名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活標本——評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這樣一文兩名的失誤,撰稿人順手查一下期刊網就可避免。
第五,口述涉侵他人權益,或損害他人名譽時,撰稿人未對口述進行材料補充,包括在注釋中補充其他支持或否定的文獻,做到多角度反映歷史面貌,不給第三方造成無辜傷害。尊重口述者的獨立性,并不是指口述者可以借助口述話語權,獲得貶低或誹謗他人的權力。
涉侵他人權益主要指口述者對他人現有的著述版權提出質疑,意圖收為己有。
59頁“胡繩武在北京,《歷史研究》復刊,他在負責,要寫一篇文章,駁斥蘇聯在邊疆問題上的謬論。有一篇文章是用譚其驤、田汝康的名義發表的,其實是我寫的。但是,那時不能用我的名字發表,所以用了他們兩個的名字發表。”
64頁口述者談及與朱維錚教授合編《章太炎選集》,“書完成后,他(指朱維錚教授)突然提出要將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我想我剛剛平反,便說,你是學長,比我高兩年,你就署在前面吧!我這個人,人們都知道,從來不會去爭這個東西。這樣,他的名字就放在了我前面”。
75頁“‘文革’結束以后”,“以我自己的名義最初發表的三篇文章,都是關于五四運動的。”“三篇都是我寫的,《解放日報》的那篇,用的是李華興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其實那文章真的是我寫的,李華興加了幾句話吧。”
譚、田、朱、李四位教授都已故去,無法回應口述者。
譚其驤教授(1911-1992)是歷史地理領域的泰斗,長期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田汝康教授(1916-2006)是社會學、人類學、中外交流史、新文化史專家,兩位都是口述者的師長級人物,絕非素餐尸位之流。譚、田論文題為《“新土地的開發者”,還是入侵中國的強盜?》,雖為中蘇論戰而作,但其關于東北邊疆的許多學術觀點,如明代已在庫頁島、烏第河流域設立衛所、古肅慎的居住地等等,今天仍為學者廣泛引用。口述者與譚其驤教授的聯系,據自述,1962年底調回資料室后,“一度被安排到歷史地理研究室,謄抄各人所寫的‘校記’”,“譚先生所寫的校記,文字之精煉,考證之精準,抄寫中學到很多”(頁118)。史學是積累的學科,讀者很難想象,在多年深耕的領域,兩位大師需要一位年輕的資料謄抄員捉刀撰文。以他們的學問和自尊,又如何愿做小輩傀儡?如果口述者不能以本名發表論文,完全可以用筆名發表,口述者自述次年即在《歷史研究》上以筆名發文,可見用筆名發表是可行的。善意推測,口述者可能為這篇論文的寫作提供過資料,甚至提過建議,進而謄抄全文,但是“謄抄”與“寫作”有著天壤之別。
朱維錚教授在《章太炎選集》的選目、編輯、注釋、撰寫題解等方面貢獻良多,朱姜爭議之處,最后都按照朱維錚教授的意見定稿,口述者至今談及選集篇目時錯誤連連,若說選集主要由口述者編定難以服人。可參看姜鵬《〈姜義華口述歷史〉質正(下):〈章太炎選集〉的校注與署名》(《澎湃·私家歷史》2015年12月17日)。

如果口述者對三十多年前的署名不滿,可在發表文章時與署名者協商,或于署名者健在時提出修正。現在,四位教授都已去世,口述者要想確認自己才是真正作者或第一編者,必須拿出更多證據,否則任何生人都可以利用言說便利,隨意侵奪逝者的署名權。
口述中還有一處談及著述權問題,涉及其他三位已故學者,亦無任何旁證。口述者的信口開河嚴重損害了前輩學者的名譽。
49頁“周予同的《中國歷史文選》,各篇著作的那個題解提示的那些觀點,可以說全部是守老(指陳守實教授)中國史學史課堂上的東西。朱維錚做周予同的助教,在協助編歷史文選時,就把這一部分移去給周予老了,周予老原來是沒有這些理論概括的。”
這一說法如果屬實,不啻揭出一樁驚天大案。概括而言,口述者提出三項指責:1,周予同的《中國歷史文選》抄襲陳守實的觀點。2,周予同的《中國歷史文選》實際編選者為朱維錚,周予同攮奪學生成果。3,周予同學術水平較低,既無理論高度,又不了解同事的研究,更辨不出學生的抄襲。
周予同先生(1896-1981)是比譚其驤先生更年長的老一輩學者,火燒趙家樓的參與者,著名歷史學家、經學史家。1949年以后,他首次在大陸大學開設經學史課程,是中國經學史學科的奠基人。這樣一位德高望重、溫潤和藹的學者大概永遠都想不到,去世三十多年之后,竟然禍從天降,被年輕四十余歲的后生扣上一頂抄襲的黑鍋。
周予同先生到底有沒有抄襲陳守實先生?希望口述者拿出更多材料,言必有據,考而后信,而不是如潑皮小孩扔下一顆炸彈就撒腿跑開。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非專業的口述者不能編造史實,作為歷史學家的口述者更應該遵循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信手編織固然能逞一時之快,吐胸中之悶氣,卻玷污了自身形象,破壞口述史學科的正常發展。
第六,未對口述文本認真校對編輯,出現前后兩說等硬傷。
如果說口述者在本書中的敘述與其他著作不符,源于撰稿人無暇查證,那么在本書不同章節中,對同一對象的陳述各不相同,就純屬校對不精的硬傷了。
如66頁,口述者談到1979年請蔡尚思先生主編一套《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我負責的是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是李華興。第一卷后來給了朱維錚。”而170頁《姜義華教授學術活動年表》則說:“第一卷朱維錚,第二卷李華興,第三卷姜義華,第四卷姜義華,第五卷李華興。”
口述者對三十五年前做過的事情,已經記憶模糊。記憶模糊不可怕,可以翻書查一下。不愿翻書,整理成文時亦可核查。成文時沒有發現,通讀校樣也有機會統一文字,將第一種錯誤的說法改正。但是,一關又一關,關關放大水,最終呈現給讀者的是抵牾的記錄。
再如,70頁口述者言“1985年開始醞釀《中國文化史叢書》”,170頁《姜義華教授學術活動年表》則將“決定聯合籌備編輯大型學術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系于1983年之下。且不說同一書中未對“中國文化史叢書”的標點符號統一處理,這是小事。口述者曾經虛構自己是中國文化史叢書的常務編委,那么就應該記得叢書發起經過,事實卻是口述者記憶混亂,似乎對叢書不甚了了。查朱維錚教授等人的回憶,應是1983年正式對外公布了叢書計劃。

《姜義華口述歷史》口述者的整體風格可謂激情澎湃、信口開河、一瀉千里、虛實參半,很多細節不可深究,深究必誤;而撰稿人也沒有履行歷史學家的職責,以規范的整理注釋來提升全書的客觀性。結果,最終面世的文本只能算是一部粗糙的口述史料。
有學者道,競爭性口述為史家提供理解人性與歷史的豐富材料。《姜義華口述歷史》的史實錯誤太多,讀者引用需要再做核查。筆者認為,該書不具備史實史料的價值,無法為讀者和史家提供理解歷史的準確材料。但是,該書具有觀念史料的價值,如果有人想研究口述者,那么該書可以提供理解口述者思想與品性的豐富材料。
該書的實踐告訴讀者,盡管口述者和撰稿人身為知名歷史學者,但若對口述史學科缺乏敬畏之心,無視口述史現有的學術規范,把口述史當作私人工具,那么老學者也可能寫出小作品。學界應該盡快形成行業認可的口述史整理注釋規范,減少口述史作品良莠不齊的現象,推動口述史學科的健康發展。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