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孫儷新劇中被指“沒情商”?最可悲的潛規則叫“人情”
原創 壹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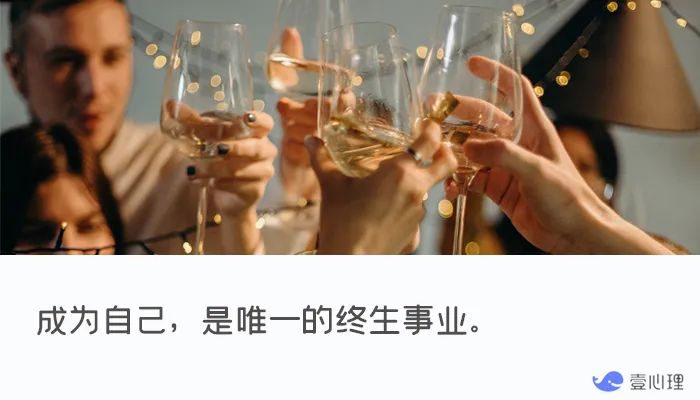
晴岸|作者
樸素的樹、如歡|編輯
anete lusina|圖源
今天,壹心理想和你聊聊:搞關系,到底要不要。
孫儷主演的電視劇《理想之城》大結局了。
開播時,其實我并不看好,以為這又是一部“畢業北漂住大平層”的職場劇,沒想到很快就被狠狠“打臉”。
在劇中,孫儷扮演的蘇筱是建筑行業的一位造價師,日夜加班的她,并沒有其他國產劇中的美顏和濾鏡,一出場就頂著黑眼圈,皮膚暗淡,非常寫實。
在劇情上,這部劇也非常貼合現代人的生活:
日常996,辛苦工作卻得不到賞識,一出問題就被推出來背鍋......
而孫儷和趙又廷狠狠吵的一架,更是把整部劇推向了高潮。
孫儷飾演的女主角蘇筱,一直牢記大學老師的教導:
“造價師的職責是保證造價表的干凈,造價表的干凈那就是工程的干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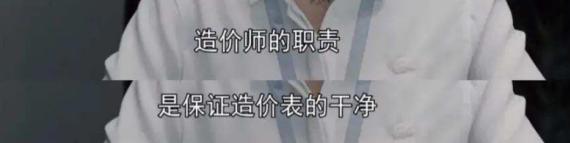
而趙又廷扮演的造價師夏明,相比之下,卻更顯圓滑。
比如,自己公司的工程出了問題,他就找到負責提供水泥的集團副總,把對方拉下水,迫使對方為自己說話,進而撇清責任。
因此,當孫儷在他面前強調造價表要干凈時,趙又廷就很不客氣地回懟:
“每一張造價表,都是一張關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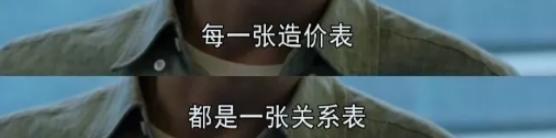
類似的爭執,貫穿了整部劇始終。
按理說,蘇筱堅守原則的做法并沒有錯,可她卻因此屢屢碰壁。
工程出了問題,她被踢出去頂缸;好不容易找到新工作,卻因為認真負責,被混日子的同事視為眼中釘。
甚至在戲外,不少觀眾也會指責蘇筱,說:這個角色太理想化、太天真,被坑是活該,應該跟著夏明好好提高一下情商。
也有人覺得:如果堅守原則就要被指責,那對她也不夠公平!
這樣的爭論,在現實生活中其實并不少見。
比如跟親戚走動少了,就被說沒人情味;前輩來了,不搶著斟茶倒水,就是沒眼色。
不少人會問:為什么不能好好做事,非要把心思花在“搞關系”上?
這背后,其實藏著中國社會最大的潛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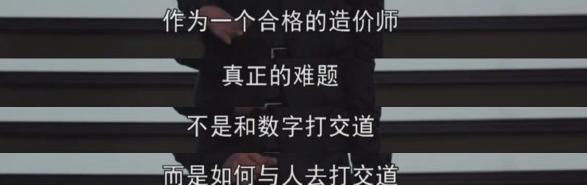

兒童化的成年人,
每一天都過得小心翼翼
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歷史學家孫隆基提出過一個概念:“成人兒童化”。
什么意思?
孫隆基解釋,在我們這個社會,規矩大于個人。
社會對人的評價,也不是看他的能力和個性,而是看他處于什么圈子,和什么人來往。
在這個文化架構之下,大家必須小心翼翼地維系著和周圍人的關系,不敢做出真實的自我表達。
就像在專制的家長面前,孩子就只能乖乖聽話。
這也被孫隆基稱為“自我壓縮的人格”。
《理想之城》中,就有不少“兒童化的成人”,他們看似已經是成人,實際上只是一個隨波逐流、用服從來換取愛的小朋友而已。
比如蘇筱的前男友周峻,他為了出人頭地,到處巴結權貴,出席各種酒會,甚至可以拋棄女朋友,和有實權的主任在一起;
蘇筱的閨蜜吳紅玫,哪怕上司一再鼓勵她有話就說,她卻硬是一個字都說不出來,生怕惹上司生氣。
有“兒童”,自然就有“家長”。
劇中的劉鐵生,就喜歡所有人圍著他,說他好話,“給他面子”。作為獎勵,他會把賺錢的項目心照不宣地留給對方。
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面子文化”。
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中說:
“中國精神的綱領就是‘面子’,只要抓住這個面子,就像揪住了阿 Q 頭上的那根小辮子,牽他往東就往東,牽他往西就往西。”
人們攀附在“人情”這張大網上,彼此交換資源。
但在《理想之城》中,蘇筱的橫空出世,把這種表面和諧摔得支離破碎。
對她來說,沒有什么面子可言,有的只有一張張干凈的造價表。
在她的推動下,原本死氣沉沉的公司,接連搶下了幾個數千萬的大單。
可即便如此,蘇筱也依然逃不過被排擠的命運。
似乎只有劉鐵生這樣的“講究人”,才能在關系網中,混得如魚得水。


攀關系講人情,
早晚都會出事
的確,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大家彼此給個面子,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更何況在熟人社會里,你不講人情,就很難生存下去。
今天你幫鄰居接下孩子,明天鄰居幫你拿個快遞;今天你幫朋友解決難題,明天朋友幫你說句好話......可以說,“人情”就是齒輪,維系著社會的平穩運轉。
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提到的,每一個家庭以自己為中心畫出一個圈子,周圍的鄰居親戚都是圈子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圈子里互幫互助。
可“人情”一旦滲入權力系統,注定會引發不可收拾的惡果。
比如震驚全國的云南孫小果案,罪犯孫小果曾多次被判刑,卻能從死刑變成有期徒刑,最后數次減刑,只在監獄里蹲了12年就出獄。
出獄之后,孫小果住著母親買下的千萬別墅,經營賭場,放高利貸,成為云南有名的黑老大。
直到中央督察組進駐云南,把該案件列為一號案件,孫小果才被判處死刑。
與此同時,19名公職人員被判刑,云南省高級法院兩任院長被處理。
最近熱播的《掃黑風暴》中的孫興,就是以此為原型。
很多人都猜測:孫家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但調查一圈下來發現,孫家最大的官員,也只不過是孫小果的繼父李橋忠,一個分局副局長。
可是李橋忠深諳人情社會的種種精髓,做事講究,很講義氣,別人也愿意幫他。
繼子出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熟人,好說話”,通過戰友、老鄉等關系,一路請客吃飯,到處找人幫忙,認識了不少云南省高院的人。
接著,他再請客送禮,說盡好話,讓對方在孫小果案上“關照一下”。
審判孫小果案的人員中,雖然有不少都收受了孫家的錢物,但相比錢財,他們更多是看在請托人的面子上,怕傷了和氣,于是答應了下來。
比如,一位牽涉其中的法官梁子安就說:“改這個案子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不對的,但面子上又抹不開。”
層層失守背后,唯一沒有為人情讓步的,只有一個監獄紀委書記,何紹平。
當時領導給何紹平打電話,要給孫小果減刑,何紹平堅決不同意減刑。
他解釋說:“(不同意)不是圖什么,是我必須要依法。”
專題片《正風反腐就在身邊》評價:“如果多一些人能夠像何紹平一樣堅持原則,孫小果也不可能‘復活’。”


時代在進步
年輕人也更勇敢
讓人覺得安慰的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蘇筱和何紹平已經不再是少數,他們逐漸成長起來,成為了社會改變的中堅力量。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沉迷于那些表面和諧,而是勇于打破平靜,去表達自己的訴求。
被公司克扣工資,他們不會“顧全大局”,而是勇敢用法律途徑維權;
被上級性騷擾,她們也不會忍氣吞聲,更不怕傷了和氣,而是一定要讓壞人繩之以法。
知乎上也有不少類似的提問:
“為什么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不合群?”
“為什么年輕人敢手撕領導?”
提問者似乎非常不能理解,為什么現在的年輕人這么剛?
遵從潛規則當然很容易,畢竟和周圍人做著一樣的事情,你不會覺得自己過于突兀,心里也會有很大的安全感。
這就是《烏合之眾》里面所解釋的:
當人們感到不安時,就會傾向于加入一個穩定的群體,讓自己成為整體的一部分,以此對抗外界的危險。
這也是為什么,那么多人一邊痛罵潛規則,一邊陪著笑容討好別人,因為離開了這個體系,他們就會覺得自己無處容身。
但就像那句話說的:大人,時代變了。
現代社會已經進入“原子化”階段,大量年輕人涌入一二線城市,在同樣陌生的環境里,誰也不認識誰,過去那種搞關系、講人情的土壤,已然開始撕裂。
更何況,他們深知,迎合與融入,并不是變得成熟,而是某種意義上的“自毀”。

心理學上有一個“心體一致”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人要達到內心的和諧,自己的行為必須要和自己的價值觀一致,否則就會產生“失調”。
而這,是幾乎一切心理問題的根源成因。
心理學家弗洛姆就在《自我的追尋》中強調,生命有其自己的內在動力,它會按照自己的節奏發展下去。
如果生命的發展受阻,沒辦法表達自己的感覺、思想和情感,那么生命的能量就會分解,進而轉化成破壞能,產生強大內耗。
《人物》曾報道過一個從卷煙廠辭職的員工王通,他離職之前早8晚4,一年到手25萬,工作就是按按按鈕,沒什么技術含量。
這份“入職即躺平”的工作,讓無數名校研究生趨之若鶩。
但對王通來說,他所感受到的,只有窒息、掙扎和煎熬。
工作內容簡單枯燥,管理模式一成不變,在里面耗費了11年青春,他總是在想,還要繼續下去嗎?
33歲這年,他想到自己已經買房買車,孩子也上了幼兒園,終于決定辭職,為自己活一次。
王通的父親氣得幾天吃不下飯,同事也炸了鍋,只有他自己覺得心滿意足,因為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能讓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顆沒有想法的螺絲釘。
坦白講,看了這篇報道,我很感動。
有志氣的年輕人,早已不甘心為了虛無的安全感而自我拉扯,而是要追隨內心,做著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站了起來,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心聲,做出了屬于自己的選擇。
他們也許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漸漸明白自己不要什么。
哪怕他們的觀點還不夠成熟,但起碼他們能夠正視自己的訴求。
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地離心之所向近一點,再近一點。
借用弗洛姆的話來說:
“每個人的終生事業只有一個:成為他自己。”
試著成為你自己吧,用自己特有的理性和愛意,去獲取幸福。
慢慢地,你會感受到,這才是活著的滋味。
2021年了,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去塑造新的話語權。
點個在看,構建屬于自己的“理想之城”。
世界和我愛著你。
參考文獻: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弗洛姆《自我的追尋》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重新認識你自己》
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
- The End -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