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亨利·詹姆斯逝世百年∣禮儀斯文背后的保守唯美分子

1916年2月28日,亨利·詹姆斯(1843-1916)在倫敦切爾西區的家中逝世,此時他已是英國知識界公認的文學泰斗,無論他的支持者還是批評者都無法否認“詹姆斯式風格”(Jamesian)的獨特魅力。
如果說一個作家或思想家的名字衍生出的形容詞,足以證明其別具一格之處的話,當年一些英國文人給詹姆斯取的雅號,雖不乏戲謔之意,仍從側面顯示出這位大作家的地位和影響力。根據詹姆斯的創作階段、內容和手法的變化,他們分別稱他為“詹姆斯一世”(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第一代國王,欽定《圣經》的英譯本)、“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和“老僭王”(the Old Pretender,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的一些擁簇甚至還自稱Jacobeans(通常指詹姆斯一世時代的人物)。
文跨兩洲,聲名遠播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1917年10月18日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發表的書評中,曾這樣描述詹姆斯的創作特點:“在呈現往昔時,亨利·詹姆斯最為游刃有余。柔和的光線在過往中穿梭游動,連彼時最普通不過的渺小人物也浸潤著無盡美妙。白日的強光所壓抑的諸多事物的細節,在婆娑的光影中得以搖曳生姿。那份深沉, 那份濃郁,那份靜謐,整出人生盛會的那份幽默自如——所有這些,似乎都是他筆下自然的氣韻和最恒久的意境,他那些以老邁的歐洲映襯年輕的美國的故事,洋溢著這種氛圍。在明暗交錯中,他以深遠的目光洞察一切。”伍爾夫接著寫道:“的確,要感謝美國作家,尤其亨利·詹姆斯和霍桑,給我們的文學帶來對過去最美好的回味——不是說遠古的浪漫傳奇和騎士精神,而是在不久的往日中消逝的尊嚴和褪色的風尚。”
伍爾夫的評論不只捕捉到詹姆斯微妙細膩又深邃雋永的筆觸,而且點明了詹姆斯特有的跨文化視角和犀利的審美眼光。她提到的詹姆斯的“美國”身份,與其說是一種國籍歸屬,不如說是一種寬廣的文化維度。詹姆斯在1888年10月28日給兄長威廉·詹姆斯的信中曾寫道:“我無法審視英國和美國的社會生活,或者對它們深有感悟,除非將兩者視為注定融匯在一起的盎格魯-撒克遜統一體,這種融合很大程度上勢必發生,以至于執拗于兩國的區別變得越來越乏味又迂腐;而且越是將兩個國家的生活作為連續不斷,或多少可相互轉換,或哪怕只是同一個宏觀對象的不同章節來對待,兩者越是緊密交融。文學,尤其是小說,為這種必然性提供了一個了不起的手段,善加運用可有上乘佳作。”詹姆斯在這里不僅強調了英美兩國深層次的歷史文化關聯,也暗示了文學所承載的超越國家和地域限制的意義和價值。他坦承,“我期望我的創作方式在外人看來,已無法分清我在某一刻是個描寫英國的美國人,還是個描寫美國的英國人(就我對兩個國家的刻畫而言),這種模棱兩可的特質非但不讓我自慚,還讓我極為自豪,因為它意味著高度的文明修養。”詹姆斯推崇的“文明修養”,顯然包涵了不為自我和民族國家身份所局限的洞察世界的能力。
的確,詹姆斯常自稱是“世界化的美國人”(“cosmopolitanized American”)。這位出生在美國上層知識分子家庭的作家和自幼敏感的心靈,一方面深諳新英格蘭的思想和道德傳統,以及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一方面很早就著迷于歐洲的文化氛圍和社會風貌。詹姆斯不僅熟悉當時美國社交生活中滲透的歐洲文化影響,而且早年隨父親和家人在歐洲廣泛游歷和旅居,在法國、意大利、瑞士、英國等地接受豐富的審美熏陶并結識文化和思想界名流,并在三十三歲時選擇定居在英國(雖然他直到1915年7月因不滿美國拒絕加盟英法聯軍才加入英國籍)。詹姆斯很快融入了倫敦的社交圈,并和維多利亞時代的眾多文化巨匠都有來往和思想交流,包括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羅伯特·布朗寧、馬修·阿諾德、托馬斯·卡萊爾、喬治·艾略特、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赫伯特·斯賓塞和安東尼·特羅洛普等等。
此外,詹姆斯和長他十來歲的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就是伍爾夫的父親,也交誼甚篤。詹姆斯著名的中篇故事《戴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最早即發表在斯蒂芬時任主編的文學雜志《谷山》(The Cornhill Magazine)上(詹姆斯同時也是雜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英國旋即獲得了巨大反響,也讓詹姆斯在中產階級讀者中一舉成名。伍爾夫的丈夫倫納德在自傳中曾詳述詹姆斯對斯蒂芬一家人的愛慕之情。1912年,兩人在一次文化活動上偶遇,當詹姆斯得知倫納德不久前剛剛娶了弗吉尼亞時,立即再次主動和倫納德握手,還講了一大通客套話,句句“錯綜盤繞,文辭華麗,還夾雜著大量插入語”,但對斯蒂芬一家“情真意切”。倫納德還生動地描述了他從斯蒂芬的子女那里聽來的關于詹姆斯的趣聞,說他們小的時候,詹姆斯常來家中做客。他有一個怪癖,就是喜歡一邊講話,一邊坐在椅子里往后仰。隨著那些長長的句子一點點舒展開來,詹姆斯的椅子也慢慢后傾,這時所有孩子都瞪大了眼睛看著那把椅子,既擔心又盼望著它失去平衡,把詹姆斯掀翻在地,可是詹姆斯幾乎總能化險為夷。有一次,危機終于發生了,椅子傾倒,小說家摔在地上,但毫發無傷,不以為意,又繼續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長句子講完。
二十世紀初,詹姆斯的聲望已是如日中天。雖然他晚期的幾部重要小說,包括《圣泉》(1901)、《鴿翼》(1902)、《大使》(1903)和《金碗》(1904)的行文越來越迂回曲折和艱澀晦暗,并包涵了大量抽象深奧的哲學思考,以致大眾讀者少有問津,但詹姆斯憑著這些作品已穩穩躋身于十九世紀小說名家所代表的英國文學傳統,他對小說作為一門藝術的深刻洞見和他的卓越藝術成就,也深深影響并啟發著年輕一代精英對文學的理解判斷和創作實踐。小說批評史上兩部早期的重要著作,珀西·盧伯克(Percy Lubbock)的《小說的技藝》(The Craft of Fiction,1921)和E.M.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1927),盡管論述側重不同,觀點也有所分歧,但兩者都對詹姆斯的小說作出周詳細致的分析,并突出了他的創作對這一藝術樣式發展的重要貢獻。現代學院式文學和文化批評的奠基人之一利維斯(F.R.Leavis)在其名著《偉大的傳統》(1948)中,將詹姆斯與簡·奧斯丁、喬治·艾略特和約瑟夫·康拉德一道,稱為英國小說傳統中最優秀的代表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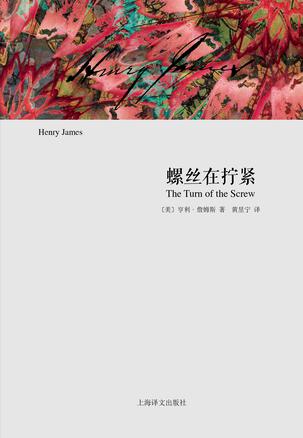
英美現代主義作家在致力于對文學形式的創新和突破中,其實也不斷從文學傳統中汲取智慧的養分。詹姆斯就是總能激發創作靈感的作家之一,比如同樣出生于美國后來移居英國的現代主義詩人T.S.艾略特,還有美國著名現代主義詩人龐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都曾借鑒詹姆斯的名作《一位女士的畫像》(1881),創作過同名和主旨相關的詩篇。一個世紀以來,雖然詹姆斯和他的世界顯得越來越古色古香,而且對每一代讀者的意義也不盡相同,但他從未離開過當代作家的視野,甚至被直接當作創作題材。戴維·洛奇曾將2004年稱為“亨利·詹姆斯之年”,因為當年不僅有兩本關于詹姆斯的傳記體小說問世——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的《大師》、洛奇本人的作品《作者,作者》——兼之當年英國的布克獎得主、阿蘭·霍林赫斯特的《美麗線條》,無論從內容(比如小說描繪的英國上層社會生活和道德危機,以及主人公正在努力完成一篇關于詹姆斯的論文等等),還是風格上,都顯示出詹姆斯為文學創作提供的寶貴而持久的藝術和精神資源。

戴維·洛奇的《作者,作者》
妙盡幽微,所述縱橫
當然,詹姆斯小說的諸多特性,也引發過不少爭議和批評。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就曾指出,詹姆斯的小說形式雖美妙精致,但它們所呈現的世界卻顯得狹隘逼仄,它們關上了“生活的大門,把小說家留在上流社會的客廳中忙個不停”。福斯特尤其尖銳地批評了詹姆斯塑造的人物的種種局限:“首先,他只有一個很短的人物清單——一個試圖影響情節發展的旁觀者;一個二流的局外人;然后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陪襯角色,非常活潑而且通常是女性;還有出色罕見的女主角,《鴿翼》中的米莉是這一類型的完美代表;有時會有一個反面人物,有時還有一個性情慷慨的年輕藝術家,大抵也就這么多了。”福斯特認為詹姆斯的人物“不僅數量太少,而且束縛太多。他們無法享樂,或快速行動,或行魚水之歡,英勇行為十有八九與他們無關。他們總是衣冠楚楚;折磨他們的病痛,和他們的收入來源一樣,從來不明不白。他們的仆人不聲不響,或者和他們別無兩樣。從社會的角度解釋我們所了解的這個世界,他們全不可能做到,因為在他們的世界里沒有蠢人,沒有語言障礙,也沒有窮人。連他們的感知力都很有限,他們可以登陸歐洲觀賞藝術品,或者彼此相互打量,但僅此而已”。
福斯特的批評不只針對詹姆斯小說看似與社會現實的脫節,也指向他的作品所表現的階級褊狹。“上流社會的客廳”無疑是詹姆斯小說標志性的場景,雖然他的人物有不少為了不失體面地滿足某種物質財富欲求而煞費心機,但很少有人忙于為生計奔波。階級分化和激烈緊張的社會沖突,貧窮困苦和雞毛蒜皮的市井生活,粗野鄙俗和殘酷乖張的暴戾之氣等等,在他的故事中更是極為少見。福斯特的論斷,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文學界對詹姆斯的嚴苛指責有相通之處。包括美國文學史名家沃農·帕靈頓(Vernon Parrington)和美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范·維克·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在內的不少學者,就曾批評詹姆斯的作品只注重形式審美,不在乎內容題材。在他們看來,詹姆斯筆下的人物充滿斧鑿的痕跡,他的小說也與現實世界相去甚遠。這些負面評價當然與美國文學本土意識日漸增強有關,畢竟,詹姆斯年紀輕輕就遠走他鄉,并二十余年不曾返回故土,他的創作主題和內容與美國社會的現實狀況往往毫不相干,再加上詹姆斯本人也毫不客氣地批評美國文明缺乏深厚的傳統底蘊和文化積淀。當然,這些評論確實指出了詹姆斯優雅華麗的藝術世界與雜亂不公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張力,詹姆斯因此被不少學者視為保守的唯美分子。在英美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以階級、性別和族裔等身份政治批評,以及意識形態文化批評為主導的領域,審美價值和經典精英白人男作家持續地受到質疑,詹姆斯也難免成為典型批評對象之一。倒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酷兒理論興起之后,一些學者開始探討詹姆斯看似不同尋常的性取向和他的藝術創作之間的復雜關系,雖然這一研究方法無法避免程式化的先入之見,但還是抵消了不少身份政治批評中對詹姆斯的濃厚敵意。
但是,在詹姆斯創作的包括小說、短篇故事、游記、傳記和文學評論在內的皇皇近百部作品中,只看到其中精雕細琢之美,而不談詹姆斯對審美與思維想象、道德意識及社會風尚之間的關系,現代性條件下社會倫理生活的特征,以及文明社會的本質和理想形式等諸多重要主題的探討,顯然失之粗淺和偏頗。事實上,美國知名文化學者和文學批評家萊昂內爾·特里林早在其重要著作《自由的想象》(1950)中,就深入分析了詹姆斯作品中一部較少被關注,但社會和政治內涵又頗豐富的長篇小說《卡薩瑪茜瑪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1886)。小說不僅生動地呈現出十九世紀歐洲社會貧富差異和階級矛盾加劇的背景下,歐洲政治極端主義對公共生活和個人選擇的影響,而且對審美感知力所強化的道德責任心,個體尊嚴感和對文明雅致的索求之間可能出現的種種矛盾,有著極為深刻的洞察。特里林敏銳地指出,“小說的核心假定是歐洲文明已經步入頂峰,正在滑向腐朽,它所發出的特別美麗的光芒,部分是輝煌往昔的反射,部分是衰頹今日的磷光,它也許難逃暴力的終結,這也不能說完全是命運的捉弄,盡管這片古老而罪孽深重的大陸從沒像現在這樣讓我們深感其榮耀和可憐。”不能不承認,詹姆斯在十九世紀末對歐洲文明所面臨的災難的想象,頗有先見之明。
在特里林看來,詹姆斯的小說可以用一種“道德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來描述,這種現實主義更著重于觀照現代生活的道德境況,但它反映的“不是對于道德原則本身的熟知,而是對于道德生活中的矛盾、悖論和危險的覺察”。特里林對于詹姆斯作品道德意涵的強調,為詹姆斯研究開啟了更廣闊的研究空間。隨著詹姆斯研究在美國文學批評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強,美國學者對詹姆斯的討論也更加深刻透徹。越來越多的評家開始探究詹姆斯筆下精微豐富的個體意識、心理和欲念,以及它們與社會生活中的秩序、自由以及倫理結構之間的關系,比如勞倫斯·霍蘭德(Laurence Holland)的《理念的代價》(The Expense of Vision,1964)和莎倫·卡梅倫(Sharon Cameron)的《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思維》(Thinking in Henry James,1989)就是這一研究路徑的代表專著。兩位學者對文本的解讀都極為獨到精彩,在哲理層面的思考也非常嚴謹縝密。
對詹姆斯作品中豐富的哲學內涵進行系統闡述的著作,包括保羅·阿姆斯特朗(Paul Armstrong)的《亨利·詹姆斯的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Henry James,1983)和羅斯·波斯納克(Ross Posnock)的《好奇心的折磨:亨利·詹姆斯、威廉·詹姆斯和現代性的挑戰》(The Trial of Curiosity: Henry James, William James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1991)。前者力圖說明詹姆斯對意識和認知的理解與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和薩特等哲學家的現象學理論的相通之處,后者則以詹姆斯的兄長對實用主義哲學的研究為切入點,將詹姆斯的思想置于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和智識傳統中,同時融入韋伯、齊美爾、本雅明和阿多諾等人關于現代性的理論和文化批評展開跨學科的討論和分析,進一步拓寬了詹姆斯和美國文化思想史研究的視野。
另外一部頗有影響力的著作,是芝加哥大學黑格爾哲學研究專家羅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的《亨利·詹姆斯和現代道德生活》(Henry James and Modern Moral Life,2001)。皮平認為,詹姆斯深知現代生活中,包括欺騙、背叛、忠誠、奉獻、寬恕、善良等道德范疇既可能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反映社會地位和權力的要求和利益,也可能只是心理層面的作用機制,反映相關主體的需要、欲求,乃至焦慮,但詹姆斯并未放棄對道德價值的尋求。在詹姆斯的作品中,這種價值既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實踐、基本機制和原則共識,也有賴于主體在追求自我欲求的圓滿實現中,將他人作為自由并同樣獨立追求自我滿足的主體來對待。
近年來,學者逐步修正了詹姆斯缺乏歷史意識,對社會、政治和物質現實不聞不問的成見。戴維·麥克沃特(David McWhirter)主編的文集《歷史語境中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in Context,2010)全面細致地闡明了詹姆斯對他所處時代的物質、文化和思想觀念變遷的深刻反思和藝術再現,詹姆斯靈慧好奇的頭腦對外界發生的各種變化始終保持敏銳的反應,外界的影響也啟發并催化著他的創作思路和藝術理念。此外,從文集對當前全球詹姆斯研究的詳細梳理中,也可看到對詹姆斯愈益豐富多樣的研究角度和有增無減的研究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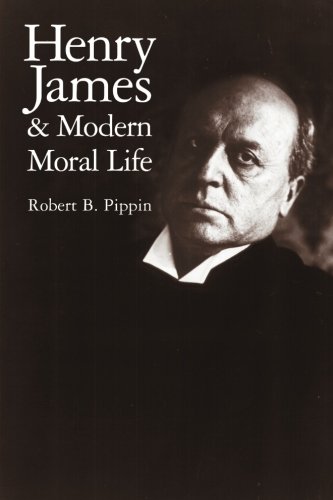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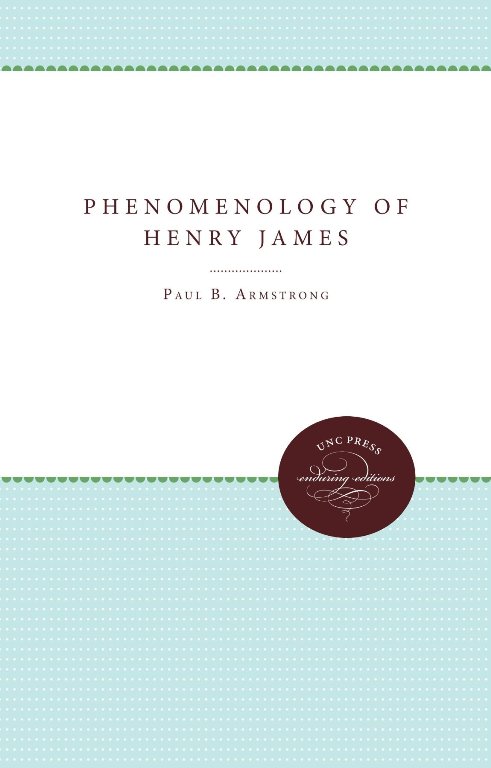

禮儀斯文,道德想象
不可否認,詹姆斯的小說從眾多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特質,是其中的禮儀斯文所交織的審美意蘊和道德內涵形成的復雜式樣。正如利維斯所指出的,詹姆斯“感興趣的禮儀舉止是精神和智識雅趣的外在符號標記,或至少可以這么來看待。本質上,他在追尋一個理想的社會,一種理想的文明”。詹姆斯最受評家稱贊的小說之一《一位女士的畫像》將這一特征展現得尤為淋漓盡致。

不久,伊莎貝爾在杜歇家遇到梅爾夫人,這位出生在美國但已久居歐洲的女士,言談舉止優雅得體,伊莎貝爾被她的教養和識見深深吸引。同時,伊莎貝爾的姨父老杜歇先生臨終前,經兒子拉爾夫的勸說,在遺囑中留下七萬英鎊遺產給她。伊莎貝爾雖然考慮到富足可以讓她去有所“作為”,而“作為”要比消極自由更“甜美”,但她對此饋贈始終心有不安。之后,伊莎貝爾在佛羅倫薩認識了梅爾夫人的朋友吉爾伯特·奧斯蒙德,一個中年鰥夫,有一個漂亮乖巧的女兒,名叫潘茜。奧斯蒙德也出生在美國,在意大利已定居多年,他并不富有,也安于平淡,但卻沉醉于藝術的世界。伊莎貝爾不僅被他清雅敏感的儀表和氣質所吸引,也著迷于他對藝術的審美品位,其實兩者在她眼中已渾然一體。伊莎貝爾接受了奧斯蒙德的求婚,并憧憬著她們可以一起同享高尚生活,對她而言,這種生活“意味著充分相知和充分自由的結合,相知給人責任感,而自由使人幸福”。
然而,伊莎貝爾婚后終于發現自己識人不深,錯看了奧斯蒙德的品性。對他來說,高尚的生活,“完全是何種形式的問題,是一種蓄意謀劃的態度”。奧斯蒙德的自以為是和獨斷專行,絲毫沒有因他的藝術品位有所改變。他認為伊莎貝爾沒有文化和歷史傳統,她的獨立見解讓他討厭;他覺得伊莎貝爾應該完全遵從他的看法、追求和喜好。小說的下半部在詳細展現他們婚姻破裂的同時,也引入另一條相關的敘事線索。伊莎貝爾和奧斯蒙德在潘茜的婚事上又出現了嚴重分歧。潘茜的兩個追求者都是伊莎貝爾的舊友,一個正是沃伯頓勛爵,另一個是她兒時的朋友羅西爾,旅居巴黎,財富地位和沃伯頓勛爵都不可同日而語。奧斯蒙德很快原形畢露,他很清楚沃伯頓曾追求過伊莎貝爾,但他毫不考慮她的想法,要求伊莎貝爾利用沃伯頓對她的感情,幫助促成沃伯頓和潘茜的婚姻。奧斯蒙德的謀劃(最終伊莎貝爾得知,自己和奧斯蒙德的婚姻也是他昔日的情人梅爾夫人謀劃、奧斯蒙德參與的一個圈套,而潘茜是兩人的私生女),提醒伊莎貝爾必須確定沃伯頓追求潘茜的動機。她意識到自己所處的道德困境:從潘茜的婚姻考慮,她的確認為沃伯頓是更好的伴侶,可如果沃伯頓追求潘茜的動機是他對自己仍有的愛慕,那出于對潘茜的愛和責任以及出于自己對婚姻許諾的忠誠,她都無法接受。
在一次舞會上,沃伯頓不經意間提到潘茜似乎總在伊莎貝爾身邊,稍作遲疑后又補充說,其實所有人都希望接近她。片刻間,伊莎貝爾似乎了解到沃伯頓的真實意圖。隨后,沃伯頓提起從前在英國的美好時光,有一瞬間,兩人互相凝視著對方,伊莎貝爾覺察到他表情中閃過一絲疑慮,而沃伯頓也從她的眼神中感到些許不安。這一刻短暫的對視,將不能用言語道破的微妙心思精巧地呈現出來:伊莎貝爾明白了沃伯頓打算娶潘茜乃是為了在她身邊,沃伯頓則領會到這會讓伊莎貝爾無可忍受。更重要的是,伊莎貝爾對過往的緘默,無論其中包含多少無奈、痛苦和掙扎,也是斬斷沃伯頓舊日情愫最堅決的方式。如此纖毫畢現于筆端,詹姆斯高超的心理描寫譽不虛出。而在百感交集的對視中凝結的那份斯多葛式的冷靜和克制,也可以說是詹姆斯式禮儀斯文最好的詮釋。
伊莎貝爾是詹姆斯作品中最具理想主義,也是最具想象力的人物之一。她的道德意識與審美敏感密不可分,比如她繼承的那筆財富,始終讓她感覺是一種道義的負擔,因為在她看來,“繼承七萬英鎊不是什么非常美妙的事;美妙之處在于杜歇先生給她的饋贈本身。不過嫁給吉爾伯特·奧斯蒙德,并把這筆饋贈帶給他,這也許有些屬于她的美妙之處”。伊莎貝爾認為奧斯蒙德對藝術的專注,意味著“他對自己這筆財富的使用,會讓她對財富的看法有所改變,也可以抹掉意外之財這樣的好運所附帶的某種粗俗”。伊莎貝爾在這里對“美妙”和“粗俗”的強調,以及對慷慨和公道的理解,再次混淆了美學和道德范疇。伊莎貝爾豐富的想象力,也常常糅合了凄美的畫面和溫暖的情感。在她對奧斯蒙德的幻念中,除了他的文雅表象,她也感到他的“無助和無能,但是這種感覺是一種柔情,它是敬意中最精華的成分”。伊莎貝爾仿佛看到奧斯蒙德是個“充滿疑慮的遠行者,在海灘徘徊等待起航,他朝海的那一邊望去,卻還沒有駛向大海”。她會“為他的船放下水”去起航,愛他會是“一件美好的事”。雖然伊莎貝爾的道德想象給她帶來巨大的痛苦,在詹姆斯后期的作品中,道德想象也從起初的瑰麗絢爛慢慢變得黯淡失色,但無論如何,這一想象中始終殘存一份美的期許和愛的力量,這也許是進入詹姆斯美妙而博大世界的一把鑰匙。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