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吳謝宇,曾活在令人窒息的愛里
令人窒息的愛 原創(chuàng) 維舟 維舟
吳謝宇弒母案日前已正式宣判。雖然他的辯護律師馮敏表示吳對一審判決不服,已提起上訴,但除非有重大新證據(jù)出現(xiàn),案情取得新進展,否則改判的可能性恐怕很小。
像他這樣的罪行,在中國社會是很難取得同情的。在他上訴的新聞底下,最高贊的評論是:“居然還有臉上訴!”在我們的傳統(tǒng)法律觀念中,子女弒父弒母是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但父母殺子女的倒是很容易從輕發(fā)落,因為儒家社會秩序的根本就奠基于子女順從父母的“孝”。
毫無疑問,吳謝宇肯定犯下了大罪(那畢竟是殺人,即便弒母并不加重,也不能因此就寬赦),但將他論罪處死很容易,難的是如何從這一悲劇中汲取教訓。因為悲劇根源的那種病態(tài)親子關系,其實廣泛存在于中國社會,如果不能清楚認識,恐怕類似的極端事件還有可能重演。

學生時代的吳謝宇
一個原本前途光明的天才,為什么要弒母?這我曾分析過,簡言之,在這樣過度密切的母子關系中,只能活一個。
各方面的信息都證實,其母謝天琴是一個控制欲極強的母親。吳謝宇小升初本來可以上本地最好的福州一中,但他媽為了把他留在身邊,只讓他去了普通中學。在得知丈夫出軌后,謝天琴直至他病死也沒再去看他一眼,轉而把生活的全部重心都放在兒子身上。
無疑,兒子考上北大,極大地寬慰了這個望子成龍的母親,但即便到了北京,吳謝宇也仍然無法擺脫媽媽的陰影,他被要求每天打電話向媽媽匯報。當他意欲出國留學時,謝天琴起初不許,也不許他向親友籌款,隨之表示也要去美國陪讀,由此可見這對母子共生和控制的強度。
這位母親決意不惜犧牲自己的全部事業(yè)與人生,為孩子付出一切,這已經(jīng)傳達出一個清晰的信號:母子一體,我們將緊緊捆綁在一起,不分彼此。然而她沒有意識到的是,對于一個日漸長大獨立的個體來說,這種吞噬一切的母性已構成最大的威脅。

很多人都懷疑,這對母子關系可能有某種“亂倫傾向”,這不無道理。這倒未必是他們有何不正當關系,而是如榮格在《英雄與母親》中所言,“亂倫欲望的根本并非只是性的交合”,而是“一種重返童年,回到雙親的庇護之下,進入母體重獲新生的奇思異想”。換言之,這是向母體的退行,被一種強大的欲望所驅使,那就是“對過去的一切都不情愿放手,總想永遠緊緊地抓住它們”。
然而,一個人的獨立自主和意識發(fā)展,卻必然意味著要與母親分離,此時人們常常懷有兩種矛盾的欲求:既要走出去,獲得屬于自己的人生,在面對艱難適應時又難免渴望退回母親的懷抱。如果這位母親自己就不肯放手,那就只有依靠個人頑強的意志努力,才能擺脫其糾纏,實現(xiàn)自立。母性既是生命的起源、始終包容的原鄉(xiāng),在另一面卻又代表著最可怕的危險,那是“恐怖的母性”。
正因此,在許多神話里,英雄都是通過對母體的分離,甚至是用戰(zhàn)勝母親來表現(xiàn)對本能的征服,由此克服亂倫禁忌帶來的恐懼,最終才擺脫與無意識渾然一體的朦朧狀態(tài),真正開始擁有自我意識的。
榮格曾治療過一位母親,“她用變態(tài)的愛和奉獻把子女們始終與自己捆綁在一起”,結果在更年期后陷入抑郁型精神病之中,“在其精神病狀態(tài)下,她使自己變成了吞噬一切的恐怖母親的象征”。
他對此的解釋是:“真正的母親也可以用病態(tài)的柔情迫使子女進入成年生活,因而延長其幼稚期并超出恰當?shù)臅r期,這樣就會給子女造成嚴重傷害。與其說被妖魔化的是真正的母親,不如說是無意識中的母親意象。”
不過,榮格也明確指出,在這樣的病態(tài)關系中,兒子未必能意識到自己身上的亂倫傾向,母親對兒子不肯放手也未必都是母親的責任,因為成長的個體應當少將自己的無能推諉于父母,堅決抵制對“回歸母親懷抱”的誘惑,戒斷孩童式的依戀。不僅如此,他認為,真正的問題并非“我怎么才能擺脫我的陰影”,而是必須自問:“人如何能夠與他的陰影共存,而不會遭受它促發(fā)的一連串災難?”

吳謝宇的家,也是弒母案的現(xiàn)場
這些都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案件中的當事人母子幽暗的心態(tài),也可以解釋為何吳謝宇完全可以預見弒母的后果,還是非做不可——這說明,即便付出那么大的代價(不僅是母親的生命,他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也毀了),他仍然覺得值得,因為他在這令人窒息的母愛之下太久,哪怕?lián)Q取自己短時間的快感和自由也甘愿。弒母其實是為了分離。
對吳謝宇來說,去北大上學原本可以跨出與母體分離的第一步,但媽媽仍要他“早請示,晚匯報”;甚至他想出國的最大動因可能也是為了擺脫媽媽,然而也失敗了。當然,他也可以先哄著母親,最后再亮底牌,自己孤身去留學,其母就算抓狂要追出國,也不可能長留,畢竟有簽證的問題,但由此引發(fā)的后果,或許又是他畏懼的。到最后,他很可能發(fā)現(xiàn),要擺脫母親,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她去死。
在庭審時,吳謝宇辯解說,他之所以弒母,是因為察覺到父親死后,母親長期郁郁寡歡,有輕生的念頭,于是決定“幫助”母親去死,因為他想起自己在某本小說上看到的話:“愛你愛到極致的時候,你不敢做的事情,你不能做的事情,我替你解決,我什么事都給你解決。”
這話無從證實也無法證偽,但這很可能是一種心理上的逆向投射,也就是把“希望媽媽去死”,說成是“媽媽自己想死”,以此減輕自己的內疚感,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弗洛伊德早就說過:“神經(jīng)癥患者身上那種自殺沖動,通常被證明是對希望他人死去的愿望的自我懲罰。”換言之,許多人自殺,其實內心是希望他人死去,潛臺詞是“等我死了,看你怎么辦”。

吳謝宇在庭審中解釋為何選擇7月10日作案
就此而言,這一病態(tài)的親子關系原本未必走向弒母這一結局,它至少有三種可能的走向:
孩子徹底屈從于母親的意志——嚴重者自殺,但都意味著個體死亡;
矛盾公開爆發(fā),家里長期爭吵,孩子決裂分家;
隱忍不發(fā),最終突然爆發(fā),弒母。
在此,自殺是向內攻擊,而弒母是向外攻擊,結果都是“只能活一個”。如果他不是男孩,或許也不會爆發(fā)得這么厲害,但如果個性懦弱,那結果就很可能是孩子的個體靈魂完全被母親所占據(jù)。
如果母親潛意識里總覺得自己和孩子是一體的,但兒子卻想要分割開來,那最后的弒母就像是一次“暴力分娩”,兒子通過殺死母親,第二次從母體中“把自己生出來”。
當然,還有一種更好的可能,那就是經(jīng)歷矛盾公開化之后,母親逐步接受孩子獨立、分離的事實,放手讓他們自己去過活,而孩子也理解、接受媽媽的苦處,兩代人在適當距離下和解。然而,在這對母子中間,這種可能性看來微乎其微。

為什么吳謝宇不能和媽媽坦誠交流,化解矛盾?這我們外人無從得知,但很有可能的一點是:他試圖交流過,卻發(fā)現(xiàn)媽媽根本無法接受自己真實的一面,拒絕進行任何溝通。
認識吳謝宇的人都說他很“完美”,甚至被稱為“宇神”,但很少人意識到,這既未必是他自己真正想要的,也造成了他內心極大的壓抑。可想而知,謝天琴不允許兒子任何一點偏離自己為他設定的完美形象,這在他成年后造成了一種高壓鍋式的狀態(tài)——他的“完美”本身就是巨大的壓力。如果你一直很完美,要主動暴露自己不完美的部分比掩蓋它更難,因為稍稍偏離這樣的完美人設,都是媽媽、周圍人乃至他自己所難以接受的。
有時,過于完美主義也意味著缺乏面對真實的能力。對這樣的人來說,那種一點點的裂痕,反而更難接受。他對他媽媽最后選擇這么極端的手段,就好像一個“完美”的幻象,不能接受有點破損的痕跡,所以最后直接用暴力打個粉碎。
他在弒母后走了一條放縱享樂的人生道路,很難說媽媽在他心目中是沒有壓迫感的存在,是“開明”的家長。相反,在這個家庭里,媽媽就像是上帝,“上帝死了”之后,任何事都被允許了,對吳謝宇來說也一樣,“媽媽一死,什么都可以做了”。這恐怕就是他為什么在弒母后舍不得去死,反而肆意放縱自己的欲望,做的都是其母生前絕對不會允許的事。
吳謝宇之所以有嚴重的性癮,也極有可能是此前過度壓抑的結果。謝天琴為人刻板、自制、極為禁欲,有強烈的潔癖,丈夫生病時住院的所有東西都不能帶回家,親友也因此很少能去她家做客。吳父出軌,說不定也是一種受不了這種家庭氣氛的逃離之舉,但到頭來,卻使謝天琴更謹防兒子變得跟父親一樣,向他灌輸了“欲望是可恥的”這類信念,嚴重壓抑了他青春期的正常欲望。

吳謝宇原本是自制力極強的人(別的不說,維持一個完美人設就需要強大的自制力),但卻無法壓制性癮,因為那正是過分自制的結果。這是一個無法袒露、只能壓制的秘密,但越壓制問題越大。可想而知,他在青春期也沒辦法正常戀愛,弒母出走之后,找的也不是“正常”女性,而是性工作者。
看起來,他可能沒想過自己有朝一日能擁有一個正常和諧家庭的希望——他事業(yè)上有成功的可能,但自己可能幾乎看不到幸福的可能。那正可以說明,他母親的影響使他無法和別的女性建立起正常關系。
但凡他有一點發(fā)泄的口子,可能都不至于壓抑到產生如此嚴重的性癮。有一點很奇怪,就是他好像沒有情感的出口,也沒什么辦法消化、紓解這些壓力,除了那時手淫。如果更早之前他有個人可以商量下、傾吐下,或許也能好一點。如果他此前能對自己喜歡的女孩子坦白這樣見不得人的隱私,并獲得接納,恐怕最終也都不至于走到弒母這一步。
在他沒落網(wǎng)之前,大家對他未來人生軌跡的普遍預測都還是往著“成功的精英”方向去設想的,覺得他會換一個身份在國外繼續(xù)遵循普通人對成功向往的方向努力。這也是我一度想不通的:在他作案后,一度有長達7個月的時間都沒被發(fā)現(xiàn)(要不是他主動透露,極有可能更久),其實滿可以逃出國去。現(xiàn)在來看,可能他當時也沒打算換個身份重新過自己生活,而是壓抑得太久,迫不及待想爽一把,過一天是一天。
當然,或許還有一種可能性,在他看來性癮的問題無法克服,那他就不可能真正去過“正常”的生活,但他忽略了,如果他真的變成了人上人,金錢和權力可以讓他的性癮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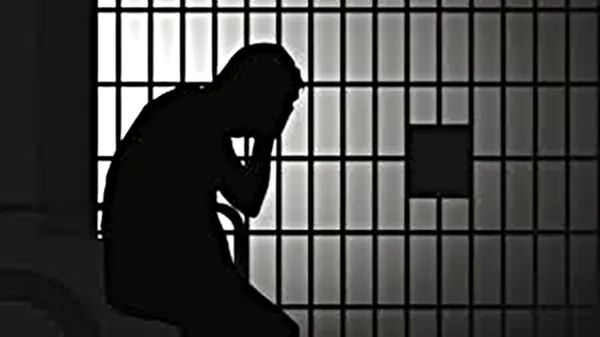
當他選擇了活在黑暗里的時候,他又漸漸開始發(fā)現(xiàn)活著挺好,甚至開始和陽光下的女孩子交往,因為他以前其實沒有享受過這樣的人生。他在很短時間內就花完了從親友那里騙來的100多萬,可能他的家庭對錢的事情上管得也太緊了,所以才會有他這樣不計后果的揮霍。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外,除了用假身份證,也沒有爆出他在工作期間有進一步的犯罪或者暴力,事后沒有起訴他在歡場詐騙搶劫之類罪行,即使那么壓抑,也沒像高承勇那樣暴力傷害其他女性。這反倒證明了他的人性。
說這些不是為了替他辯護,只是想盡可能地理解這個悲劇,理解人性的復雜性,避免重演。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在他最終走出那一步之前,好像沒有什么外部力量能介入干預,這才是最棘手的地方。
對每一個中國家庭來說,這都是一個值得記取的深刻教訓:為人父母,我們其實只是陪伴孩子走一程,不論我們是否情愿,他們遲早都得走自己的路。不明白這個道理的,當然也未必都釀成弒母這樣慘烈的后果,反過來想想,其實有多少父母正在不知不覺中吞噬、殺死自己的孩子?
原標題:《令人窒息的愛》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