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神探夏洛克》特煩惱:粉絲與“官方”的相愛相殺
2016年伊始,有一股颶風從“老霧都”倫敦刮到了“新霧都”北京,在現實空間和賽博空間都掀起了巨大的波瀾,這股颶風的名字叫做——《神探夏洛克》(Sherlock)。事實上,這已經是這部由英國廣播公司(BBC)出品的電視電影,第四次掀起席卷全球的流行風潮:2010年、2012年、2014年,BBC先后推出三季《神探夏洛克》的電視連續劇,均在世界范圍引發了收視狂潮和網絡熱議,堪稱近年來最受追捧的英劇;今年元旦,《神探夏洛克》的新年特別篇在BBC播出,吸引了超過800萬觀眾收看首播,收視率高達34.7%,創造了英國電視歷史上年節期間的最高收視率紀錄,該特輯隨后還以“大電影”的形式在世界各地陸續發行,并于1月4日登陸中國院線,造就了網絡在線觀看和影院購票觀看并行不悖的奇特景觀。
《神探夏洛克》不僅每回推出新劇集時都能收到風靡全球的效果,而且在過去五年的時間里始終保持超高的人氣熱度。這部系列劇集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功,當然有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在于,它與粉絲文化之間形成了一種相當有趣的交互關系——如果借用《神探夏洛克》的許多粉絲喜歡使用的一個修辭,或許可以將這種交互關系稱作“粉絲與官方的相愛相殺”。所謂“官方”,在當代流行文化的語境中,常被用來作為“粉絲”的二元對立項,指稱某個文化產品的原作方、出品方。然而,在《神探夏洛克》這里,“官方”與“粉絲”之間的關系,不僅只是原作方與接受者、出品方與消費者,而是更加難解難分、糾纏曖昧。

《神探夏洛克》=官方名著改編+粉絲同人創作
可以說,官方的名著改編與粉絲的同人創作,共同構成了《神探夏洛克》的一體兩面。
一方面,《神探夏洛克》是BBC對阿瑟·柯南·道爾的系列小說《福爾摩斯探案集》(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所做的名著改編。這套最初連載于1887年至1927年的系列小說歷經百年而長銷不衰,積累了一代又一代的“原著粉”,攜帶著豐厚的認同經濟學價值;與此同時,這套包含4部長篇與56個短篇的偵探小說內容豐富而情節多樣,蘊含有可供不同時代的人們放置其社會經驗和生活經驗的潛在空間,因而成為英美電影電視工業改編翻新的慣常之選。而且,作為一家接受英國政府財政資助的國有公營型廣播電視公司,BBC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在對英國文學名著進行周而復始的改編重拍,這既是電視工業針對穩定市場需求的商業行為,又是高度自覺的“國家形象工程”和“文化軟實力塑造”,而《福爾摩斯探案集》就是其中的一部名著。
另一方面,《神探夏洛克》又可以被視作一種粉絲同人創作。所謂“同人”,在當代流行文化的語境中,指的是粉絲隨性挪用源文本的世界觀、角色設定、人物關系、故事情節,由此進行的二次創作——在英語世界,這種二次創作通常被稱作“FanFic & FanArt”。正如《神探夏洛克》的制片人、編劇史蒂文·莫法特在新年特別篇的片頭花絮中所言,他和另一位聯合制片人、編劇馬克·加蒂斯,以及主創團隊的多位核心成員,都是《福爾摩斯探案集》的忠實粉絲,而在某種意義上,《神探夏洛克》正是這些粉絲集體創作的同人作品。

套用粉絲同人文化自行形成的術語,《神探夏洛克》可以被視為《福爾摩斯探案集》的一份“AU同人”——也就是“平行世界(Alternative Universe)同人”。它固然沿用了源文本的一些基本設定:倫敦貝克街221B的住址,福爾摩斯的私家偵探身份及其與蘇格蘭場(倫敦警察廳)的微妙關系,福爾摩斯與華生的合租和搭檔關系,福爾摩斯與莫里亞蒂的夙敵關系,等等。然而,它又重新設置了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將福爾摩斯的探案故事從維多利亞時代的“霧都”搬到了21世紀的后現代都市來上演,于是,各方面的角色特征與故事要素都隨之發生了整體性的改變。
隨著文化語境的變換,人物之間的相處方式與情感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例如,兩位男主角就由互相尊稱姓氏(family name)——“福爾摩斯先生”(Mr. Holmes)與“華生先生”(Mr. Watson)——的老派紳士,變為了隨意稱呼名字(first name)——“夏洛克”(Sherlock)與“約翰”(John)——的新潮基友。系列劇的總標題取名為“夏洛克”而非“福爾摩斯”,事實上正呼應了這種變化,標識著這部劇的新時代特征,提示出這是一部為男主角賦予新時代情感元素的粉絲向同人創作。
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動,恐怖主義與反恐行動成為了結構故事的重要背景。華生這位在阿富汗戰場負傷的退伍軍醫,因此由殖民戰爭(1878至1880年的第二次英阿戰爭)的參戰者,變為了反恐戰爭(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從2001年起針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發動的戰爭)的參戰者,第一季第一集的第一個敘事段落,就是關于華生采納心理醫生的建議,試圖以更新日志的方式來治療反恐戰爭留下的精神創傷。而莫里亞蒂則由一位暗中主導倫敦各種犯罪事件的數學教授,變為了一位熱衷于在英國都市制造恐怖爆炸案、并且與國際恐怖組織存在千絲萬縷關聯的恐怖分子。
隨著媒介技術的變革,華生發布福爾摩斯探案事跡的平臺,由紙媒《海濱雜志》變為了網絡自媒體——他的個人博客;而約翰所記錄的夏洛克,也變成了一位擅長使用互聯網信息搜索與GPS智能定位來協助偵查的技術達人或者說“極客英雄”(geek hero);智能手機、可移動數據存儲器以及其中的數據信息,則成為了夏洛克與對手斗智斗勇、奮力爭奪的對象。與時俱進的科技手段搭配著數字化升級的視聽語言,在喚起當代觀眾親切而熟悉的世俗經驗的同時,激蕩出妙趣橫生的藝術效果。

隨著社會狀況的變遷,女性扮演了比過去重要得多的角色。新年特別篇特地借女房東哈德森太太之口,對柯南·道爾的以華生為第一人稱敘事者的原著進行了一番饒有趣味的吐槽,在發表于《海濱雜志》的故事中,哈德森太太沒有任何臺詞,仿佛一個純粹功能性的NPC;而在《神探夏洛克》里,哈德森太太則充滿存在感,搖身變成一位有血有肉的重要角色。這條女性地位獲得提升的歷史脈絡,在新年特別篇中成為一條重要的線索,在跨越百年的時空變幻間,華生的妻子瑪麗從一位受到忽視與壓制的家庭主婦,經由爭取權利的女權主義運動,變成一位能夠輕易“黑”進英國軍事情報局數據庫的超級特工;而《神探夏洛克》的自創角色茉莉·琥珀,也從一位遭受嚴重就業歧視因而不得不女扮男裝的醫生,變成一位能夠為夏洛克提供關鍵幫助的職場女性。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神探夏洛克》的主創作為《福爾摩斯探案集》的粉絲,在“忠實原著”與“同人創作”之間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張力,令“原著粉”既感到親切熟悉又覺得耳目一新,同時還為新時代的愛好者設置了諸多“萌點”,從而獲得了風靡全球的獨特魅力。
《神探夏洛克》對粉絲文化的吸收內化
更進一步說,莫法特、加蒂斯等主創人員作為“骨灰級的原著粉”,深深地內在于“福爾摩斯粉絲圈”,他們深諳圍繞著《福爾摩斯探案集》而形成的粉絲文化,并在其劇作中對這種粉絲文化進行了精妙的吸收內化。
這種吸收內化最為突出的表現,當屬夏洛克與華生、莫里亞蒂、邁克羅夫特等重要男性角色之間基情滿滿的“Brom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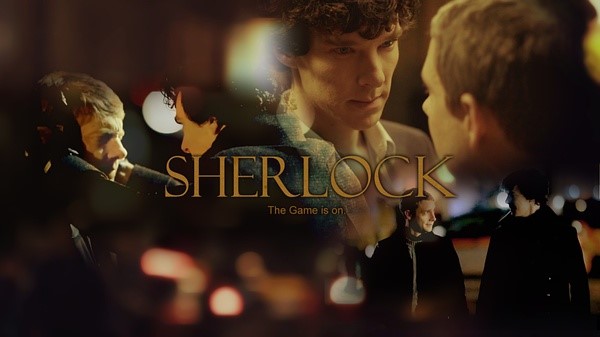
雖然《福爾摩斯探案集》的故事主線是偵探推理,福爾摩斯在原著中也并未與他的搭檔、對手或兄長發展出明顯的親密關系;但在“福爾摩斯粉絲圈”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很多粉絲——尤其是女性粉絲——在進行同人創作的時候,都會極力挖掘福爾摩斯與他身邊的人物角色之間的情感潛能,并且在同人文所創造的一個又一個平行世界中,為這些男性角色設想出各式各樣的情感糾葛與親密關系。粉絲們樂此不疲的同人創作歷經數十年的積累與發展,在新媒體時代借助互聯網的傳播效應徹底爆發,各個圈子的類似寫作匯聚成一場蔚為壯觀的“Slash”文化潮流。

《神探夏洛克》高度內化了這種“Slash”文化,通過主角之間的曖昧互動、多位配角的暗示烘托,以及“故意賣腐”的攝影和剪輯,恰到好處地渲染了夏洛克與約翰之間非同尋常的男性情誼;《神探夏洛克》還將莫里亞蒂塑造為昭然若揭的男同性戀者(這一身份在新年特別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夏洛克與他的這位夙敵之間制造了“相愛相殺”的情欲張力;《神探夏洛克》還對福爾摩斯兄弟的情感糾葛進行了深入的刻畫,打造出一對既“虐心”又“有愛”的“兄弟CP”。此外,在夏洛克與女性角色之間,《神探夏洛克》也延伸出好幾條情感脈絡,不僅是將原著中的歌劇演員艾琳·阿德勒改寫為一位氣場強大的SM女王,在她與夏洛克之間發展出一段惺惺相惜而又“相愛相殺”的情感經歷,而且還為原著中并不存在的自創角色茉莉演繹出一份令人唏噓的單戀情感。在此基礎上,《神探夏洛克》建立了夏洛克-瑪麗-約翰、夏洛克-艾琳-約翰、夏洛克-莫里亞蒂-約翰等多組三角關系,從而將耽美/言情的線索與推理破案的線索交織纏繞在一起,將夏洛克不僅打造為一位特立獨行的偵探片英雄,而且塑造為一位聰明而性感——正如艾琳所言:“Smart is the new sexy!”——的愛情劇“男神”。這樣的敘事方式與人物塑造,令《神探夏洛克》對“推理迷”群體與“腐女”群體同時構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作為《福爾摩斯探案集》的超級粉絲,《神探夏洛克》的主創不僅擅長“賣腐”,而且還特別精通“玩梗”。所謂“玩梗”,指的是對于流行文化典故的創造性運用,《神探夏洛克》就對《福爾摩斯探案集》的各種“梗”進行了富有創意的化用。例如,大偵探福爾摩斯的經典形象是手拿煙斗抽煙,但由于英國政府在近年來推行的禁煙法令,新時代的神探夏洛克不得不被迫戒煙,只能借助尼古丁帖來緩解煙癮。在這里,《神探夏洛克》不僅使用尼古丁帖來對“原著梗”進行致敬,令“原著粉”產生一種既相似又不同、既親切又陌生的新奇感;而且,《神探夏洛克》作為一份“AU同人”,還把夏洛克的戒煙與吸煙成功地化作表現人物情感的強有力手段,在第二季第一集中,用夏洛克絕無僅有的一次獲得濃墨重彩描繪的吸煙行為,來表現夏洛克因艾琳之死而遭到的巨大心理打擊。

作為資深的粉絲,《神探夏洛克》的主創還在劇作中引入了很多“福學”的研究成果。正如《紅樓夢》在中國形成了一門源遠流長的“紅學”,《福爾摩斯探案集》也在英美世界形成了一門規模龐大的“福學”,粉絲們作為“過度的消費者”,對原著的主線、支線情節和各種各樣的細節進行了過度的解讀與闡釋,他們或是以天馬行空的同人想象,或是通過嚴謹細致的“福學”研究,費盡心思地對原著的諸多空白加以填補。例如,約翰·華生在原著中只展現了first name和family name,卻缺失了middle name,讀者所能了解到的唯有其首字母“H”,那么,華生的中間名究竟是什么?——這個原著遺留的空白,就成為“福學”研究者為之爭論不休的一個熱門話題。在數不勝數的“研究成果”中,一個獲得較廣泛認可的是“H”指代“Hamish”,《神探夏洛克》就采納了這種說法。在第二季第一集中,當華生試圖打斷夏洛克與艾琳用智力進行的調情時,他就略顯笨拙地插科打諢道:“我的中間名是哈密什,如果你們想給孩子取名字的話……”而在第三季第二集中,“哈密什”這個“福爾摩斯粉絲圈”集體智慧的結晶,更是化作劇情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了夏洛克推理破案的關鍵線索。
從多個方面來看,《神探夏洛克》都可以說是吸收內化了“福爾摩斯粉絲圈”的粉絲文化,只不過,與一般的非商業性質的粉絲同人作品不同,這同時又是一部“官方出品”的文化產品。在這個意義上,《神探夏洛克》本身又成為了一部新的源文本,由此衍生出一個新的粉絲圈——“神夏粉絲圈”。而《神探夏洛克》的主創一直都在密切地關注這個新興粉絲圈,并且自覺地在其劇作當中與這個圈子的粉絲文化展開有趣的互動。例如,《神探夏洛克》的第二季以夏洛克的跳樓自殺作結,在第二季播放完畢與第三季終于問世之間的兩年時間里,無數“神夏粉”撰寫了大量的分析文章與同人小說,沿著不同的路徑對源文本埋設的伏筆進行詳盡的細讀,對夏洛克如何死里逃生這個問題展開無盡的猜想。這些猜想幾乎窮盡了一切的可能性,使得編劇幾乎不可能再給出一個全新的創意。面對粉絲同人文化所構成的挑戰,《神探夏洛克》的主創并沒有回以某種唯一正確的權威正解,而是選擇在第三季第一集里,將三種早已存在于“神夏粉絲圈”的解釋版本,分別作為宅男粉絲的中二向猜想、腐女粉絲的耽美向猜想、推理愛好者的嚴謹向猜想的代表,內化為劇作的有機組成部分。但這些解釋只是諸多可能性中的三種,《神探夏洛克》將“黑轉粉”的安德森作為狂熱粉絲的代言人,借他之口對夏洛克親自提供的疑似“官方”版本發出質詢和吐槽,通過這種自我反諷的方式保持了劇作的開放性,及其與粉絲文化的對話關系。

在《神探夏洛克》這里,“官方”與“粉絲”猶如一對“相愛相殺”的CP:他們既是命中注定的對手,又是形影相隨的伴侶。而在官方文化與粉絲文化的互滲互動上,《神探夏洛克》固然格外突出,但卻絕不會是孤例。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